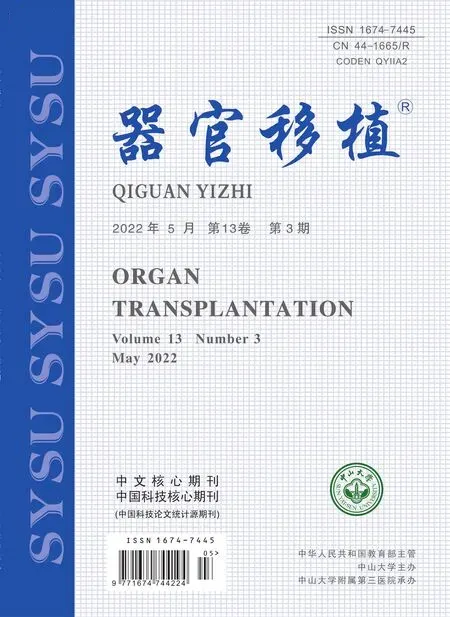儿童肝移植的手术技术革新
高伟
我国的儿童肝移植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较于欧美国家起步较晚,但在近年尤其近十年来发展迅速,逐渐缩小了与国外先进儿童肝移植中心之间的差距。与成人肝移植受者相比,儿童受者体质量小、脉管口径细,对外科技术要求更高。而我国儿童肝移植的特点,如受者年龄大部分在1岁以内、供者来源以活体为主等,是我国儿童肝移植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瞩目成绩的主要推动力。儿童肝移植手术技术的发展主要以“移植物”为中心展开,如劈离式肝移植(split liver transplantation,SLT)、多米诺肝移植、辅助性肝移植等,而以腹腔镜、达芬奇手术系统为代表的微创外科技术在活体肝移植供肝切取中的开展,是近年儿童肝移植技术的新亮点。
1 劈离式肝移植
作为一种扩大供者来源的有效方式,1988年德国的Pichlmayr教授首先开展了SLT[1]。但在SLT开展的早期,由于经验较少、手术技术不成熟等原因,效果欠佳。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目前SLT已成为临床上的常规术式之一。儿童受者大多体质量偏小,小体积移植物与儿童受者匹配度更高,SLT对成人肝移植受者的等待时间影响有限,但极大缩短了儿童肝移植受者的等待时间。在英国的伯明翰,65%的儿童肝移植受者接受的是SLT[2]。
美国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OPTN) 与 移 植 受者科学登记系统(Scientific Registry of Transplant Recipients,SRTR)2019年年报指出,20.3%的儿童肝移植为SLT,而10年前为14.4%,劈离肝脏的使用率从2007年至2009年的15.5%增加到2017年至2019年的19.3%[3]。在Perito等[4]的研究中,共纳入了37333例尸体供肝,6.3%符合劈离的标准,但最终仅有3.8%用于SLT,在每个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的区域内潜在的可劈离的肝脏数量都多于在等待中死亡的儿童的数量,因此其认为在不减少成人受者移植机会的前提下,更多地开展SLT可降低等待移植的儿童的病死率。
对于可劈离供肝的评估,各国并无统一标准,主要包括年龄、体质量、生化指标、感染情况及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等。来自欧洲肝移植注册系统的研究认为在SLT中供者年龄>50岁和<10岁是移植物失功的关键危险因素[5]。自2018年开始,笔者所在单位开展了儿童供肝的SLT[6],16例儿童肝移植受者分别接受了来自8例儿童脑死亡器官捐献(do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供者劈离后的肝脏,供者年龄均<7岁,在随访(8.0±2.3)个月后,移植物与受者的存活率均为100%。儿童供肝SLT的成功开展,将极大丰富可劈离肝脏的来源。
SLT包括原位劈离和离体劈离两种手术方式。原位劈离式供肝获取可参考活体肝移植供肝获取,而离体供肝劈离则对技术的要求较高。由于供肝获取前往往缺乏腹部影像学检查,劈离开始前需对肝脏的解剖结构进行详细评估,主要是发现血管及胆管的解剖变异。对于胆管系统,应避免对胆管周围组织进行过多解剖,尽可能减少对肝门板胆管分叉处与肝动脉之间的解剖游离,以保护胆管周围的滋养血管。上述两种手术方式于笔者所在单位均常规开展,早期的经验总结发现,离体劈离组中移植物累积存活率低于原位劈离组、需再次肝移植的比例显著高于原位劈离组,但血管并发症、胆道并发症等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7]。毫无疑问,离体劈离会导致移植物的冷缺血时间延长,对于经验较少的移植中心,笔者不建议选择离体劈离的方式。
在我国,儿童SLT的比例偏低,建议对可劈离的肝脏制定相应的分配体系。在不影响成人受者手术机会的情况下,最大化利用SLT的供肝资源,增加可劈离肝脏的实际使用率。
2 辅助性肝移植与多米诺肝移植
辅助性肝移植是通过提供部分移植肝来确保肝功能,直到自体肝脏出现再生、功能恢复后,再撤除免疫抑制剂,主要应用于急性肝衰竭或代谢性疾病的儿童[8]。最常见的是辅助性部分原位肝移植(auxiliary partial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APOLT), 术中切除受者部分肝脏(一般为左外叶)后移植相应大小的供肝,移植物可来自于尸体或活体供者;若采取异位移植,则不必行自体肝脏部分切除。首例成功的APOLT于1991年完成,受者为暴发性肝衰竭的患者[9],此后APOLT在世界各地陆续开展。在Quadros等[10]的总结中,纳入的45例APOLT受者在6个月至14年的随访期内,22%(10例)的受者死亡,13%(6例)的受者行再次移植,值得欣慰的是35例存活受者中69%(24例)可完全撤除免疫抑制剂。APOLT手术较复杂,手术相关并发症高,尤其是血管并发症。APOLT可作为治疗急性肝衰竭或代谢性疾病的有益补充,但不建议将其作为常规手术方式。
手术技术方面,行APOLT时需考虑以下因素:移植物体积、自体残肝体积、受者体质量。对于儿童受者,首选左叶或左外叶作为移植物,其与儿童的腹腔容积更易匹配。由于移植物所在空间狭小、血管断端较短,术中吻合难度大,须重视血管吻合的方向,避免扭转,警惕流出道梗阻的发生。术中处理的关键在于自体残肝与移植肝的门静脉血流分配,术中需分别测量自体残肝与移植物的门静脉压力、血流量,参照两部分肝脏体积及病肝切除前的门静脉压力与血流量,调节移植物门静脉血流至适宜水平。术后继续以超声密切监测移植肝血流情况。
多米诺肝移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活体供肝,多米诺供者接受传统的肝移植,以纠正其自身的代谢紊乱,将切除的患有代谢性疾病但解剖学正常的肝脏移植给其他终末期肝病的患者[11]。多米诺肝移植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供肝来源,但对术前评估、供受者匹配度、手术技术等要求较高,总体开展数量较少。首例多米诺肝移植于1997年由Furtado等[12]报道,将家族性淀粉样蛋白多神经病患者的肝脏移植给1例肝恶性肿瘤的患者。截止到2019年底,多米诺肝移植注册中心报道了来自21个国家67个中心的1288例多米诺肝移植[13]。多米诺肝移植的特点是供者年轻、冷缺血时间短、术中输血少、缺血-再灌注损伤轻、手术难度大,其治疗效果较好。美国匹兹堡儿童医院报道的一组数据显示,该组接受多米诺肝移植的受者的移植物与受者存活率均为100%,需要干预的并发症包括胆道梗阻、腹腔积液、小肝综合征等[14]。
多米诺肝移植手术需要很高的团队配合度,整个过程至少需要3个独立的外科团队,包括供肝获取、多米诺供肝切取及肝移植、多米诺受者肝移植。多米诺肝移植手术的关键点在于移植肝血管系统的解剖,主要是肝静脉、肝动脉和门静脉的长度,必须保证同期开始的多米诺供者与受者的血管残端长度足够,同时尽量保证多米诺供肝的血管长度,尤其是肝静脉[15]。根据受者腹腔容积、供肝体积等因素,在移植肝与受者的血管需求间取得平衡,是移植科医师面临的严峻考验。有条件的移植中心,在多米诺肝移植术前可保存异体血管,以备术中行血管修整。
在此方面,笔者所在单位也做了一些有益尝试,以活体肝移植联合多米诺APOLT治疗儿童代谢性肝病[16]。3例患有代谢性肝病的儿童接受了活体肝移植,其肝脏作为多米诺辅助供肝移植给另外3例患有不同代谢性疾病的儿童行APOLT。APOLT的肝脏与原肝脏相互弥补自身缺失的代谢酶,发挥相应的代谢功能。6例肝移植受者在平均随访26.6个月后,各项指标良好。
3 移植肝与受者匹配度及超减体积肝移植
大部分儿童肝移植受者手术时年龄较小、体质量偏低,这一点在我国尤其明显。其对移植物大小的要求较高,与成人肝移植不同,儿童受者需警惕“大肝综合征”所带来的风险。移植物过大可导致门静脉血流量不足,若同时伴有受者腹腔较小,则加重外部压迫,导致腹壁闭合延迟,增加血管并发症、移植物失功的发生风险。
儿童肝移植中最常用的反映移植物与受者匹配程度的指标为移植物与受者质量比(graft to recipient weight ratio,GRWR),与成人不同,儿童肝移植的GRWR尚无统一标准。对于婴幼儿受者,即使是使用部分移植肝,匹配到大小合适的移植物亦非常困难。有学者认为GRWR不应超过4%[17]。笔者所在单位的经验表明,肝脏是否需要减体积不应单纯以GRWR为标准,应综合考虑移植肝与患儿腹腔的匹配程度及肝脏血流情况[18]。GRWR本身包括了移植物与受者两方面,依据个体情况(如受者体质量、腹腔容积、门静脉压力与流量等),动态把握GRWR而不是拘泥于数字,有助于制定最佳的手术方案[19-20]。判断是否需要减体积,还可利用影像学资料计算移植物厚度与受者前腹壁内壁至脊柱距离的比值,若比值<1.0,则无需减体积,若比值>1.0,则需行减体积肝移植、甚或行Ⅱ段移植[21]。此外,借助近年快速发展的数字成像技术,利用3D打印技术制作供肝、受者肝门解剖与受者腹腔模型,有针对性地规划手术步骤,并可反复推演,有助于应对“大肝综合征”[22]。
减小左外叶移植物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非解剖性减体积与单肝段移植,后者也可看作是超减体积的延伸。这些技术最早多出现在以活体肝移植为主的日本与韩国,大大提高了移植物的实际使用率。相比而言,原位非解剖性超减体积在技术上比解剖性单肝段移植更简单、更直观,是改善婴儿受者肝移植效果的一种有效选择,但非解剖性减体积对减少移植物的厚度无效[23]。从解剖学上讲,单肝段移植物可有效减少移植物的厚度,更适合腹腔容积小的受者,但对外科技术要求更高,且容易损伤包括门静脉在内的Glisson鞘。
在两项对移植时受者年龄<3个月的活体肝移植的研究中,移植物在行减体积后,受者与移植物均获得较好的长期生存,同时研究者也指出婴儿行肝移植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大小匹配的供肝,克服较大移植物的选择就是对左外叶行减体积,但在减体积时必须考虑移植物的厚度、长度、体积、形态及其与腹腔容积之间的关系[24-25]。左外叶移植物在行减厚处理后,受者出现腹部伤口延迟闭合的几率较小、重症监护室入住时间缩短、术后并发症少、移植物存活率高[17]。
单肝段移植更适合婴儿或腹腔空间狭小的新生儿。临床工作中,以S2单段作为移植物更为常见,其优势是移植外科医师能够减少约一半的移植物体积并使移植物形状变薄,将其植入腹腔时更稳定;以S3单段作为移植物的优势是从技术角度来讲更简单、安全,因为使用S2段需要在脐裂处做广泛解剖,才能暴露供应S2段和S3段的门静脉与肝动脉,增加了损伤血管的风险。
4 微创外科技术在儿童肝移植中的应用
在儿童肝移植中,微创外科技术主要体现在活体肝移植的供肝切取上,包括全腹腔镜切取与达芬奇手术系统切取。
首例小儿单纯腹腔镜供肝切取术由Cherqui等[26]于2002年首次报道。Gautier等[27]将全腹腔镜与开腹肝左外叶切取术进行比较,两组在失血量 [(96.8±16.5) mL 比(155.8±17.8) mL)]和住院时间[(4.0±0.4)d比(6.9±0.5)d]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1)。在另一项包括100例儿童活体肝移植的分析中,与开放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不会增加供者手术时间,但术后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缩短[28]。微创外科技术使得供者腹部伤口的美容效果好,操作可视化,在术中出血、术后疼痛感、住院时间、恢复正常生活的时间等方面优于开腹手术[29]。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微创外科技术将成为活体肝移植供肝切取的重要发展方向。
对于腹腔镜供肝切取术的质疑主要来自于对其安全性的评估,这一点极其重要。此处需指出的是,对于技术成熟的儿童肝移植中心而言,在完成正常的学习曲线后,全腹腔镜肝左外叶切取术完全是一种安全、便利的手术方法[30-31],但术前必须对供者进行详细、全面的评估。
正是由于腹腔镜微创手术存在的上述限制,在肝移植术中引入达芬奇手术系统将微创外科带入了一个新兴领域。达芬奇手术系统克服了传统腔镜技术的诸多缺点,使移植外科医师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扩展。一项研究表明,借助达芬奇手术系统行肝脏切除术至少与开放手术和腹腔镜手术相当[32]。与传统腹腔镜手术相比,达芬奇手术系统的主要优点包括:(1)3D视图,可完全恢复手眼协调,且保持手术视野稳定的前提下可将手术视野放大10~15倍;(2)提供类似于人类手腕的远端关节,运动的自由度极高,克服了传统腹腔镜手术的支点效应与盲区;(3)通过运动缩放消除人体生理震颤[33]。
自2021年8月,笔者所在单位已累计应用达芬奇手术系统行左外叶供肝切取术近20例,供受者均顺利康复。与开腹手术相比,达芬奇手术系统的手术时间、供肝温缺血时间有所延长,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考虑与新技术的学习曲线相关。就目前的整体发展而言,达芬奇手术系统的成本效益、较长的操作时间以及移植物温缺血时间,是限制其在肝移植领域广泛开展的主要原因。
5 显微外科吻合技术在儿童肝移植中的应用
在儿童肝移植中,相比于流出道与门静脉,肝动脉更为纤细,且供、受者肝动脉口径不匹配的情况较为常见,显微外科吻合技术主要用于肝动脉重建与胆道重建。在儿童尸体供肝肝移植中,供肝的肝动脉较长,且大多留有动脉袢,可采取与成人肝移植肝动脉吻合相似的方法进行吻合。而在儿童活体肝移植中,供肝肝动脉往往较短,绝大多数不存在动脉袢,需要行对端吻合,尤其存在动脉口径<2 mm的或多支动脉重建等高危因素时[34-35],动脉吻合难度较高。《中国儿童肝移植操作规范(2019 版)》推荐使用显微外科技术进行术中肝动脉重建,以降低肝动脉血栓形成的风险[7]。
显微外科技术最早于1992年应用于活体肝移植中的肝动脉重建,此后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普及。在引入显微外科技术前,动脉并发症的发生率在15%~25%,在儿童尸体供肝肝移植中则更高,在使用显微外科技术后这一并发症降至4%以下[36]。在一项包括73例儿童肝移植受者的研究中,术中使用显微镜吻合肝动脉,术后肝动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为3%[37]。同样应用显微外科技术,在另一项包括30例成人与8例儿童肝移植受者的研究中,肝移植术后动脉血栓的发生率为0[38]。
笔者所在单位于2013年开始,在儿童活体肝移植、SLT以及部分全肝肝移植中以台式显微镜代替手术放大镜行肝动脉重建,放大倍数通常为5~7倍,根据血管口径选择8-0至10-0不可吸收单丝缝线间断缝合。结合自身经验,笔者认为在使用台式显微镜行肝动脉重建过程中,应注意以下细节:(1)保持术者姿势、供受者动脉方向、术野稳定;(2)手术缝线、显微外科器械不宜过长,以免影响操作;(3)动脉末端应修剪成光滑的界面,以肝素化盐水冲洗,清除可能存在的血块和外膜组织,必要时修整成斜面或轻轻扩张,以使供受者血管口径更匹配;(4)缝合过程中,必须做到外翻缝合。
诚然,在使用台式显微镜亦或手术放大镜的问题上尚存争议。有研究表明,二者在术后肝动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9]。有研究认为使用高倍率放大镜进行肝动脉吻合,操作简单、视野大、手术时间短、成本和设备的需求低[40]。而通过调整手术吻合技术,在不使用手术显微镜的情况下,活体肝移植术后肝动脉血栓形成的发生率可由2.00%下降到0.86%[41]。在二者中,笔者更倾向于在儿童肝移植术中使用手术显微镜进行肝动脉重建。其优势包括:(1)使外科医师能够充分评估供肝和受者的血管条件,消除动脉血栓形成的潜在因素,尤其是损伤的内膜边缘、内膜和中层分离,动脉残端管腔内小血栓等;(2)术野更稳定;(3)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缝合确切,尤其是血管的口径<2 mm时,其优势明显。
显微外科技术在胆管吻合中的应用有限,主要在活体肝移植中,在面对胆管口径细小、解剖变异、多支胆管吻合、供受者胆管口径不匹配等情况时,预后较好[42]。显微外科技术吻合胆管最突出的优点是增加了缝合的准确性。在使用显微外科技术吻合胆管的早期,其优势并不明显。一项来自韩国的研究在肝移植术后平均随访5个月,未出现胆漏或与胆道重建相关的胆管狭窄,研究者认为显微外科技术可减少肝移植术后早期的胆道并发症,但还需要技术改进,缩短操作时间[43]。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该团队自2006年以来常规应用显微外科技术行肝移植术后胆道重建,有效降低了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发生率。在活体肝移植中,使用显微外科技术后胆管吻合口狭窄的发生率为6.79%,其中只有2.5%需要介入治疗[44]。
6 小结与展望
我国儿童肝移植已突破早期发展的技术瓶颈,进入平稳发展的快车道。在不断完善、健全器官分配体系、评估体系的基础上,儿童肝移植手术技术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SLT技术、胆道吻合技术、低体质量和低月龄儿童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的使用、快速康复外科理念的普及等方面。在缓解受者数量与供肝短缺的矛盾、扩大供肝来源的基础上,减少儿童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手术相关并发症,提高移植物远期生存率与受者生存质量,是儿童器官移植科医师继续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