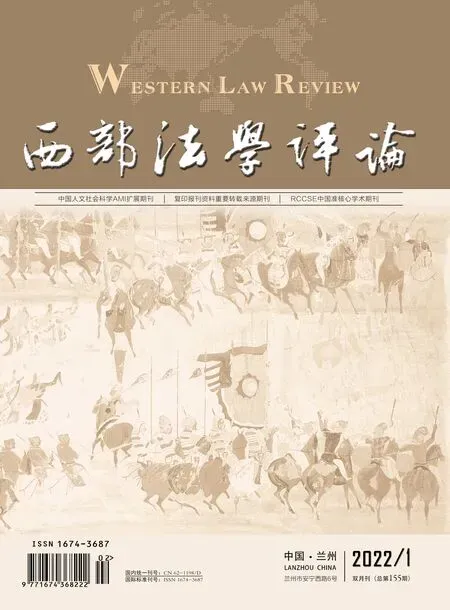认真对待视听作品之创作
兰 昊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理解视听作品之创作是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修改后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随着直播经济和短视频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非影视剧节目价值不断凸显,在成为人们精神消费主流的同时,也成为了著作权纠纷的常客。视听作品的前身“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就曾在体育赛事直播(1)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再审)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7号民事判决书。、短视频(2)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诉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音乐电视MTV(3)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珠海至尊KTV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东高级人民法院(2011)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70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上面临挑战。虽然独创性的不同标准对于认定是否构成作品有所影响(4)我国法院在独创性标准出现了“独创性有无”和“独创性高低”两种标准,比如“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民事判决书。,但是除此之外,对视听作品之创作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也是造成不同判断结果的原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只是解释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一种伴音或者不伴音的画面,而没有说明这类作品的创作要求与创作特点,或者说,没有说明在什么方面作出独创性表达可以构成这类作品的创作。另外,虽然“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提到了创作,但并没有对创作进行说明。(5)“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其实与《伯尔尼公约》所使用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同义。因此除了表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产生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之外,没有任何进一步实质含义。参见万勇:《功能主义解释论视野下的“电影作品”——兼评凤凰网案二审判决》,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5期。这就使得在分析直播、短视频这种连续图像组合是否满足作品要求时出现了不同思路。
一种思路是,著作权法意义上视听作品的创作可通过画面的选取、表征、排序、组合实现,因而在画面形成上作出独创性表达就可以让整个连续图像组合构成视听作品。体育赛事直播的作品认定过程是这一思路的主要体现(6)比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般而言,对于由多个机位拍摄的体育赛事节目,如制作者在机位的设置、镜头切换、画面选择、剪辑等方面能够反映制作者独特的构思,体现制作者的个性选择和安排,具有智力创造性,可认定其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独创性要求,在同时符合其他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即可认定为电影类作品。但对于仅通过简单的机位设置、机械录制的体育赛事节目,由于在镜头切换、画面选择等方面未体现制作者的个性选择和安排,则不宜认定为电影类作品。参见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再审)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8号民事判决书。,由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中的直播内容是体育赛事,不属于文学艺术科学范畴,但是基于特定的拍摄制作手法,一些看法认为:从选择、拍摄、编排三个方面看,体育赛事节目均体现了较高的独创性。(7)参见来小鹏、贺文奕:《论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所以,体育赛事节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8)参见戎朝:《互联网时代下的体育赛事转播保护——兼评“新浪诉凤凰网中超联赛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载《电子知识产权》2015年第9期。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思路是,视听作品的创作可通过连续图像组合的内容设置实现,比如有独创性的故事情节或独白解说,即使画面的录制比较固定和机械,也有机会构成视听作品,这一思路主要体现在游戏直播的认定过程中。比如有观点认为,游戏直播画面中如果是专业性的在游戏运行画面基础上形成的解说,与游戏运行画面结合后形成的游戏直播画面,是一种演绎作品。(9)参见焦和平:《类型化视角下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著作权归属》,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5期。解说如何与游戏画面组合存在很大的选择空间,玩家为了突出展示游戏技巧,会在二者的组合上下功夫,从而体现出较强的独创性。(10)参见许辉猛:《玩家游戏直播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及保护途径》,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还有一种思路是,视听作品的创作要通过一个整体过程实现,需要按照一定的模式才可能满足要求,因而仅在画面或者内容上进行独创性表达并不足以让整个连续图像组合构成视听作品。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凝聚了剧本编写、演员表演、导演执导以及摄像、配音、配乐、剪辑等大量前期创作和后期处理的综合性智力成果。(11)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酷溜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23448号民事判决书。因此仅是一方面的独创性表达,比如主持人的对白,可能会单独构成作品,但这些独创性内容不可能使得整部节目变成一部“影视作品”。(12)参见王迁:《论“春晚”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知识产权》2010年第4期。其他的一些判决中,法院虽然没有直接对电影作品的创作进行阐述,但是从侧面分析了什么样的过程能够视为电影作品的创作,进而反映出视听作品的这种整体性的要求。(13)比如重庆法院认为:涉案节目系根据文字脚本、分镜头剧本,通过镜头切换、画面选择拍摄、后期剪辑等过程完成的综艺节目,其连续的画面反映出制片者的构思、表达了某种思想内容,具有独创性,应当认定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式创作的作品。参见重庆伯明翰酒店有限公司诉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渝民终1560号民事判决书。又比如广州法院认为,涉案节目制作方配备了制作团队,选择了拍摄场地,通过摄影、录音、剪辑、合成等创作活动,制作了各具特色的VCR,并可在介质上制成一系列有伴音的相关画面,凝聚了多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参见长江龙新媒体有限公司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知民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书。
上述不同思路的核心争议在于,在什么方面进行独创性表达可以构成一种视听作品的创作,是画面形成上、内容设置上还是一个整体过程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解决一些直播节目的作品属性认定具有现实意义(14)因为直播类节目相比于影视类节目。很可能由于讲求即时性和现场性,直播节目的画面较为固定,一般达不到影视节目那样的画面剪辑、加工、合成的效果程度,也很可能由于直播是对现实发生事情的同步传送,因而一般不具有影视节目水平的故事性或者情节性,这往往容易给直播节目的作品认定带来挑战。。同时,理解视听作品之创作,也是《著作权法》相应规则运行的必要前提,是确定作者、著作权人以及划定保护范围的关键。2020年《著作权法》修改之后,视听作品取代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这样的变化是否会对理解创作产生影响并不明确。因此,基于过去一系列的不同解读以及法律概念的变化,本文希望对于视听作品之创作展开探讨。本文将从现有的一些理解出发,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中电影作品成为作品示例的过程,来把握视听作品之创作的具体表现,以此提炼出理解视听作品之创作的特定思路,然后通过当前我国《著作权法》的运行情况来检验这一理解的合理性。
二、视听作品的特殊性是分析的起点
(一)视听作品的特殊性给创作的理解带来挑战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指出:“创作是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由于作品本身又可视为一种独创性表达形式(表现形式)(15)参见崔国斌:《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因此,创作应当是一个直接产生特定独创性表达的过程。比如产生了具有独创性的字词组合,可以视为创作文字作品;产生了具有独创性的线条色彩,可以视为创作美术作品;进行了一段精彩的有独创性的脱口秀,可以视为创作口述作品,然而,自行固定录制一段具有独创性脱口秀内容的视频,可否视为创作视听作品呢?
如果结合“凤凰赛事转播案”再审判决来认识上面这个情况,不免会陷入困境:一方面,这个固定录制的脱口秀视频内容上具有独创性,而再审法院认为独创性是有无而非高低,因此,只要有体现出独创性便可构成电影类作品,所以,上述视频达到了独创性有无标准下的构成作品要求;但另一方面,再审法院又指出,复制性、机械性或者忠实地录制,所形成的是录像制品而非电影类作品,这相当于间接否定了固定录制下融入独创性口述表达的过程是一种视听作品的创作。(16)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再审)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8号民事判决书。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同一个独创性标准下得出的结论,而不是运用独创性高低标准来排除程度较低的连续图像组合。另外,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创作本身对应的是作品的产生,如果一个智力活动产生的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难以被视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因此,不能认为这里有在进行创作但只是成果不满足独创性要求而不构成作品,或者形成连续图像组合的过程就属于创作尝试。既然如此,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根据再审法院的看法,在固定的镜头下录制了一段有独创性的脱口秀难以构成电影类作品的创作呢?
事实上,这与视听作品的特殊性有关,视听作品这种连续图像或者连续画面组合的表达带有综合性,其可以通过图像画面传递的内容、音频传递的内容、图像画面的拍摄制作、音频的加工制作等方面展现表达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连续图像组合的表达是多重、复杂的,特别是像影视剧这种,往往是视听结合的、从内容到画面深度衔接的连续图像组合。有法院就曾指出:电影作品是一门综合艺术,其本质在于画面、声音的衔接,是通过各种画面、声音的前后衔接表达了某种内容。(17)梁智等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37647号民事判决书。这样的特点使得视听作品和文字作品、美术作品这些单一表达有所不同。在一个方面进行的独创性表达可以构成一种单一表达的作品类型,但是是否可以让一个包含这一方面表达的综合表达构成特定作品则有待辨明。同时,这也是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即视听作品上是否能够一以贯之对创作的基本理解——只要进行了独创性表达就创作了作品?还是说需要根据视听作品的特殊性来调整这一理解?又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区需要澄清?
(二)结合视听作品的特殊性进行分析的相关思路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些解读对视听作品之创作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比如有看法认为:影视作品的独创性最终都表现在活动画面的“镜头”以及画面之间的“衔接”两个维度上,这是在结合影视创作理论的基础上,将影视作品的活动画面从创作和表达角度进行抽象分析和归纳之后的结果。(18)参见严波:《论春晚的影视作品性质——基于著作权法下的作品独创性视角》,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虽然这里强调的是独创性的表现,但是间接反映出的是,这种独创性的表现可以让一个连续图像组合构成影视作品,即在活动画面的“镜头”以及画面之间的“衔接”上进行独创性表达可视为影视作品的创作。按照这一思路,当具备对“镜头”和“衔接”的个性化选择判断时,就可以创作出影视作品,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专业机构制作的晚会直播节目和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同时,如果没有在“镜头”和“衔接”上有所安排,即使其中的内容是独创性表达,也不属于创作影视作品,比如上文提到的固定录制的独创性脱口秀视频。
这一思路借鉴了影视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是过于强调画面的重要性,容易忽视内容的价值。事实上,连续图像组合中呈现的可视化内容是表达者进行思想情感传递的重要部分,另外,即使根据影视理论来理解视听作品,也不意味着要将创作限缩到“镜头”和“衔接”上。电影是通过一个个活动的画面来塑造自己的艺术形象, 从而表达意念、再现和反映生活。(19)参见尚雅莉:《电影蒙太奇功能探究》,载《电影文学》2010年第9期。在发展的早期,电影更多是一种对现实的记录。比如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为了突破这一局限性,法国人梅里爱将电影与戏剧相结合,通过故事情节与演员表演,大幅提升电影的趣味性的同时也增强电影的艺术色彩,因此,梅里爱的影片是电影成为艺术的第一步。(20)参见魏锦蓉:《蒙太奇手法在电影中的艺术表现力》,载《电影文学》2011年第5期。然而,梅里爱在拍摄电影时,基本上将摄像机固定在舞台前对舞台剧进行拍摄,因此整场的戏都是在一个机位拍摄的,镜头的连接十分简单,人们看电影其实和看戏剧差不多。真正让电影成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的标志,是蒙太奇手法的应用。“蒙太奇”一词出自法语,它原本的含义便是剪接,后来这一词语被苏俄的艺术家运用到了电影镜头中,并被当作镜头组合的一个理论。(21)参见曹伟:《电影蒙太奇的美学应用》,载《电影文学》2015年第21期。作为电影艺术的基础,蒙太奇手法是通过相关摄像机进行拍摄并将拍摄的画面进行剪辑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影视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修辞手法,是一种创造美的艺术手段。(22)参见温婷:《论电影蒙太奇的艺术功能》,载《艺海》2011年第9期。至此,电影这门现代艺术的独立价值才最终形成。在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下,电影可以体现出不同的表达内容,这让电影能够比单纯的戏剧营造更多的表象,呈现更多的内涵,传递更多的情感。因此,从电影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电影的创作过程至少可以体现在故事题材和制作手法两个方面,且两者同等重要。
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出了视听作品上的“内容与画面的二分思路”,认为视听作品画面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过程事件的可视化、过程事件的画面拍摄以及后期制作。这些环节的独创性与底层的过程事件本身的独创性在观念上可以相互分离。(23)参见崔国斌:《视听作品画面与内容的二分思路》,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5期。在此思路之下,视听作品的创作可理解为在可视化、画面拍摄以及后期制作上进行独创性表达。相比于前文提到的“镜头、衔接二维分析法”,“内容与画面的二分思路”有所扩大对视听作品之创作的理解,将可视化的过程纳入创作的范畴,比如对一个故事情节的可视化呈现安排。这一思路对于把握视听作品的创作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这一思路也存在一些未尽说明之处。
“内容与画面的二分思路”将视听作品之创作理解为可视化、画面拍摄和后期制作的独创性表达过程,意味着只有参与这三个过程的人才能视为视听作品作者。然而,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是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他们的作者身份意味着他们也是创作视听作品的人。对此,“内容与画面的二分思路”给予了回应,认为这是要求制片者在视听作品中说明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的作者身份,但没有明确他们是否是视听作品的合作作者。(24)参见崔国斌:《视听作品画面与内容的二分思路》,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5期。但是,《著作权法》第十七条并没有指明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是视听作品中不同独立作品的作者,否则该条规定的表述应当是“视听作品中……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品作者”而不是“视听作品中……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另外,该条规定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这五者并列,即认为他们处于同样的法律地位,此时如果认为编剧、作词、作曲是独立作品的作者,那么与之并列的导演、摄影分别属于什么独立作品的作者呢?因此,从该条条文表述来看,视听作品的创作似乎不等同于只在可视化、画面拍摄和后期制作上进行独创性表达,否则将无法匹配作品与作者的创作对应关系。所以,怎样进行独创性表达才属于创作视听作品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对此,我们可结合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历史发展来分析。
三、视听作品之创作是指为呈现效果贡献独创性表达
(一)《伯尔尼公约》中电影因为两方面体现独创性而受到保护
现在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连续图像组合这种表达是因为什么而满足独创性要求成为一种独立的作品类型。对此,我们需要回归到视听作品的前身“电影作品”来分析,虽然到了布鲁塞尔文本电影才被加入到《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一项的作品示例中,但是在1908年的柏林文本中,电影就已经通过特定的形式在《伯尔尼公约》中得到保护。柏林文本14(2)(25)《伯尔尼公约》柏林文本中,14(2)的原文表述是:Cinematographic productions shall be protected as literary or artistic works, if, by the arrangement of the acting form 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cidents represented, the author has given the work a personal and original character.反映出对电影中的独创性认识和戏剧大体相近。而柏林文本14(3)(26)《伯尔尼公约》柏林文本中,14(3)的原文表述是: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the author of the original work, the reproduction by cinematographic of a literary, scientific or artistic work shall be protected as an original work.则反映出,当时的一些代表认为对已有作品的影像拍摄过程会涉及一定的手段和技巧,比如对一个戏剧演出的影像拍摄,而这些手段和技巧足以构成一种创作。因此,电影的摄制过程被视为和翻译一样的再创作,如何将先前作品中的内容“装”进画面涉及很多的选择和判断。(27)See Sam Ricketson, Jane C. Ginsburg,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Beyond,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28.
然而,柏林文本中电影的保护模式,会使得包含自然风光或者生活场景的电影无法获得保护,而获得保护的电影——那些对表演形式和情景衔接有个性安排的电影,其实本来就可以通过戏剧作品获得保护。那么柏林文本的内容其实并没有真正让电影制片者的利益得到进一步的保护,甚至是有点原地踏步。因此,在这些电影制片者的努力下,罗马文本对柏林文本进行了修改,罗马文本14(2)(28)《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中,14(2)的原文表述是:Cinematographic productions are protected as literary or artistic works, when the author has given to the work an original character. If this character is missing, the cinematographic production enjoys protection as a photographic work.修改的意义在于为非戏剧内容的电影打开了著作权保护之门。而罗马文本14(3)(29)《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中,14(3)的原文表述是: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the author of the work reproduced or adapted, a cinematographic work shall be protected as original work.修改的意义在于,电影的拍摄制作过程,无论是否简单复杂,都足以使其构成一种原创作品。罗马文本之后,把电影视为一种作品似乎已没有太多障碍。但是依然有一些国家的代表认为一些不具有独创性的电影影像应当被视为摄影照片。这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不同国家的著作权传统的差异。然而,当布鲁塞尔文本中摄影作品被添加到第二款第一项的作品示例中时,这种区分情况认定的思路已没有太大意义了。(30)See Sam Ricketson, Jane C. Ginsburg,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Beyond,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32.至此,电影被视为一种独立的作品类型享有著作权保护。
由此可以看出,《伯尔尼公约》对电影作品性的认可经历了从类比戏剧到区别戏剧的过程。早期的电影其实比较接近于一个戏剧表演的影像记录方式。因而柏林文本14(2)保护电影,是因为动作和场景的安排策划上体现出了独创性而构成作品,当然,这样的保护原因和戏剧的保护原因差不多,所以一个电影能够因为其中呈现的可视化内容的独创性而构成作品。然而,电影的内容不一定每次都是新创,很有可能会使用一些已经成型的戏剧演出,在这种情况下,柏林文本14(3)中依然认为可以构成新的作品,原因在于这样的影像化或者画面化的“再现”被视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过程,也就意味着,电影这种依托连续图像进行的表达单独就能够因为将特定情景“装”进连续图像的过程而满足作品独创性要求。这背后的原因是,在电影中,人们看到的是连续图像呈现的效果,这种效果因为画幅和角度的限制区别于真实场景下的视听效果,而对于使用了蒙太奇手法的电影而言,连续图像的组合过程还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再叙述方式或再表现方式,从而产生特有的基于连续图像的特有呈现效果。在柏林文本之后的罗马文本,这种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虽然背后有一些利益相关团体在发挥作用,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电影逐渐具有了独立于戏剧等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产生了更为独特的表达效果,这样的独立性和独特性需要被强调。我们可以把这种艺术价值或者表达效果理解为一种“镜头和画面的艺术”或者“镜头和画面的效果”。
所以,我们从电影在《伯尔尼公约》中定位的变化中可以看出,电影是因为两个方面体现出独创性而构成作品:一是因为电影对一个类似戏剧的场景内容进行了个性化的安排策划,这种独创性体现方式和戏剧作品独创性体现方式大体接近;二是因为电影对一个场景内容进行了影像化呈现时的安排策划,这种独创性体现方式是专属于电影这种艺术类别的。因此,在《伯尔尼公约》中,电影的创作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拍摄的场景内容上作出独创性表达;二是在把该场景内容“装”进连续图像的过程中作出独创性表达。而这两个方面可以分别对应连续图像这种表达的内容效果和画面效果。
(二)通过“呈现效果独创性”来理解视听作品之创作
内容效果和画面效果是建立在早期电影的制作特点上的一种简单二分,因为早期的电影主要是通过对场景的拍摄实现,所以它们是电影呈现效果的两个基础单元。原始的景象经过镜头和画面的运用后变成了连续图像上的景象(即电影影像),所以原始景象本身情况会对电影影像有所影响,同时镜头和画面运用的情况也对电影影像有所影响。从电影作品发展而来的视听作品,和电影一样以连续图像组合为表现形式,因而,连续图像组合的内容效果或画面效果是否满足独创性要求是判断其是否构成视听作品的关键。
内容效果的通俗理解是视听节目所拍摄的场景内容或原始景象本身。如果所拍摄的是自主安排策划的场景或景象,而非那些无法安排策划的生活景象或者自然景象,那么在不涉及抄袭模仿的情况下,这种安排策划就有可能让内容效果体现独创性,因为这个拍摄的过程中,既可以对人的语言、动作、表情进行安排策划,也可以对人的服装、道具、场地进行安排策划,还可以像戏剧一样对这些元素组合形成的故事情节进行安排策划。在专业制作的影视剧中,这种自主性安排策划体现得较为明显,因为所拍摄的对象就是一个需要编剧、导演等人设置好的景象,而在一些新闻节目或者综艺节目中,这种自主性安排策划也会有所体现,集中在形象、背景以及所展现的内容中。同样,脱口秀者以什么样的形象、背景以及讲述什么样的内容也是一种安排策划的体现。
除了场景中本来已经存在的安排策划外,内容效果还可以通过原始景象和特效的搭配或音频的搭配形成新的内容效果,这是现代影视制作比较常见的手法。此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内容效果:最基础的拍摄是把真实存在的场景中的信息,包括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进行记录,比如拍摄一个艺术家现场载歌载舞,那么记录的内容效果就包括歌声(听觉信息)和表情、服装、动作(视觉信息)。在此基础上,如果采用了原始景象和特效的搭配或音频的搭配的制作方法,虽然表面上和传统的内容效果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对真实场景中的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进行了一定的替换,比如添加了背景音乐,其实和在原始现场直接放音乐然后拍摄录制下来的效果类似,又比如添加一些特效,其实和在原始现场摆出真实特效然后拍摄录制下来的效果类似。当然,这是一种类比,有些特效无法被制作成真实的形式。但是,这里想强调的是,内容效果可以囊括这些特殊情形,而且这些特殊情形可能体现出编排策划者的风格或用意。因此如果内容效果是自主安排策划的结果,有可能满足独创性的要求。
相反,如果所拍摄的是那些无法安排策划的生活景象或者自然景象,且没有添加任何配音或者特效,那么内容效果就可能很难满足独创性要求,此时若要构成作品,则需要依靠画面效果来“补救”,从而让整个呈现效果满足独创性要求。画面效果上的安排策划主要集中在拍摄过程和剪接过程的安排策划上。拍摄过程的安排策划体现为角度的选取,但是仅仅依靠拍摄过程,画面效果将很难满足独创性要求,主要原因在于,在视听节目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下,利用摄录技术选择特定角度产出的表达不容易得到评价者认可,即不容易让评价者认为这一选择判断是源自表达者自己的而非从他人那里“得来”。(31)有观点从这一角度否定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独创性,认为虽然不同导播摄制的画面形式会有所不同,但都是遵循固定的套路,而且这些套路是公有领域的知识。参见张志伟:《体育赛事节目直播画面是否具备独创性》,载《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4期。因此,如果拍摄的是生活景象或者自然景象,往往很难在画面效果上体现出区别性(32)有观点指出:独创性判断变成一个纯客观的在表达形成后的事后判断。其实质是新生成表达与既有表达间的差异。参见孙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1期。,不过,不排除一些情况仅仅是固定、机械地录制也能营造出与众不同的画面效果,比如角度特别新颖出彩。然而,多数情况下,画面效果满足独创性要求,往往需要剪接过程的安排策划。我们常见的电影、电视剧、综艺这些专业制作的视听节目大多是由一个个原始的影像片段剪辑拼接而成,在一些体育赛事直播、晚会直播这样的直播节目中,制作者也有可能对不同机位摄录的影像进行剪接,进而形成一种画面效果。(33)体育赛事等直播也可能存在不同情形,有观点指出,判断到一个体育赛事节目是制品还是作品应该由主张权利的人举证。这一问题涉及到对赛事过程固定机位的机械录制或者活动机位的选择拍摄两种情形。参见王自强:《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保护问题探讨》,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1期。这些剪接的方式,既可能是一种专门的叙述或者表述方式,也可能是一种专门的表现或者展现方式,因此有可能融入更多的个性化选择判断。
既然内容效果和画面效果都是连续图像呈现效果的组成部分,也都是视听作品这种综合表达中的部分表达,那么根据《著作权法》中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要求,只要这一表达中的部分或这一表达的整体满足独创性要求即可让特定连续图像组合构成视听作品。因此,对呈现效果进行独创性的安排策划,可以形成独创性的连续图像组合表达,这个过程属于视听作品的创作。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画面的形成者进行了独创性的安排策划并反映在呈现效果上,那么可以认为其在进行视听作品的创作;同样,如果内容的设置者对连续图像组合的内容贡献了独创性安排策划并反映在呈现效果上,那么也可以认为其在进行视听作品的创作。每个贡献独创性表达的过程单独就能构成视听作品的创作,如果结合着进行,则属于从不同方面对视听作品进行创作。因此,为连续图像组合的呈现效果贡献独创性表达可视为视听作品的创作,本文将其称为“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
虽然在内容设置上或者在画面形成上进行独创性表达都可以视为视听作品的创作,但这种认识的成立,需要内容设置者或者画面形成者均有意为连续图像呈现效果贡献独创性安排策划。这意味着,视听作品的创作不仅要求是一种独创性表达,还要求是一种为了连续图像呈现效果而进行的独创性表达。一些拍摄现场演出的视听节目当中,在内容上进行独创性表达的主体,比如其中的戏剧、歌曲、舞蹈或者其他视听内容的作者,就不一定具有为了连续图像呈现效果而表达的意图,此时他们的独创性表达过程不能视为视听作品的创作,而视听作品的认定只能针对拍摄者对呈现效果的安排策划来分析是否满足独创性要求,即使这些视听节目具有了一定的内容性——内容可以单独构成作品且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是也不能因为内容上的独创性而认为整个连续图像组合构成视听作品。
四、“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与《著作权法》运行相适应
(一)“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适应于有关视听作品的现有规定
一方面,从“呈现效果独创性”理解视听作品之创作能够与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规则相适应。在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后,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规则有所调整,但是部分内容依然延续了修改前的思路,即“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以及“视听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另外,增加了“前款规定以外的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制作者享有,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因此把握视听作品的创作其实也是在明确作者的范围。现行《著作权法》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人员视为作者,意味着认可他们进行了视听作品的创作。原因在于,这些人员实际上都对电影、电视剧的连续图像呈现效果贡献了独创性表达,都是安排策划整个呈现效果的一份子。编剧是剧本的作者,也是整个电影、电视剧故事情节内容的主要提供者,编剧创作的剧本中所包含的内容,为连续图像所呈现效果提供了最基本的主线和框架,演员们的对白、台词都以剧本为依托,因此编剧作出的安排策划会反映在呈现效果上。作词、作曲人员的作品融入到电影、电视剧当中时,就可以认为他们的创作内容实际上是整个电影、电视剧呈现效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电影、电视剧所呈现的就包括词曲上的效果。因此,从“呈现效果独创性”来看,作词、作曲人员也应当是视听作品的创作作者。摄影人员是直接形成画面的人员,或者说影像的直接形成者,对呈现效果影响重大,因而也是视听作品独创性表达的主要贡献者。而导演更是全程指挥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制作,是连续图像整体呈现效果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安排策划人员。因而,将导演视为作者也与“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相吻合。
另一方面,以“呈现效果独创性”把握视听作品之创作能够与视听作品和录像制品的界分要求相适应。2020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中,视听作品取代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作品分类中的主要类别,同时录像制品得到了保留,意味着区分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依然是一个重要环节。我国《著作权法》只是要求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34)《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2020)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这里只提到了“具有独创性”,对此有观点指出:“是否构成作品以有无独创性为标准,不受行为人技艺水平高低的影响。”(35)冯晓青主编:《知识产权法》(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因此,按照这样的理解,只要有体现独创性便可构成作品,并不要求在什么方面体现出独创性。对于一个连续图像组合的表达,如果它传递的内容体现独创性,或者它形成的过程体现独创性,都能够因此满足作品要求。
在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的区分中,“呈现效果独创性”可以避免其他方法导致的问题,比如“机械固定录制法”(36)这一方法是在“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再审判决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使用的方法。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8号民事判决书。,这一方法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即特定连续图像组合中的内容上体现出独创性,而画面却是机械或者固定录制的,可能不被认为是创作了视听作品,此时若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均为录像制品的要求(37)《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需要一定时间跟进,在其修改完成前,录像制品依然被界定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形象、图像的录制品。,这种连续图像组合就应该被视为录像制品。但是由于传递的内容满足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因而又能够被视为作品,作品和制品两种定性不能重叠和交叉,否则可能会产生权利的冲突。所以,如果视听作品的独创性有专门要求,而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不一致,会出现一个让现有概念界定与框架体系不相协调的情形。其实,促成作品与邻接权客体之间分野的依然是独创性标准。(38)参见王国柱:《邻接权客体判断标准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邻接权制度的产生虽然有偶然的一面,因为邻接权制度的产生源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催生出来的新利益保护需求,但根本上还是一种制度的妥协,因为邻接权制度是欧洲大陆国家严守“作者权理论”所做的不得已选择。(39)参见王超政:《著作邻接权制度功能的历史探源与现代构造》,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因此区分视听作品与录像制品,还是需要回归到独创性上,而回归独创性,又更适合通过“呈现效果独创性”来把握视听作品的创作。
(二)“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适应于新型视听节目的裁判方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视听节目著作权纠纷中,电影、电视剧作为传统的影视类节目,在《著作权法》上的定性思路较为明确;而以体育赛事节目、短视频以及游戏运行画面为代表的新型视听节目的定性则依然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如果采用“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这些新型视听节目的定性将可能得到更为一致的评价。
首先,“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适应于体育赛事节目定性的裁判方向。我国个别法院已经明确肯定了体育赛事节目可以构成电影类作品。(40)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诉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再审)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再审)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128号民事判决书。相比于影视类节目,体育赛事节目的主要特点是,其内容是现场进行的体育赛事活动,而非事先安排策划好的文艺表演,因而体育赛事节目主要通过画面的拍摄、拼接来进行个性化表达。因此,如果承认体育赛事节目构成作品,其实间接承认在画面上而非内容上进行独创性表达依然可以构成电影类作品的创作。事实上,这些思路与“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较为相似,均从整个连续图像呈现效果的安排策划来分析独创性,这样即使内容上独创性有限,但是依然可以通过结合画面上的独创性而使整个连续图像组合构成作品。在“NBA赛事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涉案体育赛事节目制作过程中,大量运用了镜头技巧、蒙太奇手法和剪辑手法,在机位的拍摄角度、镜头的切换、拍摄场景与对象的选择、拍摄画面的选取、剪辑、编排以及画外解说等方面均体现了摄像、编导等创作者的个性选择和安排,故具有独创性,不属于机械录制所形成的有伴音或无伴音的录像制品,符合类电作品的独创性要求。”(41)美商NBA产物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562号民事判决书。相反,如果坚持按“剧本、导演、后期”这样的“摄制电影方法”来理解视听作品的创作,则有可能得出与法院相反的结论——认为体育赛事节目达不到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毕竟这个过程中没有剧本,可能也没有导演,甚至因为是直播也没有什么后期加工。但是,即使是没有“剧本、导演、后期”的体育赛事节目也依然可以因为画面选取、表征和排序上的独创性表达构成作品,因为理解和认识视听作品的创作应当围绕连续图像的呈现效果,而非其中的个别方面进行。
其次,“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适应于短视频定性的裁判方向。短视频是否构成视听作品也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相比于传统的影视节目,短视频的最大特点是时长较短,同时拍摄制作的复杂程度有限。对此,如果按照传统影视节目的拍摄制作方法来理解视听作品的创作,那么短视频就可能无法满足作品要求。但事实上,对短视频之表达的理解不应过于狭隘,在“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下认定是否构成视听作品,应当关注整体连续图像呈现效果的独创性,即从多个方面来分析短视频制作者的个性化选择判断。在“短视频第一案”中,一审法院虽然认为“在给定主题和素材的情形下,其创作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体现出创作性难度较高”,但是强调涉案短视频“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视听整体”“其编排、选择及呈现给观众的效果,与其他用户的短视频完全不同,体现了制作者的个性化表达”。(42)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诉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而在“爱奇艺诉字节跳动”一案中,涉案节目为脱口秀系列节目中的一期,二审法院认为:“涉案节目有解说字幕、画面插播、画外音、镜头切换、特效及特写,节目结尾处还有嘉宾向主持人提问及主持人回答,系通过镜头切换、画面选择拍摄、后期剪辑等过程完成,其连续的画面反映了制作者独特的视角和富有个性化的选择与判断,表达了与主题相关的思想内容,其独创性程度符合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要求,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43)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1910号民事判决书。可见,在上述这两个案例中,法官实际是从连续图像的整体呈现效果来分析和判断独创性。
最后,“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适应于游戏运行画面定性的裁判方向。在众多新型视听节目认定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方式创作的作品”的裁判中,游戏运行画面可能是最为特殊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游戏运行画面独创性的体现侧重于游戏中元素、场景、角色设计的独创性,而非像影视类节目那样,侧重于内容编排或者画面衔接的独创性。以这种方式进行独创性表达能否被视为一种视听作品的创作有待明确。在“壮游诉硕星”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游戏整体画面在其等级设臵、地图名称以及地图、场景图的图案造型设计、职业角色设臵及技能设计、武器、装备的造型设计等方面均具有独创性,且游戏画面可以以有形形式复制,符合法律规定的作品的构成要件,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涉案游戏在运行过程中呈现的亦是连续活动画面,具有类电影作品的表现形式。因此,涉案游戏整体画面构成类电影作品。(44)上海壮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广州硕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190号民事判决书。而在“网易诉华多”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游戏运行时呈现在终端设备上的画面属于文学、艺术领域的综合表达,其表达融合了故事情节对话、人物角色形象、场景地图设计、技能法术动画、背景音乐音效等可感知的对象,勾勒出以《西游记》取经故事为背景的“人、仙、魔”三界各门派争斗、合作、发展的虚拟社会,体现了游戏开发者对于游戏故事体系、具体玩法规则及整体艺术风格的综合考虑,体现出游戏开发者富有个性的选择与安排,具有较高的独创性。(45)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552号民事判决书。游戏运行画面的呈现效果由具体的游戏元素设计和游戏画面衔接组合而成,因此理解和认识游戏运行画面是否满足独创性要求,应当从整体的呈现效果加以把握。游戏中的元素设计,比如场景、人物、武器装备等,是游戏运行画面整体呈现效果的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游戏开发商最主要的展现游戏特色的方式手段。游戏用户通过这些基础性的元素,直观感受到游戏运行画面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因此,对于这些画面中出现的元素本身进行独创性设计,也可属于对游戏运行画面这一视听作品的创作过程。而游戏画面的衔接组合,体现了游戏开发商安排、策划游戏运行画面呈现效果的基本思路。他们通过编程等手段,将预置的衔接方式以一定的效果展示出来,让玩家或者观众感受到他们独特的构思理念。因此,游戏运行画面被认定为视听作品的裁判思路,其实是通过对游戏呈现效果的整体安排策划加以把握后得出的,是一种应用“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进行分析的体现。因此,“呈现效果独创性”的思路适应于游戏运行画面定性的裁判方向。
结 语
视听节目代表了今后文娱产业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因而可能面临更多的著作权纠纷。通过《著作权法》的基本框架,视听作品的作者可以在与传播者、使用者的关系中获得一定的利益控制,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但前提是视听节目达到视听作品的基本要求,因此把握视听作品的创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种连续图像画面的组合,视听作品的表达可以具化为反映在连续图像呈现效果上的安排策划,而创作视听作品则是对连续图像呈现效果贡献独创性表达,这是一种“呈现效果独创性”的分析法。“呈现效果独创性”的应用不仅能够适应于有关视听作品的现有规定,而且也适应于新型视听节目的裁判方向。总体来看,这一理解视听作品之创作的思路让视听作品既能保持传统的特点又能适应新情况、新问题,为合理确定视听作品的保护范围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