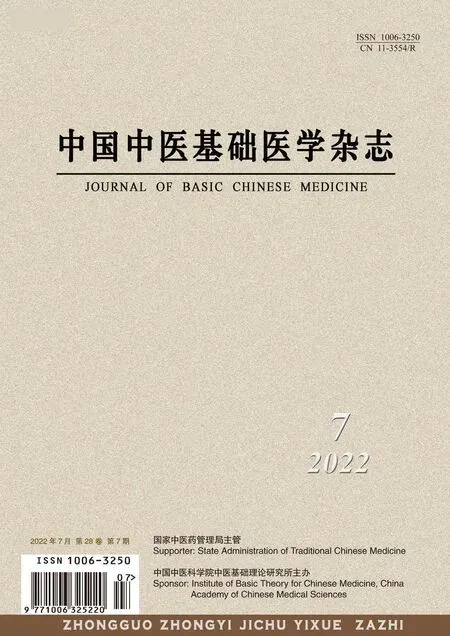基于“调和阴阳”探究张仲景治疗不寐的学术思想❋
孟庆鸿, 刘姝伶, 张泽涵, 连雅君, 汤菲菲, 程发峰, 王雪茜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不寐是一种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深度和时间为特征的病症,临床表现为经常入睡困难,或睡时易醒、醒后难以入睡甚或彻夜不眠,同时伴有白天精神状态不佳,属于现代医学“失眠症”范畴。据不完全统计[1]2,约有30%的人患有一种或者多种“失眠症”。作为一种临床常见的疾病,早在两千年前的张仲景就已经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多处提及。《伤寒论》中关于“不得眠”“不能卧”“不得卧”“不得卧寐”“卧起不安”“不得睡”等相关词汇共出现12次,而《金匮要略》中这些词汇共出现8次,不仅出现次数频繁而且创制了数个治疗不寐的千古名方,如酸枣仁汤、黄连阿胶汤等。遗憾的是,张仲景并未为“不寐”设立专篇讨论其辨证论治规律,为更好地学术探讨和临床诊疗,故通过梳理相关条文,探究其处方用药特色。
1 睡眠的生理基础
与人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一样,人体之中的阴阳之气亦有相似的运行规律。根据《灵枢·营卫生会》所记载,人体通过运化水谷精微得来的后天之气可以分为精粹之营气与剽悍之卫气。营气行于脉中主化生血液,营养四肢百骸;而卫气行于脉外肌肤腠理之间,主调节腠理开阖,维持体表温度以及抵御外来邪气。由于卫气其性属阳,外可达肌表,内可达脏腑,故当卫气行于阳分时人体处于活跃状态,当卫气行于阴分时人体处于休眠状态。故《灵枢·口问》云:“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主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因此,在生理状态下,睡眠是一种卫气由阳分进入阴分和在阴分运行的过程,而行于阳分、行于阴分、阴分与阳分交接分别构成了睡眠的三个重要环节。
2 不寐的病机讨论
根据睡眠的生理基础可知,当阴分、阳分以及阴分与阳分交接任何一个环节异常,都会导致不寐的发生。《灵枢·大惑论》云:“黄帝曰:病而不得卧着,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也。”王建华根据阴阳的升降关系提出不寐的病机为“阳不入阴”“阳扰于阴”“阳早出于阴”三种情况[2]。而笔者认为不寐的主要病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阴不涵阳。以阴阳偏盛或偏衰为核心病机,一方面由于阳分热盛,阳气亢盛,热扰心神,而出现阳盛实热证的症状表现;另一方面由于阴分有热,阴血不足,虚热扰心,而出现阴虚虚热证的症状表现;二是阴阳失交。以实邪阻滞阴阳相交为核心病机,常见于因饮食、劳逸、产后等导致有形实邪或病理产物阻碍阴阳气相交接的途径,但不会造成机体明显的阴阳偏盛或偏衰,而是以实邪阻滞,影响气机、血行、津液输布等为主要临床表现。
3 治疗不寐的方证分析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调和阴阳”治疗观源自《黄帝内经》,“调”为“调整”之义,为手段,为过程;“和”为“恢复平和”之义,为目的,为结果。因此“调和阴阳”既包含“调整阴阳”,即通过观察阴阳失衡的状态,从阴阳角度出发进行治疗,损其有余,补其不足,恢复阴阳平衡的治疗原则;又包括通过分析阴阳失衡的病因,从病机层面驱邪扶正,实则泻之,虚则补之,恢复阴阳平衡的治疗原则。
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继承了《黄帝内经》的知识体系[3],并将其应用于临床。虽然在《伤寒杂病论》中对理论的描述相对较少,但对于经方的临床应用较为详细。对于不寐的治疗,通过对条文整理笔者发现,张仲景以阴阳盛衰状态作为辨证基础,以“调和阴阳”为总体的治疗原则,结合六经[4]脏腑气血虚实进行遣方用药。以下将具体陈述不同病机所导致不寐的方证以探究其在不寐中的处方特色。
3.1 阴不涵阳
3.1.1 栀子轻清宣郁阳 阳分有热,是导致阴不涵阳型不寐最直接的原因。心属上焦,五行属火,因此当心阳亢盛或被郁遏致使阳热内扰心神而出现烦躁不安并难以入睡。《伤寒论》第76条云:“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忄农,栀子豉汤主之。”第79条云:“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两则条文均有“卧起不安”的症状,前者为误治所致上焦阳热亢盛,无形邪热留扰胸膈;而后者亦经误治上焦阳气郁闭而致化热,而兼见中焦气机不畅。故前者以栀子豉汤清宣郁热,栀子豆豉二药一宣一降,一辛一苦,相辅相成,得其阴阳寒热升降的作用;后者以栀子厚朴汤清热宽中,栀子宣上焦阳郁,枳实厚朴理中焦气滞,三药共奏心腹两解之功。两方同用栀子,旨在取其轻清宣透之性,寒而不重可直入心肺;寒而不凝,不冰敷邪气。故《本草逢原》曰:“栀子仁体性轻浮,专除心肺客热。[5]877”因此,针对心肺阳热亢盛时可首选栀子宣散邪热。
3.1.2 龙牡沉降敛浮阳 通过梳理《伤寒杂病论》中含有“龙骨-牡蛎”配伍的方证,笔者发现轻则出现烦躁,重则出现不寐、谵语等心神外越的神志症状。如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证中的“烦躁”,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证中的“惊狂、卧起不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中的“烦惊、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中的“男子失精、女子梦交”等。而出现诸般证候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主神明的功能异常,心藏神,当心中阳气不足、虚阳外浮、心神亦不归常位,导致烦躁、不寐、谵语等症状的发生。因此,急则治其标,镇心安神便成为当务之急。《医学衷中参西录》云:“凡心中怔忡、虚汗淋漓、经脉滑脱、神魂浮荡诸疾,皆因元阳不能固摄,重用龙骨借其所含之元阴以翕收此欲涣之元阳,则功效立见。”又云:“牡蛎咸寒属水,以水滋木,则肝胆自得其养。且其性善收敛有保合之力,则胆得其助而惊恐自除,其质类金石有镇安之力,则肝得其平而恚怒自息矣。[6]326-327”可见,龙骨、牡蛎二药相伍,以其质重收涩之性,既可向下收涩浮越之阳气,使心神得以归位;又可以向内收敛外泄之精气,使肾精得以封藏。因此,当在不寐发生发展的病理进程中,可以选用“龙骨-牡蛎”潜镇浮阳。
3.1.3 阴虚辨脏腑 阴分有热,亦是导致阴不涵阳型不寐发生的原因之一,五脏六腑中任何一脏阴津亏虚、热扰心神都会导致不寐的发生。如心肺阴虚内热所致“欲卧不能卧”,心脾气阴两虚内热所致“数欠伸”,心肝阴血两虚内热所致“虚烦不得眠”,心肾阴虚火旺所致“心中烦,不得卧”等。因此对于阴分有热所致不寐的诊疗,在原则上应先行脏腑辨证确定病位,再结合药物的性味归经运用养阴清热法进行治疗。
针对心肺阴虚,张仲景运用清心安神、养阴润肺百合与滋补心阴、清热凉营的鲜地黄汁相伍,辅以凉润之泉水以滋心肺之阴为主,清心肺之热为辅。针对心肝阴血虚,张仲景以酸甘之酸枣仁入心肝二经,滋阴养肝,宁心安神,与甘草相伍酸甘化阴,以治阴虚之本;知母苦寒,清泻相火,滋阴润燥,以治虚热之标。针对心脾气阴两虚,张仲景以小麦入心脾、养心脾、滋阴血,大枣、甘草补脾益气,三药药性平和,共助气血化生,缓缓补益,以期阴阳平和。针对心肾阴虚火旺,以黄芩、黄连苦寒清热、泻火坚阴,以治其标;芍药酸甘养阴和营,阿胶味甘滋阴养血,以救其本;辅以血肉有情之物的鸡子黄。吴鞠通称鸡子黄“乃安奠中焦之圣品”“其气焦臭,故上补心,其味甘咸,故下补肾”“上通心气,下通肾气”[7]122,故有交通心肾、养阴清热之效,同时顾护中焦,防止芩连苦寒伤胃。因此,张仲景以百合养肺阴,酸枣仁补肝阴,小麦滋脾阴,阿胶坚肾阴。
3.2 阴阳失交
由于各种病理产物均可影响阴阳的正常运行,因此对由于有形实邪所致阴阳失交而出现不寐进行治疗时,首先应从导致其阴阳失交的病因着手。瘀血阻滞则活血逐瘀,痰饮闭窍则化痰开窍,水饮为患则淡渗利水,食积内停则通腑泻热,湿热中阻则辛开苦降。张仲景在运用各种治法治疗与不寐相关的疾病时处方极为灵活,下面具体介绍各种治法在处方中的体现。
3.2.1 活血逐瘀法 在《伤寒论》中,瘀血与热互结常常导致神志异常,如桃核承气汤证中的“其人如狂”,抵挡汤证中的“其人发狂”等。而《金匮要略》中,枳实芍药散证中出现了“烦满不得卧”的症状,因产后气血虚弱、气血郁滞,故以芍药补其虚,枳实行其滞。若药后不解且腹痛仍在,说明瘀血凝滞胞宫较重,行气活血之法难以胜任,于是采取破血逐瘀之法,以苦寒邪热逐瘀之大黄、辛润活血化瘀之桃仁、破血消癥的虫类药虻虫相伍,并以酒化丸,旨在体现“血实宜决之”的治疗原则。
3.2.2 淡渗利水法 《伤寒论》第71条云:“太阳病,发汗后,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因治疗所致津液耗伤,患者欲饮水自救便会引起不寐的发生。《伤寒论》第319条云:“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少阴病下利数日伤及肾阴,患者渴欲饮水,饮后咳喘而呕吐,同时夜卧不安,可知水饮内蓄,而阴虚生内热,水热互结,阴阳失交所致“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故治以养阴、清热、利水。猪苓汤以猪苓入肾膀胱二经,淡渗利水兼以清热;茯苓健脾祛湿,培土制水;阿胶滋阴润燥,防利下伤及阴血;泽泻性寒,既可利水又可泻热;辅以滑石助二苓、泽泻利水。全方以淡渗利水为主,辅以滋阴清热,意在张仲景先师“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的治疗原则。柯韵伯称猪苓、茯苓“不根不苗,成于太空元气,用以交合心肾,通虚无氤氲之气也”[8]342。但笔者认为全方实则开泄水热之结,给邪气以出路,消除病理产物,恢复阴阳平衡的状态,因此可以起到除烦安神的效果。
3.2.3 涤痰开窍法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云:“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无论是邪实气闭所致的肺痈病,还是痰浊壅肺所致的咳嗽上气病,都会引起卧起不安的症状。虽然二者病位均在肺不在心,并不影响心神,并且不会明显造成机体的阴阳偏盛或偏衰,但是通过影响患者呼吸,导致阴阳气相接出现异常,进而导致不寐的发生。关于其中的用药,《长沙药解》云:“皂荚,辛烈开冲,通关透窍,搜罗痰涎,洗荡瘀浊,化其黏联,胶热之性。[9]146”“葶苈,苦寒迅利,行气泻水,决壅塞而排痰饮,破凝瘀而通经脉”[9]190,两者均为峻猛祛痰通窍之药,皂荚辛温走窜,涤痰开窍,针对胶着黏腻的痰饮,有直捣黄龙之势;葶苈子苦寒泻肺,祛痰化饮,祛痰饮的同时亦可开泄肺气。从其药性特点可以看出,两者病性虽均属实证,但都以痰饮为患,前者侧重痰饮胶着日久,损伤阳气,病性偏寒;后者侧重风热壅肺,水湿痰饮停聚,肺的气机不利病性偏热。此外,由于二药攻伐之力过猛,前者配以蜂蜜并以枣膏和服,后者配以大枣,均取甘缓补益、缓和药性,防止伤及正气。
3.2.4 通腑泻热法 《素问·逆调论篇》云:“胃不和则卧不安。”《内经》时代就已经发现食积是影响睡眠的病理因素,并创制半夏秫米汤治疗不寐。《伤寒论》第242条云:“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阳明燥热内结,腑气不通而使阴阳失交,故致难以入寐。根据其燥屎与热邪相搏结、腑气不通的病机,可以通腑泻热为治法。因此,临床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或者调胃承气汤,或者合方使用。
3.2.5 辛开苦降法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云:“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于上部则声喝,甘草泻心汤主之。”张仲景并没有着手于直接清热利湿或是杀虫解毒,而是着眼于中焦脾胃,脾胃升降斡旋正常,则水湿痰饮皆化为乌有,湿去则热孤,虫无所附,故以甘草泻心汤辛开苦降,和中益气。方中重用生甘草清热解毒,扶正补虚;半夏、干姜温中和胃,祛湿化痰;黄芩、黄连苦寒清热,燥湿解毒;人参、大枣健脾益气,顾护胃气,诸药合用辛苦祛湿热,寒热调阴阳。全方未有杀虫之药奏驱虫之功,未有安神之药却有宁心之效。
4 结语
中医对失眠认识历史悠久,临床经验丰富,方法多种多样[10],临床中有许多不同的治疗原则与方法。张仲景在“调和阴阳”治疗观的指导下将不寐的病机划分为“阴不涵阳”与“阴阳失交”两大类。针对阴不涵阳型不寐,运用不同药物制亢阳、敛浮阳、养脏阴,使失调的阴阳恢复平衡;对于阴阳失交型不寐,针对病因病机遣方用药,灵活使用活血、利水、涤痰、消食等诸多治法祛除有形之邪,以达到“阴阳自和”的状态。虽然并未设立“不寐”专篇,但是其中医理与方剂蕴藏在各个篇章中。正如陈修园所言:“读仲景书,当于无字处求字,无方处索方,才可谓之能读。[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