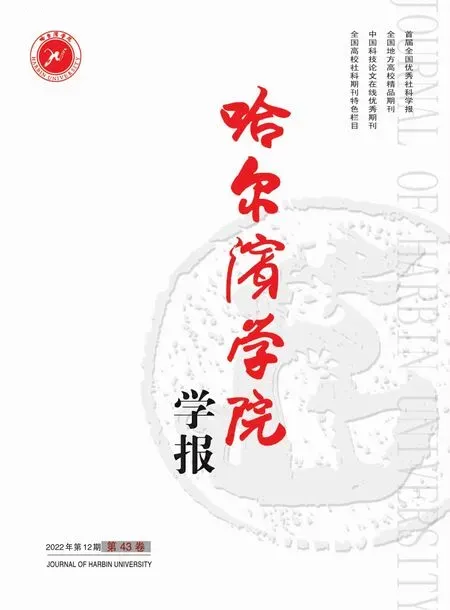高拱《大学》改本研究
陶 莎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高拱是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不仅在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平定叛乱、巩固边防等方面建树颇丰,学术思想上也深有造诣。除了与政治措施相关的著作,其代表性学术著作还有《日进直讲》《春秋正旨》《问辨录》《本语》。其中《日进直讲》是高拱担任裕王侍读期间的讲稿,此书先训解字词,后陈其大意,再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逐段串讲;《春秋正旨》主要体现出高拱针对胡安国、程伊川等人对《春秋》经义的穿凿附会的批判;《问辨录》是高拱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疑意,逐条辩驳,以求圣人遗言之真诠;《本语》记述了高拱对各种问题的基本见解,是他一生思想的概括和总结。
一、高拱《大学》改本结构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体现了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学》本为中国古代重要书籍《礼记》中的一篇,未独立成书,主要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修齐治平之论,以彰显内圣王外之道。最初的《大学》本没有古今文本之殊,所传经文无石经本和注疏本之差,在理学尚未崛起的一千多年期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诠释甚至修改。直到唐朝,韩愈首先发见并引用到《大学》中的文字,阐明其说,并与其“道统说”相联系,阐扬《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用以对抗佛教空谈治心、泯灭伦常的虚无思想。自韩愈后《大学》地位得到一定提升,但真正受到儒者的广泛重视,是随着“二程”洛学的崛起。“二程”兄弟提出自己的《大学》改本,认为古本存在错简,此举开启各家为《大学》文本改序、疑经惑传的风气,这对朱熹的《大学章句》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认为《大学》有错简阙文所以移其文,补其传,并且和《中庸》《论语》《孟子》编集在一起成书为《四书章句集注》。古本《大学》这个概念实际到了王阳明时才提出,在王阳明生活时期,朱熹的《大学章句》已被奉为权威,早年王阳明的思想受到朱熹的影响,但在经历过多次格物失败和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有了自己关于“格物致知”的见解,并对朱熹《大学》的改本提出了批评,主张恢复《大学》古本,认为《大学》无错简,无缺文可补,并作《大学问》《大学古本旁释》《大学古本序》,重新确立《大学》古本的权威地位。“今本《大学》始于二程又定形于朱熹,其主要是通过朱熹对《大学》古本的划分、调整、补传来实现的,所以今本《大学》的特色也主要体现在朱熹如上三步的调整操作中,由于经传的划分本身并不改变《大学》原有的结构,今本《大学》的特点主要就体现于朱熹的调整和补传中。”[1]以古本《大学》为对照,朱熹重新调整了《大学》的段落次序,还分经传,一共分为十一章。《日进直讲·大学直讲》篇中,由于讲授对象为准君主及时代背景的特殊性,高拱则以朱熹改本为讲本,肯定朱熹对《大学》的诠释路径;但后期在《问辨录》的卷一《大学》篇中,高拱认为古本《大学》并未出现缺漏,也无经传之说,脉络清晰,自成体系。他不仅对朱熹《大学》改本中的观点有着针锋相对的见解,还提出自己所理解的古本《大学》。他认为《大学》应不限于“三纲八目”的概念争论,并在批判吸收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基础上,力图摆脱学术争论的禁锢,发扬其治国理想,倡导经世致用风尚。他所提出的《大学》改本较之“古本”而言,无严格意义上的改动,只是将“瞻彼淇澳”至“此谓知本”等六节移至“此谓知之至”之后,移在“所谓诚其意者”之前,其余仍从古本。“故曰‘此谓知本’。前云‘知本’,盖示其的,始之也;此云‘知本’,乃证以事,终之也。文义既有收拾,脉络亦自分明,故曰‘非有错也’。”[2](P1090)高拱以“知本”作结,“瞻彼淇澳”以后诸条自然是对“知本”的解释;“而又揭言其‘本’,欲人之知要也。”[2](P1090)且因前文有“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知本”以其为提挈,既然“瞻彼淇澳”以下诸条以“此谓知本”作结语,为前后呼应,有始有终,则“瞻彼淇澳”后诸条当移至于“此谓知之至也”后。至于“格致”阙文的问题,高拱以“瞻彼淇澳”至“此谓知本”的几节经文作为“格物致知”的解释,他认为如上几节经文是承“知本”而言的,“皆以明‘修身为本’之意,而‘格致’亦在其中”,这就解决了“格致”阙文的疑虑。高拱改本是经过轻微处理后的“古本”,文本上并没增字改经补传,而是建立在“此谓知本”与“此谓知之至”两句连属的基础上,不过其依旧采纳了“二程”的“新民”说。《大学》古本是无任何章节划分痕迹的,高拱自己也说过:“但旧本无传之几章之说。”但通过其在对文本的行文注解以及他关于“前云‘知本’为始,后云‘知本’为终”的结构改序,可见高拱在对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是带着章节划分意识的。这一举动与古本《大学》本身“文义自有收拾,脉络亦自分明”[2](P1091)有关。如古本《大学》中,从“所谓诚其意者”节开始,开头均为“所谓”,尾句都以“此谓”结束,历来那些对《大学》进行解读的学者们,在释义进行章节划分的时候,对“所谓诚其意者”及其后部分划为五章鲜有争议;而此部分之前的内容在章节次序段落的划分上颇有争议。所以大多学者们在阐发大义的时候容易受文本自身结构、脉络的影响,因而会或多或少带着不同程度上的章节划分意识。概而言之,高拱改本虽有别于程朱,但仍然借以程朱之技来将《大学》改本还原为古本面貌。
二、《大学》改本义理初探
(一)大学之义
何谓“大学”?目前最早出现讨论“大学”含义的文献为郑玄的《礼记目录》,其中道:“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认为“大学”是一门能够令人博学广识为政治国的学问。因此而后有许多儒家学者皆将“大学”释为“从政治国”之学。朱熹通过年龄来划分,将“大学”“小学”对立起来,从概念上来解释“大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术。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3](P1)在他看来“大学”是大人之学,是教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小学”则学习的是礼之节文,要先通过“小学”阶段的学习培养才能拥有进行“大学”阶段培养的基础。在《日进直讲·大学直讲》篇中,高拱对于“大学”“小学”的看法和朱熹基本相同,但《问辨录》的《大学》篇中高拱认为古之《大学》并非单纯的教书育人的纲要和准绳,也不是简单的入德之书。他不赞同朱熹所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3](P1)“岂谓孰为小学,孰为大学乎?王浚川云:‘古人论小学如农圃医卜历像千支之,非谓八岁入小学也,大学即《诗》、《书》、礼、乐、修齐治平之道,盖德行道艺之纯者也。若学其大,则自八岁至十五其学非有二本,后世乃将年之大小岐而二之,非古人之义矣。’兹言良是”。[2](P1092)高拱引用王廷相释义“大学”的话,对一些学者所释的“大学”之意提出质疑,后世将“小学”“大学”以年纪大小分而为二,歧出于古人之意。“学”之“大小”并不能以年龄来划分,“大学”与“小学”并非学有二分。“大学”非“大人”之学,也非古代的“太学”,“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所谓大学者,学为斯人而已矣,盖谓是世间一种大学问,非若小道。可观君子不由者也,固非成均教法之谓矣。”[2](P1092)他理解的“小学”为农圃、医卜、历象、干支,“大学”乃是“道行德艺之大者”,为诗书礼乐、修齐治平之道,是学之大成的结果,亦即是兼具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之学。
(二)絜矩为平天下之道
《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就在于治国平天下,“絜矩之道”是修养身心、平天下之要道。“絜矩之道”出现在《大学》最后一章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相关论述中: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2](P857-859)
郑玄曾注:“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谓当执而行之,动作不失之。”[4](P1600)朱熹解释为:“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方,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3](P10)郑玄所谓“絜矩之道”的内涵为儒家的“忠恕之道”,在朱熹这里进一步将其具体到“平天下”。高拱释“絜”为“度”,“矩”是为方的器具,“絜矩”即“恕”,言“恕”必有“忠”。他所讲的“絜矩之道”,放在治国平天下框架下阐述,主要针对者为统治者,其中不仅仅包含着治国理政的理念,亦包含着个人修身的思想,体现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孝、悌、慈”是儒家重要伦理思想,在先秦典籍中经常会出现。“孝”是子女亲爱父母,“弟”是弟弟敬爱兄长,“慈”是长辈关爱晚辈。“盖言天下无不同之心,人心无不同之理。”[2](P858)人人本生来都具有“孝、弟、慈”的良能,只不过在后天由于私欲而被蒙蔽。为人君者是万人之上的统治者,为众人所敬仰,其言行举止是万民的风向标,更应举措适宜,谨慎行事。为尽“絜矩之道”,人君应当存公心,以身作则,做好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体恤孤幼,豁显本心的表率,将自己本有的“明德”都明了,且新其德以及于民。那么百姓自然会受到君主行为的道德感化,天生纯良的明德自然会兴起,每当人民迁善改过,能自新者,应对其鼓舞振作,使其可常常为善,如此一来天下万民各得其所,自然得民心,人心平则天下自治。所以《大学》只说“平天下”,不说“治天下”,“盖人心平,则天下自治。”[2](P859)“然絜矩非可易言者,必是见理明,才能知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存心公,才能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而欲明欲公,则非修徳不能。所以君子必先于慎德也。”[2](P868)人君如果做不到修德明理,心无偏私,以天理之公,明天下之心,自然是尽不了“絜矩之道”。“所以为上的君子,有个‘絜矩之道’,度人心之所同而处分之,使天下之愿为孝、弟、慈者,皆得以自尽而无有不齐。”[2](P858)以人民拥有的最基本的“孝,弟、慈”的道德品质为“絜矩之道”的立足根基,跳出影响公允之心的私情私欲,不拘泥深陷于人情之好好色、恶恶臭的约束规范,着重在于付出具体的行动,实现“上有所行,下必效之”的道德感化,使得人人本具的“明德”展现出来。
“盖人之相处,有在我上的,有在我下的,有在我前后左右的,其心都是一般。如上以无礼使我,我所恶也;则必以此度下之心,亦不以无礼去使他。下以不忠事我,我所恶也;则必以此度上之心,亦不以不忠去事他。或有所恶于前者,即不以之先加于后;而有所恶于后者,亦不以之从及从前。或有所恶于右者,即不以之相交于左;而有所恶于左者,亦不以之相交于右。”[2](P858)
在人际社会交往过程中,不同的角色面临着不同的上下、前后、左右交互关系,他人行为举止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当他人行为的影响给自己带来消极感受的时候,更不应该用同样会带来消极感受的行为去与人相处,将人比己,将己处人,不去强求他人完成自己都不愿意完成的事情。就像工人为方的度之以矩,使其方正一般,从对自己的要求做起,形成一种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标准。“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行为标准,这也即是“絜矩之道”。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都会和谐融通。可见高拱十分重视在政治实践中践行此道,将通过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视为社会治理的关键。
(三)理财为王政之要
“絜矩之道”体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高拱认为在这诸多之中,最重要的是“理财”和“用人”。在“用人”方面,要任举贤才。奸佞的人,巧言令色,颠倒是非,如果人君若是喜好他,便不能敬贤了;有德之人忠信贤能,若人君喜好他,贤者便肯为其用之,尽心尽力,报效朝廷。因此人君作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应对百姓的本性具有正确的认识,只有知道人的本性是怎样的,才能更好的进行统治。
“理财”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5](P201)财物可以拢聚人心,应该正确合理看待对于财物的管理。《大学》中的理财思想主要集中在《平天下》一章中:“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2](P860)有德行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就会有土地和国家,也就拥有财富可以使用。高拱吸收王廷相的关于“气”论的思想并结合其在朝为政的经验,注重经世致用的理念,宣扬《大学》中并不为学者所重视的生财之道,阐发了其独具特色的新理财思想。历代儒者大多着重宣扬仁义,重“义”而非“利”,强调人们要摒除物质欲望,加强内心对道德修养的高尚追求。高拱亲眼目睹吏治腐败、士风空浮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深刻认识到空谈理学的空疏学风误国误民,更应注重实用之学。与前期将“义利”问题与“理欲”联系起来,侧重通过个人修身来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不同,在《大学》改本中,高拱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强调要实现国家之公利,而实现此“公利”要明白理财的重要性与合理性。他首先通过引用儒家经典中所言“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得出了“理财,为王政之要务也”的结论。[2](P1096)然后他将儒家的经典学说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巧妙的表达出“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2](P1096)一些“腐儒”以名利为目的,不懂“义、利”,害人误国。有鉴于此经验教训,他阐发出自己关于“义、利”的新内涵,“殊不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2](P1096)高拱认为“义”即“理财”,“利”即“聚财”,若为国家谋利益的“理财”,以是公共利益的总和为基础,此时的“利”即“义”;所以要打破“义”“利”二者之间的界限,实现它们的相互转化的条件就是将“利”建立在“公私之判”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为国谋利的基础之上。高拱对“公利”和“私利”的划分实属高见,“孟子之学,最严于义利之辩,故于篇首发之,不夺不餍,是利而不利也。不遗亲,不后君,是不利而无不利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2](P1095)他所追求的是“以义为利”,在为了保全国家利益之前不计较牺牲个人利益方为治国大利,像桑弘羊、裴延龄等言私利之徒,以聚敛财用为目的来满足个人为小人行径。刘晏的“理财”是以养民为先,为国家造福谋利,聚的是高拱所言的“义”之“财”。高拱表示,刘晏并非因为“聚财”而死,而是因为遭杨炎诬陷,昏君听信谣言下诏赐死的,并且其死后家中的财产也仅有“杂书二乘,米麦数斛”,[2](P1296)如此清廉之人实乃“干国之臣”。高拱对于因“理财”致死的言论深感荒谬,不仅违背历史而且这让那些真心为国谋利之人实感寒心,如若理财官均为言利之人,此职位设立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高拱借抨击不言利的迂腐名流之辈来强调理财的重要性及合理性,他没有仅仅停留在个人修养的道德层面,而是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秩序上来论证为国理财乃治国大道。他关于理财的观点与嘉靖中期财政危机、民族危机的社会状况也相适应。
三、结语
《问辨录》是高拱晚年最高学术成就代表之一,也是明代批判程朱理学的代表性著作。高拱公开批判程朱、陆王和胡安国等人的理学观点,反对重义轻利等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空谈理学,认为它们误国伤民。其一反之前对于《大学》义理研究的狭隘视野,与朱熹《大学》思想针锋相对,对其注释提出质疑,有针对性的答问诘辩,赋予其新的内涵,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如“本末原非条件,恶用释?且只因‘本’字,遂为之‘释本末’,然则又以何者释终始耶?”[2](P1094)高拱认为“本、末”不属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所以不需要为其解释。“晦翁因好恶字,遂以为好善、恶恶,乃使人泥于其中而不能出。”[2](P1094)高拱批评朱熹此处有画蛇添足之意,容易使人拘泥于其中,影响了对经文的正确理解。“濂、洛、关、闽,发明圣学,以训后世,厥功伟矣。然洙泗之渊源有在,学者必求溯洙泗之渊源,而参伍以濂、洛、关、闽之说则可,而若遂以濂、洛、关、闽为洙泗,而不复知所求焉,则亦不能入圣人之域也。”[2](P1244)虽然高拱公开批驳他们的学问,但他不否认濂、洛、关、闽之学为“发明圣学”“厥功伟矣”,只是这些学说并不等于孔学本身,而是只为符合圣人之学,实乃各持臆说,互有离合。他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并将其贯通于《大学》思想的阐发之中,深刻地总结和概括了他主政期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