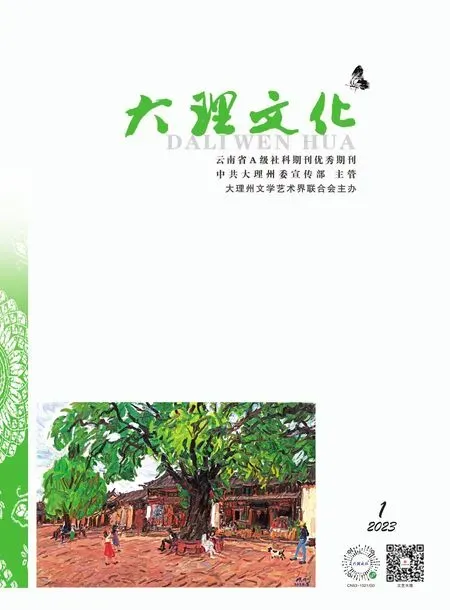大理畅想曲
●黄亚洲
我凝望阳光下的三塔
不要打搅我,我愿意凝望阳光下的三塔。大地点燃三炷烛火,大理一片光亮。
三塔正前方,大鹏金翅鸟从雕塑出发,定格为飞翔的永恒;这不仅仅是白族的图腾,我们,都需要引领!
对于点燃大地的三塔,大鹏鸟是一种向上的引领;对于浑厚敦实的苍山;三塔是一种超然的引领;对于持续发力的大理,苍山是一种稳健的引领。
不要打搅我,我愿意凝望阳光下的三塔。三塔是一种哲学的展开。
洱海、大理城、金翅鸟、三塔、苍山,这是安宁和荣耀,在时间与地理的引领下,作梯次的排列。
居中的,是十六级的千寻塔。两座十级小塔,南北拱卫。天下,仿佛再没有比这更简练更稳定的结构了。这是哲学呈现的几何图形,再加上脚下的洱海,这一片定理;再加上身后的苍山,这一排公式;再加上胸前这只大鹏金翅鸟;因此,我看见大理的未来,正在破题!
不要打搅我,我愿意凝望阳光下的三塔。从古时候一直到现在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我依次瞧见了王爷、土司、家奴、佃农,与从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大步走来的人民。我听见大鹏金翅鸟的翅膀,拍打着最准确的答案。
不要打搅我,我愿意凝望阳光下的三塔。这是一道久看不厌的大题,关乎建筑、地理、信仰、生活与哲学,看久了,也就慢慢看懂了。
所以,不要打搅我。
阳光下,她是答卷,我是答案。
洱海的生态廊道
看来,洱海西边这46公里的廊道,这些柳树、水杉、芦苇和鸟鸣,以及游人的悠闲,还有警惕的松鼠,都已经纠缠在了一起。我还看见不放心的清风,把这些,又一遍遍地绞紧。
湖边,一个个大公园,套着一个个小公园。树与花,撒得无边无际,连水鸟都找不到尽头。
我走过青石桥,刚步上亲水平台,洱海的浪便一轮轮冲我而来,哗哗地越过我脚底,顺便把刚站直的芦苇,大面积推倒。水一旦清冽了,就很任性。
确实,廊道把湖与人居彻底隔开,措施太及时了,整整做了三年。当时,一些想不通的村民,现在一遍又一遍赞叹:这个我们司空见惯的湖,怎么会和大姑娘一样漂亮!
沿途23个漂亮的驿站,都布置了休闲区与艺术馆。拍婚纱照的,也太忙了,全要预约。湖边不止一处,被称为“最佳爱情表白地”。廊道已经成为大理游客流量的担当。
我因为年龄关系,所以今天就不作年轻人的絮絮叨叨的爱情表白了。我只低下头,对向我涌来的波浪,直截了当地说:“别老舔我脚,我现在这么渴,就想喝你!”
洱海民宿
这里的民宿,全都把钢架大窗户瞄准洱海,仿佛游客,就住宿在照相机里。眼睛一眨,便是快门。
这里的民宿,都把水鸟、杉柳、鼠尾草、湖边亭阁,当做自己的家人;让每个游客,一放下行囊,就有融入大家庭的感觉。
每一家民宿,都像是洞房。推窗,就见“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花海羞红,水波搂肩。借景,那是必须的。
这里,数年前,还是陈旧的村舍与农田。一桶脏水一泼,洱海就多一条支流。现在,洞房连绵不断,湖畔廊道通到哪里,爱情就跟到哪里。
民宿都不好订房,尤其是旅游旺季。我跟好几只水鸟都打了招呼:“一有空房,就烦请伸嘴,啄一下腾讯的网络,让我的手机,振个响铃。”
古生村
没说的,古生村的位置,自古就生得好。那三棵钻出水面的大树,是村子深入洱海的飞地。无论谁的相机拍摄这半截在水中的古树,都可能摘得摄影大奖。
村里每条干净的街巷,都像大树干净的枝条。青瓦、粉墙、红廊柱,这是谁调的色?我从一个童话的南面走进,从这个童话的北面走出。
没说的,一条生态廊道,就是洱海的一条扁担。这扁担的学名,叫做“经济带”,沿途村庄,一个个的全挑起来,一个都不准少。当然,古生村是最缤纷的一个。连这个村子种的粮食,都是霓虹般的“彩色水稻”。
我跟村里的一位环保员攀谈了一下。他很有感慨,说自己也认不出自己的村子了。这话我信,这就像洱海里的一条鱼或者一只虾,已经不认识早先的洱海一样。
夜游洱海
我们的船不能再往前面走了,据说,会惊扰鱼儿。
在洱海,这当然是头等大事。那些鲤鱼、弓鱼、鳔鱼、细鳞鱼、鲫鱼、青鱼,必须保证睡眠健康。
我们的船本来就小心翼翼,船上歌手都唱得很小声。我甚至还在甲板上,几次向两岸大理城的灯楼招手,让它们,收敛一点繁华。
真不能再往前走了,前方是出水口,更狭窄了。这里的鱼儿,要过一个像样的夜。人不能把自己的夜生活强加给鱼们。过于快乐,可能就是放荡的一种。
我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对鱼来说,我是一个外来物种。我在洱海里走几步,就必须上岸。我应该像白天的苍鹭,偶尔划过水面,只叼啄三四粒水晶。
大理古城的洋人街
我走这条街,先后被拦四次。夜灯下,这些不由分说的手势是多么热情。小美女或小帅哥边鞠躬边说请请请。那些吼唱中的吉他手,把门外长街也当作了琴弦,用指甲撩拨路人。
蹦嚓,蹦嚓,蹦嚓,洋人街处处震响没有洋人的洋音乐。
蹦嚓,蹦嚓,蹦嚓,不时尚不叫古城。
洋人街每天都闪烁到下半夜两三点。卖扎染的、打银器的、挖耳朵的、锅盖打开异香扑鼻的,不时尚不叫古城。

说起来,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这里设有政府招待所专接外国友人,所以,人们眼睁睁就看着这条街头发逐渐变黄,眼珠逐渐变蓝。所以,护国路便叫成洋人街;所以,当年云南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起兵护国的群情振奋,在今夜的蹦嚓蹦嚓中,依旧万马奔腾。
一千米长的慢生活,却刮着如此激烈的麦克风。其实想想,也属正常,只要袁世凯垮台,生活便可由百姓自行调制,既可快节奏蹦嚓蹦嚓,又可慢生活挖挖耳朵;既叫洋人街,又没蓝眼睛。
蔡锷将军策马而过,微笑,刀鞘里拔出吉他:吾当年复国,就为此时!
登苍山
山峰十九,溪流十八,结构成苍山的基本框架。
是云贵高原仰卧起坐,坐成的苍山,海拔四千!
此刻,请许我啰嗦一番,罗列十九峰之大名:云弄、沧浪、五台、莲花、白云、鹤云、三阳、兰峰、雪人、应乐、小岑、中和、龙泉、玉局、马龙、圣应、佛顶、马耳、斜阳!——我的帽子掉了十九回!
可以建立这样的逻辑关系:十九峰的苍山用十八条乳汁,养育了洱海;而洱海敞开她的衣襟,养育了大理。
此刻,我戴好帽子,披起大衣,坐上缆车,登上海拔三千九的洗马潭高地。我要与冷杉、高山杜鹃合影。我要作出巍峨高冷的模样。可以让云雾,一拨又一拨跑来,为我美图。现在,我已成为苍山第二十峰,这毫无疑义。因此我要挺起胸,以一座山峰应有的神态,俯视云雾脚下,那很小的一块大理城;我还要以平和的通情达理的心态,与十九位兄弟聊聊永恒、寂寞与职守,聊聊十八条乳腺的重要与必要。
登苍山的意义,就在于,你要有悲悯情怀,要有乳汁的担当,要冷静,不显露烦恼,把经常掉在地上的帽子捡起来,重新戴回头上;更重要的是,你要感恩,是人民仰卧起坐,偶尔,让你搭了便车,拥有了四千米的海拔。
苍山顶,洗马潭
为来看你,洗马潭,我坐上海拔三千九的索道,再步行登高百米。我要把你这块难得一见的翡翠,放在我砰砰作响的心脏旁边,一起挑战。你应该明白我今天的不易。
我喘气为你拍照。想你,当然比我更加不易,海拔四千,日夜缺氧,连昨夜跑过你身边的狼与白狐都缺氧了,但你纹丝不动,冰清玉洁,谨守自己认定的纯度,不逾矩,不外泄,毫不苟且。
你洗的肯定是一匹玉马、一匹水晶做的马。你冰清玉洁,毫不苟且。
你是西施入吴时怀揣的护身符,你是黛玉葬花时裙边的环佩,你是书画大家案上的镇纸石!——你冰清玉洁,毫不苟且。
此后,哪怕我的操守,在平原缺氧,我也会及时想起海拔四千米的所在,一只银狐,曾经,疲乏地蹲在你身边,舔着自己干净的颜色;一匹水晶做的马,曾在你怀间,清理过亮晶晶的鬃毛;并且相信,一块翡翠、一块安静的镇纸石,能镇住,所有欲望小小的暴乱。
走喜洲古镇
无疑这是统一的:若是你,盛赞了一个白族姑娘“风花雪月”的帽子和服饰,你也必须,盛赞她们的宅居!你要到喜洲来,要看她们的“三滴水门楼”“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要看雕梁画栋、斗拱飞檐、照壁彩装。你要对外乡人积极申请做上门女婿,无丝毫惊讶之情!
还应该,把村口的两棵大榕树,也看作绮丽建筑群的一部分。这是风水树,是喜洲的柱、梁和魂。喜洲商帮哪怕跑得再远,那些“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哪怕跑去东南亚,哪怕买下旧金山的半条街,都也没忘,大树底部,有他们的根须!
他们账本上唯一的亏损,应该,就是乡愁。
我走进杨家院子,相逢白族民族资本家“四中家”之一的杨品相,相逢他那闻名遐迩的“光明商号”;当然,这是神交。现实状况是,这院子,早由一位美国友人经营,现在游客盈门。
我在观景台要了一杯美式咖啡,味道特浓;最后,咂咂嘴巴,就感到了涩。
也好像,大树底部一根细细的根须,塞着了牙缝。
我希望,杨品相始终是这个古镇历史的“光明商号”,而这个古镇的一部分,现在,也是杨品相后人摇扇子的地方。
喜洲农耕文化艺术馆
自古,喜洲重视农耕文化。自古,喜洲商帮就习惯于把赚来的钱,交给家乡的春风,吹成秧田。
喜洲所有的商贸集团,都沉甸甸的,看上去,都是每年金秋饱满的稻穗。
所以,艺术馆就把这句话,放在进门的地方:“土地是一个大写的创造者。”
显然,墙上各式的图片,屋脚各式的农具,都出自土地。民间所有的风俗,都是节气的孩子。
插秧时节的秧官,看他的一身衣服,就是一首诗:蓝裤子是洱海,白色小坎肩是苍山雪,帽穗是风。八角帽上,全是风花雪月。
所以说,喜洲商帮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其实,都是秧官的形象。他们都善于在自己的账本上,用熟练的插秧动作,插下泰铢、卢比、美元、英镑,然后在金秋,验收稻谷、麦穗、蚕豆、菜籽。
这就是中国式的收成:喜洲在自己的土地上,插下商帮;商帮在农耕的理念里,收获喜洲。
这就是我今天的学习体会:喜洲,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农耕文化艺术馆;这样的艺术馆里,应该挤满成片成片的秧苗一样的孩子。
大理饵丝
看上去,跟米线也差不多,吃进嘴里,绝对不一样。米线滑爽,饵丝韧糯。
此刻,我就放下筷子叫了一声:“啊呀,真的带劲!”
年糕一样的饵块,切细了,就是饵丝。但做饵块,就有讲究,要选具有较多直链淀粉的大米,要反复捶打,然后要在案板上,使狠劲,把米团压擀成块;也就是说,要采用百炼成钢的原则!
同样是大米做的,米线就有点速成班的意思,学历经不起检验。
后来我做诗赛的评委,就习惯于把长长短短的诗句,摊在案板上察看,看哪些是米线,哪些是饵丝;然后就指着其中一首,叫一声:“啊呀,真的带劲!”
喜洲粑粑
就是现在,汽车必须停下,必须下车购买。对,就是现在,不要说人,汽车也馋了。
人们都把喜洲粑粑称作“大理的披萨”,不仅可口,而且存在感普遍,连公路边都有大声的叫卖,甜馅的,咸馅的,搁在手心,热烈万分。
一口下去,这么酥软,且层次这么分明,老外的披萨怎么能比!当地人说,这一层层的,其实,不是别的,就是苍山十九峰十八溪!
啥叫秀色可餐,你现在,懂这个成语了吧?
我选甜馅的,味道舒服得像大理;我的牙齿、舌头和味蕾,一起在洱海里荡漾。
听说烤制很讲究,须上下两层炭火,上层猛火,下层文火。面胚刷上猪油之后,又反复刷,烤香,再烤酥,直至烤出苍山十九峰十八溪!
幸亏我来喜洲,有了这份口福,心里充满了对大理热腾腾的爱,一会儿猛火,一会儿文火。
弥苴河
全长22公里,北起普陀泉,南至洱海;两岸绿油油的滇合欢、黄连木,她一路手牵。
仿佛,绿油油的波浪走在河里,也赤脚走在岸上。
谁喊我一声,都看不见我人影,只有树叶替我回答。若是树叶的声音不响亮,鸟儿会赶来补充。
走入弥苴河,就是走入纵深22公里的公园。鸟鸣的袭击,来自四面八方。我一路幸福地中弹。
好几棵树上都挂着这样的牌子:“洱源净、洱海清、大理兴。”于是我知道了,洱海那勺水,为什么总是清冽的;原来,我走的是一条勺柄!
劈面见一棵“霞客树”,树冠好大。徐霞客游记说“其中弥苴佉江似可通大舟”,又说自己“乃复下舟”。这位老徐,是从我们浙江宁海开游的,他就在这里,划上了自己全部游记的句号。
没别的原因,他是太喜欢这里了。我猜想,那年,他肯定也像我一样,刚下舟,在“霞客树”上系紧缆绳,忽尔,就“中弹”倒地了。
茈碧湖
你好啊,茈碧湖,洱海的源头!——洱海的瘦削而安祥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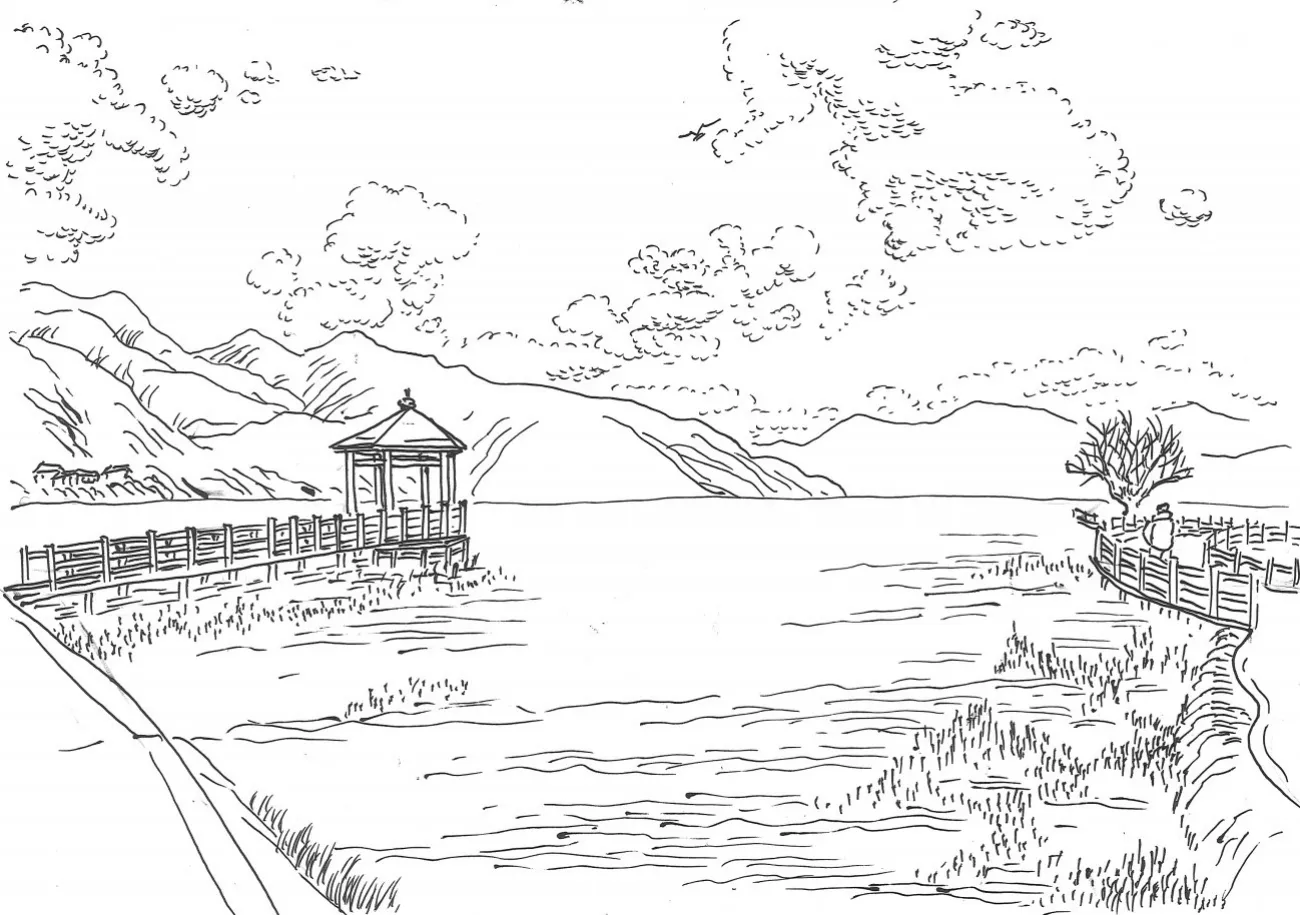
你比我家乡的西湖略大一些,每天,你坐在罴谷山下,用波纹,做着针线活。日子宁静。
也时常放下针线,想起远方的孩子。其实,远方的孩子,也做母亲了,她哺育着大理!
一切的缘由,都是你太清冽了,全域Ⅱ类水质。你指给我看水下森林,我就看见了,叶子上,鱼以鸟的形式生存;你又指给我看草海湿地,我就发现,湿地大片的红荷花都是重瓣的,花形比我家乡西湖的略复杂一些。我知道这湿地的复建,让你特别开心,那么多白云,都能以白鹭的名义降落,让你的透明,更接近天空。
你好啊,茈碧湖,我今日远道来看你,就因为,我红尘过于疲累,生活的外衣,已多有破损。我祈望,在你递给我的木凳上小坐一会,祈望你细腻而安静的针线活,立等可取。
茈碧湖深处的梨园村
梨花季节,那种白天白地的盛景,我没见着,但是看见湖边荷花,纷纷从举伞的荷叶中钻出,向我致意,要求我把她们写到诗中。说她们不输梨花。
但我觉得,大片的浮萍,在波浪中那种不停的立正与稍息,那种悠然的节奏,更见诗意。
其实我看见,整个村子,都是依着这一律动梳妆自己的,头上,遍插花、云和鸟;鞋面,缀满小雏菊、狗尾草和蚂蚱;见我来,立正,见风来,稍息。
我沿着村道逶迤前行。七千株古梨树,以及许多身材绰约的年轻梨树,约好了似的,一起用她们密集的影子,推撞我,仿佛是故意让我,一路醉步。
我在村里用午餐,整村的梨树陪坐。她们,甚至劝我吃得清淡一点,以果蔬为主,以便与村子的节奏,保持高度一致。我还没应答,窗外荷花就一起点头叫好,见我挟一筷,就立正;见我喝一口,就稍息。
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数字体验
你在这个展馆里摸着了剑川,就是摸着了丝绸、瓷器与茶马。
剑川是国家级的驿站。现在,你就通过数字进入了唐宋,进入了明清,进入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喉结。
大屏幕在我的上下左右,布置不同的时空。不同肤色的国家一起转马灯。滇越道、永昌道、灵关道、安南道、天竺道、红水河道,都是马鞭子。
我是最后一个出发的,我牵上了马,牵上了所有的路,牵上茶叶、青瓷、丝绸、中药材。
我走出展馆的时候,没问题,我已经是一个英俊的共和国商帮形象,左胸,佩有党徽。
剑川古城,早街
这条街是明清时期最早醒来的街,是吃早点的街。所有的马帮汉子在这里吃饱肚子,马脖上的铃铛就响起来了,驮在马背上的茶马古道就开始活了,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截就蠕动起来了。
早街就是一根米线。早街上的一个铺子,就是一块粑粑。牵马人互相一吆喝,就满嘴喷着酸辣鱼、羊乳饼、千张肉。
早街一热闹,茶叶、药材、瓷器、香料、布匹,还有叮叮作响的银元,统统跟着热闹了。去蜀都,去西昌,去汉源,去雅安,叮叮当当,一条早街,全都出发了!饱嗝、油腻、酸辣、酱汁、快活的吆喝,全都出发了!
我走在这条街上,一直有饱腹感,脚步也渐重,鞋底敲着石板路发出马蹄的声响。
我忽然希望早街竖起来,做我人生的路标!
我要做一匹早晨的马!
美丽的剑川县石龙村
海拔两千六,马铃薯、玉米与芸豆很适合生长;美丽乡村的荣誉,也适合生长。
猴子也是一种生态的美丽。还没进村寨,就能看见猴子成群。这时候老乡会借你一根木棍,你砰砰一敲地面,所有猴子,立马就守法文明了。
歌声当然就更美丽了。杨丽萍要的白族群众歌手,全是从这个村子挑选的。我今天欣赏的是“龙头三弦”与“石龙霸王鞭”,还有情歌对唱,休止符是双方的媚眼。我甚至觉得所有这些接地气的节目,都应该上央视。
现代民宿也是这个美丽乡村的亮点。我坐在“喜林苑”的玻璃露台上,伸手,就能搂住近处的云南松和远处的青山。猴子幸亏也在远处,没有过来。
唱罢情歌的歌手悄悄告诉我,歌一旦唱完,事也已成功,地点便是村外松林。我虽没听懂一句歌词,但顿然觉得,这个村子,所有的时间与地点,都美丽得要命!
剑川县的县树,是黄连木
我一大早就瞅着一棵树龄六百年的黄连木发愣,如此抱团上升的树干,如此坚韧美丽的叶子!好似大半个天空,都降落在树冠上;它的根系,也几乎团结了整个寨子。
它年轻的时候,当过拴马桩。每天晚上,马帮们都把湿透了的南方丝绸之路,拴在它身上。现在长年岁了,那就不妨,以县树的身份,出任剑川县形象大使;稳重、坚毅、大气,不用走上主席台,就人人鼓掌。
二月的新叶还能食用,降燥热,使人清醒。当然,十月一到,它又准时呈现高度的政治敏感,满树的绛红与橘黄,仿佛,东风在展开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
我在沙溪镇的这个早晨,惊讶地长久地注视着它。
它与它的弟兄们,遍布整个沙溪,也遍布整个剑川。这一刻,我就听见了驮马的响鼻。马帮汉子们一圈一圈解下拴马绳,吆喝一声“上路”,只把这棵树,留给现在的人民政府,作为这个县,一马当先的图腾。
剑川木雕
今日进一家以木雕为主题的餐厅用餐,艺术,突然就从一块木头里冲出,跟我握手。
这才注意到剑川木雕。
副县长告诉我,木头里那么多的姑娘、智者、神仙,脚劲都厉害,已经走遍了一百二十多个国家;还说,看木雕大师的手法,如同看魔术,低浮雕、高浮雕、镂空雕、透通雕,而现在最多的一块木头,已能雕刻到九层。
我的理解是,这不是剑川人对木头的雕琢,而是他们对于生活意义的精准奏刀。
据说,早在唐代,剑川人就擅用雕刀,为南诏五华楼梳妆打扮;到宋代,更厉害,雕匠进京献艺,全国知晓剑川;至于如今,所有具有文化自信、自我感觉良好的木头,都想进入剑川深造,试图千古不朽。
过去我只为家乡的东阳木雕自豪,此刻,我不能不讴歌剑川木雕。
木头,正以转世灵童般的神圣,在中国,选择东阳与剑川这两把刀,脱胎为艺术。
我明白了,今夜,为什么艺术要从木头里伸手,突然握住我,因为,它认出我是浙江人了!
剑川的木头,特认纹路,特认兄弟,特讲究双赢。
剑川火腿
游走大理的日子,我几乎每顿饭都相遇剑川火腿。我自己还没理解是怎么回事,我的筷子已加它为好友,每天互相点赞。
确实满嘴醇香,且后味十足;咸度要低于宣威火腿,更宜入口;当然,也丝毫不逊于我家乡的金华火腿。一头好猪,把自己的后事托付给剑川人,再合适不过。
剑川火腿的首府,应该就是石龙村。这个村的腌制有讲究,对于猪,必选长满一年的“年猪”;至于宰杀,必选小雪节令,因为低气温与高海拔,会让所有细菌都不敢靠近“腌制”这个词汇,而之后的晾晒期与自然醇化期,也有了保证。
上述知识,都是我后来慢慢获知的。至于我的筷子,不加分说,早就与它打成了一片。
我的筷子文化程度不高,只认口感。
沙溪古镇
可以看看,这镇子的区域位置有多么的好:夹在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三大旅游区之间!所以常有人说,看一个人的格局,就看交啥样的朋友!
说实话,这个镇子,唐宋之时就很注意交朋友了,左手茶叶,右手丝绸,跟谁都想加个好友。每年,都用驮马的铜铃,敲响和平的法器。
它是贸易,它是和气生财,它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是有来有往,是大家发财,是南方丝绸之路上,和平咬下的一个线结。
今天,它又来跟我交朋友,那些古戏台、古寺、马店、百年古树、古巷道、寨门,都是它挥动的非常新鲜的花束;甚至,有几句古戏台的唱腔,以露珠的样式,从花瓣上溅出来,溅到我脸上。
就是这样,这个古镇以它苍劲有力的街巷,一笔一划,今日教我待友之道——茶叶、香料、丝绸、青瓷的威力,绝对,胜过子弹与炮管!
途经巍山古城随感
这是谁告诉我的,是自由的风,还是浪漫的鸟,说中国的土司制度在这里特别根深蒂固,这唐代大理南诏政权的发祥地,这元代的古城?
是谁,让我登上城门的楼,伸手,指着砖缝,点数密密麻麻的中国等级制度?
左土司的治巍,整整514年,是云南省承袭土司职位最久的土司府;那么,是谁,让我走在古城安祥的街道上,想象当年青石板上溅起的,是水花,还是血花?
是谁在说,土司做好事不少,为朝廷讨逆,兴办学校?又是谁在说,土皇帝的军队与牢狱,截死了百姓上访的路?
古城的父老乡亲,现在生活得气定神闲。他们仰坐在“露天大碗茶”的竹制靠背椅上。在我的相机前,一群群的,尽作“半躺平”模样,而谁,总是在问我,土司时代的人们,是不是也这样舒心的笑,手里捧一支亮晶晶的水烟筒,每天,看太阳,东城头升起,西城头落下?
是谁,是自由的风,还是浪漫的鸟?
还是我自己,那颗经常要打哆嗦的不安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