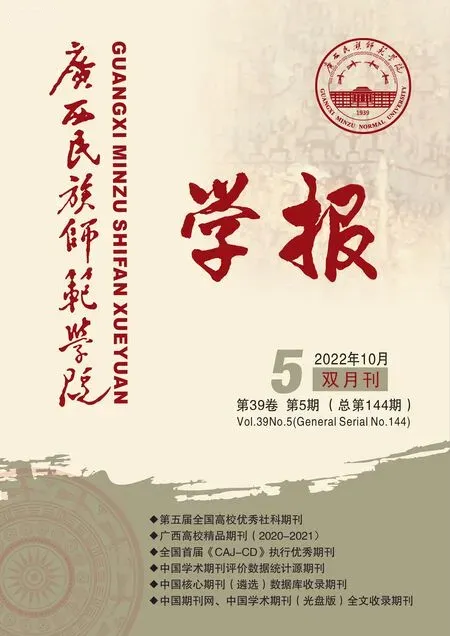力量·限度·神秘
——论朱山坡早期短篇小说的内在特质
郑立峰
(玉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朱山坡从诗歌进入小说创作亦有30多年,他的小说文本创作呈现多维开放性的意蕴,在讲故事上具有恒定的主体意识,彰显个人良好的想象力和精准的语言表达,故事吸引力强,人物性格执拗,以及依靠人的执拗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做到极致,这是一个小说家的本事。朱山坡为小说事业而勤,对小说的创作有“沿着经典去写”①的精神。例如《中国银行》有鲁迅《祝福》的影子,《陪夜的女人》有铁凝的《哦,香雪》的浪漫痕迹,《天色已晚》向《伊豆的舞女》致敬,朱山坡的短篇小说在浪漫主义上驰骋,显示出他卓越的想象力和叙述能力。近年来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广西文学青年文学奖”“林斤澜优秀小说家奖”等都明证了他的小说成就和文学品质。
一、好小说的一个杠杆:文本的力量
首先是朱山坡的小说故事有力量。以朱山坡最经典的短篇小说《灵魂课》为例。《灵魂课》向我们展示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进城的故事,这是小说的主旋律。而笔者更愿意把它阅读为一个有力量的故事:关于灵魂,关于母亲,关于母爱。阅读这个故事,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灵魂叩问:“你相信灵魂吗?”这是阙小安的母亲向“我”的提问,与鲁迅《祝福》关于“灵魂”问答类似,直击读者内心,引发思考:你的灵魂是否还在?(你是否还有良心?)在阙小安的母亲那里,用心来生活、落叶归根,才是老一代农民的理想。阙小安的母亲在米庄生活了近50年,觉得米庄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人死了,灵魂也应该回到米庄。所以她要阙小安落叶归根。而阙小安不然,他不想回到农村,他的理想是在城市买房,娶妻生子,光宗耀祖。《灵魂课》记叙了中国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心理,反映了时代、记录了时代,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阙小安母亲的形象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类似:“她很矮小,却拄着一根比她高出一大截的拐杖,拐杖顶头系着一只半瘪的白色气球,无规则地晃动着;满头脏的白发,面容枯槁,背有点弯了,似乎患了白内障,看我的时候眼睛要靠到我的身上了才把我看清,张嘴说话时口气很臭。嘴里没有像样的牙齿了空洞洞的,身士穿的暗灰色土布衣服沾满了泥污。”[1]252与祥林嫂相同的是,阙小安母亲与祥林嫂一样“落魄”,一样寻找“儿子”,一样具有精神错乱。不同的是,通过阙小安母亲的口吻讲述阙小安的人生和阙小安父亲以及一家人的苦难遭遇,赋予阙小安母亲忍辱负重、悲壮沉重的力量。
具有酒神般的人物形象张力的是《中国银行》中的冯雪花。小说的主人公冯雪花与鲁迅《祝福》的祥林嫂在日常行为上更为接近。冯雪花每天都拿自己的存折到中国银行的柜台咨询氮肥厂退休金发放情况。但是氮肥厂已经倒闭了,早已发不出退休金,冯雪花每天机械、重复地查询和闲聊她看到的事或者曾经经历的事,不断地重复自己女儿的故事。与祥林嫂三番五次喋喋不休地讲“阿毛故事”类似;她取钱2元,存钱8元、取钱8.5元(账户最后只剩下0.3元)的神态又与孔乙己类似。冯雪花没有了积蓄,又希望有积蓄,在希望和绝望中不断反复,导致人物性格扭曲,反复癫狂,直至死亡。朱山坡将悲悯的情怀和作家的批判力,以经典的模式植入自己的短篇,呈现了“经典”形象的力量和文本文脉的传承力。《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与《灵魂课》类似,都是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进城现象。《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的小男人和他死去的表哥的目的是落叶归根,这与《灵魂课》中的阙小安是相反的。《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小男人想把已死的表哥带回家,在回家的汽车(卧铺汽车)上为了掩人耳目,说表哥太累睡着了。邻座姑娘一路上“防狼”般警惕,想象小男人和表哥是“色狼”,小男人不断地“辩解”,最后邻座姑娘发现表哥是死人。小说顿时透露出巨大的悲剧力量:回家悲苦和底层生存的沉重,对不屈服命运抗争的由衷赞美。《陪夜的女人》关注的是乡村孤寡老人的生活,特别是对临终老人的关怀。在当下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境遇里,小说主题的力量获得了崇高的审美张力。正如张燕玲所说:“面对死亡拷问人性与世事的寓言《跟范宏大告别》,其中的临终自我救赎一直延续到《陪夜的女人》幻化成颇具人性的临终关怀……而且通过表达人性,表达人的复杂性,表达乡村新的伦理,表达时代的存在,包括自己内心的感动,显示了作品里的智慧、力量和温暖。”[2]
其次是文本想象的力量。朱山坡小说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和开阔。例如《爸爸,我们去哪里》以一句询问句式“爸爸,我们去哪里”用作小说的题目,这是有难度的。没有想象力营造,无法完成一部小说,文中的“我”不断重复问父亲:“我们去哪里?”父亲总是不回答,他漫无目的地走,就像他的人生一样漫无目的,如果说父亲有目的,那就是离开青梅镇这个村子,没有目的走,在路上遇上抱着小孩的女人——一个去看即将被枪决丈夫的女人。(“我”的母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去世了),作家用不成年的“我”猜想父亲的去处——或许父亲的目的是要去寻找一个女人,给“我”找一个“妈”,所以,当父亲知道了那个抱着小孩的女人是去看死囚丈夫时,表现出积极态度和强烈的助人为乐的精神,印证了“我”的猜想。“爸爸,我们去哪里”?其实是,一个男人寻找生命的意义,为“我”寻找母爱,寻找一个完整的家,这是基于传统文化想象力的开掘。《骑手的最后一战》也体现“家”的文化想象,讲述“我”的父亲(癌症晚期)临终前的故事:一个因贪污入狱而患癌症的“市长”(“我”的父亲),回到旧槐村等死,回到破败的前妻家,见到“垂危”的病马,为了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去训练病马,与前妻重归于好后骑马自杀。这是一出既荒诞又温暖人心的自我救赎故事,通过奇异的想象力,朱山坡构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奇幻故事。在《一个朋友叫李克》里的“我”以为身患绝症(肺癌)就要赴死了,殊不知是好朋友李克导演的一出好戏,用绝症与死亡来导演一出希望之戏,李克之死成就了“我”的理想。李克患癌死了,不是“我”身患绝症,这是一部充满奇异想象的剧本。《小五的车站》虚构的是“我”去外婆家陪外婆过生日的奇异故事。《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讲述了一个老太婆自我想象的“呼救”,揭示了人性中蠢蠢欲动的呼喊,至于呼喊什么只有老太太知道,警官小宋是迷惑的,这是小说想象的怪圈。
最后是文本的语言力量。小说的语言文字表达精确,叙事情景有强烈的碰撞景象,文字叙述产生有力的画面感。例如《骑手的最后一战》中写到“我”父亲回到槐庄,看到自己的前妻养的一匹老马:“一匹又老又瘦的马住在这里。它不断地用舌头舔着嘴唇上的两三个疮,身上长满了癞,苍蝇肆无忌惮地在它的身上安营扎寨,强盗一般的吸着这具干瘪的肌体。妹妹说,妈妈,这匹马快要死了”[1]15。把旧槐庄、前妻、瘦弱的病马,颓废的景象,特别是对马身上的疮的精准描写——苍蝇肆无忌惮趴在马身上吸血的情形,描绘得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没有多余的文字,语言丰盈、具象。在《小五的车站》中作家写“我”从株洲回玉林的遭遇。一开始上火车,遇到了一个肥胖的男人,占据了自己的座位,心里非常烦闷,非常厌恶,形容占座的肥胖男人“那头死猪仍然昂天喷气”[1]140。把占位的男人比喻成死猪,希望他离开座位,想象坐回自己的位置,还要“拂去他的余臭”,可见自己对这个男人的厌恶。与一旁“宽容和仁慈”地抱孩子哺乳女人相较,场景呈现出强烈的对照。下火车时,这个“死猪”还要“调戏”女人,“我”的愤怒到了极点,要冲上去打这个“死猪”。但是,当“我”知道“死猪”是这个女人的丈夫,而且这个“死猪”一样的男人,要带“我”从陆川去玉林的时候,“我”从厌恨变成了认可和崇拜。突然的转变,电影一样逼真的画面感和强烈的对照,情绪矛盾的产生和缓解,审美的雅俗交织,作家处理得游刃有余。采取类似叙述模式的,还有短篇小说《两个棺材匠》《你为什么害怕乳房》《鸟失踪》《响水底》《天堂散》。
二、语言的限度:不轻易说出的话
小说对于人性的探讨是永恒的。人性是什么?夏甄陶在《人是什么》里提到“人的社会存在是人‘作为人’的存在……通过参与社会的活动表现其在社会中的存在,要激发自然潜能,即是他的天资、天赋和理智”[3],也就是关注人的主体感情和理智问题。
朱山坡的短篇小说在人性的叙事上是大胆又不失理性的。在《爸爸,我们去哪里》里有这样的描写:“女人矮小丰满,面容姣好,短发,花格薄衬衣,怀里的孩子看上去约莫只有一岁多点,胎毛还没有脱干净,瘦瘦的,脸色有点蜡黄,好像永远也吃不饱,小嘴一直要吮着母亲的乳房,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始终有一只洁白的乳房半裸在我们面前。孩子睡着了,女人也在打盹,粉红的奶头挣脱了孩子的嘴,涓细的乳汁顺着他的脸流下来,白色的,除了招来几只苍蝇,还加剧了我的饥饿,我从袋子里掏出一只南瓜饼,独自啃起来。”[1]1这里朱山坡对女人在公共场所哺乳的描写是大胆的,直白呈现袒露乳房喂食小孩的情形,没有修饰,没有遮掩。他大胆地描绘着乡村的日常行为,但非常克制自我。饥饿感产生,于是“我”也掏出南瓜饼来吃。这个场面非常自然,看到孩子吸食乳汁,“我”也饿了。作家的描写表现了人对欲望的克制,把“性”的提示压制在“食”下。
《小五的车站》中写道:“在我的眼里,世界上最陌生、最新鲜的东西便是喷着新鲜乳汁的乳房。女人朝我看了一眼。我躲闪着把目光朝向窗外。窗外一点也不好看。”[1]141一样的裸露乳房,但是这一次“我”没有找食物来代替“性”冲动的提示,而是“我”不好意思再看,其实“我”是想看,所以作家来一句“窗外一点也不好看”。这里把“我”想看又不好意思看的矛盾心理全盘托出。作家对“我”的性欲的表达是非常内敛的,但是在有限的叙事中已经敞开了人性的欲望。这是自我主体性的狂欢。“我”是否喜欢这个女人?她又是否喜欢“我”?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诚然,作家对“我”的人性设置是理性的,主人公把这个女人想象为自己的姐姐,抑制了性的欲望。把荒谬的性冲动巧妙地掩饰起来。
那些没有说出因“性”而带来紧张状态的人性话题,作家在《天堂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的开始是一家人在吃饭,突然来了一个女人(唐洁美),一个从乡下带着黄瓜给“我”们家的女人,“我”的母亲对此非常警惕,“我”的父亲也非常紧张。母亲警惕的是这个女人是不是与自己的老公有什么感情纠葛。父亲(郭宏海)紧张的是:“我”与这个女人“暧昧”过吗?她是自己插队石榴村时遇到的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只是爱听自己讲故事,与自己没有感情啊?这是关于“性”引起的紧张。但是,女人(唐洁美)明确地说了,她从乡下来城里,是来完成一个心愿,即听“我”父亲讲完《天堂散》故事。于是乎所有疑虑都被打消了,故事发展下去,是“我”的父亲(郭宏海)与女人(唐洁美)私奔至“人间天堂”的杭州,共同完成小说《天堂散》。《天堂散》一时成为登上热销排行榜的书,“我”也因改编此书成名。其实,这个小说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利用两性间的情感张力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两个心灵相通的人,注定在一起。因情感相吸的强大理由,让一个有三个小孩的母亲离家出走,并与父亲(郭宏海)私奔。即使私奔被丈夫、孩子、村里人知道也义无反顾。“我”母亲接纳唐洁美,留唐洁美在家过夜七天,让父亲单独与女人在家讲故事,让父亲和这个女人有接触的可能。当父亲与女人有了“性”的接触之后,决定用行动来践行《天堂散》。他发生了两极变化:先前对于母亲的发号施令无不遵从,但女人到来第七天之后,他躺在沙发上,对母亲的叫唤不理睬。最后以低沉而认真的语调回答母亲:“从明天起,我要继续写《天堂散》。”[1]47从此父亲失踪,他先是到苏州,再迂回到杭州与女人会合,共同创作小说《天堂散》。朱山坡不露声色,对两人(郭宏海、唐洁美)的情感描写有限,避开感情的发展与爆发,依托两人对《天堂散》的痴迷,或者是《天堂散》里的爱情,又或者是没有说来的话——两人情感相吸的理由,小说的结尾自然而然让这两人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作家精巧的设计,在有限的叙事中说明人性中的理所当然。
三、故事的吸引力:神秘的意象
朱山坡的小说好读,让人越读越喜欢,具体地说就是故事有吸引力。朱山坡短篇小说的魅力,主要源自神秘。邱华栋曾说:“朱山坡小说的气质,是简洁有力的,生猛的,接地气的,”让他有一种在混沌世界中开辟光明天地的勇气。”朱山坡小说里的这种狠劲儿,“使得小说内部在叙述上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使他的小说耐读、惊悚,一种诡异的气氛弥漫其间”[4]。这非常准确地诠释了朱山坡小说创作的特征。邱华栋在这里面,提到的“混沌”“惊悚、诡异”,就是小说中的神秘,与广西的地理文化特征相关,往往与“巫气”相联,是朱山坡小说的地理文化属性,是浑然天成的。
《灵魂课》是朱山坡的经典之作,主要讲述了一个精神失常的老太太(阙小安母亲)步行到城市寻找自己儿子(阙小安)灵魂的故事。小说以描绘一间骨灰存放“客栈”开始,营造阴森诡异的景象。老太太的神秘之处,一是行为诡异,二是语言诡异。她来寻阙小安的骨灰盒,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根本就没有阙小安这个名字或者编号。但是她来到存放骨灰的架子,就直接伸手去9号存放处。她说她儿子的骨灰盒就在这里,现在不见了。好像骨灰盒是她放在这里似的,她准确说出来。其实9号存放处是否存在,“我”这个寿衣店的管理员也不知道。老太太拿出照片让“我”带她去寻找儿子。可“我”根本就不认识阙小安,现在变成灰了,更加不知道如何找了。老人有点生气:“你怎么不相信呢?我儿子的灵魂在哪里我知道的,等到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寺到你的儿子死了,你也会知道的……”[1]255(在老板娘的要求下)“我”只能带她去他儿子曾经去过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要召唤自己儿子回家。诡异的是她儿子并没有死,死的是堂弟阙小飞。老太太生病了。她儿子阙小安说:“死的是阙小飞,不是我。”但是老太太还是不相信。半年后,老太太再拿了一个骨灰盒过来,这次真是阙小安死了,老人说:“摔死了,粉身碎骨,魂飞魄散……他不愿意回家,死活要留在城里,就让他留在城里吧,反正他的灵魂我也带不回去”[1]267。还吩咐“我”把10号的骨灰存放处留给她,她要来陪她儿子,故事在惊悚中结束。
《陪夜的女人》与《灵魂课》同属一种神秘的叙事结构。陪夜的女人到凤庄去陪临终的方正德老人。老人说话声若纤蚊,还有一些沙哑。厚生的儿子说:“我阿公就在床上”“他就习惯这样,白天睡觉,晚上扰人”。每每到了晚上,老人就张开眼睛,张开嘴巴大声地喊:“李文娟、李文娟……”“有两三个月了吧,老人每天晚上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呼喊着李文娟,差不多每隔一分钟便叫一次,把凤庄喊得鸡犬不宁,没有人能睡上一个好觉”[1]273。恐怖的氛围萦绕凤庄,让人毛骨悚然。《鸟失踪》也一样,小说讲述了一个年老体弱、面目全非的父亲,为寻找30年前失踪的大儿子,独自一人跑出去了。“我”听说父亲失踪了,去寻找,遇见猎户,猎户往背后指了指说“他就是往南跑的,像飞一样”[1]36。然后像鸟一样神秘失踪了。《回头客》也一样。神秘乞讨男人得到了恩惠,于是来蒲庄,给每户人家做一件家具作为回报,但是蒲庄人以为神秘男人还有别的祈求,处处提防这个男人,神秘氛围笼罩蒲庄。
朱山坡小说作品的神秘氛围是通过意象来营造的,注重文本的意象塑造是朱山坡叙事的重要内在的特征之一。由诗歌创作而进入小说创作的朱山坡,将意象思维接入小说创作,是为了扩张小说叙事的容量和小说意味链接。《灵魂课》里千年古井能照出人的灵魂,这是饮水思源落叶归根的意识的写照,白色气球意味着无处安放的灵魂,对于民工阙小安、阙小飞之类,还有老人的灵魂在城市里是无处安放的;《鸟失踪》里的“鸟”寓意晚年的父亲要自由飞翔。还有《天堂散》里的“天堂”,作家究竟是写爱情的天堂还是生活的天堂?
最后是小说的标题的神秘。我们在看朱山坡的小说题目时,往往感觉到一种诱惑,一种暗示性的鬼魅。例如《陪夜的女人》《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你为什么害怕乳房》,乍一看是一部部通俗社会世情小说,其实不然,它们非常严肃。《陪夜的女人》关注的是乡村孤寡老人的临终大事,《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讲述的是农民工进城的艰难,《你为什么害怕乳房》深层次挖掘人性中爱不相聚的悖论。《爸爸,我们去哪里》《骑手的最后一战》《回头客》是同属一种结构,用叙事的圈套和语言的力量来纠正我们对虚无、坚决、勇猛人性的理解。
朱山坡早期的短篇小说,在地域文化的规范中发掘了神秘力量,他以奇异丰富的想象虚构了粤桂边陲小镇的斑驳和人性中的美与丑的异质,提升了小说文本的力量,用精准诗意化的语言有限的描写,创造了内涵丰富的文本,为当代短篇小说叙事多义性提供了范式。
注释:
①朱山坡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创作理想时,提到“向着经典,淡定地写”(见中国作家网2018年10月6日文章《朱山坡:向着精典,淡定地写》。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1006/c404030-30326046.html.);在2012年第3期《语文教研与研究》(下旬刊)《作家活在经典里》中也谈到“为经典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