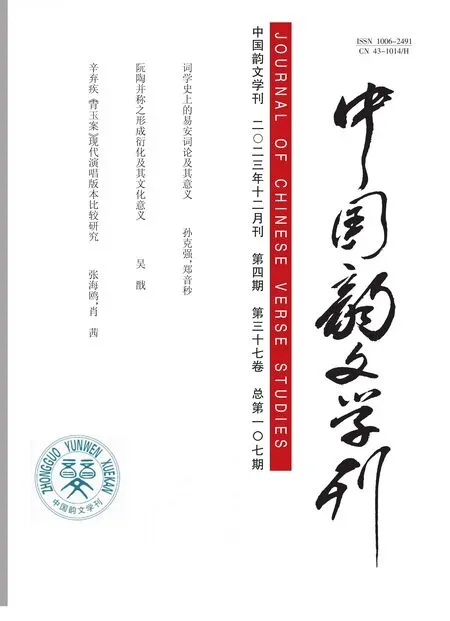“手变秀水派”:金德瑛诗派地位平议
姚 晨,李剑波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秀水诗派是清代前中期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深度参与了清代诗坛的发展走向。目前学界对秀水诗派的整体研究稍显薄弱,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大体仍因循钱仲联先生《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严迪昌先生《清诗史》中的相关论述。关于秀水诗派的渊源,严先生认为:“此诗派上限只能断自金德瑛一辈,与朱彝尊无涉。朱竹垞与‘秀水派’的分野应以对黄山谷诗的好尚与否为准绳。”[1](P804)并援引金蓉镜的说法,认为金德瑛因“善用涪翁”而“手变秀水”,为诗派之开山。这一提法得到当前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由此可见,金德瑛的诗学宗尚与秀水诗派的渊源、发展密切相关,具备进一步研究的价值与必要性。笔者兹就金德瑛与秀水派之关系,以及金氏于诗派之地位,略加探讨,就正方家。
一 “手变秀水”之由来
金德瑛(1701—1762),字汝白,号桧门,浙江仁和人。康熙五十八年(1719)婚配秀水汪绍焻长女,两年后遂即迁居秀水。金德瑛为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状元,仕途畅达,屡次出任学政、典试地方,官至礼部侍郎、左都御史,有诗集《诗存》传世。
严迪昌先生关于金德瑛的诗史定位,主要依据王昶《蒲褐山房诗话》、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以及金德瑛后人金衍宗、金蓉镜的相关论述。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总宪酷嗜涪翁,故论诗以清新刻削、酸寒瘦涩为能。于同乡最爱钱君坤一。督学江西,识拔蒋君心余于诸生中,而汪子康古其戚也。”[2](P18)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萚石斋论诗,取径西江,去其粗豪,而出之以奥折。用意必深微,用笔必拗折,用字必古艳,力追险涩,绝去笔墨畦径。金桧门总宪名辈较先,论诗与相合。”[3](P467-468)
金衍宗《重游泮宫诗》其二:“敢夸诗是吾家事,浙派还分秀水支。继此钱汪皆后起,除惟张蒋乏真知。”诗下自注云:“秀水派推钱、汪、王、万诸君,实先公为之倡。先公诗惟蒋辛畬太史、张瘦铜中书得其传,余无知者。”[4](P670)
金蓉镜《读豫章集赋呈乙公》云:“先公所师妙有绪。”诗下自注云:“《桧门诗存》多学山谷,同时萚石、又辛继之,遂别衍为秀水派。”[5](卷一)
《论诗绝句寄李审言》之十一:“先公手变秀州派,善用涪翁便契真。”诗下自注云:“竹垞不喜涪翁,先公首学涪翁,遂变秀水派。萚石、梓庐、柘坡、丁辛、襄七皆以生硬为宗。”[5](卷二)
梳理四人所言:金德瑛诗歌宗奉黄庭坚,形成自身“清新刻削、酸寒瘦涩”的诗歌风貌;且于秀水诗人中率先学习山谷,于钱载、王又曾等人为先驱,遂开秀水一派。而秀水派所以别立于浙派者,也正在于对黄庭坚诗风的学习;两派分野,即严迪昌先生所言之“对黄山谷诗的好尚与否”。至于王昶、徐世昌所言之“于同乡最爱钱君坤一”,“金桧门总宪名辈较先,论诗与相合”等语,因了金衍宗、金蓉镜的大声疾呼,也自然被理解为金德瑛在诗学上对钱载的引导和提携;而这样的理解又因为金德瑛被尊为诗派开山的缘故而显得合情合理。
但问题在于,在前人以及前辈学人对金德瑛诗歌的评价中,不难找出一些破绽来。金衍宗本人对王昶的评语即颇有微词,前引《重游泮宫》诗注又云:“王兰泉少寇《蒲褐山房诗话》论先公及萚石诗尤可怪。”[4](P670)《蒲褐山房诗话》分别就金德瑛的诗学宗尚、诗歌风貌、诗学影响作出评价,金衍宗认为“尤可怪”者,显系指王昶关于金德瑛论诗“以清新刻削、酸寒瘦涩为能”的断语。此外,更有与上述四人所论龃龉难合的表述。钱陈群《金桧门总宪〈诗存〉序》作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序云:“先生为人醇古澹泊,宋元人中,尤爱东坡、梅溪、遗山、曼硕诸家,故其所作往往相近。”金德瑛移居秀水后,与钱陈群交游甚密,“往复过从”。钱陈群自言于嘉兴初识金德瑛:“予一见以国士遇之,先生亦心重予,引为知己……后先生每言师友中交契最深者,必举松泉与予。”[6](P379)二人分属同乡,又同朝多年,“知己”“交契”之言,绝非虚语。但钱陈群所作序言论及金德瑛诗学宗尚时,丝毫未提黄庭坚,颇为可怪。钱锺书先生《谈艺录》论述蒋士铨诗学渊源时说道:“心余举主师金桧门学山谷诗,《湖海诗传》谓心余诗学山谷。”但之后补订云:“金桧门德瑛诗学山谷,乃王述庵《湖海诗传》之说。余得《桧门诗存》观之,方知王氏臆必也。”并引金诗《锦屏山归途戏语心余》为例:“见此等篇什即附会其作诗学山谷,则矮人之观场也。”[7](P356)细究可知:钱先生最初亦据王昶成说,认定金德瑛诗学山谷;待得《诗存》观之,躬身入局,即颇悔前说,对王昶遂多贬词。百年之下,仍可发一哂。
那么,现在问题就聚焦到金德瑛诗歌是否宗奉山谷上来:金氏后人标榜乃祖为秀水开山的主要依据,就在于认定金德瑛诗学山谷,且首学山谷。而钱陈群和钱锺书先生的论述,不啻若釜底抽薪,对金德瑛的诗史定位具有颠覆性的潜能。钱锺书先生曾指出前人诗歌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倾向:“翁覃溪之流似只读论诗文之语,而不读所论之诗文与夫论者自作之诗文,终不免佣耳赁目耳。”[7](P412)虽或不免诛心,失之苛刻;但闻者足戒,发人深省。而先生关于金德瑛诗学倾向的批评实践,更足以启发我们:对于探讨金德瑛是否宗奉山谷,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诗学问题,都必须从对金氏诗歌创作实际的考察出发。
二 诗宗韩苏之创作情实
目前学界论述金德瑛诗宗山谷时,多以《蒲褐山房诗话》所言为口实:“总宪酷嗜涪翁,故论诗以清新刻削、酸寒瘦涩为能。”对此,金氏后人已经明言:“王兰泉少司寇《蒲褐山房诗话》论先公诗尤可怪。”笔者仔细爬梳金氏《诗存》,亦发现王昶所言实不足为凭。乾隆六年(1741),金德瑛以不惑之龄出任江西学政,至此始潜心于诗:“予四十后始刻意篇什,手录汉、魏、唐、宋人诗数本,荟萃研究、贯穿裁择者且十载,于是豁然领悟古人诗法,知所取舍。”[8](P2000)就其总体诗学倾向而言,以宗尚韩愈、苏轼为主,在诗作中再三致意。诗风或雄壮健朗,或流利自然,绝非王昶所谓“酷嗜涪翁”“清新刻削、酸寒瘦涩”。
金德瑛对韩愈的推崇首先源于对其立身大节的敬仰。乾隆六年(1741)与李绂典试江南作《叠韵再呈临川先生》,其三有句云:“北斗声名达赤墀,昌黎端合抗颜师。群儿誉毁缘何事,万古江河自有时。”[9](P298)诗人于此以韩愈相比,表达对李绂这位翰林前辈、清流领袖的仰慕:韩愈不顾流俗,抗颜为师,自是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纵有撼树蚍蜉无端诋毁,但却无法动摇韩愈如万古江河般的崇高地位。
与韩愈同题之作《秋怀十首》作于乾隆十一年(1746),其四云:
昔者昌黎公,古道傲无比。
俯视一世人,郊贺反借齿。
王伾叔文徒,炙手薰帝里。
八司马奇才,趋骛如流水。
刘柳本厚交,独自异途轨。
身败万事裂,悔心洞骨髓。
老赴廷凑军,远贬潮泷鄙。
到今垂斗杓,瞻仰足犹跂。
假如一不慎,千载事已矣。
香山名鸡林,毕生乐杯酾。
文章或相轾,志行毋乃似。[9](P305)
贞元、元和之际,彬彬复盛,惊才绝艳,号为得人。金德瑛执笔臧否前贤,月旦文坛:孟郊、李贺,本出韩愈,借齿生辉。刘禹锡、柳宗元与韩愈厚交而异轨,终于事败而心悔。白居易较之韩愈,文学成就或可轩轾,但志行出处却大相径庭。唯独韩愈古道傲岸,冠绝当世。“老赴廷凑军,远贬潮泷鄙”,正本苏轼所言“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取其意而直述其事,高度概括出韩愈一生志节功业所在,并再次直言对韩愈伟岸人格的敬仰:“到今垂斗杓,瞻仰足犹跂。”

再如乾隆十八年(1753)金氏于山东学政任作《锦屏山归途戏语心余》,其二云:
韩公所著山石诗,其山何名竟不知。
山红涧碧松枥大,寻常岩壑亦遇之。
匆匆看画饭粗粝,暮而宿兮朝而辞。
岂其泰山北斗笔,不暇刻画穷幽姿。
故知凌空发意趣,气挟凡境皆环奇。
纷纷苦学鲍谢体,刻舟求剑将毋痴。[9](P331-332)
此诗前六句敷演《山石》成章,以文为诗的散文化笔法十分明显。诗材、笔法取法韩愈,一目了然;更须注意的是,诗人尝试从精神上去体悟韩诗所蕴藏的诗家三昧:游无名之山,睹寻常之景,本无足称道;至于观画进餐,暮宿朝辞,更是再普通不过的游览经历;而韩愈独能妙笔生花,化腐朽为神奇,成千古名篇。个中缘由,在金德瑛看来,正在于作者主体具有“凌空意趣”,挟此以往,便有如椽巨笔,挥洒淋漓,任是凡境,皆成雄奇。至于操觚之士,苦学鲍谢,“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穷形尽相以求幽姿,斤斤派别家数之论,毋乃刻舟求剑,终成楚人之愚。故知《晚晴簃诗汇》所云:“其《游锦屏山与蒋心余诗》云:‘故知凌空发意趣,气挟凡境皆环奇。’盖自道得江山之助也。”[3](P354)乃皮相之论,不足为信。
金德瑛所论韩诗胜在“凌空意趣”,不仅是长期学习、体悟韩诗的有得之言,同时也是对其创作经验的自我总结。事实上,金德瑛取法韩愈,正是重在吸收韩诗中的雄壮健朗之风,以及以文为诗的散文化笔法。
金德瑛在诗歌中屡屡直言,以“寒声”相戒,倡导雄壮诗风。如《漱玉亭》诗以李白与苏轼发起议论:“天生一双剑,万古摩青濛。唯有二诗人,浩气斗清雄。相戒后来士,慎勿号寒虫。”[9](P310)《丁卯八月阅心余闱书,和其闱中望月四绝句》其一称赞蒋士铨道:“卷里朝霞秀可餐,峥嵘气象扫郊寒。知君早有凌云兴,不作寻常月色看。”[9](P310)《送沈椒园侍御之登莱青观察任》勉励同僚宜用心揣摩取法杜甫、韩愈、苏轼三人的雄阔诗风,并参以江山之助,成碧海鱼龙之雄壮诗境:“韩之衡岳苏海市,豪厘虚实皆天工。勉将精诣追古昔,莫以伪体惊儿童。君昔南池著骚曲,千载事溯杜陵翁。七真方外虽诞幻,游眺亦足开心胸。蕃宣归时携一卷,示我碧浪翻鱼龙。”[9](P315)
《诗存》中如《康郎山功臣庙歌》《登云龙山放鹤亭见黄河北徙》诸作,皆气象开阔,音情雄壮。如后者云:“云龙头角孤岧峣,众山青翠来相朝。黄河猛迅山亦避,独缺西面容滔滔。嵩室汴洛二千里,郁郁气象连平皋。”[9](P345)诸多纪游、题画篇什,亦时逢壮语,顿见精彩,有鲸鱼碧海之妙。如《蓬莱阁观海》云:“丹崖如虎踞,毒龙不敢吞。杰阁翼以观,如凤凌风骞。五城十二楼,焉用夸昆仑。但见潮与汐,浩浩奔流浑。”[9](P328)《题沈椒园观察〈劳山吟眺图〉》云:“芒鞋无缘径路绝,恰藉按部穷岩坳。金刚崱屴玉女睇,凤凰翱翥狮虎虓。崇峦窅穴明复晦,倒根插濯粘天涛。”[9](P328-329)而王昶却认为金德瑛“论诗以清新刻削、酸寒瘦涩为能”,无怪金衍宗对此颇为不满:“王兰泉少寇《蒲褐山房诗话》论先公及萚石诗尤可怪。”
至于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在金德瑛古体长篇中,更是俯拾即是。其任江西学政期间所作《游麻姑山》《八月十七夜建昌万年桥玩月》《游青原山》诸纪游篇什,直笔铺陈,纯用赋法,于凡境中攫取诗材。不唯章法铺排宛如游记,行文用语亦多以散文化的句法,如《游麻姑山》云:
昭武三月试士毕,太守导我访麻姑。
兹山近郭十里许,瀑布胜绝如匡庐。
春云渰渰春雨织,彳亍泥泞烦舆徒。
谷口一径何谽谺,原中千亩皆膏腴。
山巅地势平于掌,灵泉沾溉旱不枯。
青枫翠栎耸苍蔚,玉柱银房半榛芜。
当年鸾鹤翔何处,松风吹落空中竽。
客当憩息雨亦止,会仙桥上开行厨。
泉声吼出坐席底,倒溅飞沫沾盘盂。
滂然陡下一千尺,怒挟乱石群龙趋……[9](P300)
诗作以出游缘由起笔,将入山、登山、野餐之事逐层展开,并以粗笔勾勒所见之景,不甚雕琢刻画,以议论述怀作结。章法结构,俨然与《山石》同貌;而字句散化之间,亦深得以文为诗之法。篇中“谷口”六句,以偶句为撑拄,较之《山石》一气之下,工整之余,稍显力弱。这自然是诗人主体才力的差别,但瓣香所在,确属韩愈无疑。
在韩愈之外,金德瑛对苏轼的学习也十分引人注目。与对韩愈的一再推崇、敬仰不同,诗人对苏轼表现出更多的亲近感。于江西初识蒋士铨,即以欧阳修、苏轼师生之谊为喻,表达对门生的期许:“吁嗟古道不可作,六一曾誉东坡仙。绝尘逸足世罕觏,嗜好异代知同然。”[9](P303)督学建昌,亦以苏轼勉励士子:“天缘倘莫吝,俗士宁与争。世间太白死,亦有东坡生。”[9](P305)持节衡文,使车四至,于苏轼旧游之地必有题咏,以求神交。如于徐州登临怀古:“猛士诗人楼九日,羽衣吹笛月三更。”[9](P298)于江西游庐山三峡桥、漱玉亭:“及乎泄地时,子瞻极形容。劈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9](P310)于山东观览海市奇景:“值我有求神弗应,令人不敢信苏公。”[9](P328)生平辗转,亦多次援引苏轼以自况。《行状》记其视学山东时,“学使署临大明湖,虚白千顷,倒衔鹊华诸峰,葭蒲菡萏,渔歌菱唱,宛如江乡。公月夜泛小舟,携诗人酒客,演漾历亭芳屿间,自谓不减羽衣黄楼吹笛时也”。甚至直至生命的尽头,仍对苏轼念念不忘:“癯瘠日形,气力微薄,而目光奕奕,心神清明。友朋存问者,每为关问他事,至家庭琐屑,不及一语,唯三复坡诗云:‘我是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8](P2286-2288)钱陈群在论述金德瑛诗学宗尚时,于宋元人中举苏轼为先,并指明金氏是由人格而诗学的全方位靠拢:“先生为人醇古澹泊,宋元人中,尤爱东坡、梅溪、遗山、曼硕诸家,故其所作往往相近。”较之王昶所言,庶几近乎金氏诗法真相。
金德瑛不唯诗酒唱酬时屡用苏诗原韵相赠答;在诗歌创作中,取法苏轼的痕迹亦随处可见。如《同年王介眉下第后,出〈月下观潮图〉索题》一诗,“与君罗刹江边住,似神而非见无数。”命意、造境即本于苏轼《游金山寺》:“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压缩苏诗四句成章,而江中所见神异之景,也就作为深层文意被叠于句中。“何用射之夸吾能,振衣抱膝白眼横。”[9](P314)句法即本于苏轼《石苍舒醉墨堂》:“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晓憩圆津庵示灿一上人》一诗颈联云:“来去今中多著句,马牛风外一逃禅。”[9](P354)对苏诗《过永乐文长老已卒》的模仿之意,更是显而易见。
金诗对苏轼的学习集中体现在五、七言古诗和七律中。其古体纪游诗比喻新颖,用语自然,状物委曲详尽。如《游麻姑山,出谷未晡,续作从姑之游》描述麻姑山两石对峙所形成的一线天:“疑是当年次仲翮,两岸裂堕中存天。又疑仙人承露盘,一茎袅袅当空悬。廊房嵌入岩下窦,雨点不打僧檐端。有时罡风一吹动,便欲摇曳开云烟。”[9](P301)连用比喻,想象奇特,文势流利,明快自然,诗人思致与神奇石势相得益彰。《三峡桥》描绘庐山栖贤谷水势云:“水无一寸直,石作千重墉。遂令至刚物,长受至柔攻。射之不可透,激散乃飞空。”[9](P309)于前人之作外自出新意,不用比兴,纯是赋法,充分发挥语言的表现力,极力描摹峡谷水势。
金德瑛七律对苏轼的学习,主要表现为中间两联对仗工整新颖,并且在字面对偶之外,尤其注重上下联意脉之间的流动之势,寓单行散笔于骈偶中,于整饬中见流利。赵翼认为苏轼七律最可称道之作:“乃是称心而出,不假雕饰,自然意味悠长;即使事处,亦随其意之所欲出,而无牵合之迹。”如:“倦客再游今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请看行路无从涕,尽是当年不忍欺。”“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11](174)
金德瑛七律中尤多此种作法,如《江州》:“即今膏泽沦肌久,犹见田园半郭平。”[9](P302)《蒲州道中送涂石溪、周石帆别各一首》:“马首向西数百里,春风吹绿十三陵。”[9](P325)《保定守王蔗村饷龙井茶赋谢》:“一烹秋水旗枪小,尚觉春云态度存。”[9](P351)尤其以《十月朔,宿石陂街逆旅,主人出画卷求题》最为典型,诗云:
昔来戊午今庚午,中隔庚申作画年。
纸上蒲帆原不动,人如飞鸟却飘然。
凉风木叶声萧瑟,茅舍山桥路折旋。
老去东坡还好事,烟江叠嶂赋新篇。[9](P320)
此诗作于乾隆十五年(1750)典试福州后返京途中。首联两句以拙笔散句写起,暗暗打入人生仓促之感。颔联出句“原不动”三字以貌似无理之语,在视点转换之间,更加凸显出个体生命的飘零,诗思奇特,对仗工巧,语势连贯。前四句一气盘旋而下,颈联则直摹画作,以工对收束文势,结以尾联引苏轼自况。不唯颔联对仗流动自然规模东坡,全诗章法也明显有苏轼《和子由渑池怀古》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七律地负海涵,堂庑特大,尽得古今体势;而金德瑛出于对上文所言七律对仗样式的偏爱,于杜诗所取,亦在于此。《到建昌五叠韵》颔联云:“欲携刺史龙鸾笔,来访仙人锦绣衣。”[9](P304)《壁间杂画蔬果酒尊竹石,是坤一于丁卯随司寇时游戏也,率题长句以代书款》颈联云:“远携彭泽篱边酒,来采云卿圃里蔬。”[9](P343)这对杜甫《望岳》颔联的模仿是十分明显的:“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杜诗详注》于《望岳》诗后引黄生语曰:“‘玉女洗头盆’五字本俗,先用仙人九节杖引起,能化俗为妍,而句法更觉森挺,真有掷米丹砂之巧。”[12](P407)金德瑛必有意于此。桧门《蓬莱阁观海》有句云:“世间惟阳乌,至大莫与尊。东瀛几万里,只作洗头盆。”[9](P328)亦可见出金氏对杜甫《望岳》一诗之偏爱,故对其中语词亦爱屋及乌,兼而取之。
三 学黄转向与诗派之关系
如上文所述,金德瑛论诗可谓“酷嗜韩、苏”,其诗歌风格亦向韩愈、苏轼靠拢,或雄壮健朗,或流利自然。但在其身后,亦颇有以黄庭坚相推许者。如门生蒋士铨《金桧门先生遗诗后序》总结乃师诗作云:“无不扫除窠臼,结构性真,顿挫淋漓,直达所见,出入韩杜苏黄间。”[8](P2001)钱载《左都御史金先生挽词二首》亦云:“诗篇黄鲁直,著处见摅诚。”[13](P388)这些赞誉之辞很容易与王昶所称“酷嗜涪翁”相混淆,使得对金德瑛诗史地位的辨析,又回到“先公手变秀水派,善用涪翁便契真”这样的圈子里来。但实际上,承认金氏诗学山谷,与对其总体诗风以韩、苏为主的推论并不矛盾。据笔者考察,金德瑛诗作确实有师法黄庭坚的成分。但值得关注的是,其诗学山谷的时间节点,已经是乾隆十八年(1753)视学山东期间。金德瑛在这一时期的创作集中体现出诗学兴趣向黄庭坚的靠拢。
金氏此期诗歌编录于《诗存》卷三,有诗《古镜一枚,血皴,成僧披袈裟坐石像,名曰达摩影》云:
片苇只履自往来,十二时偈空疑猜,血皴神凝奚为哉?
堕地七步人天敬,恒星夜伏清如镜,孙诃饲犬祖心映。
呼负局翁磨拭净,嵩颓花灭五叶静,当前一语廓无圣。[9](P331)
此诗三句一转,逐句押韵,然而六七句间换意不换韵。黄庭坚《观伯时画马》诗云:“仪鸾供帐饕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菣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14](P97)《苕溪渔隐丛话》评曰:“此格,《禁脔》谓之促句换韵,其法三句一换韵,三叠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15](P330)山谷此格人少用之,金氏《古镜》诗则系取法山谷的同类之作:逐句押韵,三句一换韵,三叠而止;所不同者,止在二三叠之间换意不换韵。而有意打破换意与换韵之间的和谐,又系山谷常法,如《送范德孺知庆州》之类。二三叠之间意韵参差,金德瑛或有意为之;但全诗章法布局,明显承自山谷。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一云:“山谷七古,三句一换韵,三叠而止,谓之促句换韵,即禁脔格也。今人仿之,若于三叠之外多用韵,便失初格。”[16](P878)明确指出此种诗格仿自山谷。
再如《锦屏山归途戏语心余》其一云:
其出如泉波如天,蓬莱海外诗谪仙。
山行水立自颠倒,石牛洞中风格老。
奇外出奇见豫章,峨眉竞秀各一方。
锦屏山石拗几摺,仿佛谷诗镵天立。
摺如累堵危当中,半侧不倒欺罡风。
乌鸦白鸽翩翻出,树梢岩空安巢窟。[9](P331)
钱锺书先生认为不可据此即附会金德瑛诗学山谷,但金氏于此确实已经透露出对山谷诗风推崇和有意取法的消息。在金德瑛看来,山谷诗歌造诣所在,正在于奇外出奇,凭此可与苏诗平分秋色,竞秀一方。“锦屏山石”句以诗喻山,造语新警,纯是山谷笔法,深得以人喻物之意:“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章法上亦有意求新出奇,逐句用韵,两句一换。此种作法既非常见格式,在《诗存》中也没有先例,求新求异的意味非常明显。作者之意,正在于将诗歌形式的新奇与内容中对山谷“奇外出奇”诗风的体认达成一致。
再如《张氏漪园率笔》其二云:“红鱼白鱼数十尾,方池戢戢游千里。”[9](P332)此诗所用“鱼千里”正是山谷诗中著名的惯用典故,这同样也可视为金德瑛此期用心山谷的一例旁证。此外,金氏于乾隆十八年(1753)所作诗章,皆一改前貌,形式上极力生新的意图昭然可见。以诗歌用韵言,上文所引《古镜》诗逐句押韵,三句一转,三叠而止;《锦屏山归途戏语心余》逐句用韵,两句一换。此外,另有《题沈孟公〈西溪高隐图〉》四句一换韵,前后两段隔句用韵,中间一段逐句用韵。中间一段吟咏画作,首尾两段兼论藏者,实为有意安排章法。就造语用字言,《九月十三日游锦屏山》描写山势云:“线缕直以泐,根垠卧而扁。中屏突地肺,孤瘦吓人眼。膏液暗粘缀,攲危累棋卵。分天一痕青,过云半截短。”[9](P331)运字造语偏于险峭,亦与前作或雄壮、或宛转的纪游诗篇风格迥异。至乾隆十九年(1754),金德瑛作《天津查礼官庆远同知,重修龙溪黄文节公祠征诗》云:“石牛晚作宜州梦,笔力方圆规矩中。墨花泄入龙溪湍,溪光泼眼如流汞……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如公诗。”[9](P334)再次表达对山谷诗风的体认和推崇。凡此种种,都共同指明:金德瑛视学山东时,确实有向黄庭坚学习的诗学转向。蒋士铨评其诗歌“出入韩杜苏黄间”也就落到了实处。
乾隆十八年(1753)金德瑛诗风丕变,刻意学习山谷,这一诗学理念的转变亦可从其弟子蒋士铨的诗学历程中得到辅证。蒋士铨晚年所撰《学诗记》总结自身诗学历程云:“予十五龄学诗,读李义山而爱之,积之成四百首而病矣。十九付之一炬,改读少陵、昌黎。四十始兼取苏、黄而学之。”[8](P2060)钱锺书先生言:“今按,其丙子(乾隆二十一年)以前诗,无以拔乎时调;丙子以后,自卷五起,摹放黄诗之迹显然,尤以七律拗调为甚。《十八夜露坐柬谷原》所谓‘诗好近耽黄鲁直’是也。远在丙寅(乾隆十一年)见知桧门之后,未必化于桧门之教。丙子,心余实三十二岁,《学诗记》所谓四十岁者,举成数言之。”[7](P356-357)钱先生关注到蒋士铨诗风历时性的动态生成过程,指出其“摹放黄诗”是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之后,这对考察金德瑛的诗史地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蒋士铨于乾隆十一年(1746)受知金德瑛,“自是从学岁余,船窗署斋,一灯侍侧。凡修己待人之道,诗、古文词所以及千古,孳孳诲迪,未尝少倦”[17](P13),“于公雅言绪论,与闻最详”。他对乃师诗作亦推崇备至,步武相随,《王澹人雨中见过,出桧门先生诗卷相示,澹人作五言一首见寄,次韵奉答》一诗即充分表明师门自豪:“吾师贱浮名,把笔压诸老。窃怜贵人诗,望秋各枯槁。篇成使我读,藉心作梨枣。师如韩退之,我郊汝则岛。”[8](P490)钱先生指出蒋士铨早年“改读少陵、昌黎”时所作诗歌“无以拔乎时调”,并未见出学习山谷的痕迹。而金德瑛视学江西时亦以宗奉韩愈、苏轼为主,师生之间宛然相契。之后蒋氏又于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入金德瑛山东学政幕,直至乾隆十九年(1754)六月,二人返京后始分别。山东学政任内正是金德瑛刻意学习山谷的时间节点,蒋士铨入幕后,“周流十郡,登山观海,与桧门先生极倡酬之雅”[17](P22)。前引《锦屏山归途戏语心余》诗一述苏黄,一述韩愈,即金、蒋师生二人论诗之作。此后蒋士铨诗风亦很快随之一变:“摹放黄诗之迹显然。”钱先生显然忽略了蒋士铨于乾隆十七年(1752)入金德瑛学政幕这一经历,因此得出蒋士铨诗学山谷因“远在丙寅见知桧门之后”,故而“未必化于桧门之教”这样的推断之辞。蒋士铨紧随乃师之后,诗学山谷,不仅可以见出师徒之间在诗学上的密切联系;同时,这种密切联系又反过来进一步证实了金德瑛此期的诗学理念,较之江西学政时期,的的确确出现了宗奉山谷的转变。这与上文对金氏诗作的分析是相一致的。
我们进一步要追问的是,金德瑛于乾隆十八年(1753)诗学山谷的背后,对秀水诗派而言,诗学意义到底几何?
首先,对个人诗歌创作而言,乾隆十八年(1753)业已进入金氏诗歌创作的后期阶段,并未改变其诗歌总体风貌,其创作仍以韩、苏为本,诗歌风貌宛然在是。上文所举《登云龙山放鹤亭,见黄河北徙》《保定守王蔗村饷龙井茶赋谢》《晓憩圆津庵示灿一上人》诸篇,皆为乾隆十八年(1753)后诗作。这与金氏此时用心山谷的诗学转向并不矛盾:长期心摹手追所形成的稳定诗风,并不会因为师法对象的转移和诗学理念的变化而骤变;相反,经过陶冶之后的沉潜,才正是诗人的本色所在。此外,同时论诗者言及秀水诗派宗奉山谷,亦多不及金德瑛。乾嘉时嘉兴桐乡人陆元钅宏《青芙蓉阁诗话》云:“自竹垞殁后,檇李之言诗者,如钱(载)、王(又曾)、祝(维诰)、万(光泰)及二汪(孟钅肙、仲鈖)诸公,大率以山谷为宗,操唐音者如《广陵散》矣。”[18](P2622)可见即便金德瑛后期兼学山谷,但识者甚尠,人多不以学黄目之,起码是排除在秀水诗派以山谷为宗的诗人序列之外的。
其次,就秀水诗派而言,乾隆十八年(1753)已经是诗派发展极为成熟的时间节点。诗派主要成员中,是年钱载46岁,王又曾48岁,汪孟钅肙33岁,个人诗歌创作已趋于成熟;更有前辈诗人钱陈群、诸锦皆已年近古稀,诗名早已誉满都下;而汪仲鈖于此年病殁,万光泰逝世于乾隆十五年(1750),诗歌风格、成就亦足以盖棺定论。更重要的是,自乾隆十二年(1747)始,秀水诸人陆续进京;至乾隆十六年(1751)十一月,钱陈群、诸锦、钱载、王又曾、汪孟钅肙、汪仲鈖、祝维诰等秀水籍诗人大会京师,诗酒唱酬,广通声气,成为彼时京城诗坛最为活跃的诗人团体。这一诗坛盛事一直持续到乾隆十九年(1754)六月,随着秀水诸人先后离京才告一段落。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至乾隆十八年(1753)时,秀水诗派已经由一个地方性的诗人团体发展为高度知名的诗歌派别。而“秀水派”的得名由来,亦在于此。
至于对黄庭坚诗歌的认同和学习,远在乾隆十八年(1753)之前,就已经成为诸锦、钱载、二汪等秀水诗人的诗学共识。在钱载、王又曾早年诗作,皆可找到用心山谷的例证。而前辈诗人诸锦不唯对黄庭坚诗集的任渊、史容注本进行删补整理,甚至早在康熙末年,就已将山谷纳入其诗作的取法范围。汪仲鈖《桐石草堂集》卷五有诗《枕上无事,日课数绝句,每韵各得一首,总为病中杂诗,语无伦次,次以韵而已》:“黄诗翻阅枕函亲,学杜先宜此问津。宗派百年谁复识,解人弦外两三人。”诗下自注云:“山谷为诗家不祧之祖,元明以来,无人齿及。朱秀水皆近时巨老,而动有贬词。余素酷嗜其诗,天社任渊、青神史容所注,行止辄以自随,惟同里钱萚石、万柘坡及兄厚石以为然也。”[19](卷五)汪仲鈖以山谷诗为学杜津梁,推其为“诗家不祧之祖”。而识此诗家秘宝者,则举钱载、万光泰、汪孟钅肙为同道,并未言及姑丈金德瑛。这一诗史事实的辨析旨在说明:诸锦、钱载、二汪等秀水派诗人对黄庭坚的学习,远在金德瑛用心山谷之前。金蓉镜所谓“先公首学涪翁,遂变秀水派”,确属无稽之谈。
再进一步而言,金德瑛诗学理念转变的契机,又与秀水诗人先后入京的时间相吻合。秀水诗人于乾隆十六年(1751)底大会京师,由一个地方性的诗人群逐渐发展为高度知名的诗歌派别。此时秀水诗人群往来密切,声势浩大的雅集活动,自然将诸人早已形成的宗奉山谷的诗学共识在京城诗坛中广为流布。而金德瑛与秀水诗人群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秀水诸位诗人时相往来的若干记录,如汪孟钅肙《厚石斋集》卷七录乾隆十六年(1751)诗作《奉常金桧门姑丈招饮论诗有作》,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金德瑛诗歌于乾隆十八年(1753)用心山谷的诗学转向,正是受钱载、汪孟钅肙等秀水诗人的影响。
四 结语
最后还须补充一点,就个人诗歌创作起步而言,早在雍正六年(1728),钱载、王又曾等五人就已将早岁所作诗歌结集合订为《南郭新诗》,自此同人之间诗酒往来,唱和不绝;而金德瑛“未第时,于帖括文最为攻苦……年四十余,始肆力于诗”[8](P2289),“刻意篇什”已经是乾隆六年(1741)之后的事情。此外,不论是秀水诗人群早年偏居嘉兴时的交游唱和,抑或钱陈群屡次返乡时召集雅集,还是乾隆十六年至十九年(1751—1754)间,秀水诗人群在京发起的多次集会,金德瑛出于致力科考、王事靡盬等原因,竟至一次未与,长期游离于秀水诗人阵营之外。因此,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来判断其人在诗派同人间,以及诗派发展中的影响力。
行文至此,我们再来审视王昶、金衍宗等人关于金德瑛与秀水诗派关系的相关论述,皆与金德瑛本人创作情实出入甚远,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金德瑛长钱载7岁,且高中乾隆元年(1736)状元。钱载于乾隆十七年(1752)以45岁成进士时,金德瑛已官至太常寺卿,仕途畅达,确乎“名辈较先”。然而,于仕途,钱载可谓晚遇;但于诗道,金德瑛亦属“晚遇”。就诗学成就而言,金德瑛实难与钱载同日而语,前者对后者主动学习的成分要更多一些。王昶、徐世昌所言之“于同乡最爱钱君坤一”,“金桧门总宪名辈较先,论诗与相合”,亦当作如是观。而金德瑛“诗道晚遇”且与秀水诗人群相游离的创作情实,于韩愈之雄壮健朗、苏轼之流利自然为近的审美追求,后期受钱载、汪孟钅肙等秀水诗人影响转学山谷的诗学历程,都使得金衍宗、金蓉镜对乃祖的过誉吹捧充满了讽刺意味。金德瑛其人其诗之于秀水诗派,许为中坚尚可,誉为开山则显然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