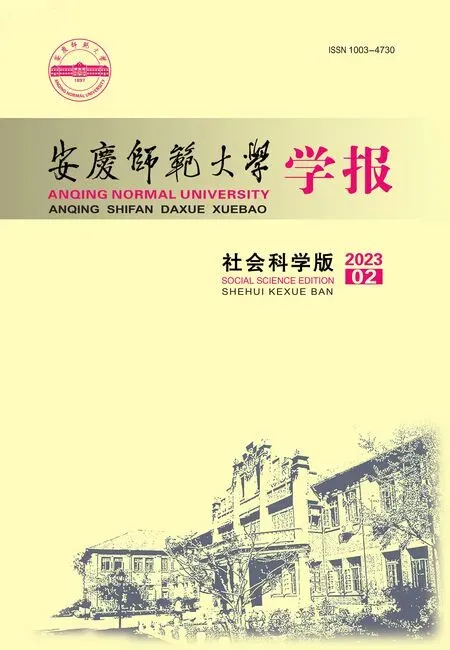苏州评弹与张恨水《啼笑因缘》的编演与传播
——以弹词艺人姚荫梅为中心
郝佩林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20世纪20年代末,市民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激荡相生,像水银泻地般流入江南民间,不断挤压着精英文学的读者边界。1929年,凭借《天上人间》《金粉世家》等小说展露翘楚的张恨水南下上海,为申沪通俗文坛注入了新鲜活力。1930年,他应《新闻报》副刊总编严独鹤邀请,开始创作《啼笑因缘》。从3月17日起,《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刊登。这部弥散着京味魅力的小说轰动了上海文坛,瞬间成为家弦户诵之作。此后,电影、戏剧、曲艺等竞相改编,不断翻新其传播样式。1935年,深受弹词浸润的陆澹盦品读《啼笑因缘》之后,“制为弹词,播之弦索,兼欲以是乐天下人”[1]。于是,沈俭安、薛筱卿率先演唱戚饭牛改编的弹词开篇。尔后,朱耀祥、赵稼秋拼档弹唱长篇弹词《啼笑因缘》,开创了苏州弹词说唱现代新书先声,并以此跻身名家响档之列。1936 年中秋节,姚荫梅赴沪郊金山县憩园书场开码头。场东贴出书牌:姚荫梅日夜弹唱《啼笑因缘》。这让本来说唱《玉连环》的姚荫梅啼笑皆非。无奈之下,姚荫梅以《啼笑因缘弹词》为蓝本,适当调整后登台试艺。之后,姚荫梅凭借新编弹词《啼笑因缘》蜚声书坛,并另辟蹊径,形成独具特色的姚氏说唱风格。
在长达九年(1936—1945)的跑码头历练中,姚荫梅在表演中不断融入日常生活素材,逐渐把小说故事演绎成生趣盎然的弹词书情;同时巧妙发挥乡谈、噱头等说唱技艺,让听众在通俗幽默的氛围中品味啼笑情缘。这样,姚荫梅的《啼笑因缘》自成一家,誉满江南书坛。他每到一处,深受书场老板欢迎,经常“轰动一时,生涯极盛”[2]。抗日战争胜利后,姚荫梅应上海沧州书场邀请,重返申沪书场。姚氏以幽默风趣之说表、逼真传神的“起脚色”,倾倒座中书客,轰动了上海书坛。因此,上海各书场争相竞邀,有时“他一天要连赶八个书场,据说还有两个电台播音”[3]。当时有媒体戏言,“他(姚荫梅)的屁股不是骑在脚踏车上就是坐在书台上”[3]。另外,姚荫梅利用消夏时节辗转水乡腹地的书码头,为乡民听客送去弦索之乐。1946年,姚荫梅莅临常熟虞山镇“西园”书场,演唱《啼笑因缘》,曾兴旺一时[4]。1947 年底,姚荫梅赴常熟仪凤书场,“卖座不恶,常有二百余听客。仪凤书场说毕,即转吴江,荫梅在每一书场,都为期四十天”[5]。姚荫梅长期往来于江南城乡书场,在赢得书迷听众认可的同时,也赚取了相对可观的收入,他在上海书场,“每月说书的进益,要在四十万元以上”[3]。姚荫梅尝谓,“近来所有积聚,获够苏州住宅一所,这倒可以弹三弦弹穿,吃开口饭吃穿,在道中言来也是不可多得的幸运儿”[5]。数年之后,姚荫梅凭借《啼笑因缘》弹词名利双丰,也不时地受到地方报媒舆论关注和热议。
一、吐纳风土民情,“说唱”表演通俗鲜活
如果说试水《啼笑因缘》弹词是因缘际会,那么,姚荫梅对小说情节和说唱风格的再造则是基于对弹词艺术的独特理解。原著中沈凤喜等民间艺人形象激起了他强烈的情感共鸣和独特的创作灵感。再加上小说中类似生活起居注的白描手法为其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启示。深谙民间艺术存续之道的姚荫梅改编《啼笑因缘》时,尽量融入共同体生活的表现元素,努力缩短原著内容与乡民生活之间的审美距离。
一是借用日常物品的形态巧妙刻画人物形象,极尽揶揄能事,诙谐有趣。譬如,他在书台上这样形容军阀刘将军的形象:
身体像浸泡的海参,肚皮像打了气的河豚,脑袋像丰收的冬瓜,耳朵像杜裹的馄饨。眉毛像熟透的香蕉,红枣子一般的眼睛,鼻子像一个高装馒头,如果秤秤,足有半斤。两片酱油色的嘴唇,又像打破的五茄皮酒瓶。仁丹招牌的胡须,像特大的乌菱。脸色像走油肉的肉皮,乌黑伦敦,两只手像熊掌,笑起来像雄鸭子叫的声音,一副吃相实在难看,想不到是一个有名的将军[6]335。
可见,姚氏通过努力寻找人物形态与日常物品的相似特征,然后拼合成人物形象,彰显评弹艺人对比喻和夸张等手法的独特理解。这种从小说到说唱的艺术转化使得说唱表演中人物塑造更加逼真。诸如封建军阀这种远离乡民日常的人物尚能刻画得如此传神,姚荫梅拿捏天桥艺人、货摊老板等民间形象更是得心应手。姚荫梅通常采用传统工笔素描,即简笔勾勒人物日常穿戴,姿态动作等,再辅以体态动作,使江湖郎中、撂地艺人等形象跃然台上。例如,他口中的旧货摊老头儿亦是百般传神:
只见看摊的老头儿身穿一身黑布褂裤,长筒布袜子,一双千针万衲的布底单凉鞋,鞋带还扣上结头,上不带帽子,盘了一根大辫子,额上一张粗草纸。插在辫子里,这样可以遮遮太阳光,免得再戴凉帽了。左手拿了一根一尺左右长的旱烟,管儿挂上一只荷叶包,烟锅里没有装上烟末,看他把烟嘴含在口里好像是在打瞌睡[6]7。
这些人物开相能够精准捕捉到天桥艺人的行为特点,同时嵌入易于理解的日常生活元素,洋溢着浓郁的市井气息。在乡镇书场演出中,这样的说唱方式极易被听众理解接受,能够有效地黏合起人物叙事与审美期待之间的联系。
二是“说唱”表演注意植入各地风俗民情,弥散着浓郁的生活韵味。在大多数乡民眼中,《啼笑因缘》最精华的部分无疑是来自皇城根儿的京味民俗。这些都市风情对于久居乡里的座客来说格外新鲜,很容易满足他们崇奇尚乐的审美愿望。当然,让乡民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市井民情并不是一件信手拈来的事情。要想获得适合书台“文哏”的地方话题,说书人必须深入体察当地民众生活。演出之余,姚荫梅“花了很长时间去逛城隍庙旧货市场,有时整整半天,不停地在这个摊上看看,在那个摊上和摊主聊聊,……积累了很多素材”[7]。他甚至利用闲暇时光,亲自“设旧货摊于吴门旧居,兼售古董,故于此业,知之綦详”[8]。这种地域生活的相似性为书台艺术呈现带来某种方便,也印证了民间曲艺的地方特性。他将收集来的形形色色的素材组织到《天桥旧货摊》的弹唱中,使书台演绎更接地气,弥散着人间烟火的地道韵味。与此同时,他多方访察北京风土人情,翻阅北京导游图之类的书刊,还与早年曾在北京开过茶馆的房东详细攀谈,了解北京的乡俚习俗,谙记那儿的风土人情[9]。通过日常积累,他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名牌馆子、娱乐场所,诸如“丰泽园饭店、“六必居”酱菜店等,皆烂熟于心,如数家珍,说到天桥、先农坛、大鼓场等一些场景时,甚至连一些老北京也毫不怀疑他是个地道的北京通。在他“说唱”表演的《游天桥》一回书中:
五光十色的旧货摊,黑吃黑的买卖,茶馆里如何泡茶,饮食摊的各种小吃,舞刀弄石担的伤科行医,大鼓艺人的露天鬻艺等等,以及其他回目中的二荤铺、西菜馆、舞厅、戏院、鸦片烟铺等等,无不绘声绘色,使听众如临其胜景[10]。
姚荫梅通过察访小说背后的风土民情,既厚植了弹词创作的民间基础,也弥合了艺术创作与现实世界的缝隙。民间艺术之所以深入民间,往往缘于艺人口中所展现的乡情日常。弹词艺人姚荫梅将乡民们并不陌生的日常元素化入说唱表演中,使乡民在感知生活的同时,从而更易接受评弹所展示的叙事世界及艺术导向。
二、妙用“噱头乡谈”技艺,书台演述轻松风趣
乡谈、噱头等演述手段通常代表着弹词艺人本事和能耐,也是他们“一招鲜、吃遍天”的艺术资本。乡间的书迷听客常常是冲着这些民间技艺走进书场,过足“泡书场”之瘾。因此,机趣俏皮、幽默诙谐的噱头是艺人留住听客的重要筹码。评弹表演中的噱头分两类,一种为“肉里噱”,一种叫“外插花”。“肉里噱”就是书情范围内生发出来的笑料噱头。“外插花”是指书情以外,但又因书情的某一点或某一句进而穿插于其中的噱头。通常以比喻形容、巧合、反常、讽刺、误会等手法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奇闻轶谈,开掘出噱头的成分。天生巧嘴的姚荫梅在说唱《啼笑因缘》时,适宜地穿插着各类花式噱头,让听客在谈笑俯仰之间,感知着书情故事的流淌。例如,“沈凤喜迁入新居”一节,他借着樊家树道喜祝贺:
过去新房落成,迁移进宅都当喜事办,要办酒、送礼,还要讨口彩,送馒头、糕点,主人欢喜,意味着兴隆高兴。
接下来话锋一转:
格末一样面粉做个,送几笼烧卖(麦)阿来事?勿来事格,巴望人家新房子烧脱卖脱,倷当心吃耳光[11]。
他将生活中“不宜用烧麦恭贺乔迁之礼”的现象转化为插花噱头,接引到说表过程中,带来了出其不意的艺术效果。可见,一个来自生活的简单噱头往往能使原本枯燥的书情变得轻松生动,着实增彩不少。1944 年秋,常熟西街口老同春书场请姚荫梅开书,他在场上放了一个常熟贩子在火车上兜售常熟特产“绿毛乌龟”的噱头,“一口地道的常熟白,由他加腔加调,滑稽突锑,令人喷饭”[12]。
乡谈是评弹表演中耐人寻味的噱头。运用方言乡谈既能区分角色,塑造人物,同时能挑松书情,调剂听众审美情绪。如果艺人的乡谈“纯在动听,乡土气息浓郁,听了大快朵颐”[13]。姚荫梅便是靠着“实在是天生的巧嘴”,辗转各埠,随学随唱,“描摹书中人物,有声有色,愈受听客激赏。噱头百出,竟使听者神往,常展笑颜”[8],甚至“死的方能成活的”[14]。有一年,姚荫梅初到浙江西塘镇弹唱《啼笑因缘》,巧遇敌档秦纪文说同一部书,恰逢其热闹关子,每天座无虚席。姚荫梅在人生地不熟、听客甚少的情况下,开书第一回就用乡谈紧紧抓住了听客。后来,浙江嘉善籍剧作家顾锡东曾这样回忆儿时所见的姚荫梅演出场景:
他登台付之一笑,说表樊家树自杭赴京,列车汽笛长鸣,沿途上来浙北,苏南、苏北和山东、天津等地旅客,各种南腔北调乡音攀谈,形容过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无不惟妙惟肖;接着说樊家树逛天桥,形形色色的游艺杂耍,行贩叫卖,说真方卖假药的大力士,设诈骗局的古董商人,结识江湖豪杰关寿峰妇女,初听沈凤喜唱京韵大鼓,夹杂着警察地痞的敲诈勒索,一回书中出了无数人物,是众生相,是风俗画[15]。
他这段表演一共用了杭州、嘉兴、硖石、松江、上海、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浦口、徐州、蚌埠、济南、天津、北京等地十八种方言,可谓集方言之大成,堪称口头文学的上品。作为弹唱《啼笑因缘》的后起之辈,姚荫梅“以善模仿各地方言,且说噱新颖,较赵(稼秋)朱(耀祥)尤滑稽突梯”[16]。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1898—1956)谈到类似说唱叙事的戏剧时,曾强调过方言的意义,其中指出:“在这种叙述气氛中,演员希望能将观众带到现实世界中去,引起他们积极的思考和联想。”[17]换言之,说一口地道的方言是营造“当地人在场”氛围的最佳途径。这种声音模拟最容易将听众带入艺术营造的故事情境中。姚荫梅的《啼笑因缘》中“常熟娘姨”和“上海看护”形象惟妙惟肖。他的“沈大妈探女”一段有着“出神入化,足堪使人解颐”的对话场景:
常熟娘姨说:“沈老太太,我告诉侬,勿要哭”“戤要骂三门个,朋朋外国人,拨听见,能要吃勿消哉”(常熟土白)“侬哪能?阿是又要哭是㕹?外国人闲话勿相信,侬哪能?”(沪语)“老太太阿是,上海看护凶来,又在骂山门哉,戤又拿外国人招牌掮出啊来哉,我怕来”[17]。
同时,他的“绍兴白,山东白,北平语等莫不入木三分,尤其是江北腔的扬州白,咬字咄音,一句呵唷喂隽永深长”[17]。方言对白集锦无疑提升了整个说唱表演的画面感和代入感,使听客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在姚氏的书台演述中,裹带了乡谈、噱头的《啼笑因缘》更加契合乡民审美习惯,提升了小说故事的传播速率和效能,也让姚荫梅风靡水乡村镇。各地听众都知道“其《啼笑因缘》不循原著书路,对于唱词,亦经增剔,独多常言俗语”[5],常将他视为与严雪亭等弹词名家并重的响档。
姚荫梅与严雪亭可称一时瑜亮,二人均以善放噱头,说表火爆为听众所喜,且二人复各善采各地方言。《啼笑因缘》与《杨乃武》二书。又最多卖弄各地方言处。已是大红大紫,无人与之对抗[18]。
在书码头演出中,由于口碑尚佳,姚荫梅往往被当地听众久留,不能及时开赴另外书场。1947年底,姚荫梅在常熟仪凤书场献艺,以说功老到,方言逼真“卖座拥挤,口碑载道”。此次常熟之行延续到转年春节,“明春年档,姚受梅李龙园书场之聘,已定元旦开书”[19]。由此观之,民间艺术引介通俗小说自有其别样路径,即是以幽默诙谐满足乡民娱乐需求。书台说唱剥离了通俗小说文本叙事的琐碎与平面化,用口头演述的艺术形式,拓展了文学故事在江南社会中的传播路径。
三、都市精英语境中姚氏弹词的“乡野”气息
无论市民小说,抑或弹词说唱,在都市精英的传统认知中,这类通俗文化大抵被归于粗野俚俗之列。掌控着文化鉴赏权利的“知识精英”不但指责“说书一家,诲淫劝杀”[20]。甚至认为:“现今乡村民间风俗之坏”完全归咎于这些“卑鄙的、恶劣的、迷信的,充满神话式,甚至诲淫色彩的(唱书曲子)”[21]。因此,姚荫梅踏入上海书坛以后,曾在乡镇码头上“很受听众激赏”的《啼笑因缘》却陷入了两难境遇。都市精英对其说唱风格的指责言论频见于报端。不少知识人聆听过姚荫梅的《啼笑因缘》后,发现其“并不按照原编脚本说唱,自作聪明,另编油腔滑调之篇子。书中情节亦多增损,牵强附会,与原著迥异”。而且“描摹书中人物,颇多漏洞”,几为“骗子用书”[22]。就连听客津津乐道的乡谈、噱头,亦被多方诟病。姚荫梅所讲之常熟方言:“满口戤笃、能笃、唔俚者,而且咬字勿准……感觉到刺耳万分,必有立刻离座之想。”如果更进一步,“以国语论,简直蓝青之至,其他地方方言更不值一提”[23]。可见,都市精英用国语标准苛责通俗说唱的方言乡谈,甚至认为姚荫梅乡谈比较别人要纯熟是因为“一向在外码头活动,所谓游过三关六码头”[24]。至于说唱过程中的噱头,更是被斥为“所受教育有限,批评事物,仅作浮面之解察。一知半解,自作聪明,似是而非,语多失当。影响知识浅薄之徒,危险孰甚”[8]。有时书台上的插科打诨,亦是“参杂出于己意,毫无根据之歪曲理论,……专装下流社会之恶俗习惯”[8]。整体看来,在都市精英的舆论风评中,姚荫梅的《啼笑因缘》不过是一部疯魔了上海听客的小热昏式的弹词,“论其书艺,说噱有余,弹唱不足,往往形容过火,仍不脱一个野字”。在当时的上海舆论界,这种评价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此非苛论,凡为书场中之真赏知者,均有此感”[8]。即便是在火爆的演出票房面前,刻薄的报媒舆论并未见松动。它们虽然承认姚荫梅登台现身说法,卖力非凡,笑料亦充斥书台空间。但是,从报媒的视角审视,这种演艺盛况不过是“好像是看香头的巫婆一样,如痴如狂,喜欢听听噱头的上海人,当时趋之若鹜”[3]。同时,他们坚称,大部分听客是奔着“‘九子廿孙大出丧’及‘一泡尿撒拉头颈里’等滑稽开篇”而来。在知识精英的潜意识中,毕竟像姚荫梅这种“徒知媚俗野狐参禅之徒”“终非大路作风,将来或有一蹶不可收拾的一天”[25]。
当然,报端疾书的都市精英对姚荫梅说唱的责难并非完全意气用事。他们也承认:
听书者寻开心也,根本是长脚笑话。万不能求全责备。书场并不是国学专修馆,在文字上毋庸深加检讨。并且说书人能有几人是前清科甲出身,几个是学校毕业生,只要能劝忠教孝,扬善嫉恶,不越大书一股劲,小书一段情之原则[26]。
但是,在需要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立场的舆论导向中,他们依然声称:“姚荫梅之装腔作态,并爱听其各地方言。此子于弹唱固不足取。”[26]这样,在都市知识精英看来,他们与射利谋存的说书人是天然对立的,势如水火。他们严格恪守着艺术审美的界限,时刻暗示着文化权利的阶序。在乡间极具号召魔力的乡谈噱头等民间艺术被诟病为滑稽可笑的“乡野土气”,甚至妄言“不能以成败论艺”。
但耐人寻味的是,同为智识阶层,身处乡镇社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都市读书人那般尖酸刻薄。他们在小镇书香茶韵的熏陶下,“竟与同化,驯乃浸淫成癖,也成了书场“瘾君子”[27]。每当开书以前,“高谈阔论,或评说书之艺术,孰优孰劣,或谈生活之过程,乍升乍降”[26]。1943 年,姚荫梅在无锡剪书后,载誉至江阴卢家桥长安书场。卢家桥虽为江阴县一个离城三十里的长江边境之小镇,居民朴实无华。但“颇多智识分子,长日无俚,除听书外,并无其他娱乐,姚书艺精湛,定能展其所长”[28]。抗战后,姚荫梅自平湖转往青浦朱家角民乐书场,尽管他在台上“遍洒狗血,卖尽力气,纯如表现滑稽戏”,但仍被认可“以乡谈取胜”[29]。因此,在江南乡镇社会,由于日常娱乐匮乏,姚氏《啼笑因缘》的通俗属性自然消解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抗击力度,他们愿意让渡自己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知识精英、农夫、艺人三者在文化消费场域中的和睦相处。
显然,姚荫梅弹词的艺术风格在城市和乡村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境遇。曾经被乡民俗众热捧的通俗风格在进入申沪都市书场后,频遭把控艺术评点话语的知识精英所诟病,甚或被冠以乡野粗鄙的名声。透过姚氏弹词的城乡双重境遇。可以发现,身处大小传统的精英和乡民的审美情趣是迥然不同的,并且试图“刻意”地保持着泾渭分明的审美界限。从这一视角切入,我们似乎可以窥探出姚氏《啼笑因缘》在乡土社会传播的一个侧影。
四、结 语
20 世纪上半叶,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啼笑因缘》蜚声沪上文坛。克承家学的姚荫梅敏锐地索解出市民小说与民间曲艺所共有的通俗特质,将其转化为鲜活生动的评弹说唱。姚氏的《啼笑因缘》在保留张恨水小说的基本故事框架下,积极吐纳风土民情,宛若一副流淌着日常风韵的生活画卷。同时,颇具语言天赋的他在表演中运用乡谈、噱头等技法,将书台演述点染得轻松诙谐。这种幽默的艺术风格深受水乡听众喜爱,也契合乡土社会中民众的审美趣味。20世纪30年代,姚荫梅长期活跃于江南乡镇的茶馆书场,将姚氏风味的《啼笑因缘》传播到水乡腹地的各个角落。抗战胜利后,姚荫梅重返申沪书坛,其表演赢得市民大众的激赏。然而,都市精英对其说唱颇多微词,并利用报媒舆论频频指摘乃至诘难。他们罔顾演出实际效果,偏执于姚荫梅说唱风格的通俗与粗野,讥为“小热昏”“滑稽戏”。姚荫梅弹词的城乡迥异双重境遇反映了大小传统两个世界对待通俗文化的态度差异,也昭示出知识精英与乡民俗众的审美界限和文化芥蒂。这种境域反差折射出《啼笑因缘》在江南城乡社会中传播、接受的别样路径与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