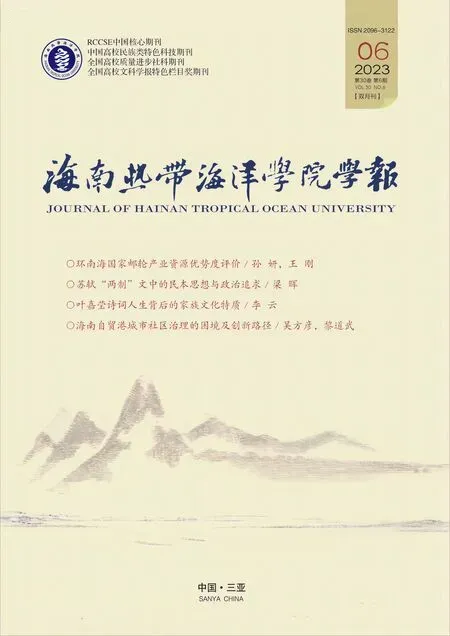养生如何介入苏学
李景新
一
养生是一个极为复杂而神秘的问题。中国人尤其热衷于谈论养生、探讨养生、研究养生、实践养生。
然而数千年的养生理论与经验一直令人处于迷茫之中。孟子教人养浩然之气,然而这个“浩然之气”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人的身体内怎么养成,却很难弄得一清二楚。道家主张物我齐一,蔑视一切人为的文化,只要顺应自然就好了,然而道家的养生实践却往往违背自然,甚至用极端的方法追求长生,却丧失了生命。佛教只修来世,好像现世与我无关,禁止一切世俗欲望和享受,又何谈养生?然而不少僧人却实现了长寿。
由此看来,养生似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情。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养生了呢?养生是否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了?当然不是。小到微生物,大到天体,无不看似神秘莫测,而又无不需要人们去探索其中奥妙。生命是珍贵的,养生无论多么神秘而复杂,都需要不断地去研究和追求。
从另一个角度看,养生又是一种文化,一种哲学。养生的理论与实践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既然发生过,就无不打上文化的印记、哲学的痕迹,也就具有了被研究的价值。比如苏学,蕴含着丰富的养生资源,那些养生言论和被记载的养生实践在一个叫大宋的时段发生过,它们与宋以前的历史相接,又对宋以后的人们产生长久的影响。养生,必然成为苏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
二
苏东坡,仍然是养生介入苏学研究的首选对象,因为他比其他人有更多关于养生的论文、赋、杂记、书信、题跋、诗词、书法等,他的养生故事也被更多地记载于各种文字之中。他有很多来自古代、同时代以及自己冥想和实践而得到的方法,有时看似很正确,有时不怎么合理。但这些似乎与东坡都没有关系,他关心的只是个过程,所发生的也只是一个一个天真可爱的故事。他的千年知己林语堂说:“他自采药草,被视为药学权威。他试行炼丹,几乎到死前还兴致勃勃地寻找不朽的灵丹。他祈求天神并与魔鬼争吵——偶尔还赢哩。他想夺取宇宙的奥秘,半受挫败,却含笑而死。”(《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无论如何,这是一座研究中国古代养生不可绕过的峰峦。
我曾就苏东坡海南时期的养生话题写过一篇文章,文章分上下两大部分。上部分为“苏东坡居儋时期对养生的哲学思考”,分为六个小节:形、影、神的对话;白乳泉的哲思;从白蚁说起;儒释道的汇合点;众妙之门;“铅汞龙虎”说。从这六大方面可以看出,居儋是苏东坡养生理论的集大成时期。下部分是“苏东坡居儋时期的养生实践”,也分为六个小节:酒与养生;医药与养生;美食与养生;茶与养生;养黄中之法;作为日常功课的“谪居三适”。(《苏东坡居儋时期的养生理论与实践》,载《中国苏轼研究》2020第2期)从这六大方面可以看出,苏东坡居儋时期的养生理论深奥而玄秘,实践却是贴近日常生活,比较接地气的。我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穷尽苏东坡在海南时期涉及养生问题的所有作品,主要运用这些资料来透视苏东坡的养生理论与实践。除了苏东坡自己的作品外,其他有关苏东坡养生的记载也都可以运用。据说,书画、文玩等也都有利于养生,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涉及,当是写作时没有考虑到这些方面所导致。
我的那篇拙作水平很有限,之所以在此提及,是想给学者们和读者诸君一点启示而已。儋州之外,苏东坡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有关于养生的诗文,不同的阶段对养生的思考和所进行的养生功课都不一定相同,每一个养生故事对苏东坡这位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具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资料,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方法,必然能够产生不同的成果。
三
在养生问题上,苏辙仍然是被东坡热所遮掩的人物。但我总觉得,从养生效果看,苏辙也许是更加值得研究的重要苏学人物呢。
苏辙自幼体质就比苏轼差很多,一生多病,有些病是从小就种下的顽疾。疾病引起了不少研究苏辙的学者的关注。金国永《苏辙》(中华书局1990年版)中就苏辙的一首描述衰老的诗而进一步阐发道:“在其他一些诗歌里,他也自称‘老’或‘老病’,而实际上只有三十四岁……这原因虽然主要是政治失意,心情恶劣,但也与他众口俸微,家计艰难,营养不足,以及多病体弱有关。”王水香、陈洁琼《苏辙肺病诗医案价值探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11 期)说:“苏辙又多病,年少时患有肺病、脾疾、胃疾,晚年又罹患风痹、手战、眼疾等症。”陈金现《苏辙诗文中的疾病书写》(《平顶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6 期)指出:“在苏辙的诗文中,脾胃、肺疾、寒热证是属意较多的病症,诗文中的这些疾病书写对我们认识苏辙其人或有裨益。”就是这样一位终生为疾病所困扰的人,却活了73 周岁或者更多(73 周岁据孔凡礼《苏辙年谱》,宋代何抡《眉山三苏先生年谱》则认为苏辙“年八十,以病卒于颍川”)。苏东坡终年64周岁。
影响生命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而养生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学者也注意到了苏辙养生的问题。金国永《苏辙》中指出,苏辙“任陈州教授时,因体弱多病,更注意研究养生”,在筠州时期则更加频繁地与僧道交往,“他把学释道作为解除自己多病多难遭际的良方,并收到了效果”。曾枣庄在《苏辙评传》(巴蜀书社2018年版)中说:“苏辙年少多病,夏天脾不胜食,秋天肺不胜寒。治肺则病脾,治脾则病肺,以至于参加制科考试,韩琦因其病而为之延期。平时虽不离药,但总不能愈。苏辙在陈州期间,向道士学服气法,坚持一年,两种病都好了。苏辙还通过读书研究养生之术。”又说:“从任陈州教授开始,苏辙又注意研究道家的养生之术。”从论述语气看,这几位作者显然都认为养生在苏辙生命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沈如泉《苏辙养生修道简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 期)则专门从修道方面论述苏辙的养生方法,发现苏轼、苏辙兄弟“不但都有修习道教内丹的经历,且兄弟之间对此还多有探讨与交流”,并强调说,“特别是苏辙,曾被兄长苏轼誉为得道之人。虽说苏辙不像苏轼,后者在其丰富的作品中记载了许多丹方口诀及修道法门,但苏辙在其诗文创作中对自己养生修道的经历、经验也有不少描述”。苏辙修道的记载虽然不如苏东坡那么丰富,然而苏辙修道的水平相对于苏东坡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此看来,苏学养生结构中,苏辙不仅不应该被苏东坡所遮掩,而且可能更加值得大力研究呢。
四
苏学其他人物身上应该也有养生资源吧,有待于学者们去发现,去挖掘。我这里则想提示一个链接和比较的方法,由苏学的主体人物连类而及于其他在养生方面可作比较的人物,在更加宽广的资源中对养生问题、养生哲学、养生文化进行探讨。兹举一例。
“南宋四名臣”之一的李光在苏东坡离开海南50年后被贬到海南,于琼州、儋州居住6年,有许多诗文写到苏东坡。我在阅读李光的诗文时发现,李光在养生方面有一些甚为珍贵的观点和方法,于是我在《东坡遗风》(南方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中谈到了李光诗歌中的养生问题,并与苏东坡进行了简单的比较:
与旷达诗篇相呼应的是谈论养生的诗篇。《客有见馈温剂云可壮元阳感而有作》一诗,很集中地表达了他的养生观念。他反对以外药壮阳的方法,认为“元阳本无亏,药石徒损伤”,养生的要义在于自然而然,适应环境。为了阐述这一观点,他举出相对立的例子:一种是田间野老,他们自然而然地生活着,从不知道有什么长寿丹药,住着茅屋,吃着五谷杂粮,却能够健康长寿;另一种是所谓达官贵人,整天美女伺候着,金丹保养着,结果是“真元日渗漏,滓秽留空肠”,往往因此而死亡。李光的观点与苏东坡之“冰蚕火鼠”“皓齿蛾眉”的论调甚为接近。他在诗中大力抨击生色药石的危害,并提出正确的养生方法:“我有出世法,亦知不死方。御寒须布帛,欲饱资稻粱。床头酒一壶,膝上琴一张。兴来或挥手,客至亦举觞。涤砚临清池,抄书傍明窗。日用但如斯,便觉日月长。”诗的最后指出:“此理甚明白,吾言岂荒唐?书为座右铭,聊以砭世盲。”他在《食无肉》《居无屋》等诗中,继续阐发他的养生理念。
很值得一提的是,李光极为崇拜苏东坡,其崇尚自然朴素、善于适应环境、旷达超脱的养生观显然受苏东坡的巨大影响。所不同者,苏东坡比较重视外丹的作用,李光则反对外丹,这一点李光可能比苏东坡更高明一些。事实证明,李光活到八十多岁,而苏东坡只活到六十多岁,虽然影响人的寿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正确养生的因素恐怕也是不可忽视的。
书中只写了李光的这些内容,但我觉得李光能活到80多岁,他的养生应该是很成功的,他养生的资料也应该有更多吧,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呢?李光是因为与苏东坡被贬谪到同样的地方而与苏学研究发生关联,其他人物也一定有可能因种种因缘而可以被纳入苏学养生研究的视野,比如与“三苏”同时代的富弼(1004—1083)、晚于东坡而崇拜东坡的南宋陆游(1125—1210)、早于东坡而为东坡所崇拜的东晋葛洪(283—363)等都是高寿之人,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养生理论和实践是否可以通过链接和比较的方式引入苏学研究范畴呢?
五
养生介入苏学,不仅仅是理论问题,也可以应用于实践。有些明显对身心有利的养生方法,我们常常会忽略,而通过相关资料的阅读、研究、学习,便可以直接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我曾认真研读过苏东坡、苏子由兄弟梳头、坐睡、泡脚的日常养生法,认为可以作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良好习惯,兹作为一例进行简单介绍。
我曾在《苏东坡居儋时期的养生理论与实践》中写道:“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的谪居三适法,吸收了佛学的心理调节,道家的肉体调节,儒家的日常调节,堪称儒释道相融合而又便于知行合一的养生方法。所谓‘三适’者,晨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者也。”(《中国苏轼研究》2020年第2 期)苏东坡在儋州将“三适”写成三首诗寄给贬居雷州半岛的苏子由,苏子由也次韵三首。“二苏”的“三适”之法本没有多么深奥的道理,简单易行,效果良好,只是人们没有觉察,或者没有养成习惯而已。
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深刻的记忆之一,是先父用桃木梳子梳头发的事情。先大人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站在屋子里或庭院中梳头,其他空闲的时间或思考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拿起梳子梳头,我当时并不能理解其中真谛,只是感觉梳头时发出的声音十分悦耳,直到读过苏东坡兄弟的《晨起理发》之后才悟出其中的道理。回忆起来,先大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注意养生的。他通达儒释道,没有什么奇异的养生方法,而注重朴素自然而有规律的日常起居饮食,喜欢读书写字,适时调节心情。后来我把先大人的桃木梳子带到了海南,又备了几把木头梳和牛角梳,放在书桌上,时时拿起来梳理几下,甚是舒适。
午睡的好处,在现代医学发达的时代,已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了。西方医学家和精神学家们早就找到了午睡的科学依据。人除了在夜间睡眠之外,白天也有一个睡眠节律,午睡是人体保护生物节律的一种有效方法。适当地午睡,可以补充精力,清醒头脑,提高效率。据说爱因斯坦喜欢用午睡来提高大脑的创作能力,丘吉尔则告诉人们别以为午睡会耽误工作。按照现代科学的分解,午睡不宜时间太长,据说半个小时之内即可,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浅睡眠状态效果尤佳,在浅睡眠期醒来,既补充了精力又能很快进入下午的工作。苏东坡、苏子由兄弟俩《午窗坐睡》诗中都谈到了午睡的时间长度。子瞻说“息息安且久”,子由说“坐睡一何久”,但我想这种姿势睡眠,应该不会时间太长,诗的语言毕竟只是写一种感觉。其实“二苏”诗中描述的应该是现代人所说的“浅睡眠”状态。现代人生活节奏甚为紧张,尤其职场之人,中午很难得到更多的睡眠时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东坡兄弟的“午窗坐睡”获得一些启发呢?
我曾专门撰写一篇题为《苏东坡的诗意泡脚》的文章阐述苏东坡兄弟的“夜卧濯足”,发表于2017年4月18日的《光明日报》,兹将结尾一段引于此处:
泡脚适应于不同人群,而于老年人尤为重要。医书上说:“人之有脚,犹似树之有根,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东坡兄弟当时都已年逾花甲,又没有优越的条件享受其他,而于睡前脱去履袜,用热水泡泡脚,舒适而利于养生,这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何乐而不为?说到此处,望坡居士也想起昔时在北方生活时,冬天泡脚的情景。回首总是美好的。现在于海南生活,每日淋浴,方便多了,却也忽略了那种泡脚的享受。
足浴的好处早为人们所熟知,而今天濯足之汤加入艾、姜之类的百草,质量比东坡兄弟贬居蛮荒时要高得多,但是当代人能够坚持每天“夜卧濯足”者也许并不多见。
六
古今养生理论虽然往往不同程度地带有神秘色彩,但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养生对于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历程所具有的良好作用,何况养生还带有多方面的文化、哲学的意义。显而易见,苏学所蕴藏的养生资源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由于苏学是一个包含众多领域的学术系统,养生介入苏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是十分丰富的,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以及饮食文化、起居文化、性别诗学、雅玩文化等角度都可能有不同的发现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