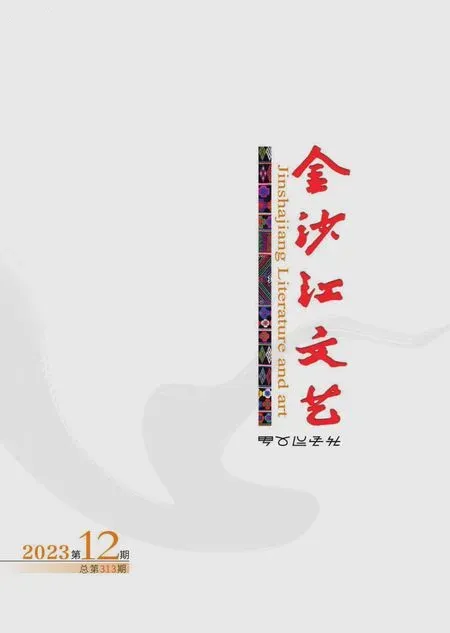寒冬里的温暖
◎张亚宁(陕西)
秋天就这样去了, 冬天也就这样来了。
一夜的雨夹雪, 秋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树枝上摇坠的那几片树叶也飘落了, 极不情愿地粘在冰凉的大地上。 秋天的离别, 无意中留下了些许遗憾和伤痛。 懵懵懂懂地望着雨夹雪的天空, 心里空空的, 即使浓浓的迷雾笼罩了山丘和山庄, 也无法阻挡恋秋者的心绪, 情不自禁地想着秋天整山整洼红黄绿相接的树叶、 肥嘟嘟的果实、 健壮的家禽、 喜笑颜开的农人……幻想眼前的景象只是一个梦而已, 幻想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雨夹雪只是秋天遇到的一个意外而已。
一场纷纷扰扰的雨夹雪迅速结束,冬天就这样来了。
站在冬日的旷野静想, 恍惚觉得秋天转身离别是乐意给冬天一个广阔的舞台, 显出秋冬两季各有千秋的独特之美。 秋, 让得理所当然, 冬, 来得自然而然。 要是秋天赖着不走, 谁还会起早贪黑收割地里的庄稼呢? 母亲头上拢着淡蓝色的头巾, 在结束打谷子不久的场里, 捡拾遗落的豆子和谷粒。 远道而来的风掠过村庄, 在打谷场旋转。 母亲不高不低地说道: 再不抓紧收拾, 下雪了就要受损失哩!就是这场恰到好处的雨夹雪, 督促农人装回打谷场遗留的粮食, 覆盖好室外怕冻的东西, 堆积好散乱的草垛,捆好地里的玉米秸。 没多久, 雨夹雪不再光顾, 或大或小的雪花成为常客。
北方的冬天一向是萧瑟的, 山山洼洼光秃秃的, 树木赤裸裸的, 风干冷干冷的, 偶尔下的雪、 降的霜, 能添点迷人的颜色。 一场场白雪在雨夹雪的邀请下缓缓而来, 似乎把北方冬天的荒芜一夜间全部遮拦起来了, 满世界显得整齐划一。 多雪的日子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和兴奋, 大人倒不是那么突出, 大多惊叹气候湿润、 来年会有好收成、 可以先歇几天。 一群毛孩子就别提多高兴了, 对他们而言, 寒冷算不得什么, 结伴在雪地里玩耍, 涌在心中的兴奋与喜悦, 唯有在雪地里尽情嬉戏, 方显对雪的欢迎够热情。
大地银装素裹的早晨, 外婆总是早早起来在院子里 “扫雪路”, 在我的故乡, 将这种扫部分雪、 开出一条条小路都叫扫路, 或 “扫雪路”。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外婆起来要做饭, 出门拿着扫把, 扫开她要去拿柴、 倒垃圾、 取煤块的地方。 偌大的院子, 扫开几条交叉且细长的小路。她不去的地方, 仍然是白雪一片。 外婆准备好东西, 围着热乎乎的灶台,叮叮当当做出香喷喷的饭菜。 吃了饭, 外爷带着儿孙出门扫雪, 把院子清扫得干干净净, 堆积起大小不等的雪堆。 当太阳满山了, 外爷坐在阳光充足的门道里, 折一张白纸条, 包进去干枯的烟草叶, 然后卷成食指长短的香烟, 叭嗒叭嗒吸着。 孩子们围过来, 他一会儿说这个的长处, 一会儿说那个的不足。 有时候, 我们邀请他讲故事, 他故意不讲, 孩子们软硬兼施, 他才肯慢慢讲开, 一旦讲开便滔滔不绝, 讲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讲战争讲饥荒, 动听迷人。 我们十分好奇, 很快就能进入外爷所讲的世界里。
下雪不冷融雪冷。 隔一夜大地上冻, 向阳坡悄悄地低下了头, 不再骄傲自己是一个向阳的坡, 随着冬天的大流, 心甘情愿地与冬天里的寒风、雪花、 冰层融为一家。 远眺, 黄土高原呈现一个色调, 原有的色彩被冬以极端的方式彻底摧毁。 升起的炊烟,嘶叫的家禽, 觅食的飞鸟, 行走的农人……给寂寥的冬日增添不少色彩。这块土地上养育的小草小树, 都是有恩的草木, 陪伴空旷的山丘, 保持地肤一样的颜色。 刺骨的寒风把可怜的树叶吹打走了, 乖巧巧地躲在暗角里, 粘在潮湿的土壤上, 混杂在冰层里……光秃秃的树枝落些鸟儿, 鸣叫嬉戏。 冉冉飘起的炊烟, 行走的牛羊, 一副优美的村庄图。 走进这块神奇的土地, 惊叹之外, 就是说不尽的赞美。 每当黄昏来临, 静静地站在山岗或者山丘, 远眺陕北的山山崖崖,沟沟壑壑, 别有一番美景。 远道而来的画家, 三三两两走进村庄, 或在村口画下仰视的山河, 或在山丘眺望,画了俯视的村庄。
父母和村里人不会停下来, 牧羊,砍柴, 碾米, 捡粪, 拉炭……从早到晚有做不完的活。 记忆最深的是杀年猪、 碾米磨面、 用洋芋粉制作粉条等大事, 好多是孩子们帮不上大忙的事, 站在一旁做点小活, 甚至是看看热闹, 等于就参与进来了。 最累的就是收拾玉米, 孩子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有活干。 阳光好的日子, 父母把院子扫干净, 在玉米架的某个角落打个水桶般的洞, 藏了几个月的玉米棒子直泻而下, 金黄的玉米棒堆在一起。 父亲用木棍敲打一阵后, 大多数玉米粒会掉落, 满地金黄。 风来的时, 用工具扬玉米粒, 粉末性的杂质随风刮到一边, 金黄的玉米依偎在一起。 有不少玉米粒死死粘在玉米芯上, 需要用手一颗接一颗地抠下来。 小孩子手小皮嫩, 抠不了多少个, 两手发麻, 一不小心就划破手指, 得伤痛好几日。
闲暇之余, 一群孩子相约, 在就近的河槽滑冰, 玩得热火朝天。 小村的河不宽, 河流不急, 到了冬天却满河槽结冰, 站在山头望去, 犹如蜿蜒曲折的银龙甩在村里。 一早太冷, 中午冰面有水, 唯有下午冰滩上人来人往。 每人用木头做一辆冰车, 左右手各抓一根冰锥, 在冰上玩转自如。 大孩子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 技术好的孩子总是让大家羡慕。 有时候, 一群孩子将冰车摆成一排, 听到口令就一起出发。 一场竞赛, 决出滑冰大王, 场面煞是热闹。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孩子们玩得正起劲, 大人们喊他们回家吃饭了。 听话的孩子, 带着冰车, 恋恋不舍地离开河滩。 也有些孩子因弄湿衣服不敢回家, 在河槽边燃一堆火, 把衣服烤干才敢回家。 孩子们有时候正烤衣服, 大人跑到河滩,没有理由地骂他们一顿, 然后揪住他们的耳朵把他们抓回去了。 第二次,冰面上还是这群孩子, 依然兴高采烈地玩耍。
整日忙碌在都市里的人, 对季节的感觉似乎慢了远远的一大步。 似乎要见到一场皑皑大雪, 或者被一场刺骨的寒风刮醒, 才能意识到冬天彻底来了。
有一年冬天, 去城里走了一趟,发现城里人的忙是另一种景象。 与乡下相比, 他们忙得更加直白, 而且节奏极快。 乡下做洋芋粉是常见的事情, 也是节奏较快的, 家乡人称之为“漏粉”。 预定好做粉条的时间, 便约上帮忙的人, 再请位 “漏粉” 的师傅。 主人将提前碾磨好的洋芋粉拿雄黄熏炝, 次日一早碾碎与水拌均匀,一群男人光着一只膀子, 齐心协力,和成粉团, 通过粗细不同的粉瓢, 将羊芋粉团倒入粉瓢, “漏粉” 师傅不停地用拳头敲打粉瓢, 粗细不同的粉条随即 “漏” 入热气腾腾的锅内。 有人用细长的棍子来回搅动, 煮上数分钟便捞出来。 这时候的孩子们早早站在旁边, 翘首期盼热乎乎的粉条出锅。 一盆洁白的粉条端上来, 大人用碗均匀分配好, 孩子们伴着提前做好的西红柿酱、 酸汤、 酱油等佐料, 狼吞虎咽, 与吃杀猪菜的热劲不差上下。
冬天的寒冷, 似乎成了懒人的理由, 有困难来临, 总会不紧不慢地说: 冻得手都伸不出去, 春天来了再说。 于是, 一次次好的机会擦肩而过。 春暖花开的日子, 连点影子都找不到了, 何况春天总有春天该干的事情, 怎能补回冬天的事。 那些勤快的人恰恰相反, 及早地储藏过冬的食物, 备着春耕, 手里或多或少忙着点活儿, 心情也好起来了。 正如古人的一句话: 口勤不缺吃, 手勤不缺钱。夏天孩子们去山山洼洼里摘野果子吃。 冬天树叶落尽, 草木枯黄, 孩子们将饱满的玉米、 黑豆拿出来, 在院子里, 用几块砖头或者石头支出一个简易的灶台, 放一只铁锅, 将干净的黄土取来揉成粉末, 倒入铁锅, 然后起火烧土。 等待锅内的黄土热了, 然后就玉米豆类放进去, 快速搅拌片刻, 迅速用铁笊篱捞出。 硬邦邦的豆类立刻酥软了许多, 有时候还能蹦出小小的花儿, 干脆而顺口。 爆出来的豆类, 没等彻底凉了, 孩子们便抢着抓一把, 吃得津津有味, 其乐无穷。
冬天像一位美丽的少女, 有说不出的迷人地方。 从腊八开始, 年的味道十足。 爆玉米花, 买年货, 杀年猪, 做豆腐, 清扫院落, 购买新衣服, 挂灯笼, 贴对联, 燃篝火, 放鞭炮……从寂静的小山村, 到偏远的小镇, 这个时候的所有事情, 小孩子参与最多, 热情最高, 冷与累似乎好遥远, 不需要大人嘱咐, 个个积极主动干起来忙起来。 腊月过得特快, 热热闹闹的一个大年过后, 便进入了另外一个季节。 村村寨寨、 老老少少扭起欢快的秧歌迎接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