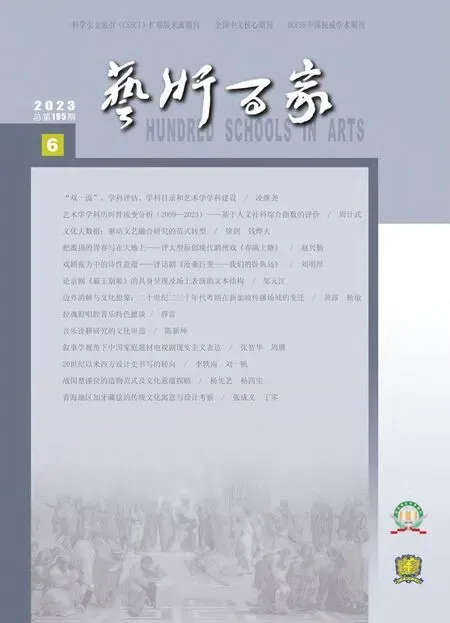明清桃源主题图像的空间建构*
孔 翎
(南京晓庄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桃源图像是明清时期的绘画主题之一。桃源是中国文人结合民间传说创造出来的仙境。关于桃源的传说,主要有天台桃源和武陵桃源两种文本流传。天台桃源指向了一个典型的神仙山水空间,空间结构与其他仙境区别并不大;而武陵桃源则指向了一个与田园村居融合的仙境空间,其空间结构与景观元素成为明清桃源主题图像的典型特征。
一、文本中“桃源”的空间建构:文字的图像化
桃源文本关于空间的描述具有视觉化特点。后世画家根据文字塑造出具有典型特征的桃源图像,并衍生出多样的图绘模式。石守谦在《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中归纳了中国桃源的四种图绘模式:仙境山水图绘模式、“人世化”桃源图绘模式、古代风俗图绘模式、隐居山水图绘模式。[1]32-50不同的图绘模式从不同层面承续了桃源文本中的空间建构。文本的流传使得“桃源”成为语图互补、具有典型性的绘画主题。不同的文本在表达上也各有侧重,给画家提供了灵活开阔的创作空间。明清画家在传承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在文本基础上用图像语言建构起不同结构类型的空间,塑造出具有典型特征、不同意蕴的桃源。
(一)天台桃源的空间建构
天台桃源与“天台二女”的神仙传说有关。南朝刘义庆编录的志怪小说《幽明录》及北宋时的《太平广记》都记载了刘晨、阮肇在天台山采药迷路遂遇见两姝的传奇经历,描绘了一个桃花流水的仙境。
天台桃源延续了传统的神仙山水模式,呈现出“高远”的纵深结构特点。在古人的观念里,“仙”与“山”联系紧密。“仚,人在山上貌,从人山。”[2]167“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3]152在早期文本记载中,神仙大多生活在遥不可及的崇山峻岭中。《淮南子·地形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玄圃之山,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4]328可见神仙居于山的高处。因此,神仙山水模式大多采取了“高远”的纵深结构。《幽明录·刘晨阮肇篇》描述到,天台桃源处于天台山深处,那里有结满果实的桃树和流水大溪。文本详细记录了刘、阮二人进入仙境的过程:“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再向内“逆流二三里”,体现出天台桃源空间的“高”与“深”。另外,仙境中女仙“其家铜瓦屋”,富丽堂皇。高耸不可及的深山和金碧辉煌的灵台楼阁是神仙山水空间中的典型景观元素。(表1)

表1 天台桃源的空间建构
明清桃源图像有的借鉴了神仙山水模式,如仇英的《桃源仙境图》,立轴幅式,画面分上中下三段,青绿山水浓烈奇幻、云雾缭绕,华丽的宫殿点缀其间,渲染出仙境的氛围。他的另一幅作品《玉洞仙源图》与此十分相似,可见《桃源仙境图》建构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仙境空间。
(二)武陵桃源的空间建构
武陵文本塑造了更为典型的桃花源,相关文本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桃花源’是凝聚着传统文人对于自由、和睦等向往的精神原型,但是陶渊明却能以图景式的表现方式将抽象的精神原型幻化为可视、可感的桃花源世界。”[5]240他赋予桃源异常朴实平淡的色彩,武陵桃源并不是缥缈不定、如海市蜃楼般的洞天仙窟,而是落地到现实世界。文本描绘了一个可以生活生产、自给自足的微型农耕社会,较为清晰地描述出壶天模式的空间结构。这个空间构成“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山间盆地景观模式:一条长长的溪谷走廊,一个仅容一人蛇行的豁口和一个豁然开朗的洞天。这一‘走廊+豁口+盆地’的世外桃源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寻访、所追求”[6]46。至于古代传统的仙境,著名的有昆仑仙境与蓬莱仙境,二者都指向遥不可及的隔绝模式。而壶天模式却将仙境与现世通过小小的通道联结起来,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仙境模式。
武陵桃源的景观元素有桃林、山口、渔船、田园等。“桃花”自古就是美好的文化意象,如《诗经·周南·桃夭》中就以桃花象征家族繁荣:“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源以桃林为始建构起兴旺的农耕社会;“山口”是武陵桃源的空间通道,它不同于天台桃源,天台桃源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或通道;“渔船”是隐逸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与天台桃源的神仙文化亦有所区别;“良田美池桑竹”则是武陵桃源中具有生活生产特征的典型景观。(表2)

表2 武陵桃源的空间建构
二、桃源空间建构的视觉表达:文本的图像转译
天台桃源是典型的神仙山水模式,典型场景元素有仙山、云雾、楼阁、桃树等。空间的基本范式为云雾缭绕仙山,其间点缀灵台楼阁。武陵桃源是田园隐居与仙境结合的空间模式,分为自然生态景观和生活生产图景两大空间。明清桃源图更多参照了武陵桃源。
(一)桃源图像中的空间划分
依托于文本,武陵桃源图的空间主要划分为“源外”“山口”“源内”。“源外”桃林与“山口”侧重于自然生态景观。“源内”又划分为“田园”“仙境”空间模式,前者侧重于生活生产图景,着重表现田园农耕生活,这是明清桃源主题的经典图式;后者援引传统的神仙山水模式,比如灵台楼阁在武陵仙境中的呈现。(图1)

图1 武陵桃源图像中的空间划分,笔者绘制
文本中的空间分类各有侧重点。比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对两大空间的描述不分主次,而在《桃花源诗》中却舍弃了对“桃花林”“山口”等景观空间的描述,着重描绘了更为详细的、顺应自然时节的源内耕织生活,直接表达他对桃源的真实构想——一个平凡的田园村居空间。除了陶渊明文本,王维的《桃源行》对桃源图像的空间建构影响也较大。《桃源行》取材于《桃花源记》,二者叙事内容十分相似,但与陶渊明描绘的日常农耕图景不同,王维的整篇诗歌偏重于优美景观的描写:“红树”“青溪”;由远及近的“云树”“花竹”;以及“月明”时的松影、“房栊”,“日出”时的云彩、“鸡犬”。王维建构的是有着绚丽视觉奇观的“灵境”“仙源”,这为偏重自然景观空间的桃源图像提供了范式。(表3)

表3 “桃花源”空间分类的文本比较
桃源图像除了具有完整叙事性的空间模式外,还有对空间元素的解构与重塑模式。不同的空间侧重点表现出不同的意趣:有的图像偏重于表现绮丽的胜景,如清代王翚的《桃花渔艇》只截取了“桃花流水”的空间片段,明代项圣谟的《桃源图卷》着重描绘了旋涡状的奇幻山洞;有的图像偏爱和乐融融的乡村生活,如清代吴伟业的《桃源图》重点描绘了星罗棋布的千里农田。
(二)叙事场景的空间建构:《桃花源记》的图像转译
《桃花源记》有着完整的空间叙事与场景建构,是创作明清桃源图的蓝本。“陶渊明诗文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图像与空间意识,例如,《桃花源记(并诗)》的文学语言在创造‘桃花源’世界中就超越了文学的表现常态,模仿图像符号的表现方式,形成了图景式的表现状态。”[5]240比如明代仇英的《桃源图卷》(图2),其图像依据文本建构出具有完整叙事性的桃源空间,可分为三大空间、五段场景(表4)。

图2 〔明〕仇英《桃源图卷》,33cm×472cm,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表4 《桃花源记》文本和图像的场景空间建构
图像从右至左,在文本叙事的基础上进行三大空间的分割,清晰划出桃源的内外空间:图中自右至左,从两株松树开始到山洞口为空间①,即源洞前的空间。这段空间结构清晰,上山下水,充分体现了桃花流水、山高水长的特点。渔人在这里发现并进入桃源。空间②从“洞”开始,渔人穿过长长的山洞便进入了桃源的内空间。经过这段隐秘的通道,画面豁然开朗,出现了大片农田,由此才真正进入了空间②(桃花源内)。除了自然景观和乡村景观,陶渊明还重点描绘了源内居民的活动。这种日常安稳的田园家居生活才是武陵桃源真正的魅力所在。空间③以最左边的松树、山路为界,界外就是源外空间,占整体画幅的1/32。源外空间在画幅中一般占幅较小,有的甚至省略。桃源图像虽然依据文本建构空间,但在图像视觉呈现上具有自身的语言特点。(图3)

图3 〔明〕仇英《桃源图卷》中的空间建构图,笔者绘制
三、“深”而“隐”:明清桃源图像的空间特征

“隐”是桃源空间的另一特征。丰富的空间层次使得仙境愈加隐秘。首先,桃源的“隐”体现在壶天模式的空间建构上;其次,空间上显隐关系的处理使得图像空间层次更加丰富,语言表达更具艺术性。
(一)“深”:桃源图像空间层次的建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空间层次的描述较为具体。他将桃源空间主要分为自然图景、生活图景与社会风尚图景[5]240,又“从远近、上下、内外等空间构成描绘出桃花源自然图景的不同层次”[5]241。因此,明清画家在建构桃源图的空间时将不同的层次加以叠加以凸显空间的“深”。如明代周臣的立轴式《桃源图》,纵向的画幅中分为源内、源外两大空间,而画家描绘的重点是源外空间,即空间①部分。空间①层次复杂:“溪”“桃花林”“山口”置于画面下方1/6处,一块斜置的巨型山体遮蔽住了“山口”,使得这里多出了一层空间。这样的处理使得源外山口更为曲折幽深,犹如游走于中国园林里的假山石空间中;从图像空间分割看,空间①又暗含多个“△”构图以进行层次叠加——第一层次的“△”由三组松树组成,第二层次的“△”由最前面带有山洞的山体围合而成,第三、四层次的“△”依次是后面的山体。(图4、图5)

图4 〔明〕周臣《桃源图》,161.5cm×102.5cm,苏州市博物馆藏(左);图5 〔明〕周臣《桃源图》的空间建构图,笔者绘制(右)
另外,图像中山石与树木“隐”与“现”的交替变化,也起着丰富空间层次的作用。比如仇英《桃源图卷》中巨松的空间处理:松树②、③组群与周围山体一同将源内围合成盆地状空间,源内的松树和其他树木又进一步将源内空间分为三组小单元空间——依山处的三个村落,在壶天空间模式中叠加了“一池三山”的蓬莱空间模式。(图2、图3)在大空间层次中又层层分割小空间,空间多层次叠加凸显桃源深深。
此外,“奥”“旷”的节奏变化使得空间张弛有度,给人适宜的审美体验。王维的《桃源行》对空间节奏的描述简洁而清晰:“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从弯曲的山口进入,沿着幽深曲折的水路行走,突然间豁然开朗,视线所及的是平阔的土地。“山口”与“山开”这两处空间呈现出“隈”“隩”—“旷”“平”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特点。如周臣《桃源图》,前景幽深崎岖的山口与后景空旷疏朗的田园在空间节奏上就形成了强烈对比。仇英《桃源图卷》中,还以山的“远近”视角强化其空间节奏。画面中的山有两处与众不同,第一处是山洞所在的山体,从“进洞”到“出洞”,图中展示了隔绝源内外空间的巨大山体。仇英为了表现这处不同寻常的空间,从“洞”开始描绘,因此在视觉上就拉近了这段山体,它如一个巨大的屏障,顶天立地,严实地遮蔽了桃源世界;山体意象处理得格外崎岖复杂,与入洞前具有程式化风格的“△”山体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处是最左边空间③的山体,与第一处山体相同,其视线是拉近的,也是山的局部截断,山体充斥于整个画幅的上下空间。(图2、图3)从视觉感受上看,这两处山体遮蔽并围合源内空间,将其在地理空间上隔绝出来,并在视觉心理感受上通过这两处山体的逼仄彰显源内空间的疏朗。(表5)

表5 仇英《桃源图卷》的空间层次建构
桃源空间的“深”还伴随着找寻的动态过程。“深”与“探”字同一字源,其甲骨文状如一只大手在一个洞穴里探测深浅。“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深远与高远、平远所体现的空间特点相异。“所谓‘高’,是由下而上的纵向体会,‘深’是由前而后的轴向体会,‘平’是由近及远的横向体会。”[8]59“仰”“望”是山水画“以大观小”的观察方法,有一定的距离感,而“窥”是一种视觉找寻活动,指“从小孔、缝隙或隐蔽处偷看”,空间上有遮蔽的意味,并伴随找寻过程的时序。因此,观众观看山水图像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仇英《桃源图卷》遵循《桃花源记》的完整叙事时间线,按照入源、出源的时间顺序从右至左,观者顺着渔人的视线,分别经历了发现桃源、进入桃源、源中见闻、离开桃源、桃源问津五个典型场景,图像展示了完整的深入桃源的过程。
除了典型的空间时序外,有的图像则采取了倒叙的手法。明代陆治的《桃花源图》,按照手卷的观看模式,其空间设置与叙事情节正好相反,画幅的右手边先出现的是平阔疏朗的源内风景,约占画幅总空间的2/3;画幅左边1/3空间里安排了一个巨大的山洞。按照时间顺序,观者观看时是由虚幻的桃花源回归到现实世界。(图6、图7)这种空间建构的逆向序列也出现在其他“桃花源”主题绘画中,比如清代石涛的《桃源图卷》等。无论时间顺逆,桃源图像都遵循空间叙事的逻辑。

图6 〔明〕陆治《桃花源图》,尺寸不详
(二)“隐”:桃源图像空间显隐关系的表达
桃源是仙境空间。武陵桃源的空间结构是带有窥视性的壶天模式。《后汉书·方术传下·费长房》记载,集市上一卖药老翁悬一壶于肆头,每日市罢就跳入壶中,费长房从楼上窥见其不同寻常,次日与老翁一起入壶游历。这是一个不断深入的窥视过程,在壶外看不见壶内景观,入壶方知壶内另有乾坤。壶的内外空间有着“显”“隐”关系的对比。典型的桃源图像亦重视表达空间的显隐关系,如仇英、陆治、周臣、石涛等绘画。
例如周臣的《桃源图》,图像中空间①部分如壶腔一般包裹住了低洼盆地般的空间②(源内空间)。其屏障,即山体的空间层次处理得丰富复杂。除了密合的山体,三处松树在空间层次安排上亦起着重要的遮蔽作用:松树①遮住“山口”,松树②③使得近处如屏障般的山体更加高耸。(图4、图5)周臣在空间处理上更加偏重表现壶天模式的屏障和入口,这里空间的“显”使得整个着墨不多的源内空间更加隐秘。源内空间是平实普通的乡村图景,在画面中占幅不大。
石涛的《桃源图卷》在空间建构上是横向的壶天模式,共描绘了三个空间:源内的田园空间;源外空间,“溪流”与“山”隔离了内外空间;城内空间,由“城门”和“城墙”作为空间隔离物。石涛《桃源图卷》与陆治《桃花源图》虽时空序列一致,但空间的显隐关系却不同:卷首空间①(源内)和卷尾空间③(城内)都采用虚化处理,从而凸显了空间②——一段云烟缭绕的源外山水,约占画幅的1/2。在空间②中最引人入胜的是前景处呈“U”形的两座山峰挤压并围合起来的桃源入口,其宛如山口隧道,虽然没有显现的“山口”,但弯曲的溪道和一艘空船点明了桃源主题。(图8、图9)石涛《桃源图卷》着重显现壶天模式中的仙境通道(曲折悠长的溪水)和屏障(如山口的“U”形山峰),与其他表现该主题的绘画相似,这里仍是用顶天立地、密不透风的山体作为屏障以遮蔽源内空间。

图8 〔清〕石涛《桃源图卷》,25cm×157.8cm,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图9 〔清〕石涛《桃源图卷》的空间建构图,笔者绘制
周臣《桃源图》和石涛《桃源图卷》在图像的空间建构上有着明显的显隐关系,都突出表现壶天空间中的屏障和入口。而仇英《桃源仙境图》则塑造了完整的桃源空间,除了屏障和入口,他更为详细地描绘了源内空间。他将整个源内山水在视线上推远,而源外山水在视线上却被拉近,视线上远近的区别,使得源内空间更加虚幻隐秘,如盆景般嵌入整个桃源空间中,空间上的疏离感易于为观者所感受到。
由宏大缥缈的昆仑、蓬莱模式,转向空间小而层次丰富的壶天模式,这种空间建构有其所遵循的规则。首先,无论是昆仑还是蓬莱模式都描绘遥不可及、难以掌控的景观,而壶天模式的规模却是可以掌控的。在仙境传说中,壶隐喻仙境,壶腔的包裹状也给人安全感。其次,壶天景观空间是内向含蓄的,是藏匿的、多层次的空间叠加,而非向外扩张。这源于传统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物我融合的思想。最后,壶天仙境与现实世界有着一定的、必要的联结。壶天仙境之所以成为最吸引后世文人的空间,是因为其与世俗联系紧密,其空间底色是“深”而“隐”的。
四、结语
桃源是一个融合了日常现实经验的仙境空间。从文本到图像,从想象仙山幻境到向往田园之乐,桃源都是美好自然空间与和谐社会空间的交融。武陵桃源建构了“深”而“隐”的壶天仙境空间模式,将田园村居的人世生活图景移入仙境空间之中,形成了典型的桃源空间模式。明清桃源主题图像延续了这种典型的空间模式,强调完美山水形象的人世化,关注人与自然空间的交融,从而建构理想的人居空间。桃源意象在后世逐渐泛化,由仙境落地到田园,再转向山水、进入书斋,最后简化为“桃花”意象,成为传统文化中典型的空间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