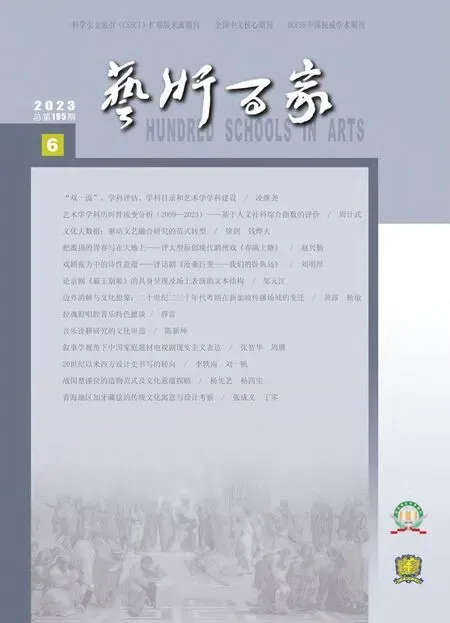战国楚漆奁的造物范式及文化意蕴探赜*
杨先艺,杨四宝
(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两千多年前,楚人以漆为贵,无器不髹,战国时期楚人创造了中国漆艺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楚人髹漆既精美务实又新奇灵巧,既不拘于物又不滞于心。楚漆奁作为日用梳妆器具的造物艺术形式,其美感常常表现为方寸之间见气象万千,小中见大,形中有形,象外有象。它以奇丽的想象和极富个性的创造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艺术天地。楚漆奁线条流畅、色彩瑰丽、情感外向,极富浪漫想象和自由精神。那么,充满原始浪漫激情的楚漆奁艺术品根植于何种土壤?维系楚漆奁文化特征发展演变的内在文脉为何?让我们循着这条古老之路,追溯楚漆奁的远古回音。
一、战国楚漆奁的历史寻绎与艺术特征
中国古代漆器的发现不绝如缕,虽发现有少量商周春秋漆器,但从未形成高潮,而战国漆器则有大量发现。据统计,全国已有40多个县、市的近80个地点出土了战国漆器,5000余座楚墓中有近千座出土了漆器。迄今为止出土的战国漆器绝大部分出自南方楚墓,数量较多,保存完好,反映了楚国髹饰漆器的兴盛。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时期,楚国已从弹丸小国发展为七雄中最大的诸侯国。至此楚人的生活已不再如昔日的筚路蓝缕,楚国新兴贵族“逞志究欲”,竞尚奢靡,这种局面带来了观念转变和思想冲动,民族个性和文化得以展开。新的价值观念、生活风尚和审美趣味,极大刺激了漆器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轻巧、实用的漆器迎合了官僚贵族的审美风尚。新的艺术思潮风靡涌动,不断冲击旧有制度和意识形态,漆器取代青铜礼器应时而生,漆奁代表一种新的审美追求与艺术趣味。
奁是古代盛放梳篦用品的物化载体。因奁中所盛放之物多属化妆品,故又称为妆奁。古代妇女妆敛,男子渥发,都需要使用妆具。妆奁由来已久,但何时起源难以定论。由于文献资料缺乏,漆器文字的辨析考证难度较大,古代对奁的称谓难以确定。奁最初除了用于存放梳妆,还用来盛放食物。这类以圆形为主的贮存容器发展成为专门的化妆用具,历经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西周时期妆奁的常见材料为铜,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方奁是妆奁的前身。春秋晚期铁制生产工具的推广和使用大大促进了漆器胎骨工艺的制作技术。将棬木胎用于漆奁胎骨制作工艺为妆奁的形制提供了一种范式,楚奁的制作工艺因此获得较大发展。楚式妆奁的制作在外形上多采用以直壁、矮扁的圆筒形为主的造物范式,这一妆奁形制一直沿续到秦汉乃至魏晋时期。唐宋变革之后,妆奁的实用性凸显。明清以后,妆奁逐渐进化成大型梳妆台和便携式梳妆匣。“妆奁”这一概念在战国早期初露芬芳,在战国中晚期展露花容,其名得以确定。妆奁是我们追溯古代梳妆面貌、寻绎古代梳妆文化变迁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因此,考察先秦时期楚漆奁的特征及其与秦汉漆奁之间的差异就有其必要性。
(一)楚漆奁形制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在先秦漆器研究中,形制、纹饰、铭文是十分重要的三个考察方面。形制不仅是物质生产的直接产物,更是政治文化符号的合规律性的审美活动的产物;纹饰与铭文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对漆奁作形制、纹饰、铭文三个方面的阐释,不仅要关注实用器物等物质层面的外在信息,更要观照蕴含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内在精神。当然,形制、纹饰、铭文也是我们全面深入认识漆奁的重要视觉因素。楚漆奁的形态演变受到多元耦合因素影响,主要包括制作的材料与技术、器物的使用与审美功能、生产生活环境与社会心理等。一般而言,楚漆奁形态的变化与楚艺术浪漫飘逸的审美特质密切相关。
从战国中期到楚国灭亡的百年历程中,楚漆奁作为一种日用容器,在形制规模、纹饰装饰、胎骨制作等方面变化不大。为了进一步剖析楚漆奁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寓意,笔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查阅先秦典籍,抽丝剥茧,整理出楚漆奁造物艺术的图式符号,探索楚漆奁造物的艺术特征,全面深入探讨其造型、纹饰、寓意及其发展脉络,分析其图式所饱含的精神内涵。在论述中参考刘芳芳制作的战国楚墓出土漆奁一览表[1]300,实地考察湖北、长沙等地博物馆所藏文物。由于保存不佳,考古发掘出土的近100件战国楚漆奁中,仅20余件的类型与纹饰可以分辨。其中包括残朽漆奁54件,有纹漆奁41件、无纹漆奁9件,刻有图语漆奁4件。按照形状的不同,楚奁形制演变共有四种分式分类。
第一类:器身圆形,腹壁直,平口,平底。外壁设有两个对称金属环钮。底侧安装三个兽面蹄形足。盖顶隆起,顶部中心安设一铜质铺首环钮。其形制沿袭青铜樽,不同之处在于奁的腹部为直壁,而樽的腹部为斜壁,奁的腹部比樽要浅。此类楚奁出土于天星观二号楚墓(M2:11)。(图1)

图1 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楚奁的形制(左);
第二类:长方形折叠梳妆盒,迄今仅此一件。该奁设计巧妙,梳妆功能齐全,是当时贵族美男的便携式梳妆器具。此类楚奁出土于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楚墓(M1:669-1)。(图2)

图2 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楚奁的形制(右)
第三类:扁圆形,直口,盖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布脱胎,彩绘纹饰。此类楚奁出土于包山楚墓(包山2:432)。(图3)

图3 包山楚墓出土楚奁的形制(左);
第四类:椭圆形,盖套盒在器身的外部,器身靠底部内收,平底。此类楚奁出土于四川渠县城坝墓,属于战国晚期到汉初移民墓(M2:55)。(图4)

图4 四川渠县城坝墓葬出土楚奁的形制(右)
通过以上四式漆奁形制的变化趋势可见,从战国早期的仿楚樽式演化为楚国的圆漆盒形制,器壁由斜腹壁变为直腹壁,使器口的广度增大,内部空间变宽。利于单独的小漆盒分类存放;从有足演化成平底,除个别新颖别致外,器形基本上呈现为矮扁圆形,器盖由子母扣合演变为直口扣合至器身底部,漆奁的盖顶由早期的平顶逐渐到晚期的隆起,胎体由厚木胎胎骨演变为卷木胎、夹贮胎,胎骨质地更轻巧适形,在装饰方面,早期的多素髹无纹演变成楚国时期的彩绘,有的漆奁内外饰彩绘。在铭文方面,四川地区楚移民墓出土的漆奁铭文比楚国旧地出土的铭文要早。
综上,楚漆奁作为一种小型日用妆具容器,便于古代女子携带。楚漆奁形态继承青铜器装饰风格,呈现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形制:器形基本上为扁圆形,奁的直径一般是高的两倍以上,腹直壁,器盖直口扣合至器身底部,盖顶隆起——这种穹隆盖设计不仅能加固漆奁、扩大其内置空间的贮存量,还为秦汉多子奁的盛行提供制作技术,其图式顺应了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审美情趣。楚人崇尚内红外黑的装饰色调,将凤鸟纹作为装饰的母题,凤鸟穿梭于层层卷云纹中,呈现为幻想性、抽象性的动物形象,这些因素都显示出楚先民多元而炽热的巫风信仰。画面纹饰主次分明,生动活泼,互融互生,令人遐思。在楚漆奁的方寸之间,楚人将传统写实手法与幻想抽象手法娴熟运用于图案设计之中,给人以艺术享受和审美愉悦。妆奁图式不仅满足了当时贵族梳妆所需,还展示出楚国的技术智慧和艺术精神。
(二)楚漆奁与秦汉妆奁的差别
战国秦汉时期的髹漆妆奁经历了产生、发展与繁盛的演变过程,在数百年间,妆奁在形制、装饰工艺上发生了巨变。
秦奁传承了楚奁的技法。在形制上出现了椭圆形漆奁。在制作工艺选材与用料方面相当考究,多以卷制薄木胎为主,并运用青铜、银箍予以装饰加固。秦奁管理制度严格,实行铭文责任制,分工更加细致明确。在装饰上不仅有写实性的凤鸟纹,还有变形鸟纹,尤其是鸟首纹、云鸟纹成为秦奁装饰的一种常见程式,“B”字形鸟纹成为秦奁装饰纹样中的一种标示性符号。
汉承秦制,西汉的漆奁在秦漆奁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形制上承继了秦卷制技术,其造型更加规整、合于规律性。漆奁技艺日趋成熟,增加了堆画、镶扣等工艺,整体高度有所增加,出现了双层奁、多子奁。西汉中后期,多子奁常以奇数形式形成定制。汉奁题材广泛,包括动物纹样、植物纹样、自然纹样、几何纹样、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纹样等多种纹样,其中,云气纹凸显,常常与这些纹样相互衬托,组合巧妙。
二、战国楚式妆奁的造物范式
漆文化是一种极其古老的独特文化,它深深扎根于楚人心中,孕育出丰富的浪漫情感。战国楚漆奁艺术表现出物之为用、饰之有理、形之有法的造物范式。透析楚漆奁的造物范式,可以感受楚人喜好灵巧、生动、变化和力度的审美趣味,感受楚人造物艺术浪漫轻灵、充盈灵性的美学风格。
(一)物之为用:巧制物象适于用
楚国日用漆器设计立足于生活实用。“物尽其用”是一切器物存在的基础,器物一旦失去使用功能,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任何形式的设计都应在设计创造中注重功能性与适用性,在实现器物“物用”功能的同时,还需遵循自然事物的和谐发展秩序与生态演变规律,促使人与环境和谐共生。妆奁作为楚国日用容器的物化形式,与楚国贵族日常生活中梳妆打扮的需求相伴而生。妆奁以几何化的构造设计传达器物清晰的功能属性,其适用性更符合人性化规律。
第一,结构设计。结构一般是指器物的固定结构与机械结构。固定结构只能承受和传递力,而机械结构在固定结构的基础上还能灵活转换器物的运动方式,增强使用性能。九连墩楚墓中出土的一件长方形便携式妆盒,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楚漆奁,在结构设计上独具匠心。它是为方便楚国贵族男人出行时梳妆而量身定制的,由两块长方体木板通过根部的铜合页扣接而成,在两块长方体木板相应部位加以凿空,以用于放置铜镜、木梳、削刀、脂粉盒等梳妆用品。由于铰接处为青铜构件,结构构件便可以围绕主轴板作相对转动,以便更好地契合器盖的开合,这就为妆奁开启时提供活动构件的支撑,提高了妆奁的耐用性。这件便携式妆奁“最具匠心的设计,是在奁内中下部位置上下各装有一个可以伸缩的支撑,使用时两者上下对接,既能支护着漆奁呈45度夹角打开,又可以作为支架承放青铜镜”[2]404-406。该“Y”形活动支架打开后可以支撑铜镜以便于梳妆照容,铰链连接结构能够更好地契合器盖的开合——开启时有活动构件做立撑。妆奁盖上设计有卡扣,体积小,可卡紧,方便携带。(图5)这件妆奁梳妆、收纳功能齐全,做工精致,构思巧妙,综合平衡了灵巧与耐用的关系。

图5 九连墩楚墓中出土的长方形折叠式梳妆盒
第二,器身设计。器具尺度是设计适用的关键因素,不仅给人以视觉美感,还使人在使用器物时获得美好的身心体验。笔者以扁圆形妆奁设计为例,对出土保存较完整的17件战国时期楚式扁圆形妆奁样本进行数据统计。从楚墓出土漆奁的高度来看,绝大多数为8至11厘米,高于12厘米的楚漆奁在器壁上饰有金属环纽,或在底部设计有足。依据学者李天元对江陵九店墓人骨的测量数据,楚国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6.94厘米,女性157.12厘米[3]521。这与史料记载的古代中国人身高相吻合。依此数据,人的手一拃长为17至20厘米,双手刚好能舒适围合12厘米直径的圆形器物。因此,楚漆奁在8至10厘米的高度是人适宜抓握的高度。根据现代人机工程学,这一高度也能使人手获得较为舒适的握力体验。楚漆奁的器身尺寸是根据人的身体尺度和结构功能进行有意识处理的结果,楚漆奁设计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人体工程学知识,还要考虑到与身体尺度相适应。个别楚漆奁通高超过11厘米,其器身设计在共性中显个性。例如荆州天星观二号墓(M2:11)出土的漆奁通高13.2厘米,蹄高5.4厘米,有足、铺首、环纽等金属附件,其细部设计令人叫绝。漆奁外腹中壁上饰有两个对称的铜环形鋬供人手持,顶部中间饰有一铜质铺首环纽。在器腹壁高三分之一处设计有一鋬形环扣。鋬上的圆状物刚好占据一拇指位置,使用者可以借助环扣施力,轻松把持妆奁,体现因地制宜之美。区区一个环扣却将“物”与效用的关系凸显出来,物宜与工巧成为楚国工匠造物设计思维活动中的定型化、模式化准则。(图6)可见,楚人在设计漆奁时既考虑到器具尺度与身体尺度的适应性,也注重到装饰的视觉美感。楚漆奁的设计既是设计者对适用性作合理思考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设计者平衡舒适度与劳作功效之间关系的体现,使之符合力学与人体工程学原理。这种设计思路拓展出“物宜”,补充了“人和”,强化了“工巧”,从而彰显了“巧其思,巧其力”的造物艺术,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图6 双手拿取器物尺度示意图(作者自绘)
(二)依之于理:巧饰物象顺其理
妆奁是楚人梳妆日用器具的承载器物,既是手工技艺产品,也是清赏之物,工艺性与审美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楚漆奁图案在形式上体现出红黑两色的强烈对比、奇巧富丽的装饰、反复精工的奇技淫巧。楚漆奁的视觉图像积淀着工匠巧饰妆奁顺其理的设计智慧、生存智慧。楚漆奁的造物思想绝不是只注重物理形态的纯粹功能主义,其纹饰也不是虚无的装饰,而是一种顾及人与物亲和关系的人文思想,一种感性与理性、心理与物理、主观与客观、技术与艺术相互交融的思想。巧饰楚式妆奁设计之理,主要体现在物理和心理两个方面。
1.巧循自然之理
造物制器离不开特定的物质材料,材料是人类实施造物活动的物质基础。人们利用大自然给予的材料进行各种造物活动,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性能认知和材料加工技术,总结出制作法则和造物规律。楚漆奁作为一种手工技艺,包括割漆、制漆、选材、制胎、彩绘、髹饰等一系列生产工序,其中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工匠,每道工序都顺应自然天成、巧夺天工的美学原则。巧循自然之理主要从善用自然资源与巧循自然法则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善用自然资源。自然是天然的领域,是生养人类之母体。漆艺取于自然,是自然的恩赐。漆艺材料主要是天然木、天然漆,是一种“天巧”,即自然工巧,天然的美是自然赋予的美。楚地属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适宜漆树、油桐和其他树木生长,为楚国漆器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嘉木良材等物质资源。《诗经·国风·鄘风·定之方中》言,“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可见楚国注重漆树的栽培。“巧生以待”的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潜在资源宝库,需要灌注人的智慧才能实现物为人用。中国典籍关于漆树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晋崔豹《古今注》:“漆树,以钢斧斫其皮开,以竹管承之,汁满管中,即成漆也。”[4]《荀子·王制》曾提到,工匠砍伐制器的木材要“将时斩伐”,即按季节砍伐树木。漆艺从来就是自然的漆艺,采集漆液要合乎时宜、取之有度、善待自然、尊重生长规律。漆树体液可谓“液体黄金”,[5]4一棵生长七八年的成熟漆树,每年可开口割二三十刀,出漆量约为250克,整个生命周期可以割漆二三十年。可见,在采集、制作、使用、再利用的过程中,要循其物性、量材为用,保持对自然的尊重之心。楚人凭借灵巧的双手,从自然中获得生漆这一优良材料,从大自然中获得制作灵感,巧饰漆器,赋予漆艺一种超自然属性。
第二,巧循自然法则。造物实践的背后,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与法则。从典籍上看,先秦时期官营手工的制器过程顺时机、循物理。《礼记》:“季秋之月霜始降,则百工休。”《吕氏春秋·季秋纪》:“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从中可见制漆休工、用工的时间法则。“霜降天寒,朱漆不坚”,从而影响油漆的粘黏性、降低器具的审美品质。《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工师检查库中物料,在分工过程中催促百工遵守时令、听从监工号令行事。百工所遵循的这些“理”就是自然科学与气象科学相结合的古代物候学,百工依据气象物候经验制定造物制度。这是楚国官营作坊生产工艺的管理模式。战国时期“百工咸理”,遵循天地之理。楚国官营作坊除依据气候为造物选料、制作生产外,还设专管百工的“工正”,考核工匠制作器物,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迄今发掘出土的楚漆奁中有4件刻有烙印图语,佐证了这种官营手工监督制度。
从中国传统造物史料中可以窥见先秦时期造物实践中积淀的一些理材之法。《髹饰录·乾集》记载,“巧法造化”是漆器制作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与科学规律。①可见,与自然和谐、顺应天时、适用地气、审视良材、精工制作方能巧制物象、技拙意巧,乃为上佳器具。“真正的巧在于处处顺应自然规律,在这种顺应之中使自己的目的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6]219
2.巧顺情感之理
情感是先秦楚人的本质力量,是他们集中化了的生命力量。若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么在先秦楚人的审美意识中,美就是情感的对象化。[7]87楚漆奁作为楚文化观念和情感的物化形式,承载了丰富的视觉美、生活美。作为楚域风格的典型艺术事象与情感表征,楚漆奁凝聚着楚人的文化思想和审美品格。
第一,巧和先秦之风。“先秦时期的楚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物质丰富,经济发达,以浪漫主义为特征的楚文化孕育了瑰丽精巧的造物文明,‘礼崩乐坏’的先秦,是一个思想活跃、社会动乱的变革时期,社会的动乱与变革,思想的解放与碰撞为手工技艺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8]32楚国漆器手工业之所以发达,既有物质因素也有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一,物质因素包含政治和地域生态环境。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政由方伯,礼崩乐坏,致使中央王权衰落,社会秩序失衡,黎民怠工斗争。通商惠工政策的施行,促进了漆器等手工业的发展。战国后期,楚国贵族生活奢靡,楚妆奁的制作也偏重于华丽。南方的楚国地理环境优越,百工管理体制严密,各种精美的髹漆木器得以涌现。铁制生产工具的推广普及,促进了木工技艺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漆器胎骨制作水平,致使楚漆奁等漆器生产得以正规化、专业化。其二,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为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象。楚地道学、巫风盛行,融会、孕育出楚人的浪漫情调和瑰丽想象。楚地之民“信巫鬼,重淫祀”[9]1666,氏族遗风、多元信仰、炽热巫风致使楚人信奉万物有灵,对大自然产生深深的畏惧和无穷的遐想。楚漆奁上那变幻莫测的云纹、涡状纹及各种变形纹样都源于楚人对自然景象、物象的抽象化处理。楚地特殊的社会环境、文化意识、哲学思想、科学水平和人文观念成为这种造物思想的价值尺度和实质内容。楚人特有的神巫之玄想、老庄之精神是构成楚漆奁精神意象的基本因子,促使楚漆奁艺术极具浪漫主义风格,体现一种新的生活风尚和艺术趣味,展现了一种人神交融的艺术境界。
第二,巧和美感之灵。楚纹饰是楚民族文化心理在器物上的投射。[10]203楚人的造物活动中,普遍存在一种饰美心态,饰美源于造物。楚漆奁作为一种造物艺术,既包含设计主体即漆艺工匠的思想,也映射出欣赏主体,即使用者的思想。在楚官营作坊中,工匠遵从统治阶级的意志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造物活动,他们的设计思想与统治者主体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审美观念受制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楚漆奁设计是楚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它的发生与楚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他们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认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心理学上说,饰美是人类特有的艺术禀赋和才能。因此,楚人形成一种爱装饰的习惯和定势。楚漆奁的造物活动反映了楚人的饰美心态。战国中后期,楚国上层贵族的奢侈享乐之风愈演愈烈,促使漆器更加精细奇巧;为了顺应贵族的审美需求,楚漆奁制胎工艺在原来木胎上发展出薄木卷胎、夹贮胎,在制作工艺、髹饰材料等技法上具有更高的审美品位,在形体上更加轻巧美观。楚漆奁纹饰不是对自然现象的简单模拟,而是在顺应自然规律与审美情趣基础上富有视觉空间动感的物化形式,也是楚人为追求神秘意义而绘制图式符号,其中不仅蕴含着大量的风俗信仰,还展现出楚人的文化精神。这种心灵化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对贵族享乐生活的向往和对感观愉悦的追求。楚漆奁所传达和表达的内容具有强烈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属性,其审美观念是多元化和多维度的。楚漆奁的审美观念、思想内涵,既是创造者(工匠)和使用者(贵族阶层)思想的巧和,也是个体与群体思想的巧和。总之,楚漆奁是楚人心灵意象的情感表征。
(三)形之于法:模拟物象窥其法
楚人的艺术史就是一部造物史,也就是一部装饰史。[10]205任何一件漆艺作品不仅具有形式的“表情”,还表现具有形式的“意义”。[11]31追求形式的完美、功能与文化的完善是漆艺设计的目的。《说文》:“规,有法度也。”“律,均布也。”美的规律就表现在宏观的“法度”和微观的“均布”上。楚漆奁之美在“规”“律”中求得动态平衡,在合目的(善)、合规律(真)中得以表现。楚漆奁的装饰纹样特色鲜明,图案形式具有灵巧、生动、流畅、运动的美感。楚国工匠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场景物象高度浓缩于方寸漆奁之中,表现一种生动、自由、唯美的艺术思想。
第一,图案题材。楚漆器图案题材承袭商周艺术风格特征,在此基础上融入楚人特有的文化基因。楚国漆器纹样摆脱青铜器纹样束缚而逐渐分流,纹饰繁丽,风格诡谲,独具神韵,引人入胜。陈振裕将漆器的纹饰分为动物纹样、植物纹样、自然景象纹样、几何纹样、社会生活纹样等五大类。(图7)动物题材图案是楚式妆奁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纹样中最惹人注目的艺术物化形式是凤鸟,凤鸟纹常饰于楚漆奁顶盖的视觉中心之处。凤鸟是楚人的图腾,楚人认为凤鸟是先祖的化身,不仅具有曼妙的身段,还有引魂升天的神性。楚人甚至以凤喻己,象征美好寓意。漆奁装饰的动物纹样还有龙、马、狗、猪、鼠等。植物纹样在漆奁的纹样装饰中占比较小,多用于衬托主要纹饰进行叙事。自然景象纹样在战国妆奁纹饰中一般作为图案的辅助装饰,与动植物纹搭配出现。卷云纹是自然景象纹中的一种重要纹饰,线条流畅,动感强烈。几何纹样在楚漆奁纹样中较为次要,但在图案构成、空间排列上发挥着巨大作用。几何纹样常饰于妆奁的漆盖边缘与器壁的口沿。社会生活纹样在楚漆奁纹饰中出现得最晚,其内容主要是对社会生活的生动再现。例如包山大冢出土漆奁的盖圈上,以长卷画面的形式,绘有表现贵族现实生活的漆画。漆奁盖外壁以黑漆为地,用红、褐、赭、土黄、翠绿、蓝等色描绘了十匹马、四辆车、九只雁、两条狗、一头猪、五棵柳树等形象。画中物象皆来自现实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特定贵族的生活场景,一种反映新的趣味与主题的社会生活场景。画面中的人物身材矮小,体形纤细,印证了“楚俗以细腰为美”[12]533的社会审美风尚。从人物图像上看,主人与侍从头戴獬冠,随从戴帻。帻状如圆锥形冠,下部平齐,无系带,而长沙楚墓漆奁上的女性形象头上之物呈凸起状,是对自然物象的模拟。从楚奁的配饰设计中可以管窥楚人善于模仿但又不囿于自然事物,而彰显楚民族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品格。

图7 楚式妆奁生活图景类纹样②
第二,图案构成。构图是图案的组织形式,像文章的结构,所以又叫章法。[13]50图案构成是指图案设计中各个要素的组织方式与构造规律。楚漆奁的构图方式主要有单独图案、适合图案和连续图案,这三种图案构成方式不是孤立地装饰在漆奁上,而是彼此和谐、互融互生。其一,楚漆奁的单独图案不受器物外轮廓及骨架的限制,在器物面上可以单独成形。其二,适合图案多为外轮廓图案样式,题材多做变形处理,图与器完美融合,具有浑然一体的形式美感。楚漆奁中心适合纹样的构图形式主要有二分式、三分式、四分式,其中三分式最具典型性。其三,连续图案源于商周带状纹样,是战国时期漆奁图案装饰中较为成熟的一种图案形式。由于巧适其圆形之需,目前只见二方连续图案,二方连续图案用于营造视觉形式之美,表达一种节奏、韵律之美感。它具有较强的张力,常常饰于漆奁中心纹饰周围、口沿内外以及妆奁的器壁上。从图像学的角度看,常见的构图形式有三角式、折线式、混合式等。“连续图案的审美内涵就在于表现一种节奏与韵律的美感。”[14]75二方连续图案通过繁复排列设计体现条理、反复的形式原则,秩序感较强。这体现在妆奁图案上,就是对比与变化、统一与均衡形式美法则的运用。另外,楚漆奁在色彩搭配上注重色彩之间的调和关系,既注重整体的统一,又在局部中追求变化。
每个时代器物纹饰风格都与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楚漆奁的图式既是楚人审美观的再现,也是工匠情感的形式表征。出土的楚墓考古资料表明,漆奁这种小型日用器具最早出现于战国中期以后的楚墓中,出土楚式漆奁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地。这些楚墓出土的妆奁图式既具有楚文化的图式意象精神,又渗透了地域特色文化。在湖北出土楚漆奁的图式中,凤鸟纹位于视觉中心,周围饰以辅纹衬托。楚髹漆妆奁中的凤鸟纹主要有两种类型:写实具象型、写意抽象型。在造型方面,写实型凤鸟不囿于具象模拟,而是具象中有意象。湖北包山出土楚墓漆奁的器壁上,描绘有写实性的《车马人物出行图》。这种写实性的连续生活画面,既是一种时代风尚,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写意型凤鸟造型中,楚人善于将事物形象打散、重组进行意象造型,创造出大量超越模拟的变形凤纹。以下是几种楚地具有代表性的漆奁图式装饰纹样。
湖北江陵九店712号楚墓出土的妆奁,有三凤盘旋于画面之上,是为似云似凤的变形凤纹,最具荆楚风韵。楚人有时故意省略和弱化凤鸟的一些部位,突出凤鸟的形体特征,将之置于三分式圆形构图形式中,以增强意象之美与神奇色彩。楚人善于运用变形手法,撷取凤鸟的形体特征,如凤冠、翅、爪、羽、尾等部位,根据需要大胆运用打散、重组等手法,再现新的艺术形态,看似支离破碎,实则意象浑成。方寸之间,凤鸟造型别具新意、趣味盎然。(图8)。

图8 湖北江陵九店712号楚墓出土妆奁上的纹样(左);图9 长沙楚墓出土圆漆奁上的纹样(右)
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圆漆奁,在构图上采用一种向心式旋转图式,在同心圆的外圈饰以“北极星象纹”,与装饰带图案融于一体。之所以“北极星象纹”多次出现在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奁上,是因为,首先,楚国王族曾是掌管天文、制定历法的世家,“北极星象纹”装饰纹样的出现缘于楚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同时也与楚国王族所精通的天文历法密切相关;其次,这种构图模拟了楚人心目中的天体结构;最后,“北极星象纹”能表现出旋转的运动之美。长沙楚墓(M1195:9)出土的圆漆奁,其盖面纹饰自顶部中心至外缘分为四圈,顶部中心圆形内绘有阴阳相对的龙凤纹,龙纹为旋形又似“S”形。围绕奁中心有一圈连弦纹,其上绘有由一昂首奔腾状的小马组合而成的适合纹样以及4个双菱形——4个变异菱形合8数。其外第二圈有4个变形凤鸟、8组外形呈云纹状的组合纹饰,其数位关系吻合于四象八卦、四时八节。因此,顶部中心圆形内的两个龙纹,代表阴阳相生;龙与卷草呈旋形,表示与太极图有关,似卷形表示与大火、心宿有关。漆奁的最外圈装饰圈上,有一些将双菱形上下两个角反向排列的变体纹样,画面极具视觉张力。这与楚国历代祖先曾经从事的“观象授时、点火烧荒、守燎祭天”[15]6等重要活动有关,表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运动感。(图9)
安徽舒城秦家桥楚墓出土的漆奁,黑漆为地,绘以朱色纹样,盖壁与器身装饰有两道“Z”形星斗纹;在漆奁盖面的视觉中心处绘有一小凤鸟纹,周围绘有两道细长的蔓草纹而间以涡纹;外围三圈由卷云纹、鸟纹和几何纹组成同心状装饰圈。内外装饰纹样协调一致。漆奁盖面呈弧形,其造型、纹饰与长沙楚墓出土妆奁的纹饰多有相似。凤鸟、菱形等星纹分别位于漆奁的同心状装饰圈画面中,其菱形纹的数量与四时四季、方位象数有关。
战国早期,西渐影响不显著,楚国发生饥荒,其支系开始从今湖北西部经过巫山、奉节北部陆路西迁入蜀,楚文化得以延伸;战国中晚期,楚国与强秦抗衡,后灭巴蜀,巴蜀漆奁因而一直深受楚文化影响。如四川青川郝家坪41号楚墓出土的凤纹漆奁(图10),其凤鸟装饰与湖北沙市二龙戏珠50号墓出土漆奁上的凤鸟纹如出一辙(图11)。前者作展翅傲立状,后者展翅欲飞,跃之欲出,皆生动飘逸。但从战国曾家沟、青川战国中期墓和荥经秦墓漆奁上出现的“成草”“成亭”烙印来看,其内容多标明产地是成都,这种物勒工名制度早于楚国旧地出土的漆奁。

图10 四川青川郝家坪41号楚墓出土漆奁上的凤纹(左);图11 湖北沙市二龙戏珠50号墓出土漆奁上的凤纹(右)
从战国早期的写实型凤鸟纹饰到后期写意型凤鸟纹样的演变过程中,云纹的运用最为显著。在自然纹样中将云纹与凤鸟等诸多动植物纹嫁接,导致楚漆奁卷云纹出现了对称式、复合式、延长式三种表现形式,由早期的静态图案逐渐演化为更具动感性、自由性的云纹图式,从而形成一种更为自由、飘逸的装饰效果。漆奁上纹饰的演变不仅凝聚着楚国先民的意图与需求,还映射着他们的思想与文化。楚移民不断迁徙,融合当地多元文化,生活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变化,漆奁装饰纹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川蜀漆奁经历了从接受、融合到独立发展的阶段,直至开宗立派,形成特有的漆器图像文化圈,楚人通过漆奁图式表现他们的设计思维和审美情趣。
综上可见楚漆奁装饰纹样的变化趋势:在图案题材方面,早期主要有动物纹样、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中晚期出现了植物纹样和生活场景纹样。在装饰方面,早期以写实型具象纹样为主;中晚期以写意、变形纹样为主,尤其表现在将云纹纹样嫁接于装饰之中。在图案结构方面,早期同心状装饰圈中心以单独适合纹样为主,装饰圈的纹样以由凤鸟几何纹组成的连续纹样为主;中晚期多见于装饰圈中心处的呈现二分式、三分式、四分式的同心状适合纹样,装饰圈上等距分布着大量形态各异的单体菱形纹以表现画面的视觉张力,这与楚国贵族崇拜天文有关。其图式骨骼结构多层分割,主次分明。重叠的带形几何图案的外围是同心状装饰圈,用以辅助纹样装饰。一些以线性立骨的楚漆奁图式图底互生,源于自然物象变幻莫测的视觉元素,是一种生命形式的情感表征。
三、战国楚奁造物艺术的文化意蕴
任何艺术形态都是人们精神意象物态化的结果。楚漆奁的视觉艺术样式与风格面貌蕴含着一种浪漫的激情、充沛的生命力和自由的精神。楚漆奁造物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楚地特有的巫之玄想、道之壮阔是构成其文化精神的基本因子。方寸妆奁蕴藏无限宇宙,楚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事象、情感积淀尽收眼底。
(一)楚漆奁图式中的精神意象
第一,神巫之玄想。巫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被认为是能与神灵沟通的人。巫风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起源于原始社会信仰。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楚国,深受巫风浸染。在列国之中楚巫最为炽热,巫风不仅流行于祭祀仪式之上,还弥漫于日常生活之中。祝融是楚人的先祖,是原始社会巫文化的代表。“先秦时期的楚人崇巫,他们通常依靠神巫的力量,增强超越畏惧、战胜困难的信心,实现精神的坦荡与畅达。周朝立国之后,殷商极盛的巫风逐渐被抛弃,中原的理性精神突破巫术的束缚占据主导地位,地处南蛮的楚地却仍保存和发展着巫风,沉浸在神话世界之中。”[16]17楚国的巫风观念形态不可避免地映射在器具设计中。万物有灵观念根植于楚人的日常生活,也渗透到楚漆奁的造物艺术中。制器尚象既是先秦工匠的设计观念,也包含着社会风尚、民俗信仰以及统治阶级的规范要求。比如从楚漆奁的凤鸟纹饰设计来看,凤是一种虚幻的形象,而非客观形象,凤鸟是楚人敬仰、崇敬的图腾形象,是心灵、精神的象征。漆器妆奁中的凤鸟形象,连接着工匠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写实纹样中,凤鸟纹大多表现出一种激昂飞动的运动之势,凤鸟有的昂首站立,有的展翅欲飞,超然于妆奁之外。在写意纹样中,点、线、面、色彩等元素构成一种极简的形式语言,以凤鸟最具特征的部分作为典型,营造出飞动的形式美感。楚漆器妆奁上的云纹、旋纹、波折纹变幻莫测、幻化灵动。楚人信奉万物有灵,对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自然物象进行抽象化处理,在漆奁的造物艺术中表现审美的冲动和求新、求异、求奇的心理追求。从对神灵的情感寄托到对自然生命的情感移植,楚人的神巫情感折射在楚漆奁的造物艺术中,是以美娱神、寄托情感的表现。
第二,老庄之哲学。信巫好鬼、崇拜神灵是楚人的信仰,而崇道哲学则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楚人的精神世界。崇道哲学发源于楚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庄子都是楚人。“楚地的崇道哲学脱胎于巫,是对巫学的理性化,道家把巫师的宇宙观抽象化、逻辑化之后发展为崇道哲学。”[7]192“道”是自然的本性,人们按照自然法则造物。老庄哲学中的“道”包括世界万物,天地生于道,而“道”则是自古以来存在的,它是无为的。这种思想也促使楚国工匠在艺术创作中随心所欲、追求个性,体现最高审美境界。楚人的精神之游具体体现在庄子的“游心”思想中,精神之游即是人的心灵遨游。[7]192那些刻画在楚式漆奁器物上的浮云运动旋转、灵动飘逸、生生不息,表现出一种神游于宇宙的意味——这似乎与战国楚地初兴的神仙思想密切相关;那些回旋盘旋、周游天地的旋转形式既是神仙之游的形象模拟,也是他们幻想成仙而作逍遥之游的情感表达。老庄美学思想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超越性,超越感性形色和理性观念从而达到自由境界。漆奁纹饰上夸张变形的凤鸟等装饰纹样都体现出楚人超越世俗、超越生命的美感。
(二)楚漆奁纹饰的情感符号
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曾说,“图案具有‘生命’形式,更精确地说,它就是‘生命’形式”。[17]75楚漆奁的图式描绘,表现出奔放、自由的审美风格,承载着楚人特有的生命精神。
第一,艺术生命。皮道坚认为,楚艺术精神本质上就是生命意味的体现,楚漆器艺术的造型与图案形式,是一种运动生命的形式,它充分表明了楚人对生活活力的崇尚。[18]197刘纲纪认为,楚艺术中的生命意味与情感表现联系紧密。比如旋形图式作为一种装饰母题,在楚漆奁装饰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尽显旋转变化特征,整齐一律,产生一种生生不息的运动节奏。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楚漆奁,上面的三凤既有旋动之美,又整齐一律地融于图式中。这种旋纹不仅多见于屈家岭纺轮旋纹、马家窑彩陶装饰上,而且在历代器物造型的装饰设计中一直沿用,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对后世纹样产生了深刻影响。楚漆奁纹饰构形及其漩涡旋转特征,源于楚国巫师通灵的仪式。可见,图案的艺术不仅有其自身的传承序列,而且还具有生命的精神。
第二,情感符号。楚漆器妆奁纹饰不仅是一种装饰手法,也是一种图像符号。从美学角度看,艺术装饰的任何形式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或“表现性的形式”,它与人们的内心情感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凤鸟纹之所以得到楚人的钟爱,是与楚人的凤鸟图腾传统有关。凤鸟纹虽然在西周铜器上具有较强的族源叙事及政治寓意功能,但在楚人的饰美之下,仍然可以找到其现实动物原型。楚漆奁中凤鸟图式的情感符号表征,通过生动的线条、动态的纹样、十足的活力和空间感,生动反映了他们的内心情感。(图12)

图12 楚式妆奁中“C”形凤纹简化脉络③
楚漆奁具有一种超越模拟的意象美,在抽象意识构成中给人一种视觉美感,在整体上具有抽象化、形式化的特征,同时,在局部表现上也进行了抽象提炼。通过幻想与真实、抽象与具象手法创造一种耐人寻味的形象、空间、意境。战国漆奁纹饰推动和丰富了后世装饰的图案范式与情感表征。如果说抽象之形出于原始宗教的需要,那么移情表现则源于泛神论思想——这里的神不是巫神,而是自然万物。庄子认为美在于客观存在本身,四季更替轮回是自然法则,天地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庄子在静观中体悟世界的本原。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观鱼,庄子将自己的情感移植到鱼身上,用“子非我”反驳“子非鱼”。这就是庄子移情的智慧。楚国的工匠也有这种智慧,他们通过模拟自然物象将情感移植到妆奁巧饰中。长沙楚墓(M1195:9)出土的楚奁、安徽舒城秦家桥出土的楚墓(M3:4)的漆奁图式都表明,楚人将天体星象的纹样嫁接到漆奁的形体设计中,以大量形态各异的菱形表现画面的视觉张力。战国末期楚漆奁上出现的大量植物、花草图式,是楚人对自然界生命万物进行移情的重要表现;画面中那五彩缤纷的色彩,表明楚人将情感移植于自然生命而呈现为物化符号,以抽象的几何图形表达审美情感。那些跳跃在楚髹漆妆奁表面的物化符号既是自然生气的体现,更是楚人情感灌注于其中的表现。《髹饰录》“骨肉皮筋巧作神,瘦肥美丽文为眼”,就是说将人的情感移植到漆器的胎体或外形上,使之具有生命,显现人的情感生命。
四、结语
楚国漆器艺术是中国漆艺史上的一座高峰,楚漆奁则是高峰之巅。它是先秦时期先民文明与智慧的物化载体,也是楚人精神意象的物态表征。楚漆奁的造物艺术既受楚地风俗的影响,又有其独特的审美取向。因此,须从对楚漆奁的历史寻绎中探析其设计之用、设计之理、设计之法的文化意蕴。
楚漆奁的设计之用,在于以器合宜。“物尽其用”是一切器物存在的基础,使用功能使之具有价值和意义。在设计之“用”层面,楚漆奁立足于适用,在造物时一要考虑人造物的目的,二要考虑物对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物为人用”的价值理念,一是遵守几何形体中数的设计规矩,二是在视觉心理、文化意识上符合楚人的审美观念。楚漆奁的设计之“理”,在于使器物合于尺度、应于规矩。制造楚漆奁,要遵守当时制器规则,在采漆备料、巧制施艺、成器考核等方面要符合造物规范;要顺时机,循物宜,满足楚人的情理需求。楚漆奁的设计之“法”,在于以器合理。楚漆奁图案上既有商代青铜题材,又有楚人自创的题材,这些题材涉及楚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信仰乃至自然万物。楚漆奁图式兼具具象和抽象,继承商周铜器“三层花”图案结构,发展为多分式适合纹样设计法则。纹样造型层次分明、井然有序,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运动感。方寸之间,包罗万象。漆奁图式不仅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还是一种情感符号,反映出楚人特有的审美观念、生命精神和文化意蕴。
① 《髹饰录·乾集》:“凡工人之作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所以有圣者有神者,皆以功以法,故良工利器。然而利器如四时,美材如五行,四时行、五行全而物生焉。四善合、五采备而工巧成焉。”参见〔明〕黄成著,杨明注《髹饰录》,《中国生漆》1991年第3期,第43-48页。
② 图7楚式妆奁生活图景类纹样,依次为:①人物纹;②植物纹;③~⑦动物纹;⑧波折纹;⑨涡纹;⑩兽面纹;社会生活纹。图片来源:①~⑧、⑩、战国中期包山楚墓;⑨成都龙泉驿区北干道木椁墓群;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群。参见彭德主编《楚艺术研究》,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
③ 图12图片来源:①长沙楚墓;②江陵马山一号楚墓;③湖南临澧九里一号大型楚墓;④包山2号墓;⑤江陵九店东周墓;⑥四川青川县战国楚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