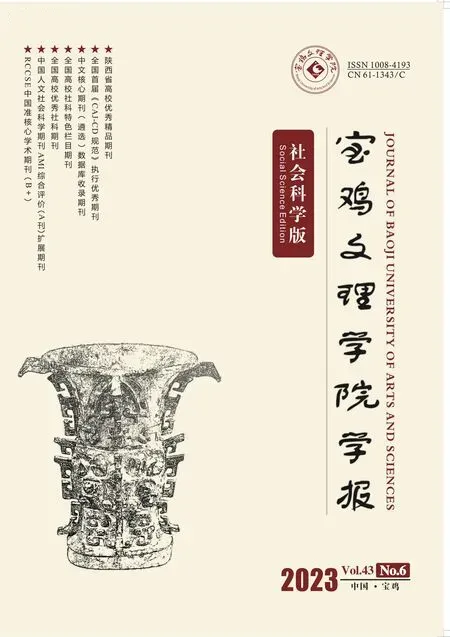“世界诗歌”论争背景下中国现代诗境遇探析*
李雪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包含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打破和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反思。首次明确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歌德曾满怀信心地表示:“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了令人高兴的步子。”[1](P4)在歌德的构想之中,“世界文学”“是由所有文学共和国的居民构成的”[1](P115),它破除了单一民族国家文学的壁垒,构筑出一个跨时代、跨地域和跨民族的普适性文学空间,为一种“世界文学产生的永无止境的螺旋式的霸权和抵抗”[2](P249)提供了可能。在世界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歌德的理想逐渐成为现实,尽管“世界文学”作为一个至今未被明确定义的概念仍在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探讨乃至争论,但总体而言是一个可被接受的中性词汇,对当代跨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后殖民研究等影响深远。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莫莱蒂(Franco Moretti)、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巴斯奈特(Hutcheson Posnett)等西方学者亦在不断为“世界文学”赋予着更多内涵,共同推进着“世界文学”概念的延展,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努力探究着“世界文学”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发表了一篇题为《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的文章①,并于文中提出了“世界诗歌(World poetry)”这一概念。“世界诗歌”与“世界文学”表面上看似乎一脉相承,然而从根本而言,“世界诗歌”并非像“世界文学”那样是一个充满包容色彩的文化理想,而更多是对以北岛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现代诗歌西方化的批评。在宇文所安看来,“世界诗歌”是一种写给国际读者看、为翻译而生、模仿西方的所谓“诗歌”,它披着政治正确的外衣讨好西方读者,以谋求“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奖项的认同。这一不无尖刻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在海外汉学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而其所探讨的诗歌“世界化”特征及少数族裔诗歌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西方视野下的文化政治:宇文所安和他的“世界诗歌”
西方汉学家队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了解中国文化后产生兴趣并着手翻译中国典籍的商人和早期传教士,另一类则是系统接受过中国文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宇文所安即属于第二种类型。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宇文所安,师从著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取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系统而优良的教育,使其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底蕴与汉学专业素养。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宇文所安译介了大量中国古典诗词并以选集形式出版,无论是“唐诗系列”、《杜甫诗》全集抑或《中国文学选集》,其“重塑中国经典”的目的都十分明显——宇文所安编选的诗歌并不以中国读者及研究者的喜好与选择为标准,而是凭借个人视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体系来对中国经典加以编排整合,以图完成“重写中国史”的目标。如此体例与野心,非对中国经典足够熟稔且对自身知识水平足够自信不可完成。
在这样的理路之下,宇文所安对打破中国传统诗歌样貌的中国现代诗心怀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现代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中,诗歌语言方面的试验与出新及至当代则更加具有“先锋”色彩,甚至有意要与古诗的节奏韵律和文化内涵割裂开来。这种富有反叛意味的创新,为中国诗坛带来了近乎全新的挑战,而这正是宇文所安通过北岛诗歌英译这一案例得以管窥到的潜在危机。在《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及十余年后所做的补充文章②之中,宇文所安所提出的中国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过分重视、中国现代诗是否具备系统的理论建构之探讨,以及中国现代诗未来的价值走向等,实际上均是中国学者自身亦在不断反思和探索的问题;而作为“第三世界”非英语国家的诗歌写作者,既希望被英语世界接纳又希望保存自身文化价值的种种矛盾在诗歌中体现了出来,宇文所安实际上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对此表示出了合情的警惕。客观而言,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宇文所安并非没有意识到中国古诗所面临的危机,在他看来,中国古诗“措辞巧妙、充满智慧、典故迭出”[3](P52),但同时也“承载着长久的历史重负,已经濒临绝境,缺乏生机”[3](P52)。对于中国现代诗所进行的文化革新,宇文所安将其看作西方以浪漫主义诗歌为首的“新鲜空气”“渗透到这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中”[3](P52)产生的结果,而对西方诗歌的译介使得汉语的固有文化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西化而易于被翻译的诗歌语言。正因如此,宇文所安主要的不满在于北岛等人诗歌的西化,这是整个中国现代诗需要共同面对且涉及面十分广泛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宇文所安认为少数民族和国家的诗歌要想被世界接受,则需要翻译成英语并获得为英语世界读者所认可的奖项,正是这一违背“诗歌民族性”的矛盾导致了中国经验的倒退。宇文所安为此感到的痛心不仅与其所受到的古典文学教育密不可分,更“显示出他对中国诗歌的丰富知识和热爱以及对世界文学动态的高度敏感”[4](P72)。
然而,中国现代诗自诞生之初即带着打破传统诗歌藩篱、摆脱旧有文化束缚的目的,需要以新的标准来判断现代诗的审美合法性与艺术内涵。尽管宇文所安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维护饱含深情,但其对整个中国现代诗生态的否定未免因涉及面过广而流于偏激。一方面,宇文所安认为中国现代诗是目的性强烈的对西方的讨好与模仿,故而在否定了现代诗的独立价值的同时难免陷入西方话语的逻辑之中——通过设定一个一成不变的优秀中国诗歌典范模式而据此批判所有“不合规”的现代诗,这实际上亦是一种“西方的目光”——宇文所安以其西方汉学家的视角为中国诗歌划定评判标准,便将自身也推至了“中国文化维护者”的地位,这并没有改变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看待少数族裔文学的固有逻辑,即使其原本的出发点恰恰是维护少数族裔文学。另一方面,宇文所安对北岛诗歌的评价实际上是基于翻译版本,那么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翻译和原文在此条件下能否等同。在《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中,宇文所安批驳北岛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其诗歌缺少民族性:“这些‘新诗歌’——中国新诗、印地语新诗、日本新诗——也总是阅读已经翻译的西方诗歌而写成的。”[3](P51)因而这些诗歌不自觉地带有西方语言色彩,当它们被译进西方时会令西方读者感到熟悉。但需要承认的是,即使翻译成英语的中国现代诗看上去与西方诗歌无异,实际上也并非西方作者的创作,其核心更接近于对现代汉语的拓展与延伸。如今,“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伴随着通讯技术及跨国旅行的日益便捷而愈发常见,这些“不同国家的文化基因彼此‘杂合’(Hybridity),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质主义观念,即不再将一国文化看作固有的本源”[5](P141),这种全球化的文学实践以其流动特性而避免了一国一民族“闭门造车”的弊端,而文学的健康发展本应是流动而不断丰富和出新的。宇文所安用固定的标准评判流动的中国文学,并认为中国文学应该像其认为的样貌发展,难免有身处文化霸权中心的西方主义学者所常见的自大之嫌。
二、被遥望的他者:东方民族诗歌的今日困境
早在1772年,被称为“东方学家”的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出版了《诗歌,主要由亚洲语言翻译而成》(Poems,ConsistingChieflyofTranslationsFromtheAsiatickLanguages)一书,探讨诗歌在以亚洲各国为代表的东方的流变及演进情况。在附录中名为《论东方民族的诗歌》(On the Poetry of the Eastern Nations)一文中,琼斯以阿拉伯、波斯、印度及土耳其诗歌创作为例,论证了“他们的作品一定是同类中的佼佼者”[6](P174)的观点,可以被看作西方学者对东方诗歌进行肯定乃至褒扬的先声。彼时囿于语言不通,这些东方民族的诗歌精粹尚未被西方学界所重视,琼斯对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的译介可谓开创之举,以欧洲为首的西方诗歌界得以通过其翻译认识东方。然而,此种状况下产生的问题直到两个世纪之后的宇文所安一代仍然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我们至今依然不得不对诗歌的翻译版本产生怀疑——琼斯等人的西方学者身份使得他难以摆脱自身既有的西方目光,因而被其选择并大加赞扬的诗,是否的确如其所言是东方民族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而这样的“优秀”如何界定(是否能够获得量化标准),以及由谁来界定的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
这便是宇文所安对“世界诗歌”的又一重警惕:西方学者对东方民族诗歌的拣选与认可反过来会影响东方民族的判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往往顺理成章地成为优秀文学的公认典范,而设立这套评价体系和筛选标准的依然是西方。西方话语的优越性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获得东方学者自身的认可,如国内学者李清泉即在《世界诗歌:自由体诗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精神倒退》一文中把北岛的诗歌当作一种文化工具③,认为它是背叛了中文的一场精神倒退。不难看出,该论文的话语模式和中心思想都存在对宇文所安的效仿甚至迎合。当然,众多国内学者更加认同奚密、周蕾等海外华人学者的观点,并对宇文所安和他的“世界诗歌”概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驳,然而,当批驳的出发点在于维护本民族文学创作而未能对种种质疑背后的文化动因进行反思时,一种新的困境正在悄然而生:对西方话语权力的驳斥正在带来一种反向歧视,以致以东方民族为代表的少数族裔文学被夹在一个左右为难的矛盾困境之中。
第一重困境便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东方各民族诗歌,亦即被翻译的诗歌在英语诗歌环境下面临的困境。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在《反对世界文学》(AgainstWorldLiterature)一书中对基于“可译性假定”(translatability assumption)[7](P3)的世界文学表示了怀疑,而诗歌因其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性而更倾向于“不可译”,这实际上为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都在为“文学之可译”做出努力的翻译界泼了一盆冷水。由于语言不通,东方民族诗歌大多需要经由翻译的媒介进入西方,而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西方读者不得不从自身经验出发,试图为这些翻译文本寻找合理的解读。这样一来,语言与文化的双重隔膜使得西方读者离诗歌原文本更加遥远,正如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所指出的“世界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存在巨大的隔膜”[8](P1),身处东方民族的中国诗人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惑:“西方读者读不懂,是否就可以成为拒绝的理由?假如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以及文论在写法上与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完全一致,又怎能体现出中国诗学理论的‘独创性’?”[9](P194)在此之下,中国诗人不得不在“被理解”与“多元性”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北岛及其诗歌便成为这种矛盾之下的“牺牲品”——西方读者将被翻译为英文的北岛诗歌看作对自身的模仿,因而并非中国诗歌,只能被看作拙劣而功利的“世界诗歌”;而诗人北岛因其“中国经验”被称作“中国诗人”,却因诗歌写作面向西方读者而被认为“背叛了中文”。斯坦纳在他的《巴别塔之后》(AfterBabel)中提到了纳博科夫在提及普希金英译本时所宣称的“在诗歌翻译中,除了‘最笨拙的直译主义’之外,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欺骗”[10](P254),诗歌译文所具有的主体性是否能够独立于原诗尚有争论,但翻译导致涵义流失故而带有的“欺骗性”的确容易带来先入为主的种种偏见与遮蔽。与此同时,尽管上述定论均由西方做出,但如同“诺贝尔文学奖”对作家的肯定具有世界性意义那样,西方学术话语权的有效性使得这些定论从诞生之日起就戴上了“权威”的光环,任何一种对它的驳斥都像是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下的自说自话和无力自证。
由此,第二重困境亦即与之相伴的文化批评困境随之产生。宇文所安的文章发表后,最激烈的批评声音几乎都来自华裔学者及旅居西方的离散学者,他们的文化身份促使他们对此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场域。然而,这样的批评声音尽管尖锐,但在西方学术环境之下却难免仍然身处边缘。奚密对全球化时代下民族诗歌与世界诗歌(奚密称为“‘国际’诗歌”)间界线如何划定、是否需要划定的追问[11](P63)实际上并未消弭二者间本质上必然存在的对立;周蕾借以分析宇文所安的“东方主义式偏见和忧郁症候”[12](P167)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仍然是西方的学说。以奚密、周蕾等为代表的批评者长期旅居西方而仍然关注着中国文坛动向,这本是动摇西方中心主义、重置西方文学批评话语权边界的最好例证,然而,这些来自东方“第三世界”的学者因其离散身份而难免被边缘化的结局。一如北岛诗歌译入西方后被西方读者看作对其经验的模仿,这些“东方学者”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发出的声音难免引发“模仿西方学者”的争议;而与此同时,他们远离中国故土,其“中国经验”也因离散和疏远而易被怀疑。在这种“双重不可信”的语言文化困境之中,这些试图抵抗西方话语权的努力显得如此短暂而天真,甚至中国本土学者的声援亦像是一场对西方“诺贝尔文学批评奖”的迎合与追随。
三、中国现代诗的身份问题:在世界文学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国目前仍然是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方民族的代表之一,中国现代诗所面临的困境依然如东方各国一般,甚至因全球化升温后西方世界的关注与期待而带来更多挑战。如同宇文所安这样“文化上过分严厉的审视者”[13](P29)并不少见,他们都在注视并解读着中国。
不可否认,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深受20世纪末的西方诗歌潮影响。无论是红极一时却影响持久的朦胧诗,抑或更具先锋色彩的“第三代”诗,其形式与内容上对西方现代诗的借鉴都非常明显。意象派、芝加哥派、黑山派、自白派等西方诗歌流派不断译介进国内,自由体诗风格影响了一大批试图摆脱传统桎梏、寻求新的表达方式的中国诗人,这些诗人里,就有北岛这样长期旅居西方的“异乡诗人”,异国文化环境的浸染,使得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更深。与此同时,中国现代诗的诗律建构甚至要更早——20世纪20年代开始,即有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对新诗格律问题进行讨论,此后亦有朱光潜、何其芳、卞之琳等学者和诗人提出自己的观点,“新格律诗”倡导、诗歌形式问题论争等中国新诗史上的“大事件”即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然而,诗歌的“格律”(meter)与“节奏”(rhythm)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中国学者所探讨的诗歌格律,实际上更偏向于西方的节奏,亦即哈特曼(Charles O. Hartman)在《自由诗的韵律》(FreeVerse:AnEssayonProsody)一书中所提出的自由诗抛开格律后仍然具备的“韵律”(prosody)。这样的“韵律”具有非固定、一次性的特征,中国学者的例证来源与实践模仿对象大多来源于西方文本。例如,郭沫若使用泰戈尔、惠特曼等人的诗歌范例来论证自己的“内在韵律”理论,闻一多亦采用“音尺”等西方传统诗歌理论来对自己的“新诗格律论”加以支撑。这些前辈学人的理论探讨加之诗人借鉴西方诗歌后的创作实践,使得中国现代诗看上去的确与西方诗歌密不可分。
但正因如此,中国现代诗并非彻底的对西方诗的复制。在接受影响的过程中,中国现代诗人亦不断追求着属于自身和自身所处群体的诗学观念,这是一场基于中文本身的语言更新。每一种被用作日常交流与文学创作的“活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翻译文学、音译外来词汇等的进入,中文也在不断地丰富自身。在今天,现代汉语依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语言,它有着尚不成熟和仍未固定的评判标准。然而,正如国内学者王峰所言:“新诗因为过度模仿和过度无视传统而导致与欧美诗的高度同质化,在某种成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文化自我,这才是宇文所安所不安或忧虑的。”[14](P28)尽管中国现代诗正在随着现代汉语的发展而继续成长,现在就为其下定义和确立地位或许显得仓促和为时过早,但却是需要被考虑的事,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现代诗在世界诗坛的发展前景,更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汉语具备独立性、主体性和民族性的重要保障。如同莫瑞蒂的“树枝与波浪”比喻:“民族文学是对那些看到树的人而言的;世界文学是对那些看到波浪的人而言的”[15](P134-135)——即使占主导地位的英语“吞噬”着其他语言,这种“创新活跃的强势文化对创新颓靡的弱势文化所产生的覆盖性或吞噬性的作用”[5](P143)也无法完全掩没分化出差异来的文化“分支”,这正是民族性不会在世界文学中消亡的证据。基于此,我们应该对中国现代诗歌怀抱信心。
那么,作为“第三世界”东方民族诗歌典型代表的中国现代诗该如何在世界文学之林立足?这是一个值得后辈学人思考和探究的问题。詹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6](P48)西方文学批评及学术体制长期影响着全球人文学科走向,身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及文学研究往往面临被裹挟的局面,但在此之上寻找自身突破点,立足属于自己的价值导向与批评视野,并不断尝试表达自我的新途径,中国学人总会找到适合自身也适合时代的新路。而作为创作者的中国作家们,遵从内心声音,以抛开功利主义概念的“纯文学”帮助卸下民族责任感和为世界认可之心理的沉重负担,或许能够以更轻松的方式进行写作。中国现代诗仍然处在成长阶段,其中能够经历时间淘洗而留存下来的部分必定融合着民族与世界的双重情感共鸣,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留下动人的篇章。
四、结 语
在《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中,叶维廉从古今与中西两个侧面对比评述了中国现代诗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在充满动荡与变迁的现代中国,诗人所面对的问题和焦虑的事物已与传统不尽相同。或许我们的确可以将中国现代诗人的创作倾向看作一种主动的“自我他者化”产物——内容上的明白晓畅与意象的错综繁复使得诗歌“西化”特征明显,而这恰是摆脱“文化恋母情结”后催生出的新的表达系统的诞生。20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神话被逐渐打破,政治与文化的多元性,以及越来越多的“双语习得者”“多语习得者”促使各国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互渗成为可能,中国现代诗的西方色彩正如同庞德等英美意象派诗人借鉴中国古诗意象而创作的“中式诗”一样,都是民族诗歌在世界范围内互通互鉴的体现;而中国现代诗人从边缘向中心的努力,正是打破单一文化、通向“异质融合”的重要一环。传达人类共通情感的诗歌作为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体裁,有待后人继续探索和创新,关于“世界诗歌”的论争也始终警醒着致力于为本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做出贡献的诗歌创作者。因此,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境遇我们或许不必过度担忧,文学发展规律将公正评判文学史长河中的每一首诗篇。
注释
① 该文原载《新共和国》(New Republic)杂志,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2003年,宇文所安于Modern Philology杂志发表了《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Stepping Forward and Back: Issu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World Poetry”)一文,坚持为自身立场辩护。该文于2006年译为中文,发表于《新诗评论》。
③ 在这篇发表于2008年的文章中,李清泉以北岛《八月的梦游者》《我们》《重影》等诗为例,措辞不无激烈地指出北岛的“世界诗歌”“是自由体诗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精神倒退”,“掺杂了太多的非诗因素,因而没有自由的情感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