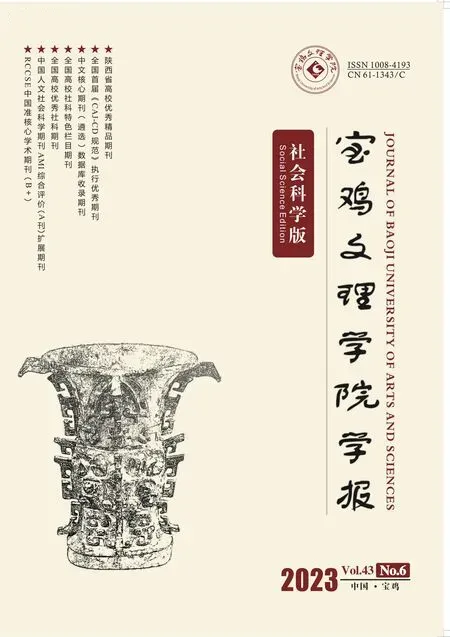私人化表达、类型化叙事与大众情怀消费*
——电影《你好,李焕英》大众作者式生产叙事策略探析
高字民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春节是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档期之一,也是观察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重要窗口。近几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电影行业发展遭遇困境,但春节档期的影片却表现不俗,票房大卖。这期间,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现象是,高票房的强劲势头和对影片评价的激烈争议往往相伴相随。比如,2021年和2023年的春节档票房冠军《你好,李焕英》和《满江红》,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却遭遇了观众和专家评价的两极分化,引发了巨大争议。从研究的角度看,争议即问题。认真直面春节档高票房影片的观众直觉认可和专家及理性观众对其的批评、吐糟,对这两者间的落差,审慎地反思各种缘由,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电影产业研究颇具学术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1春节档电影的票房冠军《你好,李焕英》,可称作中国电影史的一匹“黑马”。喜剧演员贾玲第一次执导大银幕作品就创造了票房奇迹,一跃成为全球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女导演和中国喜剧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导演。目前,《你好,李焕英》以54.13亿元的业绩,高居中国内地影史总票房排行的第三。这样一部投资不大的生活喜剧片,如何能取得如此的商业成功?这样的成功能否被复制?作为一部现象级电影,该片上映后,观众热情追捧,媒体给予肯定,但影视、文艺界不少专家却从专业角度多有诟病,认为《你好,李焕英》不过是一个加长版的小品,其叙事结构、情理逻辑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那么,审美接受上这样的矛盾该如何理解?本来,在票房奇迹的表面热闹之下,这一现实问题理应得到充分关注和深入思考。然而,虽距影片热映已过两年多时间,但应有的思考却暂付阙如,尚未完成。
在笔者看来,《你好,李焕英》的商业成功是电影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意外”和“例外”。作为意外,影片的票房神话不但导演贾玲没有想到,就连专家学者也颇感费解。而作为例外,该片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不仅别人不能如法炮制,导演贾玲自己也难再重复。试想,国内任何一位其他的女导演或女演员可以拍类似题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其一,像李焕英和贾玲这样的真实母女悲情故事世间绝难重复,即便有可能出现极小概率的重复,但也绝少有人能像贾玲这样,把一个悲情的缅怀寄托的故事演绎成一出笑点频发的通俗喜剧。其二,《你好,李焕英》的成功模式,对于贾玲来说,也仅能用一次。即便他的父亲或别的亲戚朋友也有类似的悲情惨烈故事,而她若再拍一部《你好,贾文田》,观众绝不会再买账、像以前那样热情地贡献票房了。
《你好,李焕英》这部“意外”和“例外”的“爆款”影片,对于中国电影艺术而言的意义到底何在呢?它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启示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毋庸置疑,从故事叙述、结构逻辑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细究,《你好,李焕英》的确存在不少差强人意之处。但专家们强调的败笔和缺点,广大观众却没有太当回事。那么,《你好,李焕英》到底“魅力”何在,以至于让观众对其艺术叙事的“问题”采取了选择性回避的态度。这一点,是我们关注和研究该片的关键所在。由此,我们有理由追问该片艺术审美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
笔者认为,《你好,李焕英》艺术生产和审美表达的独特性在于私人化个性表达与商业化类型创作有机融合,在悲喜杂糅中探索喜剧风格的突破创新,在高度假定情境中实现潜意识情结冲动向热情逼真和情感真实的转化。虽是第一次当电影导演,但贾玲在类型选择和情感叙事上,凭着强烈的直觉冲动,立足自身基础优势,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大众作者式”生产的典型案例。
一、私人化表达、类型化叙事和大众作者式生产
《你好,李焕英》是一部个人印迹非常鲜明的影片。由于是贾玲的导演处女作,我们只能说它具备“作者电影”潜质,很难直接称其为作者电影。2001年,贾玲刚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一,母亲李焕英就横遭车祸,意外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打击,给贾玲带来了莫名的惆怅和痛切的遗憾。2016年,她和团队在浙江卫视《喜剧总动员》栏目演出了小品《你好,李焕英》,舞台效果和现场反馈非常之好。作品以亦喜亦悲的艺术形式,实现了编导及主演贾玲对母亲的挚诚缅怀和深情致敬的夙愿,同时也深深打动了广大观众。在对母亲的思念有所释怀之后,贾玲又产生了把妈妈李焕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的冲动——而这,正是贾玲当导演、拍电影的“初心”。面对记者采访,她说:“我不是为了当导演才去拍电影,是为了拍李焕英才去当的导演。”[1]
作者电影理论认为,导演应该身兼编剧,因为他(她)才是影片真正的作者,而作品则是电影作者对其自身生活的个性表达。“特吕弗把真正的电影‘作者’解释为一个把某种真正个人的东西带进他的题材,而不仅仅是在饶有趣味、不爽分毫但却毫无生气地制作出表现原始素材的作品的人。”[2](P250)影片《你好,李焕英》是同名小品扩展版,而小品又源自生活原始素材的“本事”——这条理清晰的“三点一线”,表明了影片鲜明的作者电影气质。然而,与特吕弗的《四百击》、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等高度个性化的作者电影有所不同,《你好,李焕英》的创作是作者式个性化表达和类型片的模式化叙事的调和与融合。表面上看,《你好,李焕英》的个人化经历与体验的影像表达很有点儿像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但相比于《喜剧之王》,《你好,李焕英》却自有其独绝之处——其艺术表达与其说个性化,莫如说是私人化。如果说个性化主要关注创作者内在的精神气质和独立的思想内涵,那么私人化则强调影片直接的亲身素材及其亲密的质感细节。影片《你好,李焕英》以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对话的口吻,通过浓郁的私人化叙事和煽情,淹没了一般作者电影常见的个性化思考及表达,完成了一次类似徐志摩的名诗《别拧我,疼》那样的私情抒发。
作为一部类型片,《你好,李焕英》在个性的艺术追求和独立的反思批判方面都十分有限,但其私人化的情感抒发和素材挖掘却充分、饱满,彰显了创作者鲜明的自我特色。如在片名里直呼妈妈的真名;在片尾叠化展示妈妈的生活照;在片中出现爸爸的真名角色;在情节叙事上,大量地从自己家人的生活“抄作业”;在美工设计上,则高仿再现,逼真还原——这种不避隐私的“高调暴露”风格,在中外电影史上实不多见。如此直接率真的私人化表达,憨拙诚朴的情感倾向,构成了《你好,李焕英》个性独具的艺术风格,突破了一般类型片的叙事常规,催生了当代中国电影一道引人注目的独特景观。
作为一部“准作者电影”,《你好,李焕英》除了原始素材和私人化表达外,到底把什么真正个人的东西带进了这个题材?是海报宣传所谓的“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悯,还是“笑顺爸妈”的温情?细细思之,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因为,以上能引起强烈共鸣“金句”式主题内涵,只是大众对伦理道德的普遍期待,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公约数”。但在《你好,李焕英》中,独特的私人化表达似乎才是导演贾玲真正个人的东西。具体而言,它包含了互为表里的两个层次:一是不避真姓实名、直接坦率的切身性质感,二是发自肺腑、淳朴浓烈的极致化真情。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指出,艺术创作是艺术家被压抑的潜意识的审美升华,“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3](P9)。对普通人而言,白日梦者往往会掩藏自己的幻想,因为来自原始“力比多”的冲动幻想会使他感到羞耻。他担心观众由此产生的厌恶感。“但是当一个作家把他创作的剧本摆在我们面前,或者把我们所认为是他个人的白日梦告诉我们时,我们感到很大的愉悦,这种愉悦也许是许多因素汇集起来而产生的。”[3](P10)为了克服这种“厌恶感”,艺术家必须运用艺术技巧进行审美加工。“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来减弱他利己主义的白日梦性质,并且在表达他的幻想时提供给我们以纯粹形式的、也就是美的享受和乐趣,从而把我们收买了。”[3](P10)
在《你好,李焕英》中,贾玲对妈妈直抒胸臆的呼唤和缅怀,以其前所未有的私情化叙事而有别于其他影片。片中类似“十年生死两茫茫”生活素材及其惆怅与伤感的情感基调,在一般导演那里很可能会被拍成纯粹的悲情片,但以喜剧为生命追求的贾玲,却依循天性选择了喜剧路线,她在私情化缅怀之前“拼贴”了一个喜剧化故事。于是,无论小品还是电影,都采用了“奇幻浪漫喜剧+现实悲情宣泄”的两段式结构。这一喜一悲、一虚一实的两个板块,在叙事结构上“头重脚轻”,在情感含量上却“头轻脚重”。喜悲虚实的不同情感,靠时空穿越的情境假定,被技术化地黏合在一起。这种略显生硬的黏合,既填补了贾玲个人表达私情化和观众审美接受公共性的裂隙,又调和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书写在“读者式文本(readerly)”和“作者式文本(writerly)”之间的矛盾,通过约翰·费斯克所谓的“大众的作者式”书写,创造了“生产者式文本”(producerly)。
“生产者式文本”是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立足罗兰·巴特的“读作者身文本”和“作者式文本”的创造性延伸。在罗兰·巴特那里,“读者式文本”是指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作品,它“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的、被规训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的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4](P127);而“作者式文本”,一般则晦涩、玄奥,“更难、更具先锋性,因此只对少数人有吸引力”[4](P128),它凸显文本的“被建构性”,邀请读者参与文本的意义建构。而“生产者文本”这一范畴,“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对这样的文本进行‘作者式’解读,不一定困难,它并未要求读者从文本中创造意义,也不以它和大众文本或日常生活的惊人差异来困扰读者”[4](P128)。“生产者式文本”不强求“作者式”主动的探求行为,但也不控制这种行为。因为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中,文本的“作者性”无法被阻止。不同于“作者式文本”那种先锋性的陌生化效果,“生产者式文本”的“作者性”来自文本内部松散、无法控制的结局和自我矛盾的悖论,其间的裂隙,大到足以可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来。
就《你好,李焕英》来说,穿越情境中的喜剧故事是通俗的“读者式文本”,但当它被嫁接在悲剧煽情的“私人化”抒情缅怀时,就产生了“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生产效应”,引发了奇异的共鸣。由此,对影片悲喜杂糅的观影过程,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对一个精致影像故事的单向度审美接受,而是面对人生“私人化”情感的互动共鸣,直觉激发。当然观众们都明白,贾玲这个喜剧故事只是导演用以缅怀妈妈李焕英的一个“艺术化由头”。但正是自此过程中,观众自己与母亲的亲情联结在不经意间被激活了。贾玲以“外挂”喜剧的方式,既减弱了她直呼母名这样“私人化”表达的尴尬唐突,又为观众的大众化文本生产提供了可能。这种生产,无需“作者式文本”先锋、晦涩的“高门槛”,具有大众化生产的酣畅与浅白。这一点,从网络、新媒体铺天盖地的反馈留言即可略见一斑。无论是上网搜寻和研究生活中的李焕英的真实经历,还是在微信和微博上晒出自己妈妈的照片,抑或在留言区向贾玲亲切喊话、把张小斐直接叫妈,这些电影观众,以“大众文本读者”的身份热情地参与到“缅怀李焕英,致敬天下母亲”的文化再生产行为中去。这种基于生活与艺术“相关性”的“大众作者式生产”,像滚雪球一样,倍增了影片的口碑效应,成为《你好,李焕英》票房奇迹背后最核心的文化产业逻辑。
二、悲喜混杂、情感复调和“爆笑又爆哭”的正剧
无论小品还是电影,《你好,李焕英》都是“前笑后哭”“头重脚轻”的拼贴复合结构。但若仔细品味,这种“复合”又不同于悲喜交融、“含泪的笑”的悲喜剧,更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剧作家瓜里尼所谓的“悲喜混杂”剧。其复调的情感带来独特的观影体验,也使受众对影片的类型认知存在不小的争议。浏览网络、新媒体,“先笑再哭,直击心灵”“前半场笑哭,后半场哭哭”“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意外惊喜,让人爆笑又爆哭”[5],林林总总的评论不一而足。那么,就戏剧类型而言,《你好,李焕英》到底是喜剧、悲剧还是正剧,抑或悲喜剧或喜悲剧?影片的宣传,基于编导和主演贾玲是大众公认喜剧明星的事实,称此片是喜剧。贾玲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喜剧表演班,毕业后一直说相声、演小品、参与综艺节目,从未离开过喜剧舞台。更何况本片还有开心麻花喜剧明星沈腾助演、相声名家冯巩客串,真可谓笑点密集、“笑果”鲜明。由此,《你好,李焕英》归类为喜剧片,应该没有问题吧?
但我们不妨“较一下真”,从戏剧类型学的逻辑审辨一下。喜剧是笑的艺术,然而喜剧性并不直接等于可笑性。“那些偶然的、无意义的、庸俗低级的或纯生理机能的笑,并不能等同于美学意义上的喜剧性。喜剧性是可笑性、滑稽性的深化,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因素,体现着广泛深入的人生感悟。”[6](P195)黑格尔认为,喜剧冲突的基础在于主观性。悲剧与喜剧的差别“要看在个别人物,动作和冲突起决定作用的是实体性的因素还是主观任意性,愚蠢和乖僻”[7](P284)。在他看来,喜剧世界主人公的主要特征在于其主观任性随意和愚蠢、乖僻。“作为主体使自己成为完全的主宰,在他看来,能驾御一切本来就是他的知识和成就的基本内容;在这个世界里,人物所追求的目的没有实质,所以遭到毁灭。”[7](P284)这也即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喜剧是把无有价值的撕破给人看”[8](P192-193)。
李焕英是在贾玲19岁刚上中央戏剧学院时,因意外事故而不幸辞世的。美好的理想刚刚开始,梦想的蓝图还未展开,最亲爱的妈妈却撒手人寰,不辞而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年轻的贾玲猝不及防,难以接受,以致十多年来都无法释怀。现实是残酷的,往事是凄惨的,但作为一名优秀的喜剧演员,当追忆感伤往事进行艺术表达时,贾玲却天然地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喜剧视角。然而,“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要通过主人公滑稽、笨拙或诙谐、幽默的行动,展现人物主观的任性随意、愚蠢乖僻,或者反思社会的丑恶、荒诞。但很显然,这些内涵元素在贾玲与母亲生活经历的“本事”中并不存在。痛心往事因其严肃基调,也绝不可能被转化成“含泪的笑”的悲喜剧式的反讽调侃。面对悲情缅怀的素材,又要让喜剧叙事能够成立,贾玲不得不凭空敷演一段喜剧性的故事硬性“嫁接”在悲伤抒情的段落上。这样特殊的创作“初心”与前情,决定了《你好,李焕英》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别致的艺术样态。
在2016年的小品《你好,李焕英》中,“嫁接”的喜剧故事讲述了少女时代的贾玲一梦穿越到妈妈的青春年代,邂逅了李焕英“初恋时不懂爱情”式的喜感初恋。少女贾玲,怀着偷窥的猎奇和青春的叛逆,像调皮的爱神丘比特一样,手持神奇弓箭,帮妈妈追求心中的“偶像”欧阳柱,想极力促成一段“傻得可爱”的纯真姻缘。由于贾玲来自“未来”,她知道妈妈李焕英与“帅哥”欧阳柱的初恋只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浪漫际遇。因为李焕英最终嫁的是贾玲的父亲贾文田。由于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心理负担,贾玲可以放开手让妈妈趁“年轻”大胆追求,潇潇洒洒浪漫一回,青春一把!这略带恶作剧色彩的喜剧游戏,在无形中解构了缅怀至亲悲情叙事的刻板印象。贾玲说,在她的印象中,妈妈一直就是个贤淑温婉的中年妇女,她从来没见过妈妈青春烂漫、花季少女的模样。所以,富有喜剧才华的她才斗胆以开玩笑的方式,完成了对妈妈青春年华的天马行空想象。这样的创造性想象既是对一生开朗、乐观的妈妈的缅怀,也是与刻板、严肃的母女关系“幽了一默”。现实中,李焕英是否真有过婚前懵懂“可笑”的初恋并不重要。贾玲知道,她开这个玩笑,妈妈是不会嗔怪她的。因为妈妈天生爱笑,生性豁达乐观。贾玲觉得,她的喜剧演艺之路与妈妈乐天、爽朗精神气质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冥冥之中妈妈对她的“托福”和“神助”。贾玲特意编织了这个稍显离经叛道的故事,以自我的任性、乖僻完成了对少女初恋中的妈妈浪漫、纯真的喜剧化想象。这个故事,既是讲述妈妈的,又是讲给妈妈的。
电影《你好,李焕英》是同名小品的延续、扩展。继小品播出获得广泛好评、赢得强烈反响后,贾玲对妈妈的痛切思念得以释怀,但由对妈妈青春往事的浪漫想象,又激发了她想把妈妈李焕英介绍给更多人的冲动。但从小品到电影,叙事篇幅的扩张,使得以前喜剧主人公的行为动机难以支撑,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在小品中,贾玲梦中的穿越没有专门目的,是一个偶然。她见到母亲,也是不经意的邂逅,意外地发现了妈妈浪漫的婚前秘密。于是,她才像看(演)一出好戏一样,突破伦理旧规,帮助妈妈大胆追求所爱。但扩展到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主人公偶然的行为动机就显得孱弱,无法支撑起更长行动的弧线。为此,编导必须重新寻找,建构更强烈的冲突,激发更有力的动机。于是,贾玲将自我“矮化”,变成了又胖、又笨、又没有出息的“贾小玲”。这一形象,与小品中的少女贾玲已有很大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说小品中的贾玲是诙谐、幽默、爱自嘲,也更爱调皮、搞怪、开玩笑,基本是生活中贾玲的翻版,活脱脱一个嘻哈机灵鬼的形象,那么电影中的贾小玲其喜剧人物的底色已从嘻哈机灵则转为傻笨愚憨。影片一开场,贾小玲由于高考失利,愧对妈妈,故而自作聪明,花钱买了个假录取通知书来糊弄妈妈。不料,高兴的妈妈居然摆了庆贺宴,席间被“成功人士”王琴发现破绽。假象被识破,穿帮又露馅,妈妈为此颜面扫地。小品中的“机灵鬼”在电影中变成了“笨小孩”。但影片中,妈妈并没有嗔怪和批评贾小玲。在回家的路上,贾小玲和妈妈欢声笑语,不料飞来的车祸残酷地夺去了妈妈的生命。深深内疚,让贾小玲充满悔恨与自责,她一面希望渺茫地想挽留母亲的生命,一面想努力弥补过错,做点儿什么事情好能让妈妈真心高兴、扬眉吐气起来。
按照普通人的常规逻辑,贾小玲的努力应该设法提升或改变自己,从而避免让妈妈再次蒙羞,但影片故事中,编导却按照愚笨的喜剧人设路线,刻意强化了贾小玲的“自作聪明”:她肤浅庸俗地认为,妈妈总是被“成功人士”王琴“压一头”,妈妈不幸的祸根在于嫁得不好!于是,她带着强烈使命,穿越回妈妈的青春年代,以期改变妈妈的境遇,让她的人生重焕光彩,更有面子。在遇到厂长的儿子沈光林之后,她想竭力撮合两人“欢迎光临(焕英光林)”的姻缘,闹出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循此逻辑,那么电影中贾小玲肤浅、庸俗、势力、荒唐的人生观、爱情观和价值观最终必须得到清算。换言之,影片应该通过主人公的洋相百出和深陷窘境,把有问题的“三观”否定和扬弃掉,荒唐无价值的东西必须被撕破,且明示给观众。然而遗憾的是,影片《你好,李焕英》在此问题上却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贾小玲对“欢迎光临(焕英光林)”愚蠢而庸俗的撮合,不仅是出于对妈妈的不了解,更是出于对爸爸的不尊重,在一定程度上还构成了对父母爱情的亵渎。设想,如果贾小玲真的被撮合成功,那么贾文田和贾玲将被置于何地?这,是一个关乎“三观”的严肃问题!对此欠下糊涂账,观众一定不会买账。纵观观众对影片吐槽、质疑,针对这一问题的绝不在少数。
当然,为了讲好电影故事,习惯于小品叙事的贾玲还是用了几年时间打磨剧本,做了不少努力。影片通过母亲温情的否定,试图把“糊涂账”问题“抹过去”。神圣的母亲,温顺地配合女儿演戏,与沈光林交往好久之后才温柔地告诉女儿,自己早有所爱。然后镜头一转,推出李焕英、贾文田、贾小玲一家三口温馨幸福的动人画面。但在这里,人物的行动逻辑显然是断裂的。贾小玲那么心心念念的“欢迎光临(焕英光林)”的美满婚姻和成功幸福,怎么忽然间只字不提了?贾小玲任性的乖僻、愚蠢,怎么一瞬间烟消云散了?而李焕英,对贾小玲既没有一句批评,也没有对为什么选择贾文田做出必要的解释。质言之,无价值的东西,这里没有被撕破,有问题的“三观”没有被否定掉。影片从这一场景开始,戛然收敛了喜剧思维,开始转向悲剧煽情。喜剧本应有的理性反思和批判超越,被悲情的眼泪所淹没。前面以“喜剧男神”沈腾担纲的爆笑故事,与后面以贾玲自身悲惨经历垫底的爆哭抒情,硬性“焊接”在一起。在戏剧结构上,这个影片无论怎么爆笑和爆哭,其实质上只能是一部叙事割裂的正剧。前面的笑,是一个敷衍的故事,其主人公无价值的喜剧动机没有得到清算,直接被后面妈妈更高的温情、柔情和亲情所裹挟、埋没。换言之,妈妈李焕英的温柔敦厚、善解人意化解了傻笨女儿为她重找老公的荒唐之举。影片在最后为我们揭秘:李焕英竟然是先于贾玲穿越回过去,专门等待女儿,来陪可笑又孝顺的“笑顺”女儿深情游戏一遭。这个浪漫虚构的圆满结局,虽然煽情且生硬,但却总算让女儿的思念和妈妈的关爱,都得到了平衡的慰藉。
三、母亲情结、穿越情境和大众情怀
作为一部“现象级”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创造票房奇迹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影片两极分化的口碑评价,在中国电影史上实不多见。不少专业导演对此片的高票房表示不屑,也有专家对观众追捧此片颇感困惑。作为贾玲的导演处女作,《你好,李焕英》在情节叙事和影像呈现上难免有不成熟之处。但就是这样一部制作不大、题材现实的影片却为何能创造票房神话?是家庭亲情题材碰巧迎合了春节档“合家欢观看”的节奏,是疫情背景中观众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还是娱乐大众没有太高的精神追求?仔细探究高票房背后的秘密,读解高票房与贾玲独特创作之间的有机关联,对于促进和提升中国电影当代的产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前文说过,《你好,李焕英》是把私人化表达和类型化创作有机融合的“生产者式”文本。这一独特的文本生产模式,紧扣情感宣泄的主线,通过悲喜混杂和情感复调,开辟了一条“爆笑与爆哭硬性嫁接”的煽情正剧的叙事新路。在笔者看来,母亲情结、穿越情境和大众情怀是本片三个依次递进的审美叙事策略。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艺术创作和欣赏与人的无意识(潜意识)结构息息相关。作为这一流派的核心人物,弗洛伊德强调个人无意识,而他的学生荣格则发展了集体无意识学说。“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结构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或‘原始意象’。”[9](P355)荣格认为,“母亲原型构成了所谓的母亲情结(mother-complex)的基础”[10](P59),“与母亲原型相联系的是母亲的关心与同情;女性不可思议的权威;超越理性的智慧与精神升华;任何有帮助的本能或冲动;亲切、抚育与支撑、帮助发展与丰饶的一切”[10](P67-68)。《你好,李焕英》的创作,源自贾玲埋藏心底、挥之不去的母亲情结。李焕英过早地意外离世,让贾玲怅然若失:妈妈生前特别想要一台冰箱和一件绿色的皮大衣,但当她撒手人寰时,这两个愿望都没来得及实现。电视节目《静距离》的访谈中,贾玲说:“从此感觉自己的快乐缺了一角,我越是成功,那个角就越大。”在电视节目《金星秀》的访谈中,她说:“十五年了,我就不敢想这个事。我过得不好,我想躺在妈妈的怀里;我过得好,我想跟我妈妈分享,我想着我妈享受不到这些,我一个人享受有什么用?”
李焕英既是贾玲的生养者与呵护者,又是她的情感源头和精神寄托。对妈妈深深的依恋感和因妈妈意外亡故而产生的强烈孤独感,在贾玲那里凝结为个人无意识的母亲情结;但投射到观众心里,则转化为集体无意识的母亲原型。影片私人化的表达模式和“喜剧故事+悲剧抒情”的“嫁接结构”,衍生了李焕英这一形象作为母亲情结和母亲原型的独特魅力。私人化表达——片名中对妈妈直呼其名的问候、对父母青春年华时场景的仿真还原以及片尾对妈妈照片和生平简历的直接展示,突破了常规观影的心理预期和审美期待,让许多观众不由得联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妈妈。悲喜混杂的“嫁接结构”及其想象的能指,有如让·鲍德里亚所谓的“拟像”(Simulacrum)的拟仿效应,“内爆”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产生了一种“超真实”的“晕眩”效果。影片《你好,李焕英》中的角色李焕英,常常让观众有一种虚实难辨的恍惚感:银幕上,哪些是艺术演绎?哪些是生活实录?这种基于“母亲情结”迷离恍惚的好奇心,引发了观众关于影片背后故事的猜想、搜寻和求证。被触动了的观众,纷纷在微博、朋友圈、微信群里发文、发图、反馈、评论、抒情、感悟,缅怀自己的妈妈及亲人。《你好,李焕英》观影过程,构成了普罗大众关于中国式亲情一次难得的“文化再生产”。
穿越情境的设定,是《你好,李焕英》在剧作结构上的最大特色。李渔说:“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11](P9)本来,妈妈意外亡故的生活经历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常事,但在“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抒情冲动和艺术想象推动下,编导突破现实主义的框范,设定生死穿越的情境,把影片叙事转化成一段率真表达的亲情传奇。通过时空穿越的情境,贾玲让“母女爱”弹出“闺蜜情”的“别调”,在戏剧性的夸张中演奏了一曲温婉动人的情感交响。“穿越”情境,让互不关联的时空偶然并置在一起,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不协调的尴尬误会和滑稽冲突。作为影视与戏剧创作技巧,穿越情境的艺术效果深受观众青睐——电影《大话西游》《古今大战秦俑情》《夏洛特烦恼》《重返20岁》和电视剧《太子妃升职记》都是典型的明证。奇幻的穿越带来的时空差异的陌生化效果,极大地拓展了影片的叙事张力,但也给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除了对不同时空的细节逼真还原外,主人公面对虚拟的时空错乱时复杂的内心矛盾和情感波澜,也必须得到令人信服的揭示。这就需要作者能紧扣叙事的核心冲突,充分理解人物动机,大胆发挥想象,在超现实的时空结构中,探寻人情与人性的可然律之美。
普希金在一篇题为《论戏剧》的未完成论文中曾说:“在假定(规定)情境中的热情的真实和情感的逼真——这便是我们的智慧所要求于戏剧作家的东西。”[12](P277)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则进一步补充道:“我们从自己这方面也要肯定地说,我们的智慧所要求于戏剧演员的也是同样的东西。”[12](P277)与一般穿越影片稍显不同的是,《你好,李焕英》叙事张力的侧重点,不在于穿越时空错位引发的陌生化效果和行为冲突,而在于穿越回过去情境的喜剧氛围和轻松格调——它必须为后面部分的悲情抒怀积蓄动能,制造反差。喜与悲、虚与实的“硬性嫁接”和强烈对比,构成了本片情感基调最鲜明的特色。
舞台小品《你好,李焕英》是三场结构。第一场,是青春期的贾玲和母亲的一段对话,结尾用了一段画外音,含蓄隐晦地表现了妈妈遭遇的不幸场面;第二场,则是穿越到自己出生前三年的贾玲帮妈妈追求心仪男友的喜剧场景。在这一场结尾,不期而至飘来的时针滴答声,提醒贾玲这是梦境。面对这一极富戏剧性反转,观众心里不由“咯噔”一下。一瞬间,贾玲穿越回了后来的时空。舞台上母女虽近在咫尺,但剧情里却阴阳两隔、视而不见了。看至此处,不少观众已泪眼婆娑了。接着是第三场,延续转场时的情境设置,贾玲能看见妈妈,妈妈却看不见她。舞台上,妈妈所处的时空是贾玲童年的光景:这是母女二人共同经历过的难忘的一幕幕,开朗的妈妈一直不停地笑着;贾玲所处的时空,则是她年轻时,即开头第一场的情境。贾玲望着妈妈,禁不住潸然泪下。在舞台表演的同时,幕后还传来了已成为喜剧明星的现在的贾玲和远在天堂的妈妈隔空倾诉的“灵魂对话”。
妈,你怎么那么爱笑?
因为妈生了你呀!
妈,我现在是喜剧演员了,很多人都喜欢我!
妈知道。
妈,我好想你呀!
妈知道。
青年的贾玲、年轻的妈妈、当下母女二人的“灵魂对话”,另外还有一首名为《依兰爱情故事》的插曲——这四重时空,构成了多维交织的复调情境。依托前两场脉络清晰的铺垫,此时的舞台凝聚了超强的情感磁场和巨大的戏剧张力。通过深沉哀婉的悲喜杂糅方式,一种极难表达的复杂情感被酣畅淋漓地抒发出来,直击观众心灵。在电影《你好,李焕英》中,为了适应160分钟片长的更大叙事规模,剧情中的穿越情境,由贾玲一个人的穿越改为贾小玲和妈妈母女二人的“双穿越”。这样一来,小品第三场原来四重时空的复调情境,得以在时间轴线上充分展开。影片中,贾小玲眼望自己裤子上的补丁,忽然领悟到原来母亲是先于自己一步穿越回20世纪80年代的。她既感动又伤心,突然泪崩,一路狂奔,想在最后时刻挽留住妈妈。但突然一跤摔倒,恍惚间,历历往事如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摔跤哭鼻子、出丑拉裤兜、考上省艺校,一幕幕场景在19岁的贾小玲的眼前浮现、身旁上演。这一段落,抒情散文式的笔法与累积蒙太奇的剪辑有机融合在一起。其时空处理,有点儿类似小品《你好,李焕英》的第三场,青春的贾小玲和青年的李焕英虽然同框出现,但女儿看得见妈妈,妈妈却看不见女儿。这是角色同框的阴阳相隔,是虚实相生的镜头内蒙太奇——视听语言建基于戏剧的假定性,朴实无华却极富情韵。
细究片中“母女双穿越”的情境设置,有一个不易察觉的逻辑疏漏必须指出:穿越回80年代的中年李焕英和原在80年代的青年李焕英,应该是两个人——她俩应该在胜利化工厂邂逅才对。两个李焕英,先相遇,再神奇地“合二为一”,才能统一为同一角色。但现在的影片中,中年李焕英穿越回80年代,却直接发现自己的面貌已是花季少女的模样了。但我们不禁要问:原来的那个80年代的青年李焕英,她去哪儿了?难道“人间蒸发”了?此问题虽小,但细节交代不清,逻辑不顺,观众的审美接受是会大打折扣的。
原小品第三场母女画外音的“灵魂对话”,在影片中也得以充分展开,转化为鲜活的场面和具象的镜头了。此时的李焕英,已烫了头,穿上了绿色皮大衣,坐在已成为明星的贾玲的敞篷车里。母女二人谈笑风生,满脸幸福。敞篷车的车号,是“鄂HY1012”。据热心观众考证,这是贾玲妈妈李焕英的名字和生日的代称。接下来,镜头切换,摄影机从另一侧缓缓摇过来,我们却陡然发现,敞篷车里已没有了妈妈。空荡荡的车里,只剩下孤寂落寞的贾玲一人。
戏剧假定的穿越情境与镜头语言的视听创意完美融合,把喜剧的类型叙事巧妙地切换成了私人的亲情抒怀。贾玲对妈妈真情至性的表达,让观众联想到自己的私人阅历,引发了强烈共鸣。由此《你好,李焕英》为芸芸大众提供了感悟家庭亲情、体味悲喜人生的绝佳契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多少家庭经历了生离死别、体验了孤独和分离。2021年春节,当疫情稍稍好转,观众再次重回久违的影院时,贾玲这部抒写挚爱与亲情、咀嚼死别与思念的影片可谓恰逢其时,为大众的情感消费提供了最好选择,也为大众的文化再生产提供了最佳的契机。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部没有高科技和大制作的影片却为何创造了票房的神话。把个性私情与类型规律的碰撞创意激活,在时空的偶然中蕴含文化的必然,影片《你好,李焕英》凭借着其独特的审美艺术表达,暗合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大众文化生产逻辑。这一成功虽然不能复制,但其独具一格的真情表达、审美创造和大胆探索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和启示,却是长久且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