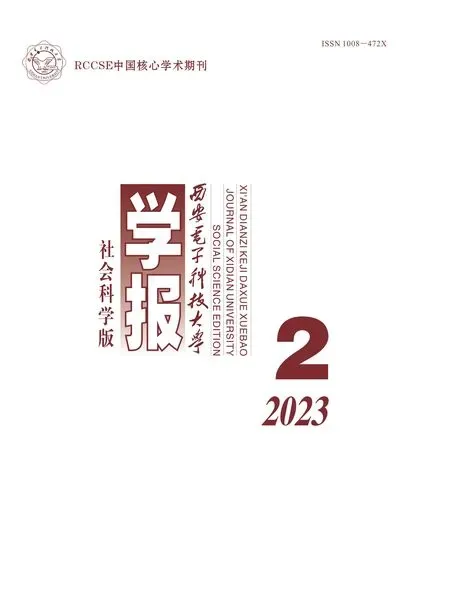全媒体助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机理与路径
夏玉汉,周燕来
■教育学
全媒体助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机理与路径
夏玉汉,周燕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智能化传播是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提升意识形态传播力的重要力量。全媒体时代,媒体发展呈现以网为媒、移动为先、智媒融合的特征,形成了媒体数字化、终端移动化、传播智能化的媒介生态。大数据、算法推荐、计算机视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拓展意识形态传播对象、方法和途径,构成了意识形态数字化传播、精准化传播、可视化传播的逻辑机理。全媒体时代,以智能化传播塑造现代媒介意识形态,核心在于坚持用主流价值驾驭算法的价值导向,重点在于自主创新智能化传播技术,关键在于着力推动一体化传播的媒体融合发展体系。
全媒体;意识形态;传播;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着传播智能化,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是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和经验时指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从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高度,以传播手段和方法创新段加强新闻舆论引导,是意识形态工作守正创新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2]44。舆论格局的塑造关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适应全媒体时代媒体智能化发展趋势,才能凝聚网络空间价值共识、塑造良好网络舆论生态,进而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凝聚力和引领力。
一、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媒体格局
作为生产力渗透性要素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推动传播媒介的发展,塑造出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可以说,“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大众传媒得以不断改进……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工具”[3]。全媒体时代,全媒体以网为媒、移动为先和智媒融合的特点形成了媒体数字化、终端移动化、传播智能化的趋向,媒体格局的新变化为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带来新的契机。
(一)以网为媒:媒体数字化
意识形态传播智能化的动力在于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以网为媒的传播创新建构了数字化媒体,推动着媒体数字化。在传统意识形态工作中,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媒介工具是报刊、广播、电视等,这些媒体有专业机构组建和管控,新闻舆论传播具有权威性、单向性、中心化、结构化的特征。随着网络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传统意识形态工作遭遇到网络新媒体的挑战,尤其是碎片化、互动性、去中心化和去结构化的自媒体的冲击,在全媒体传播场域中意识形态工作在以网为媒的助推下形成数字化媒体传播新格局。在全程、全员、全息、全效传播的全媒体环境中,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打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监测和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互联网空间国家话语权的争夺等要求意识形态工作适应媒体数字化发展趋势,不断抓住智能传播机遇,开拓创新。媒体数字化是媒体机构通过触电入网建设网络新媒体,借助网络传媒技术特别是网络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传播新闻舆论、传递价值导向的过程。这一过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深化,媒体数字化在传播智能化的趋势下不断创新网络传播技术、平台、手段和方法,为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提供了媒介技术基础支撑,塑造了网络生态环境。因而可以说,以网为媒是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前提,媒体数字化构成了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基础,在数字化媒体的推动下智能化传播是意识形态媒介传播的必然趋势。
(二)移动为先:终端移动化
全媒体传播移动化是意识形态传播智能化的重要媒介表征,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推动着意识形态传播智能化转型。1994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的元年,自此互联网技术不断推动着网络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末,面向互联网的舆论宣传推动着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守正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异军突起,智能手机成为现代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调查,截至2022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0.47亿,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27亿,占整体网民的97.7%,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95亿,占网民整体的94.6%[4]。在传播终端移动化的趋势下,智能手机成为网络信息化社会的主要通信、交易、社交、娱乐设备,5G移动通信技术和基站建设推动着全媒体传播理念和手段创新。“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对此要坚持“移动优化策略”[5]。移动优先策略关键在于适应全媒体发展趋势,推动意识形态传播移动化,运用移动终端扩展传播对象,提升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开拓网络传播空间。事实上,移动优先的传播策略为意识形态工作智能化传播创造了条件,智能化的移动终端普及不断扩展意识形态传播的覆盖面,提升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三)智媒融合:传播智能化
人工智能与媒体产业不断融合发展推动着传播智能化,是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核心动力,为意识形态传播塑造了全新的传播生态、催生了全新的应用场景,创新了智能化的传播手段,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俱进。传播智能化指向的是媒介传播的鲜明特征和发展趋向,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着智能传播技术、产业和制度不断创新,形成智媒融合下传播智能化的媒体发展趋势。就传播技术而言,人工智能不断解构传统传播具有的权威性和中心化结构,提升面向用户的精准传播能力,特别是“以算法推荐、机器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则力求满足个性需求,提供智能化传播的技术平台”[6]。在互联网发展之初,人们通过计算机编码、解码实现人类自身的需求,机器智能是人类智能的“执行者”,互联网延伸了人类的声音。全媒体时代,智能化传播把几乎所有民众纳入到互联网场域,数据积累和算法推荐极大地扩展了机器智能的应用场景,AR、VR、元宇宙不断拓展虚拟传播的界限。机器智能不断模拟人类智能,向人类智能快速延伸,互联网放大了人类的声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一些人的声音。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向新闻生产、传播和消费领域渗透,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中越来越在某些功能上接近人类智能的新闻舆论传播工具,特别是仿生机器人和社交软件进入大众视野,如“人工智能新闻主播”(AI主播)、人工智能软件chat GPT等。在媒体融合发展实践中,智能化传播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智能技术、平台和环境,因而以全媒体助推意识形态工作离不开人工智能传播的有力支撑。
二、全媒体助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逻辑机理
全媒体为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环境、途径和方法,也不断消解传统媒介环境下意识形态传播逻辑,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逻辑。以数据为基础、算法为核心、可视化为重点,不断推动意识形态数字化、精准化、可视化传播,形成以传递主流意识形态、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服务网络社会治理的现代智能媒介传播体系,构成了全媒体助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逻辑机理。
(一)大数据:深化意识形态数智化传播
网络新媒体在一定程上实现了信息传播的数字化,大数据则把数字化传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数字化媒介不断推动意识形态传播向数智化方向深化发展。数据化是网络传播的鲜明特色,在网络信息化之初数码技术通过对传播对象的编码和解码实现数码化,为大数据传播奠定了基础。大数据则超越了简单的数码化传播,通过海量数据的存储、计算、分发和使用,在新闻资讯、消费、娱乐和社交等领域形成大数据资源、大数据思维工具和大数据方法,进而推动信息传播数智化。“大数据标志着人类在寻求量化和认识世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拥有大量的数据和更多不那么精确的数据为我们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7]。大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快速的概率计算进行量化分析,以近似全样本数据统计分析的方式描述事物的现象,挖掘事物的本质,透析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
大数据在推动意识形态数智化传播中强化了在数据积累和数据分析中价值嵌入和渗透的意义,意义的建构被嵌入到数据结构中为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提供了新机遇。全媒体助推意识形态数智化传播核心在于通过大数据分析重构意识形态工作模式,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到数据收集、分析、传播等技术领域。一方面,从数据样本收集来看,大数据在数据采集中强调完全样本而非随机样本,在传统传播中主要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进行分析,但这种分析限于样本收集和调查工具往往是不完全的,而在全媒体时代大数据通过扩容数据存储实现传播对象的完全样本收集,在提升算力水平实现数据量化和统计分析,强化了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提升了传播的效率。另一方面,从数据处理能力上看,大数据不仅在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选择和过滤上实现了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而且自动化的“云计算”和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进一步实现了数据分析的智能化,这都催化了动意识形态数智化传播。大数据通过对海量用户数据的动态监测和量化分析,提取传播对象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态,进而分析传播对象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在智能化信息传播中反映社情民意,有针对性的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
(二)算法推荐:推进意识形态精准化传播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推荐对算法的结构和功能进行重构和完善,海量的数据和算力的提升形成了精准化传播,为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提供了重要工具。所谓算法是指“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机器学习能力不断提升,通过计算系统实现对数据的精准收集和处理,进而开展信息匹配的技术能力”[8]。算法推荐则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通过精准化的数据处理实现传播主体和传播度对象的信息匹配,进而实现传播主体的目的,满足传播对象的信息需要。全媒体时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意识形态传播不在是面向所有传播对象的中心化和结构化的单向传播,而是以交互性为基础,以数据的有效匹配和精准推送实现思想理论和社会舆论的传播与引导。
算法推荐的价值嵌入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精准传播,主流价值驾驭算法创新了意识形态话语内容智能化传播的方法和途径。马克思用物质生产过程来理解精神生产,认为“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9]。当算法成为生产力的要素,就一定会成为生产关系调整的渗透性要素,进而影响思想观念和政治上层建筑,算法推荐的价值渗透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算法推荐内在地规定了谁来制定传播的规则与方法、推荐的内容与形式、面向的对象和问题,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传播通过算法权力的使用和规制来实现。当前,在算法推荐的技术支撑下,立足于用户需求、改进信息推送模式、提升用户体验,意识形态理论化话语过媒体融合发展体系进行系统化和精准化传播,在话语的智能传播中思想理论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不断提升。
算法推荐的信息过滤推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防护升级,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构建了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媒介屏障和生态。在网络意识形态场域,杂音噪音和负面舆论往往成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导火索,网络舆情的爆发和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和弱化网民群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认同。算法推荐通过大数据分析以算法模型筛选发现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以气泡过滤的形式对网络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过滤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通过风险的防范、筛查和监测,及时有效地进行有针对性的智能化处理。当前,网络舆论众声喧哗、网络舆情错综复杂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强化算法权力的运用、深化算法伦理的规范、落实算法责任的管理,最大限度地利用算法技术优势精准识别和应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和风险是推进意识形态精准化传播必然要求。
(三)计算机视觉:拓展意识形态可视化传播
人工智能具有的智能已经突破执行简单命令的范围,计算机视觉以深度学习和模拟仿生等技术特征向“认识”客观存在范围发展,这拓展了意识形态可视化传播空间和领域。在传统传播中,以文字为核心的文本构成了传播的主要形式,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和5G等技术的支撑下,声音和图像文本成为新媒体传播的核心内容。人工智能技术在声音和图像文字的符号识别、特征的定位、意义建构及其与文字文本的转化中具有算力优势,物体图像识别、人像识别、美学特征识别等成为机器智能的重要内容,机器智能向人类智能的延伸从“客观世界”向自主反映的“主观世界”发展。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正是在更为智能化的人工智能传播中成为现实,VR拉近了虚拟现实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元宇宙创造了数字化的平行世界,图像化、符号化的虚拟表征为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提供了新场景和新途径。
计算机视觉在新闻传播中不断得到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的可视化研究不断深化,意识形态可视化传播不断适应全媒体传播场景,塑造虚拟传播情境,延伸着图像声音文本的意识形态表征功能。从人工智能助力意识形态可视化传播的媒介业态来看,全媒体推动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化转型,传统媒介在媒体融合趋势下纷纷进行转型升级,在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战略部署下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新生态,打造多样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场景和渠道。从人工智能助力意识形态可视化传播的网络生态来看,虚拟化的传播情境塑造了意识形态可视化传播生态,现实世界的图文声像通过计算机视觉的可视化再造形成丰富的意识形态传播场景,在视界拓展与融合中形成沉浸式的隐形传播环境。从人工智能助力意识形态可视化传播的意义延伸来看,可视化传播把意义的传播蕴含在图文声像的数字化世界中,通过信息的意义建构和解构形成意义的延伸,进而通过算法推荐形成主流价值观的再传播和再建构,在信息的链式传播中凝聚价值共识。事实上,计算机视觉打破了文字传播中读者与作者的空间区隔,以图像化的叙事重构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场景和情境,自然地激发传播对象的意识形态认同。例如,越来越多的线上博物馆通过云游览的形式满足游客的文化需求,VR思政课教学体验等不断丰富意识形态智能化教育形态,AI+文化产业提升用户文化体验,意识形态可视化传播不断推进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传播融合发展。
三、全媒体推动现代媒介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策略优化
智能化传播成为全媒体时代媒介传播的鲜明特征,主流意识形态的智能传播必然在媒介格局之变中遵循其逻辑机理,优化其传播策略。这需要“建立在提高对媒介时代问题的解释力上,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媒介’意识形态”[10],立足于全媒体时代特征,在推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价值导向、技术支撑和媒介格局塑造上不断优化。
(一)价值导向:用主流价值驾驭算法
算法权力的价值引导和规约指向的是算法权力的滥用引起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用主流价值驾驭算法的核心在于把算法权力的运用纳入到推动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正确轨道上来。之所以立足于正确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就在于在资本的裹挟下算法权力带来了技术的异化,技术异化不仅带来了工具理性和功能主义的偏狭观念,而且增加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风险。在算法权力的异化下,通过热搜排名、广告推荐、制造奇闻轶事等形式追求热点、引爆流量、迎合猎奇心理等,进而通过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网络负面情绪等贩卖社会心理焦虑,甚至散播网络社会错误思潮。这些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源自于工具理性催生的技术异化、舆资本宰制下的舆论乱象、差异化和分众化形成的分散传播问题。面对算法权力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风向和挑战,以辩证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在立破并举中发挥主流价值驾驭算法的功能。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治理需要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发展,以价值理性的嵌入、主流舆论的强化、思想理论的聚合形成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正确导向。全媒体时代,智能手机成为现代社会的必需品,通过移动客户端获取和传播信息成为网络信息化社会的基本技能,伴随着巨大便利的同时以计算思维为核心的工具理性认知支配着社会生活实践,进而衍生出技术异化的力量,在资本的推动下工具理性盲目扩张,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异化的社会后果。克服这一力量首先正是技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全媒体时代不能简化为机器智能支配的社会结构和动力系统,而是“建构在‘网络’(net)与‘自我’(self)的互动,以及网络社会与认同力量的互动之上”[11]。因而,主流价值驾驭算法需要从意向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在机器智能参与下的网络信息化社会中嵌入主流价值观念,让机器智能传播主流舆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技术发展理念作为技术与意识形态互动的指导原则,强化智能传播形成舆论共识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构建聚合性传播和网格化管理社群,在强化网络社群治理中推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以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推进网络社群治理现代化,凝聚网络空间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共识,提升网络传播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
(二)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智能化传播
科学技术的作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科技创新是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核心推动力量。作为生产力渗透性因素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具有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在历史发展中具有调节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发挥科学技术的强大功能就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35。事实上,技术创新尤其是媒介技术创新不仅延伸了人的话语方式和话语权利,而且确证了媒介技术在影响意识形态话语权上的特殊重要性,媒介延伸是人自身本质能力的延伸,也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延伸。
智能化媒介技术从话语主体的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的传播方式上深刻影响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也是推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突破口。就话语主体的话语方式而言,以媒介传播为核心的科技创新突破思想僵化的传播窠臼,以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构适合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通过智能化媒介技术创新增强中国话语的传播力、中国故事的感染力、中国精神的凝聚力。就话语内容的传播方式而言,以媒介传播为核心的科技创不断延伸和拓展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领域和空间,以智能技术扩张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应用场景和情境,占领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前沿阵地,挤压非马克思主义生存空间。需要强调的是,以科技创新推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并非一味地强调技术功能及其价值的实现,而是将其置于推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制度基础和文化背景之中,进而实现传播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避免陷于技术功能主义和价值主义的错误观念中。
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体制为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也要求科技创新立足于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断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和良好氛围,教育、科技和人才的一体化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提供了保障。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实践中,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重点,打造现代化的智能传播和服务中心,同时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算法推荐加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传播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和精准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然而,“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12],推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既不能过度张扬科技的工具价值进而被工具理性宰制,也不能忽视科技在推动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中的杠杆作用,而是在强化主流价值对科技创新的引导和规约中实现科技创新和意识形态传播的良性互动。
(三)融合发展:着力推动一体化传播
全媒体助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根本在于处理好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媒体融合发展体系的支撑下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体化传播[13]。所谓一体化传播就是以系统性思维考察全媒体助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这一复杂问题,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全面把握要素、结构、功能和属性之间的关系,全面审视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机遇和挑战,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协同性和时效性。事实上,融合发展不断突破传统传播的时空限制,在互联网思维的导向下媒介划分的标准与界限不断更新与拓展,因而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要“反对‘割裂思维’‘对立思维’‘技术无用思维’‘唯技术思维’”[14],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形成意识形态智能传播的互动性、整体性、辩证性认知。需要强的是,这些认知并非强调各类媒体在传播和结构功能上的简单相加,进而在分散化和差异化传播中弱化意识形态凝聚力,而是把通过各类智能化媒体的互动和协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传播,形成推动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合力。
打造一体化传播的途径在于全面把握技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激发和调动意识形态传播的智能性因素,以智能化传播形成点、线、面全面联动的互动式传播样态。全媒体时代,智能化传播带来的不仅仅便捷的传播方式,同时也蕴含着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如何在全媒体传播战略部署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构起具有全面性、体系化和立体式特征的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15],是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的实践策略。具体而言,以大数据和算法推荐实现用户精神生活需要和主流价值传播的精准推送和合理匹配,以点对点传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性,做到有的放矢。在此基础上,主流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要通过智能化传播手段连点成线,形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辐射和聚合效应,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凝聚思想理论和文化价值共识,如推动不同文化类型和形态以多样化的方式触电入网,尤其是以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元宇宙文化传播新空间。此外,在交互传播中形成以点带面的立体化传播样态,打破传播媒介之间的传播壁垒,减少主流意识形态同质化传播,丰富意识形态生活化传播渠道和生态,在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实践中形成文化和意识形态认同。
全媒体助推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是应对智能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工作要不断“适应社会信息化,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加快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16]。实现这一融合就是要全面审视技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利用智能化的传播技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多途径、立体化传播,凝聚和引领意识形态话语共识,巩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大数据技术、算法推荐、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利用重在发挥其意识形态智能化传播的积极作用,增强其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特别是“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17],以人工智能传播形成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互联网屏障。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4.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5.
[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01-04)[2023-04-01].https://www.slidestalk.com/Apache/StatisticalReport.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8.
[6] 陈昌凤.未来的智能传播:从“互联网”到“人联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35(23):8-14.
[7] (英)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2.
[8] 陈联俊.算法技术的新挑战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举措[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268(4):126-130.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10] 陈锡喜.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81.
[11]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35.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01,318.
[13] 史向军,夏玉汉.全媒体时代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提升路径[J].思想政治课研究,2022,254(2):116-124.
[14] 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68.
[15] 王永贵.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264(6):114-124,156.
[16] 石云霞.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266(8):61-74,160.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4.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All-media Boosting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of Ideology
XIA YUHAN, ZHOU YANLAI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in the all-media era, and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in enhanc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ology. In the era of all media,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is characterized by taking the internet as the medium, mobile as the first, and intelligent media integration, forming a media ecosystem of digital media, terminal mobility, and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big data,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and computer vision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 objects, methods, and channels of ideological dissemination, forming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digital, accurate, and visual dissemination of ideology. In the all-media era, shaping modern media ideology through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lies in adhering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using mainstream values to control algorithms, focusing 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focusing on promoting a media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ystem of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All Media; Ideology; Communi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206
A
1008-472X(2023)02-0146-07
2023-01-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传播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2CKS037);西安市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辩证思维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2ZD3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XJSJ23075)。
夏玉汉(1990-),男,陕西安康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周燕来(1968-),男,陕西合阳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本文推荐专家:
史向军,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张红霞,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