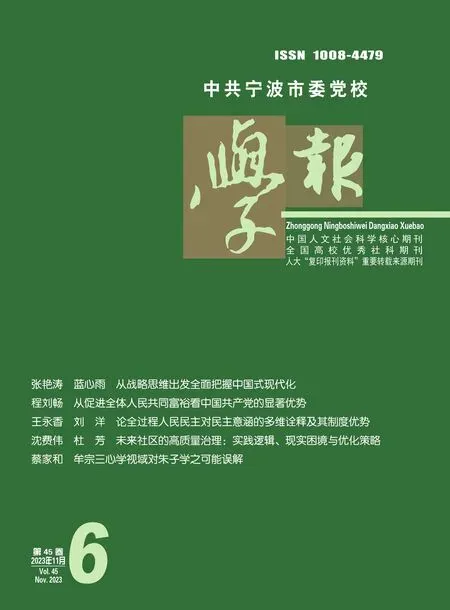林希逸庄学中的以理学解庄略论
暴庆刚,杨小华
林希逸庄学中的以理学解庄略论
暴庆刚1,杨小华2
(1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审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林希逸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以理学解庄是其庄学的重要特点。理学中的“理”或“天理”范畴、宇宙生成论、“天理”“人欲”观,以及为理学家所乐道的“道心”“人心”之论等,皆被其用于诠释庄子思想,目的在于揭示庄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的一致性。林希逸以理学解庄,虽然在很多地方有违庄子之意,却顺应了宋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风尚,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以儒解庄和沟通庄儒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其庄学带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
林希逸;庄学;理学;理;天理人欲;道心人心
宋代庄学是自魏晋之后中国庄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在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背景下,尤其是伴随着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形成,理学的观念和思想全面渗透在庄学中,以理学解庄成为宋代中后期庄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其中又以林希逸的庄学最具代表性。林希逸(1193—1271),字肃翁,号鬳斋,又号竹溪,福清(今属福建)人,南宋末著名理学家,艾轩学派一代名儒,其学本于陈藻,上又可追溯至林光朝、陆景端、尹焞、程颐,其庄学著作有《庄子鬳斋口义》(又称《庄子口义》《南华真经口义》)。林希逸解庄有明确的儒学立场,又因其理学造诣颇深,故理学中的“理”或“天理”范畴、理学的宇宙生成论、“天理”“人欲”观,以及为理学家所乐道的“道心”“人心”之论等,皆被其用于诠释庄子思想,并体现出鲜明的以儒解庄、沟通庄儒的理论指向。
一、以“理”或“天理”范畴解庄
“理”或“天理”是宋代理学中的核心范畴,表示宇宙万物之本体根据,在不同的意义上,“理”也被称作命、性、心等,如二程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1]204又说:“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矣。”[1]274林希逸对《庄子》中的道、生死、古今终始、成心等问题皆以“理”或“天理”进行诠释,使得庄子思想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
理学中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理”或“天理”,与庄子哲学中的“道”具有内涵上的相通性,林希逸即以“理”去解释庄子的“道”。如《庄子·秋水》中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2]588林希逸注解说:“道,总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权,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体,而后有此大用也,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知轻重也。”[3]269林希逸将“道”解释为万物之共同本体,故说是“总言也”;将“理”解释为物物各具之理;“权”则是对“理”的具体运用,然此权之大用最终乃根源于道之全体。在此明显可以看出,林希逸是借用朱熹“理一分殊”的理论去解释“道”与“理”之间的关系。朱熹曾说:“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4]2374又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4]398可以看出林希逸的注解与朱熹的观点基本一致,所不同者,仅在于朱熹只说“理”,而林希逸既说“道”又说“理”,只不过“道”为“理一”,“理”则为“分殊”,本质上与朱熹并无分别。《庄子·知北游》中东郭子“所谓道,恶乎在”之问,庄子答曰“无所不在”,并以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进行说明。林希逸注解说:“此段撰得又好,虽似矫激之言,然物无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说话。”[3]340在此林希逸直接以“理”代替庄子所说的“道”,认为物无精粗,都体现为道“无所不在”之“理”。
林希逸又用“理”去解释《庄子》中的生死问题。庄子在《知北游》中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2]733庄子认为生死是气的聚散变化,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同时生和死又是循环往复的,一种生命形态之生即意味着另一种生命形态之死,反之亦然。因此,生死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2]66,是“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2]733,庄子是从“通天下一气”的超越视角去解释生死现象。林希逸对此注解说:
且如花木之发,为枝为叶,是其生者也,然此已发者,终无不尽之理,则是其生者犹死矣。伊川曰:“复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语极好,便是此意。“硕果不食”,《剥》者,《复》之萌也,谓之硕果,死者矣,种之再生,非死为生之始乎!死生往来,万物皆然,孰知其所以为之者!纪,纲纪也,主张而为之者也。气之聚散为生为死,人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则吾又何患为徒者!死生为一也。死生本一理,万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恶好恶。[3]330
可以看出,林希逸的解释中着意强调一个“理”字,因生者终无不尽之理,故说其生者犹死。又引伊川语说明此意,意为气息出入乃人之生,然复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气息出入的同时亦同时在死,此即是生死为徒之理。又以“剥”卦、“复”卦为例,剥,即剥落之意,硕果喻成熟,喻指生命之尽,所以说“谓之硕果,死者矣”,但硕果之种又可再生,如此则死而生也,所以说“死为生之始”。人们只知道气之聚散为生为死,并进而好生恶死,却不知生死本是一体之理,明晓此理则可不以死生穷达祸福为分别。
在《庄子·知北游》中庄子还说:“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2]746林希逸注解说:“物之初生本无而有,又化而死,则是既有而无。同乎一理,而人物之类,自以为悲哀,愚惑也。”[3]339庄子之意是说,因为生之短暂而死亡又不可避免,故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其中实含有生物、人类皆留恋于生而拒斥死亡的悲情无奈。而林希逸仍是将阐释的重点落实在生死一体之理上,认为物之生是本无而有,物之死是既有而无,生死本就同乎一理,人物不明此理,因有生又有死而悲哀,故为愚惑之行。对于庄子所说的“死生之有待邪?皆有所一体”[2]763,林希逸注解说:“死生之有待,一体而已,一体犹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3]347庄子意在说明死生是相待而存的,因此死生一体,林希逸则将“一体”解释为“一本”,又将“一本”直接等同于“一理”,最终归结为造化之自然,显然是以本体之“理”代替了庄子所说的生死之“一体”。庄子之意,仅在于说明生死一体的客观事实,并无本体论的意涵;林希逸则进一步将生死阐释为本体“理”的体现,带有明显的理学本体思维。
林希逸又用“理”去解释庄子所说的古今终始问题。《庄子·知北游》说:“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2]762林希逸注解说:“无今古,无始终,言太极之理,一动一静,无时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穷,如人之有子孙,不待其有而后知之也,有此人类,则有此子孙,有此宇宙,则有此阴阳,无一息之可间断也。”[3]346以庄子之意,以子孙递嬗相续推测,则天地之前别有一天地,以今推之,古亦应如是,故曰无古无今,无始无终,古今、始终本质上是一样的。林希逸则将无古今、无始终解释为太极之理和造化之理的体现,太极之理即造化之理,体现为一静一动,生生不穷,无时不然,无一息间断;同时太极之理和造化之理又代表一种必然性,即有此人类必有此子孙,有此宇宙必有此阴阳。可以看出,庄子是从客观现象上言古今、始终之无别,林希逸则从本体理上言古今、始终之无别,也体现出明显的理学本体思维。
林希逸又以“天理”解释庄子所说的“成心”。在《齐物论》中庄子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2]56林希逸注曰:“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浑然而无不备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见成一个天理,若能以此为师,则谁独无之!”[3]21庄子所说的“成心”,乃是人囿于一己之见而生发是非判断的偏见之心,成心的存在是导致是非争论的根源,因而是庄子所批判的对象。林希逸却认为成心人人皆有,并认为成心乃人无不具备的浑然“天理”,是人生而现成具备的,因此“成心”即成为“天理”的代名词,这显然是借用了陆九渊心学的观点。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5]4—5又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5]149可以看出,林希逸在此沿用陆九渊心理无二的心学路数对庄子的“成心”进行了理学化的解读,一方面使庄子学说蒙上了理学色彩,另一方面将“成心”解释为积极意义上的“天理”,也是对庄子思想的一种误读。
另外,在《庄子》一书中还有“天游”“天随”“天行”“无欲”等说法,林希逸亦用“天理”解之,如将《庄子·外物》中的“心有天游”解释为“以天理自乐,则谓之天游”[3]425,将《庄子·马蹄》中的“同乎无欲”解释为“纯乎天理也”[3]149,将《庄子·在宥》中的“神动而天随”解释为“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动容周旋,无非天理,故曰神动而天随”[3]165,将《庄子·天道》中的“其生也天行”解释为“行乎天理之自然也”[3]212,如此等等,都是借用理学的“天理”范畴去解释庄子思想,诸如此种情况,在《庄子鬳斋口义》中不胜枚举,充分说明林希逸以“理”或“天理”范畴解庄的普遍性。
二、以理学的宇宙生成论解庄
理学的宇宙生成论模式,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所述影响最大,其中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6]137—138即宇宙是一个“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生成过程。林希逸在《庄子鬳斋口义》中多次以之去解释庄子思想。
《庄子·齐物论》中说: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2]74
林希逸解释说:
未始有物者,太极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无物之始看起来,则天下之理极矣。其次为有物,是无极而太极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极分而为两仪也,两仪虽分,覆载异职,各随其理,何尝有所是非!是非起于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则自然之道亏丧矣。道既亏,则有好有恶,在我则爱,而在物则恶,佛氏所谓爱河是也。[3]28
庄子在《齐物论》中讨论了人的认知层次问题,庄子将之分为“未始有物”“有物而未始有封”“有封而未始有是非”,到最后由“是非之彰”而导致“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的是非纷起阶段。“未始有物”指的是人的认知没有任何分别的混沦状态,也即“道”的未分的混一状态,这是最高认知阶段;其次,“有物而未始有封”指的是已经有了整体的“物”的概念,但还没有对物进行界限的分别;再次,“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是对物进行了分别,但未进行是非的判断;最后则因人的成心而对事物有了是非好恶的判断,最终导致道由成而亏。庄子在此所要揭示的是人的认知由高到低逐渐下堕的过程,人的“成心”是导致是非之争的根源,也是导致大道由“成”而堕为“亏”的原因。林希逸显然借用了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对人的认知阶段进行了宇宙论的解读,将庄子所说的“未始有物者”解释为“太极之先”,也即“无极”,此是宇宙未分的混沦之初;将“有物而未始有封”解释为“无极而太极”,也即宇宙由混沦而至有形的物之初生阶段;将“有物而有封”解释为“太极分而为两仪”,也即形成阴阳对立的阶段。阴阳两仪虽分,但天覆地载各随其理,还没有是非之别。进而人心之私彰露,而自然之道亏丧,于是有了是非好恶。由上可知,林希逸是借用周敦颐的理学宇宙生成论模式去比附庄子所说的人的认知阶段,有意将理学的宇宙论观点融入对庄子思想的解释。
《庄子·齐物论》中又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2]79庄子此言也是承上文论是非而发,按照蒋锡昌的看法,“庄子所以欲推源天地万物演进之时期者,不过欲使人明白后世是非之别,实起于有天地或万物以后,在泰初未有天地或万物之时,固无所谓是非也”[7]145,此言甚确。笔者认为,庄子此意还在于说明,辩者之徒的是非争辩就如在时间的视域中去追问世界的本原一样,会陷于无穷的追问而不具有确定性,因此庄子之意并非在于论述宇宙万物之起源。对此林希逸注曰:“始,太极也;未始有始,无极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无极之上又一层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无而始,故曰有无也者。无字之上,又有未始有无,即无极之上一层也。”[3]32此处林希逸依然是借用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去理解庄子,将庄子所说的“始”和“有”解释为“太极”,将“始”之前的“未始”和“有”之前的“无”解释为“无极”,进而将“未始”之前或“无”之前的阶段称作“无极之上一层”,按照“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模式,“无极”已是宇宙的最终本原,因此“无极之上一层”只是时间序列上的一种形容,即如《庄子·庚桑楚》中所说的“无有一无有”与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
由上述可知,庄子所论述的人之认知阶段问题,其核心并不在宇宙论问题之探讨,作为精通儒释道诸学的林希逸对此不可能不知,但他却有意忽略和转移了庄子的认知论立场,而对之进行了宇宙论的诠释。究其原因,就在于理学所建构的宇宙论是理学的形上学基础,也是对儒家形上学建构向来薄弱的重大理论补充。林希逸将之与庄子所论述的人之认知阶段进行比附,既是其沟通儒道、以儒解庄的重要方式,亦是其对理学宇宙论的一种有意传扬。对于庄子思想中带有宇宙论的观点,林希逸更是直接以理学的宇宙论进行解释,如对于《庄子·大宗师》中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林希逸注解说:“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则自古未有天地之时,此道已存矣,是曰‘无极而太极’也。”[3]109对于《庄子·大宗师》中的道“生天生地”,林希逸注曰:“天地亦因道而后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是也。”[3]109可以看出,在此林希逸也是以“道”为“太极”,道生天地之前的阶段或状态即“无极而太极”,仍然不脱理学宇宙论的路数。
三、以“天理”“人欲”观解庄
林希逸除了多引“理”或“天理”解庄外,还常引理学中的“天理”“人欲”观解庄。作为本体的天理与现实社会伦理问题发生勾连时即产生所谓人欲问题,此也为理学家所尤为关注。按照朱熹的说法,人欲是人的天性没有将天理安顿好而产生,故人欲表现为恶。朱熹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4]223因此天理人欲相对立,“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4]224,所以要存天理而灭人欲,这也成为宋代理学家共同的主张,“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4]207,由此建构起以“天理”为最高道德本体的伦理学说。林希逸在《庄子鬳斋口义》中也自觉运用了理学家的“天理”“人欲”观去解释庄子思想。
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2]83庄子在此讨论的是对道的认知问题,道不可辩不可说,体道所达到的境界即为天府,这里的天府意谓自然的府藏,指的是涵容大道的心胸。“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则指的是在体认大道后而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的境界,完全消除了知性的分别。对此林希逸注解说:“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辩,便是不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则可以见天理之所会矣,故曰此之谓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会也。天理之所会,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满;欲损之而不能损,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无终无始,故曰不知其所由来。”[3]36林希逸将天府解释为天理之所会,将体道的境界跟对天理的认知相比附,进而引出人欲之说,认为“注焉而不满”指的是欲益之而不能益,“酌焉而不竭”指的是欲损之而不能损,也即朱熹所说的“天理存则人欲亡”。显然,林希逸将庄子对道的认知问题诠释为天理人欲问题,与庄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又如《庄子·大宗师》中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2]228所谓嗜欲,指各种各样的欲望;所谓天机,按照成玄英的解释是“天然机神”,也即天然的灵性,“天机浅”可以理解为天然的灵性迟钝。这是讲真人无情虑嗜欲,故其息深深;而世俗之人因为嗜欲太深,故灵性迟钝。庄子在此只是强调嗜欲过多会对人的自然灵性造成消极的影响,林希逸则注说:“嗜欲者,人欲也;天机者,天理也。曰深浅者,即前辈所谓天理人欲随分数消长也。”[3]99这显然也是以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辨去理解庄子。对于《庄子·人间世》中的“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2]150,林希逸注解为:“为人使易以伪,言为人欲所役,则易至于欺伪。唯冥心而听造物之所使,则无所容伪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3]65庄子在此处的意思是,如果人顺从人情则容易产生虚伪,一切顺遂自然而行则可以杜绝虚伪,其所体现的乃道家“道法自然”的理论主旨,并无明显的道德意义。林希逸以人欲天理解之,则使其呈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实寄予了理学家以天理克制人欲的道德伦理观念,但不可否认,这是对庄子思想的过度引申,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庄子的思想。
四、以“道心”“人心”之论解庄
“道心”“人心”之论最早出现于《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至宋代则被理学家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道德善恶问题,成为诠解性情善恶最为重要的理论根据,也成为林希逸诠释庄子思想的重要论据。
如《庄子·养生主》开篇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2]115庄子讨论的是人认知的有限性问题,所谓“殆”,《经典释文》引向氏云“疲困之谓”,意为以有限之生逐无穷之知,则导致人疲困不堪。对此林希逸将“知”解为:“思也,心思却无穷尽。”进而注解说:“以有尽之身而随无尽之思,纷纷扰扰,何时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于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为知为能,吾见其终于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警后世者深矣。此之所谓殆,即《书》之所谓‘惟危’也。”[3]48可见林氏将“知”解释为“心思”,进而将“为知”解释为“用心思算”,从而赋予“知”以善恶的伦理判断,将之归为“人心”之所为,由“知”所导致之“殆”即《尚书》“人心惟危”之“惟危”。通过如此诠释,就将庄子所论的人的认知问题与宋代理学中盛行的道心人心问题相勾连,使之从认知问题转化为道德善恶问题。
在《庄子·人间世》中,庄子通过颜阖将去游说卫君的寓言,揭示说君之难和世故人情之难,又通过叶公子高将使于齐的寓言,揭示处世之艰,对此林希逸说:“此篇名以人间世者,正言处世之难也。看这一段曲尽世情,非庄子性地通融,何以尽此曲折!说者以庄老只见得‘道心惟微’一截,无‘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议论果为如何!但读其书未仔细尔。”[3]71在林希逸看来,道家学派以无形无相之道为其探讨的核心,因此世人多以庄老只见得“道心惟微”一截,盖道家哲学又以自然无为出世为重要主张,故世人多以其不关心现实社会为论,所以无“人心惟危”一截。林希逸即通过《庄子·人间世》中所论,认为庄子其实是性地通融,对“人心惟危”一截也是曲尽世情。因此庄老之学不仅关注“道心惟微”,也没有遗落“人心惟危”的一面。将《庄子·人间世》中所论的处世之艰与“人心惟危”相联系,既迎合了宋代道心人心之论的时代特点,也是林氏以理学解庄的重要方面。
又如《庄子·秋水》对于“何谓天?何谓人?”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勿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2]590—591庄子所谓“天”“命”“真”皆自然、天然之义,如牛马四足之类;所谓“人”即人为,所谓“落马首,穿牛鼻”之类,人为是对事物自然、天然状态之扭曲破坏,故天人对立,因此主张勿以人为灭天,应谨守自然之性而勿失。林希逸对此却注解说:“这数句发得人心道心愈分晓。牛马四足,得于天,自然者;不络不穿,将无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灭天,以故灭命,贪得而殉名,则人心到此流于危矣。三言无以,乃禁止之辞,犹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于此谨守而勿失,则天理全矣,故曰是谓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3]270林希逸认为,庄子关于“何谓天,何谓人”之论将道心人心之别说得非常明晓。林氏所说的牛马四足得于天,故为自然,此颇合于庄子之意。而落马首穿牛鼻,在庄子那里重点在于揭明人为对事物自然之性的破坏,林氏则将重点落实在何以穿落上,即“不络不穿,将无所用”,如此即将重点归为人对外物的功利追求,实是将人为归为与“天理”相对的“人欲”意涵,故说“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灭天,以故灭命,以得殉名,皆是人心之危的表现,对于庄子所说的三“无以”则认为如同孔子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将庄子对人为矫性的批评诠释为对人心危恶的批评。另外,又将庄子所说的自然义的“命”直接说成“天理”,将具有人为义之“故”说成“人事”,从而与宋代理学家尤为重视的道心人心之论得以相接,使庄子的“天”与“人”之辨具有了更为浓厚的道德善恶色彩。
再如《庄子·在宥》中说:“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2]401包括庄子在内的道家在政治上都主张无为,反对有为。无为根源于道之自然,故曰无为乃天道。从无为的内在指向而言,针对的是君王或统治者,故曰“主者,天道也”。此处与无为相对而言之有为,并非道家所批判的违背自然意义上之有为,而是从臣道层面而言之职责上的有为。因有为体现为具体事务之运作,故说有为乃人道,乃臣下之所为。天道与人道或说主与臣的职责分工本自不同,不可相混,故曰不可不察也。因此,此处庄子承认人道或臣道之有为与道家无为的主张并不矛盾。对此林希逸注解说:“此两行最妙,最亲切于学问,但读者忽而不深求之。无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为者也。上句便属道心,下句便属人心,此一累字,便与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听命也。”[3]181林希逸认为庄子此两行最妙,最亲切于学问,就在于这两行所说通于“道心”“人心”之论,上句便属道心,下句便属人心,也即无为而尊之天道自然属于道心,有为而累且不得不为之人道属于人心,并且认为有为而累之“累”即是“人心惟危”之“危”。由此可以看出,庄子所说的天道与人道主要指向于政治上君臣的职责之分,与道德伦理上之道心人心并无关涉,但林希逸却将二者混同在一起,是对庄子思想的一种过度引申。
五、结语
由上可以看出,理学中的重要观念在林希逸的庄学思想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①,以理学解庄在《庄子鬳斋口义》中俯拾即是,上述所引仅是代表性的例证。通过林希逸以理学解庄的个案,笔者想说明的是,南宋中后期,随着理学的成熟和兴盛,理学的观念已经广泛渗透和影响到整个学界,同时伴随着儒释道三教的深度融合,在庄学中大量出现理学的内容,以理学的范畴、观点和思想去诠释庄子的思想已经成为常态,作为理学家的林希逸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林希逸以理学解庄,虽然在很多地方有违庄子之意,却顺应了宋代三教融合的时代风尚,“正是时代精神在庄学发展中的反映”[8]438。其所注解和诠释的《庄子》,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以儒解庄和沟通儒道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其庄学带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而“他在解说《庄子》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儒学化思想倾向,实际上也往往表现为理学化的思想倾向”[9]438,其根本目的则在于论证庄子思想“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也”[2]1,揭明庄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的一致性,进而发掘庄子思想的治世功能,这也是宋代学术重学以致用特征的客观反映。鉴于上述所论,作为理学家的林希逸对待《庄子》的态度就不是单纯一味地排斥,而是以儒家为主导,去调和儒道之间的关系,从而纳庄入儒沟通儒道②。
① 在《庄子鬳斋口义》中也涉及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内容,如《庄子·秋水》中的“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林希逸注解说:“此心广大如四方之外,无所极穷,则无私畦町矣,故曰无所畛域。”(周启成:《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8页)这与陆九渊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3页)之“心”毫无二致。另外,陆九渊还认为心即理、心即道,道即在心中,“道未有外乎其心者”(《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页),林希逸也认为心是道,心外无道,“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无道也”(周启成:《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1页),这显然也是受到陆九渊心学的影响。
② 宋代庄学发展过程中,在庄子对待儒家或孔子的态度上,自从苏轼《庄子祠堂记》提出“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的观点后,就在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为很多人所认同。后来林希逸在《庄子鬳斋口义·天下》中也说:“庄子于末篇序言古今之学问,亦犹《孟子》之篇末‘闻知’‘见知’也。自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至于道术将为天下裂,分明是一个冒头。既总序了,方随家数言之,以其书自列于家数之中,而邹鲁之学乃铺述于总序之内,则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书皆矫激一偏之言,未尝不知圣门为正也。读其总序,便见他学问本来甚正,东坡云:庄子未尝讥夫子。亦看得出。”当然,在宋代庄学中也有对庄子及其思想的激越批判,但调和儒道仍然是主流的趋势。
[1]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3] 周启成. 庄子鬳斋口义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4] 朱子语类[M]. 黎靖德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5] 陆九渊. 陆九渊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6]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7] 蒋锡昌. 庄子哲学[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8] 刘固盛, 肖海燕, 熊铁基. 中国庄学史(上)[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9] 方勇. 庄子学史: 第三册(增补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B223.5, B244.99
A
1008-4479(2023)06-0118-08
2023-06-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释道三教融合视阈下的宋代《庄子》解释学研究”(16BZX045)
暴庆刚(1976—)男,河北邯郸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道哲学、魏晋玄学;
杨小华(1974—),女,河北唐山人,哲学博士,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 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