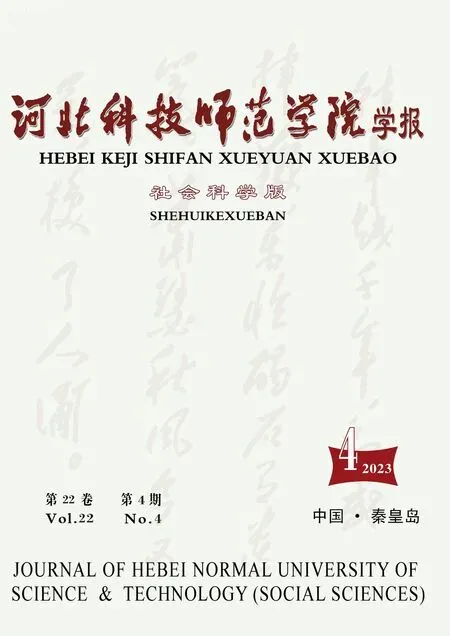当代文学经典生产中的“伦理重建”意识
——以“21世纪新经典文库(第一辑)”为考察中心
彭 婧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危机正在真实地发生着。在一个没有创作和阅读门槛的“后文学时代”,纯文学的经典地位不再是无可撼动的,对文学的传统理解也正在面临焦虑与困惑。然而,总有一群文学经典主义者们仍坚守在纯文学领域,致力于文学新经典的生产与整合。《长篇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纯文学杂志,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编辑部精选一百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辑成“21世纪新经典文库”,其中第一辑已出版完毕,共20本,分别为:阿来的《空山》、毕飞宇的《推拿》、陈彦的《装台》、都梁的《狼烟北平》、浮石的《青瓷》、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贾平凹的《极花》、李佩甫的《生命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刘醒龙的《天行者》、马原的《牛鬼蛇神》、麦家的《风声》、王海鸥的《成长》、王跃文的《爱历元年》、熊育群的《己卯年风雪》、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阎真的《活着之上》、杨志军的《藏獒》、叶广岑的《青木川》和张炜的《独药师》。虽然选择的范围仅限于刊登于《长篇小说选刊》的作品,但入选的作家和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有一定分量,其中大多数都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等奖项,具备进入“新经典”的备选名单的实力。这些作品涉及面广泛,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外,还包括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等类别,既囊括历史题材,又不乏回应现实之作。因此,这由20本长篇小说构成的“新经典”序列,有一定的文学史分量和的考察价值,可以视作当代长篇小说文坛的一个缩影。
《长篇小说选刊》对“新经典”的有意识建构,首先对其价值根基的确立,这种价值根基主要源自于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层认知,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性。因此,这些入选“新经典”的书目绝大多数都是符合现实主义要求的文本,“写什么”重于“怎么写”,这也与茅盾文学奖的筛选标准不谋而合。而“写什么”自然也有一套内在的评判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写作内容必须合规、合矩,有叩问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意识,而这里的“规”和“矩”指向的正是社会主流的伦理价值体系。“伦理”指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是所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但是,随着“后文学时代”的降临,“道德——既是理论意义上的,又是伦理习俗意义上的——正在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与磨难。”[1]传统伦理面临的危机,注定会催生出伦理重建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文学经典焦虑是同时发生的,这二者共同影响了当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面貌。可以说,伦理价值体系的新时代重建,已然成为“文学经典”的生产过程中的潜在任务,也是潜伏在“21世纪新经典文库(第一辑)”(以下简称“新经典文库”)中的一条暗脉。
一、从启蒙到守成:城乡二元伦理的撕裂与弥合
“伦理本位”为近代中国社会构造的基本特征之一。费孝通提出了与“现代都市”相对的“乡土中国”概念,即保留了乡土伦理的中国熟人社会。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存在于一个如向外推的水波般的连续同心圆结构中,“以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2]。李良、韦潇竹在此基础上将“乡土伦理”界定为:“在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时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3]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和深入,费孝通所说的传统乡土伦理已然千疮百孔,并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乡土伦理究竟是负载着“原罪”的“吃人的礼教”,还是被城市文明侵蚀的人类古老精神,这样的讨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反复上演,一直延续到了“新经典文库”所处的当下。
“五四”以来,不少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农村人口最多,文化水平最低,积淀的传统封建文化也最深,它自然应该成为启蒙运动的最主要对象。”[4]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文化批判主题的乡土小说,而鲁迅作为这一流派的先驱者及精神领袖,站在启蒙的制高点上,审视着以阿Q为代表的那些未经开化的“庸众”;继而,许钦文、彭家煌、鲁彦等一众作家接过鲁迅手中的接力棒,对乡村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批判。启蒙俨然成为了内嵌于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中的恒久命题。20世纪80年代以降,鲁迅的“阿Q”形象再次复苏,比如高晓声发表于1980年的小说《陈奂生上城》、韩少功“寻根文学”的代表作《爸爸爸》等,都可以视作对“五四”未完成的启蒙命题的再书写。但是,启蒙命题在继续深化的同时,又在逐渐偏转方向:“阿Q”形象仍然存在,但作家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譬如都梁《狼烟北平》中的车夫文三儿,平日里偷奸耍滑,粗鄙撒泼,凭着莫名的本能冲动、迷信和“精神胜利法”,浑浑噩噩地活了一辈子,俨然是一个换了名字的“阿Q”。但作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对这一类底层百姓的同情乃至认同,并借革命者的口吻道出尽量“少折磨”老百姓的愿望。自始至终,酿成悲剧的与其说是“阿Q”们精神的荒蛮和麻木,毋宁说是支撑启蒙主义的现代政治本身。就这样,都梁借着《阿Q正传》中人物的躯壳,完成了一次对启蒙命题的戏仿与重构,与那些在文学史上站稳脚跟的“五四”文学经典展开微妙的互动与反拨。
“启蒙命题的逆转”不单单是对启蒙命题的反写,此外,当代作家也在寻找“逆转”之后新的价值落脚点,但他们的落脚点总是跳不出文学史上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新经典文库”中接近一半的文本都触及了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与20世纪上半叶的乡土小说相比,当代作家笔下的乡土社会危机,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价值流失上,这是一场比乡村经济凋敝与地主阶级的压迫更严峻的危机。那些担负着“史诗”使命的长篇小说,一旦触及城乡问题,都会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传统道德的呼唤者,为湮没在现代都市文明废墟中的古老精神招魂。当招魂的铃声从文本深处响起之时,现代知识崇拜在那一刻遭到了悬置或是倒转,这是一种对于启蒙命题的质疑与反写。而在20世纪一对此消彼长的文学命题——“启蒙”与“救亡”,它们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后者的完成,进一步转化为“启蒙”(或现代化)与“反思启蒙”(或质疑现代化)的矛盾,文学对于后者的表述,宛如一幕幕呼唤乡土伦理的现代招魂。
在城乡二元冲突的叙事中,从乡土中孕育出的伦理道德经常被视为现代都市文明的参照系,为其提供价值重建的价值依据。在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村精神“招魂者”笔下,文学已经自觉退出启蒙语话,以“他者”的目光打量着喧嚣的现代文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抱有乡土情怀的作家开始了所谓的“寻根”之旅,但这一时期,“当代乡土文学有可能也不应当再背负国族形象的建构,承担启蒙与救亡的重塑,力图表现乡村的进步性与革命性,而是回归到个体的经验与伤痕,真正实录与反思置身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及其情状”[5],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继续探索前行。“新经典文库”选取了近年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如张炜的《独药师》、阿城的《空山》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其中,以梁鸿《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新世纪乡土小说,试图综合鲁迅的文化批判思想与沈从文的怀旧情结,向乡土小说的固有观念发起挑战。《中国在梁庄》一开篇,长期在城里生活的“我”带着儿子坐火车从外部进入乡土,仿佛在重演鲁迅“离去—归乡”式的戏码。到站后,儿子“突然哭着不愿意下车,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6]5。接着,“我”以理性的审视目光,点出“县城火车站的落后与肮脏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个保守小城内在的顽固性格”,显示出典型的启蒙立场。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反思的不再限于县城或乡村的“顽固性格”,而是启蒙立场本身:“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信、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力。而在启蒙者和发展论者的眼光里,这是农民的劣根性……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过于不自信,一切都想连根拔起,直到面目全非。”[6]266梁鸿将矛头直指启蒙立场,质疑历来乡土小说中“农民的劣根性”问题的真实性。在她看来,乡下人所谓的“劣根性”,亦即“阿Q”们愚昧麻木的顽疾,更像是“五四”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以特定的思维和观念建构出来的,虽“符合当时的新知识者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整体判断”[7],但并非事实的全部;而知识分子引为自傲的理性优势,也被梁鸿批评为“对民族过于不自信”。通过对于“反思”的再反思,梁鸿将启蒙的合法性推到聚光灯下予以审视,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自我身份与被审视的对象相连接,在呼唤“伦理重建”之时亦呼唤着一个完满自洽的自我。
然而,启蒙主题可能被逆转,但不会被彻底驱散。事实上,只要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它将永远镶嵌在当代“新经典”的建构理念中,与逆流碰撞出一块块伦理价值的灰色地带。在这一意义上,贾平凹的《极花》虽然饱受争议,但正因为它揭示出了这块灰色地带的存在,反而具备了进入文学史的特殊价值。《极花》从一个被拐女性的故事入手,剑指中国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贾平凹有意无意地将一对相矛盾的主题强行扭合在了一起:一为对被拐女性悲惨命运的书写,一为符合作家写作惯性的城—乡二元对立命题。前者在人道主义的启蒙关怀之下,显得极其触目惊心,圪梁村民众比“阿Q”更甚的野蛮与愚昧,昭示着百年启蒙在今天仍然任重而道远;而后者的存在,将故事所呈现的人性深渊归因于城乡发展差异,并将矛头直指城市——“城市是一个血盆大口,把农村的钱、物和姑娘都吸走了”[8]10,村人拐卖城市姑娘也是出于无奈,而且城市姑娘在结尾处也接纳了乡村,朝着村子深处走去,“去村口的路也看不见了”[8]214。在前一个主题中,《极花》揭示了乡村伦理的“劣根性”,但在后一个主题中,更符合男性利益的乡村封建伦理仍占据上风,甚至不惜以牺牲女性的主体性为代价,在道义上不具有合法性。这两个主题彼此抵牾,相互动摇对方的价值根基。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作家尝试“重建伦理”时的价值两难。贾平凹一代似乎与“寻根”纠缠得太深,但是当“寻根文学”的“根”,已经被叙述为某种暴力的源头时,他们一以贯之的文学主题又该在何种意义上成立呢?另一方面,《极花》又恰恰反映出了作家在面对乡村伦理重建时的焦虑心态,这种焦虑使得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再度被叙述为罪恶之因。而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城市女性,作为乡村与男性双重层面上的“他者”,在被拐后也只能归顺于异化的乡村的封建伦理,这无疑宣告着启蒙命题在人性内部的溃败与投降。
城市和乡村是空间概念,却与一系列与线性时间有关的概念捆绑在一起,被描述为现代与传统、启蒙与守旧等对立的两极。于是,这对貌似天生矛盾的宿敌就在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循环厮杀。此外,由乡土伦理背后的前工业时代价值体系还延伸出了另一个命题——生态伦理。乡土精神的覆灭与自然生态的破坏都是人类文明为城市的疯狂扩张所付出的代价,只不过生态小说将城市与乡村的文明对峙置换为了人类与动物的生存竞争而已。纵然政治和经济现实总是充斥着大量复杂含混的事实,但是,文学作为一个承载着无限可能性的精神之邦,能否突破这种单向度的零和博弈思维,探索实现城乡和谐共存的新路径?如果21世纪的“新经典”想要创造出一套不同于20世纪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叙述模式,就不能不正面应对这个问题,更何况,如今的时代也正在找寻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从分庭抗礼到归顺妥协:性别伦理的对立与整合
家庭的伦理本质是社会伦理共同体,即以家庭伦理关系为纽带、伦理结构为支撑和伦理功能为血脉的伦理规范体系。然而,“随着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性解放,建立在传统‘血缘—宗族’观念之上的等级式家庭伦理共同体关系逐渐裂变,以自由意志为核心的契约式家庭伦理共同体关系日益突出。”[9]现代文学史视野中的女性写作的合法性,可追溯到晚清的民族危机、“五四”时期的女性启蒙以及共产主义语境下的革命生产话语。20世纪80年代以降,个人话语的再度兴盛促成了新一轮的性别觉醒,继而出现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一派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她们撕破一切伦理的外衣,将性别中的自由意志发挥到极致。步入21世纪后,随着现代性个人理想主义式微,“家庭”共同体渐渐恢复其强大的召唤力量;与此同时,一些女性作家表露出对“女性写作”标签的排斥情绪,她们尝试着以一种整合性的力量来弥合性别间的鸿沟,在一个较为稳固的伦理体系中继续创作,而这种伦理体系恰恰是21世纪“新经典”的建构所需要的价值根基。因此,在多方面的作用下,女性作家的写作开始显示出向日常生活与家庭伦理靠拢的趋向。
显然,能够入选“新经典文库”的都是经过某种标准过滤后的文本,那么那些活跃在20世纪90年代、“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10]的女性能否作为正面形象编入“新经典文库”之中?这背后不只是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从接受层面看,今天的读者是否还能接受超出伦理价值体系以外的女性?他们又是否能接受对这一类逾矩女性作出价值肯定的文学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重要的不是后人到底会为时代筛选出哪些经典,而是今天试图想把什么样的文学确立为“经典”。至少在一个道德感至上的时代,人们想为时代留下符合今天的价值理念的作品。越来越多的女性写作选择回到伦理秩序之中,这或许意味着妥协,尽管很少会有女作家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留给她们书写的题材非常广泛,使得她们可以自如地绕开两性战争,在伦理秩序许可的范畴之内尽情舞动,并在相对保守、稳妥的价值评判体系中获得认可。
在“新经典文库”收录的20部作品中,出自女作家之手的仅有3部,分别为叶广芩的《青木川》、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王海鸥《成长》,基本延续了20世纪文学经典中不平衡的性别构成。不过,这3部作品基本代表了近年来女性写作的几种走向。其中,《青木川》将女性形象与性别意义之外的宏大价值观念结合,对历史传奇进行还原与重构,其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在与“悬疑故事、文化考察、乡村写作”等诸多模式相结合后,变得端庄、包容而充满力量,几乎不会与传统伦理发生激烈冲突。《成长》和《中国在梁庄》都落笔于现实题材。编剧出身的王海鸥善于讲述婚姻生活的琐碎俗事,而自称为“文化批评者”的梁鸿则对乡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宏大议题更感兴趣,尽管题材不同,但她们都选择了相对理性、克制的笔调以隐藏性别立场。纵观“新经典文库”中女作家,以及部分男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不难看出“新经典文库”想要为文学史留下怎样的女性典范,她们是默默承受着苦难的伟大母亲(《成长》中的田海云和安叶、《中国在梁庄》中的五奶奶等),是在贫穷的土地上奉献自我的乡村女教师(《青木川》中的程立雪、《天行者》里的夏雪等),是响应革命伦理号召的女战士(《风声》里的李宁玉和顾小梦、《狼烟北平》里的罗梦云和杨秋萍等)。这些女性的价值取向都是向外敞开的,她们认同的是在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中才能显现的伦理道德,而非内在的自我价值。
在这3部作品中,最直接地展现女性自我价值与伦理道德的正面对撞的是王海鸥的《成长》。从表面上看,“成长”的主体是男性,然而,在这位女作家、女编剧的笔下,男性的“成长”却回到了一个宿命般的原点,他将重复父辈的人生历程,而承受着这一切的两代女性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接二连三地在为人母、为人妻的伦理道德面前投降。与之相较,20世纪90年代类似题材的女性写作将主战场放在了两性战争上,女性以“黑夜”的名义向男性主导的“白昼”发起反击,目标非常明确,但在《成长》中很难找到具体的、确切的诘难对象,仿佛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即使女性最终被逼回了家庭,但出于伦理的内在要求,她们也不可能归咎于与自己血脉相通的孩子,尽管是孩子的出现才使得她们开始接受以“母性”为名义的社会角色修辞的。但是,也正是这种由社会建构出的“母性”,被描绘成了女性“成长”的战利品,而这种战利品却反过来将女性逼回了家庭。可悲的是,21世纪小说中的女性依然在重演子君(鲁迅《伤逝》)、沁芝(庐隐《胜利之后》)一代的悲剧。一旦确定了伦理体系中的自我定位后,新一代的母亲们便开始以母职的崇高标准塑造自我,克制欲望,恪守规范,拼尽全力地捍卫这一以极大代价换来的人生角色。这种角色分工为小说带来了戏剧性的情节,也将一个自“五四”以来困扰了人们多年的问题再次抛给读者:究竟怎样才能在不牺牲女性的社会价值、消解“母性”神话的前提下实现家庭的共利性幸福?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相比,“新经典文库”所收录女作家的作品与之在对伦理道德的态度上出现了分歧,前者是对男性主导的伦理价值体系的激烈反抗,而后者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对于新的伦理价值体系的重建期待,而且这一期待是在某种和解的基础上发生的。这里出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当中国社会的整体价值认同外移时,女性更倾向于在性别内部寻求自我认同。“五四”时期,儒家伦理体系的崩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男尊女卑、子承父位的固有观念,女性意识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作为“五四”精神在新时期的自觉展开,在反传统的意义基础上再度倡导个体意识觉醒,质疑并解构传统的历史修辞,在整体化的启蒙语境中愈发趋向激进。而今天正处于一个夺回自身历史、宣扬文化自信的时代,儒家的中庸主义覆盖了反抗既有秩序的激进情绪,经过筛选后的“伦理本位”道德观念开始召唤新的受众。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认同对象向伦理价值体系外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建成规的死灰复燃,在理想的情况下,女性也能够作为一股积极力量参与到伦理重建的行列之中,因为她们在重新整合伦理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过滤、改造这一体系,寻找通向家庭共利性幸福的可能性。
三、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战争伦理的反思与超越
阿佩尔曾提出了一种能够约束全人类的伦理学概念——普遍伦理学,并申明了这一概念对于当下的重要性:“一方面,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也即对某种能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迫切。另一方面,为普遍伦理学奠定合理性基础这一哲学任务,似乎也从未像我们这个时代那样困难重重。”[11]随着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现有的伦理范式很难继续解释和应对当下错综复杂的道德状况,而“普遍伦理”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道德活动空间的变动及其所带来的伦理危机。当伦理危机的挑战变得愈发严峻,人们或许可以向已经成为历史、又与今天密切相关的20世纪历史索取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因为20世纪是一个将人类的全部伦理撕裂的时代,也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弥合人类矛盾、重建伦理秩序的初始点。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像某种历史标记,直到今天仍在以各种艺术方式被不断再现。仅仅在入选“新经典文库”的20个文本里,涉及抗日题材的就占了五分之一,包括都梁的《狼烟北平》、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麦家的《风声》和熊育群的《己卯年风雪》4部。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各有侧重,分别演绎着21世纪文学再现历史的多种可能。《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基本延续的是新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立场和风格,它所展露的残酷之处,与其说是在于“屠杀”二字,毋宁说是在于虐杀对人类道德底线的突破,指向了伦理道德的撕裂以及人性的至暗深渊,而整部小说自始至终都是以一种道德审判的姿态去再现历史、点评历史。以这一文本为参照,“新经典文库”的其他3部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主流的历史叙述方式,体现出将战争伦理置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中加以反思的立场和倾向。
和《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一样,熊育群的《己卯年风雪》表现的也是“屠杀”题材,但作家不再仅仅为读者提供单向的理解视角,而是站在人类的整体性视野来审判战争,乃至审判人类群体本身,因为战争是内在于人类文明的暴行,恰恰是人类自己撕开了弥合内部矛盾的普遍伦理,召唤出了伦理道德出现以前原始、野蛮的兽性幽灵,而《己卯年风雪》真正揭示出了这种兽性幽灵在文明社会中潜伏的普遍性:日本侵略者同样是有着完整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的“人”,但他们最终为古老的兽性幽灵所吞噬。如出生于教育世家的武田修宏,自小怀揣着文学和哲学的梦想,在战争爆发前正处于享受爱情的青春年华。然而家人的殷切期待、“圣战”的冠冕堂皇的说辞以及国内狂热的爱国主义潮流,将他不可避免地推向了战场。尽管他深知“战场就是一个工场,一个人类重工业的屠杀场”[12]49,但随着战争的深入,为战友复仇的狂热欲望使他丧失了理智,终于沦为残忍、麻木的杀人机器。小说中一次次地上演各种错认情节,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国风景与日本风景交叉叠合,不同立场的人物恍惚于爱恨之间,但在故事最后,凭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道义认同,杀戮的幽灵失去了血与仇恨的滋养,人与人的关系在超越民族、国家的人性范畴内得以重建,这也正是“伦理”原初的内蕴所在。正如洪治纲在该书收录的评论中所写下的:“人毕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伦理的存在。在黑暗的深渊,我们依然看到,还有温暖的人性之火在闪耀。”[12]9在麦家的《风声》和都梁的《狼烟北平》中都存在类似的主题,只不过将战时对峙的双方换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而已,而支撑文本的价值观念,实际上与《己卯年风雪》是相似的,都是在反战主题的笼罩下强调消弭矛盾、重建现代伦理的必要性。
相比于历史小说是否真实还原了历史,文学研究更关注的是作家是在何种时代语境下,以何种立场、何种方式书写历史的。其作品入选“新经典文库”的大部分作家都成长于和平年代,并在青年时期接受了人道主义的熏陶,这使得他们在回溯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时,不约而同地站在了超越战时伦理标准的立场上,以一套新的伦理道德标准重写20世纪的战争。他们在描摹敌人之可鄙的同时,亦将“他者”视作自身的镜像,在相互镜鉴的双向关系中达成基于人性层面的情感认同。因此,在故事的最后,被战争撕裂的伦理在多年后渐渐弥合,被战争一分为二的人类走出了战争,并试图重新构建人类内部的完整性——一个迷人的乌托邦诞生了。文学对于人类普遍伦理的呼唤,与阿佩尔所提出的普遍伦理概念相互呼应,相互印证。文学从最残酷的屠杀中建构出最理想化的人类伦理,并以此照耀着人们身处的时代。
道德重塑是新时代推动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环节,没有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道德,就不可能会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伦理是与道德相伴的概念,不仅维系着一个群体外在的道德秩序,还组成了群体成员内在的心灵秩序,是“民族史诗”内在的价值根基。因此,对于以《长篇小说选刊》的“新经典文库”为代表的有文学经典建构自觉的新世纪书系来说,“伦理重建”意识成为了它们潜在的选择标准。但这种试图整合伦理秩序的意识在文学实践中并不算顺利,尤其是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等固有的现代性二元冲突,仍在困扰着当代作家的创作;而小说中超越种族、国别的人道主义精神,虽然弥足珍贵,但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来看,也很难说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构想。但无论如何,透过“新经典文库”的入选作品名单,还是能够看到当代作家在创造“新经典”时较为自觉的“伦理重建”意识和探索精神,以及他们在伦理层面试图弥合矛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而这些都在或隐或现地改变着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文学的面貌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