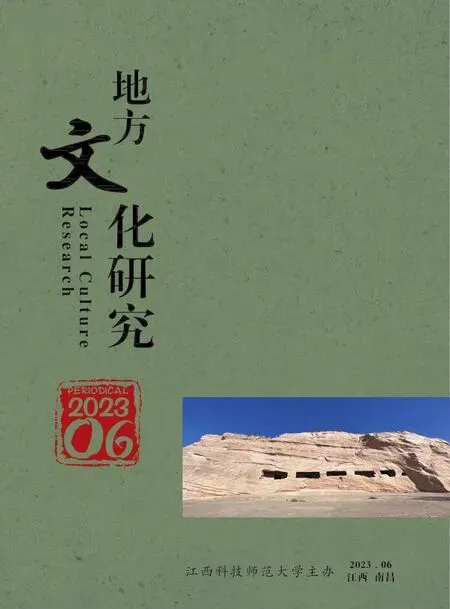太平军入徽的底层记忆与地方书写
王玉坤
(安徽工业大学,安徽马鞍山, 243002)
太平军与清军在徽州反复争战十余年,几与金陵战事相始终,战火所及,创痛巨深,地方随之由繁盛走向衰落。 近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徽州研究渐成趋势,研究视域不再局限于整体战争创伤的延展,而开始顾及社会群体内部的差异,涉及商人、士绅、宗族、团练及官府等诸多要素,论析战争前后徽州社会的兴衰递嬗,以此呈现太平天国战争运动的地方缩影。①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601—622 页;唐力行:《“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史林》2007 年第2 期;冯剑辉:《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考辨——兼论徽州咸同兵燹》,《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2 期;郑小春:《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安徽史学》2010 年第3 期;梅立乔:《兵祸与文化传承——以晚清徽州为例》,《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第2 期;舒满君:《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捐输运作与战局演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4 期;袁为鹏,龚达:《从徽商账本看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徽州地区的货币使用》,《江海学刊》2023 第1 期。相形之下,作为这场战争最广泛的参与群体——普通民众,其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情感体验与身体记忆虽屡被论及,②王振忠依据著名徽商余之芹生平履历勾勒出太平天国以还的徽州社会实态(《上海徽商余之芹的生平及其时代:近代徽州重要史料〈经历志略〉研究》,《安徽史学》2013 年第2 期),张小坡利用家谱传记描绘了一位徽州农民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传奇经历(《太平天国前后一位徽州小农的个人生命史》,《徽州社会科学》2019 年第8 期),戴昇藉助大量文人笔记、年谱,呈现了士绅个人经历及一般民众的避难日常生活(《徽难疏略: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地方记忆与民间书写》,《地方文化研究》2017 年第6 期),余晓东等透过周懋泰所遗诗歌揭示了战争背景下徽州民众的生活状况及文人心理 (《清代诗人周懋泰诗歌中的太平天国运动——以避“寇”诗为中心》,《滁州学院学报》2017 年第3 期)。 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并未得到充分的反映,至于放置于近代徽州地域史的脉络中去考察,仍有不小的发掘空间。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太平军入徽前后地方社会的复杂反应入手,勾勒出战争阴影下的众生样貌,以期全景式呈现兵燹对徽州历史走向的影响。 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地方动乱的成因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在长江流域左突右进,而地处要冲的皖南随之成为太平军与清军长期鏖战所在。 面对重兵压境,承平日久的徽州,因天险地利易势,兵匪交相为患,官与民日渐疏离,地方社会随之陷入多事之秋。
(一)大军压境
在太平军挺进皖南地界之前,战乱之于徽人似乎遥不可及。 单从地形来说,此处“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①道光《徽州府志》卷1《舆地志·形胜》,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坐拥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居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②《方氏家谱·序》,明万历二十二年(1592)刻本。有清以来,徽州除“康熙初年,三藩之乱时有闽寇,底定二百余年不见兵戈”。③光绪《婺源县志》卷17《兵防志·兵事》,清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长此以往,“人士习于承平日久,不知兵革之事,闻贼踪日近,皆愕眙不知所为”。④黄崇惺:《凤山笔记》卷上,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上编《事略》,1924 年油印本。突如其来的战乱引发巨大心理恐慌,其慌乱之情形,犹如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所言:“夫徽在万山间,缭延崄峻,较之平原广野,防御宜易。 然当宣、睦、衢、饶、池阳之中,界联三省,山寇窃发,数百为群。 士人聚族而居,不习兵革,一闻小警,挈家逃避,近邑者避城郭,远邑者避山谷,所遭焚掠,亦甚惨矣。 ”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二)·凤宁徽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1026—1027 页。
与历代徽州兵事相比,太平军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 据不完全统计,自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兵临祁门,至同治三年(1864)由歙县、绩溪遁走,徽州下辖六县前后遭攻占合计达66次,其中绩溪、黟县各15 次,婺源和祁门各11 次,休宁10 次,歙县4 次。 在太平军频繁的袭扰之下,徽人引以为傲的天险屏障形同虚设。 且不说历经明清两代的持续开发,“商民修岭以通往来,栈者夷矣,而天险一失,山川之形便,适足以夺其所恃也”,⑥夏燮著,欧阳跃峰点校:《粤氛纪事》卷9《皖南逾岭》,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256 页。给农民起义军留下可乘之机。 单就是浩浩荡荡的太平军队伍中“多楚粤之人,深箐巨嶂,上下如履平川”,⑦黄崇惺:《凤山笔记》卷下,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上编《事略》,1924 年油印本。在层峦叠嶂的徽州,“出此入彼,避实冲虚,驯至兵分力弱,无所不备,无所不寡”,⑧夏燮著,欧阳跃峰点校:《粤氛纪事》卷9《皖南逾岭》,第224 页。令清军防不胜防。 尤其是咸丰十年(1860)以后,作为太平军东图浙江的孔道,“徽州境外,三面皆有贼踪来往,处处可入”,⑨黄崇惺:《凤山笔记》卷下,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上编《事略》,1924 年油印本。整个徽州皆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
尽管清廷不断加固徽州防御力量,但其独特的聚落结构又令布防者疲于应付。 亲历兵燹的南陵人刘镇鐈在向曾国藩条陈皖南善后事宜时谈道:“皖南情形与他省迥异,江西、江北多平原旷野,势宜谨守城营,兵法云平地守城是也。 ……。 皖南则不然,山势罗列如城,堪舆家所谓罗城也。 ……高甍大厦,鳞次栉比,千家万家,群居聚处,村落之盛,势媲郡县。 故贼数十万众,至随地安下窝巢,绰有余裕,不必得城池可以久驻。 盖我皖南富庶,不在城池,而在乡村,徒守城池,贼来乡村,惨遭蹂躏,一城空存。”⑩民国《南陵县志》卷41《艺文志·文(二)·同治三年皖南肃清上曾涤生相国议善后条陈》,1924年铅印本。换言之,只要太平军能够深入徽州乡村,便可就地取材,以战养战,拖住清军。这是普通百姓所始料未及的,也是徽州受祸剧烈的根由之一。
(二)兵匪滋扰
面对太平军咄咄逼人之势,徽州地方官府紧急备战,在四乡筹办团练。 只因操之过急,招募的乡勇参差不齐,与作战要求相距甚远。 当时活跃在府城和歙县的义练团,乃是由绩溪人吴定州网罗一批花会赌徒改编而成,毫无战术素养可言。 曾有人赋诗揶揄道:“城头鼓角声不齐,城下哑哑乌夜啼。 天明四顾无贼迹,塞巷填街说功绩。 山环水绕途纷义,贼去贼来如到家。 梳肌剔髓供鱼肉,不弄干戈弄丝竹”。⑪鲍宗轼:《新安吟·防堵乐》,许承尧:《歙事闲谭》,合肥:黄山书社,2001 年,第291 页。由于军纪松散,这些人在兵匪之间随意切换,“不守要隘,而驻祁、黟之市镇,终日四处,奸淫掳掠,无所不至”。⑫王茂荫撰,张新旭等点校:《王侍郎奏议》卷7《省稿2·论徽州续捐局扰害折》,第110 页。
战时徽州本土兵力单薄,主要仰仗客籍兵勇作战。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来自浙江的台勇、江南大营的川勇,以及曾国藩带入的湘勇,其他诸如贵州勇、江北勇、果毅军等也曾穿梭于此。 这些兵勇鱼龙混杂,不受地方节制,例如“台勇类多海盗,乌合鸟散,来去自如,专以剽夺为事者也”。①贝青乔著,马卫中、陈国安点校:《贝青乔集: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31 页。又如江北勇实系“江北舆台孙大、高三等,推石埭薙发匠丁三余为首,自称防勇,为害闾阎,官不能禁”。②余本愚:《杂兵谣》,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中编《诗歌》,1924 年油印本。他们打着就地筹饷的幌子,疯狂罗掘民财,害民甚于保民。 当时一位来自休宁的黄姓地主悲愤道:“官兵之初至也,盈街满巷,打门觅馆,甚至破门登屋而入;既打馆也,衣物银钱,见即窃去,拆门坏壁,搅扰异常;及至扎营,锅、碗、缸、椅凳、谷簞、柴火,尽数搬去,……而搬去之物,撤营之日,或官兵放火一焚,或土匪轰然一抢,各家之物,被官军搬去者,十不获一矣。 然居家应用之物,不能不办,岂知此番兵去,彼番又来,居家之物,屡添屡抢,(咸丰)六、七、八、九,四年之间,我五城遭官兵之害者,已民不聊生矣。 ”③王二:《关于〈咸丰十年庚申大乱记〉》,《历史研究》1957 年第3 期。
与兵祸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匪患。自太平军逼近皖江,徽州境内“狼烟逐万霙,狐鼠恣纵横”。④黄德华:《琐尾吟》,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21 页。咸丰四年(1854)初太平军奇袭祁门时,“黟西土匪纷起”,⑤同治《黟县三志》卷12《杂志·兵事》,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而绩溪“此时小村坊多遭土匪之劫,大村坊则免,以人多众也”。⑥汪士铎著,邓之诚辑录:《汪悔翁乙丙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 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7 年,第73 页。时任休宁县令唐宝昌坦承,“休境迭遭蹂躏,皆由花灯蛊招集土匪,勾通逆党所致”,⑦马昌华:《皖著太平天国资料摭录——《旭斋杂抄》,《安徽史学》1985 年第2 期。因而他严饬各乡竭力弹压土匪。 但动乱的时局不断“造匪”的同时,还让匪徒们有恃无恐,甚至打着太平军的旗号,浑水摸鱼。 如咸丰六年(1856)石达开率部自江西开赴婺源,“八月二十三,贼由南乡太白司窜高砂等处,乐(乐平)匪乘机劫掠中云、盘山、许村、港头,各村庄集民勇格杀土匪”。⑧光绪《婺源县志》卷17《兵防二·兵事》,清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这些土匪犹如跗骨之蛆,让百姓避之不及。
(三)官民疏离
自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顺江而下,连拔安庆、芜湖诸要塞,皖属“沿江郡县官,或乡居,或舟宿,十九弃城不顾”,⑨贝青乔著,马卫中、陈国安点校:《贝青乔集: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27 页。大小官吏丑态百出,“其甚者如庐州知府胡元伟、六安知州宋培之、铜陵知县孙润、舒城知县钮复畴屈身降贼,辱如奴隶而不忍一死”。⑩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6《祁门知县唐治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166 页下。这些“父母官”将守土之责尽皆抛诸脑后,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引发社会剧烈动荡。 赴徽避难的苏州人贝青乔尝言:“民间遂藐无王法,或从逆诪张,或乘乱恫吓,良懦亦畏祸蓄发。 而伪官之设,渐至编籍抽丁,计田索赋,贼势日以内陷,而徽岭以外,几不在普天率土中矣。 ”⑪贝青乔著,马卫中、陈国安点校:《贝青乔集: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31 页。
事实上,徽州本土早已暗流涌动。 咸丰四年(1854)秋,吴定州所部越境建德县纵火,“居民衔之,遂赴皖邀贼渡江,再由(东流县)张家滩入岭,追破花会勇于岭东三十里外。 祁、黟震动”。⑫夏燮著,欧阳跃峰点校:《粤氛纪事》卷9《皖南逾岭》,第230 页。尔后又有徽州乡勇在被派往石埭协防时“恃功骄恣”,⑬曹蓝田:《璞山存稿》卷9《乙卯难行纪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325 页上。横行霸道。 及至次年春,不堪其扰的乡民再次邀来太平军进剿徽勇。是役,徽郡六县陷其五,仅绩溪苟存。在太平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徽州知府达秀偕安徽学政督办团练大臣沈祖懋等大小官员悉皆逃遁,惟歙县县令廉骥元自缢公堂。 府城失陷后,“四乡警怖,百十里阛阓迁闭一空”。⑭贝青乔著,马卫中、陈国安点校:《贝青乔集: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40 页。即便未遭战火波及的绩溪,“不特城内搬空,即附近村乡亦如无人之境”,而县令田宝琛“私行逃遁,城内空虚,越十数日回署”。①汪光泽:《有关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的一些史料——摘录自〈介夫年谱〉》,《安徽史学通讯》1957 年第1 期。此番官府表现,令其威严扫地,也应验了明清之际徽人赵吉士的忧虑:“凡所以卫吾民者,法至密也。 顾兵强,往往恣睢以为暴。及其积驰而媮也,懦怯畏葸,乃更逾于民。 是故闻警则望风而逃,委民以为寇饵;寇退则反咎民之不能固圉,乘寇之余氛而流其毒。 ”遭此一劫,官民离心离德。
尽管安全保障毫无着落,官府却要民众在团练上尽心尽力。 依照朝廷规定,“每团按户选勇,按村出资”。②同治《祁门县志》卷36《杂志·记兵》,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表面上看,“各村之钱,各村用,各乡之钱,各乡用”,关键是“所最不易者,团练总得人耳。……若权而假非其人,则小民未困于贼,而先困于团练矣”。③赵莲城:《豹隐堂集》不分卷《论团练》,《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23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6 页。当然,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那些被官府倚重的局董们,“一面勒掯,恐喝土人以取钱,讬其名为‘助响’……一面执涂人、市人及恇弱瘦怯之书生为乡勇”,结果招募而来的乡勇“日取清钱三百,既而贼来则皆溃”。④汪士铎著,邓之诚辑录:《汪悔翁乙丙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 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7 年,第53—54 页上。更有那等劣绅混迹局内,专事攀缘附仰,“早将捐款各私藏,或置田畴或入嚢。哪管生民受涂炭,只知贪得若豺狼”。⑤佚名:《新安难民词》,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33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184 页。久而久之,徽州出现了“官吏不和于上,绅民不和于下,而望其齐心团练,同心杀贼,势必不能”的乱象,最终落得“饷无所出,捐无可集,绅富袖手,士民腾谤”。⑥杨沂孙:《观濠居士文集》卷上《李、陈两观察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359、366 页。
二、战时民众的抉择
旷日持久的太平天国战争,在徽州基层社会引发极端混乱,如何求生成为摆在广大士民面前的一个棘手难题。 面对大门口的“陌生人”,无论抗争,还是合作,抑或逃亡,徽州民众都要及时作出抉择。
(一)抗争者
在地方读书人看来,太平军带来的不仅有刀枪棍棒,还有极具煽动性的“歪理邪说”,这是对“文公阙里,东南邹鲁”莫大的亵渎。 他们斥责太平天国“废五伦,而男曰兄弟,女曰姊妹,宣讲泰西邪教,动称天父天兄,权能广大,智力高强。 毁塔如元魏,焚《诗》《书》如暴秦,侮圣则孔子木主受笞,慢神则平夷土谷诸神祠”,⑦贝青乔著,马卫中、陈国安点校:《贝青乔集: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51 页。罔顾伦理纲常,实乃离经叛道之徒,不屑与之为伍。 婺源庠生酆声拒受“伪职”,忿而“骂贼”,遭乱军砍杀。⑧光绪《婺源县志》卷21《人物志五·忠节一》,清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黟县诸生胡浚听闻“贼以计劫文士”,身赴敌营叱骂,被太平军视为“狂疾”屏退,后复怒闯军营被杀。⑨程鸿诏:《有恒心斋文集》卷8《胡吴汪俞附诸死事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235 页。歙县附贡生仰元颇受太平军仰慕,“使为治文书”,被执不屈,赴死前嘱咐家人,“汝辈须继吾志,不可苟活以玷吾。 厥后,其子士昉被执,骂贼殉节于邑东门外。 孙女定转,年十七,惧污投井,妻子及子妇相继死者十余人”。⑩民国《歙县志》卷7《人物志·忠节》,1937 年铅印本。
不惟士人义愤填膺,一些服膺朱子理学的俊彦豪杰,“或矢志同仇,荷戈赴义;或临危授命,尽室捐躯”。⑪同治《黟县三志》卷6 中《人物志·忠节》,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歙县义士程文谷“性机警,有侠气”,当“庚申秋,郡城再陷,乡团渐散,文谷犹堵御村口。太平军已分路入村,兄弟侄妻子被掳,愤益甚,持刀杀贼数人。 复返至大安桥,敌众纷擁,矛戟交加,死之”。⑫民国《歙县志》卷7《人物志·忠节》,1937 年铅印本。黟县商人舒彩芬,跟随乡团“偕众防御,每以身先,里中恃以无恐。继复率众移家底岭,扼险据守,排列滚木石寨,相拒十余旬,毙贼甚多,致遭贼愤”,面对太平军四面围攻,他只身负母攀援逃避,因“行迟为贼所及,遂同遇害”。①《(绩溪)华阳舒氏统宗谱》卷17《具禀徽州府学附生舒安仁禀》,清同治九年(1870)叙伦堂木活字本。绩溪人周兆基“尚义侠,负勇略”,及至“洪杨乱作,即纠合同志周国栋、耿金柱等设同志局于虹溪桥,身充练长,选骁勇子弟,日夜训练。 以人面石为一乡避乱地,督率练勇扼险守御,一乡倚如长城。 每遇贼至,必迎击,无一败创,并时出为官军声援”。②《(绩溪)周氏叙伦堂族谱正宗》卷17《兆基公传》,1912 年木活字本。
当太平军狂热的宗教政策与徽人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激烈碰撞,彼此对抗亦在所难免。 地处歙南三阳坑的洪氏族人,村居要冲,“迤浙诉番,取迳于此,鹰伺鹜集,战争无时”,聚居于此的梅溪洪氏族人为捍卫乡梓,遂“爰自丁壮,下及妇孺,执戈卫墟”,阖族三百余人捐躯赴难。③程秉钊:《梅溪洪氏节烈双褒录序》,王经一编著:《王茂荫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61 页。又扼守祁门西乡险要之新安岭的金谿金氏,在敌人进犯而徽属练勇“拔营而潜去之”时,“金谿居人独倡率同族各持器械赴岭守险,以为之御,且徧树旗帜,时击金鼓,历数昼夜皆然。 其口粮则由合族祀众给发,以故贼知团防之谨,不敢侵也,倏为之远徙焉”。④《(祁门)金氏统宗谱》卷1《团防纪略》,清光绪三年(1877)木活字本。与之相似的,来自祁门的沙堤叶氏、韩楚二溪汪氏以及为曾国藩行辕服务的桃源洪氏,也在保卫桑梓中不遑多让,借用祁门县令周溶的话说:“祁以地处冲要,被祸尤酷。 此十年中,士绅之筹饷练团,义民之同仇敌忾,以及愚夫愚妇,或从容殉节,或节烈捐生,其足泣鬼神而光志乘者,不知凡几。 ”⑤同治《祁门县志》卷首《序·重修祁门县志序》,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二)合作者
太平军扰徽前,乡间的卫道士们不厌其烦地向村民灌输“何代无盗贼,此贼凶且顽。 擢发罪难数,言之摧心肝。 人所异禽兽,尊卑差等明。 贼皆呼兄弟,五伦全弃捐。 ……民货皆贼货,民田皆其田。诛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⑥黄德华:《琐尾吟》,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13—314 页。的恐怖言论,冀望百姓们能够奋起反抗。但事与愿违,在刀枪棍棒面前,普罗大众本能的反应是求得一线生机。
咸丰五年(1855)春,太平军首度攻陷徽州府城,只因纪律严明,给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咸丰六年九月七里亭之战,村人皆隔岸观战,妇女亦有聚观者”。⑦黄崇惺:《凤山笔记》卷下,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上编《事略》,1924 年油印本。尽管如此,一旦有风吹草动,神经紧绷的乡民仍然不敢掉以轻心,纷纷主动向太平军示好。 一众来自绩溪岭北的村民,在某文人的带领下赶往郡城向太平军献礼,“送以蜜枣、大枣一筩,曰‘早早一统’,筷子、灯笼鸡九十五只,曰‘快登九五之尊’,筩笱十三枝,曰‘一统十三省’,其人素闻明时两京十三省,而又忘两京,故云云也”,当时夹杂在送礼队伍中还有附近旌德及歙县的居民。 事实上,战前不少绩溪人已同太平军频繁互动。在绩溪乡下避难的汪士铎发现,距其塾馆不远的“上庄民有蓄发,借名与贼通市者甚众,人皆知之,彼亦不畏人也”。 甚至他还听闻,七都有位在扬州经营墨谱的商人,年届五旬,太平军让他充当信使,并许之重酬,此人欣然应允,并以难民身份躲过官兵的盘查。⑧汪士铎著,邓之诚辑录:《汪悔翁乙丙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 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7 年,第59、67、93 页。
徽州其他几县亦不乏追随者。 咸丰四年(1854)七月下旬,在祁门西乡忠信里人李国成的带领下,驻扎在建德境内的太平军大举向榉根岭进发,只因不敌徽勇及西乡民团夹击乃退。⑨同治《祁门县志》卷36《杂志·记兵》,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而关于黟县商人通敌之事早已传得满城风雨,“黟人平日素贾于省城,贼据省城(安庆),而黟人之贾如故,且与贼甚习”,所以太平军能兵不血刃拿下黟县。⑩杨沂孙:《观濠居士文集》卷上《书黟人馈献引寇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372 页下。在恐怖如森的环境中,人人自危,社会道义的约束显得苍白无力,一如歙人许承尧所言:“悲夫! 贼据徽久,继以疾疫,吾家吾族同烬,于是遗民寥寥,半隐忍从贼。 府君独愤之,濒死者数矣。 ”⑪安徽省博物院编:《许承尧未刊稿整理研究》,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7 年,第42 页。
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太平军纪律涣散,但乡民们眼见李世贤所部“贼安民后,有主兵、客兵之别。 客兵纵杀掠,主兵辄庇护”,①许承尧著,汪聪、徐步云点注:《疑庵诗》乙卷《过祁门吊曾文正公驻兵遗址因追述咸同间事六首》,合肥:黄山书社,1990 年,第37 页。依旧有不乏归顺纳降者。 据绩溪在城绅士胡晋柱反映,“有等无知之徒,阿附贼党,十一都横睦高美德,九都何家田圩何焕,此尤孽之著者”。 令其始料未及的是,次年族弟胡晋陞“自芜湖与贼同来,到绩之日,即令该贼住于丰芑堂,并在堂内安置骡马”,公然进驻宗祠。②汪光泽:《有关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的一些史料——摘录自〈介夫年谱〉》,《安徽史学通讯》1957 年第1 期。躲在深山避难的胡传(胡适之父)亲眼目睹,“乡间匪类争投贼,贼招人充乡官……余川人汪茂吉于贼酋梁姓者昵,倚贼势,屡借端以逼索官人财粟,小康之家无能免者”。③胡传:《钝夫年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447 页。随着战事的推移,归附者队伍不再局限于黎民百姓,“时粤寇方炽,邑(绩溪)中衣冠巨姓往往降贼,短狐长鲸,抅乱未有已”。④《(绩溪)遵义胡氏宗谱》卷12《文艺一·梅花百咏自序》,1935 年铅印本。
(三)逃亡者
太平天国后期,徽州成为其东图江浙之管道,其用兵之多、往来之密,为当地历世所罕见。 在与清军的反复拉锯战中,太平军为抢占先机,对徽用兵的方针变得简单粗暴。 这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令徽民苦不堪言,除了逃亡,别无他选。
据《新安柯氏宗谱》记载:“洪杨军初踞江浙时,尚不甚骚扰闾阎,因湘勇外逼,党羽内讧,军心无主,乃四出窜扰”。⑤《新安柯氏宗谱》卷26《杂记》,1925 年刊本。对于这种微妙的转变节点,有位黟县文人清晰记得,咸丰五年(1855)“以前之贼,假仁假义,不杀百姓,不烧民房,只杀官兵劫库而已”,与民秋毫无犯,“以后之贼无信无义,放火、杀人、打掳三者当先”。⑥佚名:《徽难全志》,《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96 页。另据亲历者黄崇惺追述,当咸丰庚申年(1860)九月李世贤所部攻陷徽郡后,命人到附近“各乡村皆出伪示安民,遣人献银米蔬菜,谓之‘进贡’,约不复掳掠人”之际,“会伪忠王李秀成自芜湖来援,众号十万,自箬岭入,而出黄泥关。 所过焚掠益甚,凡进贡之村落亦不能免。而侍逆之党散居乡村者,亦并受其屠掠”。这骤然间的反转,令徽民猝不及防,“深山穷谷之中几于无处不被其扰,其焚掠之惨,胁迫之苦,较他郡为尤烈”。⑦黄崇惺:《凤山笔记》卷上,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上编《事略》,1924 年油印本。
比杀戮更让人不安的是,连年征战对徽州的农业生产与商品贸易产生猛烈冲击,物资极度匮乏,在民间引发巨大的恐慌。 在庚申之乱期间,“至是徽、歙境内遍地皆贼,无路可通粮”,⑧胡传:《钝夫年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450 页。几乎将难民逼上绝路。 据绩溪仁里村老人程秉江回忆,“当太平军来仁里,有一二百村民携老偕幼逃往对面山春坞里,因粮食断绝,误食山中青桐子中毒身亡,甚为惨烈。 其时,仁里十室九空,死的死去,逃的逃生”。⑨绩溪县瀛洲乡仁里村民委员会编:《千年仁里》,绩溪: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2009 年,第233 页。由于朝不保夕,民众“或经险历远以避乱者有之,或如草饮以资生者有之,甚至饥饿之极,即将贼匪所杀之人刳其肉以为食者亦无不有之”。⑩《(绩溪)锦谷程氏宗谱》卷2《重建惇庸堂宗祠记》,清光绪三十年(1904)惇庸堂木活字本。当战争的血腥残酷暴露无遗,又进一步加剧社会恐慌,迁避风潮愈演愈烈。
三、避难途中的遭遇
在咸同兵燹猛烈的冲击下,徽州广大士民纷纷踏上流亡之路,但受家庭背景、社会身份及与官府关系的影响,个体对于战争的敏感程度则有强弱之别,这也就决定了其逃难的时机、路线及遭遇。
与本土民众的后知后觉相比,在这场大逃亡中率先行动起来的非徽商与游宦群体莫属。 在他们眼中,徽州“虽间遭兵革,而世家大族窜匿山谷者,犹能保其先世之所藏。 非若金陵南北,土地平衍,一经离乱,公私扫地,其势然也”,①《(歙县)昌溪太湖支吴氏族谱》不分卷《新安昌溪吴氏太湖支谱序》,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木活字本。返乡避难理所当然。 寄籍江宁的歙县士子郑由熙,“迨至癸丑粤寇犯金陵,急尽室归黄山,伏处十年”。②郑由熙:《晚学斋诗二集》“叙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29 页下。服贾金陵的绩溪人冯经甫以为,“绩溪人比他处人不同,世治则出而贸易,世乱则归家,家各有田,多者数十亩,少亦数亩,风俗俭朴,力耕可以自给。 寇至则避于深山,退则返,不过数日。 地不当孔道,寇不留行也。 衣物无值钱者,贼所不取”。③汪士铎著,邓之诚辑录:《汪悔翁乙丙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 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7 年,第23 页。故此,“当粤贼东下,徽人贾于四方尽挈资以归,……自(咸丰五年)五月以后,以至十二月,徽郡皆无寇警,而远方游宦与夫寓公之地而来者,皆视徽为乐土。 ”④黄崇惺:《凤山笔记》卷上,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上编《事略》,1924 年油印本。乃至徽州周遭府县的民众,“人皆信为古无兵灾,避乱者迁如归市焉”。⑤贝青乔著,马卫中、陈国安点校:《贝青乔集: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28 页。及至曾国藩移师祁门,“祁以大营所在,四方倚为安,避难者源源至”。⑥同治《祁门县志》卷14《食货志·卹政局》,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面对汹涌的迁徙潮,徽州本土社会精英们也提前谋划落脚地点,以期从容避难。 在歙县的北岸村,“乾隆年间村里有一赫赫有名的茶商,是村里有名的景隆号,道光年间出重资建造了吴氏宗祠,这一家族人丁盛旺,自洪杨之乱发生后,找个深山向阳的四季如春的所在——吴家山,做了幢36间房屋的大屋子,为了年长的老人和妇女能坐上轿子去豆腐垯的山湾处,还修建了百步街,有台阶可上,一大家族人虽挤了点,倒是个避难的好场所”。⑦歙县《北岸村志》编委员会编:《北岸村志》,2015 年(内部发行),第55 页。黟县艾溪村的大绅商余国谨,出任渔亭镇团练公局董事,因洞悉局势,“一闻发匪将来,举家远徙。 先将老祖母,时年八十岁左右,乘舆而行。 次则少妇幼儿,每人交洋两元,钱二百文,炒米一包,布套雨伞一把,小包袱一个,除派人保护外,壮年者后行”,每当余家“老幼行后,而歙县、休宁之逃难者,接踵而至”。⑧余之芹:《经历志略》,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04 页。
由于上述家庭准备充分,脱险时尚有余力护全家财。 前述那位休宁地主出门前特意写下《避乱须要》,他认为“避乱须舍得物事,如贼来急,雇人夫不多,则先将人撤开,次及契据,有余力,再搬物;常见先将物事搬出,及贼到,人不及避,有物无人,有何益哉! ”再者就是“离乱之世以谱牒契件为要,须要三五副底子,一副用二层锡盒或皮漆藏内,外用锡皮裹好封密;再用化松香四围浇成一块,有松香浇,即低湿亦不受水也,择高阜埋藏;一副挑随身边;再而二三副与兄弟叔侄辈携带,方可保无虞。 其谱牒契件,用薄绵纸,小字抄下,大约大者埋藏,小者携带;或两副大者,一副埋藏,一副随带”,在所有契据中又要属“租簿最关紧要,盖佃户名目,非租簿不能知也”,⑨王二:《关于“咸丰十年庚申大乱记”》,《历史研究》1957 年第3 期。其见解可谓独到。
相形之下,出身寒微的士人,家赀不足,且身无长技,只得东躲西藏。 据休宁塾师马旭斋追忆,在探知咸丰七年(1857)五月太平军自浮梁窥伺休宁后,全家避乱佃公坑,“一月之内,兵声纷纷,难安之至,田禾不能耘,山草不能耨,工不能作书不能攻,困守家中,凄然待毙。 并且浮梁不能通商,米价滕贵,洋钱以毛光辨别,将及捧金而亡”。⑩马昌华:《皖著太平天国资料摭录——二、《旭斋杂抄》》,《安徽史学》1985 年第2 期。来自同邑的汪钟淑一家靠着亲友接济,“大儿昌鉽,同媳詹氏寄居古黟范姓,予同内人、次儿昌镈、三儿安吉、三女还珠另避山中,遇贼得脱。 嗣觅长儿,始迁得屏山避地,儿更代筹薪水,奈寇踞不退,难以久支,其能得免为流民乎”,⑪汪钟淑:《避乱词五首》,休宁29 都1 图黄氏文书(未编号),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藏。惶惶不可终日。 而歙人许学诗家族由其父许恭寿带入深山避难,“数年间,自先曾大父以下,手殓十二人之尸,皆被棺衾,哭至于无泪,惟眶陷而已。 所携赀物尽,则犯百险而求之,时仅吾母吾叔父,及学诗与一妹存”。⑫安徽省博物院编:《许承尧未刊稿整理研究》,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7 年,第42 页。
至于底层的穷苦百姓,出门无依无靠,对于外出逃难犹豫不决。 在不少乡民看来,太平军数次过境徽州,于民无犯,只要避其锋芒,便能保全周身。 由此“咸丰十年贼陷之后,居人狃于前事,皆不肯远徙,谓贼皆必不久住。 贼入山焚掠,犹以为官军所为”。 及至众人发觉太平军用兵迥异于前,数十万大军靡集徽州,“向之惮于迁徙者,今且无地可迁,无物可载”。①黄崇惺:《凤山笔记》卷上,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上编《事略》,1924 年油印本。在凶相毕露的太平军面前,百姓们慌不择路,“投亲友,搭饭食,暂避灾星。 男子们,没奈何,自担行李;女人们,背儿女,扶杖随行。老人们,不能行,桌圈当轿;小孩子,只得用,贮篓挑人。 那山中,屋宇小,家住数十;到夜间,打地铺,手足难伸。 更苦的,盖茅棚,山窝里住;风来吹,雨来打,衣湿淋淋”。②佚名:《徽州义民歌》,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下编《杂记》,1924 年油印本。加之“贼踞徽城,久不能克,紫阳乌聊之巅,丰川箬水之源,樵斤渔棍所不能往者,寇能往。 徽人多豪商大贾,中人拥资钜万,无论大户,故贼之欲得而甘心也,较他郡尤甚”。③郑由熙:《晚学斋文集》卷1《节孝汪母宋孺人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本,第135 页。
客观上说,由于对大战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在咸丰庚申(1860)大逃亡中,大抵每个徽民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而绩溪士人曹向辰所撰七言诗《流民篇》可谓是最佳注脚,兹引录于下:
岁届庚申徽宁失,死里逃生真靡术。没者没矣尚何言,幸而苟全十股一。动谓贼据难久长,携家挈眷躲山庄。 到得深山搜始遍,廼知近避计不良。 踰关至卡脱虎口,侥倖妻孥相奔走。 吃餐用现总难糊,起棵藁嚢嗟莫有。思量某处若而人,与吾夙昔为至亲。料他不作薄情辈,少少亦借数十缗。 谁知费尽攀跻力,进门相见不相识。 地生人生样样生,两眼乌珠真漆黑。 靧却面皮做赖皮,长跪而请救权时。些须不敷往返用,太息伥伥再何之!随行包裹常作伴,旧衣旧被值几贯。 济了朝餐没夕餐,无钱难硬英雄汉。 废物卖完卖到人,童儿幼妇活换银。 初逃数数七八口,毕竟难逃剩只身。 几度思归归不得,省识乡闾踞毛贼。 黄金用尽究无颜,未学吹箫也乞食。 蒙袂辑履苦莫支,残喘一线濒于危。东顾无家西无路,风炙雨淋悲不悲。自惭薄命若蝼蚁,当初畏死今要死。 指点累累饿殍堆,半属昔年富家子。 噫吁嘻哀哉痛哉! 搔首苍茫问几回。 好生之天生不好,难民难极横罹灾。④曹向辰:《流民篇》,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中编《诗歌》,1924 年油印本。
方此大乱未休,瘟疫踵至,整个“庚申之乱,徽人之见贼遇害者,才十之二三耳,而辛酉(1861)五月,贼退之后,以疾疫亡十之六七。”⑤黄崇惺:《凤山笔记》卷下,胡在渭辑:《徽难哀音》上编《事略》,1924 年油印本。及至是年底,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席卷徽州。当时外出觅食的胡传发现,“大雪降,深八尺,并草根树皮不能得。 日见饿殍在沟壑,明日视之,则肉已尽,只余骨。盖已夜为饥民取而食之矣”。⑥胡传:《钝夫年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450 页。然而祸不单行,“同治纪元,壬戌(1862)正月也,天气异冻,毒侵作疫,饥寒交加,人民叠遭难劫,竟至十人九病,十室九空,其生者野草充饥,遭其死者赤身就土处”。⑦休宁《戴氏荆墩家谱》不分卷《录谱意略》,1944 年钞本。
万般无奈之下,不少徽民远走他乡。 众多原生家庭支离破碎,“竟有妇女愿随人走,不计一文钱而听人选择者,贸易带至蕲、黄等处,人多娶之”,⑧邓文滨著,眉睫编校:《邓文滨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70 页。严重动摇传统的宗族基础。 例如绩溪柯氏一脉:“洪杨以前,阖族丁口约七百有奇。自经浩劫,流亡转徙,耗损甚多。同治元年科丁修理祠宇,壮丁仅一百十三名,益以妇孺共约二百,竟减去七分之五,创深痛钜,迄今六七十载,虽稍蕃息,然元气固难恢复矣。 ”⑨《新安柯氏宗谱》卷26《杂记》,1925 年刊本。这也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是十九世纪中叶徽州大逃亡的真实写照。
四、乱后徽州的转向
自同治三年(1853)夏湘军规复南京的消息传到徽州乡下,无数在外逃难的民众纷纷踏上返乡之路。 历尽艰辛抵家的难民,虽获得喘息之机,却要面对乡居环境恶化、宗族组织衰退及社会经济凋敝的现实,不禁陷入进退维谷之地。
(一)聚落环境恶化
归依家园、安居乐业,是徽州返乡难民的迫切需要。 只不过,“贼退民归,斧甑俱空,四邻悄然”,①《(黟县)屏山朱氏重修宗谱》卷8《补遗汇呈癸亥殉难状》,1920 年铅印本。昔日徽州“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②赵吉士著,周晓光、刘道胜点校:《寄园寄所寄》卷11《故老杂记》,合肥:黄山书社,2008 年,第872 页。的图景早已面目全非。 源出休宁黄石洪氏的飞山洪氏,自元初“迁歙居邑城之上路街,入籍东隅。 厥后子孙繁衍,与何、许、毕、项立会社曰‘新城’,共称望族”。 及至清中叶,“其时上路街同族犹繁,乃就邑城江氏祠左之祖宅建为祠宇,始克明礼祀焉。 迨咸丰间,发匪军构难,兵祸之惨,亘古所无,山与城之间共同殃及,祖祠居宅,尽付劫灰,上路街同族劫后更无噍类,而我山居之五派宗支,亦仅有孑遗耳”。③《(歙县)飞山洪氏宗谱》卷首《飞山洪氏宗谱序》,1931 年木活字本。黟人余之芹清晰记得:“先严为渔(亭)镇公局董事,时与统领交接,……而我村借以保全,只被焚去明代古屋一所,然临近上圩、溪滩二村,全遭焚毁,现无居人”。④余之芹:《经历志略》,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05 页。
不少村落侥幸走出战火,但因战事频仍而满目疮痍。 以歙县西溪南吴氏为例,“自经太平军役,十室九空”,根据20 世纪30 年代族长吴裕祜的调查,其“老屋祠、大宗祠、永锡祠仅存墙圈;二门祠,完整,崇文小学设此;三门祠,亦存墙圈;四门祠,缺头门;散胙厅,完整。 庙宇存者:仁义寺游廊、僧舍尚存,余俱倾圮;关帝庙,完整;忠烈庙,完整。 社宇存者:仁德社,完整;古银杏,存在;丙村社,若不速修,势将倾批”。在过往的生活中,这些公共建筑不仅是乡民从事集体活动的物质载体,还是维系众人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的纽带,其破坏殆尽足以撼动整个社区的根基。其中,仅因吴氏“住宅存者十分之一”,就给外来者留下空隙,导致“客籍在溪南者占十分之七八”,⑤胡传:《钝夫年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450—451 页。大大稀释了吴姓在当地的人口优势。
实际上,战后皖南主政者大力招抚流亡,安置客民迁入徽州,不仅未能扭转地方经济衰退的困局,反而因无序开发,引发生态环境退化。 一如同治《祁门县志》所云:“近来棚民为害,开垦四山,雨集砂卸,山下陇亩半为石田,而溪涧亦渐壅塞,日碛日增,米艘不达,岂唯一邑之害? 合郡生灵行将坐困能忽虑焉。 ”⑥同治《祁门县志》卷12《水利志·溪河》,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徽州主客籍之间的嫌隙日益滋长。 据1917 年绩溪人程宗潮返乡调查反映,“本乡客工近日渐多,大率为江西人、开化人、安庆人、歙南人。 因本乡工人甚少,乘隙而入,近更有从事于垦荒者。 在平时颇受其补助之益,然遇饥馑,则不免有恃强逞暴、掠夺远避之祸”。⑦绩溪县瀛洲乡仁里村民委员会编:《千年仁里》,第237 页。直到解放前,“由于封建地主的挑拨,主客籍之间的纠纷成为本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⑧胡兆量:《徽州专区经济地理调查报告》,《教学与研究(北京)》1955 年第2 期。
(二)宗族势力式微
宗族作为徽州最普遍的基层社会组织,其兴衰隆替攸关整个地方社会的稳定大局。 然而,为战乱所重创的大小宗族,重建之路道阻且长。 以绩溪南关许氏为例,“自二十九世惠字辈以下,殁于兵难者十居其九”,各房派系失联者高达70 余支,像迁居市北派“经咸同兵难,居故址者已无人矣,虽有子孙散居四乡,实零落堪伤”,⑨《绩溪县南关惇叙堂(许氏)宗谱》卷1《谱例》,清光绪十五年(1889)木活字本。其时欲“敬宗收族”,势比登天。 垂垂老矣的休宁隆阜人戴光梁在抄录完残谱时寄语后人:“噫嘻! 贼扰十年,财竭民困,逃逝散失,流难他域,以致族党人丁薄稀。 嗟乎! 曩昔之盛,今日之衰,信夫沧桑易变,兴衰有常,是泰极而至否也。 然气运循环,否极必可转泰,侪虽不及见,后昆自欺昌大,故而录言,以达后世”,⑩《(休宁)戴氏荆墩家谱》不分卷《录谱意略》,1944 年钞本。无限悲怆跃然纸上。 世居黟县二都白干村的栢川尤氏,祠毁谱佚,阖族“仅留(祠堂)门枋基地一片”。 战后迁居江西的族绅尤连章,念及族人“各迁其地”,深感余生亢宗无望,只能冀希“日后子孙昌盛,复行创造可也”。①《(黟县)栢川尤氏支谱》不分卷《祠堂图》,清同治五年(1866)木活字本。
随着宗族组织整体衰退,其社会控制能力出现变形乃至扭曲。 战后黟县鹤山李氏在清理祠会时发现,“吾族之中冬至祀会始于康熙乙亥之岁,共二十股,一应祭祀悉有成规,历数十传世世相继,日增月盛,无怠无荒,可谓美善已备。 迨咸丰之际频逢危难,人心离散,所有簿据、祭器等物,遭寇遗失,零星散落,兼司理者相继殂谢,以致各款乖张掣肘”。②《(黟县)鹤山李氏宗谱》卷末《添祥公冬至会序·其二》,1917 年木活字本。无独有偶,前述绩溪南关许氏族内也出现了不少僭越族规之事,“至兵燹后,族中继立往往糊涂妄继,有抛亲继疏、志在继产,有跨祧远房为兼祧,有一继两家为兼祧”,抑或配合女殇,“兵难年时,人家男女死于非命,为父母者痛念不忘,致兵后往往以殇丁选配殇女,入祠享祀,遂寝成风俗。 在山乡衰替、宗族不懂事务,任其施为”。③《绩溪县南关惇叙堂(许氏)宗谱》卷10《宗祠规约》,清光绪十五年(1889)木活字本。
由于族产式微,许多宗族根本无力开展集体活动。 据歙县新馆鲍氏宗祠管理者称:“吾族自咸丰间遭粤匪蹂躏,继以水灾,居庐大半为墟,人亦仅存什一。零落之况,古所罕有。时著存堂、春和堂两祠宇,榱桷半圮,器物荡然,春、秋祀事无以为礼。 ”④《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3《祠规序》,清光绪元年(1875)木活字本。上引绩溪南关许氏,族内原设有特祭胙、斯文胙、老人胙,经费皆由祠产负担。 挨至战乱结束,“宗祠产业大半荒失,所得熟田,以祭祀为重,余则不能复古”。⑤《绩溪县南关惇叙堂(许氏)宗谱》卷10《宗祠规约》。加之宗族精英相继凋零,“凡属先正典型,非遗佚即残缺,数十年来,因循苟且,未尝修辑”,⑥《(绩溪)坦川越国汪氏宗谱》卷24《祠规》,1925 年木活字本。所谓宗族教化也只得听之任之。 凡此种种,不禁有人悲叹道:“族运大衰,人丁寥落,且均失恒产,各为衣食走四方,其分支在他省。离乱之余,不通问讯,欲敦本睦族如昔日者,不可复得矣。然必待建宗祠,置祭产,而后可以聚宗人,敦族谊,几不知在于何时? ”⑦《新安戴氏支谱》卷首《重刊支谱序》,清光绪七年(1881)木活字本。
(三)乡村经济凋敝
在战争尚未结束前,有些难民不避锋镝,“逃回里中”,可映入眼帘的是“尸横遍野,秽气难闻,大厦焚,器物毁,死伤掳去之人,不可胜数,地方情景,实为不堪”。⑧王经一编著:《王茂荫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232 页。众多返乡者一贫如洗,根本无力复工复产,“田园多致荒芜,生齿凋零,资财空匮”,⑨《(婺源)韩溪程氏梅山支谱》卷首《韩溪程氏重修梅山公支谱序》,清宣统元年(1909)木活字本。生计弥艰。 对此,婺源词源王氏一族有切肤之痛:“此数年内,寇婺邑者不下数十次,我村惟咸丰十年、十一年遭劫最甚,烧毁民房六七十堂,被杀被掳者亦百人以外,频年以来人无生业,而团练经费如厘金、家头、亩角等项,曾见迭出,有增无减,真觉民不聊生也。 ”⑩《(婺源)词源王氏宗谱》卷1《辛酉纪事》,清光绪元年(1875)木活字本。
伴随清末内忧外患不断加深,徽商经营环境受到洋商挤压,地方经济复苏前景一片黯淡。 据载,光绪十九年(1893)春,甫任全台营务处总巡的胡传急疏皖南道观察袁爽秋,请求后者能对家乡凋敝之势给予关切。他在信中指出,“皖南四府一州,曩遭粤寇蹂躏,为时最久,受祸最酷。其民死于兵役饥饿者十有八九,存者无几;其田原山泽之荒废,不待问矣。 难平之后,休养生息未三十年,人口未甚蕃庶,土地未尽开垦,而沿江上下千数百里,夹岸列郡数十,每年秋登,惟皖南谷价最贱”。 在外人看来,“徽、宁、广多山,产茶利厚;池、太滨江,圩田易种而屡熟;土旷人少,农有余粟”,实际上“皖南各处,户鲜盖藏;民贫甚,往往不能完纳赋税”,究其根由,“乱后茶税加重二十余倍于原额,商久困,茶价年减一年;春夏采茶得值,除偿工力而外,所余无几,以供烟赌,固不足也。 秋禾未熟,责债者已候于门;谷既登,不急卖、不贱卖,不得也”。 归根到底来说,“天地山川自然之利,悉以供烟赌之费,瓮飧已难自给;催科者至,唯有逃避耳。 此皖南逋赋之所以多也”。⑪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卷2《上皖南道袁爽秋观察》,《台湾文献丛刊》第71 辑,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 年,第140—141 页。
在胡传看来,从土地抛荒到谷贱伤农,再从茶税盘剥到烟毒肆虐,种种繁难交织在一起,业已成为皖南战后重建的瓶颈。颇为遗憾的是,此后数年间徽州仍未摆脱上述困境,却又迎来“近十数年来,故家耆老,相继沦谢,商务外移,弃贾归者,力不任耒耜,户庭食窭”的局面,①黄质:《丛谈:滨虹杂著·叙村居(续)》,《国粹学报》1908 年第43 期。注定其社会振兴举步维艰。
五、结 语
纵观整个太平天国时期的江南一带,像徽州这般饱受战火蹂躏的区域并不鲜见,个中离乱书写亦不足为奇。 但若将之置于地域史的脉络之下,借助徽州底层记忆的多元书写来审视这场战争,重现那些曾被官方话语无视与隐匿的真情实感,或能发现民众对于太平军的态度反复无常。 它不仅受交战各方势力的影响,也与个人利益诉求和地方传统、经济状况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多重因素交互影响的复杂呈现,存在前后冲突、阶层分化的表征。 客观把握太平军与民众的动态关系,既有助于加深对大战背后暴力、失序与逃亡的理解,也有利于把握太平天国运动在地方的政治走向,从而为推进太平天国研究这类史学“老问题”持续走向深入提供新思路。②崔岷,马维熙:《“底层眼光”下的战争书写——以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为中心》,《史学月刊》2022 年第3 期。
本文力图全景式展现战乱下徽州各群体的诸面相,不惟在反映太平天国运动兴衰递嬗的地方缩影,更在于勾勒出“小地方”的“大历史”。 以长时段为坐标,太平天国战争给徽州带来创伤可谓史无前例,“徽居深山,历代寇乱之最著者,唐则有剧盗洪贞、苏寇方清与黄巢,宋则有睦寇方腊,江东盗张琪,元则有蕲黄贼,明则有倭寇,然间被祸最残酷者,殆莫逊清咸同间粤寇洪杨之难苦矣”。③胡在渭辑:《徽难哀音》“序”,1924 年油印本。之所以会如此严重,在湘军将领彭玉麟看来,“徽人多于维扬业盐,家资富饶,姬妾艳丽,自宋以来,未遭兵燹,所蓄书画古玩甲天下。此次初恃黄山白岳,守险避乱,以为安乐窝也。几年余,为土匪指引,悉为贼得,死亡流离,惨甚他省。 天道循环,噫可悟矣”。④彭玉麟,梁绍辉等点校:《彭玉麟集》下册《从征草·悲徽州》,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第22 页。其说虽失之偏颇,但徽商及其家族的败落却无可争辩,而这直接撼动了徽州社会赖以维系的根基。 后来有人归结道,徽州尚未走出咸同兵燹之阴影,“而甲午、庚子诸役又相继以起,内政未修,外患日亟,议者遂欲变而新之,天下靡靡,无所适可”,元气大伤的徽商后裔实难再与时代争锋。 逮至“辛亥遽变,国体乃更,举乡之一切政教而空之”,⑤《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末四《目乙一·后序》,1935 年铅印本。徽州上下渐与时代脱节,坐失近代化转型之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