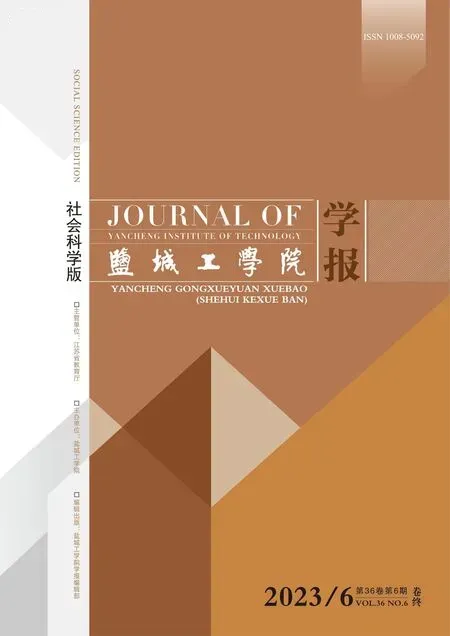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特点论
冯晓斌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有清一代,《论语》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扬州学派《论语》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台拱《论语骈枝》;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论语论仁论》《论语解》《论语一贯说》;焦循《论语通释》《论语补疏》;刘宝楠《论语正义》;刘宝树《论语说略》;刘恭冕《何休注训论语述》等。还有一些学者如刘履恂、朱彬、李惇以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他们关于《论语》的研究重点多为字音训诂、文字考证、文本校勘等,义理诠释较少,且内容散见于个人研究成果之中,并未单独成篇。
受当时学术风气影响,“考据学”盛行一时,固然此法是对宋明学者解经空疏的纠偏,但如果走向极端,势必对学术研究产生负面影响。扬州学派学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论语》研究中注重义理诠释,具有较鲜明的特点。
一、《论语》义理诠释内容特点
关于“义理”一词的理解有很多种,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的观点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内容,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他强调三者统一,然而无形中将“义理”与“考据”变成两个独立甚至对立的概念。“义理”二字分开来看,“义”可以理解为文本在字词表达层面的意思,而“理”是超出文字与文句之外的意思,即更深层的意义。这样一来,义理诠释也具备更加多元诠释的空间,才有了形成丰富诠释成果的可能性。
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的内容特点主要为探寻原意与阐发己意相结合。原意是指《论语》所包含的圣人之旨,己意则为学者通过注疏研究所生发出的个性化的观点与体系。两个概念似乎存在矛盾,若一味遵循原意,则会掩盖住自我特点;如仅仅追求特立独行的观点,又易坠入无妄空谈之境。扬州学派学者却能将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成果较为集中的当属阮元与焦循。阮元《论语论仁说》《论语解》《论语一贯说》等三篇文章虽篇幅不长,但着力从义理阐释角度对 “仁”“一贯”等核心概念提出己见。在《论语论仁论》中,他将《论语》中与“仁”相关的语句归纳为24类,清晰呈现出“仁”的义理不同的指向,而他的依据就是《论语》原文,正如他所言“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1]1他的义理诠释创新之处则在于从实践角度分析“仁”。他认为“仁”的实现有两个层面,一是平行层面中犹如水中投入石子,是一个由己推人的过程,所谓“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2]176二是垂直层面中有上下之分。小到人自修身,大到王治天下。他认为《论语》中所论这两个层面的“仁”最终的实践形成一个由个人内在修养而至“治天下之道”的“仁”的发展过程。这样的论述系统地阐述《论语》文本的深层含义,既遵循原意,又生发新意。
焦循《论语通释》则打破《论语》卷目限制,挑选出“一贯忠恕、异端、仁、圣、大、学、多、知、能、权、义、礼、仕、据、君子小人”等十五个核心命题分别诠释。各命题征引《论语》原文展开论述,数量不一,最多“仁”下有11条,最少“君子小人”下征引1条。众多命题以“一贯忠恕”为核心,诠释基本围绕“一贯忠恕”展开;同时各命题之间力求融会贯通。如释“知”与“异端”相联系;释“知”又提到“盖异端者,生于执一。”执一的原因在于所知囿于某个方面,忠恕之道推到“知”,即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焦循另有一篇文章《一以贯之解》,其中他提出“今夫学术异端则害道,政事异端则害治,意见异端则害天下国家。”[3]133这里的义理诠释超越了《论语》经文所包含的意义,追求经世致用的意义。
焦循还著有《论语补疏》,虽以补邢昺注疏之名,然而其中多有阐发己意之处,且具有新意。他对前人注疏中的义理阐释提出质疑。如“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子张》)一条,他首先指出邢昺疏解为“必有小理可观览”并非《论语》原义,继而提出所谓“小道”,因为“执己不与人同,其小可知”而为“异端”,“道大”与“道小”在于是“一贯”还是“执一”。即使是“小道”,只要做到“相观而善”,即“攻乎异端”,便能使“小者旁通而为大”。他在诠释义理时条理清晰,且具有思辨色彩。
除了阮元和焦循有义理诠释的专题研究外,扬州学派其他学者在研究中也多有义理诠释之成果,除了体现出上文所提及的特点外,还有值得关注之处。如在论语研究集大成之作《论语正义》中,刘宝楠的义理阐释虽然散见于《论语》各篇章之下,然而综合分析会发现其对于儒家经典原意的诠释有的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如“文以礼乐”,这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刘宝楠通过三条相关的分析诠释,体现了自己对孔子教学内容的理解以及试图还原孔子选拔人才的标准。仅以第三条为例:在“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宪问》)一条中,刘宝楠加案语“言加以礼乐,乃得成文,故曰‘文之以礼乐’。”[4]568礼是重要的学习内容,但是刘宝楠并不止步于学礼循礼,在《论语正义》疏“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后云:“谓人但循礼,不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谓‘礼胜则离’者也。”[4]29此解不仅具有新意,且境界更为高深。
二、《论语》义理诠释方法特点
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方法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循家法之轨,无门户之见。所谓家法是指乾嘉时期的学术规范,而门户则是指由学术派别所生成的壁垒。
扬州学派的经学研究方法与吴、皖两派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吴派针对宋儒说经“凿空”之风而兴起,注重尊古崇汉,以汉注驳斥宋解。研究之法则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尤其重视古训。代表学者江声著有《论语竢质》,举证时多偏向选择儒家原典。
但是任何一种学术方法需要不断地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变化需求。皖派代表学者戴震有些学术观点与吴派代表人物惠栋相同,如戴震认为自宋代以来,经学研究最大的弊端在于凿空,他云“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5]187因此,两派有一些共同的学术宗旨,都重视汉代经注,然而戴震摒弃惠栋“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取向,追求“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并能从训诂通义理,突破旧学,提出己见。梁启超曾评价“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6]55戴震治学严谨的态度与精审方法对扬州学派阮元、焦循、刘台拱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后,扬州学派学者也反思吴、皖两派的治学方法,提出不同意见,如王引之在《与焦理堂先生书》中提道:“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7]205他指出治学应当视野宽阔,不能囿于小范围之中。这些都预示着扬州学派在具体治学方法上遵循学术规范,然而又有所修正,从而具有新的特点。
刘师培曾云:“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惟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8]728门户在当时主要指汉宋之分,扬州学派学者在义理诠释中重视“汉宋兼采而为己所用”的模式,对于诸家学说取舍并不以汉宋为依据,而是以是否符合经义为重。如阮元自述其治经之法:“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9]250不持一家之说,善于梳理学术发展的变化,仔细辨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在义理诠释中多有新得。如刘宝楠《论语正义》征引文献时,对于已有的诠释成果凡是有利于阐发经典原意者均采用,如南宋张栻继承了二程的“理”本体思想,提出天、性、心三者,名异实同,皆同体于理。虽然是理学家代表,但是刘宝楠对其《论语解》征引达14次之多,皆为义理诠释。
最后还需要关注的是《论语》义理诠释的成果形式主要为札记体。札记体篇幅不长,但从内容上看往往是学者思想火花的结晶,是最为鲜活的学术成果。即使是完整的文章,也多为日积月累之作。汪廷珍曾云:“予尤服膺端临、怀祖二先生,著书不多,每下一义则皆前人所未及知,后人所不能易者也。”[10]296此法对后来扬州学派众学人影响非常大。
三、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的价值
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所呈现出的特点对后学形成了较大影响,这里仅对其学术价值进行分析。
首先是其义理诠释成果的价值。扬州学派学者对于《论语》义理诠释的目的很清晰。《论语》文本是圣人言行与思想的直接体现,故学子自幼便开始学习,然而真正参悟义理的人并不多,门人弟子多有请教。刘台拱撰写《论语骈枝》,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近人不解此义,闻愚说或颇以为怪用。敢旁推交通,敷畅厥旨,冀学者无惑焉”,[11]292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义理诠释成果中存在许多讹误之处,可见有针对性的义理诠释非常有必要。由此形成的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内容成为论语学研究成果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众多研究者征引的材料。
其次,扬州学派学人科学严谨的方法体现了他们的义理诠释研究的理念,其中以“实学”与“变通”为最突出。正如王念孙评价刘台拱“以视凿空之谈、株守之见犹黄鹄之与壤虫也。”[12]130焦循所云更为直接,“依经文而用己之意以体会其细微,则精而兼实”,[13]233既能实现义理之“精”,又做到训诂之“实”。如何“依经文”?他又云“夫融会经之全文,以求经之义,不为传注所拘牵,此诚经学之大要也。”[14]241这些都为后学治经提供了科学的范式。
第三,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对当时学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乾嘉时期经学研究的重点偏于训诂考证,有很多影响因素,其中一个与学术相关的便是《四库全书》的编纂,此举汇集了许多佚书、古本和善本,加之同时期出土的金石碑碣,为经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孙星衍对此认为经学研究可以超越古人、推动经学研究发展,但同时也有相反的声音,如章学诚认为由于四库开馆出现了大量文献,导致许多家贫之学子将校书作为谋生手段,而治学之人陷入贪多务博、不求甚解的风气之中。与此同时进行所谓义理研究的学风也存在问题,焦循提出有一类谈义理的学究,自幼学习八股时文,所使用的讲章是根据宋儒语录汇编而成,因此“舍宋人一二剩语,遂更无所主,不自知其量,尤沾沾焉假义理之说以自饰其浅陋,及引而置之义理之中,其茫然者如故也。”[15]243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将考据学从治学目的变成追求更深层次经典原意的手段,强调《论语》义理诠释的重要性,纠正了经学研究中的学风,同时也为经学研究打开广阔的视野。
这些影响对后学而言,并不仅限于《论语》义理诠释研究,甚至还在为学、为人等实践层面产生一定的指导意义。如阮元《论语解》一文篇幅不长,所释《学而》两章内容概括出孔子一生的大事,即“为学”“为人”。论及“为学”,重点阐述学习当注重“讲习”与“贯习”,前者着眼于方法,“习”需要诵之、行之,后者则强调持久性,体现出实践意义与价值。在谈及“为人”时,他着重从“孝”与“仁”分析,引范晔《后汉书·延笃传》内容阐明个人观点。显现出阮元对经典文义领略的高度和深度,通过义理诠释以实现教化之功用。
四、结语
自汉代经学研究起始,义理探寻一直是重要内容,但因为其间受到学术发展规律、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并非每个阶段都被关注。所流传保存的义理诠释成果也有各种各样的偏差或者谬误;随着研究观念与方法的逐渐完善,这些都成为清中叶时期学者重新疏解经典以及重视义理诠释的缘由。
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虽然存在一些诸如内容不够精准、主观性较强等问题,但瑕不掩瑜,其成果在清代《论语》义理诠释成果中也独树一帜,得到学术界认可。张舜徽先生曾认为吴、皖两派“专精”之学发展到乾隆时期已出现“士子疲老尽气以从事者,杂猥而已耳,破碎而已耳”[16]6的状态,最终得力于扬州学派学者将经学研究发展成“汇通”之学,重现广大之貌。
儒家经典文本具备广阔的诠释空间,为学者展开义理诠释提供了可能性;而经典的传承发展又使义理诠释具备了必要性。通过对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特点的研究以希望对经学研究发展提供一些可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