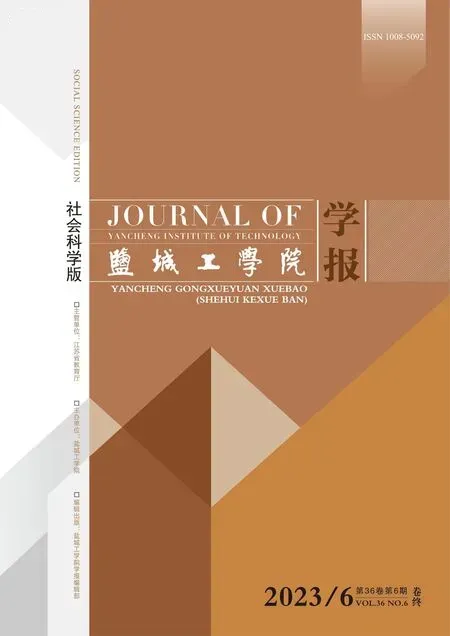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形象建构研究
——基于互文性的考察
余静良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毛泽东不仅以卓越的政治、军事与领导才能而闻名于世,其诗词文赋方面的造诣亦颇深。毛泽东诗词堪称一部宏伟的中国革命史诗,其不但记录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诞生,且抒发了诗人的革命情怀,展现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宝贵精神。可见,毛泽东诗词是文学、军事、历史与政治的高度融合。[1]无怪乎柳亚子曾对毛泽东诗词做出“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的极高评价。
毛泽东诗词英译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采访完毛泽东后,将《七律·长征》进行意译,收录于《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第五节“长征”(The Long March)的结尾。[2]此后,国内外相继出现了众多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其中,国外影响力较大的英译本有:迈克尔·布洛克(Michael Bullock)和陈志让(Jerome Ch′en)译本(1965)、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译本(1972,2007)、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Hualing Nieh Engle &Paul Engle)译本(1973)、王慧明(Wang Hui-ming)译本(1975),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英译本包括外文出版社译本(1976)、许渊冲译本(1978,2015,2020)、赵甄陶译本(1980)、黄龙译本(1980)、辜正坤译本(1993)、李正栓译本(2010,2011,2018)。上述译本的问世,均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讨论与研究热潮。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的内容较为单一,仅聚焦于译本的对比分析、英译策略和方法的探讨等;研究视角较为有限,仅基于生态翻译学、“三美论”、副文本等视域开展相关英译研究。而从互文性理论视域出发,探究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形象建构研究却寥寥无几,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毛泽东诗词在海外的译介、接受与传播。
一、互文性理论内涵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提出。“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点。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3]可见,所有文本都是互文的,所有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互文性是文本的基本属性,乃文学文本的重要特质之一,它关注的是文本的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4]互文性又分为广义互文性和狭义互文性。广义互文性是指一切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即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间的相互作用。而狭义互文性往往指的是某一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如以文本为依据的引用、抄袭、套写、拼贴、戏拟、影射和重写等关系。无论是广义互文性,还是狭义互文性,都能有效映射文学文本内部和外部自我指涉、文本互涉、文本互指、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及互相转化的复杂关系。概言之,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任何文本都具备互文性。互文性认为,任何文本皆为对其他先前文本的吸收、转化、改写、重构与创新。
翻译本身就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创造性语际转换活动,其中必定充满着语言与语言、文本与文本、意义与意义、人与人的互相交流和互相指涉,且不同原文和译文可能还会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进行互指、互涉、互证、互补活动。由此可见,众多文学文本、原文用典、翻译作品的相互交织与碰撞,似乎构成了一个巴特所说的万花筒,随着不同的摇曳,形成斑驳杂糅的所谓“互文性景观”。[5]
诗歌文本原本是一种互文建构,[6]诗歌的创作与阅读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互文互动。因此,无论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互文性始终是诗词研究、翻译研究及诗词英译研究的“得力助手”。透过互文性,能够有效地管窥诗词英译的节奏、韵律、修辞、原型、张力及人物形象,从而体悟到诗词本身的文学性与诗学魅力。
二、军人形象
毛泽东诗词记录下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镌刻下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闪耀着毛泽东的伟岸人格和光辉思想。毛泽东诗词真实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画卷,也是解读革命文化的独特文本。[3]其诗词拥有三次高潮:(1)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斗争时期;(2)长征时期;(3)“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在上述三次高潮中,诗人利用典雅辞藻、丰赡用典、高远意境、丰富意蕴及大胆想象,于诗词中建构出了无数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不惧强敌、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工农红军形象及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随时准备保家卫国的女民兵形象。
1.红军形象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跨越14个省份,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最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这期间,毛泽东共撰写7首诗词,《七律·长征》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10月,为一首七言律诗。彼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在历经艰辛后,终于看到黎明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挥毫写下此首壮丽诗篇。该诗全篇仅56字,但却高度概括了长征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歌颂了红军不惧艰险、勇敢顽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例如,在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中,诗人运用奇特、大胆的想象和夸张的写作手法,表明“逶迤”“磅礴”的崇山峻岭在红军眼里,就宛如微波细浪和小小泥丸一般,从而凸显与建构出红军藐视并战胜困难的大无畏革命形象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然而,不同译者在各英译本中所再现的红军形象又如何呢?兹举三家译文以析之。
译文1:
Wu Liang’s Range rose, lowered, rippled,
And 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7]
译文2:
The Five Sierras meander like small waves,
the summits of Wumeng pour on the plain like balls of clay.[8]
译文3:
The five ridges are meandering like fine ripples;
The majestic Wumeng peaks are but rolling balls.[9]
从互文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译文1将“五岭”译为了“Wu Liang”。通过查阅《威妥玛-汉语拼音对照表》可知,“五岭”的威妥玛式拼音和现代汉语拼音保持一致,皆为“Wuling”。可见,此处斯诺的译文出现了误译现象。此外,译文1将原文中的“五岭”置于句首,将“乌蒙”调至句末进行翻译,很明显不符合原诗的语序,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文的节奏美与对称美,从而无法与原文形成互文参照。再者,译文1将原文中的“逶迤”译为了“rose, lowered”,将“磅礴”译为“the rounded steps”,消解了原诗“五岭”的蜿蜒曲折和“乌蒙”的高耸险峻。倘若运用回译法对译文1进行回译,我们会发现,回译译文无法较好地与原诗形成互文,破坏了原文山峦的绵延奇峻之感,从而不利于红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形象的建构与再现。
译文2将“五岭”译为“The Five Sierras”,凸显出原文“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五岭”专有名词的特点。此外,译文2将“逶迤”“细浪”分别译为“meander”和“small waves”,均与原诗形成较好的互文对应,体现出五岭的弯弯曲曲、绵延不绝。同时,巴恩斯通将“乌蒙”译为“the summits of Wumeng”,彰显出乌蒙山的陡峭与险峻。译文2中最传神之笔莫过于“pour”一词的使用。巴恩斯通使用“pour”这一动态性极强的词汇,与原诗中的“走”字形成鲜明对照,生动形象地复刻出乌蒙山的宏大、磅礴和崎岖。最后,译文2将“泥丸”处理为“balls of clay”,与先前译文一道,共同构建出红军藐视一切困难、英勇顽强的高大形象与精神伟力。
在译文3中,李正栓将原文“五岭”中的“岭”译为“ridges”。而“ridge”与原诗中的“岭”词义较为贴近,更加符合原诗语义内涵。译文3将“细浪”处理为“fine ripples”,意为“细小的涟漪”,表明五岭虽连绵不断,但在红军眼里却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最后,李正栓认为,翻译毛泽东长征题材诗词时,在不损失原文意义的情况下,适当的增译或曰超额翻译或许更能达意。[10]因此,译者利用增词法,通过增添“but”一词,与原文的“走”字遥相呼应,形成互文;凸显出乌蒙山虽崎岖险峻,但在红军脚下,却仿佛小泥球一般,从而再现红军不畏艰险、舍生忘死的革命形象。
译文2与译文3的传神之译及译文3中使用的增译法,不禁让读者唤醒互文记忆,联想到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诗句及相应译文。不同于巴恩斯通采用直译法的译文“The grim pass is like iron[8]”,李正栓的译文为:The strong pass is indeed iron-clad on all sides!,[9]其通过运用超额翻译法,增添“iron-clad”“on all sides”与“!”,充分彰显出娄山关的地势险要,与原文的“真如铁”形成完美互文,进而建构出红军藐视艰险、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伟大形象。
2.女民兵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民兵建设与发展工作。1961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猖狂叫嚣反攻大陆,并不断侵扰东南沿海地区。因此,大陆便进一步加强了民兵训练。同年,毛泽东提笔为身边一位参加民兵训练的女机要员写下《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的七言绝句,并勉励其要有志气,向花木兰、穆桂英等历史巾帼英雄学习。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前两句通过对女民兵军事训练风姿和场景的勾勒,描绘了新中国妇女的飒爽英姿。后两句则盛赞了女民兵“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质,歌颂了新中国妇女的不凡志向与时刻准备保家卫国的坚定意志,从而建构出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不畏强敌及志向高远的伟大女民兵形象。
然而,女民兵形象在各经典译本中的再现和建构情况又如何呢?且看诗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如下译文:
译文1:
Daughters of China with a marvelous will,
you prefer hardy uniforms to colorful silk.[8]
译文2:
Most Chinese daughters have a desire strong
To face the powder, not to powder the face.[11]
通过对比分析不难发现,译文1第一句较为准确地传递出原文中华儿女具有极不平凡志向的内涵。第二句则使用较为具体化、形象化的表达,如“hardy uniforms”“colorful silk”,和原诗“武装”“红装”形成互文参照。然而,事实上,原诗第二句所要传递的信息为“女民兵不爱华丽浓艳的装扮,而爱革命的武装”,进一步深化即为:女民兵志不在浓妆艳抹,而在保家卫国。由此可见,译文1并未再现原文的深层内涵,属于浅化的译文。相较而言,译文2首句使用了“desire”一词,突出强调女民兵高远的志向。第二句则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原文中“不爱红装”译为“not to powder the face”,将“爱武装”译为“To face the powder”。“Face”一词既有名词“脸部”的释义,同样又具备动词“面对”的内涵。同时,“powder一词既有名词“火药”的意思,又含有动词“涂脂抹粉”的内涵。如若将译文2第二句进行回译,其译文为“要面对火药,而不是给脸涂脂抹粉”。可见,译文2第二句深刻传递出原文中不愿匀脂抹粉、艳丽装扮,只爱身着戎装、手持刀枪、保家卫国的大无畏女民兵形象,与原诗的深层内涵形成较为完美、恰切的互文。故此,译文2为深化的译文,可谓神来之笔。
三、伟人形象
用典英译这一翻译过程充满了互文性,互文性可为包括诗词用典英译研究在内的翻译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
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北上抗日,来到西北高原。在陕北清涧县袁家沟,毛泽东登高望雪,感慨万千,诗兴大发,写下《沁园春·雪》 这首壮丽诗篇。该词集写景、评论与抒情于一体,用词考究,设喻用典,意境豪迈,气势恢宏,感情奔放,一泻千里,颇具毛泽东诗词豪放的特征。其中,下片引经据典,着重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评价,并颂扬了当代英雄,赞颂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于字里行间建构出无产阶级毛泽东伟人与领袖的形象。
在毛泽东诗词对外译介与传播过程中,倘若过多地进行译者主观介入,采用归化译法,甚至对原文进行错误解读,不仅有损毛泽东诗词本身所蕴藏的丰厚的文学魅力与诗学价值,还不利于真实、立体、全面的毛泽东形象的建构。试析“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三家译本:
译文1:
It’s pitiable, forsooth, for Qin Huang and Han Wu
To be in some measure less talented in literature,
And for Tang Zong and Song Zu
To be in a sort less refined in culture.[12]
译文2:
Yet the emperors Shihuang and Wu Di were barely able to write.
The first emperor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ere crude.[8]
译文3:
Alas! Qin Huang and Han Wu,
Knew little of civil art;
Tang Zong and Song Zu,
Knew little of literary art;[9]
通读上述三家译文,我们发现,译文1将“略输文采”译为了“To be in some measure less talented in literature”,将“稍逊风骚”译为了“To be in a sort less refined in culture”。虽相较原文,字数较多,句式较为冗长,但该译文忠实于原文,理解精准,表达恰当。此外,该译文还于第二句与第四句开头运用了“To be + in…”的固定句式,在句末同样使用了以“-ture”为词缀的单词;在做到押头韵的同时,还不忘兼顾尾句押韵。可谓既做到了忠实原文,又实现了韵律和谐,与原文实现了较为完美的互文,从而建构出了最为真实的伟人和领袖的毛泽东形象。
译文2四句诗均出现了误译现象。首先,巴恩斯通借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和意译的翻译方法,将原诗中“秦皇”误译为“Shihuang”。实际上,“秦皇”的全称应为“秦始皇帝”,此处为简称。其次,该译文将“唐宗宋祖”误译为“The first emperor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属于典型的历史错误。原因在于,唐太宗李世民并非唐朝的首位皇帝,而唐高祖李渊才是开国皇帝。再者,最令人不解的便是译文2将“略输文采”译为“were barely able to write”,将“稍逊风骚”译为“were crude”。原文的意思即为“可惜的是秦始皇、汉武帝在文学才华方面略微不足,而唐太宗、宋太祖在文治功劳层面略为逊色”。但译文2回译译文为“秦始皇、汉武帝几乎不会写字,而唐太宗、宋太祖又极为粗鲁”。毛泽东作为一代历史伟人和人民领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出此种感慨。很明显,此处为译者对原文的错误理解所致。这样一来,译文2不仅全盘否定了历史人物,还歪曲了作为伟人、领袖的毛泽东形象,甚至迎合了西方部分人士诋毁毛泽东形象的观点,实属不当。
译文3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且增加注释(尾注),对原文部分历史典故进行注解;在帮助译入语读者理解原文的同时,又能很好地减轻译文负担,使之长度、外形与原诗形成恰切的互文参照。此外,译文3运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利用“Knew little of”“civil art”及“literary art”等表达,传神地译出了秦始皇、汉武帝在文章辞藻方面略显逊色和唐太宗、宋太祖在文治成就方面的不足之处。同时,“Knew”与“Knew”的押头韵、“art”与“art”的押尾韵均形成了译文节奏重构的和谐相生,实现了与原文的跨语际、跨文化互文,进而再现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伟人、领袖形象。
四、诗人形象
毛泽东一生共创作了100多首诗词,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诗词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宏伟史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境界。[13]其诗词以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想象丰富、雄浑豪迈、自信乐观、体恤人民为特点,无不建构出充满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矢志不渝、悲悯情怀及胸怀人民精神的毛泽东形象。
(1)从外部空间来看,园区位于古城区东部,其与外部连接的交通非常发达。高速公路、铁路、水路及航空网使苏州工业园区与外部畅通无阻。依靠发达的轨道交通,可以实现20 min到上海、60 min到南京,从而实现与上海、南京、杭州同城轨道化生活。此外,苏州市新制定的城市规划中,明确了苏州工业园的“苏州新城”地位,未来将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心之一。
《清平乐·会昌》写于1934年夏。彼时,蒋介石集结百万大军,对红色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然而,此时恰逢博古、李德等红军领导层执行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红军和根据地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已无军事指挥权和发言权。他在会昌养病,远离主战场。此诗正是在红军身处逆境、面临极大挑战的情形下所创作的。该诗反映了毛泽东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与坚韧不拔的意志。
由于受意识形态、诗学形态、文献资料、翻译策略等因素的制约,不同译者译本所建构与再现的毛泽东诗人形象亦有所差异。鉴于此,兹举《清平乐·会昌》中诗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三家译本以析之。
译文1:
Day breaks in the east;
Don’t say we march too early,
For we’ll cover all green hills before we grow old.
The view from here is singularly beautiful.[14]
Dawn wakes in the east
Don’t say we are marching early.
Though we stomp over all these green hills
We are not yet old,
And from here the land is a wonder.[8]
译文3:
Dawn tinges the eastern skies.
Boast not you start before sunrise.
We have trodden green mountains without growing old.
What scenery unique here we behold![11]
通过分析原文及其三大译本可知,译文1中,王慧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进行直译。从语义层面来看,王慧明的译文忠实于原文,没有任何问题,但却消解了原文所蕴含的毛泽东诗词固有的慷慨激昂和荡气回肠,从而未能完整再现毛泽东积极乐观的形象。
译文2中,巴恩斯通亦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段,与原诗形成较好的互文参照。同时,此译文还与译文1一样,于第一句、第二句开头部分使用“D”打头的单词,构成了押头韵,进而与译文1形成了恰到好处的互文呼应。此外,译文2的点睛之笔便在于第一句中“wake”一词与最后一句中“wonder”一词的使用。“wake”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突出强调了东方即将初露曙光,暗示着正确的思想和领导即将战胜错误的一方,毛泽东的个人主张也将很快被接受。而“wonder”表面上指的是毛泽东此时所处的会昌风景最佳,堪称奇观;事实上,则暗指自己所坚持路线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性和革命前途的光明性,从而呈现出毛泽东乐观豁达的态度和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北宋诗人苏轼所作的《惠州一绝》中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相较而言,译文3更能凸显出原文作者的深层所指内涵。在第一句译文中,许渊冲通过使用“tinge”一词,表明天将破晓时,朝霞浸染了天空。同理,此处破晓的朝霞似乎也暗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革命的光明前景。这同样亦让人产生联想,回想起毛泽东此前所著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外,原文第二句“莫道君行早”实际上是用典,该典故出自旧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可见,译文3的“Boast not you start before sunrise.”与原文、原文用典出处形成了双重互文。该译文最后一句属于感叹句和倒装句,将“scenery”和“unique”前景化,彰显了会昌风景的独特之美,暗示了毛泽东对其主张路线的坚定和对革命光明未来的信心满满,进而建构出积极乐观、恪守不渝与胸有成竹的诗人毛泽东形象。然而,译文3同样也有瑕疵之处。例如,为了实现“skies”和“sunrise”“old”和“behold”的两两尾句押韵,于第二句末尾无故增添了“sunrise”一词,属于过度增译和因韵害意。又如最后一句在感叹号前使用“behold”一词,侧重点落在了“看”这一动作上。事实上,原文此处旨在强调会昌“存在”独特的风景,进而暗指此处有正确的路线和光明的前景,而并非凸显出“看”这一动作。
五、民族形象
中华民族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纵览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其无一不呈现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毛泽东诗词也并非例外。通读毛泽东诗词,会发现,其中处处闪耀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崇高精神,建构出了具有爱国主义与仁爱之心、勤劳俭朴、艰苦奋斗、勠力同心、同舟共济的中华民族形象。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江西与湖南的农民、江西修水、铜鼓及安源等地的工人和部分北伐军,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不久,彼时中国革命正处于极为艰难的关头。此时毛泽东意气风发,激情满怀,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该词分为上阕和下阕。上阕主要叙述了秋收起义的行动,下阕重点描述了秋收起义的根本原因和浩荡声势。整首词语言通俗,平中见奇,气宇轩昂,刚健有力,引经据典,文采斐然。其运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抒发了对工农革命武装暴动的赞扬之情,从而建构出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同仇敌忾、不畏强暴,敢于同反动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工农革命军和中华民族形象。
然而,该词各英译本中民族形象建构现状又如何呢?兹举“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两译本以析之。
译文1:
Heavy was the landlords’ oppression.
Each of the peasants bore hatred deep.
At Autumn Harvest dusky dark clouds heap.
Like a thunderbolt started the uprising.[9]
译文2:
The landlords piling up oppressions thick and high;
The peasants bearing common hatred one and all.
The evening clouds look heavy in the autumn sky;
The revolt breaks out as a thunderbolt does fall.[11]
对比分析不难发现,首先,译文1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不破坏原文语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贴近原文,从而真实再现了自强不息、众志成城、不畏强暴的工农革命军与中华民族形象。其次,译文1第三句将“秋收时节”译为大写的“Autumn Harvest”,使之前景化和陌生化,既突出强调了起义发生的时间,又延长了译入语读者的审美时长,让读者深度思考此处大写的深层内涵,从而还原出原文的文学性与诗学价值。同时,该行使用“dusky dark”“clouds”和“heap”等词与原文中的“暮云愁”进行对应,仿佛建构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氛围,象征着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之下,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情形。再者,该译文还于第二句和第三句运用了尾句押韵,与原诗第二句、第三句句末的“ou”韵形成深度互文。然而,译文1同样存在不足之处,如第二句中,仅使用“deep”一词,表现出农民对地主深深的仇恨和重重的打击,但却未呈现出原文“同仇”的所指内涵。实际上,“同仇”源于《诗经·秦风·无衣》中的“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意为同心协力共同对抗敌人。因此,农民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的精神和反抗地主阶级的普遍性在译文1第二句中并未得以充分彰显。
译文2第一行通过使用“pile up”“thick”及“high”等具体化、形象化的词汇,表明地主对农民的压迫犹如秋收时节的草堆一般,又“厚”又“高”。农民“背负”着巨大压迫与奴役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行中,译者运用“bear”“common”“one and all”等词汇和表达,阐明了每个农民都怀有共同的仇恨。然上述表达过于强调农民“怀有共同仇恨”,遗漏了原文“同仇”之“同心合力打击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内涵。第三行中,译者采用模糊翻译法对原诗的“秋收时节”进行模糊性处理。此外,译者利用“heavy”一词深刻揭露了在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下,农民生活窘迫、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的历史画面。最后一句译文通过采用前景化的方法,将“revolt”暴动一词前置,使之中心化,从而表明秋收起义是工人和农民在不堪忍受的重重压迫之下的必然结果和正确抉择。同时,原文该句中的“霹雳”为用典的写作手法。此典故为口语化的典故,出自《七发》的“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译者运用“thunderbolt”一词,与原文“霹雳”的典故形成深度互文,凸显出暴动的突如其来和浩浩荡荡,进而建构与呈现出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中华民族伟大形象。
六、结语
本研究立足互文性理论视域,结合毛泽东诗词的国内外经典译本,重点分析了毛泽东诗词英译中所建构的军人形象(红军形象、女民兵形象)、伟人形象、诗人形象及民族形象,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就理论抓手而言,可适当借鉴互文性理论。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完全可以基于互文性理论,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与深入理解原诗的基础上,以先前优秀译本为互文参照,遵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翻译原则,进而创造出别出心裁的高质量译本,从而实现原文与典故、译文与原文、译文与译文间的三重互文。其二,就翻译策略而言,可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毛泽东诗词可谓文学魅力、诗学价值、革命历史与政治理想的高度结合。故此,在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应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着力保留原诗的文学性和诗学功能表达,竭力传达原作的意美、音美、形美,从而努力建构与还原出客观、真实、立体、全面的毛泽东形象及其宏大抱负。其三,就译者主体而言,应力求避免译者主体过多的主观介入。毛泽东诗词不仅具备深厚的文学特质,还彰显出毛泽东宏伟的政治理想,是文学、历史、政治、地理、哲学与军事的高度统一体。因此,在进行毛泽东诗词英译时,应尽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着力避免创造性翻译方法的运用和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发挥,从而真实传递出原文的文学韵味,呈现出客观、立体、全面的毛泽东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