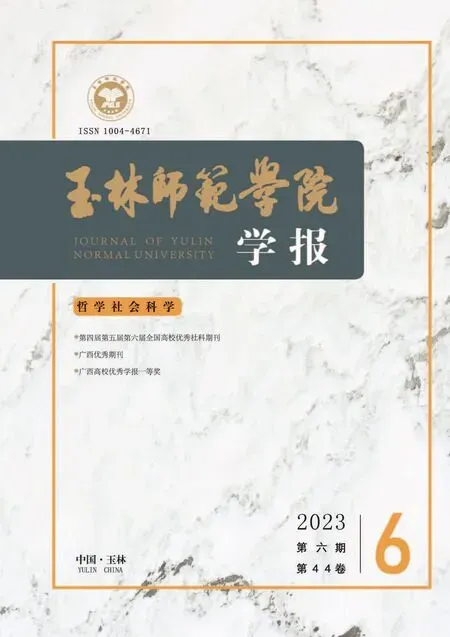杜甫《洗兵马》诗系年研究评议
吴怀东,杜 马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杜甫《洗兵马》诗曾被王安石选为杜集压卷之作。①王安石:《老杜诗后集序》,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466页。此诗句似排律,自成一体,笔力矫健,饱含杜甫对唐帝国中兴的热切期盼,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萧涤非先生评价此诗“用寓讽刺于颂祷之中的手法对唐廷提出了严厉的指斥和‘意味深长’的警告”②萧涤非选注,萧光乾、萧海川辑补:《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1页。。对《洗兵马》诗创作时间的判定,直接影响对此诗主旨的解读。
关于杜诗的系年问题,早在宋代就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北宋初年,王洙以唐代“旧蜀本”为底本编次《杜工部集》,主体上是按照古、近体编次,在分体之中,又寓编年。王洙本参校精良,此后成为一切宋本杜集的祖本。自北宋中叶以来,杜诗逐渐获得经典地位,士人对杜诗的需求空前高涨,对杜诗的整理与编辑成为当务之急,不过当时的杜集编纂情况甚为混乱。北宋末年产生了第一部杜诗编年诗集——黄伯思《校定杜工部集》,打破了旧集分体的界限,完全以年月为纲。此后,蔡兴宗以及鲁訔等人编纂的杜集将分体本重新编纂回到编年形态。诗文集的编年实践同时也促成了年谱的产生,吕大防率先为杜甫编年谱,赵子栎继之。梁权道《杜工部年谱》、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鲁訔《杜工部年谱》等分别对杜诗进行编年整理。到了南宋中后期,黄希、黄鹤父子对杜诗逐一系年。黄鹤对之前的杜集编年本皆不满意,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中对杜诗重新编年,版本上仍采用最具源头性的王洙本为底本,同时照顾到杜诗“诗史”的性质,对每首诗进行题下系年并阐释理由。经由黄氏的整理,杜诗编年初现轮廓,虽仍存在编次混乱的情况,不过,传世的杜诗名作大多明确了作年且没有争议,而《洗兵马》一诗的系年就属于争议较大的名篇。吕大防《杜诗年谱》、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梁权道《杜工部年谱》认为《洗兵马》诗是乾元元年(758)作,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认为是乾元元年“春在谏省”作。③参见吕大防《杜诗年谱》,四部丛刊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附;赵子栎《杜工部年谱》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蔡兴宗《杜诗年谱》,《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影印四部丛刊本。按,梁权道,生平无考,其所编《杜工部年谱》未见公私书目记载,书中对杜诗的“编次先后”,散见于《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中,黄鹤常引用其说。现原书已佚失,对现存文献搜集、整理,仍可见其年谱中部分内容,详见徐昕《梁权道〈杜工部年谱〉研究》,《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黄希则认为此诗作于乾元元年春,《选诗补注》卷四《洗兵马》“田家望望惜雨干”,黄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乃作此诗云耳。”黄鹤继承黄希之说,继而阐发云“此诗当是乾元二年春作,末云‘田家望望惜雨干’,盖二年春无雨也,梁权道编在元年,恐非”①参见黄希原本、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杜甫撰,黄希、黄鹤补注《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卷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山东省博物院馆藏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认为梁权道等人编在乾元元年有误。自宋以来,杜诗研究者对此诗系年聚讼纷纭,重要杜诗注家如黄鹤、仇兆鳌、浦起龙、杨伦认为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春,而赵次公、钱谦益等认为此诗作于乾元元年春②参见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14页;浦起龙著《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7页;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215 页;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当代学者看法也一分为二:詹锳、徐树仪、邓魁英、聂石樵、莫砺锋、林继中、郝润华等赞同乾元元年春说③参见徐树仪《〈洗兵马〉系年及解释辩误》,《草堂》1983年第1期;邓魁英、聂石樵编注《杜甫诗选》,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85页;莫砺锋著《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林继中《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24—28页;郝润华、章蕾《杜甫〈洗兵马〉诗的创作主旨》,《杜甫研究学刊》2019第4期,第23—31页。林继中《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和郝润华、章蕾《杜甫〈洗兵马〉诗的创作主旨》两篇文章都认为此诗系年有三种说法,除本文叙述的两种说法外,另一种说法是作于至德二载(757)收京之后,即原注:“收京后作。”按,原注只是提供了一个大概的线索,且时间上包括乾元元年和乾元二年。乾元元年三月,楚王李俶改封为成王,根据诗中“成王功大心转小”一句,即可判断本诗的创作时间一定在乾元元年三月或之后。考察诸注本及相关研究论文,最具争议的仍是“乾元元年春说”与“乾元二年春说”,本文不另立“至德二载收京后”为一种说法。,萧涤非、朱东润、陈贻焮、廖仲安、张忠纲等赞成乾元二年春说④参见朱东润著《杜甫叙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9页;陈贻焮著《杜甫评传》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页;张忠纲选注《杜甫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2页;廖仲安《〈洗兵马〉系年再辩——答徐树仪同志》,《文史哲》1985年第6期,第65—68页。——此说也是学界流行的说法,二说必有一是一非。纵览诸家讨论,他们讨论所依据的证据无非三个因素,即官职变化、地理方位、典故指向,据此讨论此诗系年。本文梳理文本细节,比较两种说法对所依据文本解读之偏颇得失,认为乾元元年春作说更为可靠。
一、地理方位与战争时局的判断
乾元元年春说与乾元二年春说主要分歧,是此诗首段叙述的战事到底是收复两京之战还是九节度兵围相州之战?两次战事都是以平叛安庆绪为主展开的持久战,作战地点亦集中于河北一带,且官军一方占据舆论、军事等有利形势。存在争议的地理方位主要是“山东”和“淇上”。
先来看“中兴诸将收山东”之“山东”⑤战国、秦、汉时代,称崤山以东为山东;北魏、隋、唐以后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赵次公注:“山东者,今之河北也,盖谓之山东、山西,以太行山之分也。”⑥杜甫著,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发生于河北一带之战事,诸家举史料不一,且各有理据。持乾元二年春说者据《资治通鉴》载,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自杏园渡河,破安太清,围卫州。鲁炅、季广琛、崔光远、李嗣业皆会郭子仪于卫州。安庆绪来救,复破之,拔卫州,追安庆绪至邺。许叔翼、董秦、王思礼、薛兼训引兵继至,围邺,认为九节度兵围相州之局势为“中兴诸将收山东”。又引《资治通鉴》记载“(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自冬涉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食尽,一鼠值钱四千,淘墙及马矢以食马。人皆以为克在朝夕”⑦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68页。,认为“克在朝夕”与诗中所云“只残邺城不日得”的形势正相吻合。而持乾元元年春说者则根据两《唐书》之记载:安禄山反,先陷河北诸郡,至德二载(757)九月王师收西京,十月收东京,安庆绪奔逃于河北,史思明、严庄、能元皓相继投降,河北诸郡渐复,形势可喜,称收复两京之局势为“中兴诸将收山东”。持乾元元年春说者又据《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十一月,……张镐帅鲁炅、来瑱、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十二月)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⑧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44、7048页。等记载,认为沧州、德州、棣州皆近渤海,使得下文“已喜皇威清海岱”有了着落,比引乾元元年十月围相州一事更切合诗意。
仅从上述史料来看,两种战局都具备激发杜甫创作《洗兵马》的可能性,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准确,还须从文本与史实进一步判断,关键在“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两句。至德元载(756)七月,唐肃宗即位于灵武,着手反击安史叛军收复失地,不过肃宗急于求成,否定了李泌提出的歼灭叛军老巢范阳的长期作战计划,执意先收复两京。至德二载十月两京收复后,安庆绪败走守邺城,肃宗又拒绝继续追击叛军的建议,转而准备迎接玄宗、朝祭宗庙、策勋行赏等事,这也为双方留了一年的休整期。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再掀反旗;九月,肃宗命九节度之师讨伐安庆绪;十月,郭子仪收复卫州,安庆绪战败困守邺城;十一月,郭子仪收魏州;十二月史思明复夺魏州,时王师围邺城,安庆绪食尽,求史思明支援,自冬至春,王师未能破贼,双方对峙数月之久。若此诗作于乾元二年春,此时之战况已不能称为“不日得”,而是久攻难下,叛军也非“命在破竹中”。杜甫于乾元元年春至乾元二年春所作诗文多涉及当时战事,如《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诗云:“胡骑潜京县,官军拥贼壕。鼎鱼犹假息,穴蚁欲何逃。”又曰:“今日看天意,游魂贷尔曹。”《观兵》诗云:“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候其形势渐进,又遣李广琛、鲁炅等军进渡河,……逐便扑灭,则庆绪之首可翘足待之而已。”可以看出,杜甫一直秉持“只残邺城不日得”的看法,对官军的军事实力充满自信,“不日得”表明杜甫对叛军将被快速消灭的预测与信心。
两京顺利收复,郭子仪领导的朔方军功不可没,肃宗感激郭子仪,曰“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①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旧唐书》卷一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52页。,充分肯定他的功绩,所以诗中称“独任朔方无限功”也有现实根据。而九节度兵围相州之战,李俶并没有参与,且肃宗认为郭子仪、李光弼皆为元勋,难相统属,派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使,不立元帅,因此,“独任朔方”便与史实不符。一些持乾元二年说者认为“独任朔方”是以正言寓婉谏,意在劝诫肃宗专任郭子仪则中兴可期,但是,肃宗的任命已是定局,并未置身军营中的杜甫对于前线的军事行动不可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又怎会先知般地预感九节度军失利从而劝肃宗专任郭子仪的朔方军?再从诗歌的结构来看,如果首段是写九节度兵围相州之局势,后文又写“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之收复两京的胜利景象,则明显叙述逻辑就比较混乱,所以,首段叙述之战局应是收复两京之战,也即乾元元年春之系年说合理。
另外,“淇上健儿归莫懒”中“淇上”也有阐释空间。此句是写杜甫期盼战争尽快结束,“淇上”的士兵们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持乾元二年春说者根据首段战局是九节度兵围相州之战,认为淇水在卫州,与相州相邻,由此判断“淇上健儿”指围相州之兵。但“淇上健儿”不一定非指围相州之兵,林继中先生认为可能是指李嗣业赴关中屯河内之部队②参见林继中《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其说可从。河内县,属怀州管辖,在东都洛阳东北,为京畿屏障,淇水所在的卫州正处于相州与怀州之间。《资治通鉴》乾元元年三月条载“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兵河内”,四月条载“安庆绪闻李嗣业在河内,与蔡希德、崔乾祐将步骑二万,涉沁水攻之,不胜而还”③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53页。。李嗣业与安庆绪之间的卫州(即淇上),在乾元元年三、四月已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当时的主战场,李、安之间一定发生过多次交手,因此“淇上健儿”有可能指李嗣业的部队,不必待九节度围邺城。不过,“淇上健儿”也可能泛指平叛敌军的士兵,毕竟收复两京之战与九节度兵围相州之战都是围绕相州附近展开的持久战,作战地点多有重合,且前线将领皆以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等人为主。因此“淇上健儿”为围相州之兵的判断有待商榷。
二、官职变动与系年范围的判定
根据职官称谓推测此诗的创作年代,是乾元元年说者与乾元二年说者争论的焦点。诗中提到的官职集中在“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四句的解读之中。“成王”指李俶,安史之乱时作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郭子仪等诸将领收复失地。《旧唐书·肃宗本纪》卷一○载:“(乾元元年三月)甲戌,元帅楚王俶改封成王,……(乾元元年五月)庚寅,立成王俶为皇太子。”①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1、252页。萧涤非选注,萧光乾、萧海川辑补:《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7页。此诗如若作于乾元二年,称李俶为“成王”便有些不合时宜。册封“成王”之时间,成为持乾元元年说者的有力证据。持乾元二年说者则有反对意见,浦起龙认为“王已立为太子,句意在于纪功,故称其勋爵”②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7页。,是杜甫意在赞扬李俶在职时的收复之功,所以称“成王”。萧涤非先生虽也持乾元二年说,但在《杜甫诗选注》中指出,杜甫称呼官爵有时与史事有异,如《新安吏》“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句中的“仆射”,因为乾元二年郭子仪早已由左仆射改中书令,《新安吏》仍旧称他为“仆射”③萧涤非选注,萧光乾、萧海川辑补:《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7页。;再如李光弼,晚年已官至太尉,而杜甫《八哀诗》尚题为司徒,原因是“盖写诗非写诏令公文,固可不必随其官职之迁转而改称也”④杜甫著,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7页。。因此,根据不称太子而称成王以断定此诗的写作年代,显然并不准确。不过,成王封为太子一事,事关社稷,意义重大,可以说是天下皆知,杜甫应该会在诗中如实书写。
诗中“郭相”指郭子仪,“司徒”指李光弼,对此诸家没有异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载:“(至德元载八月)以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⑤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一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90页。《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载:“(乾元元年八月)丙辰,以郭子仪为中书令,光弼为侍中。”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60页。至德元载八月,郭子仪和李光弼同为平章事,都可以称相。萧涤非先生以此反驳乾元元年春说:“此诗若作于乾元元年,郭子仪和李光弼二人同为平章事,何以独称郭相,不称李光弼为李相而称司徒?”萧先生认为中书令是右相,位于百官僚之首,是真宰相,郭子仪于乾元元年八月任中书令,所以称郭为相,不称李为相。⑦参见萧涤非选注,萧光乾、萧海川辑补《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08页。《旧唐书·职官二》载:“(中书令)天宝改为右相,至德二年(757)复为中书令。本正三品,大历二年(767)十一月九日,与侍中同升正二品,自后不改也。”⑧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48页。赖瑞和先生也提到:“左相即门下省首长侍中,右相即中书省首长中书令,两者(左右相)都是一时的改名,只行用于高宗龙朔二年到咸亨元年(662—670),以及玄宗天宝元年到肃宗至德元载(742—756)年间。”⑨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0页。郭子仪在乾元二年升为中书令,也就是说,乾元二年册封的中书令已不再是右相,所以萧先生据“称右相”而判断此诗写于乾元二年并不准确。杜甫称郭而不称李为相,是考虑到诗语书写忌重复,成王、宰相、司徒和尚书,依次为后文的“二三豪俊”,是根据个人地位及官阶排列。司徒为正一品,品秩高于宰相,为朝臣加官而设,彰显其荣誉,并无实际职权。李光弼原是郭子仪手下裨将,经由郭子仪推荐后被皇帝重用,作为后进,无论是资历还是声望,都不及郭子仪,所以称郭为相并置于司徒之前也合情理。
诗中“尚书”指王思礼。《旧唐书·肃宗本纪》载,乾元元年“八月,……甲辰,上皇诞节,上皇宴百官于金明门楼。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来朝,加子仪中书令,光弼侍中,思礼兵部尚书,余如故”⑩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3页。。此条史料是持乾元二年说者的重要依据,萧涤非先生据此认为:“王思礼加兵部尚书,事在肃宗乾元元年八月,……此诗必作于乾元元年八月以后之明证。”○1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1、252页。萧涤非选注,萧光乾、萧海川辑补:《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7页。乾元元年说者也引史料反驳,《旧唐书·肃宗本纪》载:至德元载,“癸未,……上素知房琯名,至是琯请为兵马元帅收复两京,许之,仍令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新唐书·肃宗本纪》载:至德元载十月,“房琯为招讨西京、防御蒲潼两关兵马元帅,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资治通鉴》至德元载十月条:“房琯上疏,请自将兵复两京,上许之,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①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03页。这三则史料记载事实都发生在乾元元年之前,其时王思礼就已被称作兵部尚书,不必待乾元二年。但此处有一疑点,王思礼如在至德元载是兵部尚书,为何在乾元元年八月又册封为兵部尚书?可见《旧唐书》关于王思礼官职记载前后矛盾。《旧唐书·唐纪》载,天宝十一载(752)三月,“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其部内诸司有部字者并改”②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90页。,至德二载复故,也就是说,《新唐书》《通鉴》所谓王之“兵部尚书”,是沿误《旧唐书》,当作“武部尚书”。至德元载十月之时,郭子仪为武部尚书③参见严耕望撰《唐仆尚丞郎表》第1册,中华书局1968年出版,第263页。,但唐制规定,六部尚书员额各为一员,此时王思礼不可能是武部尚书。《旧唐书》关于王思礼官职之记载不仅前后矛盾,还弄错官称。持乾元元年春说者引用的史料不足为凭。
王思礼在乾元元年八月迁兵部尚书前究竟担任何官职?《旧唐书·王思礼传》:“至德二年④按,“二年”当作“二载”,“年”当是“载”之误。《新唐书·王思礼传》:“至德二载,攻贼崔乾祐于潼关,乾祐败,退保蒲津。”唐天宝三载(744)改年为载,见《新唐书·玄宗本纪》:“(天宝)三载正月丙申,改年为载。”唐肃宗乾元元年又重新改“载”为“年”。《肃宗本纪》:“改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故“至德二年”当作“至德二载”。九月,思礼从元帅广平王收西京,既破贼,思礼领兵先入景清宫。又从子仪战陕城、曲沃、新店,贼军继败,收东京。思礼又于绛郡破贼六千余众,器械山积,牛马万计。迁户部尚书、霍国公,食实封三百户。”⑤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13页。《新唐书·王思礼传》记载则相对简略:“长安平,思礼先入清宫;收东京,战数有功。迁兵部尚书,封霍国公,食实户五百。”⑥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四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50页。“户部尚书”变成了“兵部尚书”。严耕望先生考证《全唐文·肃宗收复两京大赦文》 “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兼工部尚书持节充招讨西京并定武威武兴平等军兼关内节度……兵马使王思礼……可开府仪同三司行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封霍国公,实封六百户”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0页。及《唐会要》功臣条,认为王思礼任兵部尚前为工部尚书,纪传皆失书,旧传载“户部尚书”不确,新传载“兵部尚书”亦误。⑧参见严耕望撰《唐仆尚丞郎表》第4册,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910页。王思礼在乾元元年春时任工部尚书,乾元元年说者所举史料虽有误,但并不影响杜甫在诗中称王思礼为“尚书”,故“尚书”一职并非此诗作于乾元元年八月后的明证。
三、典故意指与文本理解的歧异
《洗兵马》诗中重要人名典故所指也有助于推断本诗系年。因为典故所指之人并不明确,因此,诸家对典故意指看法也不尽相同,须先确定意指之人并根据其为官时间进行合理推测。
(一)“萧丞相”意指析疑
诗句“关中既留萧丞相”中“萧丞相”的指向争议较大。宋人旧注指萧华,赵次公认为是郭子仪,蔡梦弼认为是指杜鸿渐,朱鹤龄、仇兆鳌亦从此说。钱谦益、杨伦则认为是房琯。浦起龙云是杜鸿渐或房琯,但二说未知孰是。当今学者多认同钱谦益、杨伦之看法,最近卢多果撰文认为是苗晋卿。⑨参见杜甫著、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235 页;鲁訔编次、蔡梦弼笺注《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一,影印元大德年间陈氏刊本;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页;浦起龙著《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8 页;卢多果《从史家之心到诗人之眼——杜甫〈洗兵马〉史事及主旨新证》,《文学评论》2023 年第3 期,第198—206页。“萧丞相”如指萧华,萧华曾陷贼“伪署魏州刺史”,见《旧唐书·萧华传》,必非所指。郭子仪虽可比萧何,但诗的前两段已叙其武功并反复称颂,此处无须重复。至于杜鸿渐,杨伦认为鸿渐为人无功勋,且非公所喜,自当以房琯为是,其说可从。至德元载八月,房琯与韦见素等大臣由蜀地至灵武,《旧唐书·房琯传》载:“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①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90页。房琯在当时地位可见一斑。至德二载五月,房琯受贺兰进明、崔圆的诬告及门客受贿事件被罢相,贬为太子少师。是年十一月,房琯随唐肃宗返回长安,十二月肃宗大赦天下,策勋行赏,加琯金紫光禄大夫,进封清河郡公。至于苗晋卿,《旧唐书·苗晋卿传》载:“会肃宗至凤翔,手诏追晋卿赴行在,即日拜为左相,军国大务悉以咨之。既收两京,以功封韩国公,食实封五百户,改为侍中。”②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21页。《旧唐书·肃宗纪》载:“(至德二载)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百僚班于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晋卿率百辟称贺,人人无不感咽。”③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9页。苗晋卿改授侍中。可见,从肃宗即位灵武到收复长安后,苗晋卿一直是深受唐肃宗信任的宠臣。
乾元元年三月,楚王李俶改封成王,此诗既然提到了“成王”,那么本诗的创作时间一定在乾元元年三月或之后。《旧唐书·房琯传》记载至德二载五月房琯罢相后,“既在散位,朝臣多以为言,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当国家驱策,冀蒙任遇”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23页。。《资治通鉴》乾元元年六月条载:“太子少师房琯既失职,颇怏怏,多称疾不朝,而宾客朝夕盈门,其党为之扬言于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⑤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056页。乾元元年三月至六月期间,房琯虽被排挤出权力中心,退居散位,但仍身处关中。房琯多次招揽宾客,让朝臣为其美言,希望重新得到肃宗的认可与重用。注家及学者多执着于“萧丞相”意指主掌内政的宰相,房琯早在至德二载五月就已罢相,从时间来看,只有苗晋卿符合。只是苗晋卿无功无过,与杜甫交集尚浅,杜甫在诗中也很少提及他,称其为“萧丞相”的可能性较小。而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之交,二者皆奉儒守官,意气相合。杜甫曾上疏力救房琯,既出于个人交情,也是为国家社稷考虑,房琯作为旧臣出任新朝宰相,是能在政治上团结“二圣”的关键。诗句中的“留”字也可以看出杜甫的用意,是对房琯品德才能的肯定,也是对肃宗重新启用房琯的期冀。
(二)“张子房”“张公”意指析疑
“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两句中“张子房”“张公”的意指对象颇有争议,学者多认为同指一人——张镐。林继中先生则认为分指二人,“张子房”指李泌,“张公”指张镐。⑥参见林继中《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林继中先生认为赵先生所论明快,颇具说服力。清代梁运昌《杜园说杜》笺云:“子房则从来并指张镐,但不应琯一句而镐五句,则此子房当指邺侯(李泌),不以切姓论也。张镐独详于二公者,此时琯已罢相,泌已还山,张乃现在倚任之人,故借作收科。”⑦梁运昌撰:《杜园说杜》,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页。林先生赞同梁氏之说,认为“顶针”不必绝对化,盖杜甫用典注重切姓,如“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既然此处“萧丞相”指房琯,不姓萧,则“张子房”意指之人亦不必姓张。⑧参见林继中《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赵昌平先生认为:“‘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此为顶为针句格,‘张公’必复指上句之‘张子房’,二句说一人,无可置疑。”学者卢多果也持此观点,认为所指之人是张镐,不可分指两人。
怎么判断意指何人?仍须回到文本中寻求线索。按照本诗的叙述逻辑,“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在“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禁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四句之后,那么“幕下复用”之人应当在两京收复,玄宗回朝、肃宗大赦天下后(即乾元元年初)仍在任职。诗句中的“关中”与“幕下”相对,“关中”应指在皇帝身边辅佐的朝臣,“幕下”当与军旅将帅有关,所以二者与所处位置应是一内一外,言“既留”“复用”,是相当“既……又……”的句式,并非先后之序,是同时并用之意。李泌参与军事行动在收复长安前,长安收复(至德元载十月)后李泌就已归隐,不能称之为“幕下复用”。至德二载八月至乾元元年四月,身为平章事的张镐兼任河南节度使,持节统淮南等道诸军事,符合“幕下”之条件。任节度使期间,张镐杖杀畏敌不前的濠州刺史闾丘晓,协助郭子仪收复二京,后又洞察到史思明伪降,足见其是“扶颠筹策良”的人才。萧涤非先生在《杜甫诗选注》中认为:“凡是在节度使幕府任职的,则云‘幕中’或‘幕下’,张镐如未罢相,岂得云‘幕下’?在相位,居廊庙。”①萧涤非选注,萧光乾、萧海川辑补:《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15页。其实,安史之乱属于非常时期,唐肃宗鉴于张镐是文武全才,才予以张镐重任,派遣其挽救河南局势。宰相为何不能居幕下?身为平章事的张镐兼任河南节度使,就是一个最佳例证。至于张镐符合“张子房”的其他条件及理由,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已有阐发②详见卢多果《从史家之心到诗人之眼——杜甫〈洗兵马〉史事及主旨新证》,《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论述精深得当,兹不赘述。
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被贬为邠州刺史,张镐此时已罢相,乾元二年三月的杜甫,在叙述人事功勋时,已没必要再大力表彰在当时政治军事格局中已无关紧要的人物。部分乾元二年春说者认为,杜甫作此诗时房琯出为邠州刺史,据《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载邠州均属关内道,因此诗中“关内既留”不直云罢黜,应是杜甫对肃宗重新启用房琯犹存厚望;同年五月,张镐罢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仍居幕府之中,也是劝谏肃宗复用之。凡诗中涉及的人事,部分注家皆解读为措辞深婉、讽谏规劝,尤以钱谦益为甚。清人吴瞻泰在《杜诗提要》中指出:“按史,乾元元年二月,徙楚王俶为成王。夏五月,张镐罢。又是年立成王俶为皇太子。称成王之日,正张镐以宰相兼河东节度使之时,至五月罢相,成王已为太子,不得复称成王矣。但李泌已归衡山,李辅国已兼大仆射,肃宗信馋远忠之渐,公或逆睹其萌,故望其任用张公之心愈切,而歆动之语愈不觉其浓至耳。若既罢相矣,公方咨嗟叹息之不暇,亦何暇作期许殷恳、满心快意之笔如此哉!”③吴瞻泰:《杜诗提要》,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112页。因此“萧丞相”“张子房”应分别指代房琯和张镐,此诗创作时间当为乾元元年三月至五月之前。
四、余论
除上述讨论的官职、地理、典故等因素,杜诗内容所涉节候也可以辅证系年判断。且看“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两句。部分学者据史载乾元二年有春旱,认为此句中“雨干”的意思是无雨,是写天旱无雨而田家盼雨,由此判定此诗作于乾元二年春二月。萧涤非先生则认为“雨干”是雨晴的意思,如杜甫《寄赞上人》“当期塞雨干,宿昔齿疾瘳”、《重简王明府》“江云何夜尽,蜀雨几时干”中的“雨干”就是雨晴之意。萧先生认为此句是写杜甫预言一两个月后,邺城战事结束时的太平景象,是杜甫设想当时春雨既足,田家正待耕而盼晴。林继中先生也认为“惜雨干”并非无雨,恰好相反,是有雨而眼巴巴地看着雨干掉,并猜测是由于丁壮皆上前线,春种无人,所以惜之。部分持乾元二年春说者,如仇兆鳌认为此诗作于“春二月”之证据,大概就是黄希所说的“按《史》:乾元二年春旱,乃作此诗云耳”④黄希原本,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检《资治通鉴》、两《唐书·肃宗本纪》等,并无记载乾元二年春天有干旱之记载,应该是黄希以杜甫诗句而意逆之词,不足为据。《洗兵马》诗最后两句“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用武王伐纣典故:“武王伐纣……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散宜生谏阴说:‘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刘向《说苑·权谋》)点明了杜甫对战争正义性的认同,也呼应首段叙述的胜利在望之战局。历经三年战乱,农村社会遭到破坏,兵役、赋役、饥荒致使劳动力短缺,田地荒芜,农业凋敝。两京收复后,国家恢复了久违却也短暂的和平,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诗云:“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时值春种之际,春雨降临,热心时事、悲天悯人的杜甫很难不感于哀乐,缘景感发。诗人希望春雨不仅“净洗甲兵”,也润泽农田,《洗兵马》应是杜甫当时的感受,而不是预想邺城之战结束后的景象。
历来的研究者对此诗进行阐释,多着眼于历史与诗歌文本之间的贴合互证,征引的史料有限,史料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分歧,部分注家自我带入式地注解诗句必然使诗中呈现的“史相”与“史实”之间产生距离。除了关注史料之外,更应注意杜甫所处的现实处境和情绪心理。浦起龙在《读杜提纲》中主张读杜诗“须通首一气读。若一题几首,再连章一片读。还要判成片工夫,全部一齐读。全部诗竟是一索子贯”①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2页。。文本的意味就存在于部分与整体的相互说明之中,只有“上下文”的整体性才能“显出一时气运”来。《洗兵马》一诗不仅有内容,还有其感情和节奏。此诗描绘的正是一种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秩序的青春景象。宋代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观此诗闻捷书之作,其喜气乃可掬,真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下,《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8页。明末王嗣奭也认为《洗兵马》诗“笔力矫健,词气老苍”,虽然部分诗句“微有风刺,如当时封爵太滥”之情况,但整体而言“喜跃之象浮动笔墨间”③王嗣奭:《杜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应当说,乾元元年春收复两京后之情形,就已具备激发作者这种情绪的可能性,林继中先生比较了乾元元年春与乾元二年春两个时段杜甫的现存作品,认为杜甫在乾元元年春要比乾元二年春更具书写的冲动性。④参见林继中《杜诗〈洗兵马〉钱注发微》,《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3期。
乾元元年春,杜甫在京任左拾遗,在长安过着比较闲暇的生活,他为两京顺利收复而欣喜,几个月来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皆在《洗兵马》一诗中有反映。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被贬为邠州刺史,与房琯关系密切的严武等人也被外贬,杜甫也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日益衰老的诗人离开长安后,凝望皇城的千门万户,或许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事实上杜甫再也没有回到朝廷,也没有机会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洪业先生说:“《洗兵马》代表了杜甫在生命最快乐的这段时期欢乐情绪的顶点。”⑤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考察杜甫贬官华州后的作品,多抒发感伤、苦闷、愤慨之情,很少论及朝廷与皇帝,创作视角主要集中于下层生活,多反映社会现实,诗歌创作中的青春气象虽逐渐消逝,却进入了一个别开生面、浑然天成的新阶段。综合古今学者的考证研究,显然,《洗兵马》作于乾元元年更为可靠。
——润心至德 立德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