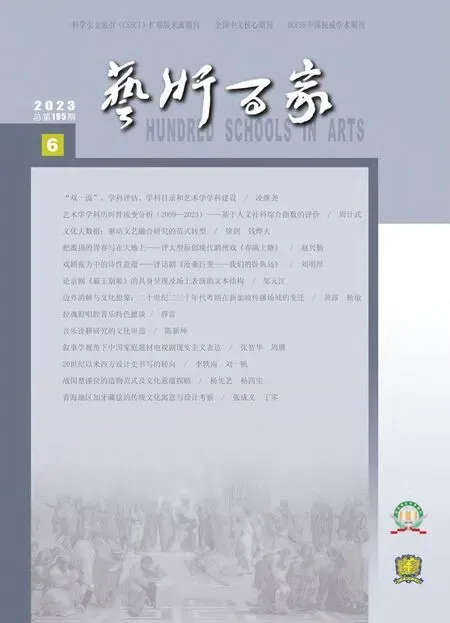论京剧《霸王别姬》的具身呈现及场上表演的文本结构*
邹元江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022年是杨小楼、梅兰芳主演的《霸王别姬》在“第一舞台”首演100周年。杨小楼(1878—1938年)在该剧中饰演霸王项羽时44岁,正是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早在29岁就入昇平署为外学民籍学生,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梅兰芳(1894—1961年)与杨小楼合作饰演虞姬时只有28岁,也正处于声誉鹊起的时期,1919年梅兰芳应邀赴日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梅兰芳对如父般的杨小楼极其敬重,尤其在他第二次与杨小楼同班合作排演《霸王别姬》的过程中,杨先生的具身表情思维对其表演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霸王别姬》的反复删减修改过程,也充分说明正是具身表情思维决定了传统戏曲场上表演文本结构的生成,它遵循场上搬演的简繁规则。
一、化合“可引用的姿势”的具身表情
梅兰芳曾说:“我心目中的谭鑫培、杨小楼这二位大师,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虽然我是旦行,他们是生行,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最重要。他们二位所演的戏,我感觉很难指出哪一点最好,因为他们从来是演某一出戏后就给人以完整的精彩的一出戏,一个完整的感染力极强的人物形象。”[1]671有学者认为齐如山对梅兰芳的影响更大。[2]336-342其实,齐如山对梅兰芳的影响,尤其在早期,是外在的、话剧化的;[3]98杨小楼对梅兰芳的影响则是内在的,是更符合戏曲艺术的审美本质规律的。[4]64-68尤其是杨小楼在《霸王别姬》中为项羽唱词“力拔山兮”安身段动作的具身表情思维,深深影响了梅兰芳的演艺生涯。
1922年2月15日,杨小楼、梅兰芳主演的《霸王别姬》在“第一舞台”首演。第二天晚上,梅兰芳和冯幼伟、齐如山、吴震修等人去笤帚胡同看望杨小楼。杨先生问:“您三位看着哪点不合适,我们俩好改呀!”吴震修说:“项羽念‘力拔山兮……’是《史记》上的原文,这首歌很著名,您坐在桌子里边念好像使不上劲,您可以在这上面打打主意。”杨先生轻轻拍着手说:“好!好!我懂您的意思,是叫我安点儿身段是不是?这好办,容我工夫想想,等我琢磨好了,兰芳到我这儿来对对,下次再唱就离位来点儿身段。”[1]661-662据崇林社经理刘砚芳回忆,从第二天起,杨小楼“就认真地想,嘴里哼哼着‘力拔山兮……’,手里比划着。我说:‘这点身段还能把您难住?’老爷子瞪了我一眼说:‘你懂什么?这是一首诗。坐在里场椅,无缘无故我出不去,不出去怎么安身段?现在就是想个主意出去,这一关过了,身段好办。’老爷子吃完饭,该沏茶的时候了,掀开盖碗,里头有一点茶根,就站起来顺手一泼,我看他端着盖碗愣了愣神,就笑着说:‘啧!对啦,有了!’原来他老人家已经想出点子来啦,就是项羽把酒一泼,趁势出来”[1]662。
几天后,梅兰芳就被杨小楼叫去。据梅兰芳回忆,“一见面杨先生就说:‘回头咱们站站地方啊。’我说:‘大叔您安了身段啦?’杨先生说:‘其实就是想个法儿出里场椅,不能硬山搁檩地出去是不是?’我说:‘您有身段,我也得有点陪衬哪。’杨先生说:‘你念大王请,[三枪],喝酒,我喝完酒把酒杯往桌上顿一下,念“咳”跟着我就站起来把酒一泼,杯子往后一扔,就势出了位,你随着一惊,也就站起来啦。我念“想俺项羽呵!”唱“力拔山兮……”咱们俩人来个“四门斗”不就行了吗?’当时我们来了几遍‘力拔山兮……’,他在‘大边’里首按剑举拳,我到‘小边’台口亮相;‘气盖世’,他上步到‘大边’台口拉山膀亮相,我到‘小边’里首亮高相;‘时不利兮,骓不逝兮’,双边门,‘骓不逝兮’,各在自己的一边勒马;‘可奈何’二人同时向外摊手;‘虞兮虞兮’他抓住我的手腕。我说:‘咱们就先这样来,唱完了再研究。’”[1]662-663
这就是当年京剧鼎盛时期全能的戏曲艺术家,排戏根本不需要导演,他们就能自编自导,或互为导演。关于这一点,1935年梅兰芳访苏演出时,汉学家尼·沃尔科夫在3月29日的《苏联艺术报》上发表的《梅兰芳的演剧》一文中就已经指出:“中国戏剧,这是以演员为中心的戏剧。我们在中国戏剧中找不到复杂的导演痕迹。”[5]146当年,梅兰芳就请人翻译了这篇文章,现藏于梅兰芳纪念馆的这篇文章的这段译文为“中国戏剧是一种演员技术占最重要地位的戏剧。从中国戏剧里我们找不出导演设计的奥妙”。①中国戏曲演员的表演为什么不需要导演?苏联学者,哪怕是汉学家也未必真正明白。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包括杨小楼、梅兰芳在内的戏曲演员从童子功训练开始就扎实掌握了本雅明所说的“可引用的姿势”(Zitierbarc Gestus)。[6]335-336所谓姿势的“可引用”性,也即使极工练就的艰奥繁难的行当程式动作能够反复组合、化合,“把姿势变得可引用”[6]335。而能不断组合、化合姿势的直接审美效果就是具身表情的凸显。所谓“具身表情”,也即戏曲演员处处以“有声皆歌、无动不舞”[7]310的身体姿势来“表(述、演)情(感符号)”,它是以唱、念、做、打(舞)以及口、手、眼、身、步等极其繁难、艰奥的“四功五法”童子功为根基所建构的身体“姿势化”的审美符号系统。[8]108从杨小楼受泼茶启发而泼酒扔杯“就势出了位”,到梅兰芳看到杨先生安的身段马上意识到“我也得有点陪衬”,之后两人围绕项羽的唱词所设置的身段(“拉山膀”)、动作(“按剑举拳”“勒马”)、姿势(“向外摊手”)、呼应(“四门斗”“双边门”)、调度(“大边”“小边”)、亮相(“台口亮相”“亮高相”“拉山膀亮相”)等,都是戏曲化的具身表情思维过程。
二、非“情节整一性”的场上表演文本结构
杨小楼在《霸王别姬》中安身段动作的具身表情思维,不仅深深影响了梅兰芳,而且,“梅党”反复删减修改《霸王别姬》的攒戏过程也充分说明,正是具身表情思维决定了传统戏曲场上表演文本结构的生成。苏联学者艾姆·别斯金通过比较欧洲话剧与中国戏曲,尤其是梅兰芳表演的京剧,极其敏锐地发现,“京剧在字面意义上是表演”[5]85。由于京剧场上表演的文本结构注重的不是起承转合的完整故事铺排的情节高潮,而是故事梗概与优伶具身绝艺绝活瞬间展示的情感高潮,因此它的“对话非常简单、浓缩……目的是迅速导向主要事件,让演员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舞台技艺。这里几乎没有性格、心理、戏剧性的积累,剧情跳跃式、纲要式地推进”[5]85-86。由此看来,场上表演文本不同于细密铺排的文字文本,也不同于咬文嚼字的文学文本,而是具身姿势化的提纲文本。具身姿势化的提纲表演文本的结构是开放的、不确定的,而文字、文学的文本结构是封闭的、确定的。
时下流行的“现代戏曲”结构就是文字、文学的文本结构,它在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方面强调“四个弱化,一个强化”(即弱化写意性、 虚拟性、程式性和舞台时空流动性,强化写实性)。[9]54-56所谓“写实性”,即遵循西方戏剧的“情节整一性”的文体原则。亚理斯多德认为,一个结构完美的布局就是建构出“整一性的行动”。而结构完美的布局是不能随便起讫的,因为这个“整一性的行动”内部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10]24。即按照“情节整一性”的原则,“一出戏应该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活到任何一处遭到割裂后便会流血的程度!”[11]224据此,吕效平认为,“现代戏曲”的“现代性”就集中体现在“情节整一性”的文体结构原则上,相对于这个文体结构的形式原则而言,一切具体作品的“现代”内容都是偶然的。“情节整一性”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drama”最重要的文体结构原则,它的世界观基础是“理性主义”和“个性主义”。“现代戏曲”的“情节整一性”结构原则的形成固然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但是归根结底,它也是中国社会现代世界观在戏剧形式上的反映。戏曲的“现代化”便是它的“戏剧(drama)化”。[12]1这里所谓的戏曲“现代化”便是“戏剧(drama)化”,即戏曲现代化的出路就寄托在西方戏剧的“情节整一性”结构上,这实际上是将戏曲艺术与西方戏剧强行“置换”。“置换”(displacement)这个词具有变形/毁形、“曲解”、“谋杀”和“被强行脱离自身的语境”的意思。[13]43也就是说,来自古希腊亚理斯多德的“情节整一性”或“整一性的行动”戏剧结构是与传统戏曲的场上表演文体结构,尤其是京剧的场上表演文本结构根本不同的文本结构,“现代戏曲”盲目借鉴这个非戏曲的文本结构,实际上就是“被强行脱离自身的语境”,因而,我们并不能认为“现代戏曲”就是合理的,恰恰相反,它是有违传统戏曲的场上表演文本结构精髓的。1922年“梅党”编攒《霸王别姬》和梅兰芳、杨小楼在该剧上演后反复删减修改的过程,就可以充分说明传统戏曲的场上表演文本结构与“情节整一性”的“现代戏曲”文本结构的区别。
早在1918年4月,杨小楼就在其与钱金福、尚小云、高庆奎合编的《楚汉争》中演过霸王项羽。对于这出分一二三四本的戏目,梅兰芳说:“我曾看过这出戏,是分两天演的。我记得杨先生在剧中演项羽,过场太多,有时上来唱几句散板就下去了,使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虽然十面埋伏有些场子是火炽精彩的,但一些敷衍故事的场子占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就显得瘟了。”[1]6581921年下半年,齐如山依据明代沈采所编的《千金记》传奇,也参照了《楚汉争》的本子,写出了《霸王别姬》的初稿,场子还是很多,分头二本两天演完。梅兰芳、杨小楼准备撤“单头本子”排演时,吴震修看了剧本后说:“如果分两天演,怕站不住,杨、梅二位也枉费精力。我认为必须改成一天完。”[1]659为此,他与齐如山还发生了争执,齐如山把本子扔给吴震修,让他去改,吴震修说他没写过戏,让大家给他两天时间试试看。当时梅兰芳也感到吴先生的主张“很有道理,因为《楚汉争》就是分两天演失败了。《霸王别姬》的初稿,仍有松散的毛病,改成一天演,的确是高明的见解”[1]659。没想到两天后吴震修拿来了修改稿头二本的“总讲”,将初稿的二十场删成不满二十场,以霸王打阵和虞姬舞剑为重点场子。他对齐如山说:“我已经勾掉不少场子,这些场子,我认为和剧情的重要关子还没有什么影响。”[1]659后又经过大家的修改润色,到1922年《霸王别姬》在“第一舞台”首次演出时场子又有了变化。
据梅兰芳回忆,“那天后台贴的提纲虽然是已经从二十多场,删成十多场的提纲,可是过场还是多,有的场子相当长,最大的就是九里山大战那一场,打的套子也很多。我在后台听前面锣鼓喧天,武行头管事的朱玉康在台帘旁注视着场上,有时又招呼着后台,一会从场上进来几个扎靠的,一会从上场门出去几个藤牌手,前台固然很火炽,后台也是显得熙熙攘攘。这场大武戏完了之后,杨老板下来双手轻快地掭了盔头,对我说:‘兰芳,我累啦,今天咱们就打住吧。’我说:‘大叔!咱们出的报纸是一天演完,要是半中腰打住,咱们可就成了谎报啦。我知道您累了,这场戏打得太多了,好在这下边就是文的了,您对付着还是唱完了吧,以后再慢慢改,这个戏还是太大。’当时他没有加可否,接着说了一声:‘还勒上吧。’我赶紧赔笑说:‘您再歇会儿,还有工夫哪。’正说着就听见管事李春林大声说:‘来啦!来啦!虞姬!虞姬!’我看杨老板又戴上盔头,我才放下心出去,总算一天把戏唱完了”[1]660-661。这是梅兰芳的一段极其刻骨铭心也很无奈的回忆。虽然戏已经从二十多场减到了十多场,但过场还是太多,像九里山大战一场还太长,打的套子也很多,累得已经四十多岁的杨小楼都想中途弃演。
由此可见,齐如山的这个本子完全违背了传统戏曲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场上表演文本结构的要求,习焉不察地将西方戏剧讲一个“情节整一性”的完整故事作为出发点,差点将原本武功高强的杨小楼都累趴下,而演出效果却并不理想。
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次痛苦演出的教训,几天后他们在吉祥戏院演出时,场子比上一次又有所减少,只剩下十四五场,但打戏还是不少。梅兰芳回忆说:“当时这出戏我还唱了一段西皮慢板,这一天的演法给初期的《霸王别姬》暂时定了型,演了一个时期,逐渐修改,觉得慢板也有点瘟,后来就不唱了……杨先生也觉得打得太多,反而落到一般武戏的旧套,这出戏的打应该是工架大方,点到为止,摆摆样,所以也逐渐减了不少。这出戏在北京每年义务戏总要演几次,最后是1936年的秋天我从上海回来,又合演了三次,到这个时期我们已减到十二场,解放后减到八场。”[1]663②为何要一减再减?原因就是要不断剥离遮蔽情感高潮戏核的层层情节之“皮”。而戏曲艺术的真正审美魅力正是由演员具身表情的“姿势意义”[14]237、242而凸显的情感高潮戏来实现的。这个“姿势意义”正是经由行为的本义到达行为的转义,并成为“习惯”(第二天性)而获得的。莫里斯·梅洛-庞蒂认为“习惯的获得就是对一种意义的把握,而且是对一种运动意义的运动把握”[14]189。对梅兰芳而言,只有习得虞姬“技艺非凡”的剑舞的“姿势意义”,才能使该剧瞬间达到悲剧的情感高潮。梅兰芳“在《剑舞》中以动作的精确性和力度以及在劲爆的舞蹈节奏中掌握双剑的技艺,都令人感到惊讶”[5]189。这正是1935年3月22日梅兰芳在莫斯科音乐厅大剧院首次表演《霸王别姬》中的剑舞,就令列维多夫感叹“应该激发并迫使我们最好的芭蕾舞演员思考”[5]129的原因。
《霸王别姬》故事情节的一减再减过程说明,场上表演文本的结构形态并不是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铺排,更不是“跑”故事,而是对懂行的观赏者而言早已真相大白的故事梗概——霸王“别”姬——让优伶以家门绝技绝活的具身姿势加以敷衍,以虞姬舞剑的“姿势意义”瞬间推出情感高潮戏。其实,最初吴震修在删减齐如山的初稿时,已经圈出了场上表演文本的“关子”(结构),即“以霸王打阵和虞姬舞剑为重点场子”[1]659。但无论是齐如山,还是“梅党”,最初都没有抓住这个关键的情感高潮戏的“关子”,更没有突出虞姬舞剑的重点场子以凸显梅兰芳饰演的虞姬舞剑的具身“姿势意义”。这正是齐如山的剧本被不断删砍的原因——未能确立霸王如何“别”姬的情感高潮戏。原本太多的“敷衍故事”的过场戏、武打戏,其实都是为了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服务的,而这正是齐如山因早期模仿西方戏剧创作了一出并未上演的话剧《女子从军》而留下的追求“情节整一性”的弊病。[15]72-73、102③这种对《霸王别姬》起承转合、陡转、发现、高潮的故事情节编排,并不能使该剧瞬间达到情感的高潮,反而会显得“瘟”。
三、传统戏曲场上表演文本结构的启示
《霸王别姬》不断删减,最终的主角由杨小楼饰演的项羽转换为梅兰芳饰演的虞姬,且全剧在剑舞中终结。这显然更符合该剧的情感高潮戏演绎逻辑,使其不至于陷入展示霸王武功神勇的情节铺排的泥沼。虽然这样的改动让梅兰芳觉得对不起杨小楼——一代剧坛英豪落得如此暗淡落寞的下场,甚至在虞姬舞剑自刎后,杨小楼的戏份都没有人再看了,但这对我们重新理解传统戏曲的场上表演文本结构有诸多启示。
一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场上搬演的简繁规则。“有话则长”的“有话”,即能习得凸显情感高潮戏的“技艺非凡”的具身“姿势意义”。“无话则短”的“无话”,即非“跑”完整故事情节、“最高行动线”的铺排过程。其实,后来杨小楼也意识到这个场上搬演的简繁规则,他说:“这出戏的打应该是工架大方,点到为止,摆摆样。”[1]663也即不是为打而打、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要凸显霸王“别”姬的情感高潮戏,因而,戏的重心在“别”姬,而“别”姬的悲剧性在于虞姬自刎前还为霸王解忧而舞剑。至于霸王如何奋力厮杀走到垓下的困境,不应是该剧的重心。杨先生能意识到这出戏应该冷热相济,而“打应该是工架大方,点到为止,摆摆样”,或许是因为他受到昆腔的影响。杨小楼、梅兰芳戏班里的管事李春林说:“杨先生当年打阵一场,跟汉将樊哙、彭越都打‘单套’,对汉八将还有个‘整套’,再上来就左手拿枪、右手拿鞭,是一根很壮的方棱鞭,藤牌兵‘翻毛’上,打四个藤牌,还接‘挡棒攒’,这段不是从昆腔《十面》来的,《十面》韩信唱一支曲子,霸王上来一场,跟两个汉将比划一下就过去了,摆摆样没什么打的。杨先生后期演这出戏,已经不打‘单套’了,下去之后再上还是照旧拿鞭,可是不打藤牌了,还保留‘挡棒攒’。”[1]663-664杨小楼显然借鉴运用了昆腔“摆摆样没什么打”的简繁处理方式,跳出了过去“武戏的旧套”。
二是非“情节整一性”的场上观演互主体性表演文本结构。据许姬传说,“我看过杨、梅合作各种不同样子的《别姬》,真是奇迹,照原本虞姬自刎以后,霸王还有精彩场面,‘开打’、‘马失前蹄’、‘乌江自刎’,杨老板表演得有声有色,非常过瘾。有一次义务戏,时过午夜,在虞姬自杀后,观众开始抽签(后台术语,少数看客中途离席,谓之抽签。多数哄散,谓之起堂。演员最怕遭遇此等情况),小楼只能敷衍了事,草草终场。梅先生心中说不出来的难过,但是群众的决定,无可奈何。此后再演,索性在虞姬自刎后,干脆就‘撩幕’;霸王的生死,成了一个谜。我有一次在后台,请问杨老先生说:‘我看了几次《别姬》,都是不同样子,最近连霸王的生死都不明了,真有点莫名其妙。’他感慨地说:‘观众不拥护我,我变成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可见演员的个人英雄主义,完全是观众造成的,并且是多数人压倒少数人。譬如我当时的看法,杨、梅是并重的,因为霸王的戏多,可能还偏重杨一点,但是一般人经过了虞姬舞剑的高潮,他们的需要满足了,就不愿再看下去”[16]281-282。这出让杨小楼尴尬无奈的戏,其实颇耐人寻味地反映出戏曲观众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虽然杨小楼对自己曾借梅兰芳之名拿戏份子很无奈,④与他合作的梅兰芳也心知肚明、非常不安,但这就是中国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观赏者”(与西方一般的“观众”不同)和“角儿”良性互动的场上表演文本结构使然,是西方戏剧家完全不明白的东方戏剧场上规则。虽然在浮躁的当下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观赏者”,但在中国古代,这种与优伶互主体性的“观赏者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加达默尔说:“观赏者的存在是由他‘在那里的同在’(Dabeisein)所规定的。”[17]161而所谓“同在就是参与(Teilhabe)。谁同在于某物,谁就完全知道该物本来是怎样的”[17]161。加达默尔把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主体行为称为“专心于某物”(Bei-der-Sache-sein)。[17]161吴小如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看戏的经历时说:“记得有一次在吉祥戏院看杨小楼的戏,当戏正演到高潮,观众一个个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望着台上时,偏有收茶钱的跑来干扰。座中有几位老年观众因之大为不满,一面尽快把茶房打发走,一面已在慨叹新来的这一批服务人员‘太不懂戏’了。”[18]207这些观众就是“专心于某物”的“观赏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完全知道该物本来是怎样的”。即这是懂行者的一种纯粹的审美欣赏,完全按照戏曲特有的场上表演文本结构规则来评价,甚至不会顾及未被叫好的人的脸面。而当代之所以再难产生这种纯粹的“观赏者”,正是因为当代正襟危坐的观众,仿佛在观看西方戏剧般被“情节整一性”的“现代戏曲”的文本结构驯化了,他们很少或完全不知道古代的场上表演文本结构“本来是怎样的”。
三是非“最高行动线”情节高潮的情感聚合审美高峰体验。戏曲艺术并不追求故事情节展开中人物性格的“最高行动线”高潮,只有更加依凭艰奥繁难技艺的剑舞、袖舞、嘎调、吊毛、僵尸、铁门槛等具身表情才能让戏曲观众瞬间获得情感聚合审美高峰体验。因而,情感聚合的审美高峰体验一过,观赏者就会离座。对此,梅兰芳记忆犹新,他说,当年上海的观众“不问戏的长短,着重的是要有精彩的地方。譬如《空城计》的诸葛亮下了城楼,《击鼓骂曹》的祢衡打完了[夜深沉]的鼓点,就有人认为精彩已过,离座而去。下面听与不听,是无足轻重的了。相反的如果是《捉放曹》不带《宿店》,《武家坡》不带《回窑》,那就不满意了。因为他们认为这里精彩的地方是在后面的”[1]141-142。演《捉放曹》必带《宿店》,并不是观众要看讲述陈宫对曹操由捉到放、由追随到放弃的心路历程的复杂故事,演《武家坡》必带《回窑》,也不是票友们要欣赏薛仁贵、柳迎春离别十八年后寒窑相见的情感诉说场面,而是因为《宿店》这一折里有一段余(叔岩)派最经典的[西皮]唱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战”,《回窑》这一折里有谭(鑫培)派令人拍案叫绝的经典唱段,这是懂行的票友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舍弃的。同样,《空城计》中马连良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唱段、《击鼓骂曹》中具身表情般的鼓点声,也是令票友们难以割舍的。
四是非封闭、开放性的戏曲场上插演文本结构。不同于“情节整一性”结构的闭合限定原则,以演员为中心的传统戏曲场上表演文本结构是自由开放的,这为观赏者在期待视野里目睹艺术大家临场插演逞才能留下了瞬间掌声间断剧情的审美时空。这种开放式的场上间断情形,在京剧舞台上时有发生。据许姬传回忆,梅兰芳剧团第一次在上海演出《抗金兵》时,到了午夜十二点半,观众已纷纷“抽签”离座。这时,金少山的“牛皋解粮”一场,闷帘导板“一路上好威风旌旗飘荡”一句唱,“如同山谷中打了一个响雷,离座的观众,立即回到原位”[19]505。这就是场上表演文本结构的非确定性、灵活性。“牛皋解粮”一场戏本来就是梅兰芳专为他非常倾慕的金先生而开放的审美时空,所以,金少山离开梅兰芳剧团后,这场戏也就删去了。这就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另一个绝妙之处:为了充分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也为了获得更高的票房收益,宁可专门为身怀绝技的艺术大家增设一场戏,哪怕这场戏对全剧而言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这是完全不能用西方戏剧的“情节整一性”结构加以解释的。所以,1935年梅兰芳访问列宁格勒时,瓦西里耶夫这样总结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特色:“重心转移到演员表演上,允许舞台上出现专门表现技艺的人物。”[5]166
其实,这种插演模式不是到近现代才出现,也不仅仅是专为艺术大家的临时串演而设,早在元杂剧中,鬼门道外的检场人或乐队就曾以“外呈答云”的方式与场上净扮角色进行插演了。[20]146-156这种调笑讽喻的插演就是为了调剂场上演出的冷热效果,甚至插演的内容与正剧可能都没有什么关系,完全不能用“情节整一性”加以解释,而是适合古代观演关系、符合戏曲民间性的结构方式。
这种开放性的临时插演文本结构,即身怀绝技的艺术大家临场加持插演,对戏曲观众而言,无疑是意外的惊喜和巨大的福利。马连良曾回忆说,有一次杨小楼和他到上海同台演出,“本来预定合演的戏有《连营寨》、《八大锤》、《摘缨会》等武生、老生合演戏,到上海之后他老人家又提出演《借东风》的赵云。这个角色是地道配角,我本不敢这样提,可是他要演,我当然欢迎,观众就更欢迎。《借东风》的大段二黄唱完之后,向来高潮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次末场赵云接孔明,箭射篷索时的念白和开船的‘云步’又博得全场掌声。这种情况在以往演《借东风》时是从来没有的”[1]639。但这种临场加演带来的意外惊喜,也可能让戏曲观众一时兴奋难抑,从而导致后面的大戏因难以为继而作罢的尴尬局面。荀慧生就曾听梅兰芳、姚玉芙二位说,有一次“他们在第一舞台听戏,大轴是刘鸿声的《斩红袍》(又名《打窦瑶》),倒第二场是杨小楼的《挑滑车》。姚先生说:‘大轴《斩红袍》本来是一出拿手好戏,可是听完《挑滑车》,就像吃饱了一样,下面再有多好的也吃不下去了。’”[1]639
无论是金少山的“牛皋解粮”,还是杨小楼箭射篷索时的念白和开船的“云步”及《挑滑车》,都是具身技艺姿势表演直接达到的情感高潮戏。而这种审美情感高潮戏,是可以脱离“情节整一性”起承转合、陡转、发现的情节高潮结构的限制而单独存在的,并能瞬间让懂行者激赏不已。这就是古典戏曲艺术极其独特的间离、间断的陌生化审美效果,它和西方戏剧的“情节整一性”是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
四、余论
1935年梅兰芳访苏献演,列·切尔尼亚夫斯基在《梅兰芳》一文中说:“梅兰芳塑造的女性形象,目的不仅仅是描述与具体情节相关的女性形象,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动作细节、表情、嗓音转调所形成的复杂体系来创造概括性的、反映传统善恶观的女性形象。因此,精心设计的身段和双手的微妙动作仿佛伴随着角色的温柔、顺从、机灵等不同的心思,所构成的画面就被赋予了重要意义。这种形象的抽象诠释迫使观众一直注视着演员高超的技艺,而不是所扮演的角色。”[5]137切尔尼亚夫斯基说,这个观点是梅兰芳表演艺术的诠释者张彭春所特别强调的。⑤他还引用了陪同梅兰芳访苏的余上沅的说法加以佐证:“梅兰芳、杨小楼和其他中国演员也是一样,他们照旧是演员,而不会变成他们扮演的人物,他们……是以自己的艺术光芒使观众着迷和激动。”[5]137这就说明,早在1935年前后,张彭春、余上沅就已经明确意识到古典戏曲艺术并非亚理斯多德“情节整一性”的戏剧,西方戏剧中的与情节相关的故事、与故事相关的人物、与人物相关的性格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最高行动线”,对戏曲艺术而言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脚色自报家门介绍的类型化的人物性格特征、副末开场和盘托出的故事梗概,优伶会进行行当程式化唱念做打的具身性“敷衍”,而这才是戏曲观众最关注的内容。这就是“这种形象的抽象诠释迫使观众一直注视着演员高超的技艺,而不是所扮演的角色”的深层原因。优伶永远不会设身处地、进入角色地逼真扮演人物,而只需要通过具身技艺这个中介,间离、间情地边表述边演符号类型化的人物。这就是优伶“不会变成他们扮演的人物,他们……是以自己的艺术光芒使观众着迷和激动”的根本原因。
① 梅兰芳纪念馆的这篇发表在3月24日《真理报》上的文章标题为《看过梅剧之后》,作者沃尔科夫被翻译为“伏尔科夫”。译文作者名、文章标题、发表的报纸名称和发表时间,都与原文作者名、标题、报纸名称、发表时间不一致,但文章内容大体一致,不知何故。
② 《梅兰芳演出剧本选》中的《霸王别姬》为九场。参见梅绍武等编《梅兰芳全集》(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至第112页。
③ 齐如山曾于光绪末年(1908年)往法国巴黎的豆腐公司(由李石曾创办,他的兄长齐竺山经营)送工人,来回不过半年。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又去过一次巴黎,并于民国元年初(1912年)回国奔丧。在前后不足两年的欧洲之行中,齐如山先后到德、法、英、奥、比等国看过戏,共看了几十部,主要是歌剧和话剧。齐如山回到北京后,与曾留日的几位春柳社友人盘桓了几日,编了话剧《女子从军》,该剧曾被梆子名角在家中排过几次,后被婉拒。齐如山又编了两出旧戏《新顶砖》和《新请医》,也想交给梆子名丑排演,又被拒。
④ 齐如山说,梅兰芳与杨小楼在崇林社合作时,梅兰芳拿戏份,杨小楼拿加钱,每一座他拿一角。一日杨小楼演《冀州城》,上座一千零几十人,小楼拿了一百元零几角。次日梅兰芳演新戏《嫦娥奔月》,上座一千八百多人,创“第一舞台”史上最高纪录,杨小楼拿了一百八十元。由此可见梅兰芳的叫座力量之大。参见齐如山《谈四角》,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至第166页。
⑤ 1935年3月22日,在莫斯科艺术大师俱乐部举行的梅兰芳与苏联艺术大师丹钦柯、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塔伊洛夫、莫斯克文、特列季亚科夫等及社会各界代表的见面会上,张彭春作了关于中国戏曲的历史、艺术特色和梅兰芳及梅剧团表演艺术特征的报告,梅兰芳也着西装示范表演。切尔尼亚夫斯基的这段话反映的就是张彭春报告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