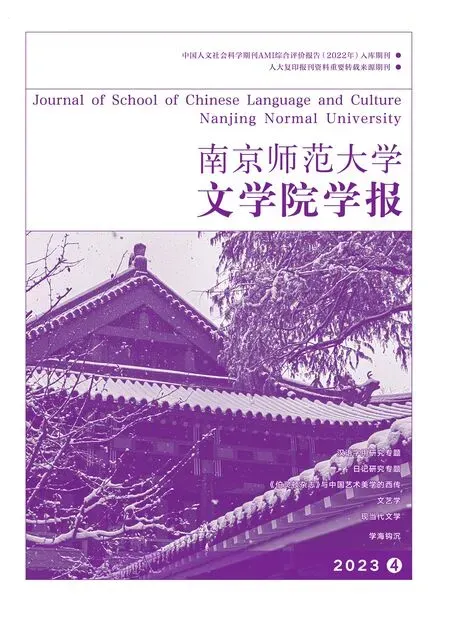近代名人日记叙录三种
张 剑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中国近代史包括文学史的研究,私人日记是很重要的史料,但以前限于各种条件,学术界对此利用不够。近些年来,这种状况得到较大改观。凤凰出版社从2014年开始,每年推出一辑“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其中仅日记即刊出近百种;2018年,笔者的“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近代日记更加引起学界和社会关注。鉴于近代日记存世数量超过千种,需要逐步和系统地清理,兹选取华学澜、丁福保、左霈三位近代名人日记,对其版本情况、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做一概要介绍,以就教方家。
一
华学澜(1860—1906),字瑞安,号莱山,天津人。光绪十一年(1885)顺天府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入北京时,正在北京。光绪二十五年(1901),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光绪二十九年(1903)会试同考官。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任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并为京官教授算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三日(1906年6月24日)因病去世。华学澜生年,其举人朱卷载为同治壬戌(1862)十月十四日,此为“官年”,比实际年龄小两岁。
华学澜有记日记的习惯。据华学澜姻亲周支山(字鸣西)称:“太史自幼而壮而老,日记必蝇头细书,逐日登记,数十年如一日。”(陶孟和《〈辛丑日记〉序》)可惜,目前所见,只有己亥、庚子、辛丑三年的部分,而且情况不一。
《己亥日记》稿本现藏天津图书馆,题名《华瑞安日记》。起于己亥三月初一日,止于庚子四月十六日,其中缺失己亥九月初四至九月二十日的内容,主要反映华氏的日常京官生活、人际交往情形。如十一月初六日:“早,为范孙作书,催取诗幅,送还文稿。到王桂生处,谈梦侯夫人度日事。晤云生,知乡夔断弦,即为点主。到性初处,留早饭,食黄花鱼,甚美,未修铁路前所未有也。饭后同性初到秋叔祖院,为写喜联、大帖、时书各件,宪叔续弦用也。同性初到亦香处,朗先、翰臣在焉,谈至暮,芰洲来即去,性初亦去,余与朗先、翰臣均留晚饭,谈至子刻归。诗幅取回,范孙已书就。阅卷。见伯鹏信,约明日到范孙处,与鞠人一见,鞠人今日到津。”先是给严修写信催讨诗词条幅,送还(县试名列前茅者)文稿;又到其同年王桂生处商量接济黄梦侯遗孀;又见到王桂生之弟云生,听说乡夔丧妻来请题灵牌,遂答应之;又到任性初处早饭;饭后同任性初到华氏叔祖处为其子写喜联和生辰八字帖等;又同任性初到乔亦香处,与高朗先、祝翰臣谈论至晚,其间韩荫桢(芰洲)来即去,任性初亦告辞,华学澜与高、祝二人同晚饭,又谈至深夜子时始归;归时见严修所书条幅已到;又阅卷;又看韩伯鹏信,约其明日到严修处见徐世昌。除阅卷公务外,还与友人书信往还、诗酒雅谈,并接济同道,襄助喜丧,一日之间甚为忙碌,观此可对其此期生活感受一二。
该日记曾收入《中国古籍珍本丛刊 天津图书馆卷》第18卷,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3年影印出版。
《庚子日记》稿本二册,红格本,原由周支山之子、清华大学化学系教师周昕保存,后由陶孟和于上世纪50年代捐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稿本第一册起庚子四月十七日,讫于八月三十日;第二册起闰八月初一日,讫十二月三十日。记录了庚子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京城见闻,包括亲友信函、外间传闻、亲身感受等,颇有史料价值。择录二则如下:
早,实甫送卫哥出城,酌升来信,索去所存银两。(知襄臣骨早为其署中客李松生(廷栋)乘夜窃得,被裹,送之其家,余见孙仙实时已经办毕,负酌升托,余心甚疚,得此少减余愆)伯茀来,观我朵颐。饭后,伯茀去,遗扇一柄,少顷,遣人取去。阅《京报》,知合肥调北洋。接家信,内有姚阶平信,知伊已由山西回津。训平信是初九所写,七弟信是初五所写。晡时,实甫归,言在峻山、弼叔、孙中堂(因被乱军抢掠,移居安徽馆)各处坐谈,故归迟,并言卫哥以车未雇妥,未行,尚留润生处,嘱有家信即为送去。遣陈庆为卫哥送家信,至暮始归。晚,仍挂红灯,并用红布写“义和团之神位”张之门首,皆坛上所传,不敢不遵也。极热,挥汗如雨。(六月十四日)
早,雨一大阵。与酌升谈。午后,弼叔来,言昨王仁安由霸州来京,(本日又回霸州)于途次遇天津逃人甚夥。并见户部街、东大街两院人,知洋人入城后闭城一日,以土匪为向导,向各富户索银,满其欲始去,否则放火烧房。王奎章、吉润泉皆被烧,延及户部街院。其院人于洋人入城时已逃,只乐农六哥一人看家,房烧乃不得不逃矣。洋人所抢皆极富户及各当铺,其次皆未扰及。东街源昌当亦未动。余家陋巷,可谓极贫,约可无虑矣。惟回回则无论贫富皆不扰,以彼教人无入义和团者也。西方居人颇有自称“回回”以求免者。见人身有红色者必杀,(白旗不能全与,须以食物易之)。津中妇女向好着红,冤死者不知几许矣。仁安并见李崧生与其戚信,云合肥相国于十九日到津,住吴楚公所,以节署已成瓦砾场也。谈至晡时去。晚饭后,伯茀来,傅梦岩来,谈及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刚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未知确否。申三所荐司更与执杂役扈三来试工,人甚朴诚。酌升仍留宿。枪声大作,由北来,时远时近,彻夜不绝。(六月二十七日)
该日记的删节本曾收入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和《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辛丑日记》有稿本四册,原藏华学澜的朋友、天津胡濬(字支孙)处,后由胡之公子交给严修次子严智怡(字慈约)保存。上世纪30年代,陶孟和从严家借阅、抄录、校点,交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而原稿今不可见。前有陶孟和长序,详细介绍作者、时代及日记内容,包括:正月初一日至二月初十日在天津的家居生活;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在京的翰林生活;五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八日,由北京出发,乘火车至保定,乘轿至江陵,乘舟至武陵,再乘轿至贵阳的行程;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在贵阳主持乡试事;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初十日,前往贵阳、主持乡试及返京的过程。郑逸梅、陈左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评《辛丑日记》:“作者以清丽文笔,写联军侵占后种种暴行、京官的醉生梦死,兼叙考场实事,为近代日记佳构。”尤其是华学澜受命贵州乡试副主考官后的乡试记录,非常详细,是研治科举史的宝贵资料。举闱墨刻墨一则可窥全豹:
本日将所取之卷按房排列,覆加删汰,粗定前后,暂取如额。自十七日即刻闱墨,每誊出一篇,先发本房删改。而各房改笔,往往敷衍了事,仍须自加修饰。(内监试赵秀升前辈六十馀矣,而文兴勃然,每于发刻之文删改一二语,思笔迥非凡手所能谈及,陈文背诵如流,是于此道三折肱者)余在病中,不能用心为文,甚为着急。筱苏窥之,谓余曰,今而后,改文之事,余独任之。于是各房改过之文皆送筱苏覆阅。筱苏一一改之,或数十字,或一二百字,且有改至半篇者,笔不停挥,每至丙夜。一人独劳,而余坐享其成,心滋愧矣。计惟有不多发刻,庶省筱苏之事。所以头场文余只发刻十篇,二场文只刻一篇而已。并劝筱苏亦不必多刻。明岁即不考制艺,此次为八股末运,不能不刻闱墨以存名目,谁其如从前之悉心揣摩哉?筱苏颇以为然。二场卷有送来者,本日阅二十卷。(八月二十四日)
《辛丑日记》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汪文学,刘泽海主编《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 第3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己亥、庚子、辛丑三年,正值清廷政局急速变化的时期,华学澜作为一位翰林院京官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所记当时北京情况,多为亲见亲闻;北京以外情况,则多依据亲友通信和传闻。书中所记的知名人物很多,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茹静、马忠文整理的《华学澜日记》(中华书局2021版),将这三年日记前后贯通,统一标准,补足缺失,重新标校,并编制了人名索引,是目前最良善之本。
二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号梅轩,又号畴隐居士、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次年中秀才,曾随华蘅芳学数学,1898年任无锡俟实学堂算学教习,因善病又习医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就读东吴大学堂读英文半年,暑假至上海,就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学习日文。后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文明书局编辑、上海自新医院院监,创办丁氏医院、医学书局、诂林精舍等。编著有《历代医学书目提要》《算学书目提要》《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佛学大辞典》《丁氏医学丛书》《文选类诂》《说文解字诂林》《古钱大辞典》等,译有《西洋医学史》等,是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收藏家。
丁福保日记,分稿本和印本两种。
稿本日记一册,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著录题名为“辛丑日记”,作者为“秦宝钟”,实误。致误之因,当由该日记系用一页南菁书院课艺名次表作封面,该表上题“辛丑日记”,下署“秦宝钟”,不知何人误题。
此日记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计六页,朱丝栏,半页六行,记事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正月一日至二月八日;第二部分计四十三页,蓝丝栏,半页八行,上单鱼尾,版心上印“东吴大学堂日记”,记事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二月九日至六月二十六日。第三部分封面墨笔题“日记”,下钤“薛福荪”朱印,正文计三十三页,蓝丝栏,半页十行,上单鱼尾,版心下印“竢实学堂”,记事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六月二十七日至当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后附书账一页。
该日记为丁福保光绪二十七年全年记录,中间不少教育、医学、出版等方面的史料。如正月十八日:“今日开学,学生皆排放床铺、书籍等物。”此系东吴大学堂开学日期明确之记载。之后至六月五日东吴大学堂放暑假,皆为丁氏在其间求学经历,其中多记课暇补辑《卫生学问答》一书,又自言:“余读书向不能熟,忆十一二岁时每日仅读五行,虽百遍亦不能背诵,故近读英文甚觉竭蹶,每日约读四十遍,早晨二十遍,午后十遍,黄昏十遍。”(三月十八日)知其非记忆超群之人。本勤奋异常却自责:“余近数年来废驰已极,自今以后当于懒字上痛下针砭。心绪作恶,因不能耐苦并无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适。”(五月三日)该年十月十六日,丁氏入东文学堂学习,期间除勤学外,又编成《东文典问答》等,犹嫌己用功不够:“余颇多戏言,不能刻苦用工,此大病也,嗣后当严定课程而束身心。”(十月十八日)知其终成一代博学通人,固有以也。
袁家刚首先辨识该日记作者为丁福保,并将之整理释注,以“丁福保《辛丑日记》释注(上)”“丁福保《辛丑日记》释注(下)”为题,分两期发表于邢建榕主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3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4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丁福保印本日记,散见于丁福保创刊的《中西医学报》中,统计如下:
1.《日记之一斑》,载《中西医学报》1911年第11期,第1-16页。系丁氏辛亥二月初六日至二十日在上海和安徽芜湖一带的医疗活动记录,兼记其诗文创作,知丁氏救死扶伤,甚为忙碌。如十九、二十两日所记:“十九日,晨起,检阅累日账目,以本月医报内之社员来稿付印。今日门诊极多,自九时起至十二时诊毕。即雇人力车到南市春在楼,孙君友蘧已先在焉。稍坐,相与下轮船,二时抵闸港,乘轿至金汇桥孙宅,患者乃孙君惺叔之夫人。自去岁三月起,患咳嗽,今则新受风寒,声哑,咳甚剧,痰不易出。余用吐根、杏仁水、燐酸古垤乙涅、安母尼亚茴香精,与以四日之药。……是晚寝甚早,次日天未明即起,乃作五言诗一首云……上午八时,乘轿赴闸港,趁小汽船,在船中背诵庾子山《哀江南赋》,阅戴南山集,抵寓,已午膳。编本月之《函授新医学讲义》,译外科丛书。得工部卫生局史医生书,极赞《急性传染病讲义》,谓有功社会之书。晚核算去年出款,共支出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元,内印刷书籍费居五千元,印医报费居七百五十元。”
2.《日记之一斑(民国二年)》,载《中西医学报》1913年第3卷第12期,第1-18页。系丁氏民国二年(1913)五月十日至十六日的医学及其他活动记录,包括记录自己的诗文作品,其中有关医政、医院、医德、医书、医者、医疗、患者及其家属之议论颇多。如十三号:“余之《医学丛书》,在罗马万国卫生赛会所得之最优等金牌一块已寄到,价值一百五十佛郎。今日门诊颇多,内有患肺结核者五人,余编《肺痨病之天然疗法》今日已印成,凡患肺病者,每人各送一册。菊生又偕学生数人来谈医,余谓今日德国各大学中,均设医生补习实验科,此科非常佳良。入是科者,既可补学识之不足,习检查及治疗之新法,又可与大学内壮年之教师相交际,满载学问上之鼓舞与精神上之振作而归,其所受之益有非吾人所及料者。”“为医师者,虽业务繁剧,亦当钻研医术,时时访学问之深造者,在家阅各科之杂志,使学问日渐进步,对于医疗之患者,务求成绩佳良。”“吾人为医士后,不问乞诊者之贵贱,均负担生命与健康之重大责任。……余夜间辗转不能成寐,甚苦,因吟放翁诗曰‘放翁不管人间事,睡味无穷似蜜甜’,久之,乃得酣睡。”十四号:“菊生询余曰:医生对于病人及其家族,以何种态度为最宜?余谓:医士对于病者,诊察宜严密,意见之发表宜慎重,命令宜明确,关于命令遵奉之条件宜峻严,然须有恭敬之风,笃实怜恤之心。”《丁氏医学丛书》荣获罗马万国卫生赛会之最优等奖凭及最优等金牌,也许正是丁氏医者仁心的公正回报。
3.《日记选录》,在《中西医学报》连载四期。具体期数为:1914年第5卷第3期,第1-16页,题“日记选录”;1914年第5卷第4期,第17-24页,题“日记选录(续)”;1914年第5卷第5期,第25-44页,题“日记选录(续)”;1915年第5卷第6期,第45-60页,题“日记选录(续)”。
此系列虽题名“日记选录”,实类丁氏忆旧录或年谱简编,中摘录日记若干。开篇即云:“余以同治甲戌,生于书院衖旧宅。二岁时,值邑中讹言纸人剪发,终夜锣鼓不绝,余日中亦敲锣打鼓以为戏。七岁时,全国始设立电线,是时读《大学》不能成诵,吾父嘱吾母任督课之责,故吾读《大学》《中庸》《论语》,恒终日楼居在母旁也,每日所读,仅三行,多则五行,非百遍不能背诵。至十三岁时,读《孟子》始毕业,《诗》《书》《礼记》等,每日仅读七行,亦以百遍为度。读书至勤苦,尚不能成诵,余天性之钝有如此者。”以后历述至民国二年其四十岁时之事。尤详于宣统元年(第13页至38页),该年丁氏被两江总督端方特派为官派考察日本医学专员,任务是“凡日本之各科医学及明治初年改革医学之阶级与日人所录用之中药,以及一切医学堂、医院之规制课程,均应一一调查”(第14页)。又受盛宣怀委托,调查东京养育院、冈山孤儿院相关规章制度。因此丁氏五月二十日乘山日丸赴日本,二十七日抵横滨。之后六月一日开始正式考察,至六月二十一日考察结束,六月二十四日“早五时抵长崎,下午四时开船向上海”(第35页),逐日详细记录日本医院、养育院、图书馆等可取法之处,颇有价值。
另外,第44-60页侧重记载购书藏书,第44页四十岁条下自云:“吾家自乾嘉以来,颇多藏书,自先祖殉粤匪之难,则列代之藏书尽失。余性嗜书,而为衣食所困,无馀力多购书籍,少时所买应用各书,大抵皆石印小字本,已不能检阅,而寻常本又不足以餍余嗜书之癖。故四十岁以前所买之书,约有三大椟,尚在连元街宅内也。余自今岁起,将所得各书,依日月之先后,次第记之,以备他日之遗忘焉。”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内容丰富,颇得力于其勤记日记之习惯。
三
左霈(1875-1937),字雨荃,正黄旗汉军,广东广州驻防旗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编修;宣统元年(1909)外放云南知州,十月到云南省府,委署楚雄府知府,旋丁母忧。宣统二年三月委两级师范学堂监督,五月兼充高等工矿学堂监督,筹办一切,十月扶柩回籍安葬;辛亥后,担任《蒙藏报》主编;民国七年(1918)年起,任清华学校教职十年。1928年底,移居香港,在圣士提反学校担任中文总教习。
左霈日记手稿,现存20册,以毛笔楷书写于红色竹纸本,每年装订一册,左氏后人2006年捐出,由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处收藏。时间起至光绪二十八(1902)年壬寅五月十一日,止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丙子十二月除夕,中间缺失1904-1909年、1934年计六年间日记。
左霈日记虽留存长达数十年,然记录简略,许多天仅列日期而无文字,总字数不足二十万字。虽然如此,其中仍有不少值得注意之处:
其一,左霈得中巍科,日记中留有相关记录,是科举史的有用资料。如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代钰弟考府试首场,题系《与人恭而有礼义》。”十七日“代钰弟考府试二场, 一《史论》,一《孝经论》,一《性理论》。”既可见晚清科场制度之弊坏,又可见左霈确善于科场考试。光绪二十九年的进士试,左霈应考前都读什么书,以及应考的整个过程等,日记中的记录皆可与相关史料相互参证。左霈日记自闰五月初六日书“拜客”二字,初七日至十一日均书“同上”;至六月三十日,仅数日有具体记事,分别为闰五月二十一日“以上俱谒朝殿各师暨拜同乡京官”,二十二日“写联扇”,六月初二日“早七点钟,进衙门,资俸自此日始”,其他均有日期而无内容,至七月初一日载:“以上或请同乡,或同乡请吃饭,除应酬外,俱代人写联扇。自得鼎甲后,各处求写者,有数百联扇之多,又不能推辞,实可厌也。”知其非无事,而皆请客吃饭,写扇应酬也,举国人皆因人情世故耗费大量光阴,确可畏也。
其二,日记是左霈个人生命史的记录,和历史大叙事的视角可以形成一定互补。如左霈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扶母柩回到广州:“午前八时扶柩,由归德门入城,复出大北门,至环翠庵停厝,俟亲友行礼后回寓”,次年即逢辛亥,广州变化如何,在左霈日记中有不少记载。
三月初十日:“早阅报,饭后拜山,四时回,晚到大宅陪客,闻署将军孚琦被刺于东较场口,因是日演飞行机器,将军看毕,回署路经是处,遂被害焉,洵可悯也。”
二十九日:“早阅书,饭后拜客,到环翠庵,晚到潘宅吃饭。正举箸,闻炮声连作,移时旗兵拉炮登城,询系革命党攻击督署,一时枪炮之声,不绝于耳。城东北隅,火光烛天,人心颇为震动。旗界守卫尚严,不许闲人来往,余至二鼓始回家中,家人亦颇慌,用语慰之,然尚不知事体若何也。又闻督署已毁,张制军被救出,住水师行台云。”
三十日:“早起闻乱党被捕约一百余人,旗街尚属安靖,往来巡兵自昨日至今,俱未休息。乱党闻尚有数十人匿伏小北门近城一带,地方已被巡勇围住,想必全歼不远矣。据说此次革党,新军兵人不少,练兵反以召乱,真可叹息。是晚枪声,彻夜不息,闻先后击毙乱党共二百余名。”
闰六月十九日:“捡拾行李,欲在月内偕内子等晋京,以便明正起复。正在归着什物,忽闻家人来说革党在双门底,枪刺李军门凖,幸未获中,渠轿夫已被枪毙,其余护勇行人,共伤亡多人云。”
左霈所述,即黄花岗起义也,虽不及《李准自编年谱》等史料详实,但亦有参考价值。之后七月他北上京师,在八旗高等学堂帮忙阅卷,听闻武昌起义,讹言纷纷,自己也居行难定。左霈还主动学习英文,甚至在民元不久即剪去自己和家人的发辫。民国元年二月十四日(阳历四月一日):“早课读,午剪去发辫,小儿亦命之剪矣。时势所趋,几有不能独异之势,故决意剪去,免受他人指摘也。”表现出他无意做遗民,顺应时世的一面。该年十月二十五日:“午后接蒙藏局知会,编辑《白话报》,即日到馆。”开始编辑《蒙文白话报》和《藏文白话报》。
民国二年(1913)正月初七日:“接伯英来函,属充蒙藏学校教务兼学监。”民国三年(1914)五月初十日:“到学校,接蒙藏院通知,充办报处总编纂,午后到报馆。”六月二十二日:“到报馆,并到蒙藏院,因报馆已饬停办矣。”七月二十六日:“到学校,接清史馆知会,充名誉协修。”
民国四年(1915)二月十六日:“到校,接蒙藏院饬,充办报处总编纂兼经理。”《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改名《蒙文报》《藏文报》复刊,左霈任总纂。不过至民国五年(1916)即因经费问题再次停办。左霈日记该年四月初十日载:“到校,闻报馆又因费绌停版。”蒙藏学校亦停办,五月初一日:“到校,闻学校因经费支绌,亦拟停办。”初七日:“到校,学堂本日停办。”不久又复办。左霈同时兼到崇德学校和笃志学校授课。该年日记八月二十一日:“早徐齐仲到谈,崇德学校约充教员,随即应充。”二十二日:“星期,到崇德学校商量功课,午后达挚甫到,说蒙藏学校有信再开办云。”九月初五日:“早访杨竹川,杨雪松,并到聚贤堂早饭。赴石虎胡同蒙藏学校一看,因该校已迁移于此。”初六日:“到崇校,晚到笃志学校教女生。”十三日:“到校,此后每日或到蒙校,或到崇校,与笃校,或三校均到,但以到校括之,以省繁赘。”
民国六年(1917)十月十六日:“到校,辞笃志讲席。”十二月二十一日:“到校,作寿诗二首,辞崇德学校教员。”
民国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阳历八月五号):“接清华学校函,充中国历史教员。”
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二十二日:“到校,辞蒙校差。”一意在清华任教。
民国十七年(1928)左霈被清华校长罗家伦解聘,该年左霈日记八月十七日:“早到西城,窦斗权到谈,又丁嘉燕到坐,知清华学校改组,本年所发聘书一律废止,作为脱离关系矣。”遂发函给朋友同科进士陈念典求助,谋得香港圣士提反学校教席。九月二十五日:“早到账务处,接陈敦甫函,知香港馆事已有成议,遂定下月初间启程南下。”
民国十八年(1929)正月初九日:“接圣士提反凌君函,聘充汉文教授。”其后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十八日一直在该校任教,该日日记载:“午由校回,离校,瞬在校七年矣。”离开圣士提反后,左霈又在香港夜师范教课。民国二十五年(1936)正月二十一日:“回候罗君,本港夜师范约充教员。”其日记记至该年除夕为止。
其实以上都不仅是左霈一己的遭遇记录,对于蒙藏报、蒙藏学校、崇德学校、笃志学校、圣士提反学校、香港夜师范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而且入民国后的诸多大事,如袁世凯任大总统、登基、出殡、丁巳复辟、溥仪出宫等,在其日记中亦多少有所留痕,可和历史大叙事的视角形成一定互补。
值得一提的是,左霈记录极少议论,较难看出其个人政治倾向和心态变化。但民国十六年(1927)其子新儿的去世,还是让他的记述有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新儿病势危笃,晚十一点半钟,初七子时去世。抚养教育,垂二十六年,使我晚年抱丧明之痛,心肝欲裂,命也,如何!”(八月初六日)正是骨肉深情,使左霈打破了自己日记的书写习惯。
梁基永有标点整理本《左霈日记》(凤凰出版社2023年版),列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十辑,梁氏有前言,对左霈日记亦较详介绍,可以参看。其中关于左霈卒年的考辨尤有价值,移录如下:
左霈的卒年,目前所有的公开记录(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网站)均为1936,实误。因为现存左霈日记已经记录到1936年的农历十二月,即已进入1937年,事实上,他活到了1937年底,笔者所查到准确的卒年记录,是1937年12月28日《华字日报》:“左雨荃在港逝世 左雨荃太史近患心弱症,经于本月九日,病逝港寓,暂厝跑马地坟场。查左氏现年六十五岁,前清癸卯科榜眼,充翰林院撰文,国史馆及武英殿协修。民国以来,历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本港圣士提反学校汉文总教员,为人和蔼可亲,博学善诱,今一旦去世,闻者惜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