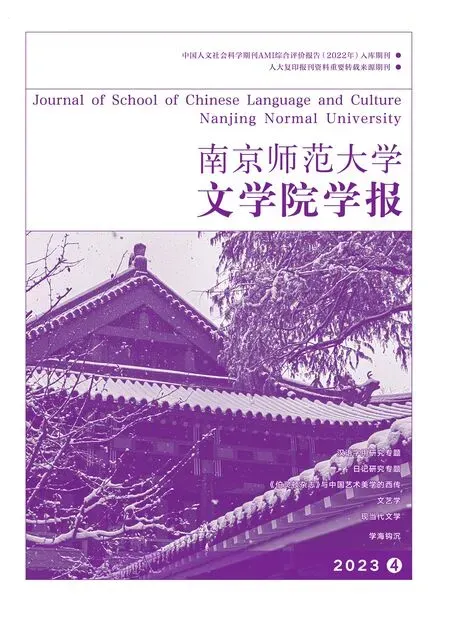梁生宝与徐改霞爱情悲剧新论
—— 重读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
曹书文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塑造时代新人形象是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使命,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的最高成就,《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立足于不同的视角对其精神性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或从政治视角给以高度评价,或从审美视角质疑其不足之处,或从人性视角探究其性格内涵的失之丰富。其实,作为经历新旧两个社会的青年农民,作为接受继父言传身教与党组织精神引导的年轻干部,梁生宝的思想性格既整体上凸显出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时代新质,又存在着传统社会的思想积淀。新与旧的纠缠、现代与传统的矛盾构成了梁生宝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梁生宝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在他与异性的相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对党忠诚、不忘初心,积极主动投身集体事业的无私奉献与其面对改霞姑娘时的被动、自卑以及旧时代大男子主义思想的遗存,二者既构成鲜明的对照又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不少学者对梁生宝与徐改霞的爱情悲剧及其成因多有论述,但尚未触及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梁生宝与徐改霞由相爱走向分手,其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既非生宝忙于合作化事业而无暇与改霞姑娘谈情说爱,又非双方父母的激烈反对和生宝的移情别恋,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两人价值观念的无形冲突。
一、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反叛与认同
《创业史》作为反映农业合作化的经典之作,其最重要的艺术魅力在于成功地塑造了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典型——梁生宝与徐改霞,而他们之间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无疑成为小说一道亮丽的风景。作为从传统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农村的青年男女,梁生宝与徐改霞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旧社会精神奴役的创伤,都有过包办婚姻的经历,都遭遇过无爱婚姻的痛苦折磨,都有挣脱父母之命婚姻束缚的欲望,都渴望自由恋爱基础上的理想婚姻。建国后第一部新婚姻法的颁布,给青年一代的自由恋爱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从此,不自由的旧式婚姻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新婚姻法的实施并不意味着传统婚姻观随之发生质的变化,在新旧转型过渡期,相当一部分人仍沿袭着旧的婚姻观念,有的是在新旧婚姻观之间动摇徘徊,还有的人则是勇敢地冲破旧观念的束缚,成为新婚姻法的受益人。
同是对美好爱情充满幻想的农村青年,改霞在面对旧式婚姻的不幸时,不是无奈的认同,而是大胆的反抗与勇敢的抗争。新的社会制度为改霞挣脱旧的婚约带来了一线生机,她以种种理由拒绝结婚,直到新婚姻法的颁布,她才解除了不自由的婚约。改霞解除旧式婚姻固然源自对包办婚姻的不满,但也与其在新的社会活动中结识了自己喜欢的生宝有关,可以说对倾心男性的向往成为其反叛旧婚约的感性动机。生宝英俊的外表、憨厚的天性使改霞的感情发生倾斜。在县城参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闲暇之余,改霞主动邀请生宝在河边散步,“改霞向他倾吐自己对包办婚姻的不满,要求他帮她出主意,怎样才能解除婚约;他建议她利用代表主任的威信,争取她妈的谅解。后来,改霞又对他的不美满的婚姻表示惋惜和同情,攻击旧社会数不尽的罪恶”(《创业史》第一部),这次愉快的接触给彼此都留下了美好印象,此后在共同从事新社会集体事业的过程中,两人逐步增进了友谊,彼此相似的情感经历、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是其滋生思想情感共鸣与萌生爱情的重要基础。
同样遭遇包办婚姻之痛的生宝在对旧式婚姻的态度上,不是如改霞一样大胆地反抗,而是委曲求全,表现出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认同。他的童养媳从小就生活在自己家里,共同的患难生活使其无法忽视对方的存在,继父言传身教的影响,使他既要固守着这个没有感情的婚约,又无法在情感上喜欢对方。生宝对童养媳的接受至多不过是理性上的承认,而并无实质性的婚姻内容。面对童养媳之死的场景,“心肠铁硬的生宝,只是怜悯地看看死者,悲怆地叹口气,他和她没有多深的关系,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觉得和那个可怜的人在一块胡来,简直是犯罪。”(《创业史》第一部)虽然他从未对自己的童养媳产生好感,甚至生活中也有不少女性对生宝含情脉脉,但他从来没有过感情出轨的任何念想。年轻俊俏的少妇素芳比较喜欢自己的邻居生宝,千方百计接近、讨好生宝,他不仅不为其所动,还严厉地训斥她,“让她老老实实与自己的丈夫过日子”,从而消除了对方的非分之想。深受包办婚姻之害有着屈辱感情经历的素芳曾向生宝哭诉自己没有获得“参加群众会和社会活动的自由,要求村干部干涉”。生宝不仅对其正当的诉求不理解,还要求其好好和拴拴过日子。“如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看,梁生宝原本应该对她给予一定的同情和谅解才对,但他没有。”(1)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78页。他无视素芳与拴拴之间没有感情的婚姻悲剧,这对一个追求感情幸福的女性是多么大的打击,他根本感受不到素芳忍受的是什么样的感情生活。作为一个乡村基层干部,年轻的生宝有权利拒绝异性的爱情,但他没有权力干预一个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权力,更不应该为了拴拴不合理的婚姻,借助组织的力量压制素芳,由此造成素芳最后不得已走进富农姚士杰怀抱的感情悲剧。
生宝之所以拒绝素芳的情感诉求,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他对乡村社会婚姻秩序的认可,在他看来,未婚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包办婚约追求自由恋爱,而已婚的女性就不再具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土改那年,生宝与改霞接触增多,改霞对生宝有意示好,生宝也喜欢改霞,但一旦意识到这样可能会触犯乡村已有的婚姻秩序,生宝便生硬地避免与改霞接近了。对非婚状态条件下异性关系的拒绝意味着生宝对传统婚姻秩序的维护。生宝偏于保守的婚恋观也表现在对自己妹妹婚约的看法上。他知道自己妹妹的婚姻是不自由的,但他从未关心过妹妹的感情生活,似乎妹妹的感情是否幸福与自己无关。由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生宝与改霞的观念差异。在对婚姻的认识上,改霞是旧婚姻制度的反叛者,自由恋爱的追求者,而梁生宝却是传统婚姻制度的遵循者。生宝尽管是一个新时代的农民,但在价值观上更多接受的是继父传统观念的影响,自由、民主、人道的现代思想并未在生宝头脑中扎根,他对包办婚姻更多的是持认同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继父梁三老汉表现出更多的相似之处。在梁三老汉看来,改霞的毁约是没有良心的表现,“他担心改霞会把他的女儿秀兰也引到邪路上去”。(《创业史》第一部)因此,梁三老汉对改霞姑娘看不惯,不愿意女儿接近改霞,甚至由此想断了女儿的学业。不管是对于素芳婚姻的不幸或是妹妹婚姻的不自由的无视,生宝都表现出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认同,成为乡村民间伦理的维护者。在这方面,改霞则更多的体现为对传统伦理与习俗偏见的反叛,“改霞恨死了村内一些庸俗的人,竟说她和周村家解除婚约是嫌女婿不漂亮”(《创业史》第一部),她对周围的舆论深恶痛绝,但不管周围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她还是抓住了法律赋予女性自由婚姻的机会,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
解除旧婚约只是改霞姑娘自由恋爱的开始,她真实的情感动机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伴侣。“她想:既然新社会给了她挑选对象的自由,总要找一个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她才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扭在一起。为了慎重,虽然女性的美妙年龄在抗婚中过去了几岁,改霞也绝不匆忙。”(《创业史》第一部)虽然她追求幸福的爱情基于自己的理性思考,但青年女性对爱情的向往也使其产生择偶的焦虑,加之同龄少女秀兰幸福婚姻的影响,她萌生了对异性的渴望,“她是觉得她那么需要和秀兰一样,想念着一个男人,而又被一个男人所想念——这个男人给她光荣的感觉,是她心上的温暖和甜蜜!”(《创业史》第一部)改霞对个人未来的人生之路感到迷茫,将自己的精神烦恼藏在自己心里,表面上尽量表现出坦然、沉静。虽然她喜欢有事业心的生宝,但碍于女性的矜持,她也只能借助生宝妹妹秀兰间接地了解生宝的动向,秀兰知道哥哥与改霞相好,尽量在改霞面前夸自己哥哥如何投入集体事业,如何参加县代表大会,如何受到领导杨书记重视。“他说,有党领导,他慌啥?你不晓得俺哥认定了一条路,八根绳也拽不转吗?”(《创业史》第一部)秀兰对哥哥发自内心的赞美与生宝献身于互助组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深深触动了改霞的心,受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改霞和当时的青年女性一样,崇拜革命英雄,把全身心投入集体事业的生宝看做自己的偶像。
生宝在婚姻观上偏于传统,而追求美好爱情的本性使其难以压抑自己爱的冲动,不过真正面对爱情问题时又流露出犹豫、矛盾与信心不足。改霞对他的好感与亲近给了他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气,而改霞母亲的顽固又成为其实现理想爱情的障碍。从自身条件看,他有时候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低,在对方面前总有一种自卑心理,觉得对方眼界高了,作为普通的庄稼人,他希望在婚姻上要务实,不能因自己婚姻问题影响革命事业。“改霞白嫩的脸盘,那双扑闪扑闪会说话的大眼睛,总使生宝恋恋难忘。她的俊秀的小手,早先给他坚硬的手掌里,留下了柔软和温热的感觉,总是一再地使他回忆起他们在土改运动中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创业史》第一部)“改霞与梁生宝的爱情并非缘起于梁生宝积极投身于合作化道路之时,而是一两年前,在土地改革运动所提供的接触机缘中,农村青年男女之间自然亲密的交往。只是现在‘生宝的心思全花给党交给他的事业上了,而对于和女人在一起的兴趣,比一俩年前淡漠多了’”(2)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76页。,所以改霞才决定自己主动。
不论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迥然不同的态度,或者是对自由婚姻追求的表现上,改霞与生宝都呈现出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这也是导致他们日后感情走向分裂的隐形原因之一。
二、乡村生活与城市文明
1960年冯牧在《文艺报》上发表有关《创业史》的评论文章,他认为在改霞“这个人身上染上了一层和农村气质不大协调的色彩,过分纤细、过分的情感多少使这个人物形象在完整和统一方面受到了一些损伤。”(3)冯牧.初读《创业史》[J].文艺报,1960(1)。与此同时,李希凡也认为“她的生活、性格没有扎根在蛤蟆滩的现实生活土壤里”(4)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N].文艺报,1960(17-18)。,改霞因游离于农村生活而遭到批评家们的一致否定,但从今天来看,这恰恰是这一形象的独特之处,在她身上表现出罕见的城市女性的精神性格与对未来工业化建设的向往,也表明作者对时代政治话语的某种偏离。
首先,乡村文明世界遵循的是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年轻女性在爱情的选择上遵循父母的意志而非个人的主观愿望,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价值取向,追求的是朴实稳重之美而非艳丽浪漫之趣。小说描写改霞的脸庞是“白嫩”的,眼睛是“扑闪扑闪会说话”,还很“俊气”“秀气”“柔软”,神态“柔媚”,说话时总“有一种打动人心的抒情调子”,“长眉毛的大眼睛一闭,作出娇嗔的样子”(《创业史》第一部),她出众的美貌在蛤蟆滩鹤立鸡群,自然诱发不少年轻异性的青睐,改霞走在路上,“吸引着妇女们赞赏的的眼光,小伙子们爱慕的眼光和姑娘们嫉妒的眼光”。(《创业史》第一部)改霞尽管俊秀美丽,但并不轻浮自傲,她认为漂亮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与她的聪明、智慧、觉悟和能力,丝毫无关。她丝毫不觉得这是自己的所长,丝毫不因人注意而自满;相反,她讨厌人们贪婪的眼光”。(《创业史》第一部)改霞不仅天生丽质,具有她人无法企及的外在娇美的形象,而且还秉有心灵与品德之美,“改霞的思想像她的红润的脸蛋一般健康,她的心地像她的天蓝色的布衫一般纯洁。她像蜜蜂采蜜一般勤地追求知识,追求进步,渴望对社会贡献自己的精神力量,争取自己的光荣”。(《创业史》第一部)可以说,徐改霞在蛤蟆滩是一个难得的让年轻男性梦寐以求的女神。
改霞外在的俊美和心灵的美质与其择偶标准是一致的,作为深受封建伦理与男权秩序压迫的乡村女性,她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与精神文化的追求都得益于时代的变革,同样,变革的时代价值观也影响置身其间的她的人生道路。有别于当时女性对家庭财产的重视,她对富裕中农的孩子不感兴趣,对接受过较高文化知识的男性没有过多的倾斜,她所看重的是体现时代主流价值倾向的农村新人,投身集体事业、一心为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是改霞心目中光荣的起码标准。”改霞认为,“既然新社会给了她挑选对象的自由,总要找一个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她才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扭在一起”。(《创业史》第一部)改霞是一个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她勇敢地反抗家长的包办婚姻,在参加土改活动中,逐渐爱上了梁生宝。生宝尽管相貌平常,但生性善良、正直勇敢、积极向上的品质吸引着改霞,生宝既有干事创业的雄心,又不自私自利,“既不露锋芒,又不自卑猥琐”,赢得了改霞的青睐。改霞不仅有柔媚的容貌,还不乏强烈的事业心,追求纯洁的爱情与热烈事业的合一,“憧憬着同生宝在一个和谐的家庭,共同创造蛤蟆滩的新生活”。生宝尽管全身心投身于农业互助组的事业,无暇顾及自己的感情生活,但偶尔闲下来的时刻,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自己与改霞相处的美好时光,他觉得,“改霞人样俊,心性也好,他要争取和她成亲”。(《创业史》第一部)可以说,在他们双方的内心世界,对方都占有着更重要的位置,都把对方看做自己择偶的最佳选择。
改霞与生宝之间纯洁美好的爱情因改霞人生选择的改变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真正促使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村干部郭振山的影响。改霞从小就崇拜自己的邻居郭振山,他不只是兄长般地关心改霞,引导她走向乡村的政治舞台,还鼓励她好好读书学文化,不要急于参加农业劳动,等将来有机会为国家贡献。当时国家的工业建设已开始,城市到处建工厂、修铁路,急需有用人才,郭振山希望改霞抓住机会考工厂,要像男子一样顶天立地,到外头闯世界,引导改霞走向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郭振山饱含深情的劝告,打乱了改霞内心的平静,她觉得进工厂是更有理想、更有前途的选择,也是党和国家的号召。本来,她情感上倾向生宝和他从事的合作化事业,但“她完全没有想到:生活向她面前突然间伸过来另一条路,而这条路更符合她的事业心,却同她的感情尖锐地矛盾”。(《创业史》第一部)自从改霞萌生了进城考工厂的想法之后,心理的平静一下子被打破,对城市工业建设的期望与对乡村美好爱情坚守二者并行不悖地交织在一起。作为农村女性,她出于对未来幸福生活的考虑,本能地向往城市生活, “尽管对于蛤蟆滩的人而言,进城参工意味着现代化事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一种新的可能,意味着对古老人生模式的一次突破,具有十足的现代性意义。”(5)徐刚.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M].中国台湾: 新锐问创,2013,第77页。“她觉得这是很值得认真考虑的前途。甚至于,这对她个人来说,也许是更有意义,更理想,更有出息的前途,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义不容辞的。”(《创业史》第一部)问题是,进城参加“国家工业化”的神圣事业与乡村青年对城市物质文明的迷恋二者交织在一起,由此才有改霞进城当工人的选择与留在乡村建设农业集体化的事业之间的矛盾,才有感情上对不起生宝之嫌疑。“经过几天的独自思量,她对进工厂比较有兴趣了。只有一样事,在她心里疙疙瘩瘩不平服,就是有种对不起生宝的感觉。”(《创业史》第一部)她的矛盾既是情与理之间的冲突,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纠葛,更是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所致。
改霞与生宝之间的爱情悲剧尽管有外在的客观条件促使,但真正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决定因素还在于改霞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最终抉择。其一,改霞一方面愿意与所爱的人搞互助合作,但对生宝全身心投入互助合作有一种不易察觉的不快。她与生宝都是有事业追求的人,但农业合作事业显然在生宝的世界里是第一位的,这里最适合生宝,但对改霞来说并非是最佳选择,只要和生宝在一起,她注定只能是第二位的,而生性争强好胜的改霞是不会忍受这种从属角色的,因此,改霞时时萌生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其中也有看不到希望遭受挫折的忧虑,“谁知道蛤蟆滩要几十年才能到社会主义呢?……我留在蛤蟆滩,几十年以后,我就是一个该抱孙子的老太婆了。我还是奔城里的社会主义吧”。(《创业史》第一部)对于改霞,搞对象既不是为了物质生存上需要,也不是生理欲求的满足,而是为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愿望,“这样一想,她觉得她离开生宝去住工厂,是正当的。她觉得她的决定是爱国的、前进的和积极的”。(《创业史》第一部)其二,在对合作化事业未来前途的认识上,年轻的改霞无法判断生宝之奋斗事业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她觉得代表主任对生宝互助组比较冷淡,她担心自己所爱的人因为没有代表主任的支持会不光彩地失败。由于对生宝领导的互助合作前途缺少应有的信心,改霞自然不愿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乡村社会,她觉得在蛤蟆滩搞互助合作不足以掀起大的人生波浪,况且还有周围习惯势力与自发势力的反对,这一切无形中增加了互助组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三,改霞与互助组始终没有做到休戚与共,而是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她不像生宝那样一心一意扎根农村,坚定不移改变农村,从事互助合作别无选择,改霞始终在乡村世界与城市建设之间徘徊,一会留恋自己的家乡建设,一会向往城市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陪衬者,改霞展现出了时代新人的另一幅面孔。因此,尽管改霞关注互助组事业,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愿望,但是她的思想与行动基本上游离于蛤蟆滩的现实之外,除了土改,她没有参加蛤蟆滩的合作化运动,她更多的心思花在找对象上。她固然关心互助组,但她关心的是互助组中的梁生宝,而不是投身其中,她始终是一个旁观者。当生宝忙于合作化的农业生产之时,改霞则是盼望着他们之间的情人约会。最后,改霞在与生宝的相处中不愿意牺牲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是要做一名独立的女性,改霞看来,“当她和他一块在田间小路上走着的时候,她将学城里那些文化高的男女干部的样子,并肩走路,而不像农村青年对象一前一后走路”。(《创业史》第一部)俊秀美丽的改霞,显然不愿满足于做一个“结婚、生孩子、伺候丈夫、围着锅台一天三顿饭”的贤妻良母,这里昭示出两种不同的爱情观的分歧,改霞是个新社会的新女性,当社会主义代替土地改革成为蛤蟆滩热议的新名词时,参加工业,进城当工人成为一种时尚,城市和工人也吸引着改霞,她考工厂为的不是显性的物质生活,而是做一个新时代的工人阶级。她最终离开生宝,是不甘心情愿当个庄稼院里好媳妇,不愿意给生宝“做饭、缝衣服和生孩子”,不想婚后沦为家庭的奴婢。对现代城市文明与现代爱情生活的追求注定了改霞和生宝爱情的悲剧不可避免。她首先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独立,不需要一个父亲的形象来时时刻刻指导她。她的内心深处萌发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从开头听惯了郭振山的改霞,今后要拿自己的脑子想事儿了,再也不能拿旁人的脑子代替自己的脑子。嘿!她已经二十一岁了。人生是严肃的”。(《创业史》第一部)尽管改霞的这种觉醒首先属于政治层面,但也昭示出女性自主意识的初步觉醒,且最后走向个人道路的自由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改霞符合马克思对新人的界定,所谓新人就是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人,从而弱化了时代赋予新人的政治强力。文本通过改霞对十七年时期的新人形象进行反思,表明梁生宝并非最理想的新人形象,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柳青与时代话语的潜在冲突,从中也可以看到改霞这一人物形象的丰富度和饱满性,以及生宝身上的依从性和从属性。
正是改霞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向往,使她具有了现代的自由人格精神,人格的强烈反差也是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
三、集体本位与人格独立
改霞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决绝反叛、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热切向往,与作为女性的人格独立是互为一体的。“在革命小说中,妇女解放和性本质几乎与阶级斗争是同义的,但改霞却表现出与这一模式很大程度的偏离。小说中,她的美貌常常得到许多男人的关注,但她的自我感觉却是如此确定,以至于男人的凝视不能将她转变为欲望对象。虽然她的角色是一个进步的革命女性”(6)刘剑梅.革命与情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227页。。但是她从未隐瞒她的欲望,当她获悉女朋友的未婚夫,是一个朝鲜战争的英雄,因战争而毁了容时,她非常失望,她想:“一个闺女家,可以拿一切行动表现自己爱国和要求进步,就是不能拿一生只有一回的闺女爱,随便许人。”(《创业史》第一部)由此可见她爱情观中的个人本位色彩,有别于时代主流话语影响下革命爱情模式,在改霞看来,自己是否喜爱是爱情的重要基础,“不论男方是什么英雄或者模范,还要自己从心里喜欢,待在一块心顺、快乐和满意”。(《创业史》第一部)她反对缺少爱情内涵的政治婚姻,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她的爱情选择与时代进步话语的冲突。改霞对生宝妹妹秀兰与志愿军英雄包办婚姻的认识显示出改霞作为一个新时代女性的自主意识。显然,改霞在择偶标准上,首先看中的不是对方家族的荣誉与对方的身份地位,而更多的是自己的情感好恶,表现出女性获得解放后婚姻上的自主与独立。
改霞个人感情选择上的个人本位完全有别于生宝超越自我之上的集体本位。在生宝的情感世界里,最让其动心的不是使人心醉神迷的浪漫爱情,也不是基于个人价值实现的发家致富,而是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互助合作事业。他与继父的矛盾、与村干部郭振山的矛盾都是源自后者家庭致富本位的自私立场,而生宝在经历了创家立业的悲剧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互助合作,为了集体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的家庭。为了在互助组内部实现稻麦两熟多打粮食,亲自徒步到郭县买稻种,为了解决互助组员的春荒问题,他带领大家进山割竹子。他每天所思所想更多的是互助组,而不是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利益满足。在与改霞的恋爱问题上,有很多误解,而造成误解的主要因素是缺少沟通,尽管改霞比较积极主动,但生宝为了互助组抽不出时间谈情说爱。他总觉得相对于互助组事业的发展,自己的感情可以暂时延迟,凡是属于与自己家庭和个人感情的事情,永远是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即他行为选择了集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由于每天忙于合作化的事情,生宝很少有时间与改霞相聚,初夏的一个夜晚,生宝和改霞终于有机会待在一起,谈论他们的事情了,“生宝在这一霎时,似乎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膊,把表示对自己倾心的闺女搂在怀里。改霞等待着,但他没有这样做。共产党员的理智,显然在生宝身上克服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创业史》第一部)显然,改造蛤蟆滩的事业与自己感情幸福之间的矛盾在生宝那里并非惊心动魄,而是轻易地解决了,原因是生宝为了合作化的事情,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哪怕是最美好的爱情。在事关互助组的重大事情时,生宝不是自己独断专行,而是服从领导的指挥,他的口头禅是 “有党在,我怕啥?”即在精神人格上,他不是遵从自己的独立意志,而是服从比他更大的政治权威,即上级领导,表现出精神人格的依附性。
改霞尽管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曾多次征求别人的意见,但对别人建议的接受并没有代替她自己的思考与行动。她从未完全依赖对方的引导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自主与独立。“这种自主意识更表现在她在梁生宝的爱情与进城当工人之间的抉择上。本来犹豫不决的改霞主动接近梁生宝,想征求他对自己离开蛤蟆滩到城里去考工厂的意见。事实上她是想用这个办法刺激拘谨的梁生宝明确的爱情表白。可没想到梁生宝一听说她要离开蛤蟆滩参加工业”,梁生宝的态度完全变了,情感距离一下拉大,开始从心理上排拒改霞,甚至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予谅解的神情”。他自己缺少文化知识,读书时间不长,在改霞面前总有那么一点点自卑,认为别人看不起他,生宝精神上的自卑无意识之中却以一种自傲的形式表现出来,既然改霞流露出看不起自己的倾向,那么,他干脆不再执着于对方,只要梁生宝认定徐改霞不再可能和自己走在一起了,那么,他就不再关注徐改霞未来的人生选择了,这无形中表现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与传统社会旧农民之间的逻辑联系,当徐改霞意识到生宝身上旧思想的流露时,“生宝在她心中的威信,一下子降低了。她发现生宝在这件事上也是自私的”。(《创业史》第一部)从表面上看,改霞借考工厂对生宝的考察与生宝听到改霞考工厂消息后的吃惊都存在心理、情感上的合理性,尽管改霞与生宝对彼此有好感,但改霞是既爱着生宝,又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实际上,她对生宝的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对考工厂的念头冲淡了,如果她是真爱生宝的话,明知道生宝的事业在蛤蟆滩,她就不会萌生进城的想法,她对城市的向往本身就表明她在事业与爱情上的矛盾,她向生宝的咨询实际上是将自己无法处理的矛盾转嫁给对方,潜意识中也是对自己背叛爱情的负罪心理的一种释放和缓解。不管生宝回答的是什么,都会对双方的感情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生宝同意支持她考工厂,那就意味着生宝对改霞情感的轻视,不能满足改霞的情感期待,如果反对对方考工厂,那就表明生宝爱情上的自私,即使是改霞出自感情的冲动放弃对城市的向往,但由此会给生宝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无形的精神负担,即他们的感情结合是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的,作为生宝,或许并不希望对方的牺牲来成全自己的婚姻。
改霞作为女性的自主意识是与其作为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相契合的,觉醒的新女性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矜持和羞涩,隐瞒自己的情感欲望与精神需求,而是勇敢地去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业与感情,而不在乎周围舆论的压力与反对,“与传统的顺从的女性形象不同,改霞从不被动地等着梁生宝来追求她。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中,她总是主动地亲昵地接触梁生宝,把她那温柔的手放在他的手中,轻轻抚弄他的袖子,故意在赶集的大马路上等他。官方所倡导的妇女解放话语培养并确保了她的女性主体性,给予她极强的自信心,使她拒绝接受仅仅是‘男性革命英雄助手’的位置。当她和梁生宝商量她打算去工厂的申请时,他漠不关心的态度激怒了她”(7)刘剑梅.革命与情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227页。;“她发现生宝也有自私的时候……只是:因为征求了他对她考工厂的意见,她就触犯了他男性的尊严了,他就用那样叫人难堪的态度对待她了。这不是自私是什么?难道这是一个男共产党员对一个女青年团员应有的态度吗?” (《创业史》第一部)实际上,在改霞考工厂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表现都是敏感的。这种敏感的背后不仅仅显示出的是双方个人本位的立场,在一定意义上也表现出他们婚姻观上的差异与矛盾之所在,生宝作为男性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与其文化水平上的自卑,他愈是心理上在改霞面前上的自卑,愈是在乎对方对他尊严的尊重。而作为改霞从政治立场上,一个党员不应该不尊重一个团员支持城市工业建设的想法,作为一个男性,不愿意让其离开农村,也有让女性充当贤妻良母角色而非共同创造新生活的理想。可以说一个是渴望男耕女织的婚姻,一个是追求男女平等的爱情,他们之间的感念差异已经在考工厂上暴露无遗。梁生宝则表现出对旧式婚姻观念的因袭。
梁生宝因钟情于互助组集体事业造成对爱情的冷漠让改霞多次失望,由对生宝的失望也相应地促使改霞终于决定离开农村去城市工作。改霞的选择不仅仅是女性对自己理想事业的追求,自己人格独立意识的呈现,更多地表现出女性自我性别意识的觉醒。接受了现代思想文化的改霞,在经历了革命与爱情冲突之后,她的人生选择既是基于自我本位的价值立场,同时又体现为女性作为独立个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在她看来,生宝尽管是新农村的典型,但按照爱情标准来要求,生宝又不是理想的对象,这不仅表现为他们两人个性上的矛盾,更体现为生宝革命本位的立场与家庭责任意识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结合将泯灭作为新女性的独立自我。生宝对集体事业的全身心投入相应的会淡化自己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责任,而这些原本应有男性承担的义务就会冠冕堂皇地转嫁到女人身上,导致对女性地位与利益的损害。在改霞看来,自己与生宝个性意识都很强,都热心社会活动,作为互助组的带头人的生宝是不可能承担家庭日常生活的责任,而她自己也不可能安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在革命与家庭之间出现冲突之时,让步的很可能是自己,生宝可能是合格的领导者,而非理想的爱情伴侣,在爱情关系中,改霞与生宝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正是由于作为年轻女性的改霞在社会解放语境中对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追求,她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超越了时代个性解放服从于政治解放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触犯了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威,从而导致小说对改霞叙事情感上出现了一定的裂痕。
在对梁徐爱情悲剧原因的解读中可以看出,梁生宝尽管贴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新人的想象,但他在婚姻观方面的保守、其人格的依附性以及旧时代的种种遗存,都表明他并不具有崭新的人格,反而是在批评中饱受指责的徐改霞才真正实现了由被新到自新的转变,其自由独立的人格显然超越了作者爱情设计的初衷,而梁徐人格的强烈反差也正是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