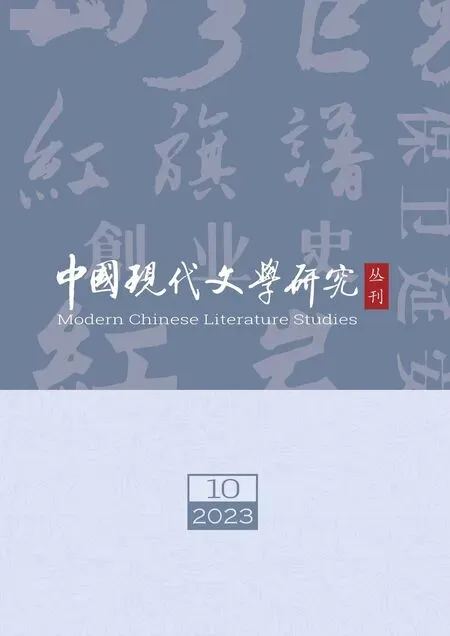鲁迅《呐喊》普实克捷克文版译介考察※
郭建玲
内容提要:普实克1937年翻译出版的《呐喊》捷克文译本,是鲁迅百余年域外传播史上第一部直接以《呐喊》命名的鲁迅小说专集,也是鲁迅特别看重的一个译本,在《呐喊》译介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普实克留日期间译介《呐喊》,是受《文学》杂志《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及鲁迅翻译观的触动,表现了二战前夕的世界形势下中捷民族文学之间的共鸣。普实克以普通读者为目标群体,对《呐喊》的篇目及顺序做了调整,在译后记中对鲁迅及其创作进行了分析。作为普实克鲁迅研究的最初成果,《呐喊》的译介在观点和方法上奠定了“布拉格汉学学派”鲁迅研究的基础。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呐喊》捷克文版的翻译,为我们了解《呐喊》的海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有助于学界更全面客观地了解普实克鲁迅研究的特点。
普实克1936年与鲁迅通信,征求翻译《呐喊》捷克文版的意见,鲁迅在病榻上回信,不仅不收稿酬,还亲自提供照片、撰写译本自序,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史上广为人知的一段美谈。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这一交往史实1如顾钧:《普实克与鲁迅》,《中华读书报》(北京)2005年10月19日;陈漱渝:《普实克和他的东方传奇》,《上海鲁迅研究》2010年第1期;张娟:《鲁迅、普实克与捷克的鲁迅图书馆》,《上海鲁迅研究》2017年第1期;葛涛:《鲁迅致普实克书信文稿回归钩沉》,《读书》2018年第10期等。,对普实克翻译《呐喊》的背景、捷克文译本的面貌、译后记的观点及影响等缺乏足够的了解。
普实克留学中国期间就得知鲁迅的大名,阅读了《呐喊》,但翻译《呐喊》是他之后到日本留学期间的决定。是怎样的契机促动普实克翻译《呐喊》?他是如何与鲁迅取得联系的?捷克文版《呐喊》是怎样的一个面貌?普实克在译后记中如何将鲁迅介绍给捷克的广大读者?与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鲁迅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呐喊》捷克文版译介史实的钩沉,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呐喊》的海外传播之旅及中捷两国之间的文学情缘。同时,《呐喊》的译介是普实克鲁迅研究的最初成果,奠定了五六十年代以他为核心的“布拉格汉学学派”鲁迅研究的基础,对捷克文译本的考察也有助于更客观全面地认识普实克鲁迅研究的内在学术理路及该学派的生成特点。
一 在日本翻译《呐喊》的背景
1932年10月,普实克获得捷克斯洛伐克东方研究所的资助,到中国做社会经济史的考察。刚到北京不久,普实克经张君劢及其夫人的引荐,拜访了胡适,希望在拜读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之后,能进一步了解新文学的发展情况。胡适给普实克开列了书单,并介绍了他认为“最优秀的作者”,“其中当然有鲁迅”。1[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 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章“世界大战后的青年运动”,第156~157,370页。普实克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品,其中《呐喊》是“最早读过的现代文学中的一部”2[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 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章“世界大战后的青年运动”,第156~157,370页。,令普实克“惊喜交集”:“我一下子就开始懂得了周围人们的面貌并理解了他们的灵魂,鲁迅为我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人内心的道路,教导了我如何去爱他们。……终于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沉思的,受着苦难的,主要是正在努力着的中国!”3[捷]普实克:《回首当年忆鲁迅》,上海《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7日。这是《解放日报》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特约稿,原稿用中文书写。但当时普实克的学术兴趣刚刚从原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转到古代话本和民间文学,还未真正转向中国现代文学。萌生译介《呐喊》的念头,是普实克到了日本之后。
1934年9月,普实克得到日本政府邀请和资助到日本进行学术考察,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官方努力争取国际舆论的结果。1932—1934年在中国学术考察期间,普实克撰写了大量的报道和社论1这些文章后来补充结集为《中国 我的姐妹》,于1940年在布拉格出版,对捷克民众了解中国以及青年学者萌发中国研究的兴趣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及时发回国内,在捷克《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使得捷克人民对中国抗日斗争产生同情”,而且“对远东的这个伟大国度产生了好奇”2[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李玲等译,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普实克的这些文章与同时期捷克记者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一道,共同奠定了1930年代捷克民众认识并接受现代中国的意识和土壤。普实克的这些文章也引起了日方的注意,当时日本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及日本国际文化关系协会遂邀请并资助普实克赴日本学术考察,以“补正”普实克在这些文章中表达的对日本的看法。3[捷]Vlasta Mádlová, Augustin Palát:Jaroslav Průšek:Source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founder of the Prague School of Sinology(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布拉格汉学派的奠基者/生命和著作的资料》),Masarykův ústav a Archiv AV ČR, v. v. i., Praha 2011, p.31。1934年9月至1937年1月,普实克在东京帝国大学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并学习日文,其间与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以及主要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汉学家盐谷温有较多接触交往,还成为了日本汉学团体Shibunkai的成员,做了有关儒家哲学及俗文学《三言》的两次专题讲座。如果不是因为来自上海的《文学》杂志的触发,普实克很可能沿着兴趣正浓的中国古代哲学和俗文学的学术方向继续开拓,而不会重新关注《呐喊》,以翻译开启日后奠定其汉学界权威地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接触到1930年代鲁迅参与主编并发表了不少文章的《文学》杂志,是触发普实克翻译《呐喊》的重要契机。在日本期间,普实克读到了《文学》杂志《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以及鲁迅的杂文《题“未定”草(一至三)》,深受感动。《弱小民族文学专号》是《文学》杂志为躲避国民党的报刊审查制度集中出版的文学专号之一,1934年5月1日出版,为总第2卷第5号,主旨是“在供读者以弱小民族文学与强国文学比较之资料,并以见出文学与民族运命关系之一斑”4《本刊辟谣》,《文学》第3卷第3号,1934年3月1日。。专号不仅登载了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庆典和波西米亚钢铁工厂的照片,以图像的方式直观呈现了捷克斯洛伐克一战胜利后摆脱奥匈帝国统治走向民族独立的建国成就及发展现状;还登载了胡愈之(署名化鲁)的理论文章《现世界的弱小民族及其概况》,其中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归为“战后新兴国及政治经济上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小国民族”,但称它“在欧洲新兴诸国中,为最倾向民主之国家。其民族文化,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文后还刊登了两篇捷克作家的作品译文以及戏剧家加拉·揆伯的介绍。鲁迅的《“题未定”草(一至三)》作于1935年6月10日,发表于同年7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1号。鲁迅就林语堂攻击其不译闻名的英美法德作品而去译介捷克、波兰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其弊在浮”,予以反击,阐明自己从《摩罗诗力说》以来介绍外国文学的一贯主张,指出凡所译介都必须同我国人民大众“易于心心相印”,对于中国革命有所帮助,而“现在又到了‘今日介绍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作为现代翻译的前驱者,鲁迅从《域外小说集》开始便特别注重外国文学作品的精神和价值,除了俄国,他翻译的几乎全属弱小民族的文学。鲁迅所说的“现在”,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爱国救亡成为主题的时代,弱小民族文学更加成为鲁迅译介的重心。
有感于鲁迅长期推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努力,1936年6月23日,普实克从东京致信《文学》杂志编辑部,表达愿为促进中国与捷克文学交流尽一份力的心情。1936年10月1日《文学》第7卷第4号“通信”栏登载了《捷克普鲁司克博士的来信》及编辑王统照的回复,使我们得以了解普实克翻译《呐喊》的背景。
在这封信中,普实克首先赞许鲁迅在《“题未定”草》中主张选择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可以武力政治力与文化相比”的观点,就读到《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刊布的捷克文学作品表达了欣喜之情,“追随着捷克文学第一次的脚步到中国的土壤上引起我最大的兴趣”。随后,普实克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新成立的文学团体“欧罗巴文学俱乐部”。该俱乐部由捷克、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文学研究者及读者组成,主旨是推介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尤其是国外的近代作品,由捷克最大的印刷家提供出版机关。作为该团体的“中日文学顾问”,普实克介绍了中国文学的译介“独付阙如”的现状,表达了“利用时机愿与中国的文学界相接触”的恳切希望。普实克向编辑部说明,他已向俱乐部推荐鲁迅的《呐喊》并获接受,但苦于对中国近代文学的隔膜,希望能得到中国文学界的协助,以校阅或翻译出版物,使中国近代文学在欧洲的译介能够落地。普实克深信,即使是“少数人的合作”对于改变当前的情形也“当有极大的助力”。
王统照执笔的《编者的复信》对普实克将中国新文学介绍到捷克的热忱表示感谢,肯定了普实克推荐翻译《呐喊》的提议,并表示愿意排除隔阂与困难以促进中国文学在捷克的传播。普实克给《文学》编辑部还随信附上了致鲁迅的英文信,希望《呐喊》的翻译能得到鲁迅同意并作序,请《文学》杂志社代为转交。不久,普实克收到了鲁迅1936年7月23日在病榻上写的回信,随信还附上了一帧个人照、《呐喊》短序、冯雪峰的《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以及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故事新编》。1《360723(捷)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8~389页。来自《文学》杂志和鲁迅的积极回复,坚定了普实克翻译《呐喊》的计划,并实质性地推动了计划的落地。
在日本的最后一段时间,普实克暂时搁置了兴趣正浓的中国中世纪通俗文学的研究,在其夫人弗拉斯塔·诺沃特娜(Vlasta Novatná)的大力帮助下,全身心地投入《呐喊》的翻译中。在普实克1937年1月返回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呐喊》捷克文译本的片段就已经在布拉格发表,并已经附上鲁迅的短序2[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李玲等译,第160页。,这不仅预告了《呐喊》的出版,而且拉近了鲁迅与捷克读者的距离。鲁迅颂扬文学是国际交流最宝贵的方式以及捷克文译本的特殊意义:“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3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页。,使对中国现代文学毫无认知的捷克读者产生良好的最初印象。普实克被热忱所鼓动,竭力向捷克民众推介鲁迅及中国新文学的热情可见一斑。
二 面向大众读者的捷克文译本
《呐喊》捷克文译本1937年12月由布拉格的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为“人民丛书”之一。这是鲁迅百余年域外传播史上第一部直接以《呐喊》命名的鲁迅小说专集11920年代,东南亚及西方国家开始关注鲁迅及其文学创作,《阿Q正传》《孔乙己》等《呐喊》中的小说被翻译成日、韩、俄、法、英、德等多种语言,或单独刊发,或被收入各类作品集,但在1937年之前,海外还没有直接以《呐喊》命名的鲁迅小说专集出版。参见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顾钧《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1926—1954》,《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1年第4卷第2期;王姗姗《鲁迅作品法译本综述》,《文学教育》2018年第10期;谢淼《鲁迅在德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等。,也是鲁迅格外看重的一个译本。
《呐喊》捷克文版封面为浅黄褐色,硬皮织面精装,32开,173页,右上角竖排黑色繁体“鲁迅”二字,字体为楷体印刷体,但笔画上有意做了调整与夸张,如“迅”字的折笔和捺笔上扬;底部一道粗重的黑线,右下角为黑色捷克文书名“Vřava”,整体设计朴素、庄重、有力。封二正中为镂空的出版社首字母LK2采用镂空大写字母的设计,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捷克文译本如茅盾系列作品的封面得到沿用,成为一种醒目的风格。,字母上横断套写出版社全称LIDOVÁ KNIHOVNA,版权页未标明发行数量。译本前面有影印的鲁迅亲笔短序手迹和与之对照的普实克的捷克文翻译,最后有注释及普实克的译后记《鲁迅及其作品》3感谢浙江外国语学院捷克语博士卢子玥对注释和译后记的翻译。。遗憾的是,鲁迅赠送普实克的个人照未被收入。
鲁迅在回复普实克的信中慷慨应允,“您可以随意翻译,我都承认,许可”4参见《360723(捷)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普实克根据需要,对《呐喊》做了三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处理。第一,捷克文版并非全译本,而是一个选译本。《呐喊》是鲁迅1918—1922年所作短篇小说的结集,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依次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加上《自序》,共计15篇。捷克文版依次收入了《阿Q正传》《孔乙己》《药》《白光》《风波》《明天》《狂人日记》《故乡》,未收入《自序》《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端午节》《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普实克在译后记中写道,所收8篇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鲁迅称之为‘年青时的家乡’的小镇及周边的乡村——未庄和鲁镇。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村镇的风光,第一次出现了生活在沉睡的荒僻角落里的村镇小人物”。可以看出,普实克敏锐地发现了《呐喊》对中国小说在农村题材上的开拓性贡献,特别关注乡村人物的形态和社会转型期旧文人的命运。考察《呐喊》选本,我们不仅要关注普实克选了哪些,还要关注没有选哪些。未入选的《一件小事》《端午节》主要是以北京为故事背景的;《头发的故事》发生地点不明确,风格上近乎杂感式的独白1王建平:《〈呐喊〉中不应被忽略的一声“呐喊”——〈头发的故事〉解读》,《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8期。;《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都写快乐的童年,具有散文化特征,“显然是一个整体”2郜元宝:《戏在台下——鲁迅〈社戏〉重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相比而言,入选的作品是更“典型”的小说,在技法层面也更复杂。在小说艺术层面上,普实克既喜爱《呐喊》中现实性比较强的作品,对于《白光》这样较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普实克也非常欣赏。《白光》描写变态心理和幻觉,是“具有多种暗示、多层含义、结构错综复杂”3[德]魏格林:《鲁迅短篇小说〈白光〉试析》,顾闻译,《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的文本,里面疯了的文人最后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个鲁迅在小说中“未解释的、不得解释”的问题,显然令普实克着迷。
第二,普实克对所收的8篇作品的顺序做了重新安排,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调到了倒数第二篇,将《阿Q正传》列为首篇。一方面,《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在西方被翻译得最早、翻译得较多的作品4参见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普实克在致鲁迅的信中提到,他尤其希望将《阿Q正传》翻译成捷克文。而且,普实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对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很感兴趣,对新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特别敏感,《阿Q正传》以“正传”的标目和章回体的史笔叙事,描绘辛亥革命前后贫苦农民阿Q的精神世界,其拟传记色彩的文体创变5辛明应:《传的解放——桐城文体与〈阿Q正传〉的生成》,《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想必令普实克印象特别深刻。相比较而言,《狂人日记》幻觉式的自白、反逻辑的叙述、奇思突起的审美话语,“传统小说的面容顿失”6孙郁:《与幼小者之真言——〈狂人日记〉的副题及其他》,《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另一方面,普实克对各篇作品顺序的“重组”,可能体现了他对《呐喊》内容上总体关联性的把握。《呐喊》对封建礼教“吃人”历史及本质的概括,振聋发聩,“吃人”不仅指有形生命的被吞噬、遭毁灭,如阿Q的被枪决,夏瑜的被杀,孔乙己的死亡,也是无形精神的被戕害、主体性的丧失,如陈士成的发疯,狂人的“候补”;而且参与“吃人”的,不仅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治阶级,受压迫的底层民众也构成了“无主名的杀人团”的一部分。1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第2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3页。如果说鲁迅以《狂人日记》开篇的“一发而不可收”,是对“吃人”主题高度象征化概括后的纷呈演绎;那么,普实克的重新编排,大致就是从对“吃人”现象的艺术呈现到本质内涵的深刻揭示,体现了从阅读者、研究者和翻译传播者的视角对《呐喊》主旨逐渐深入理解的过程。为了避免捷克读者对“吃人”的误解,普实克在译本最后的“注释”部分解释“易牙食子”的典出,并特别指出在中国“食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而将《狂人日记》与《故乡》衔接收尾,则使两篇作品因文末“救救孩子”的声音和对前路的“希望”成为一个整体,也与前面的作品构成了“吃人/救人”的某种内在张力,表露了普实克对鲁迅总体创作意图的体察与考量,正如译后记最后所分析的,“但鲁迅不是一个幻想家,也不仅仅只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他讲述奇异故事的非凡能力,是为他的‘希望’服务的。他希望知识分子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希望宏儿和水生能相互接近,希望学者与劳动人民之间根深蒂固的壁垒能够消失。这是鲁迅的希望,也是他的遗产”。
第三,普实克将《药》的篇名改为《一个革命者的坟》,这或许与普实克对《药》的主旨及艺术特征的把握有关。《药》是《呐喊》中象征主义色彩特别浓重的一篇作品,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几乎抵达了顶点”2毕飞宇:《什么是故乡?—— 读鲁迅先生的〈故乡〉》,《小说课》(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2页。。其中“药”和“坟”是小说最核心的两个意象,一明一暗,都兼具了结构情节和表达主旨的功能。“药”是与鲁迅人生早期的很多关键选择直接相关的一个个人因素,“坟”的意象则来源于鲁迅的同乡、“光复会”革命盟友秋瑾在绍兴被处决这另一个人因素。以往研究者多关注“药”的隐喻性和象征性,甚至认为它“几乎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全部中国小说的总标题”3许子东:《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香港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09页。。普实克从跨文化理解的角度加以注释,说明以人血作药、人死后可作药的说法并不局限于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迷信。相比较而言,围绕“坟”的意象的神秘感,有着新思想的革命者遭到普遍误解的痛苦和牺牲的伟大1[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伍晓明、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在普实克看来,似乎更能表达小说的意旨和艺术魅力,读来也更为动人。
无论是篇目的选择、编排还是《药》的“改名”,都可以看出普实克是有明确的翻译意图和受众定位的。《呐喊》是第一部翻译到捷克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普实克希望给捷克的普通读者提供一个便于接受和理解的版本,以引起捷克广大读者对中国及中国新文学的兴趣,而不是为了满足研究的需要。尽管普实克自谦“译文远远表达不出原作之美”,但他的翻译总体保留了各篇小说的原貌,如《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的分节,《狂人日记》前面的文言小序等,对一些读者不易理解的地方做了微调,如将《阿Q正传》第二章的“优胜纪略”和第三章的“续优胜纪略”,分别改为“阿Q被欺负”和“阿Q的胜利”。
三 译后记《鲁迅及其作品》:鲁迅研究的起点
捷克文版最后附有普实克的译后记《鲁迅及其作品》(第156~173页),这是普实克鲁迅研究的最早成果,也为普通读者了解鲁迅及其作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东京悼念鲁迅逝世的情况,转述了在上海举行的鲁迅葬礼的场面;第二部分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及其创作;第三部分分析了《呐喊》里的部分作品。
普实克并没有就东京鲁迅追悼会做实录式的报道2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根据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1月16日的通讯报道,1936年11月4日下午,日本东京举办了隆重肃穆、颇具规模的鲁迅追悼会,出席者700余人,日方以佐藤春夫为代表,中方则以郭沫若为代表,通讯披露了一些细节信息,并重点转发了郭沫若的演讲致辞。参见肖伊绯《郭沫若这样赞颂鲁迅:夏商周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北京青年报》2017年3月28日。,译后记标明东京追悼会的时间为1936年10月12日,信息也有误,推测普实克当时很可能没有出席追悼会。普实克重点引用了郭沫若的致辞:“鲁迅先生的死,就是刚才佐藤先生所说的,不但是中国的损失,东方的损失,而且是世界的损失!他的死是很值得哀痛的,尤其是死在大众被压迫的时候。但是鲁迅先生永远不死!”向捷克传递了“鲁迅属于世界”的价值,突破了将鲁迅仅仅作为中国作家的定位。在简要转述上海鲁迅葬礼的情景时,普实克则强调,“任何压迫都不会使劳动人民放弃鲁迅先生指明的前路”这一意义,凸显了鲁迅文学作品的革命性及思想价值。
译后记的第二部分是对鲁迅生平及创作经历的介绍。普实克大致按照时间线索梳理了鲁迅的一生,但并非平均用力,而是特别关注鲁迅与传统的关系、鲁迅短篇小说的开创性、鲁迅作为革命家的意义、鲁迅译介弱小民族文学以及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普实克认为,“鲁迅的文学有进步性、革命性,又与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考察鲁迅的青年阶段时,普实克特别指出了传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故乡浙江的文脉、父亲的教育以及小说的题材倾向。“浙江及周边地区自12世纪以来便是小说家、剧作家的中心。”在普实克看来,鲁迅与传统的关系还表现为从他父亲那里获得的“非同寻常”的古典文学及历史的教育,“古代文学的知识影响了鲁迅日后的创作,使他对中国文学传统价值的理解更丰富、更细腻”。在考察来自母亲方面的影响时,普实克发现,鲁迅与绝大多数现代作家不同,从未选择爱情作为小说主题,笔下人物多为男性,很少尝试刻画女性形象,“从未沉溺于中国文学惯常表现的两性关系的多愁善感”,并认为在这方面鲁迅“更接近传统作家而非现代作家”。总结这些因素,普实克认为,鲁迅的小说是“以经典传统为本质的呈现”,与其弟周作人的散文“以现代思想为完美工具,对传统文学艺术进行重塑和锤炼”异曲同工。
在简要介绍了鲁迅青少年时期的家庭变故、学习洋务、日本学医、弃医从文、回国后的沉寂生活之后,普实克重点叙述了鲁迅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及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的情况。普实克认为,鲁迅对所有事物的“独特看法”是《呐喊》“最非凡的力量,有了它,鲁迅能描绘出宏大的画面,表达出深刻的思考,这一切都使他很快在中国文学界占得一席之地”。关于鲁迅的“上海十年”,普实克评价道,尽管“革命家鲁迅的光辉掩盖了作家鲁迅的光芒”,但数量庞大的杂文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文笔犀利、特立独行的讽刺文学家”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加入“左联”后,鲁迅“开始全力投入到革命斗争中,猛力抨击当时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强烈的政府,捍卫艺术自由,以实现艺术服务民众”。普实克特别提到,尽管来自西方的各种宣传口号在当时的中国大肆宣扬,但中国国内的革命口号“仍保持了中国人文主义和社会集体主义情感的底色”,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鲁迅作为“中国青年的精神领袖”的作用。可以看出,普实克对鲁迅短篇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同等重视的,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和革命家的鲁迅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勾勒了一个热情的、顽强的、有着激烈的战斗精神的“鲁迅形象”。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普实克还特别介绍了鲁迅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语境和贡献,虽然简短,但非常有语境感和感染力,为捷克读者理解书前鲁迅的短序提供了背景性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了目的读者对鲁迅的情感认同。对于汉学家们不太关注的鲁迅的学术研究,普实克也给予了高度的认可,“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也非常有意义。鲁迅很清楚,中国的小说和戏剧中保存了最完美的民间艺术范本,一种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学,每一个想要为人民群众写作的作家都应该坚守这个传统。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第一部小说史著作,显示了鲁迅非凡的学术才能”。普实克的评价显示了他本人作为文学史家的学术兴趣1在关于《呐喊》翻译的通信后不久,普实克8月27日再次致信鲁迅,就中国旧小说的一些问题与鲁迅探讨,并得到了鲁迅“很有价值的建议”。参见《360928(捷)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鲁迅全集》第14卷,第398~399页;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 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第370页。,鲁迅关于民间文学传统及其社会功能的阐释,对普实克1950年代初的著作《解放区的中国文学及其民间传统》不无一定影响2布拉格汉学学派的某些学者近年来认为,普实克的解放区文学研究是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鼓动, 是普实克学术生涯的一个遗憾和败笔,这样的评价实际上忽略了普实克对中国文学民间传统及其发展始终关注的内在学术理路,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后社会主义”时期后设视野的偏颇。参见捷克汉学家罗然《“文章合为时而著”——普实克及其时代》,郭建玲译,《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原文为英文,发表于《欧洲汉学学会杂志》2021年第2期;马立安·高利克视《解放区的中国文学及其民间传统》为普实克“最糟糕的一个作品”,见[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李玲等译,第77、159页。。
译后记的第三部分是对《呐喊》的分析。普实克敏锐地发现,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田园诗般怡然自得的乡村,鲁迅却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南方城镇和乡村的社会环境中“揭示了一系列的悲剧”:
这些悲剧在一幅巨大而残酷的画面中汇集在一起,描绘了几个世纪以来被压垮的冷漠、麻木而徒劳的生活。……在这里,人们会因为偏离了传统偏见所设定的道路而付出生命和幸福的代价。鲁迅展示了这个看似祥和却充满了病态的人性、畸形的欲望的环境,任何外来世界的新潮流、新思想都被扭曲、化约以屈从于旧的秩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变革、政变,并没能使中国走出泥潭,使其发生任何改观。热心的革命者的鲜血被迷信的人民蘸上馒头,据说人血是治疗肺痨的良药;被罢黜的皇帝重新登基的谣言受到保守统治阶级的热烈欢迎,作为满清奴役象征的辫子迅速遍地开花,剪了辫子的人惶惶不安,害怕被斩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们心中想象的革命不过是古代农民起义的翻版,一个烧杀抢掠的机会;一个狂人恰当地描述了这是一个人们互相残食的吃人的社会。这样的短篇小说实在比一些说教的学术文章更能说明中国社会的动向。
在分析了《阿Q正传》的历史背景即辛亥革命的失败源于民众的愚昧后,普实克进一步指出,鲁迅文学思想的革命性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体会着中国社会这片凉薄静默的土地,在这种难以捉摸的无政府主义里,鲁迅做着得不到回应的抗争。他觉得,只有像在俄国掀起的革命浪潮,那种倾注了所有热忱的庞大的政治思潮,才能将中国民众唤醒,才能激发人们对于除生存需求之外的事物的兴趣”。
在艺术层面,普实克就《阿Q正传》《孔乙己》《药》《白光》《故乡》五个作品逐篇做了分析,与文学传统的内在关联始终是普实克考察鲁迅小说艺术的一个内在视角。他评价《阿Q正传》“是对8世纪受到广泛喜爱的中国文学的模仿”;《孔乙己》“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对特点鲜明人物的描写方式”;在《药》《白光》中,鲁迅则“像古代作家一样,喜欢省略、隐晦,喜欢给读者想象的空间”。普实克以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鲁迅高超的小说艺术:
《药》就是鲁迅艺术的最佳范例。只是几个场景,几段对话,两条情节线也没有被明显地讲述出来。读者只是从茶馆里面几位茶客的对话中得知要杀一位革命党示众。读者同时也会明白,人血不能医治肺痨。仅是简单描写的画面就足以完成两个悲剧的心理刻画。
以中国古代小说家为榜样,鲁迅还喜欢将小说置于现实与神秘的交界处。红白相间的花环是如何出现在坟上的?两个女人在坟前相遇又是怎样的巧合?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解释清楚,花环是革命同志放在夏瑜坟上的,但是这些在小说中都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透露出来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极大魅力。
普实克对《药》艺术层面的解读,主要是围绕“坟”而不是“药”的意象展开的,这与他将小说题目改为《一个革命者的坟》相一致。
四 情感动机与学术意义
普实克在1936年留日期间萌发译介《呐喊》的想法,捷克文译本很快完成并出版,由此鲁迅及其作品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切并非出于偶然。首先,普实克译介《呐喊》是由发自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学交流的责任感所驱动的。梁盛志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中指出,汉学家就研究对象的选择“既无国人之传统观念,亦少客观之选择标准,其汉学研究范围方向之决定,多视主观之情感”1梁盛志:《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分上下两部分连载于《再建旬刊》第1卷第8期,1940年4月11日;第1卷第9期,1940年4月21日。文章概览了海外汉学研究的缘起和现状,评价了外国汉学研究的优缺点及启示。该段引文出自连载的“下”,第24页。。中捷两国有着相似的社会境况和历史遭遇,都经历了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的近代史,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在一战后获得民族独立,但文化上仍处于被漠视或蔑视的境地。2[捷]克里玛:《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对捷克这样一个中欧小国民族文学的热情译介、高度肯定甚至向之学习的态度,使普实克看到,捷克文学之于中国不是一个“异己”的存在,而是一个“心心相印”的存在,他为中国作家能体验捷克文学中的历史、心理与情感而倍感欣慰,为中国人对捷克文学中的民族民主意识的钦佩之情而感到自豪。另外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国家贫弱的大环境下,鲁迅以其不屈的精神风貌以及反对专制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探索民族独立的创作,成为黑暗时代燃烧的火炬,使普实克找到了思想的共鸣与精神的呼应,“读了鲁迅的小说就使人体会到生活的悲剧是何等的相似,它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紧密相连而处处相通。因为生活到处皆同,生活被蹂躏,被侮辱,被践踏,在中国和欧洲是同样的痛苦”3[捷]普实克:《回首当年忆鲁迅》,上海《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7日。。正如鲁迅在《〈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中所勉励的,用文艺来沟通人类,使彼此不隔膜,相关心,这是“最平正的道路”,普实克也希望以文学翻译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
同时,在日本两年多的学术考察补充了普实克在中国的经历,使他能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具世界性的眼光来理解中国。普实克是个密切关注全球政治形势的年轻汉学家,“纳粹在德国的胜利,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和发生,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广大领土的占领,欧洲和亚洲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艰难”1[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李玲等译,第102页。,这一切在他1934—1945年间写的专题论文中都有所反映,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他1947年出版的专著《论中国的文学与文化》。2Jaroslav Průšek,O Čínském Písemnictví a Vzdělanosti, Praze: Vydavatelstvo Družstevní práce, 1947.作为一个来自弱小民族的留日学者,普实克对二战爆发前夕中捷两国各自面临的民族危难有着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体验3普实克在日期间的日本汉学界已经呈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倾向和气息。参见葛兆光《为什么“从亚洲出发思考”?》,中华好学者,2023年2月13日,https://mp.weixin.qq.com/s/x6O1z13nrDqplsM9p0yXfw。,在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及其意义有着更深刻的体认:“跨过一切混乱,中国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同等重要。这是一门充满智慧的生活学问,它教人谦虚谨慎,与世无争,注重自然之美,它的哲理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4[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 我的姐妹》“后记”,丛林、陈平陵、李梅译,第429页。可以说,在1936年的国际形势下,普实克对《呐喊》的译介与鲁迅等中国作家的翻译活动构成了弱小民族文学之间双向互动的“命运共同体”。
尽管普实克回国后并没有“趁热打铁”,继续鲁迅研究,二战期间的主要学术精力仍在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上51937年10月21日,普实克参加了东方研究所研究部举办的成员会议,会议晚上8点开始,由B. Hrozný教授主持,主要内容是由远东回国的普实克报告他的研究情况。根据《东方档案》发表的会议纪要,普实克报告了他在中国和日本的学术进展,介绍了他在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方面的收获、即将推出的论文《宋代的说书人》以及未来在这方面的研究计划,但普实克没有分享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和即将出版的《呐喊》捷克文译本。Jaroslav Průšek, On my journey in the Far East, Archiv Orientální, Vol.IX, 1937,pp.438~439。参见普实克:《我的远东之旅》,《东方档案》1937年第9卷,第438~439页。,但由《呐喊》的译介点燃的火种,使鲁迅始终成为普实克心头念念不忘的一个关切点。在为1940年出版的学术游记《中国 我的姐妹》补写的专章《小说家鲁迅及其他》中,普实克高度评价鲁迅的作品及人格魅力,称鲁迅“以其强劲有力而又简明扼要的笔锋”创作的《呐喊》,“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某些方面看,可与杜甫的诗相媲美。后者也同样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了社会的凄凉和悲惨景象。这些诗里充满了愤怒的呐喊、神秘而阴霾的心情”1[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 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第370页。普实克将鲁迅与杜甫相比,很可能是受到了鲁迅寄赠的《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即冯雪峰的文章《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的影响。。这样一种跨越小说和诗歌的文学史比较,显示了普实克对《呐喊》的思想性及抒情性艺术基调的把握。同年,普实克在柏林的《新中国》杂志上发表德语论文《中国的新文学》,认为鲁迅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并特别强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须与古代文学联系起来考察,不能一刀切为两截。2该文以《新中国的文学》收入《论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另参见顾钧《普实克与鲁迅》,《中华读书报》(北京)2005年10月19日。1940年代末,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先后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共和国以及中捷友好关系的缔结,普实克的研究重心从中国古代文学开始转向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普实克带领其弟子们投入了大量精力,较为系统地译介和研究鲁迅,形成了东欧乃至整个国外鲁迅研究领域成就突出且独具特色的“布拉格汉学学派”3参见刘燕《从普实克到高利克:布拉格汉学派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4期。。1951年,普实克与其学生(后成为其第二任妻子)贝尔塔·克列布索娃(Berta Krebsová)合译了《呐喊》和《野草》全文,以《呐喊——野草》为书名在布拉格自由出版社出版,普实克对1937年翻译的8篇小说进行了修改,并按照原著恢复了《药》的篇名及各篇小说的排列顺序。4Vřava. Polní tráva. Přel. Jaroslav Průšek a Berta Krebsová. Praha: Svoboda, 1951.1954年,该译本改名为《鲁迅选集(一)》,由捷克斯洛伐克文学、音乐与艺术出版社刊行。
普实克一直主张“翻译应该先于所有文学汉学的研究成果”5[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李玲等译,第77页。的治学路径。《呐喊》的翻译及普实克的译后记,作为布拉格汉学学派鲁迅研究的起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普实克对鲁迅与传统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注重,对鲁迅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综合考察,用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的方法对鲁迅小说叙述结构的分析,以及对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整体形象的把握,为布拉格汉学学派的鲁迅研究在观点、方法、路径上奠定了学术基础。
普实克在译后记中勾勒了一个集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体的完整的“鲁迅形象”,这成为布拉格汉学学派鲁迅研究的一个基本认识。在1960年代初对黄颂康博士学位论文的批评文章《鲁迅:革命家与艺术家》及更为著名的批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长文中,普实克进一步突出了鲁迅文学创作的“革命性”1普实克的文章《鲁迅:革命家与艺术家》[Lu Hsün: the Revolutionary and the Artist, Orientalische Literatuzeitung, 1960(55), pp.229~236]是对瑞典华裔学者黄颂康(Huang Sung-K’ang)博士的著作《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Lu Hsü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阿姆斯特丹:Djambatan,1957)的书评,被李欧梵列入《抒情与史诗》的附录“普实克现代文学研究书目”,但未被收入选集正文。普实克和夏志清的论战,参见[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李欧梵编选,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虽然其中有冷战格局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基本态度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以《呐喊》的译介为起点的研究,也影响了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形象观。普实克及其学生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作家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巴金、老舍、丁玲、周立波等,“他们和我们民族奋斗的命运、和我们从一个封建传统的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际遇相关,他们都是有担当的作家。……他们关注的才是大多数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2参见曾祥金《“我的工作实际上是随着课堂在不断地变化”——程光炜访谈录》,《创作杂谭》2022年第4期。,通过这些作家探究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成为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贯穿始终的学术关怀。
在文学史观上,普实克特别注重鲁迅与古代文学的联系,而不是将他与传统割裂开来,体现了布拉格学派强调文学内在演化过程的文学史论的影响3陈国球:《文学结构与文学演化过程——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理论》,《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与捷克斯洛伐克注重传统的民族特点也不无一定的关系4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注重传统的民族特点,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米兰·昆德拉的《帷幔》等多有论述。关于普实克的历史观点,参见《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布拉格汉学派的奠基者/生命和著作的资料》及普实克的《中国历史与文学》(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布拉格,1970年)、《抒情与史诗》的相关论述。。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传统之间的关系有着持久的好奇和学术的敏感,他在后来的代表性成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1957)、《论中国文学中传统的重要性》(1958)、《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与欧洲现代文学的相遇》(1964)、《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69)5其中《论中国文学中传统的重要性》以英文发表于《东方档案》1958年第2期,列入《抒情与史诗》附录“普实克现代文学研究书目”,但未被收入正文。参见《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李欧梵编选,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等一系列论文中有更深入全面的阐述,通过晚清甚至晚明至现代文学的转型研究,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传统资源和内生理路,提供了与20世纪50年代以费正清为主导的美国汉学界的“冲击-回应”模式非常不同的解释框架1有意思的是,普实克20世纪60年代末在哈佛大学讲学时与费正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费正清去世时将全部中国研究的英文藏书捐赠给了普实克曾多年担任所长的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设立了“费正清图书馆”。参见张娟《鲁迅、普实克与捷克的鲁迅图书馆》,《上海鲁迅研究》2017年第1期。。
在方法论上,普实克对《呐喊》的解读,尤其是对《药》的结构形式及艺术特点的分析,初步显示了他对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的运用。通过文学素材、组织原则、功能元素等来分析文学作品结构的生成及艺术特点,进而从文学结构演化洞悉社会历史变迁,成为普实克的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研究的主要理论路径和批评手段,也深刻地影响了布拉格汉学学派的年轻学者。譬如,普实克的高足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的代表性论文《鲁迅的〈药〉》继承并发展了普实克的观点和方法,曾引起海内外鲁迅研究界的广泛关注。2参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7~507页;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温儒敏《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近年来随着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等相关论述的出现,普实克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但学界多聚焦于普实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遗产”3语出陈平原《三读普实克》,初刊《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后收入《花开花落中文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尤其是他在“普夏之争”中的立场和观点,而忽略了他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的成果。对《呐喊》捷克文版的翻译及译后记的考察,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普实克的研究是一种与研究对象产生共鸣并带入情感的“有情的汉学”,我们尊重汉学家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中国的不同面向,但文学文化上的“共情”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尤其值得珍视。另一方面,在后冷战时期,尤其是在欧美汉学再次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语境下,对《呐喊》捷克文版译介的考察,帮助我们从内在的学术理路来了解普实克,使我们对塑造一个被意识形态僵化了的普实克形象保持必要的警惕。4罗雅琳:《“现代”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重返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