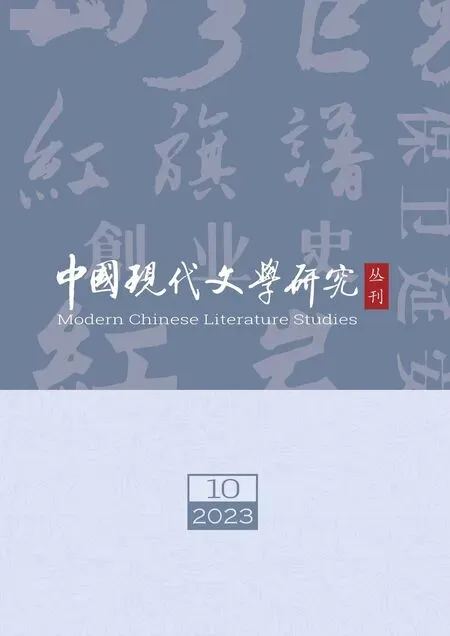近代译诗中的政治想象与革命话语建构※
——以《马赛曲》的翻译与传播为例
张 睿 孙洛丹
内容提要:《马赛曲》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过深刻影响。1871年,《马赛曲》被王韬译介入中国,初名“麦须儿诗”,此后又在30余年内被多次重新翻译。既往研究局限于对《马赛曲》翻译史的梳理,忽略了对不同译本之间关联历史脉络的挖掘。晚清民初的士大夫、革命家以及女报人以不同形式及体裁翻译《马赛曲》,其传达的精神与时代语境互动密切,成为承担警世功能、革命动员及爱国宣传的装置。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争、国族观念建构的历程中,《马赛曲》的翻译杂糅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的多重想象,是近代中国诗歌翻译的一场特殊的革命与爱国话语实践。
1792年8月,一首嘹亮激昂的战歌随马赛志愿军开进巴黎,高扬在杜伊勒里宫上空,这首将矛头直指侵略者的歌曲引起法国士兵及民众的热烈反响并广为传唱,它便是流传至今的《马赛曲》。《马赛曲》原名《莱茵军团战歌》(Chant de guerre pour l'armée du Rhin),创作于1792年4月,创作者为法国工兵鲁热·德·利尔(Claude Joseph Rouget de Lisle,1760 —1836)。由于其诞生于法国保卫革命战争之际,以马赛军传唱而闻名,因而得名《马赛曲》。1《马赛曲》最初以手稿副本和印刷品形式在阿尔萨斯地区流通,随后被巴黎书商频繁印刷,但并未规范使用原歌名,常以《马赛歌》(Chant des Marseillois)、《马赛赞歌》(Hymne des Marseillois)、《自由颂歌》(Hymne à la Liberté)等形式出现。1795年7月14日,法国国民公会确立其为国歌,法令中称其为Hymne des Marseillais。1825年,一本收录原作者鲁热·德·利尔序言的乐谱《50首法语歌曲》(Cinquante Chants Français)同样沿用该名。至1840年由Jules laisné出版社发行的《马赛曲》单行本则题为La Marseillaise,虽然上述歌名略有不同,但均以“马赛”取代原名。此外,传播初期的《马赛曲》缺乏权威版本,演奏时经常引发混乱,直至1887年法国官方重新设立曲调和声,才形成正式版本流传至今,而《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名称的使用也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规范。相关研究可参见Chailley, François, “La Marseillaise, Etude Critique Sur Ses Origin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vol. 32, no. 161, 1960, pp. 266-93; Varma, Lal Bahadur, and Lal Ba-hadur Verma. “History of La Marseillaise the French National Anthem.”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 42, 1981, pp. 583-88。作为爱国精神的象征和民族主义动员的载体,《马赛曲》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在不同国家及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中产生了深刻影响。2关于《马赛曲》创作及传播的历史,参见米歇尔·伏维尔《〈马赛曲〉:战争或和平》,载皮埃尔·诺拉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197页。18世纪以降,意大利、俄国、西班牙等国先后诞生不同语言的《马赛曲》译本。31797年,《马赛曲》被翻唱为意大利文,庆祝威尼斯解放;1875年,《马赛曲》被译为俄文版,1917年二月革命成功,被俄国共产党选为国歌;1931年,西班牙改元“第二共和”,以西语《马赛曲》欢庆新政体到来。参见吴锡德《法国制造:法国文化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4~35页。法国大革命80余年后,《马赛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产生了文言和白话多种译本。
既往的《马赛曲》研究散见于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史中,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研究者一方面关注《马赛曲》的诞生历程及历史沿革,指出其对法国大革命及法国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意义4唐伯新:《法国国歌〈马赛曲〉的历史沿革》,《当代世界》1996年第2期。;另一方面从翻译史视角出发,梳理《马赛曲》在近代至当代的多个译本,关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激励作用,例如宋逸炜指出《马赛曲》影响了近代中国制定国歌的讨论与实践5见李长林《〈马赛曲〉在中国》,《法国研究》1989年第3期;徐化夷、卞亦《〈马赛曲〉、〈国际歌〉及其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外语与翻译》2006年第3期;张峰、佘协斌《〈马赛曲〉歌词及其翻译》,《法国研究》1999年第2期;宋逸炜《〈马赛曲〉在近代中国的多重变奏》,《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经考证,王韬(1828—1897)于1871年所节译的“麦须儿诗”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法国文学译作,也是最早的《马赛曲》中译本。1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6页。此后《马赛曲》几经重译,多次出现在20世纪初中国各大报刊的刊头文末。
考察《马赛曲》在近代的翻译历程,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是,《马赛曲》自1871年被译介进入中国后,为何直至20世纪初才迎来重译的高峰?换言之,《马赛曲》在近代的再次被发掘与传播诞生于怎样的历史语境?前人研究虽注意到《马赛曲》对法国大革命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却并未深入把握《马赛曲》多个译本间的历史脉络,仅将其视作翻译个案进行简单梳理对比。实际上,《马赛曲》进入中国并非简单的文学翻译问题,更与近代中国革命话语建构密切相关。下文的讨论将梳理《马赛曲》在晚清民初的不同译本,尝试还原《马赛曲》从初译到重译的历史脉络,探析多个译本如何体现译者的不同诉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马赛曲》自欧洲到东亚的语际转换中,其翻译如何参与到近代中国的政治想象与革命论争中。
一 何以自主:救亡之诗与士大夫的矛盾立场
1867年,王韬受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邀请开启了欧洲之旅。2本次欧洲之行取道新加坡,途经斯里兰卡、也门、亚丁、开罗和马赛等地,最终抵达英国伦敦。在英期间,王韬协助理雅各翻译《诗经》《礼记》等中国经典。1870年4月,王韬回港担任《华字日报》主笔。参见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他在游记中这样回忆抵达欧陆的首站即马赛之行:“既抵法埠马赛里,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3王韬:《玻璃巨室》,《走向世界丛书 王韬卷·漫游随录》,陈尚凡、任光亮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从马赛乘“轮车”到“法京巴黎斯”,1800余里的路程“为时不过七八”。4王韬:《道经法境》,《走向世界丛书 王韬卷·漫游随录》,陈尚凡、任光亮校点,第81页。这趟“飙飞电迈”的法国之旅为王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1870年春,王韬回到中国香港,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海外漫游。不久后,他便投入近代第一部法国通史《法国志略》的编撰工作中。51870年春,王韬受托审订江苏巡抚丁日昌《地球图说》一书,广搜史料,修订增补为十四卷,初名为《法国图说》(后更名为《法国志略》),其中包括《普法战纪》三卷。1880年,王韬参考西方报刊及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等书,编撰《重订法国志略》,由于《普法战纪》于1873年单独成书,故略去。见王韬《法国图说·序》,《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189页;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凡例》,《重订法国志略》,“光绪十六年庚寅仲春淞隐庐”铅印本。同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王韬立刻将目光投向普法战场,每日“午夜一灯,迅笔瞑写”,在《华字日报》连载《普法战纪》。1《普法战纪》自1870年8月起至1871年6月连载于香港《华字日报》。参见陈桂士《普法志略·序》,《普法战纪》,“同治十二年癸酉秋中华印务总局”本。为便于叙述,下文称“中华印务总局本”;张海林《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王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7页。王韬不仅关注战争进程,更在纪中论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情等多方面,为西学知识匮乏的晚清社会注入巴黎公社、法国大革命等新知,还包括在欧洲脍炙人口的《马赛曲》。
纪中首卷,王韬记述两国开战缘由,德国首相俾斯麦以“埃姆斯密电”激怒拿破仑三世,挑起德法民族仇恨,最终引发战争。巴黎民众获悉开战在即,纷纷走上街头表达激愤之情,“是夕法京人民闻将战之,信举欣欣然有喜色,趾高气扬迥异恒态,操艺术者讴战歌以助工作,旁有和以笙笛者”2王韬:《普法战纪》第一卷,中华印务总局1873年版,第11页。。更有法国人在普鲁士驻法公使的宅邸投掷瓦砾,同时高唱“麦须儿诗”,即《马赛曲》。
法国荣光自民著,爰举义旗宏建树。母号妻啼家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
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困奸蠹。
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3该诗每小节末四句重复,为便于叙述,下文略去。
维今暴风已四播,孱王相继民悲咤。荒郊犬吠战声哀,田野苍凉城阙破。
恶物安能着眼中,募兵来往同相佐。祸流远近恶贯盈,罪参在上何从赦?
奋勇兴师一世豪,(同上)
维王泰侈弗可说,贪婪不足为残贼。揽权怙势溪壑张,如纳象躯入鼠穴。
驱使我民若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维人含灵齿发俦,讵可鞭笞日摧缺。
奋勇兴师一世豪,(同上)
我民秉政贵自主,相联肢体结心膂。脱身束缚在斯时,奋发英灵振威武。
天下久已厌乱离,诈伪相承徒自苦。自主刀锋正犀利,安得智驱而术取?
奋勇兴师一世豪,(同上)1王韬:《普法战纪》第一卷,第11页。
《马赛曲》原文共七节,节奏铿锵,格律鲜明,具有明显进行曲风格,是大革命时期歌曲的典型代表。2《马赛曲》最初为六节,第七节为1792年后人增作,学界对作者身份看法不一。参见孙景锋《〈马赛曲〉第七段歌词的真正作者》,《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王韬将其翻译为中国传统古体七言格律诗,全诗共四节,每节可大致对应原文的两小节内容。至于译介缘由,王韬自中西诗艺异同谈起,认为西方诗歌“其音韵之短长,节奏之高下虽不与中土同,而婉转悠扬以出之,激昂顿挫以谐之,则无弗同也”,并称“纪中有法国麦须儿诗、普鲁士人爱国诗类皆著自名流,传播人口,特为译录二诗,以见其凡”。3《普法战纪》中,除《马赛曲》外,王韬还翻译了德国爱国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s Arndt,1769—1860)的诗作“普鲁士人爱国诗”,直译为《何为德国人的祖国》(Was ist des Deutschen Vaterland)。1902年《新民丛报》第11期中,《军国民篇》全文收录该诗,称为《祖国歌》(为便于叙述,下文皆称《祖国歌》)。参见王韬《普法战纪》第一卷,第12页。在译诗前,王韬介绍了《马赛曲》的创作背景及原作者,其中“鲁宾棣厘士”即鲁热·德·利尔,而“麦须儿诗”即《马赛曲》(La Marseillaise)的音译。
按法国所传麦须儿诗,每歌于世乱时危之际,或多有未之知也,是诗盖作于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是时法自立为民主之国,有武士之娴于文墨者曰鲁宾棣厘士,从戎于外特作是诗,俾军中壮士歌之,以寄意焉。诗之大旨谓国敝民愁,由于暴君御下严酷,当除独夫,更新主,共睹夫升平。1王韬,《普法战纪》第一卷,第11页。
《马赛曲》原词慷慨激昂,多用感叹句及疑问句表达对君主暴政(tyrannie)、叛国者(traîtres)以及侵略者(cohortes étrangères)的控诉,将其喻为豺狼虎豹。2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é!Contre nous de la tyrannie, L’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1.1-4)起来,祖国的男儿,光荣的日子已来临!专制的血旗已举起,前来反对我们。Que veut cette horde d’esclaves, De traîtres, de rois conjurés?Pour qui ces ignobles entraves, Ces fers dès longtemps préparés? (2.1-4)这帮奴才、卖国贼和君主,为了谁,为了什么,勾结在一起?这些奇耻大辱的枷锁,这些早已准备的刑具?Quoi! ces cohortes étrangères! Feraient la loi dans nos foyers!Quoi! ces phalanges mercenaires, Terrasseraient nos fils guerriers! (3.1-4)什么!这些敌人想在我们家里发号施令!什么!这些侵略军屠杀我们的勇士们!Tous ces tigres qui, sans pitié, Déchirent le sein de leur mère!(5.7-8)这些残酷无情的老虎,撕裂母亲的心胸!据宋逸炜考证,La vérité sur la paternité de la Marseillaise: Faits et documents authentiques, Paris, 1865,该书中收录的1792年5—6月由斯特拉斯堡市政当局发行的《莱茵军团战歌》,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马赛曲》版本。笔者对照该书及法国国民议会图书馆馆藏1792年版《莱茵军团战歌》原稿,《马赛曲》歌词文本并未发生改动。本文所引《马赛曲》原文参考法国总统府官方整理的电子资料,https://www.elysee.fr/lapresidence/la-marseillaise-de-rouget-de-lisle;译文参见沈宝基译《马赛曲》,《世界文学》1989年第3期。下文除特殊注明,均使用上述原文及中译本。与法语原文的直白痛斥不同,王韬通过意译、用典等方式为译诗增添诸多细节,为读者展现了更为宏阔的革命场景。诗句“维王泰侈弗可说,贪婪不足为残贼”写出路易十六贪婪成性、“揽权怙势”,企图用普通市民的财产填补财政亏空,成为革命导火索;“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则化用“苛政猛虎”典故,将普奥联军比作伸向法国新生政权的“爪牙”;“祸流远近恶贯盈,罪参在上何从赦”一句中,“远近祸流”则指向法国内部的卖国贼与外部侵略者,二者同流合污,犯下无可饶恕的罪责,此句大意或取自原文第四小节。
战栗吧!暴君与尔等背信者
整个令人耻辱的狗党,
战栗吧!你们那卖国的阴谋
终将得到应有的报应!1Tremblez, tyrans et vous perfidies, L’opprobre de tous les partis,Tremblez! vos projets parricides, Vont enfin recevoir leurs prix!(4.1-4)
虽然“麦须儿诗”全篇意译,无法直接对照原诗,但基本涵盖了《马赛曲》传达的要义。然而,如果仅将该译本视为中法语际转换的产物进行对比研究,无疑流于语言表层。这首“麦须儿诗”经王韬精心“炮制”后,已然与法文《马赛曲》大相径庭,成了一首典型的中国古体诗,其创造性翻译正是王韬对法国大革命的再认识生成过程。诗中“我民秉政贵自主”“自主刀锋正犀利”等句里,“自主”一词的翻译应如何理解?是否意味着译者认为大革命的成功经验可以移植到晚清社会?对该词的进一步阐释成为理解士大夫的革命体认的关键。
具备西学阅历的王韬力主维新变法,曾提出“治中驭外”“强中以驭外”2见王韬《变法自强》,《弢园文录外编》第二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9页;《治中》,《弢园文录外编》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3页。,更指出重民、效法西方的两条途径。他曾多次撰文探讨西方政治制度优劣,在众多政体中,他首推英国的“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制。3王韬:《重民》(上、中、下),《弢园文录外编》第一卷,第18~19页。在《法国志略》中,王韬详尽阐述法国大革命历程并介绍立宪政体,强调必须“速订国宪”,不仅要“保王”,也要“护民”,以使其各守其职“共乐琶熙”。4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集刊》1994年第1期。而论及巴黎公社起义缘由时,王韬认为“推其致乱之由,皆因自主两字害之也”5王韬:《普法战纪》第十二卷,光绪乙未本重镌版,第19、1~2页。,国内无君主时,“诸臣当择王务之贤者而立之……而计不出此,反乘间窃兴号于众曰民主,于是莠民之妄图自立者群起矣”6王韬:《普法战纪》第十二卷,光绪乙未本重镌版,第19、1~2页。。显然,王韬诗中的“自主”为“自立为主”的民主革命手段。
由此,再次品读“岂能复睹太平年”“瞻仰我王逾日月”两句会发现,“太平年”与“我王”等词均渗透着反专制却不反王权的政治倾向。译诗前的按语中,王韬称“诗之大旨谓国敝民愁,由于暴君御下严酷,当除独夫,更新主,共睹夫升平”,其中“更新主”一词意味深长。支持君主立宪的王韬对法国大革命显然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过激的革命方式使“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欧洲数十年来的动乱皆因于此,在中国绝不可仿行。1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集刊》1994年第1期。可以说,身为浸淫在封建帝制中的士大夫,王韬翻译强调“自立”精神的“麦须儿诗”并非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反而彰显了摆荡于宪政共和与激进民主观念之间的译者的矛盾立场。
在《普法战纪》中,王韬译“麦须儿诗”后,紧随其后介绍普鲁士国内的战前情形。7月14日,普王乘车至行宫召集群臣商议军事,十万国民见到普王无不脱帽欢呼,共同唱起《祖国歌》。王韬翻译全诗并称该诗“以为张大普国之疆宇而作,盖有强兵辟土之思焉”2王韬:《普法战纪》第一卷,第12页。。在《普法战纪》中,王韬安排战前两国人民自发高唱“麦须儿诗”及“爱国诗”的戏剧性情节,无疑是将承载激烈民族情感的诗歌视为极佳的战争动员。王韬称“麦须儿诗”“每歌于乱世之际”,显然《马赛曲》的翻译与《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的撰写均在于以法为鉴,发起一场面向晚清社会的抗敌救亡动员。
伴随《普法战纪》的广泛传播,“麦须儿诗”更远渡重洋,成为日本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3《普法战纪》在日本有1878年陆军文库翻刻本和1887年山田荣造校勘本两种。参见易惠莉《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王韬——兼论1860~1870年代中日知识界的交流》,《近代中国》2002年第12期。在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的第二卷中,三位主人公谈到被压迫的悲惨经历后怅然哀戚,共同吟唱“麦须儿诗”,鼓舞士气。4柴四郎:《佳人之奇遇》第二卷,博文堂1885年版,第31页。“麦须儿诗”被“移植”到日本小说中,在文本内外的同一时空——汉文化圈内被高声吟唱,成为弱小民族的共鸣之音。十分巧合的是,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的梁启超东渡日本,创办《清议报》,并在该报翻译并连载《佳人奇遇》。5《清议报》第1期(1898年12月)上连载《佳人奇遇》,至第35期(1900年2月)未完辄止。既往研究对《佳人奇遇》译者身份存在争议,吕顺长结合书信材料,提出康有仪翻译说。参见吕顺长《日本新近发现康有仪书札选注》,《文献》2015年第5期;吕顺长「政治小説『佳人奇遇』の「梁啓超訳」説をめぐって」,『衝突と融合の東アジア文化史』,勉诚出版社2016年版。“麦须儿诗”亦随该小说一字未改从日本“漂洋过海”回到中国。6参见《佳人奇遇》,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21页。这场自西欧到东亚的诗歌文本旅行颇具传奇色彩。随后几年中,“麦须儿诗”经由梁启超的评点影响进一步扩大,在20余年的时间内迎来重译的高峰。
二 突进的革命曲:军国民教育与民族主义道路论争
1902年2月,继《清议报》后,东渡日本的梁启超于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同年蔡锷(1882—1916)在该报发表《军国民篇》1《军国民篇》分别连载于《新民丛报》第1期,1902年1月;《新民丛报》第3期,1902年2月;《新民丛报》第7期,1902年4月;《新民丛报》第11期,1902年6月。,宣扬“军国民主义”。蔡锷认为国魂是“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2蔡锷:《军国民篇》,《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4页。,并指出乐歌对于浇铸国魂、凝聚民心的作用,更以王韬译《祖国歌》为例,盛赞其“音节高古,有立马千刃之概”3蔡锷:《军国民篇》,《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4页。,彰显了德意志之国魂。同时,蔡锷将中国尚武精神匮乏的原因之一归结为缺少脍炙人口、激励人心的军歌。
此后,梁启超发表了两则诗话答蔡锷的乐歌论,更对王韬所译的“麦须儿诗”加以评点。4见《新民丛报》第21期,1902年11月;《新民丛报》第26期,1903年2月;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2~43页。梁启超对王韬本人的翻译事业并无好感:“王紫诠之翻译事业,无精神,无条理,毫无足称道者,我国学界中,亦久忘其人矣”,然而他却对王韬所翻译的《马赛曲》有着积极评价,“虽然,其所译《普法战纪》中,有德国、法国国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于两国立国精神大有关系者,王氏译笔尚能传其神韵,是不可以人废也。”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37页。梁启超所强调的“立国精神”正是对蔡锷“国魂”主张的响应。
在国内知识分子对军歌创作展开探讨的同时,赴日的中国留学生亦受到日本学校唱歌的影响。6明治维新后,日本效法西方将音乐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在中小学设置歌唱及奏乐课程,将学校歌曲作为培养“德性涵养”与“忠君爱国精神”的手段。见张前《日本学校唱歌与中国学堂乐歌的比较研究》,《音乐研究》1996年第3期。以沈心工、曾志忞等为代表的音乐教育先驱认识到音乐独特的启蒙与教化功能,回国后创作了大量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宣扬爱国民主的内容为主的乐歌,编纂学校音乐教材,掀起了晚清学堂乐歌运动。7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一科。1903年颁布的《重订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规定》中,音乐又被列为必设课程之一。1904年,沈心工编撰的近代第一部音乐教材《学校唱歌集》问世,此后的15年间,国内出版发行的音乐教材有50余种。参见张友刚《我国清末民初的音乐教育》,《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毛翰《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之歌》,《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这一时期,大量乐歌创作均以军国民教育为主题。以孙振麟编纂的《小学新唱歌》为例,其所选高等小学用诗歌“以激发伟大之志气,养成军国民之品性为目的”1孙振麟:《小学新唱歌·例言》,《增订再版小学新唱歌》,新学会社1905年版。。此外,音乐教材中还翻译了多首宣扬强兵爱国的外国乐歌,如《斯巴达军歌》《法国男儿歌》《日本少年歌》《菲律宾爱国者绝命词》等。王韬所译的《马赛曲》及《祖国歌》等作品亦被选入《小学新唱歌》《教育必用学生歌》等教材,走入了晚清广大中小学课堂。2见孙振麟编《增订再版小学新唱歌》;达文社编《教育必用学生歌》,达文社1904年版。其中,《马赛曲》的译名也由最初的“麦须儿诗”被改为“法国国歌”,其乐歌属性及民族主义立场得到了强调。
1904年,《新新小说》创刊,编辑部主要成员为侠民与陈景韩。3“侠民”为笔名,一说为“三楚侠民”,在《新新小说》上发表数量众多的译稿与小说创作,仅次于陈景韩(笔名“冷血”)。学界对侠民真实身份未有定论,参见杜慧敏《“侠民”小议》,《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4期。在《〈新新小说〉叙例》中,侠民提出创刊宗旨为“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4侠民:《新新小说叙例》,《大陆报》1904年第5期。。主张以侠义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新新小说》在晚清小说期刊中独树一帜。同年,侠民于《新新小说》音乐栏目重译《马赛曲》第一节,改题名为《法兰西革命歌》。
咄嗟其起,翳吾国青年。时其至矣,来日光天。苛政猛虎,犹自肆贪涎。残民以逞,赤帜高搴;残民以逞,赤帜高搴。恶声四起兮,尔其闻旃,王卒怒吼兮,屠人如菅。尔子为戮兮妻为奸,尔吭为扼兮,尔臂为钳。趋集尔群,体团,趋厉尔刃,甲擐。前前,速前!溅彼民贼之秽血,以粪我田!5侠民:《法兰西革命歌》,《新新小说》第2期,1904年10月。
侠民译本节取了《马赛曲》原文第一节,以传统骚体韵文为体裁,与王韬的七言译本相比,虽然没有脱离古体诗的格律限制,但通过逐句对译的方式较准确地还原了法语大意,同时兼具音韵与节奏美,用词考究、简明古雅。译诗首句“咄嗟其起,翳吾国青年。时其至矣,来日光天”,其中“翳”字的使用颇为巧妙,既有遮蔽之意,亦作副词“惟、只”,展现了苛政对人的压迫,同时也加强了对革命主体的强调。诗中多次出现的“尔”字,继承自法语原文对“祖国儿女”的直白呼告,侠民显然将“吾国青年”视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正如李长林所言,侠民重译《马赛曲》之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后,意在唤醒国人反侵略的爱国之情。1李长林:《〈马赛曲〉在中国》,《法国研究》1989年第3期。翻阅同一期《新新小说》,紧随《法兰西革命歌》其后的是各类新式小说,如政治小说《中国兴亡梦》,社会小说《新党现形记》《侠客谈》,战争小说《义勇军》等。上述文本共同建构了所谓“任侠好义,忠群爱国”的革命话语。在“前前,速前!溅彼民贼之秽血,以粪我田”的呼号中,侠民化用“民贼”一词向大众传递了一种先锋的信号——暴虐无度的独夫民贼将付出鲜血的代价。这种自下而上、朴素激昂的革命话语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和大众文化传播中颇有成效。
除了对翻译内容的探讨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从“麦须儿诗”到“革命歌”的形式转变。王译“麦须儿诗”长达336字,被选入学堂乐歌教材后亦未进行删减,亦未发现相应乐谱,仅以歌词形式呈现。而《法兰西革命歌》仅有一节,诗句简明且富于长短变化,更配有五线谱及数字歌谱。侠民认为“现吾国乐歌正在幼稚之时,不得不降格迁就,故于线谱外另填码谱”2侠民:《法兰西革命歌》,《新新小说》第2期,1904年10月。。其对晚清乐歌的评价符合国民音乐教育事业的萌芽状态,配有数字歌谱的侠译本无疑更利于乐理知识薄弱的普通读者记忆传唱。从王译本到侠译本,不仅是《马赛曲》从文本到乐歌的体裁转变,更意味着《马赛曲》自此走出了书籍报章和书斋学堂,其传播对象从阅读文言的上层知识群体及学生扩大为普罗大众,成为面向近代中国青年群体唱响的战歌,其动员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
1907年,侠民译《法兰西革命歌》又出现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刊登的《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一文中。3汪精卫:《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民报》第13期,1907年5月。该文章系汪精卫对平田东助、平塚定二郎译本的《国家论》第二卷第一章“论民族与国民”的重译,汪在文章中分段加按语评价并阐述个人观点。为便于叙述,下文简称《资料》。该诗以附录形式出现在文末并被改名为《弗兰西革命歌》,署名意译,重新句读,呈现与侠译本迥然不同的休止节奏。除此之外,该译本中还有一处细微改动值得注意。侠民译本的最后一句为“溅彼民贼之秽血,以粪我田”,而汪精卫译本则改为“溅彼民族之秽血以粪我田”。“贼”与“族”二字在构形上并不相近,若排除印刷错误的可能,又该如何解释从“民贼”到“民族”的一字之差?
咄嗟其起翳,吾国青年时其至矣,来日光天,苛政猛虎犹自肆,贪涎。残民以逞赤帜高搴,残民以逞赤帜高搴。恶声四起兮尔其闻旃。王卒怒吼兮,屠人如菅。尔子为戮兮妻为奸。尔吭为扼兮,尔臂为钳,趋集尔群团体,趋厉尔刃甲擐。前,前,速前!溅彼民族之秽血以粪我田。1汪精卫:《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民报》第13期,1907年5月。
实际上,在1905—1907年间,革命派与立宪派正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根据地展开论战。革命派质疑满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主张排满以革命手段推翻异族统治。而受伯伦知理(Johann Bluntchli)影响的梁启超等改良派高举国家主义旗帜,力主“大民族主义”,批判革命派为“小民族主义”。1903年,严复翻译英国人甄克思(Edward Jenks)的通俗政治读物《社会通诠》,很大程度上应和梁启超等对革命派反满主张的批评,受到了汪精卫及章太炎等人的批驳,并引发了双方多番论辩。21905年《民报》创刊号上,汪精卫撰文《民族的国民》回应梁启超及严复。通过引述伯伦知理的《国家学》中的“民族”(nation)和“国民”(volk)来回应严复将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联系起来从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落后”观念的做法;同时指出康梁“满汉一体”的主张也并非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唯一途径。参见干春松《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章太炎与严复围绕〈社会通诠〉的争论》,《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在持续近两年的“交锋”中,《民报》发表的文章多持“排满”主张,对清政府内政、外交及文化等方面进行抨击,尤其《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等文几乎通篇围绕“排满革命”展开。3饶怀民:《试论〈民报〉时期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基于上述探讨,重新审视《民报》译本对侠译本“一字之差”的改动,其况味越发深刻。“民贼”一词古已有之,而“民族”则是自近代以来逐步厘清的概念。梁汪论战的主要矛盾之一在于种族革命,即满汉冲突是否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障碍。汪精卫或许正是在“排满”主义的驱使下,才将“民贼”改为“民族”。译诗最后“溅彼民族之秽血以粪我田”的高呼,在“彼民族”与“我民族”之间划下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将剑拔弩张的种族革命倾向暴露无遗。
除《弗兰西革命歌》外,同期《民报》上还刊有《法国革命史论》和《人权宣言论》译文,《民报》推崇并译介法国大革命思想成果,显然与其民族主义革命主张有直接关系。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推翻王权与暴政,更意味着现代法兰西民族的统一与确立——这也是近代中国各派别革命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革命及普法战争促成了“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我们的祖国是法兰西”等起源神话的散播,世俗化的民族社会合法性和民族政治身份认同得以建构,自此法兰西建立了世界上最初的民族国家。1见曾晓阳《近现代法国学界对高卢祖先说的构建》,《安徽史学》2021年第6期。作为大革命精神的缩影,《马赛曲》显然成为宣传民族主义的极佳载体。从“麦须儿诗”到宣传尚武精神的学堂军乐歌,再到《新新小说》《民报》上的“革命歌”,《马赛曲》在晚清社会遭遇了政治先锋的文化形塑,参与到知识分子建立民族国家途径的辩论中,成为一种极具煽动性的革命装置。
三 想象的声音:爱国歌与新女国民的定义
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统治宣告终结,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就任宣言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见《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自此,狭隘种族主义被“五族共和”的平等主张取代,然而,对于一个初建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在政治上为各民族确立合法的平等身份还远远不足,对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亟须建立。在这一时期,承载蒙养与教化责任的女性群体亦被纳入了国民想象的序列中,成为重要的宣传与统合对象,多份妇女报刊“浮出历史地表”,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建构的争鸣中,女性创作和翻译的爱国诗歌也承载了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功用。
1912年4月,面向中国妇女的基督教刊物《女铎报》3《女铎报》创刊于1912年,停刊于1952年,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并未拘泥于宗教话题,刊载了诸多国内外小说及诗歌作品,深受女校学生及知识女性欢迎。该报发行过程中三次更名,初为《女铎报》;1926 年改名为《女铎》,题注“家庭月刊”;1934 年更名为《女铎月刊》至终刊。为便于论述,本文统一称作《女铎报》。创刊,出版机构广学会曾评价其“可为中华民国之纪念报,因民国成立之时,即本报创始之时”1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更表明了该刊与近代中国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创刊初年,《女铎报》便刊载了多篇爱国诗歌及文章2见李麦陔《爱国歌》,《女铎报》第2期,1912年5月;李麦陔译《苏格兰爱国歌》,《女铎报》第3期,1912年6月;谢玛利亚福建美以美会学堂来稿《中华爱国歌》,《女铎报》第4期,1912年7月;李麦陔译《马赛里爱国歌》,《女铎报》第6期,1912年9月;徐桂芳《女子爱国论》,《女铎报》第6期,1912年9月。,其创作基本遵循了如下模式,即通过对祖国地理、人文乃至历史的歌颂表达对整个民族及国家集体的热爱。如“美哉大哉中华,自古独立国家,名不虚假。声名文物之邦,尊崇三纲五常,教化士农工商,四民无杂”3见李麦陔《爱国歌》,《女铎报》第2期,1912年5月;李麦陔译《苏格兰爱国歌》,《女铎报》第3期,1912年6月;谢玛利亚福建美以美会学堂来稿《中华爱国歌》,《女铎报》第4期,1912年7月;李麦陔译《马赛里爱国歌》,《女铎报》第6期,1912年9月;徐桂芳《女子爱国论》,《女铎报》第6期,1912年9月。,“红日东升黑气消,中华五色国旗飘,国民熙皞乐逍遥,满蒙回藏曦晖同”4上海耶稣教官话合会编:《中华国歌》,《女铎报》第6期,1914年9月。,“锦绣江山亚洲东,地处温带乐意融。五千余载表雄风,代传十四通,族联满汉藏回蒙,人才物产并称隆重”5《爱国歌》,《女铎报》第11期,1916年2月。,在上述爱国歌创作中,满汉蒙回藏的五族共和主义以及五色旗等意象,成为民国精神的重要代表。
通过《女铎报》的传播,爱国诗歌以知识女性为中介走进千万中国家庭。无论满汉蒙回藏,都被赋予了一个共同的新身份,即民国国民。除诗歌创作外,《女铎报》还翻译了数首爱国诗,其中,《马赛里爱国歌》正是《马赛曲》在民国初年的首个中译本,译者为李麦陔。6据《女铎报》载,李麦陔为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第四女。在既往李提摩太研究中,对其后代的记载甚少,仅在其传记中提及其有四个女儿,均在中国长大。结合《女铎报》发刊词推测,李麦陔应为编辑部成员之一,热心传教事业并协助翻译工作。见李麦陔译《基督复生歌》,《女铎报》第1期,1912年4月。
第一节
少年英雄快起争国荣
听听万万同胞所来
各家老幼共劝从征战
观彼等苦听哀哭音
观彼等苦听哀哭音
可恶暴君残忍之酷政
用贪赃违法之官员
吓民逃散成荒芜地
平安自由皆无从发显
预备 预备 英雄奋勇持刀来战
进步 进步 众民决意拼命望得大胜
第二节
以奢华与骄傲为装饰
皇家贪心无止息
慕金银珍宝如饥如渴
虽空气几欲将钱买
虽空气几欲将钱买
视民如畜无恻隐之心
尊己如神令人崇拜
岂不知吾侪皆人也
谁能忍受诸般非法刑
预备 预备 (下同)
第三节
美哉大哉爱我强国
鼓舞引导少年精兵
监牢禁锢如何约束民
刀枪激刺非驯良法
刀枪激刺非驯良法
国民哀哭数千年之久
因受无量苛政虐治
今自由手执大盾牌
除去贪暴君王之苛政
预备 预备 (下同)1李麦陔译:《马赛里爱国歌》,《女铎报》第6期,1912年9月。
《马赛里爱国歌》共三节,与原文相比,李麦陔精简诗节,通篇意译,同时使用了大量浅近文言,如“预备”“进步”等双音节词的大量运用体现了由文言向白话转变的鲜明倾向。以副歌部分为例,原诗为:“拿起枪!公民们,编成战斗的队伍!前进!前进!让敌人的血灌溉田中的泥土!”1Aux armes, citoyens,Formez vos bataillons,Marchons, marchons!Qu'un sang impur abreuve nos sillons !(refair)李译则为:“预备,预备,英雄奋勇持刀来战,进步,进步,众民决意拼命望得大胜。”又如原诗第五节中“法兰西人,狠狠地打,或是手下留情,作为义师,对于那些被迫作战的可怜虫,免他一死”2Français, en guerriers magnanimesPortez ou retenez vos coups!Épargnez ces tristes victimesÀ regret s'armant contre nous (bis)(5.1-4)则被简译为“刀枪激刺非驯良法”。除了诗节的简化与译意的改变外,李译本还基于既往中译本进行创造性翻译:“可恶暴君残忍之酷政,用贪赃违法之官员”“以奢华与骄傲为装饰,皇家贪心无止息,慕金银珍宝如饥如渴,虽空气几欲将钱买”。上述对皇家贪婪行径的揭露或许参考了王韬译本中“维王泰侈弗可说,贪婪不足为残贼。揽权怙势溪壑张,如纳象躯入鼠穴”等句。
随着近代政治学观念的普及,李译本呈现的另一特征是大量政治学新词汇的使用:“平安自由皆无从发显”“今自由手执大盾牌”等句中,“自由”(Liberté)3Liberté, Liberté chérie,Combats avec tes défenseurs! (bis)(6.3-4)自由,亲爱的自由,你要和捍卫者敌忾同仇!一词的翻译尤为精准,此前译本均未能准确传达这一重要概念。更值得注意的是李译本对革命主体的集体性身份的强调。原诗中“祖国的儿女”(enfants de la Patrie)及“公民”(citoyens)被译为“同胞”、“众民”和“国民”。与此前译本相比,李译本开篇呼告的对象从“残民”和“青年”转为了“万万同胞”;诗歌结尾也从鼓动革命的“进兵捐躯”“以血粪田”转变为号召“众民决意拼命望得大胜”。随着译本对“国强”、“国荣”以及“国民”的反复强调,国民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呼之欲出,国民这一集体性身份认同被译诗建构起来。这种翻译的变化并非译者的一时兴起,而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语境息息相关。李麦陔曾对译诗缘由有如下阐释:
此乃最易动人之国歌,于法国革命时所作,其中含有民国之精神,故合作民国歌。何以谓马赛里歌,昔法京巴力城有一般饥饿之民,起而与法王及官长为难。虽国家发兵抵御,然此革命风潮已传遍各城各省及沿海诸地,各处民党,同时响应,此曰平等,彼曰自由,视如弟兄手臂相助。马赛里城招兵最众,而尤以女者为多。相率进攻巴力,彼等行军时途中编唱此歌,故即以其城名为歌名也。1李麦陔译:《马赛里爱国歌》,《女铎报》第6期,1912年9月。
与梁启超认为《马赛曲》中含有“立国精神”相似,李麦陔认为《马赛曲》“含有民国之精神,合作民国歌”。与《法兰西革命歌》强调“革命”类似,作为《马赛曲》在民国初年的首个译本,“爱国”这一意识形态被置于最显眼的标题之中。在《女铎报》刊载的第一首《爱国歌》中,李麦陔曾言:“罗马以金制鹰徽章激励兵士忠勇之锐气,中国昔时以龙徽章激励人之精神,今则用五色旗徽章以激励人共和爱国之心。然而最激励人心者莫如爱国歌,诚以爱国歌者对于国之感情中最有激力之一事也。”2李麦陔:《爱国歌》,《女铎报》第2期,1912年5月。可见,此时的爱国歌翻译已经成为一种激发国民对于国家情感的重要方式。
《马赛里爱国歌》《苏格兰爱国歌》《中华爱国歌》等诗歌配以歌谱被刊印在报纸上,在一声声“同胞”的呼告中,爱国歌为身处一国的各族人民提供了一种声形兼备的关于国民与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唱国歌的行动中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当爱国歌在某地被唱响的时候,想象的共同体在回声中得以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只要能够使用汉语阅读诗歌,便被纳入了想象建构的过程。《女铎报》首任主编亮乐月为南京汇文女子学堂校长,读者也多为全国各地女校学生。可以说,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女铎报》为新国民的诞生提供了独特的女性想象。
作为首个女译者翻译的《马赛曲》中译本,李麦陔着重强调了法国大革命历程中女兵的参与和贡献:“马赛里城招兵最众,而尤以女者为多。”1李麦陔译:《马赛里爱国歌》,《女铎报》第6期,1912年9月。这是此前《马赛曲》译介中均被忽略的一点,体现了女译者以及《女铎报》独特的女性视角。传统女性往往被淹没于历史叙事中,大到政治革命,小到家庭治理,女性的作用及贡献往往被忽略。作为社会隐在的重要力量,初建的民族国家如何发现女性价值?以何种方针指导女性成为新国民,女性在这一历史时期被赋予怎样的责任?这些问题亟须回应。
在民初的国民想象中,《女铎报》不仅针对女性展开宗教规训与劝导,更积极参与到针对新女国民的定义中。在该报创刊号上,亮乐月发表文章《敬告新民国女子》,称女新国民不仅能“结队联盟,戎服从事”,更应治家修身、强健身体、自食其力、讲求卫生、读书明理、摒弃迷信,实现“全国女界出昏浊而入清洁,化鲁钝而变聪明,去残废而得安全,远妖魔而崇真主。俾人人家庭跻于完善程度,以成一文明之大国,如天堂一般”。2亮乐月:《敬告新民国女子》,《女铎报》第1期,1912年4月。同年9月发表的《女子爱国论》中则提出三条女性爱国路径,分别为“兴教育”“明政治”“正风俗”3徐桂芳:《女子爱国论》,《女铎报》第6期,1912年9月。,强调女性的母职教养作用,家政优于国政。
总体而言,针对新女国民的定义,《女铎报》给出了一种以家庭为核心,以母教为义务,以爱国为责任的回应。《女铎报》将新女国民的职责限定在家庭内部,强调女性的母职责任,要求提升女性的学识和治家能力以辅佐男性,从而实现新女国民的价值。这种对新女国民的定义一方面源于基督教家庭观、女性观,另一方面则与近代民族危机下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政治需求相适应。随着《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确立,女性价值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更承担了为国家培养合格新国民、接续国力的母教职责。
自晚清传入东亚社会以来,《马赛曲》便一直被视为救亡图存、呼吁民族团结的警示与动员之诗,成为民族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的一枚精神“图腾”。《马赛里爱国歌》不仅是《马赛曲》在民初的首个译本,更是首个由女译者翻译的译本,不仅昭示着近代女学的蓬勃发展,更揭示出女学与家国同构的救亡话语体系之间的深刻因缘与深厚羁绊。《女铎报》等刊载的大量爱国诗歌将爱国主义根植于女学的沃土,批量制造出符合时代期许的女性叙事话语,这种女新国民的话语生产机制受限于历史语境,将女性主体性隐匿于国家之母的身份之下。
虽然文学史上对李麦陔等女译者的介绍仅寥寥数笔,但正如其对法国大革命中女性力量的强调一般,《马赛里爱国歌》的翻译在女性国民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提供了一种革命的视野与有别于一般“贤妻良母”的豪迈的女性爱国主义范式——女性不仅能够持家育儿,更能走出闺阁、走进学堂、走入工厂、走上战场,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纵观近半个世纪的《马赛曲》翻译史,其译者身份、立场乃至性别各异,但贯穿翻译过程始终不变的是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政治格局变迁与革命道路选择的争鸣,《马赛曲》译本的更迭亦是晚近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变迁的写照。
结 语
19世纪以降,对于民族、国家、国民的想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重要议题。爬梳《马赛曲》在晚清民初的数个译本,不仅体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变化、从诗到歌的体裁转变,更清晰地体现了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与政治诉求。以《马赛曲》的翻译与传播为线索进行翻译史的考察,会发现这条脉络几乎贯穿了晚清民初的多个重要历史节点——帝制的瓦解、革命道路的探索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均涵盖其中。在立场各异的译者的创造性翻译与操控下,《马赛曲》的多个译本参与到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建构过程中,成为一种象征意味浓厚的装置。
近代新文学发轫于新诗,新诗则发轫于译诗。译诗不仅是沟通中西的文化活动,更是革命的一种方式,与政治和历史语境密切相连:由谁译诗?译何诗?译给何人?这样的问题与近代国人对民族、国家和国民的现代想象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在革命话语的脉络中考察诗歌翻译,能更清晰地展现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以知识分子、政治家为代表的译者是如何通过诗歌翻译活动为革命和爱国主义动员指明前进方向的。《马赛曲》在近代的翻译与传播正是这种渐进的革命话语与流动的政治想象的生动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