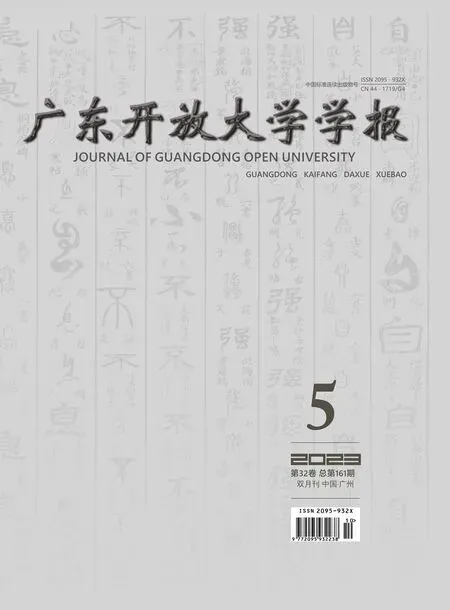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叙事变异艺术研究
朱立华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300134)
一、拉斐尔前派诗歌研究现状
在文化全球化研究成为显学的新时代背景下,在西方兴起“维多利亚文化热”的前景下,重读经典作品,发掘现代意义,反思当下问题,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198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了“维多利亚文化热”现象后,拉斐尔前派诗歌重新进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阈。国外学者对其诗歌进行多维视角研究。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在希瑟·威彻(Heather Witcher)与艾米·胡赛比(Amy Huseby)主编的《拉斐尔前派诗学》一书中,研究了其诗学的雌雄同体与雌雄间性心理。艾玛·梅森(Emma Mason)在《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生态学、信仰》一书中,研究了其诗歌的文化生态思想、环保意识,开辟了神学思想与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路径[1]。安东尼·哈里森(Anthony Harrison)在《语境中的克里斯蒂娜》中,拓展了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语境互文性”与“历史互文性”研究路径[2]。此外,布里安娜·白克罗夫特(Brianna Bancroft)、耶茨和特罗布里奇(Yeates and Trowbridge)在《维多利亚诗歌中的女性声音》《性别和权力的救援和创世神话》《“保卫桂内维尔”的性别角色转换》,以及《拉斐尔前派男性化:男性化在艺术与文学的建构》等著作中,对其诗歌进行了“男性化”与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安吉拉·雷顿(Angela Leighton)著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诗人:锥心之作》(1992),编著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诗人:艾米莉·勃朗蒂,伊丽莎白·勃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995)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诗人:批评读者》(1996),与玛格丽特·雷诺兹(Margaret Reynolds)合编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诗人文集》(1992);弗吉尼亚·布莱恩(Virginia Blaine)的《维多利亚女性诗人:注解文集》(2009)等,对克里斯蒂娜、伊丽莎白·西黛尔等拉斐尔前派女诗人,在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下,采用文化批评、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乃至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批评方法进行了多维视角研究[3]。国内拉斐尔前派诗歌研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早期代表人物包括徐志摩、赵景深、闻一多、查良铮、邵洵美和素痴、滕固等。1980年代后,飞白、屠岸、黄杲忻等一批学者,对其诗歌进行翻译和研究。当前研究主要包括朱立华的《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唯美主义诗学特征研究》和《拉斐尔前派诗歌的个体研究——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研究》两部专著、陆风所译的《罗塞蒂诗选》和殷杲翻译的《小妖精集市》两部译著、慈丽妍的博士论文“互文视域下的拉斐尔前派诗歌研究”,以及硕士论文和期刊文章三百余篇。研究发现,国外研究呈现出范式批评研究和问题意识研究并重、理论研究与文本分析并重的趋势;国内研究也呈现出理论研究与文本分析并重的趋势,体现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虽然国内外对于其诗歌的叙事艺术研究,尤其是叙事变异艺术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但其诗歌的先行研究至少为叙事艺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文本案例。
二、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叙事变异艺术研究
拉斐尔前派的主要成员但丁·罗塞蒂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兄妹、斯温伯恩、莫里斯、梅瑞狄斯、西黛尔等十多位诗人,其个人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和叙事文本在“大同”中也存在“小异”,单一的平面空间维度不足以涵盖和描摹各个诗人、诗作及其叙事艺术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因此需将其诗歌置于多重维度构建的脉络中加以考察,采用整体勾勒到局部聚焦的路径,对其诗歌的叙事变异艺术进行多维视角研究。
就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叙事艺术研究而言,《拉斐尔前派诗歌的个体研究——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研究》一书,在唯美叙事、爱情叙事、互文叙事、意象叙事、死亡叙事和女性叙事等视角下,对拉斐尔前派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的叙事艺术进行了研究,开启了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叙事与叙事变异艺术研究[4]。在此基础上,尝试以当代西方叙事理论为经,拉斐尔前派诗歌为纬,构建研究框架,立足诗歌本体,核心聚焦与整体勾勒并重,在“死亡叙事”“宗教叙事”“唯美叙事”“诗画互文叙事”与“女性叙事”等文本叙述层进行叙事变异艺术研究,(其中神话叙事、原型叙事和意象叙事,尚未考察到其显著的叙事变异特性),考察其诗歌的叙事主题、叙事路径、叙事空间、叙事焦点、叙事结构的变异模式,梳理其诗歌的叙事变异动因,诸如历史在场、宗教影响、伦理介入等现代性生成语境,分析其诗歌的叙事变异艺术研究意义,诸如叙事主题的升华、叙事文本意义的增值、叙事路径的拓展、叙事时空的失序与重构,以及叙事策略的革新等。
(一)拉斐尔前派诗歌的“死亡叙事”变异:“现世死亡”转向“虚构死亡(复活)”
死亡叙事是拉斐尔前派诗歌的主要叙事策略之一,开辟了死亡学研究与叙事艺术研究的新路径,更新了死亡叙事模式,拓宽了诗歌透视视阈;“由死变活”的转向,延续了生命的存在感,实现了人类永生和不朽的美好愿望,升华了死亡主题,重写了死亡的崇高和超越,体现了不惧死亡的“出世”境界;拓宽了叙事空间,导入了历史在场与宗教、伦理介入等元素,助推了人类死亡伦理困惑的消解;透视了战争、死亡与和平三者的交互关系,修正了其诗歌死亡叙事忽略“和平”元素的偏误,凸显了人类精神家园重建和人类现实生存状况改写的重要性。
拉斐尔前派诗歌死亡叙事的叙事变异焦点是“现世死亡”到“虚幻死亡”的转向,变异动因:其一是“虚构死亡(复活)”,对现世“不可抗”死亡的消解;其二是拉斐尔前派诗人的宗教信仰对维多利亚时代严苛的道德标准的反驳。例如,被贬称为“肉欲诗派”的但丁·罗塞蒂,由于自己的放荡不羁,导致妻子西黛尔抑郁而吸食过量的鸦片后香消玉殒,诗人悲痛内疚,愤而将自己的诗作当作亡妻的殉葬品葬入棺中。之后,为了纪念亡妻,他的创作由现世死亡转向了虚构死亡与复活。其诗集《生命殿堂》收录的《死亡歌手》等十余首诗歌,采用了隐喻式的现世死亡书写,而其名诗《神女》却由现世死亡转向了复活。现世的神女之死无力抗拒,而诗人采用叙事变异艺术,转向虚构死亡与复活,抗拒现世死亡,虚构了亡妻“正立在天庭的围墙之上”,“依栏探出身”,“从天堂依栏的地方/注视着脉搏般跳动的时光/穿越了整个世界。她深邃的目光/奋力穿越前方”,注视着凡尘中的情郎。神女经历了“生死轮回”后得以“飞天成仙”而复活。克里斯蒂娜由于宗教信仰而两次失去爱情,因此她的叙事模式也逐渐转向了虚构死亡书写与复活,诠释了“变体复活”与“灵魂永恒”思想。
斯温伯恩、罗塞蒂兄妹、巴特摩尔以及潘安、阿林汉姆等拉斐尔前派诗人都曾以书写死亡进行叙事。诗人在这些死亡叙事诗中,多采用现世死亡转向“虚构死亡”与复活的叙事变异艺术,对死亡这一终极主题进行了虚构的“死亡亲历书写”。拉斐尔前派的死亡叙事以“亲历书写”为主,即“遗书式”的虚构死亡书写,如克里斯蒂娜的《歌,我死之后》《死后》《魂归故里》,威廉·司各特的《死亡之后》等,几乎没有使用“直接书写”(“直播式”的再现死亡场景,叙述死亡感受),偶尔使用“间接书写”(死亡叙事中,叙述者不可能以内聚集的叙事模式讲述自己的死亡经历和感受),如但丁·罗塞蒂《王子的历程》中的公主之死。这种诗意的书写,体现了其死亡叙事变异艺术魅力。克里斯蒂娜的《魂灵的恳求》与《神女》叙事主题相似,只是叙述者由“情郎”变成“爱妻”,叙事空间由“天上”变为“地下”。亡夫罗宾的魂灵午夜归家,“闪身飘入屋中央”,“浑身冰凉,像寒夜的露珠一样,面色苍白像羊圈里的迷途羔羊”,恳请爱妻不要“哀啼”不要“悲戚”,使他在地下“无牵无挂,可以安息”。当然,死亡叙事与宗教叙事存在显性或隐性的关联或交叉重叠,天上或地下与凡尘的对话,与宗教叙事中的“灵肉合致”存在共性。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死亡叙事变异艺术,体现了死亡与灵魂永生、死亡与复活的传统的精神文化理念,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质朴心理,体现了人们对死亡与生命的哲思,对于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反思现代人类的生命悲剧意识,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二)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宗教叙事”变异:“灵肉合致”转向“灵肉冲突”
“灵”与“肉”,是主题学中常见的一种母题,也是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宗教叙事主题。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宗教叙事变异核心为“灵肉合致”到“灵肉冲突”的转向,“灵肉一元论”到“灵肉二元论”的转化。宗教叙事变异的动因,与其诗歌的现代性生成语境存在关联。拉斐尔前派诞生于“禁欲时代”,受到反基督教所倡导的“禁欲主义”的冲击,接受了“感官主义”和“肉欲主义”的影响,其后期的宗教叙事诗歌逐渐转向灵与肉的冲突与分裂,体现出感官愉悦、肉体享乐的道德缺失,以及人性自我反省与自我救赎意识缺省。
拉斐尔前派的生发与流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体系濒临崩溃”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影响。这个时代主张禁欲、标榜道德,是对18世纪后期奢靡、放纵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拨。清教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道德和禁欲对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引发民众对“性的焦虑情绪”。在此语境之下,拉斐尔前派诗人,尤其是克里斯蒂娜、西黛尔等女性诗人对性的描写极为敏感和矜持,但丁·罗塞蒂、斯温伯恩等诗人早期对性爱的描写也相当克制。作为“性的焦虑情绪”的心理补偿,作为维多利亚“假正经”式的道德标榜的反驳,他们创作了数百首纯粹的唯美爱情诗歌,诸如罗塞蒂兄妹的《神女》《爱之颂》《爱之生》《爱的证言》《情人眼里》《吻》和《情书》等百余首爱情书写诗歌;莫里斯的《爱在小屋荡漾》《只要有爱》等;西黛尔的《真爱》《爱已逝去》和《爱恨交织》等;梅瑞狄斯的诗集《现代爱情》收录的部分爱情诗歌等。这些早期诗歌追求灵魂与肉体完美结合、天堂的精神之爱与世俗的肉体之爱的完美统一,是肉的灵化、灵的肉化,是完美极致的“灵肉合致”[5]。
拉斐尔前派受到了当时社会、文化和宗教等现代性生成语境的影响,其诗歌的宗教叙事模式发生了从“灵肉合致”转向“灵肉冲突”的叙事变异。灵肉冲突(灵肉分裂、灵肉分离),在拉斐尔前派诗歌中,主要表现为“神性”和“人性”的矛盾、爱情与死亡的冲突、灵魂之爱与肉欲之爱的分离。拉斐尔前派诗人,如克里斯蒂娜,信奉基督教,坚守宗教信仰,遵循传统道德,展现“神性”的一面,渴求灵魂挣脱肉体的桎梏而获得心灵的自由。而事实上,当时严苛的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使宗教禁锢下的“人性”发生扭曲。“神性”和“人性”构成的矛盾,导致了女性缺乏婚姻与性自主权,导致了爱情的死亡和灵魂之爱与肉欲之爱的分离,例如,克里斯蒂娜诗歌的宗教叙事中,或爱情已死亡,或自己已死亡,她的诗“描写的几乎全是爱之失落和挫折,极罕涉及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至乐至福”[6]。神性对人性的禁锢与人的本能对情感的追求,如《少女之歌》中梅根、梅、玛格丽特与牧羊人、牧牛人、国王之间的情与爱,和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囚禁的灵魂”之间的冲突,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如:司各特的《爱情与死亡》《魂灵》《致亡灵》等,但丁·罗塞蒂的《从爱情到死亡》《爱情中的死亡》和《爱之死》等;克里斯蒂娜的《勿忘我》《爱已死亡》和《修道院门槛》等;西黛尔的《英年早逝》等,都以灵肉冲突为叙事主题(例如,爱情与死亡冲突的矛盾叙事、爱情与宗教冲突的矛盾叙事),赞颂灵魂之爱的圣洁,诠释了肉身之爱的易逝、精神之爱的永恒。有些前派诗人也尝试消解灵肉冲突。然而,如果叙事人物的灵魂消解,其肉体失去了道德,迷失于肉欲与感官享乐,如但丁·罗塞蒂描写性爱的诗歌被称为“肉欲派诗”;如果叙事人物的肉体消解(即“死亡叙事”中的“死亡”),其灵魂无法找到安置的家园,如斯温伯恩在《冥后的花园》中描述的“一个晚到的灵魂,天堂地狱找不到伴侣,趁云消雾散之际,从黑暗中走向明天”。当然,考察拉斐尔前派诗歌,并未发现其类似于中国电影《灵与肉》一类的叙事主题,即通过肉压制灵的叙事模式进行人性的自我审视。
(三)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唯美叙事”变异:“唯美”“纯美”转向“唯美偏至”
唯美叙事也是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叙事主题之一,唯美叙事变异艺术主要体现在唯美、纯美向唯美偏至的变异,叙事变异动因也和拉斐尔前派的现代性生成语境存在关联,如肉欲与感官主义的影响,“美不涉道德”与道德缺失的影响,波德莱尔的“丑学”美学的影响等。拉斐尔前派与英国唯美主义具有“共时性”“同质性”与“同源性”[7]。拉斐尔前派诗人罗斯金等将戈蒂耶在《莫班小姐》的“序”中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和“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思想译介到英国后,罗塞蒂兄妹等出版了《萌芽》,斯温伯恩创造了《诗与谣》,莫里斯提出了“生活艺术化”。他们宣传唯美思想,追求“纯艺术”与美的“去世俗化”,主张将追求美、创造美作为文学实践的目标,将美神化(“美……守护着圣洁,守护着人与动物的界线,站在人与神对话的路口”)。拉斐尔前派的早期的唯美叙事艺术作品,如克里斯蒂娜的《梦境》《爱情三重唱》和《镀金笼中的红雀》等,斯温伯恩的《配偶》等,但丁·罗塞蒂的《白日梦》等,都是唯美爱情或纯美意象的诗意书写,追求“艺术形式绝对化”与“个人精神绝对化”,重唯美形式,轻道德说教。不可否认,拉斐尔前派诗歌专注于“唯美”,而忽视了其社会与政治功能。
拉斐尔前派后期部分叙事诗歌走向了美的极端,导致唯美的偏至,经历了从唯美(纯美)意象到唯美偏至的变异,体现出“死尸”美学与“丑学”美学等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想,以及感官主义、唯美—颓废主义诗学特征。克里斯蒂娜的诗歌经常以死亡反衬爱情,以鲜花粉饰尸体进行唯美叙事。她在短诗《死后》中进行虚构死亡书写,用灯芯草、五月花与迷迭香装扮《我》的尸体。长诗《王子的历程》中,王宫中罂粟花点缀卷发的新娘尸体,洞穴中玫红缭绕周身的老怪物尸体,甚至《没有婴儿的婴儿摇篮》旁边的婴儿尸体,都毫不避讳地展现给读者。赞美尸体、欣赏尸体,表现出“以尸为美”的“尸体”美学。斯温伯恩的诗歌也体现出从唯美(如《配偶》)到唯美偏至的叙事变异艺术。诗人受到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影响(如“诗除了自身之外并无其他目的”“把善跟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丑恶之中挖掘美”等思想[8],创作了《冥后的花园》《婴儿之死》和《生与死》等十余首诗歌,讴歌尸体、猫头鹰、游魂,以及冥后“为死人酿出了葡萄酒”,表现出一种病态或变态的人类情感(如性变态、性虐狂);从死亡、恐怖、游魂等有关主题中寻求创作灵感,主张在黑暗领域,在丑恶事物中去认识美的存在,并把丑恶当作美来欣赏与歌颂,表现出“以丑为美”的“丑学”美学。但丁·罗塞蒂的婚姻和人生受到三个女人的影响:亡妻红发美女西德尔、嫁给朋友的黑发美女简和象征肉体性欲的模特芬妮。与这三个女人的情感与肉欲的冲突,使他对女性的描写极为香艳,从“金发”到“香颈”、从“粉颊”到“红唇”、从“酥胸”到“美臀”,无不充满诱惑,使其诗歌的叙事主题从唯美爱情转向大胆的“肉欲感官”描写(为此,布坎南等人贬称其为“肉欲诗词”和“肉欲诗派”),导致了其诗歌的唯美叙事发生了叙事变异。
(四)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诗画互文”叙事变异:“诗画一律”转向“诗画偏离”
“诗画互文”叙事研究是叙事学与互文性理论的交叉研究,研究核心聚焦于将诗画彼此视为“互文本”进行叙事的一种新的叙事模式。诗画的互文性主要研究诗歌语言与绘画形象(题诗画、插图书和诗意画)之间通过图解、模仿、改写与增补,形成互文关系,而互文本作为植入文本机内的“异物”,会使文本机体产生异常反应或建立新的生命机制,使叙事文本重生,叙事空间扩展,叙事意义增值[9]。诗画互文叙事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对于诗画互释、诗画互鉴、诗画创作以及诗画文本本体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拉斐尔前派作为一个由绘画到诗歌延伸的艺术团体,有些成员集诗画于一身,既可为其诗歌插图,亦可为其画作题诗,体现出“诗画一律”的唯美主义诗学观。“诗画一律”(诗画合一、诗画一致)注重诗歌与绘画的同构关系,即“绘画具有叙述的特征,诗歌具有画面的质感”,其美学价值在于抽象与具象的转换,增加了诗歌的层次感,增强诗歌的表达力和艺术效果,使审美主体根据诗的描述并通过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画面,体现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诗中有色彩,画中有诗意”的“诗画一律”互文叙事[10]。但丁·罗塞蒂自题自画的《白日梦》,题画诗“梧桐荫凉枝叶匝,仲夏犹可吐新芽,蓝天辉映知更栖,绿叶掩映画眉息……倩女情迷白日梦,目光深邃胜苍穹。痴迷梦中难自拔,书上洒落手中花”之中的各种意象都在绘画《白日梦》中再现,使该题画诗变得有声、有色、有形,增加了其诗歌的具象性,使题画诗的意义呈现不确定性与多元性,拓展了诗歌叙事文本意义。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互文叙事变异体现在“诗画一律”到“诗画偏离”的转向,变异动因也与其现代性生成语境存在关联。斐尔前派的艺术宗旨,就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经院式僵死艺术反叛,对拉斐尔之前纯真艺术的追求(因而被称为“前派”),这种叛逆和反驳,在其诗画中表现为对以往诗画的重新解读和对于诗画界限的僭越,而形成了新的互文叙事。拉斐尔前派的题诗画、插图等通过与诗歌文本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产生诗画偏离,构成诗歌文本与绘画形象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话、增补和模仿,实现诗画文本意义的延展、深化与更新,赋予文本新的生命,促成诗画文本意义的更新。如但丁·罗塞蒂绘画中与诗歌中的“神女”、《小妖集市及其他》的封面画与诗歌《小妖集市》之中小妖的意象,形成反衬与互补,深化了世俗与天堂、伪善与邪恶对立统一的诗歌主题。《无情的妖女》(济慈)和《艺术之宫》(丁尼生)的插图,以及绘画《基督在父母家中》等,也都体现出其绘画或插图与原诗间的矛盾与冲突:主题的偏离或意象的反叛等,导致了“诗画一律”到“诗画偏离”的叙事变异。当然,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诗画互文叙事研究,也存在文本语料的局限性问题,即诗歌与绘画间能够形成互文关系的数量限度问题。
(五)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女性叙事”变异:“他者身份”转向“自我身份”
“女性叙事”(Feministnarratology),主要基于苏珊·兰瑟提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是女性主义、性别政治与叙事学的交叉研究,是女性文学批评新增的一个文本叙述层[11]。女性叙事,狭义上讲,叙事对象仅指女性作家描述的女性意象,广义上,叙事对象也可以是任何作家笔下的女性叙事意象。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女性叙事变异艺术的研究,提出“女性叙事变异艺术”概念,突出“变异”后的女性身份的重构、女性话语权的争夺与女性形象的巨大提升;建构了女性主义与叙事学交互研究模型,使平面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转化为立体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同时,将诗歌的文学研究,置于法国大革命与维多利亚文化语境下,导入了历史在场与伦理介入等元素,升华了叙事主题,拓宽了叙事空间。最后,导入后现代、后殖民文学理论,如话语、身份、性自主权、第二性与他者等[12],研究拉斐尔前派诗歌女性叙事从“集体失语”到争取话语权与发出“叙事声音”的转化、从“他者”到“自我”身份的转化,研究女性问题,重拾经典,立足当下,为英语诗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文本叙事层,构建东西方女性研究的对话空间。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女性叙事”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拉斐尔前派女诗人克里斯蒂娜和西黛尔的诗歌,但也包括其他前派诗人笔下的一些女性意象。拉斐尔前派诗歌“女性叙事”变异的动因在于对女性双重道德标准的质疑与背离、女性反抗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弥尔顿时代”之后女性受教育意识的觉醒。首先,建构女性主义与叙事学交互研究模型,使平面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转化为立体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其次,将诗歌的文学研究,置于法国大革命与维多利亚文化语境下,导入历史在场与伦理介入等元素,升华叙事主题,拓宽叙事空间。最后,导入后现代、后殖民文学理论,如话语、身份、性自主权、第二性与他者等,研究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女性问题”,发掘英语诗歌研究的新文本叙述层,构建东西方女性研究的对话空间[13]。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女性叙事变异艺术研究,首先聚焦于女性“他者”身份到“自我”身份的建构、女性“集体失语”到“叙事声音”的发出、突出“变异”后的女性身份的重构与女性话语权的争夺。首先聚焦于自我身份缺失与集体失语现象: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他者”的不平等的“性自主权”和话语权,以及女性的“身体”受到来自男性世界的暴虐(如《小妖集市》中小妖对劳拉的暴虐),乃至女性的“同性恋”等;其次关注女性的自我身份建构与自我意识觉醒:“性自主权”意识、话语权与“身体”意识,以及对男权的反抗意识等;最后是女性形象赞美的解读。
拉斐尔前派诞生于父权制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形象的传统角色定位和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形象边缘化的状态,女性是第二性的“他者”,处于“集体失语”状态[14]。如克里斯蒂娜《王子的历程》中的新娘,被视为第二性的“他者”,近千行的长诗中,新娘始终处于似睡非睡、濒临死亡的失语状态:“睡了醒、醒了睡的新娘,不见翘首以待的新郎,但闻暗自啜泣与神伤”,“无论欢娱忧伤,无论沉睡清醒,她都会一直守望?”在这首长诗中,女诗人采用碎片化叙事模式,将新娘和王子置于多个事件中进行叙事。王子历经多种蛊惑,但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新娘却在被动等待的过程中郁郁而终:“太晚,爱情已逝;太晚,欢娱难留,太晚,太晚!”,“新娘离开了凡间……”。显然,新娘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领域内,只是一个男权社会的旁观者,天然地被边缘化、特殊化,失去爱情,失去自我,失去“身体”,只能“安息”“升天”。
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接受教育和进入公共社会空间机会的增加,使其敢于反叛传统道德、追求爱情和性自主权,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女性地位经历了从“他者”到“自我”、从“第二性”到主体性、从“集体失语”到“叙事声音”的转变[15]。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也体现在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女性叙事”变异艺术之中。拉斐尔前派诗人通过女性叙事,重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现代新型女性叙事意象,实现现代女性的“身份建构”,争夺话语权,力争发出自己的“叙事声音”,表达对女性新形象的赞美、崇拜和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其现代女性叙事意象主要包括姐妹形象,如《小妖集市》中反抗小妖的姐妹莉齐和劳拉、《少女之歌》中勇敢追求爱情的快乐三姐妹形象;新娘形象,如《莫德·克莱尔》中的新娘、《忆沃尔特·萨维奇·兰道》中的新娘;圣母形象,如《圣诞颂歌》中亲吻耶稣的圣母、安居在“那片小树林里”的圣母;天使形象,如《基督徒和犹太人》和《圣诞颂歌》中的大天使与小天使;平民女性形象,如《王子的历程》挤奶女工、侍女,以及《两次》中皈依上帝的虔诚女孩等。这些女性形象,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制下,女性形象的传统角色定位和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形象边缘化状态;女性不再是第二性的“他者”,不总处于“失语”状态,而是重构的全新的、敢于追求爱情且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新形象。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女性叙事变异也经历了从“他者身份”到“自我身份”的转化,从“集体失语”到“叙事声音”发出的转换。当然其诗歌与话语、空间、性欲、双性同体等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进一步关注。
三、结语
拉斐尔前派诗人的叙事变异艺术,革新了叙事模式,拓宽了叙事学研究路径。通过综合运用碎片化叙事、自我书写叙事等叙事手法,借助多个文本物化的事件与多种叠加的意象,在死亡、宗教、唯美、女性叙事和诗画互文叙事等叙事文本库内,进行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叙事变异艺术研究,为诗歌的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同时,其诗歌的叙事变异艺术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拉斐尔前派诗歌的研究文本语料,是其诗歌的“翻译文本”,而非原汁原味的“英语文本”。无论自译或引用别人译文,翻译文本的“诗学特征”直接影响诗歌研究,因此在诗歌翻译教学中需要培养译者的“诗学意识”。其次,需要厘清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唯美主义、女性主义、感官主义和颓废主义之间的隐性关联。同时,叙事学研究,除文学作品外,绘画、电影等皆可做叙事承载物,也是其诗歌的叙事对象。最后,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考察其诗歌在中国的研究、翻译和传播及其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形式和内容的影响,发掘中西文化交流轨迹,进而探究拉斐尔前派诗歌研究对中国“文化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文化战略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