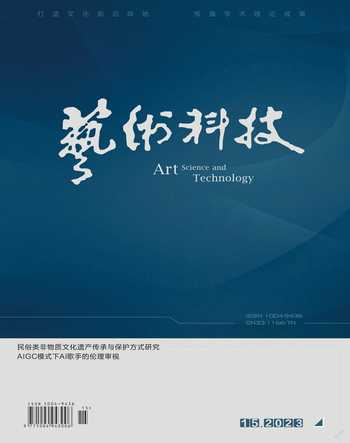论孙频小说《以鸟兽之名》的艺术特色
摘要:《以鸟兽之名》是“80后”青年作家孙频的又一力作。作为其山林系列小说之一,《以鸟兽之名》讲述了一群山民搬入现代化都市后所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小说将视角聚焦在阳关山这座大山上,通过古老与现代、自然与工业、山村与城市、迷失与追寻等矛盾交织,营造出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现代人的主体性矛盾与城乡移民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困境主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这也恰恰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整个故事围绕一桩凶杀案展开,浓厚的悬疑色彩贯穿整部小说,因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不同于传统的悬疑小说,该小说的语言具有极强的诗意性,因而呈现出多重面貌。文章探析孙频小说《以鸟兽之名》的艺术特色,深刻把握其创作取向,揭示孙频小说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以鸟兽之名》;孙频;艺术特色;山民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5-00-03
孙频的《以鸟兽之名》是其山林系列小说的又一力作,其围绕阳关山这一地理背景展开一系列矛盾冲突的对话与碰撞,以展现乡民进城所面临的身份认同与精神困境,也映射出现代人的主体性矛盾。纵观现代归乡小说,作者往往着力刻画乡野田居的恬静生活,力求再现陶渊明式远离世俗、回归乡村诗意生活的图景,以表达城市原住民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其叙述视角是由城市偏向乡村。在此创作思潮的影响下,往往忽视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根脉与归属感、宛若九秋蓬飘零的一群乡民形象,缺乏从乡村偏向城市的叙述视角。
《以鸟兽之名》是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鲜有关注到这个社会问题的小说。孙频借助悬疑小说的外壳构建文本,小说以一桩发生于山上的凶杀案开篇,“我”作为悬疑小说家为了取材,深入被锁定为嫌疑人的山民群体构建的移民小区进行调查。但在调查途中被山民发现,被赶出了小区。难以想到的是,正是这些山民在刻意藏匿凶手,自觉成为其同谋。小说在叙述的过程中用诗意的语言行文,使其以极其鲜明的艺术风格渗透于字里行间。十足的现代感、可读性强的悬疑色彩和诗意的语言是《以鸟兽之名》突出的艺术特色。
1 十足的现代感
写作对孙频而言是一场精神层面的内向开掘,每一个人物的困境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对自身生存困境的思考。
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人类文明进程大大提速。调查指出,现代人越来越容易感到孤独。每天从公司到家的两点一线、时过境迁对故土的眷恋、被时代抛弃的无力等,成为现代人难以释放的孤独的来源。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却越发感到孤独寂寞,人人都想逃避世俗的桎梏,而孤独感成为困住许多人的“捕兽网”。人们尝试着逃离孤独,摆脱孤独,而这种摆脱孤独的迫切动作反而是造成巨大孤独感的原因。正如蒋勋所言,“我们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所以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人们要学会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学会一个人走属于自己的路。
孙频身为青年作家,以敏锐的洞察力抓住了时代的痛楚,使小说现代感十足。多尔迈曾提出“现代主体性”的概念。现代人的主体性,是自相矛盾、常常陷入困惑甚至陷入困境的主体性。在《以鸟兽之名》中就有不少诸如此类陷入现代主体性困境的人物,他们大多是小人物,而正是这种小人物才更具代表性,能引发时代共鸣。杜迎春为爱情鼓足勇气,不惜与家庭决裂,却逃不出爱情的悲惨宿命。李建新为文学梦而离乡北漂,却连生活费都难以凑齐,他靠写悬疑小说为生,逃不出生活的囚牢。游小龙以文学装点自己,试图摆脱山民的身份进入高雅的境界,却摆脱不了原生身份与对兄弟游小虎的愧疚,也割舍不了对大足底的眷恋。游母装聋作哑掩盖被拐卖为人妻的悲惨人生,在逃脱无望后选择了沉默,可在睡梦中依旧难掩本能的对命运的哀恸。这些小人物不断地寻找自己,寻找人生的价值,寻找理想的生活,却都以碰壁告终。慢慢地,他们陷入了孤独、无力和困惑之中,选择将自己封闭起来,摆脱不了自己的心魔。可以说,这些人物是时代的缩影,浓缩了每个人的“时代病”,面对着追寻自我这一永恒的命题。《以鸟兽之名》如此切中肯綮地向内挖掘的精神探索,是對人性和自我的深刻思考。
“时代抛下你的时候,连再见都不会说一声。”文明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土地被日益吞并,使越来越多的山民从山村迁徙到城市。离开了大山的土壤,他们在城市中变得惊慌失措。没有鸟兽为伴,没有山林作友,面对冰冷的城市与原住民的冷眼,他们无所适从,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圈子里,抱团取暖。而这个圈子也面临着分裂,老年人延续着古老的风俗,企图通过在现代都市中恢复原始的生活方式填补那远离故乡的灵魂的空虚[1]。而年轻人在以价值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中,缺乏用劳动进行交换的概念,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山民生活模式中,他们意欲融入社会,却不被接纳,在金钱的引诱下沦为赌博之徒。无论是封闭还是融入,都殊途同归,他们显然成了时代的弃子。而这种被时代背弃的感觉导致山民们的身份焦虑,他们竭尽所能张扬外显以对抗平原文明。为了避免被平原人轻蔑,女人会穿金戴银,用家中全部的首饰来装饰自己;当城里人在夜晚跳起广场舞时,山民们特有的伞头秧歌也会接踵而起。这正是现代感的又一体现。在丛林法则下,总有一批落后于时代的人,但不可否认,他们隶属于这个社会。鲜有人将关怀投予他们,这是无法忽视的社会痛点。在《以鸟兽之名》中,孙频就描绘了大足底小区的山民这一被时代抛弃的人物群像。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我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走动,居住和生活,那不是我的,我不会留下脚印。”无论身处何时,都有时代的逆行者。“此心安处是吾乡”,在城市里,他们没有归属感,只有故乡的泥土才能安顿迷茫的灵魂。以游小龙为代表的大足底山民,内心深处的牵挂依旧是故乡的文化脉络,生于斯长于斯,大足底的山水鸟兽是抹不去的文化印记。
“乡村文学”是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虽然《以鸟兽之名》并非乡村文学,但其显然带有乡村文学的气息。在某种层面上,《以鸟兽之名》像一本地方志,记载了大足底的山林鸟兽、自然风光,也不乏民俗俚语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其对山村自然的关注,是一种回归式的写作,把人们带回原始文化色彩之中。《以鸟兽之名》有意地开掘山民文化,实际上意在引发人们对城市人生存现状的思考。李建新作为城市形象的典型,闯荡多年无果,还只是一个为了生计焦虑拼搏的小作家。而那些阳关山上的山民反而更富有生命的朝气,他们的生活与鸟兽为伴,颇具自由与野性,与代表自然的阳关山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其暗含着现代人对自然山林的渴望。
2 可读性强的悬疑色彩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的压力普遍增加,人们总想通过寻求刺激来释放自己,缓解压力。在悬疑小说中,一层层的设疑在推进故事发展的同时成功激起读者的好奇心,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因此,悬疑类型的小说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以鸟兽之名》中杜迎春的凶杀案是全文的线索,作为杜迎春小学同学的李建新为了寻找创作素材来到大足底小区,并在此遇到故交游小龙,却不想发现了一批抱团取暖的山民。在情节上,凶杀案是故事的引子和线索,使读者在阅读时始终带着探究欲去猜测凶手,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孙频设置的陷阱之中。孙频在安排李建新探案过程中多次以自述的方式揣测凶手是游小龙、游小虎两兄弟。作为小说着重描写的两个人物,作者赋予其孤僻的性格,这自然使读者将怀疑重心向其偏移。孙频借势诱导,在临近结尾宕开一笔,草草交代了凶手已被抓住。读者这才发现貌似板上钉钉的猜想被全部推翻,看似草率的结案,却让这个无名的凶手引发读者新一轮的猜想。于是,疑窦丛生,悬疑继续。悬疑小说中的侦探在读者的认知中往往具有更高的智性,因此“我”对待山民时的不屑与傲慢似乎也显得合乎逻辑。读者跟随“我”的视角,在“我”刻意制造的神秘氛围中获得快感,事实上也在无意识中参与了“我”所代表的平原文明对山民群体的凝视和异化[2]。
小说对人物神态形象的刻画颇为细致入微,烘托了悬疑气氛。小说是这样刻画游小龙的:“他虽然平素寡言,总像静静潜伏在水面之下,有时候却会忽然从什么地方浮出水面,且姿态昂扬,头顶着水草或月光,看起来就像只华美的海兽”[3]。水面之下、月光、海兽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事物,短短几句便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诸如此类的描写有许多,与游小龙大相径庭的形象邋遢的双生兄弟游小虎、装聋作哑却观察一切的游母、警惕性极强又排斥外族的大足底居民……他们诡谲的行为、原始的民俗,都让小说更显幽邃。
如果说悬疑色彩仅仅由凶杀案和人物神态动作描写来渲染,而凶杀案在小说中仅仅起到线索作用,那就不免落入窠臼。孙频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悬疑色彩的营造不局限于情节这一外显的基本因素,更高妙之处在于情境的隐喻构造。在环境的选择上,阳关山远离尘世,是具有原始气息的世外桃源;大足底小区身处城市边陲,封闭孤绝。两者构成了小说隐秘的叙事环境。这种带有自然原始色彩的舞台,为小说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平添了悬疑色彩。现代与历史交织,粗犷与野生交融,山间万物注视着一举一动。这为小说探究人性幽微及山民生存现状提供了基础。进一步来看,物理环境的封闭也与精神空间的困境呼应。回归山林找寻文化脉络,其实也是回归初心找寻自己,只是在山林中寻求慰藉罢了。
3 诗意的语言
当代作家的作品常常体现出“双向同构”的趋向,在现代化语境中糅合古典美学意象,营造出哀婉的诗意气氛[4]。孙频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诗意是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以鸟兽之名》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小说采用了大量古诗词的意象,对古诗词意境进行了移植与化用,是一种意境上的“重构”,使小说呈现出诗意化的古典韵味。桃花、月等古典意象恰如其分地出现,使李建新与游小龙酌酒叙旧的场景颇有几分文人墨客再现的意味。“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劝君莫做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等文学化语言频频出现,在赋予小说诗意的同时,暗藏主人公的心理状态。游小龙和李建新作为文学青年,天然带有某种互相吸引的意味,他们身上都带有难以自洽的矛盾。内心的诗意与孤独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文学青年心中,这可以算是文学青年的共性。这些诗歌意象的运用是个体心灵向往的体现,诗意的理想人生与残酷的现实窘境形成对比。而无论如何,灵魂都是展翅高飞的,更突显了诗意带来的精神鼓舞力量。孙频抓住了中国人深埋于心的文化基因。古诗词的意象被移植到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中后,相隔遥远的两个时空连接了起来,唤起了遗落在时间深处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情怀[5]。意象的运用并不突兀,相反,恰恰贴合人物形象,使作者产生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共鸣之感。
孙频的小说底色是苍凉的、深埋着绝望的,从一开始便笼罩着一种无边无际的哀伤,如其所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是一种精神产品,会对其他人的精神造成影响,因此不能完全以灰冷、黑暗的东西充斥其间。在文中渗入有诗意的、诗化的东西,可以冲淡小说底色的苍冷。”由此可见,孙频在创作时有意使用诗意的语言来达到调和小说整体色彩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孙频小说语言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其出彩的比喻和拟人。在《以鸟兽之名》中,她将心无旁骛、醉心创作的游小龙比作国王,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海子的那句“没有任何国王使我变成王座”。俨然,游小龙只能在创作中使灵与肉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便是自己的王。在描写桃花时,用一“杀”字便使三月桃花气势之旺、态势之猛跃然纸上。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可见其创作水平之扎实,也让文学爱好者读来不觉突兀,耐人寻味。这种诗意是潜藏的,需要心灵相通的读者在阅读中亲自体会。
4 结语
正如孙频所言:“文学可以帮助人们保持一点精神上的清洁与高贵。”孙频以其埋在文字里的真挚情感,探求现代人内心深处的隐秘。这种隐秘的困境与当今时代的经济与文化息息相关,《以鸟兽之名》并未给出一个突围救赎的方案。有采取对抗的方式如张扬山民文化,也有逃避的方式如竭力抛弃山民的符号身份,但这些都无法彻底解决他们的身份认同焦虑。而面对现代人的主体性矛盾与山民的困境,孙频更多探讨的是如何消化这种孤独,与其和解。
《以鸟兽之名》对处于城市边缘的山民群体的关注,实际上潜藏着对现代都市文化的深沉反思。这种困境根植于每个现代人的心底,不可磨灭。《以鸟兽之名》将十足的现代感、可读性极强的悬疑色彩和诗意的语言完美融合。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发掘到极强的包容性。每一个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这三种特色各自独立又彼此融合,构成了《以鸟兽之名》的独特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 王博.城市边缘处的孤独灵魂:论孙频的《以鸟兽之名》[J].今古文创,2023(17):17-19.
[2] 郑文哲.他者视角、复调对话与身份焦虑:论孙频中篇小说《以鸟兽之名》[J].新纪实,2021(36):48-52.
[3] 孙频.以鸟兽之名[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1(6):30-73.
[4] 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94.
[5] 于方方.现代性与古典意蕴的诗意融合:孙频小说的美学风格[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5):124-128.
作者簡介:张泉炜(2001—),男,江苏常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