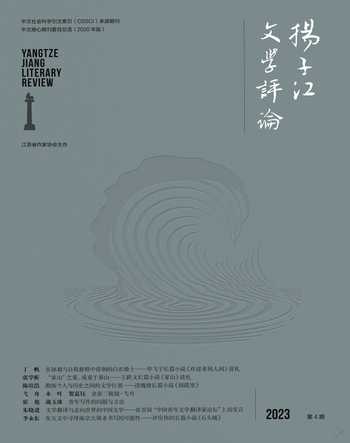《谈看书》:张爱玲对美国“非虚构”潮流的一次回应
高翔
1955年,张爱玲经由香港,途经日本,去往美国,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异国生活。同年12月,她去信一生挚友邝文美,在这封抵美的信中,她写到初入美国的印象:“廿二日到火奴鲁鲁,我上岸去随便走走,听说全城的精华都在Waikiki(威基基),我懒得去。就码头与downtown(市中心)看来,實在是个小城,港口也并不美丽。但是各色人种确是嘻嘻哈哈融融洩洩,那种轻松愉快,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至少表面上简直是萧伯纳威尔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预演。我刚赶上看到一个parade(游行队伍),各种族穿着native costumes(民族服装),也有草裙舞等等。街上有些美国人赤着膊光着脚走来走去。很多外国女人穿着改良旗袍,胸前开slit(狭长口)领,用两颗中国钮子钮上。笔直的没有腰身,长拖及地,下面只有开叉处滚着半寸阔的短滚条……”a
在这幅典型的“遭遇他者”图景中,张爱玲眼见夏威夷游行之中的各色人种,身穿民族服饰、改良旗袍,精神亢奋愉悦,却始终保持旁观——这也成为她去国后自始至终的一种姿态。而生命的版图毕竟已重组,无论张爱玲去国的意愿如何,目的中有多少出自文学的野心,终究进一步加入杂糅“各色人种”的世界文学浪潮中。十九年后,地理坐标夏威夷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重回张爱玲的笔下。在彰显其晚期文学趣味的重要文论《谈看书》中,夏威夷的复现仍不脱第一印象的“人种”考察,不经意间与张爱玲的美国初印象形成有趣暗合。
《谈看书》通篇谈人种、神话、《叛舰喋血记》史实和社会学家路易斯的著作《拉维达》,鲜少某种“标准”意义上的文学文本的赏鉴,但其根本宗旨并不离谈文艺,言在此而意在彼。《谈看书》一文中所举的种种“非虚构”作品例证,显然不是用来表现张爱玲文学口味的转移——事实上,她的口味从未变过,却是为了说明她所谓的“事实的金石声”。相隔半个世纪,在“非虚构”盛行的当下,这种对事实“韵味”的强调,其针对性不止在小说,对“非虚构”类文体写作同样有所启示。从某些层面来说,《谈看书》也提示着我们,或许应注意世界文学内部,自近现代以来,以“非虚构”为特征的潜流,以及这一潜流所参与、塑造的文学场域与张爱玲晚期风格的关系。显然,张爱玲自始至终处于这一文学场域之中。这股现代性潜流所呈现过的样貌,在中国和美国一度被命名为报告文学、特写、纪实文学、新新闻主义,或“非虚构”。在当下,这股风潮的盛行,甚至漫溢于虚构文本,拓展着读者对“真实”的感知。它远未完成,并将一直展开下去。在以西方为主导的“非虚构”写作框架内,张爱玲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和探索,于当下是一种有益的对照与补充。
一、“广泛的文学试验阶段”
“各种写作方法正处在一个转变和试验的时期。某些传统现实主义的常规手法已经衰落了……更确切地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广泛的文学试验阶段。”b约翰·霍洛韦尔在考察1960年代美国文学的境况时如此总结。虽然这一概括局限于美国,却也是世界性的。这股文学试验潮流,最突出的特征即是“文体”间的杂交,尤其是新闻与小说的交缠。现代文学的革新,无论国内还是域外,都与媒介技术的进展相关。自报纸出现后,集纳式社会新闻就不断满足着人们对事实与现实的饥渴。此后,一种杂交文体,新闻与小说的融合——“非虚构”,也由现代媒介的兴起而诞生,并正逐渐形成自身稳定的样态。张爱玲生于20世纪20年代,1950年代去国,1990年代离世,其生命历程本身便与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高度重合,这其中自然也包含着“非虚构”从无到有,从萌芽到鼎盛的完整时期。移居美国后,她更来到这股浪潮的前端,先国人一步,领受着最早的冲击。
以“非虚构”作为统摄性概念或潮流,从而描述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文体现象和倾向并不容易。在当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非虚构”的命名,某种程度上已形成各自的体裁界限,最大原因在于,“体裁像一种制度那样存在着”c,一旦体裁被命名,制度随即确立,为体裁厘定清晰的边界。谈论这一边界本身是困难的,另外有些文学上的“越界”和“例外”之作,同样让言之凿凿的定义失效。因此,当我们将“非虚构”作为世界文学的一种潮流或取向来谈,或者可以避免命名的尴尬。这种暂时的统合方式,着眼点显然不在于“非虚构”潮流中各种文体的殊异,而是意在它们之间的共性,而这一共性也为张爱玲所看重,即所谓“事实的金石声”和“韵味”。
1930年,一篇由日本人川口浩所作,名为《德国的新兴文学》的文章在国内翻译出版,报告文学这一文体首次被提及,文中称作家基希“从长年的新闻记者生活,他创出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这是所谓‘列波尔达知埃”d。“列波尔达知埃”即是日后报告文学的德语音译名。但该文体的传入,或许可以推至更早,也就是张爱玲出生的1920年代。胡仲持曾谈到:“报告文学这一名词是在我国大革命期间,随同一些马列主义的作品从日本传到中国。”e田仲济也有类似看法:“就过去印象,模模胡胡记得是二十年代末方见到这名称出现,从什么报志上见到的,已不记得。”f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报告文学在中国引入和播散的重要时期在1930年代,其最大推手莫过于左联。由于左联从译介、理论著述到写作实践的多方面倡导,报告文学得以在20世纪30年代呈现繁荣态势,“‘文坛上忽然有了新流行品了”g。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报告文学作品名噪一时。在文学史叙述之外,一些文学实践也不容忽视,尤其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上海为地理坐标的海派文人,在报刊媒介发达、消费主义盛行的时期,也进行过有关小说与新闻的融合实验。吴福辉提示我们,“海派作家本质上是一种报刊作家”,大多数作家都曾做过报人,“可见小说与新闻有不能分解的关系,小说的出路更在于报刊”。h多项以“商业”“消费”为目的的文体融合,虽并非纯粹的文学创见,仍为文坛带来生气。比如《小说》主编梁得所的实验,“在小说刊物里设‘并非小说栏,将报纸上最有故事性的新闻稿改述,‘有时令人读了几疑是小说哩!这很投每日与报纸为伍的中国市民看新闻与看小说无严格界限的心理。”有人甚至承认,在上海,“看绑票案,好像看水浒传,看烟、赌、娼案,好像看海上繁华梦;看男女私姘新闻,好像看玉梨魂;看弃妇在法院的诉苦词,好像看红楼梦;看宣传书画家卖字画的新闻,好像看儒林外史”。i再比如1940年代,报人曾水手曾用“报告文学”体,对上海的“烟花柳巷”之地进行调查走访,写出《新西游记》《东游记》等对于妓院的简洁报告,从地理位置、环境,到妓女人员、出场费,一应俱全,这难免是消费主义倾向下的一种投机,但如今看却是一种珍贵的“社会调查”实录。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新闻与小说的融合,实际上,与日后的“非虚构”差异巨大,它的基本动力在于“商业目的”,还“为了使作者尽量少地花费收集素材的精力和创造性构思的脑力,运用现成的材料,像拼搭积木一样组装小说,使海派期刊里复制式的作品大量出现。比如借用新闻写作时事小说、晚报小说,借用电影故事写电影小说……这并没有构成对小说文体的任何革新,仅是旧有文体的熟练操作”j。但这些实践已体现海派文人对于新潮媒介、技术、创作手段的敏感。
报告文学的创作遵从事实的规训,在中国,其文体除去中国传统纪实、消费社会兴起的影响,与异域文化的舶来关系更甚。西方报告文学作品成为国内作家实践仿照的经典样本,较重要的,包括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约翰·里特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爱狄密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辛克莱的《屠场》等。“一九三九年,延安鲁艺文工团员出发到晋东南时,几位团员的背包里就装着世界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的手抄本,并在行军途中背诵。”k这足见基希的影响。夏衍《包身工》中实录上海纱厂女童工的悲惨境遇,也早在《秘密的中国》里“纱厂童工”一节中有记录,这不能说仅是一种巧合。新闻写作的真实、客观、迅捷,外加文学化的叙事方式,使得报告文学的价值,聚焦于“用事实做指南的报告就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且,要是报告真正能够描绘出我们一代人的真实生活的图画的时候,就是将来,也有价值的”l。报告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辉煌,转入1940年代后逐渐暗淡,经历1950年代起伏,始终未得到足够重视,直至1980年代焕发新的生机。国内报告文学发展的进程,前后主要受到两种范式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苏联范式影响巨大,从报告文学到特写的范式转换,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苏联的倡导之下。而进入1980年代以后,于美国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构成新的潜流,张辛欣《北京人:100个人的口述史》便是在美国电视记者特克尔的《美国梦寻》启发下写就。2010年前后,通过《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寻路中国》等“非虚构”作品译介的助推,“非虚构”成为当下最为活跃的文体之一。
不可否认,自1960年代以后,世界性“非虚构”创作的中心在美国,甚至“非虚构”的命名也肇始于美国作家。卡波蒂虽以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 《蒂凡尼早餐》成名,但真正奠定其在世界文坛声望的是非虚构作品《冷血》。他耗费六年时间跟踪调查堪萨斯州农场发生的惨案,从凶手、警察到邻居,整理的访谈笔记多达6000页。卡波蒂由此声称创造出崭新文体,一种“新闻和小说叙述方式的混合物”。m这种声明,使得“非虚构”成为卡波蒂为《冷血》写下的一枚注脚,对作品的意义构成隐形的阐释。新闻与小说间配方的彼此勾兑,卡波蒂算不上孤案。诺曼·梅勒在1960年代创作的《夜幕下的大军》同样呈现出虚实间的张力,如果说《冷血》是一种作家深度观察的后果,《夜幕下的大军》则是作家深度参与的产物。作者亲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战游行,并将这一经历复刻进文学,在这部小说的副标题中,梅勒加入了那句著名的话——“如同小说的历史和如同历史的小说”——来隐喻这部虚实兼备的作品,也借此隐喻一个时代。约翰·霍洛韦尔回顾1960年代美国文坛时称:“细心浏览一下最近十年里的畅销书目,你会发现有许多畅销书是回忆录、忏悔录、自传和由心理学家以及医生写的大量的科普书。甚至当代的诗歌也显示出向自传和自白式主题发展的倾向。”n在新闻报道领域,“非虚构”写作方式的发见也许更早,1950年代末期,这种趋势便有萌芽,汤姆·沃尔夫、琼·狄迪恩、盖伊·特立斯等记者跃跃欲试,企图打破新闻一本正经、客观报道的姿态,他们大胆运用小说的叙事技巧,并在作品中极力彰显作者本人的声音和道德观点,沃尔夫以“新新闻主义”为之冠名,他的宣言如同圣经一样流行,并且原则明确,“新新闻主义采用完整的对话,而不是从每日新闻中引用一些片段;从一个场景过渡到另一个场景,就像过电影一样;吸纳不同的观点,而不是从单个叙述者的角度讲故事,并且十分关注人物的出现和行为方面的具体情况。经过严谨的报道,新新闻主义看起来‘像个故事”o。虽然这套原则未见得能够涵盖所有实践,但即使放诸文学界,卡波蒂、梅勒等人的非虚构作品也在相当程度上共享了这套原则,在文本中显现出一脉相承的特质。
实际上,美国文学在二战后的发展始终缺乏明确方向,技术上的日益精巧,反倒凸显出某种内在精神的缺失。这成为促发以“非虚构”为代表的新文学游戏的前奏。文体的杂交与拼接,在文学方向涣散后,成为1960年代美国文学的主题之一,这一系列实验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张爱玲的阅读乃至文学观念,她自始至终身处非虚构文学场域之中。在《谈看书》中,她便提及美國的新新闻学:“近来的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或新报导文学,提倡主观,倾向主义热,也被评为‘三底门答尔。”p新新闻主义重要作家盖伊 ·特立斯以美国黑帮为背景的非虚构小说,后被翻拍为电视剧,均受到张爱玲的大加赞赏,可见她对这一潮流的熟悉。在上海和香港时,张爱玲便对各种小报情有独钟,移居美国后,她对于“事实”的偏爱更拓展到各个领域,在与宋淇夫妇、夏志清、庄信正的书信中,多见她提及有关历史、社会、阶级等方面的非虚构作品,或以事实为背景的内幕小说、历史小说。总结她与夏志清、庄信正的通信,可简短罗列出一份属于张爱玲的非虚构书单,以肯尼迪车祸事件为蓝本的A Bridge at Chappaquiddick、有关肯尼亚凶杀案的White Mischief等作品都被张爱玲视为读之“心满意足”之作。
二、张爱玲与两种“破界”写作
张爱玲的“非虚构”作家书单,有俩人不得不提,其一是以《蒂凡尼早餐》闻名的杜鲁门·卡波蒂,另外一个则是一系列社会学畅销书的作者奥斯卡·路易斯。他们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由于二人都是美国“非虚构”的关键人物。卡波蒂的“非虚构”旗手意义自不待言,路易斯的社会学著作也在当时的美国广为热销,约翰·霍洛韦尔关于“非虚构小说”的学术著作,将两者的作品视为“非虚构”重要的写作范式。除此之外,在张爱玲与庄信正、夏志清、宋淇夫妇的书信中,二人的名字和作品也多有提及。卡波蒂甚至曾与张爱玲有过短暂的信件往来,是张爱玲在美国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名作家;路易斯的社会学作品,在彰显晚年张爱玲阅读趣味的《谈看书》中占据大量篇幅。庄信正表示,自己正是在张爱玲的介绍下,“买了路易斯的所有代表作,看得兴味盎然”q。路易斯去世之时,张爱玲在与庄的信中,亦表示了“震惊”。可见二人的作品与张爱玲的文学观念有“知音”之处。
1957年,张爱玲去信宋淇夫妇,信尾向二人推荐了卡波蒂的非虚构作品《缪斯入耳》。“这本书你们如果没看,希望你们找来看,一定喜欢。”r张爱玲与宋淇夫妇以往书信中所涉及的文学交流,大部分围绕中国古典文学,域外作家作品主要限于海明威、爱默生等事关张爱玲翻译事项的作家,纯粹文学审美上的推荐较少。显然这部作品很对张爱玲的口味。1968年的书信中,张爱玲再度提及卡波蒂,其时张爱玲有托卡波蒂推荐《北地胭脂》(Rouge of the North)的打算。“又写了一封信给Truman Capote,寄了本书给他,因为十一年前他的朋友Biddle夫妇(有个音乐喜剧是他们家的,Most Happy Fella(?)仿佛拍成电影的)告诉我说他们送了本《秧歌》给他,他很喜欢。”s此事在张爱玲与夏志清的书信中另有记述,夏志清回忆,“爱玲认识的美国名作家极少,一位是小说家马匡(J.P.Marquand),另一位是南方才子卡波特(Truman Capote)”t。然而信寄出后,卡波蒂并没有回应,“早忘了看过《秧歌》”u。张爱玲与这位美国南方才子之间短暂的惺惺相惜不令人意外,在文学上二人有许多共通之处,最显著的,除阴郁怪诞的哥特风格、擅用比喻外,他们还都是“跨界”写作的典范,小说、剧本、散文俱佳。我们无从得知张爱玲对这部作品偏爱的具体原因,但以“事实”为要素的“非虚构”特征不可忽视。
为张爱玲所钟爱的《缪斯入耳》,同时也被卡波蒂视为其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预示和奠定了《冷血》的诞生。1980年,距卡波蒂去世还有四年,他曾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将其分为若干阶段,《缪斯入耳》《蒂凡尼的早餐》被划为第二阶段,上承天才之作《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下启《冷血》《应许的祈祷》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在总结这一阶段时,他不惜笔墨,着重提及了《缪斯入耳》。该书以美国黑人演出团体《波吉与贝丝》剧组出访俄国为背景,卡波蒂作为随行记者,将其构思为一部简洁明快的,漫画式的非虚构作品。书中描绘了美俄一众鲜活人相,进而引出两个大国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诸多矛盾冲突。卡波蒂将这一本该严峻的主题轻松化解,叙事反其道而行之,显现出松弛、诙谐又啼笑皆非的喜剧效果。虽没有漂亮的销售成绩,但并不妨碍卡波蒂本人对这本书的看重,他认为该作为他一直以来的“创作窘境”找到了出口。这一“创作窘境”为何,卡波蒂在文中没有明确指出,但通过后文,我们可以隐约了解到,这一窘境与作家如何将其所了解的“写作形式”全部整合进一部作品中有关。卡波蒂所谓的“写作形式”,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新闻。他直陈这一形式对他构成强烈吸引,并认为造就这一吸引的,来自文学自身创新机制的乏力,而新闻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显然重构了文学的疆域。“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散文写作、或者说写作整体上都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其次,新闻作为一门艺术几乎是无人涉足的处女地,原因很简单:极少有文学艺术家写过叙事新闻,而当他们真的动笔写这类作品时,又总会采取游记或者自传的形式。”v值得注意的是,卡波蒂对新闻的态度,他是将新闻——一种以“事实”为根据的文体,作为艺术形式和文学资源加以利用和看待的,并试图将新闻收编进文学的使用框架内。因而《缪斯入耳》的写作野心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我想创作一部新闻小说,它能够大规模铺开,它有着事实的可信度,有着电影的直观性,有着散文的深度和自由度,有着诗歌的缜密”w。卡波蒂的“跨文体”写作意图,意味着对现有规则与制度的僭越与不满。在一则更早的采访中,面对质疑,他在讲述事件或新闻时,倾向于“做出更改”,“渲染过度”的声音,卡波蒂轻描淡写,“我只是把这个叫做让某件事‘活过来”x。所谓“活过来”,便是一种艺术呈现上的实验。
如果说,《缪斯入耳》是卡波蒂“非虚构”实验的起点,那么他未完成的作品《应许的祈祷》则可看作是终结。他花费四年,翻阅、改写从1943年到1965年间自己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打算将这些材料整编为一种“非虚构小说的变体”。《应许的祈祷》最终因涉及美国上流社会大量真实事件、人物和隐私,发表三篇后,即引起舆论哗然,随即被腰斩,卡波蒂几乎受到曾经朋友圈层的一致排挤。虽然这部未完之作,不乏耸动的噱头与绯闻,但仍寄托了卡波蒂的文学理想,这一理想比完成《缪斯入耳》的野心更近一步,可以说是为了解决卡波蒂文学生涯的终极“窘境”。“我并没有将我对写作的全部认知运用进去——那些我从电影剧本、戏剧、报告文学、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所学到的全部内容。一个作家应当将其所具备的所有色彩和所有能力在同一块调色板上调匀。”y他自认为《应许的祈祷》从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一目标。此后,他声称自己找到了这个框架,并得以将其对于写作的全部认知都融入这个框架之中。这一多种写作形式融合的尝试,在其晚期的非虚构作品《手刻棺材》中也有体现,这部作品依旧是卡波蒂擅长的罪案题材,但在创作手法上与《冷血》大相径庭,融入了大量对话实录、日记、书信、电报以及旁白与意识流,去小说化的意识更为明显。这种精心设计的“粗糙”,在模拟真实方面有着非凡的效果。
文学和新闻界打破体裁边界的做法,在社会学领域也有类似的尝试,路易斯以墨西哥、哥斯达黎加为研究背景的社会学著作,如《桑切斯的孩子: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拉维达》,因读起来更像小说而受到读者关注。张爱玲的散文《谈看书》,洋洋三万字,很大一部分篇幅让渡给了路易斯和他的社会学著作,可见她对该作的提倡。路易斯写作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其所仰仗的深厚的学科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以近似口述史的操作方式,让研究对象进行自我陈述。这既保持了内容的深入,增添真实的顆粒感,又比一般学术著作更亲和,具有小说般的戏剧性。特里林甚至为此发出感慨:“小说现在必须与以敏锐的描写手法写成的社会科学著作进行竞争。”z路易斯的写作思路起于他1943年进行的墨西哥研究,《五个家庭》是他此种类型写作的开山之作。此后他延续了这种方式,将研究对象继续缩小,从五个家庭收紧至桑切斯一家,《拉维达》的写作也与之类似。以《桑切斯的孩子》的调查方式为例,路易斯与桑切斯一家相处四年,深度参与他们的生活,陪他们上班、拜访亲友、去教堂……提出上百个问题,内容涵盖其世界观形成的方方面面。“我用新的方法让读者对其中的一个家庭进行更深层次的查看,每一个家庭成员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累加的、多面的、全景式的场景,每个个体是一个整体……同一件事会由不同的家庭成员描述成各自独立的版本,这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查验机制,许多数据的可靠性和合法性得以确保,从而部分地剔除了个人自传中所存在的主观性。”@7不管这种“查验机制”的有效性如何,它对真相的披露提供了帮助,还是造成了“罗生门”式的后果,都打破了常规读物所提供的“单向度”现实,为读者开放了理解生活以及人的多种可能。张爱玲认为路易斯的作品可贵也在于此,“普通人的历史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路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8。与此同时,口述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采访者的偏见,虽然采访者的编码、修正无处不在。口述采访主要依托录音机,记录后,再由路易斯整理并翻译。一个有趣的对照发生在路易斯和卡波蒂身上。路易斯信赖录音机带来的革命性后果,“甚至文盲都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然而然地、不加做作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且认为,“用来记录本书各日常生活往事的录音机使得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这种新的开端变成了现实”。@9但显然,卡波蒂与此论调相反,他本人拒绝使用录音设备进行采访。录音机“会制造假象与扭曲,甚至是毁掉任何存在于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自然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紧张的蜂鸟与它潜在的捕猎者一样”#0。两人对录音机使用态度的不同,如若说是采访目的、职业属性、知识结构上的差异,毋宁说是一种对“事实”以及对“事实”感知上的差异。在看待这一问题上,张爱玲的视角同样独特。在潜在的“非虚构”文学场域中,他们之间形成了一次隐秘的对话。
三、以“事实的金石声”为立场
《谈看书》被视为张爱玲晚期的重要文论,却少有人将其纳入美国“非虚构”潮流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张爱玲与美国文学的接触经验仿佛是一片“真空”。1974年,《中国时报》刊发了这篇长达3万字的散文,编者在按语中提示,这是关于张爱玲阅读趣味的“最亲切也最完满的解答”。对于写作这篇文章,张爱玲本人不甚满意,在通信中谈及此篇,多流露“懊悔”之感。庄信正也觉得,“嫌长了些,且有点紊乱”,但同时承认编者的按语,“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她的阅读兴趣”。#1这篇奇长的散文面向普通读者,没有“创意写作”式的教诲,但依旧设置了一道门槛。一方面,它的确彰显了张爱玲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其所设置的门槛,不妨说是中西对照视角下,张爱玲写作理念的一次整体性梳理和回顾,具有强烈的作家视角,而非只单纯从读者层面“拉杂谈论”。
张爱玲写作《谈看书》之时曾去信宋淇夫妇,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篇幅问题:“我想随便写篇《谈看书》,可以多引些英文读物,没想到这么麻烦,因为长久没写,老是怕又被曲解招骂,解释个不完,越写越长。”#2可见张爱玲此篇文章的本意,原只是想推介英文读物,而最终“解释个不完”,除去所引读物本身复述的困难,另外则是由于要说明理念缘由,必然费周章。《谈看书》的英文读物推介,占据篇幅最大的属邦梯案和《拉维达》,它们一则为了阐述“三底门答尔”、事实、文艺作品的关系。张爱玲举郁达夫所用的名词“三底门答尔”——该词既有“感伤的”“优雅的情感”之义,并暗示“这情感是文化的产物”——来表现文艺作品中不恰当的滥情。偏爱事实韵味的张爱玲,认为“所谓‘冷酷的事实,很难加以‘三底门答尔化”#3,以此声名自己反“三底门答尔”的文艺立场。二则为了伸张“含蓄”的主张。路易斯的《拉维达》在张爱玲看来,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特征:“我是因为中国小说过去有含蓄的传统,想不到反而在西方‘非文艺的书上找到。我想那是因为这些独白都是天籁,而中国小说的技术接近自然。”#4由于《拉维达》以民族志方式,第一人称口述实录而完成,“书中人常有时候说话不合逻辑,正是曲曲达出一种复杂的心理。这种地方深入浅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旧小说也是这样铺开来平面发展,人多,分散,只看见表面的言行,没有内心的描写,与西方小说的纵深成对比”#5。
实际上,从人种学、《叛舰喋血记》与邦梯案、行业小说一直到中国社会小说、《拉维达》等,《谈看书》中所列的清单甚至可以继续延伸。在张爱玲与夏志清的书信中,至少有两部分原本可再添加进去,但因种种原因未被纳入。其一,是文艺与电影的关系。“《谈看书》里本来也提起文艺与电影主动被动等,因为太长删掉。”#6张爱玲所删掉的内容具体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她对于文学的“跨媒介”运作与传播是关注的,且颇有心得,删掉的内容足以证明她对文学与媒介问题的敏感,让人联想到她与卡波蒂的类似之处。其二未被收入的,是对亨利·詹姆斯两部小说的评鉴。“《谈看书》已经太长,所以有些不想随便乱讲的就没写进去,如Henry James的The Aspern Papers看了印象不深,近年来看了书中所指的拜仑与雪莱太太的异母姊妹的事,却非常有兴趣。”#7可见她之所以想要提及詹姆斯著名的《阿彭斯手稿》,并非因为作品本身,反倒是小说背后蕴含的“事实”更令她感兴趣。同一封信中,张爱玲谈及詹姆斯另一部小说《丛林猛兽》,“厚厚一本集子里我只记得The Beast of the Jungle……我觉得命意好到极点,似乎自传性”#8。三年后,张爱玲再度提及该篇,评语几乎一样:“我只喜欢晚年的一篇The Beast in Jungle……这人——也许有点自传性——一直有预感会遇到极大的不幸,但是什么事都没发生,最后才悟到这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了。”#9除了“命意极好”,张爱玲对《丛林猛兽》念念不忘,“自传性”可以看作另外的关键词。也就是说,张爱玲对于亨利·詹姆斯产生兴趣的主要因素,即在于“事实”与“自传性”,而这两点也正是对《谈看书》所力图揭示的重要命意的相关补充。
《谈看书》一文的核心在于“事实的金石声”的阐述,它尤为体现了张爱玲晚期的文学观念。“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 ring of truth——‘事实的金石声。库恩认为有一种民间传说大概有根据,因为听上去‘内脏感到对(‘Internally right)。是内心的一种震荡的回音,许多因素虽然不知道,可以依稀觉得它们的存在。”$0“事实的金石声”这一概念,显然包含“事实”与“金石声”两部分内涵。所谓“事实”,在张爱玲看来,是涵括多种“内情”“因素”,并由此引发复杂因果联系的“事实”,它排斥的是单一线索,粗疏、浅薄的简单化陈述。而“金石声”则诉诸接受效果层面,它来自一种“内心震荡的回音”,张爱玲进一步补充到,这种震荡其实来自人们很难了解事实内情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一旦这一因素被揭示,就会带来“意外性”。“这意外性加上真实感——也就是那铮然的‘金石声——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而容易辨认。”$1因此,秉持“事实的金石声”立场,实际上意味着更加依赖作家对事件的熟悉程度和探索深度。“稍微有点不对劲,错了半个音符”,便“刺耳、粗糙、咽不下”。$2回顾张爱玲去国后的创作,耗时巨大的改写,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事实的金石声”的苛刻要求下,不断对于事实复杂的“因果网”及其“震荡效果”的逼近,《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一再改写的时间更是长达三十年。
以“事实的金石声”为立场,或以“事实”“真实”为小说的方法,并不完全是张爱玲晚期的思想产物。在反驳傅雷责难的《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就曾提出自己关于“真实”的写作观,“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3。在探讨“悲壮”(完成)与“苍凉”(启示)时,她亦表示:“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煩。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4在《论写作》中,她希望像“捡垃圾”一样捡回来的,是普通人“一点真切的生活经验,一点独到的见解。他们从来没想到把它写下来,事过境迁,就此湮没了”$5。“真实”或“事实”对于小说家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老生常谈,但张爱玲对于“事实”的倚重,不惜以“事实”为方法,在现代作家中却很少见,这同时塑造了她独特的创作观和阅读观。回到《谈看书》中,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张爱玲援引的英文读物,鲜少如小说等文艺作品,而是在“纪录体”上,甚至作为极少小说例子出现的亨利·詹姆斯也被无情删去。张爱玲做出解释:“从前爱看社会小说,与现在看纪录体其实一样,都是看点真人真事,不是文艺,口味简直从来没变过。”$6所谓纪录体,即是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非虚构”。这句话有一个关键性提示,即张爱玲将中国社会小说与西方纪录体同构,认为二者之间有可供联系和比较之处。也正是基于此,这篇奇长、漫谈式的文章,有了立论之处。
“不是文艺”,可看作是张爱玲对中国社会小说的一种理解,同时也是为其“定性”。也就是说,张爱玲将中国社会小说与西方纪录体,都视为对“真人真事”的写作。因而,她对于社会小说的评介,并非遵从纯粹文艺或标准文学的法则,而是通过阅读体验和经验,判断其是否为真。真实与否,符合事实与否,是判定其“好”与“坏”的重要准绳。这一看似“简陋”的评介体系,体现在《谈看书》中对中国社会小说的若干判断上,是一种粗疏的“真谛”。除去《儒林外史》 《歇浦潮》等著名社会小说,张爱玲额外提及了一些并不出众的,如她谈到《孽海梦》的相关情节,之所以还记得,是因为“不像一般真人实事的记载一样,没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没有墓志铭式的郑重表扬,也没寓有创业心得、夫妇之道等等。只是像随便讲给朋友听,所以我这些年后还记得”$7。“随便讲给朋友听”,即以一种闲谈的表达,近似口述,同路易斯的《拉维达》相类。另外提及上海小报记者的长篇连载、王姓作家的大连现代钗头凤故事,都因“近情理”,“看来都是全部实录”。尤其谈到社会小说全盛时期,大小报副刊连载的洪流,张爱玲判断“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虽然“粗糙”,但也可看作是张爱玲对社会小说“存真”的一种褒奖。“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俗手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色,反而原味全失。”$8张爱玲对美国内幕小说的批驳,正映衬对美国“非虚构”的某种认同,以“严谨”“客观”著称的“非虚构”几乎是内幕小说的反面。因此论及路易斯的作品《拉维达》时,中西对照之下有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以“含蓄”为入口,“立体的真实”有了傍身之地,“有些地方影影绰绰,参差掩映有致”$9。正是中国写实传统和美国“非虚构”潮流的交汇处。
在一众英文读物里,社会小说作为《谈看书》提及的唯一中文类读物,代表着张爱玲的立场。我们必须首先肯定张爱玲对于其时文坛风向的敏锐。20世纪中叶,美国“非虚构”文学大盛,这一文学盛况虽未来得及被“历史化”,但必然被张爱玲接收,这从《谈看书》以及她与他人书信交流中所透露出的阅读范畴便可看出。而对于这一“非虚构”潮流,张爱玲并非无条件接纳,而是站定在中国写实传统的立场上,对其进行吞吐与评介。可以说,美国“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同时为张爱玲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促使她一方面发现这股“非虚构”浪潮与中国纪实传统的“汇流点”,同时使她能够对其进行反刍式思考。因而,文中对于中国社会小说的概括和梳理,虽然极其简短,但却尤为重要,这可看作是张爱玲从中国古典文学——“金石声”立场,对美国“非虚构”潮流的一次回应。
四、余论
以中国社会小说与西方“非虚构”某种程度的交叉为契机,张爱玲晚期创作的散文《谈看书》,使我们有机会一窥张爱玲对于其时西方文艺作品的整体态度,也是一次她对自己几十年创作的再度回顾和梳理。大浪淘沙,一些重要的启示和经验得以沉淀。这些启示和经验,以一种中西对照的方式在《谈看书》中呈现,它的针对性不限于非虚构文类或小说,而是对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学写作提出的见解。
张爱玲虽然一直声称自己对于西方经典不甚熟悉,但从《谈看书》来看,这确是她的“自谦”,对于西方文学技巧和潮流,她有着相当程度的关注,且有自己的看法。如當时流行的新新闻主义,其偏向主观,易造成“倾向主义热”“三底门答尔化”,便遭到张爱玲隐隐的反对。张爱玲向来对作者过强的“主观性”不屑,《论写作》中她便揶揄“职业文人病在‘自我表现表现得过度,以至于无病呻吟……”%0《谈看书》中,她以电影《叛舰喋血记》与密契纳依据史实所撰写的文本作对照,指出“三底门答尔”的通病,电影两次改编的变化——一个虚构人物的增加与删减,反映的是公众“流行的信念”,并非事实,而这“流行的信念”便也是文艺创作中容易出现的“三底门答尔”。借此,张爱玲再次强调事实在文学中显现出的独特韵味,即“冷酷”、难以“‘三底门答尔化”。对于西方的“意识流”技巧,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相当的怀疑,她从心理描写的诟病入手,认为多“三底门答尔的表白”,“此后大都是从作者的观点交代动机或思想背景,有时候流为演讲或发议论,因为经过整理,成为对外的,说服别人的,已经不是内心的本来面目”。虽然“意识流”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心理描写”的弊端,但张爱玲认为,“内心生活影沉沉的,是一动念,在脑子里一闪的时候最清楚,要找它的来龙去脉,就连一个短短的思想过程都难。记下来的不是大纲就是已经重新组织过。一连串半形成的思想是最飘忽的东西,跟不上,抓不住,要想模仿乔埃斯的神来之笔,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皮毛”。%1可见张爱玲对于“意识流”的警惕,而这警惕的思考,根源依然在于这思想的来龙去脉是否为真,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
在美国“非虚构”潮流的映衬下,《谈看书》中传递出的张爱玲晚期的文学观念,愈发显示了其对于中国写实传统的坚持。或者可以这样理解,这潮流与中国社会小说之间的“共振”,使得张爱玲更确信于中国传统文学具有的某种“超越性”和“前瞻性”——其并非“现代性”的反面,甚至可能是“现代性”的未来。张爱玲创作晚期所呈现出的风格,也许与这“共振”不无关系。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如前所说,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于小说与新闻的融合,诞生了“非虚构”写作的风潮,伴随这一风潮的,是自传、忏悔录、回忆录的热销。此时,正是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创作的开端,《雷峰塔》《易经》至《小团圆》的创作时间集中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与这股写作潮流持续的时间恰好吻合。而张爱玲于1950年代创作的《相见欢》《色·戒》《浮花浪蕊》,在三十年间“屡经彻底改写”,“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2。除了“震动”“甘心”,张爱玲没有具体提及究竟为何一直修改,但其中应不乏对于“事实的金石声”标准的严苛执行。“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3“较好的作品都是deeply imbedded in the psyche(深埋在心灵里),自己虽然知道来历,唯一公之于世的办法是另写一个更接近事实的小说。”%4对“金石声”的玩味,对“内脏感到对”的执着,是张爱玲在晚期写作面临材料枯竭时,仍能继续创作的原因,也是她晚期风格转向的关键词。“《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5张爱玲最终采用了中国社会小说的传统。这一采用也许不是单纯的回归传统,而是中西汇流的后果,是“对照”下的一次“返身”与自我确认。漫长岁月过去,时间回到原点,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注释】
ars#2%3%4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Ⅰ》,宋以朗主编,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21页、61页、169页、223页、313页、247页。
bmnz[英]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仲大军、周友臯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6页、10页、14-15页。
c[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df转引自杨如鹏:《报告文学若干史料考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e胡仲持:《论报告文学》,《文艺生活》(海外版第6期),文艺生活社1948年版,第237-239页。
g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卷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hij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134页、108页。
k《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第六卷:报告文学卷·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l周立波:《谈谈报告》,《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o[美]罗伯特·博因顿:《新新新闻主义:美国顶尖非虚构作家写作技巧访谈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p@8#3#4#5$0$1$2$6$7$8$9%1张爱玲:《谈看书》,《重访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61页、56页、67-68页、65-66页、60页、61页、61页、61页、58页、60页、67页、66页。
q#1张爱玲、庄信正:《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88页。
tu#6#7#8#9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4-95页、147页、180页、176页、176页、220页。
vwy[美]杜魯门·卡波蒂:《〈给变色龙听的音乐〉前言》,《肖像与观察:卡波蒂随笔(下)》,吕奇、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86页、686页、690页。
x[美]杜鲁门·卡波蒂:《自画像》,《肖像与观察:卡波蒂随笔(下)》,吕奇、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05页。
@7@9[美]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导言》,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2页。
#0[美]杜鲁门·卡波蒂:《〈犬吠〉前言》,《肖像与观察:卡波蒂随笔(下)》,吕奇、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20-421页。
$3$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14页。
$5%0张爱玲:《论写作》,《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191页。
%2%5张爱玲:《惘然记》,《重访边城》,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2年版,第147页、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