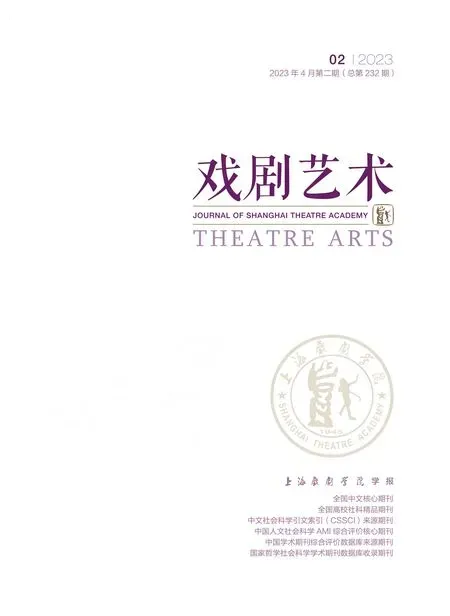五四文学的市民性渗入
——对于20世纪40年代话剧通俗化的逆向考察
尹 诗
20世纪40年代,话剧进入了职业化、剧场化发展时期。比起任何时期,话剧追求大众接受的倾向更为明显。此时的上海沦陷区,政治的弱化和商业性的凸显,将市民大众文学推向了高潮。左翼等新文学话剧都染上了市民色彩,和海派小说、散文一道融入了大众文学潮流之中。游走于商业和政治、艺术之间的话剧在经历过剧场演剧的历练后,走进市民大众不仅有着深刻的战时背景,更是文学自身的规律性使然。
一、 20世纪40年代上海话剧的趋俗化
20世纪40年代的左翼话剧呈现出多重复杂的面貌,上海以及延安、重庆、桂林等地的话剧演出给抗战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左翼话剧在30年代革命先锋性较为突出,到40年代,原本出身左翼或者倾向革命的剧作家如郭沫若、夏衍、田汉、于伶、阳翰笙、陈白尘,依然是话剧的创作主力。但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左翼色彩相对弱化了(但郭沫若《屈原》等剧的政治色彩还是较浓的)。上海话剧40年代掀起的通俗化热潮,从根本上看是其作为剧场艺术的文艺形式使然。左翼话剧初期的演剧和大众距离尚远,但一直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努力。话剧理应接受市民话剧吸引观众的某些特征,诸如题材的世俗性、观念的市民性、情节的曲折性、语言的通俗性等等。可以说,“1939年之后的孤岛,以阿英、于伶等人为代表的话剧创作的相对繁荣,和以上海剧艺社及中国旅行剧团为代表的演剧艺术的蓬勃开展,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话剧艺术的市民品性的回归和世俗观念的彰显。”(1)穆海亮: 《论孤岛时期改良文明戏论争》,《戏剧艺术》,2012年第1期。上海左翼话剧的主干力量上海剧艺社在经历了初期的摸索适应期后,已呈现出颇为景气的演出态势。左翼话剧汇入40年代上海文学通俗化的大潮,是在汲取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适应话剧职业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上海沦陷区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左翼文学色彩的隐蔽实因环境影响。李健吾曾经说过“沦陷区中的剧团若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只有与敌伪汉奸勾结‘政治化’了”。(2)韩石山: 《李健吾传》,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13页。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在戏剧界的骨干有不少撤离上海,“在中共上海市文委的领导和决策下及时转移部分比较暴露的党员力量。一边悄悄召集全体演职员宣告解散,为保存力量,党还支持翁仲马与小凤出面组建‘美艺’剧社”。(3)钱英郁: 《上海剧艺社解散前后》,《上海文化史志通讯》,1989年第3期。这之后的华艺剧团、同茂演剧公司(半年后改名为国华剧社)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话剧团。它们为了坚持演出,采取灵活的演出策略,如“同茂·国华的经营方针,采用进步剧目与娱乐剧目交替轮换演出的做法,实践证明是英明的抉择,既注意了社会效益,又保证了经济利益,还为剧社增添了一些保护色彩”。(4)钱英郁: 《上海剧艺设解散前后》。
吴天(又名方君逸)是孤岛的多产作家,如果单单从他的《红星泪》(原名《银星梦》)、《蝴蝶夫人》等作品来看,无论如何是会被看作海派作家的。但联系作者的创作经历却不能简单地加以认定。吴天1931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工作,在上海剧艺社时期以改编巴金的《家》而蜚声剧坛,作品有《没有男子的戏剧》《孤岛三重奏》《囤户》等。沦陷时期,吴天成了一个靠文为生的人,接连创作了《四姊妹》、《红星泪》、《桃李争春》、《子夜》、《离恨天》(又名《梁山伯与祝英台》)、《蝴蝶夫人》、《满庭芳》等剧作。《秦淮月》展现的是一秦淮歌女的恋爱悲喜剧: 钟氏家族兄弟二人都垂涎于歌女红玉,兄弟之间展开了争夺美人和家产的恶斗,弟弟杀死兄长,并将罪名强加于侄子曼滔身上,而曼滔正是红玉的心上人。得知爱人被抓万念俱灰的红玉跳河自尽,剧情以红玉被救、曼滔被放发生陡转,并以真凶落网,曼滔和红玉结合实现了大团圆的结局。(5)参见吴天: 《秦淮月》,上海: 永祥印书馆,1947年。剧作是言情故事和苦情戏的结合,再加上演出时采用了通俗市民剧常用的“戏中戏”手法,一度被认为和《秋海棠》是“两部姊妹作品”:“秦在《秋海棠》之先,但仍使人感到这是两部姊妹作品。秋是伶人生涯,秦是歌女外史,秋有京戏上台,秦有群芳会唱,秦还有唱大鼓,故事重心还是一个家庭。”(6)麦耶: 《新春剧坛总评》,《太平洋周报》,1943年第56期。它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主要还是“戏中戏”这一“生意眼”,如红玉解救曼滔的那一场,面对稽查队来搜查曼滔(藏身于红玉房内),情急之中的红玉唱起了蹦蹦戏《马寡妇开店》,名为助兴实为转移众人的注意力,当大家听得正酣纷纷叫好之时,红玉趁机“边唱边走到窗前,打开窗户示意曼滔逃走”(7)吴天: 《秦淮月》,第226页。,观众心系人物安危的紧张心情和《马寡妇开店》的“加唱”紧密相连,唱段充当了掩护和保障人物安全的“烟雾弹”,不仅达到了与剧情的高度融合,且在烘托剧情、制造戏剧氛围等方面有着独到的精妙之处。
另一剧作《蓝天使》的作者鲁思,原为左翼剧联成员,是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影评小组成员,曾发表过抨击软性电影的理论文章。《蓝天使》以幽默搞笑的手法展现了一大学教授与游艺场演员无厘头的恋爱故事。登载于《申报》上的广告特以戏中戏招徕观众,“三幕暴露喜剧,话剧、平剧、歌唱熔于一炉”。(8)《申报》: 1944年7月27日广告。该剧演出地点是绿宝剧场,《苏三起解》《纺棉花》《四季歌》之类的京戏、评剧、流行歌曲穿插其中,营造出了通俗甚至喧闹的舞台效果。尤其是主人公被迫辞去教授一职,不得已进入歌场做报幕员的一幕令人啼笑皆非。李教授与蓝天使合演《苏三起解》,以戏中戏吸引观众,改词儿且夹杂英文,引起了倒彩:
吟春: (积极从内奔出,忽又返身把头伸到布幔里去)Hurry up!快些!(走到桌前,向听众们)鼓掌吧,好的就来了!哦,我忘了交待。这个精彩节目是,miss蓝云裳唱标准平剧《女起解》。
[听众席中,掌声雷鸣。
[sport light 亮了,蓝天使上。
[李教授溜到幕后去化妆了。
云裳: (唱《女起解》)“(流水)苏三离了洪洞县,双膝跪在大街前,带惭含愧举目看,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三郎把信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就当报还!”
[掌声雷鸣般地响,声震户外。
吟春: (化就了小丑上)“(白)嘿,我说苏三走着,走着你不走啦!你跪在这儿祝告天地,还是哀告盘川?”
云裳:“一非祝告天地,二非哀告盘川。”
吟春:“(白)那你跪在那里干什么呢?”
云裳:“老伯,你去到客店之中,问问可有到南京去的没有?”
吟春:“(白)问有到南京去的干什么?”
云裳:“与我三郎带个信儿,就说苏三起了解儿了呀!”
吟春:“(白)到了这时候,你还惦记着他呢!你等着,我给你问问去。哎,这是好事!”
云裳: (凶凶的,白了他一眼)……
[听众大喝倒彩,嘘李教授。
吟春: (忘了置身于歌场中,竟大声地怒骂)Silence please!
[这可引起了听众的反感,嘘嘘声更高,有人喊打,也有人把香蕉皮与旁的果壳丢上台去。
云裳: (焦急地对李教授,低声的)你……疯了吗?我们是在台上吃他们的饭!(9)鲁思: 《蓝天使》,上海: 世界书局出版社,1947年。
《蓝天使》以加唱的《苏三起解》等唱段、歌曲,将游乐场的闹猛场面搬上话剧舞台,无怪乎会受到观众的热捧,而李吟春因吃醋而故意唱反调,捍卫丈夫尊严的一幕亦生动展现出来了。
左翼话剧趋于通俗化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参与文明戏改良。1941年,左翼剧人鲁思、毛羽被邀请参与东方剧场改革(10)作者不详: 《鲁思毛羽: 帮东方剧团改革》,《中国影讯》,1941年第2卷第11期。,他们秉持内容不走样,形式却趋向通俗化的原则,对舞台剧进行通俗化的改编,拟定有十大改编剧目: 《理想夫人》《情仇》《新婚燕尔》《假仁假义》《众香阁》《人欲横流》《终身大事》《狂欢之夜》《摇钱树》《夜半歌声》(11)《一日起东方剧场聘周起周刍等为导演》,《电影日报(1940—1941)》,1941年5月26日。。其中《新婚燕尔》改编自夏衍的《一年间》,《众香阁》改编自于伶的《花溅泪》,《狂欢之夜》改编自鲁思(果戈理原作)的《钦差大臣》。除了将题目加以通俗化的改编,改编者还会适当沿用文明戏的演剧形式,如当时春雷剧场的文明戏改造,发起人是关键、乔奇、黄鲁,“他们鉴于话剧的水准太高,文明戏的水准太低,太高与太低,都将阻碍演剧的进展,因此他们组织是想演一些低于话剧高于文明戏的戏。”(12)《春雷剧社正式成立》,《中国艺坛日报》,1941年3月12日。改编《少奶奶的扇子》一剧时,他们坚持演出时“摒除一般剧场幕表制,忠诚地依照脚本辞句排练上演”,但人物在“本来的面目上加些铅粉胭脂,无轮廓线条衬托,小生的白面孔红嘴唇;师爷的假胡子”(13)《观少奶奶的扇子》,《中国艺坛日报》,1941年4月7日。,这种改良的目的是要“使文明戏的观众非但不致受坏的影响,而且可以把他们的程度提高到能够看得懂话剧”(14)《春雷剧社正式成立》。,如此改编之下,剧作的思想意义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如《新婚燕尔》(即夏衍的《一年间》)的剧评:“东方话剧场上演《新婚燕尔》确是有着它的重要的意义的”,“强调了新生的一代和那些悲观主义者的对比,于阳明的死象征了一般小资产阶级悲观主义者的末路”。(15)吴瑛: 《谈“新婚燕尔”》,《新闻报》,1941年6月28日。可见新文学剧本以披着通俗外衣的形式上演,颇有成效:“观众可以仍旧拥有,而给予观众的教育意味却无形中增添了”。(16)《东方剧场演通俗化舞台剧》,《小说日报》,1941年6月6日。改良者是在以切合广大市民观众欣赏需求的形式,争取文明戏观众,进而扩张进步话剧的市场,促进剧运发展。
在左翼作家的创作、改编之外,还有话剧“趋俗化”的实践。如李健吾的《啼笑因缘》直接改编自张恨水的作品。此类市民喜爱的通俗作品的改编剧,不仅要满足观众“文艺化”的需求,还要提防落入鸳鸯蝴蝶派的窠臼。基于李健吾的身份,观众和评论者是寄予厚望的:“改编者力求其文艺化,相信,一个通俗小说入于高手的笔下,面目一改,所获亦不同。”(17)海风: 《啼笑因缘上舞台》,《力报》,1943年6月15日。而《啼笑因缘》的亮点便是李健吾于幕起时添加的一段白话诗,以新文学色彩的凸显受到盛赞:“听说一开幕就是关秀姑的独白,一连四五十句的白话诗,这风格是与莎士比亚的风格媲美的。”当时的剧评对此有记载,摘录如下:
一个没有母亲的女儿子,比什么人都需要温情,是什么缘故我不知道,她的痛苦只有自己感受,她不应该有什么怨恨。(18)海风: 《上联搬演〈啼笑因缘〉 韩非饰演樊家树》,《海报》,1943年6月9日。
评论对于“林彬饰演的关秀姑一段长长而清脆的独白”(19)秋雁: 《重观啼笑因缘》,《戏剧春秋》,1943年第3期。比较看好,白话诗的加入满足了大家的演出期待,成就了“观众心中美好的观剧体验”(20)潘正: 《评: 啼笑因缘》,《海报》,1943年6月30日。。另外,在戏剧情节改编时,李健吾去掉了何丽娜这一人物,以沈凤喜的不幸遭遇和关秀姑行刺刘国柱为主要故事情节,被评论认为“能够减少才子佳人的气氛”(21)松风: 《啼笑因缘评》,《新闻报》,1943年6月15日。。《啼笑因缘》是新文学剧人以雅俗结合的方式改编旧派通俗小说的成功典型。评论称:“《啼笑因缘》的演出意外地获得了成功,有人冤枉它把鸳鸯蝴蝶派的戏,硬妆成一个新的文艺作品,更关心这个戏的演出会染有文明戏的色彩,然而这盲目的预测,是违了良心的理论。”(22)秋雁: 《重观啼笑因缘》。可见,这种将通俗化小说直接改编成舞台剧的做法不被人看好。李健吾还专门谈过此问题:“不瞒你说,为了在敌人眼中争地位,我甘冒‘文化人’的攻击,把人们臭骂的张恨水的鸳鸯蝴蝶作品也搬出来改编,都是我的制作,钟书兄还大夸我把《啼笑因缘》改活了;我这个人不做则已,要做就做个痛快;我对朋友讲,有一天我会把它们印成书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可丢脸的。说实话,……《啼笑因缘》的第五场,就是仞之导演的那一场,我至今还有些喜欢,那是创作。人家把这看作下流,我把这看作是积极。”(23)李健吾: 《与友人书》,《上海文化》,1946年第6期。编剧在改编通俗小说时所承受的舆论压力可见一斑,而市民文学与新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高下之别亦可一窥。但这都不能阻止新文学由雅入俗的趋势。
除李健吾之外,向通俗靠拢的作家还有师陀。师陀一直以京派作家的头衔为人称道,在《里门拾记》《果园城记》里以回溯的方式讲述了充满抒情而又流露讽刺的中原故事。但他还以《大马戏团》和《夜店》两部通俗改编剧——在都市故事里增加大众成分——占到剧坛一席重要的地位。《大马戏团》,师陀用了两个多月来改编,1942年上海艺术剧团首演,黄佐临导演,自1942年10月10日在卡尔登上演,持续到11月18日,在40天里演出77场,(24)邵迎健: 《抗战时期的上海话剧》,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6页。几乎每天日夜两场。《大马戏团》轰动一时,是新文学作家创作市民剧的又一典型,通俗化色彩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发生在马戏团的恋爱故事,符合人们爱看通俗剧的心理: 全剧的矛盾斗争围绕着小铳对翠宝的爱情追求展开,交错的矛盾愈演愈烈,渐次积聚起来直至爆发,在翠宝和黄大少爷定亲的宴会上,小铳毒死翠宝后服毒自尽,滚下的油灯烧起了马戏团帐篷,盖三爷跳入大火。其次,剧本表现的“马戏团”这一具有民间特色的题材,让观众见识了浓厚的江湖气息,作品以活生生火辣辣的对白构成了风趣生动的台词,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本土风味,甚至不避讳俚俗乡野土话,如慕容天锡的“他妈的”“王八羔子”等口头禅即属于此类。在改编时,“师陀还加了许多有生意眼的所谓噱头,演出热闹,而且处理高潮紧抓住观众情绪的力量,3小时45分的演出,完全在如火如荼的情况中。”(25)周小平: 《大马戏团》,《太平洋周报》,1942年第1卷第41期。另外作者又有纯文学的深厚功力,注重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刻画“慕容天锡”等典型形象,以增强人物的戏剧性,突出舞台效果,如慕容天锡的“挥手杖”“用拇指和食指做个圈”等小动作。对于作品的通俗化,评论称“有人说是话剧大众化的先声,有人说这是低级趣味,不过,反正,在演出上开辟一条新的路线”,如“在饯行席上有‘噱头’表演,噱头是人做兽舞,先是军乐登场,接着第一个象舞,由史原、张菲担任演出,他俩扮成布型的巨象,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做成许多有趣举动,在台上兜了几个圈子,引起观众大笑。第二个是真马上台,创立话剧破天荒的记录”(26)立雪: 《大马戏团续演散唱》,《力报》,1942年11月6日。。具有十足生意眼的演出将噱头戏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
20世纪40年代,战争的风云虽然给上海市民带来动荡和不安,但是租界的特殊环境客观上又保护了市民社会的运行。话剧通俗化是立于文化市场的生存要求。海派话剧,即带有商业性的以市民观念为主的通俗话剧,于此时达至繁盛。放眼望去,海派关于情感纠葛、英雄美人题材的剧目占了整个剧坛的绝对优势。错综复杂、复悲又喜的闹剧和根据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的戏几乎占据了舞台的大部分。向通俗靠拢的左翼剧作者除了上述的吴天、鲁思,还有李之华、毛羽;当时还出现了写市民喜剧的杨绛,从事外国文学改编剧的柯灵等人。40年代,“大规模流行的与市民大众日常文化消费发生关联的,就是通俗小说和通俗戏剧作品”(27)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9页。。话剧和通俗文学一道以新旧融合之势汇入了市民通俗文学的大潮。
二、 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学通俗化的热潮
孤岛的特殊形势将市民文学推向高潮。话剧以及小说、散文、诗歌都在40年代凸显出了通俗性趋势。以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出现为标志,通俗小说取得了耀眼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张爱玲的小说化雅化俗、化中化西,达到了人生体验的深远境地。海派散文也颇为流行,伴随着大众媒介生产出来的作家苏青、予且、徐訏等人,勾勒出一幅幅的都市画面,充溢着先锋性、日常化与刺激性,迎合着消费文化的逻辑,风行一时,占有足够的市场。诗歌方面有《马凡陀的山歌》,以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市民生活为题材,从各个侧面反映当时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混乱等现象。语言通俗,形式活泼,在当时流传颇广,具有“与市民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契的休闲娱乐性的大众文化质素”。(28)王莅: 《论〈马凡陀的山歌〉及其相关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5期。而在上海,唐大郎以旧体诗加小注的形式创造的打油诗,创新性地实现了诗歌的雅俗结合。
40年代通俗化的热潮还表现在文学理论的提出和建设等方面。《万象》倡导“通俗文学运动”,呼应着时代和读者的双重要求,显示出通俗文学新旧融合的变化面貌。话剧方面的通俗化理论主张颇具代表性的有“积极的生意眼”和“有限的通俗化”。话剧从业者很清楚,观众中的大部分“是抱着娱乐的心情跑进戏场或影院的,宣传好,教育也好,但必须是渗杂或包藏在娱乐里面的”(29)路涯: 《生意眼杂感》,《上海影讯》,1944年第10期。。他们会支持生意眼,因为这样才能吸引观众的兴趣,有利于艺术的大众化:“其实无论何种艺术,都是必须有观众和读者的。用什么争取和吸引他们,其中之一就是生意眼。戏剧和电影这两种大众性的艺术,因观众的普及和庞杂,是必须有所谓生意眼来吸引他们,引起他们的兴趣。”(30)路涯: 《生意眼杂感》。“积极的生意眼”,是运用大众化的手段,接近观众,而不是迎合观众,更不应是低级趣味,具有和“商业噱头”大为不同的意图和目标。它与一味娱乐观众的恶俗海派旨趣并不相投。
与“积极的生意眼”相连的是“有限通俗化”。左翼话剧的通俗化与教育民众、宣扬阶级观念的立场和目的须臾不可分离。“有限的通俗化”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不违背社会时代的要求;不歪曲现实;不放弃领导作用;观众正当嗜好和健全的趣味,一个剧作者应尽量采取,但低级趣味不能盲从。不要忘记戏剧教育的意义,在取材和技巧上和对话动作上,极力去求观众完全了解,但决不能忘记戏剧运动的立场。”(31)鲁洛: 《戏剧的通俗化》,《新剧艺》,1944年第1卷第3期。这些将通俗化融入革命性的文学主张能够理性看待商业通俗化的负面性,不仅是新文学趋俗化的理论指导,对于市民文学的影响亦是深远的,在净化市场环境,防范商业化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等方面,左翼话剧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容忽视,这在注重商业利益,演剧通俗化的环境下显得弥足珍贵。
在如何做到艺术价值与票房价值、艺术性和娱乐性的统一问题上,话剧等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海”靠拢,向市民通俗性靠拢。可见中国现代文学追求大众接受的倾向十分强烈,我们可以从各流派彼此的许多不同点中,看出这一共通之处来。许多作品雅俗界限模糊,而呈现新旧难辨的面目。这就为文学史写作出了难题,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来考察阐释40年代的话剧等市民文学,而不是墨守成规,不承认“五四”以来新文学成熟的文体已经部分地淡化了先锋的色彩,进入都市市民普遍能够接受的日常文学视野了。
三、 五四文学的市民性渗透
相对于20世纪40年代市民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鸳鸯蝴蝶派小说遭遇激烈批评的五四时期则是现代通俗文学的低潮期。最初在“礼拜六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挑起的那场新旧文学论争,对于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及思想建构影响深远。人们对旧文学的批判不利于全面正确地理解新文学以及与旧文学的关系。突出的问题是只看到旧派市民小说的没落,却忽视了它的转型以及其中的调整和改良。事实上,在对旧派市民小说批评总结的同时,新的现代市民文学的观念和样式也在生长,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低潮期,正是现代市民文学的萌芽期。
对于五四文学的性质,历来有着不一样的观点。持启蒙文学的论者认为: 伴随着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思想的传播,文学应表现人,发展人的个性。而在左翼文学看来,从“五四”到“无产阶级新五四”,是从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从人的文学走向阶级的文学。相比启蒙论和救亡论,五四文学市民性的一面常常被忽视。“五四”的市民性质最早由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重点》等论文和《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中提出。他说:“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计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32)胡风: 《论民族形式问题》,上海: 海燕书店,1947年,第41页。这一将“五四”“大众”和“市民”统一起来的提法,提醒人们注意“五四”的市民性,认为五四文学与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渗透的观念是承继鲁迅的。在如今大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下,新的文学观跳出了秉持某一种性质的窠臼,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范伯群提出通俗和新文学的“双翼”论、吴福辉的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吴福辉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观点是现代文学具有左翼文学、通俗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四种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只有在相互的联系和张力中,才能立足生存。其文学史观注意到了现代文学的通俗化及其市民性的一面,启发我们从纯文学、左翼文学和通俗文学互动的视角来研究。
40年代上海话剧的趋俗化,以及小说、散文、诗歌朝向市民通俗化的趋势,显示出市民文学繁荣期的景象。与当时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市民社会的文化形态有着同构的关系。而30年代,现代市民文学的发展又何曾停止过呢?老舍的小说最有代表性,可以看作“五四”市民小说向30年代深入的标志性创作。“对于他所浸润的市民文化以及那些有滋有味的生存状态,老舍却从来不是‘旁观者’,他描绘市民阶层的人生理想,喜怒哀乐”。(33)李怡: 《老舍与中国生存文化的现代化——再论老舍对市民生态的表现》,《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同时期的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的文学创作,以自然主义和现代小说手法表现都市生活,“显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市民的倾向”(34)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280页。。现代市民文学的一路走来正提醒我们不能再被“五四”批判旧文学所遮蔽,任由“雅俗对立”的思想统领,而对“五四”的市民性、通俗性视而不见。20年代正是现代市民文学的萌芽期,“五四”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小说开启的时代,市民性的渗透体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诸方面。
在文学理论建设方面,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即有“平民文学”的提出。如周作人认为“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和事实”;“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35)周作人: 《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1918年12月20日。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先驱,周作人的研究注重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他也是较早译介民俗学,并将儿童学、神话学各种知识同趣味情感相互渗透,运用到创作中来的作家。胡适强调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泉,是基于平民文学的立场上提出的文学史观,且蕴含民间文学、市民文学的思想,可见其对于汉乐府、明清小说等加以研究的《白话文学史》。
“五四”市民文学的成就以散文较为突出。散文刊物《语丝》的创作阵营中,周作人、林语堂提出的幽默闲适的风格和倡导社会批评的思想主张见出分歧,分化的前景逐渐显露。1930年周作人创办《骆驼草》,可以看出五四散文变激烈的思想批判立场为个人温和的文化体认的转向。一批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声名的大作家传承了这一路向,其散文小品表现出的游戏、趣味、幽默及闲适等显露出现代市民文学的特性,突出代表是以林语堂为核心的“论语派”的产生。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市民性杂志的出现为标志,作为现代市民知识分子的刊物,在现代意识的启蒙问题上是与“五四”新文化精神一脉相承并以之为基本前提的。
在五四文学的小说领域,领头走入市民大众文学路途的张资平、叶灵凤,为了“吸引一般刚从旧小说转向新文艺的读者”(36)叶灵凤: 《未完的忏悔录·前记》,《上海的忏悔录》,上海: 今代书店,1936年。,大力调整自己的创作,将浪漫派、现代派和通俗派的文学质素融入创作之中。话剧方面带有市民性的作品可举出胡适的《终身大事》,这是以市民婚恋表现新文学主张的剧本。“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受市民文学影响的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浙东派”小说群体。如《故乡》叙写了城市人对乡村的回忆,闰土喊我一声“老爷”时“我”的反应,正是作者的平等观念等市民思想的显现。王鲁彦的《桥上》《自立》,许杰《台下的喜剧》等乡土文学的创作,描摹了部分城市化、商业化冲击下的乡镇生活,写到了商业思想逐渐传入乡镇,乡民之间朴素关系的破裂。另外还有《潘先生在难中》,这部被认为树立新文学批判市民传统的小说描摹了潘先生于战乱中的诸种痛苦、焦灼,透露出人物极力保全财产、保全家庭、保全自身的苦心,讽刺中隐现着对于逃难市民的同情之意。
茅盾认为市民文学“代表了市民的思想意识,并且为市民阶级所享用,其文字是‘语体’,其形式是全新的、创造的”(37)茅盾: 《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的演说》,《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848页。,此定义强调市民文学是表现市民的思想意识并且为市民阶级所欣赏,这即使放在今天,也是符合市民文学的基本内涵的。结合茅盾的论述,判断新旧市民小说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具有现代市民精神和现代市民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即现代市民性。而带有现代性内涵的市民性便成为五四文学以及之后市民文学的鲜明特质。中国不存在完整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是一般认为市民作为一个日益具有独立性的阶层兴起于宋代,适应市民阶层的需求、以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话本应运而生,并为明清小说的繁盛奠定基础。五四文学开启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具备了明清时期市民作家所天然缺乏的现代文化观念和对人性自由的更高要求。
因此,五四文学的市民性具有纯文学、先锋文学的成分,不同于古代市民小说惯常表现的人情世态,而是开启了以独立性、世界性、物质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意义上的市民价值观。这种现代市民性的特征首先是独立性,即对于独立自由的追求。在“五四”启蒙、个性解放的语境下,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个性独立和对自由的追求,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市民形象的精神特征。五四文学以更具人情味的书写,在人性的维度扩展了现代市民人物形象的审美内涵。其次是世界性,世界主义的想象和实践是构建五四文学不可或缺的思想维度。五四文学主张吸收世界的进步文艺,以创造中国的现代文艺,无论是新感觉派创造的都市审美感觉以及张爱玲对现代都市人生存困境的揭示,都延续了五四文学开创的新型中国现代小说的道路。再次是商业性。“五四”现代乡土小说,是以城市人视角书写的故乡的回忆,表现了商业法则带给乡村的现代意义的解体及市民思想对乡土的渗透,以客观而非批判的视野看待金钱法则的影响效应,为之后的城市文学奠定了基础。与商业性相连的还有物质性、世俗性等。“因为中国的市民社会从未完全脱离过政治的管辖。而由于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差距,遂产生了京沪两型的市民社会”(38)吴福辉: 《消除对市民文学的漠视与贬斥——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二》,《多棱镜下》,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97页。,但“同样具有世俗性、民间性、物质性”(39)吴福辉: 《消除对市民文学的漠视与贬斥——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二》,《多棱镜下》,第97页。。鲁迅、胡适、周作人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40)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2页。,他们在新的时代,接续了自晚明以来就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阔视野,体现出中国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启蒙意识。
结 语
五四文学的市民性指的是渗透了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启蒙立场与价值取向的市民特性。其实,无论是20世纪40年代的雅俗合流,还是30年代左翼、京海各流派文学的多元共生,无不是五四文学开启的,且都能从五四文学中找到踪迹。梳理五四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市民性的渗透,是从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关系一隅来观“五四”的真面目,也是尊重现代文学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所得。如果不能认清五四文学的现代市民性特征,40年代现代文学通俗化、市民化的趋势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现代市民文学的接受评价也会失之偏颇。而实际上,任何局部的历史都是更大范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水花,只有把握它们之间的衔接、对抗、失衡、渗透、融合,才是文学研究的根本路数。而这些正启发我们“五四”是可以有更宽大的眼光来看待的,再不能闭着眼睛不承认“五四”、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了。而弄清楚了五四文学的市民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五四”与大众文学、雅俗关系等问题,不仅可以启发我们消除对于市民文学的漠视和贬斥,客观看待20世纪40年代上海话剧的趋俗化等问题,更可以站在一个高点上俯视我们曾经走过的充满坎坷和希望的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