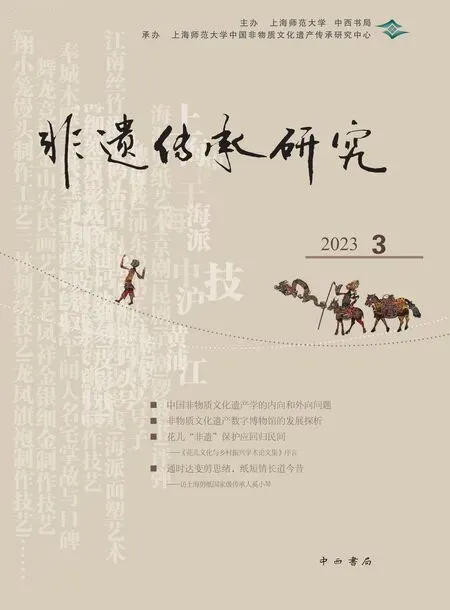媒介融合背景下晋域沿黄河地区非遗传播路径的时代变迁*
刘霄
黄河从忻州市偏关县老牛湾入晋,一路蜿蜒向西南,再由东北折回出省,流经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临县、柳林、石楼、永和、大宁、吉县、乡宁、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平陆、夏县、垣曲19 个县(市)。“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加强上述沿黄河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对于深入挖掘黄河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打造黄河文化生态文明,坚定文化自信,讲好黄河故事,全方位推动晋域特色文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非遗”资源分布概况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早期活动中心之一,与世界其他文明发源地一样,丰富的水资源灌溉和养育着沿河两岸的土地、人民,人们临水而居、聚族生存,在累世繁衍、孕育后代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并传承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反映人类早期历史的神话传说,围绕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经过反复实践萃取的手工实践,寄托美好愿望和生活情趣的艺术作品等。目前,山西省共组织五批次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申报工作,认定了530 多个非遗项目,涉及940 多家项目保护单位,①参见山西省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shanxi.gov.cn/。其中沿黄河区域非遗资源多达百余项,详情如下(粗体字表示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项目):
民间文学类17 项:董永传说、舜的传说、司马光传说、牛郎织女传说、乔阁老传说、大禹治水传说、鱼跃龙门传说、嫘祖养蚕传说、介子推传说、杨贵妃传说、黄河仙子传说、卫夫人的传说、蒲州渡铁牛传说、张生和莺莺故事、万荣笑话、蚩尤传说、汤王传说;
传统音乐类12 项:河曲民歌、保德民歌、吕梁民歌、碛口号子、晋南威风锣鼓、绛州鼓乐、软槌锣鼓、人祖山祭祖鼓乐、丁樊锣鼓、临县大唢呐、吉县唢呐、河津小曲;
传统舞蹈类8 项:垣曲武高跷、万荣花鼓、临县伞头秧歌、水船秧歌、亮宝、西石霸王鞭、盐湖龙灯舞、侯村花船;
传统戏剧类16 项:晋剧、蒲州梆子、北路梆子、临县道情戏、兴县道情、永和道情、芮城木偶戏、线腔、锣鼓杂戏、二人台、眉户、怀梆戏、夏县蛤蟆嗡、垣曲曲剧、弦儿戏、扬高戏;
曲艺类6 项;临县三弦书、平陆高调、河东说唱道情、离石弹唱、垣曲镲、河津干板腔;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7 项:心意拳、永济飞狮、打瓦游戏、动物棋、流星锤、散手迎风掌、河东风筝;
传统美术类21 项:柳林剪纸、万荣剪纸、河津剪纸、永和剪纸、绛州木版年画、刘家焉头木版年画、临县传统彩绘艺术、万荣面塑、万荣面人、乡宁花食、芮城布艺、传统民俗服饰制作技艺、运城绒绣、永乐桃木雕刻技艺、泥皮画、柴森宫灯、河津转花灯、永济扎麦草、泥金笺画、河东戏曲脸谱、河津吕氏砖雕技艺;
传统技艺类17 项:桑罗酒制作技艺、张营小米醋酿造技艺、兴县清泉醋传统酿造技艺、柳林碗团制作技艺、垣曲炒粸制作技艺、手工空心挂面制作技艺、芮城麻片制作技艺、“酱玉瓜”制作技艺、山西传统琉璃烧制技艺、桑皮纸制作技艺、晋南涂布织造技艺、惠畅土布织造技艺、木制模型制作技艺、芮城婴幼儿服饰制作技艺、地窨院建筑技艺、灰陶制作技艺、铁器锻造技艺;
传统中医药类8 项:平王中医正骨、赵氏正骨、冯氏中医皮肤烧伤疗法、武氏中医脾胃派疗法、腹揉康传统揉肚技艺、中医养生术、垣曲菖蒲酒炮制技艺、勒马回中药制作技艺;
民俗类17 项:礼生唱祭文习俗、关公信俗、鸣条二月二四圣出巡庙会、凤山庙会、海潮禅寺庙会、柳林盘子会、河曲河灯会、偏关万人会、禹王传统祭祀习俗、河东盐池文化、后土文化、舜的祭祀、后稷祭祀、尧的祭祀、永济背冰习俗、九曲黄河阵、万荣抬阁。
以黄河入晋流经地市作为参照所形成的非遗资源项目数据见表1:

表1 晋域沿黄河地市“非遗”资源统计表

续表
综上所述,晋域沿黄区域非遗资源相对集中于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美术、手工技艺与民俗实践几类项目。细论之,民间文学又以帝王传说、人物传说、风物传说、笑话、故事为主;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四类,其中音乐类分民歌、器乐(唢呐和鼓乐)两种,舞蹈、曲艺、戏曲类资源主要表现为秧歌、花鼓、民间说唱、弦子书、梆子腔与地方小剧种;传统美术主要有剪纸、雕刻、面塑、布艺、彩绘、木版年画等工艺类型;传统技艺分为酒醋酿造、饮食制作、土布织造、陶铁木器制作等领域;民俗实践则表现为传统庙会、祭祀活动、节庆习俗、人生礼仪等方面。传播地域根据资源情况大致可以划分为晋南传说故事、晋西北民歌小调、吕梁民间曲艺舞蹈、河东戏曲民俗几大典型片区,手工技艺、传统美术、传统中医药、传统体育与游艺类项目主要集聚在运城沿黄河各县市,其次分散于吕梁山区的离石、柳林、临县、兴县等地,构成晋域沿黄地区“非遗”资源的地域分布概况。
二、黄河文明传播路径解读
山西境内黄河两岸的先民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各种风俗习惯、人文传统,诸如节日庆典、人生礼仪、饮食服饰、物产商贸、婚丧嫁娶等,并在此基础之上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及手工制品。“民间文化的传播演变是区域内文化互动融合的过程,空间是考察文化传播演变的地理基础,关注的是文化存在范围的广延性与伸张性。”[2]晋南地区丰富的帝王传说、人物风物传说寄托着民众对古代先贤、历史名人的地缘情感,并在口耳相授、历代典仪活动中得以有效传播。表演艺术类遗产多与人们生产生活、贸易交往、社火祭祀等密切相关,如流行于山陕两省的“走西口”民歌、晋陕蒙大峡谷河运文化中的商贸习俗、随晋商足迹而兴起的山陕梆子、植根于社火庙会的民俗表演等。民间手工艺术类遗产作为黄河流域特定环境的产物,是民众精神需求和审美倾向的表现,沿黄河吕梁、晋南一线的剪纸、年画、彩绘等工艺作品,更倾向于选用纯度较高的红、黄、绿等明亮色彩作为主色调,作品寓意美满,兼具艺术与实用性,由血缘姻亲以及地缘文化联系承担着艺术的对外传播。民间信俗类遗产是千百年来民众在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生活中流传下来的关于自然、祖先、神灵崇拜的产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祈雨祷晴、庙会祭祀、节日庆典和人生礼俗,这类资源有着较为固定的时空限制,而且容易形成相应的社会组织,负责仪式和活动的开展,主要依靠风俗惯例与人际交流实现文化的传播。手工技艺类遗产在传统社会中属于农耕经济的重要补充,反映黄河流域小手工业的分布状况和从业者的技艺传承度,它受众面广、涵盖民众吃穿住用行各方面,但因受到母体经济形态的制约,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化,代际之间以师徒相授、家族经营实现个性化技艺展示和乡土社会中的文化价值传播。
总之,传统社会黄河流域民间文化资源以语言、文字、声音、动作、技艺和各类民俗空间与展演场所作为传播介质,民众的生产生活、精神需求又让孕育传统文化的社会体制系统得以稳固,艺术创作、展示和传承在传统文化生态下得以有序循环。
三、传统媒介助力下的文艺呈现
20 世纪随西方文明而逐渐兴起的现代传媒技术,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例如:相机的出现取代了画师的部分职能,摄影技术从实体舞台中分离了受众,报纸杂志压缩了鼓书、戏剧等传统艺术的题材范畴,广播电视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时空观念等。报刊、杂志、影像等媒介技术为人类认识世界、观察社会、信息生产输出提供了一套新法则,它拓宽了文化的传播渠道,也使受众与本体之间的互动生成新的需求。然而各种传统资源并未中断其传播路径,因为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在“人”,没有人的参与文化无法形成,也即“自然的人化”过程无法实现。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传统社会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武力胁迫下被动进行现代化转型,传统文化也即随各种媒介的运用开始适应新的生态环境,并沿不同路径向现代化迈进。“媒介基于人对自身力量的突破和超越时空限制的需求,以不同形式渗透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前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北京大学1919 年以《歌谣》周刊为中心发起的歌谣运动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7年以《民俗》周刊的创刊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标志,将社会关注目光下移到民间,逐渐形成传统文化在媒介空间中延续的新路径。延安“鲁艺时期”(1938—1943),报刊、画册、广播、电台等媒介形式成为文艺作品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中包含了大量反映黄河沿岸人民生产生活及精神状态的优秀红色文化,如抗战歌曲、“山药蛋派”文学作品、秧歌剧、大型合唱曲、新歌剧以及木刻、雕塑、版画等工艺美术品,虽然在当时国内外战争大众传媒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下略显微薄,但是通过这些简单的传媒形式依然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播电视技术逐渐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中普及开来,随之一批传统文化与影音技术相合而生的新艺术作品走进民众视野,诸如戏曲电影、戏曲电视、黄河歌舞剧、技艺专题片、影像民俗志等,并且相继出现了许多电视专题栏目——《走进大戏台》《歌从黄河来》《文旅大发现》等,为宣传、展示、传播晋域黄河文化提供了多种选择。与此同时,传统纸媒行业仍然统领文化传播的主阵地,各种报刊、杂志、书籍中记录了多样的黄河文化艺术成果,其中具有突出意义的传播活动有:1953 年中央音乐学院晓星教授组织研究人员对河曲民歌进行采风活动并出版《河曲民间歌曲调查研究专辑》;20 世纪80 年代“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编纂中,山西沿黄河市县出版的三卷本丛书及手抄本、油印本等基础资料;2001年由青、宁、蒙、甘、陕、晋、豫、鲁8 省人民出版社联合编纂的十卷本《黄河文化丛书系列》等。
与农耕社会基本固化的传播轨迹相比,传统媒介影响范围广,覆盖面大,“报纸、期刊、书籍具有理性度高、针对性强、重复阅读率高、便于引导受众需求、艺术性强等优势;电影、电视、广播等作为综合性视听平台提供良好的感受性,便于打破原有非遗文化时空的限制,进行多元化的交流”。[4]然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诞生,传统媒介成本高、视觉差、互动少、开放性低、个性化弱等缺点,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当代文化的输出与传播,无法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新媒体时代非遗保护与传播
21 世纪随着数字化技术、互联网运用的普及与推广,有别于报刊、广播、电视的新媒介形态不断出现,它“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叠加、媒体间形式上的迭代,更是在内容上助推文化的融合,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赋能”。[5]非遗在这一时期开始引入我国并逐步得以传播,它是中国政府在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成为其缔约国(2004 年)之后,为与国际社会接轨而广泛使用、宣传和推广,用以区别于有形遗产的文化表述与民众实践。回顾20 年非遗传播路径之探索,以新媒介的参与程度与保护模式、理念的探究作为主要依据,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2006—2010 年为初始阶段。这一时期各省相继开展非遗普查、申报、认定、建档、管理工作,学者们在非遗保护整体构建、策略方式的讨论过程中,普遍认为后工业时代文化失衡现象是非遗传承断裂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数字化技术将成为非遗抢救性保护的新手段,并且从记录保存、立档研究、展示展演、传承教育、弘扬传播等方面展开研究。2010 年文化部相继发文《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各省积极探索针对重点文化区域和相关遗产类型(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中医药)的整体性、生产性保护,遗产共生与文化再生产理念得到推广。与数字化保护相关的“非遗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特别是档案资料管理系统标准的统一与社会开放利用”[6],为依托互联网而生的新媒介技术有了与非遗保护进一步深度融合的基础。
2011—2015 年为深入阶段。2011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公布,各项保护工作在法律框架下得以有效进行:四级名录保护体系逐步完善、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成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设立,且“伴随非遗保护与实践深入,非遗申报热潮渐渐消退,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愈加突出,非遗的经济属性受到广泛关注,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和非遗产业开发等成为研究热点”[7]。其间各领域研究焦点侧重于对非遗再生产、再利用的跨界对接,数字化媒介由初期的建档保存、研究保护、网络展示宣传转为对技术路径的探索、应用个案的分析和综合性市场效能的结合,如晋中、平阳、吕梁、河东等区域文化生态保护数字传承发展案例,沿黄河地区手工技艺、传统美术、中医药炮制、文艺作品等特色文化资源保护形式的研发等,还涉及遗产项目的网络传播展示、数字法规建设、产业开发利用等领域。
2016—2022 年为常态化阶段。2016 年至今,非遗保护的关注点再度回归大众,学界发起关于保护主体和非遗融入民众生活的大讨论,一方面继续致力于保护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如四级名录与传承人遴选制度的体系化、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经验总结等;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非遗融入经济生产、民众生活,增强遗产持有者的认同感、参与感和获得感。政策上,继扶持和发展传统工艺、戏曲、曲艺等行业导向性措施之后,2018—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原国务院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发文,将非遗保护和扶贫工作相结合,推进非遗扶贫就业工作坊设立。2021 年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将非遗保护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非遗在增进文化认同、维系国家统一中的独特作用。此阶段“研究广度和深度并重,学者们偏向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具体应用,在文旅融合、产教联合、场景重构和跨媒介传播等方面研究较多,并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市化的战略规划相呼应,对技术伦理和数字经济进行了深度反思”[8]。媒介融合所带来的科技进步无疑为黄河沿岸非遗资源的转化和利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展示平台,元宇宙数字时代的到来,也会给“非遗”融入民众生活提供更加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创意方向。
五、小结
在媒介融合的大时代背景下,晋域沿黄河非遗资源想要获得更大的传播、发展空间,必须在充分了解新媒体传播特点和传统文化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借助媒介融合所带来的互补优势,对非遗核心价值给予新的时代解读。当今时代,“非遗”为进一步适应与媒体深度融合趋势,不断丰富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并且利用各种媒介的互通,开辟传播平台与途径,形成以传统为基础、媒介融合相辅助的综合传播模式。我们应发掘媒介融合的深度优势,利用科技手段实现黄河流域非遗资源的转型改造,发挥传统文化精神纽带作用,促进社区认同与深化,让黄河文化融入当代,实现其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