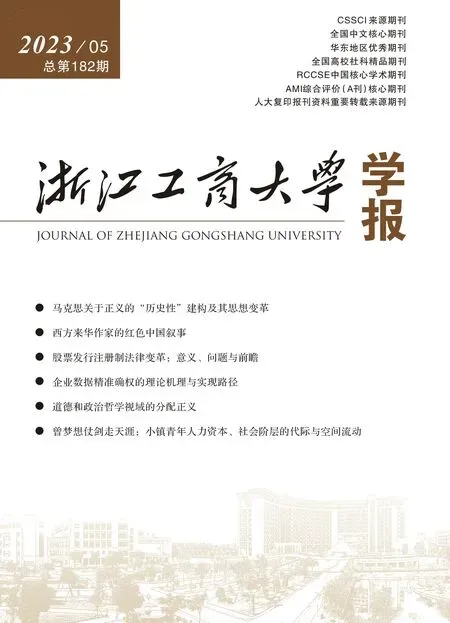家事程序立法的德系演变与中国选择
丁宝同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我国家事审判改革提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命题作为远景目标,2021年起实施的《民法典》之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的有效施行则提出更加迫切的家事程序专门立法需求[1]。为加速其立法进程,须先确定立法的模式和体例。综观域外法例,德国家事程序的立法演变占据特殊的历史地位。它主导现代家事程序立法模式的转向趋势,并塑成三种家事程序单行立法体例的鼎立格局,可概之称为家事程序立法的“德系”演变,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我国家事审判改革与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立法命题
我国地方性家事审判改革始于20世纪末,2016年起“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推向全国,提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立法命题,并确立为改革的远景目标[2]。
(一) 家事审判改革的全国化进程
20世纪末始,我国地方性家事审判改革举措崭露头角;21世纪以来,渐成燎原之势。同时,家事案件数量持续快速增长,早已成为第一大类民事案件,年收案数占比约20%,(1)2014年为163.52万件,占比19.68%;2015年为181.73万件,占比16.45%。年审结数占比近1/3。(2)2006年为115.9万件,2012年突破150万件,2013年为161.9万件,2015年为173.3万件,2016年为175.2万件。“案多人少”的结构性矛盾深度加剧[3],家事审判改革的全国化势在必行。
2015年12月“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于京召开,2016年公布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明确提出:“探索家事审判工作规律,积极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4],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5]。也是为克服家事法律秩序危机做出的司法应对,具有社会治理层面的重要价值,蕴含“政治动力学”的深层意绪[6]。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发布《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法〔2016〕128号),确定改革的目标为“转变家事审判理念,推进家事审判创新,探索家事诉讼程序……”,提出“少家合并”和“少家分头”两种试点模式,明确试点法院确定方案及两年试点期间。同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视频会议具体部署,118家中、基层法院成为试点,全国性家事审判改革开启。试点期满,201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法发〔2018〕12号)。但这绝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二) 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命题
域外民事诉讼立法奉行“程序分化”理念,普呈轨道多元和立体化形态[7]。家事案件是以身份关系为原点的复合化类型体系,对诉讼程序有着突出的立体化特殊需求。大陆法系多以“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的二元区分作为主导逻辑,单行制定家事程序立法,系统分类家事案件以配置多轨程序;即便保守法例,也会于“民事诉讼”和“非讼程序”法典单设编、章以配置专门程序[8]。我国《民事诉讼法》初以苏联法为蓝本,虽经数次修改,程序单一和平面化的不足却延续至今。它凸显为非讼程序的立法简化,延伸至家事程序的立法缺失。家事案件被迫一体适用《民事诉讼法》,全面援引“通常审判程序”[9]。但“通常审判程序”以财产案件为主导客体,基本理念是刚性适法,核心功能是高效解纷。早期的职权主义诉讼程序构造下,或尚可契合于家事案件。但随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构造的逐步确立,越发不能满足家事案件对职权主义的特殊需求[10],难以实现家事审判的纠纷管理功能[11],无力兼顾身份关系的柔性特质和治疗修复[12]。因此,这种援引违背案件类型与程序属性匹配的逻辑,折损家事审判程序质效,必然促成家事审判改革深化,催生“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命题。
试点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2017年7月,首次会议签署《关于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法〔2017〕18号),明确其“协作改革决策机制”的属性,并将“向全国人大提出家事特别程序立法建议”纳入职能范畴[13]。2018年7月,二次会议又强调:探索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推动改革成果制度化、法治化……至此,“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命题正式提出,并确立为改革远景目标[14]。
立法命题既已提出,即应加速推动立法进程。为此,又须首先确定立法的模式和体例。综观域外法例,德国家事程序的立法演变占据特殊历史地位,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 德国早期家事程序之合一立法模式与二元分化体例
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初定“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1898年《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塑成“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
(一) 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初定
所谓“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即对“民事程序”概念外延作广义定位,令其涵摄“家事程序”的概念范畴,以“民事程序法”的文本统一性为前提,于其中设专门编、章对“家事程序”作特别设定。
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现代民事程序之原生性发展轨道,即“民事诉讼程序”。它广义定位“民事诉讼程序”,自始单列“第六编 婚姻事件与禁治产事件”,分两章对“婚姻”和“禁治产”两类家事事件的诉讼程序作特别规定,从而确立原初意义之“家事诉讼程序”并令其涵摄于广义“民事诉讼程序”。至此,德国“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初步确定。
1896年《德国民法典》和1897年《德国商法典》公布后,18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完成第一次实质性修订,由872条增至1048条,基本奠定后世立法规模。之后又经数次修改,伴随“亲子”“扶养”等被纳入家事诉讼事件范畴,“第六编 婚姻事件与禁治产事件”逐步扩充。至1997年修改,该编扩至六章,涵盖“结婚”“离婚”“亲子”(包括收养)、“扶养”和“其他”(包括禁治产)五大类家事事件,编名亦改为“第六编 家事事件程序”。(3)又译为“第六编 家庭事件程序”。2002年该法修改时,据2001年《德国民事诉讼改革法》和《德国同居伴侣法》,又将“同居”纳入该编[15]。
(二) 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成形
所谓“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即先将“民事程序”区分为“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讼事件程序”,再将“家事程序”区分为“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从而以“民事诉讼法+非讼事件程序法”的二元立法为前提,分别专设编、章对“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作特别设定。
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早于1896年《德国民法典》和1897年《德国商法典》诞生,其直接样本是德意志帝国前各邦国的“民事诉讼立法”(统称《一般裁判法》),而各邦国又均有其独立普通法体系。因此,1871年帝国成立后,据同年《帝国宪法》,不仅迅速公布《民事诉讼法》,而且同步启动“民法典”和“商法典”的编纂。(4)同年连续公布的《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连同配套《实施法》统称《帝国司法法》。又因此时德国尚无独立、统一“非讼事件程序法”[16],虽理论早就将由法院处理的诉讼案件外事项定性为“非讼事件”,其程序却是由各邦国原“民事诉讼立法”(5)如,1793年《普鲁士国家法院通用规则》。或帝国对特定类型非讼法律关系的“单行立法”(6)如,1875年《德国监护法》。来规范[17]。所以,法典起草委员会迅速达成共识:新帝国实体法施行必须获得程序法系统支持,应同步制定“非讼事件程序法”[18]。后来,最初的草案是《监护事件及其他家事事件程序法》。但因其只涵盖“家事非讼事件”,委员会重新制定名为《非讼事件程序法》的草案,以涵盖所有非讼事件。后于1898年5月17日公布,并于1900年1月1日施行。
恰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也采总、分则结构。但在分则的编排线索上,两者有实质差异。前法分则采以程序阶段为识别要素的编排线索,依次对控告、抗告和上告审等程序阶段作出规定,以期支撑诉讼程序的阶段化有序推进;而后法分则采以非讼事件类型为识别要素的编排线索,以为各特类非讼事件提供特殊化审处规则。(7)又分别称为“以程序为中心”和“以事件为中心”的结构设计。
前述编排线索下,截至被2009年《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取代前,该法分则第二至十章列举式涵盖两大类合计14种非讼事件:第一类,“家事非讼事件”,包括“监护,照管和收容,其他家事非讼事件”“收养事件”“身份事件”“遗产划定和分割事件”,及“夫妻财产登记事件”等;第二类,“传统民(商)事非讼事件”,包括“船舶抵押权事件”“商事登记事件”“社团、合伙登记事件”“代宣誓保证、物的调查和保管、质物变卖事件”及“法院和公证文书出具事件”[19]。且其首条明确规定“法律授权法院的所有非讼事件,除非立法有其他规定,统一适用本法”。通篇考量,该法不仅承袭罗马法之“非讼裁判权原理”,而且立足“国家监护思想”认为“非讼事件本质是法律授权法院参与法律关系创设以形成正当法秩序”,最终抛弃部分传统诉讼程序原理而确立现代非讼程序的三项基本立场:第一,弃“两造对抗程序构造”采“单方程序进程逻辑”[20];第二,弃“当事人主张证明主义”而采“职权探知主义”[21];第三,弃“当事人进行主义”采“职权进行主义”[22]。
综上所述,1898年《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开创以单行法为所有非讼事件统一配置审处规则的先河。虽有学者认为其初始目的并非开创与传统“民事诉讼程序”并列的“非讼事件程序”[23]。但该法的内在构造,其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立体差异,及对他国立法和现代诉讼法学理论的深度影响,共同标识其实质性开创现代民事程序的次生性发展轨道——“非讼事件程序”。自此,诉讼法开始区分“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讼事件程序”,“民事诉讼法+非讼事件程序法”的二元体系正式形成。而且,恰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单列第六编以确立“家事诉讼程序”并涵摄于广义“民事诉讼程序”,《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亦选择同时涵盖“家事非讼事件”与“传统民(商)事非讼事件”,以确立“家事非讼程序”并涵摄于广义“非讼事件程序”。至此,“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终得成形。
三、 德国现行家事程序之单行立法模式与一元统合体例
2009年《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转采“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并且创制“非讼化之一元统合体例”。
(一) 转采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
2009年之前,由《德国民事诉讼法》和《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共同支撑的家事程序,在近110年运行中逐步陷入三重危机:第一,诉讼与非讼程序分别立法造成规则交叉和适用困难;第二,非讼程序适用范围开放扩张导致规则体系紊乱;第三,全面推行职权探知、进行主义诱发程序法理冲突[24]。系统修法以实现家事程序的现代化革新势在必行。
2002年《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修订计划重启,(8)1964年德国曾启动该法修改,后于1977年提出草案,但未能成为立法。2005年6月6日德国司法部公布更名为《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的“参事官草案”,2006年2月“参事官草案修正案”公布,2007年5月“政府决议草案”公布,后于2008年5月连同“立法修改理由书”提交审议,经数次小修于2008年9月通过。新法最终定名为《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于2009年9月1日施行。就德国家事程序的发展,该法的第一项历史性改变就是:彻底颠覆施行近110年的“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而转采现行“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
所谓“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即对“民事程序”概念作狭义定位,以打破涵摄关系而剥离“家事程序”范畴,放弃“民事程序法”的文本统一性,以单行立法对“家事程序”作系统规定。欲采此模式,须由《德国民事诉讼法》分离出原第六编的“家事诉讼程序”,并汇入2009年《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为此,该次修法自始就明确“系统构建适用于所有非讼事件之统一性程序”的任务,进而提出整合分散于《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德国民事诉讼法》和《德国法院组织法》等立法中的“家事事件”以实现其审处程序全面非讼化的目标。最终,该法延用总、分则结构。其第一编“总则”共110条对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审处程序的通用性规则作统一化规定,第1条就首先明确:该法适用于家事事件及联邦法律规定由法院管辖的所有非讼事件。其分则第二至八编则先采用“多元平面分类”方式将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划分为七大类,(9)即家事事件、照管与收容事件、遗产与分割事件、登记与公司事件、其他非讼事件、剥夺自由事件和公示催告事件。又于各编内以“分章列举”方式进行次级种类划分,以分别配置特殊性审处规则。其中,第二编“家事事件程序”在第一章“一般规定”对家事事件通用性规则作统一化规定基础上,又于第二至十二章以“多元平面分类”方式区分11类家事事件以分别配置特殊性审处规则。该编起始第111条,对11类家事事件作集中性列举。其中,亲子、血缘关系、收养、暴力保护、供养均衡事件属“一般性家事非讼事件”;婚姻、婚姻和家庭财产、抚养、夫妻财产制、其他家事事件及同性生活伴侣事件,则属于被“非讼化”后的“真正家事争讼事件”。《德国民事诉讼法》原“第六编 家事事件程序”所含六大类家事诉讼事件,及原《德国法院组织法》中16种家事事件,被悉数纳入其中[25]。因此,《德国法院组织法》同步删除原有条款,《德国民事诉讼法》也同步删除原“第六编 家事事件程序”[26]。这彻底宣告,由《德国民事诉讼法》分离而来的“家事诉讼程序”,最终汇入2009年《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现行之“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正式启用。
(二) 创制非讼化之一元统合体例
为化解家事程序危机,2009年《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的第二项历史性改变则是:彻底抛弃“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激进创制“非讼化之一元统合体例”。
所谓“非讼化之一元统合体例”,即以“家事诉讼程序”与《德国民事诉讼法》分离为前提,以“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非讼事件程序”及“传统民(商)事非讼事件程序”的结合为通道,以《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为外化载体,以“一元化之非讼性程序规则”体系为内在本质的立法体例。具言之,所谓“一元化”,是指其为“家事诉讼事件”“家事非讼事件”和“传统民(商)事非讼事件”统一配置一套程序。所谓“非讼性”,则是指该套程序规则体系设计颠覆“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传统逻辑,而开创“非讼性一元统合”全新法理,其虽仍以现代非讼程序三项基本立场为根基,但又适度修正以兼容诉讼程序法理:第一,弱化“单方程序进程逻辑”以兼容“两造对抗程序构造”;第二,弱化“职权探知主义”以兼容“协力证明”;第三,弱化“职权进行主义”以兼容“程序权利保障原理”[27]。
四、 家事程序单行立法体例的“德系”扩张与三分格局
德国家事程序的立法演变,主导“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的现代趋势,间接促成日本“分立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的缔造,直接引领我国台湾地区“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的诞生。因此,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例,成为现代家事程序立法之“德系”演变的扩张性组分。它们与德国法例,共同塑成家事程序单行立法体例的三分格局。
(一) 日本分立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
日本法的现代化因循德国法的步伐,但两国民事诉讼立法差异巨大。《德国民事诉讼法》秉承“一体化”逻辑,而1890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后却渐入“分散化”传统:自1951年《日本民事调停法》,至1979年《日本民事执行法》,再到1989年《日本民事保全法》,甚至1996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将原“第七编 公示催告程序”和“第八编 仲裁程序”也分离为单行立法[28]。
秉承“一体化”逻辑,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单列第六编确立“家事诉讼程序”而初定“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迈向“分散化”传统,1890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却以“身份关系诉讼与财产关系诉讼的本质差异”为由拒设该编,并在1898年单行制定《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该法涵盖“婚姻”“收养”和“亲子”案件而确立“家事诉讼程序”,(10)因而,日本法称“家事诉讼案件”为“人事诉讼事件”。从而先于德国转向“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但此时还只是“准”单行立法模式,因“家事程序”在广义上涵盖“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而该法仅及于“家事诉讼案件”,“家事非讼事件”仍于《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与“民(商)事非讼事件”共用一套程序。(11)1898年《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以《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为蓝本,仅第15条来自法国法。
1947年《日本家事审判法》终结这种状态。该法含“总则、审判、调停、罚则”四章,于第9条将“家事非讼事件”分为甲、乙两类,实质涵盖两个来源:第一,本属《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但基于简易、快速审判之目标而被“非讼化”的部分家事诉讼案件;第二,本属《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但基于家事法院统一管辖之目标迁移来的传统家事非讼事件。(12)因而,日本法称“家事非讼案件”为“家事审判事件”。《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则同步废除“第二编 民事非讼事件”原第六至八章,“家事非讼事件”与传统“民(商)事非讼事件”宣告分离。为厘定两者间关系,《日本家事审判法》第7条明确其与《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之“特殊法与一般法”的适用逻辑。[29]至此,“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分由《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和《日本家事审判法》调整,日本彻底转向“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并缔造了“分立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
2003年《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系统修改,虽更名《日本人事诉讼法》并有大幅改动,且将管辖权统一由地方法院移至家事法院,但人事(家事)诉讼案件仍由婚姻、亲子和收养关系三大类构成[30]。故其功能定位没有改变,就“家事诉讼程序”完全延续“单行立法模式”。之后,2011年《日本家事审判法》也完成系统修改,更名《日本家事事件程序法》,其内在系统和自足性显著提升。新法仍将“家事非讼事件”分为两类,只是由甲、乙改称表一、表二,并以是否适用“调停”作为区分标准。其功能定位亦无改变,就“家事非讼程序”完全延续“单行立法模式”。这意味着,“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之下,“分立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由两部立法延续至今。
综上,所谓日本“分立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即以“家事诉讼程序”及“家事非讼程序”与“传统民(商)事非讼程序”的分离为前提,以《日本人事诉讼法》和《日本家事事件程序法》为外化载体,以“诉讼与非讼分立并行之程序规则”体系为内在本质的立法体例。“分立”,是指“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非讼程序”分属于两部单行立法;“并行”,是指两套程序并列施行而无位阶差异。另外,缘于近代殖民统治,韩国承袭日本民事程序立法体系,在1991年《韩国家事诉讼法》之前,亦分置“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于《韩国人事诉讼法》和《韩国家事审判法》中,近乎日本体例的“刻版”[31]。
(二) 我国台湾地区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
最初我国台湾地区的家事程序近乎德国立法的翻版,亦属“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模式”下之“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后来《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直接引领其2012年“家事事件法”转向“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并缔造“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
我国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的现代化因循经日本法修正后之德国法步伐,其民事诉讼立法则与两国形成“交错类似状态”——既借鉴“分散化”传统制定1940年“强制执行法”,又秉承“一体化”逻辑而于1930年“民事诉讼法”自始单列“第九编 人事诉讼程序”。该编以“人事诉讼”之名确立“家事诉讼程序”,标志我国台湾地区开启对德国早期“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模式”的模拟。但因广义之“家事程序”涵盖“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由《德国民事诉讼法》原第六编和《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共同支撑,故而模拟才开始“1/2”。后来使这种模拟走向完整的是我国台湾地区“非讼事件法”。1964年该规定初定之时,采“二元分类”逻辑,以区分“民事非讼事件”(第二章)和“商事非讼事件”(第三章)。但其第二章当中的“第五节 监护及收养事件”和“第六节 继承事件”,本属“家事非讼事件”。2005年该规定修订选择了“(传统)诉讼事件非讼化”的目标[32],包含对《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之“诉讼事件非讼化”传统的借鉴[33],并且将“家事事件”集中于“亲权、监护事件”领域[34],而将“亲权变更”事项统一划归“非讼程序”范畴[35]。修改之后,该规定转采“三元分类”的逻辑,明确区分“民事非讼事件”(第二章)、“家事非讼事件”(第四章)和“商事非讼事件”(第五章),正式以专章系统规定“家事非讼程序”。至此,对“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模式”的模拟完成,近乎翻版的“家事诉讼与非讼二元分化体例”宣告确立。
但仅4年之后,《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就转采“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并创制“非讼化之一元统合体例”。我国台湾地区再次选择跟随德国步伐,2012年“家事事件法”亦转向“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但其未照搬德国“非讼化之一元统合体例”,而是缔造了“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36]。该规定首条即确立“妥适、迅速、统合处理家事事件”的立法目标[37]。所谓“统合”,即于统一程序中合并审处基础事实相关联之“家事诉讼事件”和“家事非讼事件”,以统一家事审判职权、确保程序推进并避免矛盾裁判[38]。为此,该规定并设“第三编 家事诉讼程序”与“第四编 家事非讼程序”,以全面取代“民事诉讼法”原“第九编 人事诉讼程序”和“非讼事件法”原“第四章 家事非讼事件”。(13)二者均于2013年5月8日立法修改时删除。为了区分两编的适用对象,该规定先于第3条据“讼争强度、处分权限和裁量权限差异”将家事事件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进于第37条规定甲、乙、丙类事件适用第三编,并于第74条规定丁、戊类事件适用第四编。至此,我国台湾地区置“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于统一立法中“并立协行”,从而缔造“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
综上,所谓“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即以“家事诉讼程序”及“家事非讼程序”与“传统民(商)事非讼程序”分离为前提,以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为外化载体,以“诉讼与非讼并立协行之程序规则”体系为内在本质的立法体例。“并立”,是指“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非讼程序”并属同一单行法;“协行”,是指两套程序协力运行以统合处理家事事件。另外,1991年《韩国家事诉讼法》(2016年1月19日修正)亦并设“第二编 家事诉讼案件程序”和“第三编 家事非讼案件程序”,从而全面取代《韩国人事诉讼法》和《韩国家事审判法》,彻底抛弃其早期“刻版”之日本体例。
五、 我国家事程序立法的现实迫切需求与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改革提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命题,预见了《民法典》对家事法律体系构造的历史性选择。《民法典》之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的有效施行,提出了更加迫切的家事程序立法需求。欲加速推动其立法进程,首先要立足现代家事程序立法模式的转向趋势而理性取舍其单行立法体例。
(一) 《民法典》施行的家事程序立法需求
综观域外法例,家事法律体系构造存在显著法系分野。英美法系,以完备判例系统支撑法律体系构造,其民商法偏好“实体与程序立体结合”的制度逻辑,“家事法”(Family Law)普呈“实体与程序一体分阶”的体系构造[39]。所谓“实体与程序一体”,即其家事立法普遍选择立体结合逻辑而同时设定实体和程序两类制度规范。所谓“实体与程序分阶”,即其家事法在文本体系上普遍采用二阶构造,含“议会直接立法”和“立法授权规范”两类效力层阶不同的文本,分别主导实体和程序制度规范的设定。(14)“议会直接立法”法理上统称“Statutes”,文本命名统一为“Act”;“立法授权规范”则是基于立法或议会授权而由立法(司法)改革委员会、内阁,及司法部制定的,法理上统称“Statutory Instruments”或“Legislative Instruments/Statutory Rules”,文本命名则包括“Rules”“Regulations”和“Order”三种形态。因此,英美法系家事法虽有两种基本模式,但无论是区分家事案件类型而分散制定单行立法的“多元分散立法模式”,(15)英美法系家事法的传统主流模式。还是汇编早期单行文本而形成统一立法的“汇编统一立法模式”,(16)澳大利亚以1975年《家事法》(Family Law Act 1975)和1984年《家事法条例》(Family Law Regulations 1984)为标志,基本完成这种模式转换。抑或由“多元分散”向“汇编统一”过渡的英国家事法,(17)其突出标志是英国2010年《家事诉讼规则》(Family Procedure Rules 2010)。均一体融汇两类规范于“议会直接立法”和“立法授权规范”中,而未形成现代家事程序专门立法。大陆法系,以完备法典系统支撑法律体系构造,贯彻“实体与程序二元并立”制度逻辑,塑成“民(商)法典”与“民事诉讼(非讼程序)法典”二元并立格局,其家事法统采“实体与程序分立并行”的体系构造。所谓“实体与程序分立”,即分置家事实体和程序制度规范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中;所谓“实体与程序并行”,即两类制度规范虽文本渊源不同但并无效力阶差。由此,现代家事程序专门立法得以缔造。
我国自20世纪中期,婚姻家庭法虽因单行化而逐步分散,但绝非英美之“多元分散立法模式”。因其既不奉行“实体与程序立体结合”的制度逻辑,也未采用“实体与程序一体分阶”的体系构造,而是在将家事实体制度规范置于分散化单行立法中的同时,援引《民事诉讼法》中的“通常审判程序”。所以,其自始隐性采用“实体与程序二元并立”的制度逻辑,并潜在酝酿“实体与程序分立并行”的体系构造。(18)因而,我国学界通常并列看待“分散化家事实体法的完善”和“专门性家事程序法的制定”。延至21世纪的“民法典”编纂[40],不仅早已明确家事实体制度规范以专编入典的格局,而且必须以自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即确立之“实体与程序二元并立”的制度逻辑为基本前提。2020年5月28日审议通过的《民法典》(2021年1月1日施行),最终选择专设“第五编 婚姻家庭”(19)涵盖“婚姻”(“第二章 结婚”和“第四章 离婚”)、“家庭”(“第三章 家庭关系”)和“收养”(“第五章 收养”)。和“第六编 继承”,以系统规定家事实体法律制度规范,根本标志我国家事法正式采用“实体与程序分立并行”的体系构造。其有效施行对未来家事程序专门立法提出更为迫切的需求[41],然而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历次修改并未触及这一问题[42]。
(二) 未来之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模式选择
我国当下,虽就推进家事程序专门立法渐成共识,但对未来立法模式的选择却不无争议。争议根源自对“家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之立法逻辑关系的不同定位,始现于学术领域,延伸至实务领域。学术领域,早有观点主张模仿《日本人事诉讼法》而就“家事诉讼程序”单独立法,但非严格之“家事程序单行立法”,因广义“家事程序”涵盖“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而该观点忽略后者[43]。后来学界提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概念,但或立足现行《民事诉讼法》而影射“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立场[44],或考量广义民事诉讼立法体系而将其解读为“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45]。眼下主流是狭义定位“民事程序”概念以剥离“家事程序”范畴而选择“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甚至有学者提出“《家事诉讼法》建议稿和立法理由书”[46]。实务领域,家事审判改革虽正式提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命题并作为远景目标,但对未来立法模式的选择立场亦不明确。因恰如学界解读“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概念时的分歧,它作为立法命题的内涵亦不清晰:既可理解为从属于《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也可理解为剥离于《民事诉讼法》之外的“特别程序”。
本文认为,选择“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的观点渐成主流并且被实质展开,绝非偶然现象而是现代趋势。因为,虽然法国、意大利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法例仍以广义“民事程序”涵摄“家事程序”而延用“合一立法模式”,但随2009年《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和我国台湾地区2012年“家事事件法”转采,由1898年《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和1947年《日本家事审判法》创延至今的“单行立法模式”已成现代主流。而且较于“合一立法模式”,我国采此模式更有如下两大优势。
第一,对民事诉讼立法系统化程度的要求更低,更符合我国立法的客观状态和未来需求。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经数次修改,但程序单一和平面化的不足未获实质改善。2007年和2012年修改前后,学界虽强烈呼吁立足“程序分化(类)”理念推进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但因终未触及强制执行程序、非讼程序和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等,程序分化(类)的理论设想总体落空。2017年的修改,仅止于第55条增加第2款以确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2021年的修改,在司法实践之功利需求的裹挟下,仅限于对既有之“通常审判程序”的制度性简化。而且,在此期间,关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立法的主导立场明确转向单行立法模式。这意味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因体系粗疏而缺乏对新定特别程序的吸纳能力,欲效仿“合一立法”模式而将家事案件特别程序融入其中,需要对现有体系构架的颠覆性改造甚至重构,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而选择“单行立法”模式,可在不触及现有体系构架的前提下而加速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进程,这也正是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法例于2009年和2012年分别相继转采“单行立法”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更贴近我国没有非讼程序立法传统的尴尬现实,易解决“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的立法关系定位问题。我国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缺失,迫使家事案件一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而家事审判对诉讼属性之“通常审判程序”的全面援引,则源于“非讼程序”的立法简化。我国至今无“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民事诉讼法》“第十五、十七、十八章”也限于粗疏特别规定,并未形成统一性非讼程序轨道。虽宣告失踪(死亡)和行为能力认定等家事案件为“第十五章”涵盖而应“直接”适用特别程序,也有司法解释规定代管人变更、监护资格变更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家事案件应“比照”特别程序审理。但因“第十五章”之“第二节至第七节”针对特类案件的特别规定难以“比照”适用于上述案件,其“第一节 一般规定”对适用范围、一审终审、审判组织、程序终结、另诉和审限等的粗略规定也不足以提供一般性规则支撑,且其第177条明确“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所以,名为“直接”或“比照”适用特别程序的前述家事案件,最终也实质性援引诉讼属性之“通常审判程序”。而“合一立法”模式虽有“诉讼与非讼合一”和“诉讼与非讼分化”两种立法体例,但均以“非讼程序”的系统设定为前提,才得以妥当解决“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的关系定位问题。不同在于:前者采“一典双层”的文本构造,以广义民事程序涵摄非讼事件程序,于“民事诉讼法”专设编、章建立非讼事件程序规则体系;后者采“两典单层”的文本构造,由民事诉讼程序剥离非讼事件程序,制定“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这意味着;我国缺乏非讼程序的立法传统和制度积淀,欲效仿“合一立法”并妥当定位“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间的关系,须系统化重构《民事诉讼法》中的“非讼程序”或制定“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该任务同样过于艰巨;而选择“单行立法”模式,更易在“非讼程序”超简化的窘境下妥当解决“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的立法关系定位问题。
(三) 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下的体例取舍
选择“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的主流立场下,我国学界对“家事程序单行立法体例”问题的研讨尚未实质展开,改革提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命题时也未涉及。这根源于对“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之立法逻辑关系定位问题的忽视,又凸显为“家事非讼程序”之系统性研究的缺位。早期对广义“非讼程序”的研究,虽间接提及“家事非讼程序”,但不过只言片语。晚近对广义“家事程序”的研究,虽应直接涵盖“家事非讼程序”,但也多止于一笔带过,或茫然慨叹“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搭乘商事诉讼主导之改革”的尴尬现状,或粗略构想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以涵盖“家事非讼事件”,或抽象探寻“家事诉讼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47]。宏观背景如此,少数文献能单设标题简述“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的关系”实属难能可贵[48]。所幸,眼下有开明学者立足“单行立法”模式提出“《家事诉讼法》建议稿”时,选择并设“家事诉讼程序”(第二章)和“家事非讼程序”(第三章),以隐性模拟“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然而遗憾的是,在其“立法理由书”中,既未系统论证两者间的立法逻辑关系,也未同步配置家事案件合并审判规则以确保两者“协力运行”。
本文认为,学界提出的《家事诉讼法》建议稿隐性模拟“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虽未经系统考量,但却是正当取舍。其理由有三。
第一,恪守“二元分化”法理而使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分立并行”的“分立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以德国开创之“民事诉讼法+非讼事件程序法”的二元立法格局为逻辑基础,以日本特有之民事诉讼“分散化”单行立法传统为生存土壤,难以融入我国现有立法格局,且早已为1991年《韩国家事诉讼法》所抛弃。正因沿袭二元立法格局,1890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后,1898年《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得以制定并涵盖“家事非讼事件”与传统“民(商)事非讼事件”;正因开辟“分散化”立法传统,1898年《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确立“家事诉讼程序”之后,1947年《日本家事审判法》又从《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中分离出“家事非讼程序”,“分立并行”的程序构造得以形成。此后,日本“分散化”单行立法传统延展一百余年,《日本民事诉讼法》逐步狭义化为“民(商)事诉讼案件审判程序”[49]。这样,在2003年《日本人事诉讼法》和2011年《日本家事事件程序法》的支撑下,“分立并行”的程序构造才得以延用至今。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一元孤立,缺失“非讼事件程序单行法”,更未形成“分散化”立法传统。
第二,激进化开创“一元统合”法理而将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整合为“一元化之非讼性”程序的“非讼化之一元统合体例”,本质是二元立法格局之下对原《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的系统升级,以“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的深厚积淀为历史基础,需要现代“非讼程序法理”与“诉讼程序法理”的系统兼容,无法为我国未来的“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所采用。正因原《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和《德国民事诉讼法》共同支撑的“二元分化”家事程序遭遇深度危机,《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修订才于2002年重启,并提出“为所有非讼事件构建一元化程序”的任务;正是通过对现代“非讼程序法理”与“诉讼程序法理”的系统兼容,2009年《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才得以实现“家事事件审处程序全面非讼化”的目标。而我国不仅缺失“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民事诉讼法》中的“非讼程序”也超级简化,尚无“二元分化”的家事程序;而且学界对于“非讼程序法理”的研究才刚起步,尚不足为其与“诉讼程序法理”的系统兼容提供充分支撑。
第三,折中两种程序法理而令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并立协行”的“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本质上是突破二元立法格局的一种单行立法策略,它得益于我国台湾地区相对浅淡的“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历史基础,无须苛求现代“非讼程序法理”与“诉讼程序法理”的系统兼容,契合我国未来“家事程序单行立法”的需求,且早为1991年《韩国家事诉讼法》所转采。正因“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历史基础相对浅淡,我国台湾地区2012年转采“单行立法”模式,根本上是因循于德国立法经验的惯性,而非源于“二元分化”家事程序的深度危机,故既未选择“为所有非讼事件构建一元程序”的进路,也未采取系统升级原“非讼事件法”的方案,而是选择了单行制定“家事事件法”。所以,它既不奢望于“全面非讼化”,也未苛求“非讼程序法理”与“诉讼程序法理”的系统兼容,而是以“二元两级”的家事案件分类为立法编排的基本线索,并列设置“第三编 家事诉讼程序”与“第四编 家事非讼程序”,建立“双轨四层”的规则体系以确保两者协力运行,以期实现“统合处理家事事件”的制度目标。可见,作为兼容化修正结果的这种程序构造,既因突破二元立法格局而更加贴近于我国缺失“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的现实,又能避开系统兼容“非讼程序法理”与“诉讼程序法理”的难题而为我国“非讼程序法理”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窗口期限[1]。
六、 结 语
我国推动家事程序立法进程任重道远,尚处理论积累和改革探索的初级阶段。本文基于改革提出之“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立法命题,回应《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的有效施行对于家事程序立法的迫切需求,探寻德国家事程序的立法演变规律,揭示现代家事程序转向“单行立法模式”的主流趋势,透视家事程序单行立法体例的三分格局,从而最终明确我国的单行模式立场和立法体例选择。立足于此,未来应遵循现代家事程序单行立法以案件类型为编排线索的主导规律,超越学界和改革所提出之“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概念表达,采用“家事案件特别程序法”的立法命名,据《民法典》实现“二元两级”的家事案件系统分类,并设“家事诉讼”和“家事非讼”两个程序轨道,建立“双轨四层”的审判规则体系,确保两个程序轨道协力运行,以统合审处家事案件。为此目标,提出表1之初步构想[1],以为本文之最终着落。

表1 我国未来“家事案件特别程序法”中审判规则体系的初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