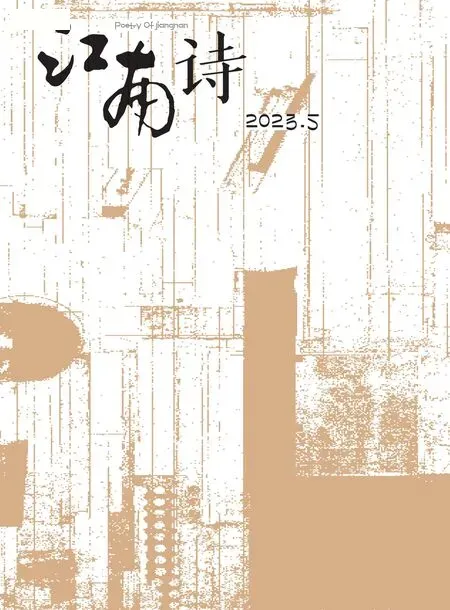诗与遗忘的途中
◎张雪萌
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将下笔的诗歌视为一首首的“道中作”。
“道中”,占据着某种物理层面的意味。去年来到英国,地理意义上的远游,更是加重了这一层确信。
我们基于不同的衡量尺度来谈论旅行的有效。一座城市,在朋友圈的镜头中留下吉光片羽式的映像,似乎是最便携的纪念品,也作为“是的,我曾经到往过那里”的证明。桑塔格谈到,照片实际上是被捕捉到的经验。可那些逃逸于捕捉之外的,又为人所切身经历的事物,这些沉寂的、未被析出的经验,又被打扫进了哪些角落?
我时常感到与外地之间相互凝视的关系——我观测经验之外的异域情调,而异域也在打量我,一个外来者的隐微的不安。这种龃龉不断催促着行人驶向别处,而高度差异化的经验,往往在来不及被记忆存留前,便延伸向新的遗忘的途中。
几乎像一种庇佑,作为写作者,尚有诗歌,可以满足旅客收集癖的私心。
回顾并点数历往的写作,每一首诗歌像一处锚点,标定着瞬时的惊异。途中的见闻,早已下潜到记忆的深水区,然而对文本的重新进入,都引领你再一次返回,并触摸、闻嗅到世界曾经表露出的知觉。我仍然记得2021年初,在深夜时分的广州南站,候车大厅天花板的吊灯,在人潮褪去后,开始重新夺回空气中光亮的体积,那是属于《车站》这首诗的场景;去年年底,在回剑桥路上的无数火车站台,电子告示牌上金黄色的列车到站讯息,闪烁在冬日的寒雾里,那股鼻腔里的冷意,再一次袭来,每当我读到《夜晚,谢菲尔德》的时候。
2023年,我的诗歌由大量的叙事与戏剧化写作,转向对生活经验本身的测定,在《墓园》《克莱尔》中,这样的尝试多少带着印象派的怀旧,即对于暂时性和转瞬之感的刻意保留。尽管,十分清楚的,在这些努力背后,是行人身份下无法摆脱的焦虑。
二
今年4月,旅行途中和两年未见的朋友在斯特拉斯堡小聚。再次开启的谈话,让我越来越担忧自己趋向模糊的记忆。说起的那些人、事、物,借由他的重提,我才意识到自己几乎让渡了对许多回忆的保管权(反而,我的朋友们大多成为了我们共享回忆的守门人)。如贝恩所写那样:
……但每天有很多经过你身边,
推广过,外向型的,
存在主义的担心,夫妻的争斗,税务问题
所有这些你自己都不关注,
一大堆五花八门形式的人生
事实上,对于生活中大量细节的遗忘,我又乐于持有一种悠游无谓的态度,这似乎是对于连贯的写作习惯帮助看守记忆的盲目乐观。在经由语言再造的现实,和真正的现实之间的孰轻孰重,过分倚重前者,也多少夹带着些狂妄的天真。在这一点上,我又与那些绝望的摄影师们没什么不同。
三
诗的形式暗示我们,它曾诞生于对遗忘的恐惧之中。一个韵母首先是其自身,它被下一个偶然的发音所找到,如果不是“a”,那就继续调整发音的位置,直到讲述间隙的停顿,开始对上一处作出回应。韵由是诞生,并以规律的形式,在游吟者和说书人之间显露,以抵抗口耳相传带来的记忆必要的磨损。
自此,诗与时间达成合作。自觉或不自觉地面向遗忘,诗歌是我们在海岸行走,沿途弯腰扎下的作为路标的石子。然而,像斯特兰德所言,它只赞美或赏识处于消逝之中的语气,思想和事件。即使当诗歌称许欢乐,它也携带着那欢乐已经结束的消息。潮浪将那些石子卷入海底,持续的牵引作用对你做出来自未来的许诺:那些路标并未真正消失。但人并非海浪,在有死性的预言下,写作是重复这样弯腰、标记、起身的姿势。
不仅是写这一动作涵盖了如此无尽的遗忘,关于遗忘的诗歌主题也何其之多。诗人擅长在遗忘的内部把握遗忘,一首歌在奏响第一个音符时便注定逸散在空气中。诗人言说,仿佛是在回忆,但如果他在回忆,那也是用遗忘来回忆,布朗肖如是说。
四
诗写的过程围绕被筛选和析出的经验展开,以一种主动遗忘的姿态面对被动遗忘的必然。
如此说来,遗忘是最精巧的剪辑师,胜过它任何的同行。甚至,像卡达莱在《H档案》中所述那样,它属于创意的构成部分。没人知道这样的去芜存菁按照何种机制,它的偶发不断构成意外和意外之间的原创。
不应以悲观作为遗忘的底色。有的诗歌追缅遗忘,为遗忘摘下帽子,许诺读者静默的一分钟阅读。在这屏息的写与读之中,我们无意来到内部时间的场所,并与外在流动的时间的重量相分离。诗歌以内聚性的凝记,为摆脱现世的遗忘赋予一种轻盈。阅读一首关于遗忘的诗歌,使我们所经历的遗忘变得美丽。
五
我不懂人们为什么还在谴责集体的遗忘,好像那并非流淌在我们体内的天性。
我并不需要为写作,为当代处境下的诗歌,施以某种崇高的招魂术,言必提及“救赎”“见证”,或“再造现实”,好像诗歌以战胜遗忘为傲,并对人类文明与历史负过高的责任。我想,更准确来说,诗歌从不应以一己之任对抗业已弥散的生存危机,并且,任何言之凿凿宣称诗歌对这一切应负最大责任的口号,仍是高蹈至可疑的。
文学史是进入诗歌的视角,但只是其一。著史者所处理的是人们面对遗忘时的某一特定情感,但并非全部。还打算伸出它的食指,为后来者说教些什么的诗歌是幼稚的:它既不对诗歌长期以来的存续与生机保有信心,又将那些非诗性的特质掩过自身。
六
哪怕是自己所写下的同一首诗,每次的返回带来不一样的心境。我们从遗忘不同长度的坐标走向那首年轻时写下的诗。
遗忘丰富人们玩味故我的审美。再次阅读时,我被再次带往诗诞生时的混沌,尽管这样的情感已非为我所有许久。借助遗忘,一首诗的生成性也是可以被这样诠释的:多年前栽植的树木,从未因我们的远去暂停它的生长。我们无法从以秒分、时日计算的线性日常中感知到差异,但却在几年后,一次对诗稿的整理中,你抬起头,发现不知何时被它如此繁茂的树荫所覆盖。
七
遗忘的诗歌没有表情,甚至没有一张完整的脸。那是一张嘴唇,紧绷着,试图抑制住即将泄露的叹息。
八
“四月十二号,朋友们去红海潜水,我留在住处,赫尔格达的临海民宿里。
这个区域接近任何一个旅游城市中成片分布的度假庄园,白色墙壁、带有泳池的独栋小别墅,毗邻又分散彼此。赫尔格达占有的红海海岸线一带,大多平整直畅,但在El Gouna附近,却显得破碎支离,不知道是否因为人工填出才呈现出这样的景致。下午三点的阳光仍然毒辣,像冶金的巧匠,把金属的颜色泼洒在碧色的海面。隔着一片小沙滩的围挡,院子内的泳池则是天蓝色的,从院子向不远处望去,两片水域,像是工匠在大地的面板上淬出的异色玻璃制品。强劲的热风从西边吹来,坐在遮阳伞下读书,喝薄荷茶,不一会儿便被那种暖融的波动包裹得昏昏沉沉。
M回来了。她擦着被海水打湿的发绺,我们聊着近况。谈到了什么,她突然停顿一阵,严肃对我说:‘你总是这样忘性大,疏于细节。’
整理笔记时,我读到年初写下的不成段的散文。关于忘性这一点,我们没有进一步探讨。我还记得M擦拭身上水渍的样子:那些在蒸发下,逐渐结晶的、小小的海水颗粒。我没有提起,诗歌于我,作为另一种结晶的方式。真的,“它以结晶存在于我们手中难以理解”,丽泽·穆勒将爱比作盐,而诗歌又未尝不是以这样的形式保存着。
讽刺的是,如果没有这段笔记,我几乎又要将我们的谈话,还有那旅途中的住所遗忘。
九
多擅长教人记住的时代:记住生日,记住结婚纪念日,记住登录密码,记住企业秋招,记住单词和高效学习法,记住这条帮你少走弯路的人生哲理。
我不需要在此之中多写下一首教诲自己与他人记住的诗歌。如果只是将一首诗作为一件备忘簿,我想我的写作还不足够勇敢。我更应该拥有那样的决心,从写下第一行时,便将它从风中递送出去,抱定它朝向遗忘的力和飞行。我欣喜它挣脱固定的任何可能。“用遗忘来回忆”,我想,如果那是写作与诗歌“真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