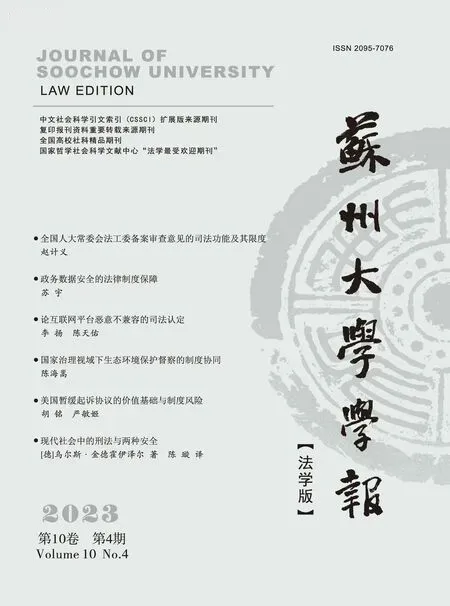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的本土化构建
——以“1元索赔案”为切入点
黄禄斌
一、引言
近年来,“1元索赔案”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然而,与以往司法裁判(1)陆耀东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5期。所不同的是,部分裁判对于1元损失赔偿的诉讼请求给予肯定。此番态度的转变,是否直接意味着法院承认了英美法中的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此问题虽仍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就社会效果而言,此类案件对于增强权利意识助益颇巨。正如德国学者耶林(Jhering)所言:“进行诉讼的目的,不在于微不足取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理想目的。”(2)[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换言之,积极维权的目的并非在于金钱赔偿,而在于私权利的保护与是非感的弥补。因此,对“1元索赔案”之肯定不仅不是廉价的救济、司法资源的浪费,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对于不法行为的零容忍,是他们为权利而斗争的有力印证,这现象令吾辈深感欣喜。当然,我们仍需对此种现象在法律层面上进行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1元索赔案”分为两种类型:一为1元财产损失赔偿;一为1元精神损失赔偿。前者例如在“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李杰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被告用虚假、欺诈手段向原告申报不真实的非授权支付损失赔偿金额,违反双方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约定。法院认为,要剔除被告的过错行为,必然造成人力、物力的耗费,存在损失。该损失虽在法律层面难以精确量化而予以确定,但出于警示、教育等目的,应当支持原告所主张的1元财产损失赔偿。(3)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7613号民事判决书。后者例如在“许昌市惠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昌金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中,被告粘贴“敬告书”的行为侵害原告的名誉权。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1元精神损失金额具有象征性,结合侵权的具体情形,应予以支持。(4)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0民终4127号民事判决书。
基于上述案件的判决理由,不禁让人产生思考的问题是,1元财产损失赔偿与1元精神损失赔偿是否皆属于英美法上的象征性损害赔偿?1元损失赔偿在损害赔偿法领域属于何种性质?此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法上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拟以中国司法实践中的“1元索赔案”为切入点,辅以法教义学方式剖析英美法中的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进而探讨在我国法上确立该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应如何构建该制度。
二、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内涵及其重构
(一)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内涵与外延
1.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内涵
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滥觞于英国普通法。在1703年的Aschbyv.White案中,英国大法官霍尔特(Holt)提出一项重要原则:尽管行为未造成财产损失(injuria sine damno),法律亦推定该侵害行为造成损害。(5)Aschby v. White, (1703) 92 ER 126.随后在1770年的Goodtitlev.Tombs案中,首次出现象征性损害赔偿概念。法院认为,一旦诉讼本身被认为是恢复原状的手段,受害人则可以另外请求象征性损害赔偿。(6)Goodtitle v. Tombs, (1770) 3 Wilson 118, 120; 95 ER 965, 967.自此,当一个案件处于维持诉因与获得金钱赔偿两个不同标准之间时,英国法院通常会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象征性损害赔偿金。(7)See Sadie Blanchard, Nominal Damages as Vindication, Geo. Mason Law Review, Vol. 30, No. 1, 2022, pp. 233-234.此制度多为普通法系国家所采纳,但以美国法最为发达,影响最大。
象征性损害赔偿(nominal damages),又称名义上的损害赔偿,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无实质性的损失,或者受有损失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具体数额,尽管如此法律仍然承认原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被告违反了对原告的义务,此时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支付一笔极少数额的损害赔偿金。(8)See Byran A. Garner e.d., 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9th ed., 2009, p. 447.然而,该项赔偿金仅为法院承认被告侵犯原告合法权利的一种象征或者标志。(9)See Howard L. Oleck, Cases on Damages, Bobbs-Merrill Co., 1962, p. 27.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07条规定:“象征性损害赔偿是判予已确立诉因但未能明确其有权获得补偿性损害赔偿的诉讼当事人的一笔数额微小的钱款。”(10)[美]美国法律研究院:《侵权法重述第二版:条文部分》,许传玺等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法上,象征性损害赔偿与蔑视性损害赔偿(contemptuous or derisory damages)存在一定的区别。后者是指法院认为某案件无须起诉,即使起诉亦仅会获得微额赔偿金的情形,(11)See Andrew Burrows, Remedies for Torts, Breach of Contract, and Equitable Wrongs, Oxford, 4th ed., 2019, pp. 503-504.例如因擦肩而过受到碰撞而请求赔偿。此时的赔偿金被认为是蔑视性的,原因在于“轻微损害不予赔偿”(de minimis non curat lex),此亦称为“法律不理琐事”,是指行为人对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法益造成轻微不利益损害,由于该行为被道德、社会规范所容忍,故而不予赔偿。(12)“轻微损害不予赔偿”是从违法性的角度出发进行考量,因为造成损害的行为属于日常频繁发生的琐碎事件,虽造成轻微损害,但此应为一般社会观念所认可,是故予以免责。然而,有学者认为,在理论上二者容易区分而实践上却易于混淆。(13)See David Pearce, Roger Halson,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Compensation, Restitution and Vindication,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8, No. 1, 2008, p. 77.亦有学者认为,蔑视性损害赔偿属于象征性损害赔偿的一种特殊情形。(14)参见李永军、刘德志:《论英美法名义上的损害赔偿金》,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58页。虽然二者的赔偿金都属于微额,但实际上可以将权益侵害之严重程度作为标准对其进行明确区分。具言之,若仅因侵害微额利益之琐事而请求损害赔偿,则为蔑视性损害赔偿;若为已超出一般社会通常认知之严重程度的权益侵害事实而请求损害赔偿,则应为象征性损害赔偿。就我国法而言,基于轻微损害不予赔偿的理念,蔑视性损害赔偿不应被认可,因为轻微损害在日常生活中发生频繁,若将其作为赔偿客体,则势必导致司法成本和当事人维权成本大幅度攀升,不符合经济效率理念,且其亦有小题大做之嫌。我国《民法典》虽未明确将轻微损害规定为容忍义务的客体,但从物权编之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中可窥见一二。(15)参见贺茜:《轻微损害行为类型化再思考》,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67-68页。
2.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外延
由上述定义可知,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外延可分为两个子类:一是受害人权利受到侵害但无损害;二是受害人因权利侵害受有损害但损害程度无法得到确定性证明。第一种类型例如在Abramsv.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案中,非工会成员的雇员对工会提起诉讼,声称工会收取代理费的行为违反了公平代表义务。法院认为,虽然工会未能通知雇员有权反对全额支付费用的行为侵害雇员的自主选择权,但是雇员没有受到任何实际损害,换言之,该侵害只是程序上的(procedural)而非金钱上的(pecuniary),故而只能判予其象征性损害赔偿金。(16)Abrams v. 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 AFL-CIO, 23 F.Supp.2d 47, 51(D. Col. 1998).第二种类型例如在Ondine Shipping Corp.v.Cataldo案中,作为船舶所有权人的原告起诉被告承揽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声称被告在其未授权的情形下对船舶进行不当改装并且修理过程中存在过错。法院认为,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损失数额,故而仅能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象征性损害赔偿金。(17)Ondine Shipping Corp. v. Cataldo, 24 F.3d 353, 356(1st Cir. 1994).第二种类型的形成根源在于损害数额的证明责任上。根据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912条的规定可知,受害人须对损害数额进行确定性证明才可获得补偿性损害赔偿。因此,若损害数额无法得到确定性证明,则受害人仅能获得象征性损害赔偿。
(二)象征性损害赔偿内涵的重构
象征性损害赔偿在两种情形下适用:一为无实际损害;一为有实际损害但无法证明其具体数额。第一种类型属于纯粹实体法上的问题,其仅能通过法教义学方式进行分析判断。而第二种类型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上的意义,它涉及的是损害确定性及证明责任的问题。因此,可从程序法角度对“未能证明损害赔偿数额”(fails to prove the amount of damages)的情形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其可否通过其他制度予以解决。对此,可将未能证明损害数额的情形具体分为两种子类型:(1)已提交基础证据但未能证明损害数额;(2)未提交基础证据。
1.已提交基础证据但未能证明损害数额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规则,受害人应当就损害的存在以及损失的大小等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若受害人仅能证明损害的存在,但无法证明损害的数额,则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然而,若损害的存在已经获得确认,仅因受害人不能证明损害具体程度而驳回其赔偿请求则与权利保护原则相违背。因此,基于实质公平的考量,近年来我国学者都建议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第1项的规定建立损害额酌定(Schadensschätzung)制度,即在损害赔偿诉讼中,若已然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但原告难以证明或无法证明具体损失数额时,法官应当考量案件的全貌,对该损害赔偿额作出裁量。(18)参见刘学在、阮崇翔:《论损害赔偿额之酌定时的举证责任减轻》,载《河北法学》2019年第8期,第45-47页;王磊:《论损害额酌定制度》,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6期,第113-117页。《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的规范目的即通过降低若干待证事实的证明度要求,从而预防权利人因程序上的要求而无法实现合理的损害赔偿请求权。(19)Vgl. MüKoZPO/Prütting, 6. Aufl., 2020, ZPO § 287 Rn. 1.多数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建立了损害额酌定制度。(20)《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1款;《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48条;《意大利民法典》第2056条;《瑞士债法典》第42条;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款。此外,作为国际示范法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亦有此规定。PICC7.4.3条第3项规定,若损害赔偿的数额无法足够确定证明时,应由法院依职权进行裁量。该项规定亦表明当损害赔偿额不具有确定性时,不作拒绝任何赔偿,法院有权就认可的损害做合理的量化。由此可知,旨在维护实质公平的损害额酌定制度已成为国际趋势。
当然,对于损害额酌定制度到底属于程序法范畴还是实体法范畴尚有争议。此为“证明度减轻说”与“裁量性评价说”之分野,但多数学者认为其兼具两种规范性质。(21)“证明度减轻说”是将损害额认定作为事实问题的程序法范畴。“裁量性评价说”认为损害额认定包含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等实体法范畴。参见许士宦:《损害数额之酌定》,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1期,第78-80页;毋爱斌:《损害额认定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2期,第119页;黄毅:《损害赔偿额之酌定:基于诉讼公平的考量》,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4期,第149-150页。就此而言,虽然在我国无论是程序法抑或是实体法皆未对损害额酌定制度予以成文化,但我国学者经过检索判例认为司法实践中已广泛应用损害额酌定制度。因此,可以将《民法典》第1184条中的“其他合理方式”作为损害额酌定的规范基础。此方案不失为一项较为合适的解释路径,因为损害额酌定制度的兜底功能对《民法典》第1184条所发挥的量化损害功能可以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22)参见王磊:《财产损害算定的基本原理与规范内涵——〈民法典〉第1184条的解释论展开》,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第130-131页。当然,若采此解释路径,则在有实际损害但无证据证明具体数额时,法院无须求助于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因为通过损害额酌定制度认定损害更能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填补,此结果既符合《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目的,又能真正实现实质公平。例如上述在“支付宝索赔案”中,人力、物力等损失虽在法律层面难以精确量化而予以确定,但法院可通过原告提交的违法账户交易记录次数酌定财产损失的数额,此时的1元损失赔偿应属于处分原则(23)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这对法院的审判范围形成了约束。参见陈文曲:《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内在沟通逻辑》,载《法律科学》2022年第4期,第186-187页。下的财产损失赔偿,而非象征性损害赔偿。由此可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1元财产损失赔偿并非象征性损害赔偿,1元仅是在损害额赔偿制度下处分原则所导致的结果。
2.未能提交基础证据
由于损害额酌定制度未排除辩论主义的适用,(24)Vgl. MüKoZPO/Prütting, 6. Aufl., 2020, ZPO § 287 Rn. 14.因此,受害人仍有必要提出评估损害额的事实基础。若法院就损害额无法形成自由心证或欠缺任何损害额评估的基础事实材料,则仍须依据举证责任规则作出判决。换言之,若受害人对损害数额未能履行其基础举证义务,此时不应适用损害额酌定制度,而应将其视为无实际损害进而适用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例如在Yostv.Studer案中,受害人牙医因被告的过错侵权行为而死亡,其遗产管理人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赔偿牙医2周的收入损失,法院以原告未提交任何有关证据为由仅判决其享有象征性损害赔偿请求权。(25)Yost v. Studer, 302 S. W. 2d 775.
综上可知,由于未提交基础证据证明损害数额可视为未造成实际损害,因此,英美法上的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仅为未造成实际损害,其应当排除虽未证明损害数额但可适用损害额酌定的情形。
(三)象征性损害赔偿具体适用情形的限制
在美国,象征性损害赔偿大多适用于故意侵权案件中,具体包括:(1)侵犯宪法权利,例如隐私权;(2)人身侵害;(3)财产侵害;(4)公职人员违反职责;(5)欺诈。(26)See 22 Am. Jur. 2d Damages §8, Westlaw (database updated Feb. 2023).而就过失侵权而言,由于该诉讼类型以原告受有损害为诉因。因此,若原告无法证明自己受有损害,其无疑无法成功起诉。而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就是没有实际损害,因此,提起过失侵权诉讼的原告无法请求象征性损害赔偿。在违约之诉中,象征性损害赔偿并不十分常见,主要原因在于合同义务的违反通常伴有财产损失,通常在财产损失无法计算的情况下法院才会赋予守约方象征性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外,在违约与侵权的混合诉讼中以及合同欺诈情形,法院亦会判予象征性损害赔偿,而两者皆与侵权责任相关联。
由于在违约之诉中,当财产损失数额无法计算时,通常可以由损害额酌定制度予以解决。因此,总体而言,象征性损害赔偿应当在侵权责任范围内予以讨论。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若原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即可起诉。由此可知,在侵权之诉中,我国《民事诉讼法》并不区分故意侵权之诉与过失侵权之诉,进言之,我国法上并无英美法上的过失侵权之损害诉因桎梏。因此,若在我国法上承认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亦无须对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进行限制。
三、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
(一)象征性损害赔偿客体的性质
损害赔偿的客体是指法律予以救济之不利益。据此,有学者将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称为象征性损害,并认为其仅为程序法(尤其是诉讼法)领域的概念。(27)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江平、费安玲:《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李显东:《侵权责任法典型案例实务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亦有学者称之为“名义上损害”,参见王军:《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首先,将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认定为象征性损害并非妥适,因为英美法上仅有象征性损害赔偿的概念,“象征性”指的是赔偿而非损害。在英美法上,无论是补偿性损害赔偿抑或是惩罚性损害赔偿,补偿性或惩罚性皆指的是赔偿而非损害,而具体赔偿的是何种损害仍需进一步分析。其次,象征性损害赔偿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毋庸置疑,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实体法上的意义,二者并非矛盾关系,但其实体法上的意义仍需从其功能角度作进一步探讨。
在英美法上,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前提是未造成实际损害。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认为可以赋予受害人象征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原因却又在于:“权益侵害必然造成损害”(28)Uzuegbunam v. Preczewski, 141 S.Ct. 792, 800(2021).。二者看似存在矛盾,实际上仅是概念内涵理解上的差异。就前者而言,未造成的“损害”应指不存在法律上的损害,即可赔偿的损害;而就后者而言,造成的“损害”应指存在尚未经过价值判断的事实上的损害。(29)应当区分事实上的损害和法律上的损害,事实上的损害经由价值判断的过滤,走向法律上的损害,即个案中应予赔偿的损害。参见叶金强:《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第166-167页。显而易见,事实上的损害范围包含但不限于法律上的损害范围,两者重叠以外部分的不利益内容即为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由此可知,此不利益应属于不适格的损害。尽管如此,此不利益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美国学者及司法裁判人员并未对此加以进一步解释说明。
就分类而言,损害存在多种分类标准,其中最基本的标准是损害可否通过金钱进行计算,以此为标准可将损害分为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前者可通过金钱进行计算,而后者并无具体的财产价值,无法以金钱进行衡量。(30)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29页。然而,根据完全赔偿原则,财产损害皆具有可赔偿性,因其不属于不适格的损害故而非为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此外,有学者认为权益侵害亦属于广义的损害范畴。(31)参见李承亮、孙鸿亮:《一般侵权责任构成模式下“权益侵害”功能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43页。由此可知,对于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性质仅存在两种可能,进而产生两种学说,即“权益侵害说”与“精神损害说”(非财产损害说)。
1.权益侵害说
在英美法中,若名誉权受侵害且受害人无法证明实际损害时,根据推定损害赔偿理论(doctrine of presumed damages),受害人应当享有象征性损害赔偿请求权。此推定的损害(presumed damage)意味着权益侵害本身可被视为一种特殊损害形态,无须进一步证明存在实际损害。与该原则相类似的规定例如《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第VI-2:203条规定,人身权利受侵害时权益侵害本身(injury as such)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法律相关性的损害。根据DCFR第VI-6:204条的规定可知,侵害本身应得到赔偿,且该赔偿独立于财产损害赔偿与非财产损害赔偿。在注释中其进一步表明,侵害本身既不构成财产损害亦不构成非财产损害,其属于一种独立的损害类型。(32)See Christian v. Bar, 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Damage Caused to Another. Oxford, 2009, p. 986.有观点认为上述理解存在逻辑矛盾,因为损害可以分为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二者的区别在于能否以金钱进行衡量,已为周延的损害概念。然而,在DCFR中将侵害本身认定为一种损害,而又将其排除于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之外,明显存在逻辑错误。(33)See Helmut Koziol, Schadenersatzrecht and the Law of Torts: Different terms and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Journal of European Tort Law, Vol. 5, No. 3, 2014, p. 270.
实际上,DCFR注释中,所谓侵害本身不构成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其中的非财产损害应指狭义的精神损害。由于非财产损害的范围较之于精神损害更为宽泛,(34)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29-230页。故而导致此种误解产生。此在其论述过程可窥见一二,在论证侵害本身应作为一种损害时,冯·巴尔教授认为,此结论是受到意大利法上的生理损害(danno biologico)概念的影响。然而,在意大利法上,生理损害被认为是独立于财产损害、精神损害之外的非财产损害类型。(35)参见费安玲、陈汉:《罗马法与学说汇纂(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页。这里的精神损害被限定为符合《意大利民法典》第2059条的类型。因此,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侵害本身是独立于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的非财产损害类型。
尽管论证上不存在逻辑矛盾,但将权益侵害本身认为是损害的观点仍值得商榷。权益侵害与损害的界分在差额说理论下显然十分明确,但由于组织说(36)组织说将损害分为客体损害与财产结果损害,前者即为侵害事实本身。此学说仅是为了克服差额说无法解决假设因果关系等难题而人为构建,有割裂损害概念之嫌。的出现使二者的区别有稍许模糊,进而才得出损害包含权益侵害的结论。(37)参见李承亮、孙鸿亮:《一般侵权责任构成模式下“权益侵害”功能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43页。然而,在德国法上,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中,权益侵害本身是原因,损害是结果,二者存在明显区别。在英美法上,损害(damage)与侵害(injury)亦属不同的概念范畴。(38)Christian v. Bar, The Common European Law of Torts, Oxford,Vol. 2, 2000, p.14.就我国法而言,《民法典》亦是借鉴德国法,将权益侵害与损害严格区分。《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及第1183条皆表明是由权益侵害“造成”损害,此原因与结果明显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若将权益侵害等同于损害,则会混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与其他侵权责任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侵权责任不仅包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亦包括第1167条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预防性侵权责任,还包括第179条规定的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事后补救性责任。在责任成立时,后二者中除了恢复原状以外,其余的侵权责任皆只需存在权益侵害而无须以损害为要件。(39)侵权上的财产返还无实际必要,其功能实际上已为物权法上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消解。在侵权法上的财产返还中,大多数情况下,无权占有并非损害,仅为一种妨害。参见王洪亮:《原物返还请求权:物上请求权抑或侵权责任方式》,载《法学家》2014年第1期,第98页。以消除危险为例,其不以实际损害为要件,仅需侵害行为对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造成危险即可。
总而言之,不应将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认定为权益侵害,原因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其无法打破权益侵害与损害二分的结构形式,损害赔偿的客体应为损害,而权益侵害仅为损害的原因。前者为初始侵害,后者为结果损害,将权益侵害视为损害则混淆了二者在侵权法上所发挥的作用。第二,尽管冯·巴尔教授认为权益侵害本身可构成损害,但其亦仅将该观点限制在人身侵害的情形。而在财产侵害中,根据DCFR第VI-2:206条的注释可知,权益侵害本身不包括财产权的侵害,此时是否存在具有法律相关性的损害取决于是否造成其他财产损害或者非财产损害。(40)See Christian v. Bar, 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Damage Caused to Another, Oxford, 2009. p. 479.由此可知,冯·巴尔教授认为财产权受到侵害本身不应视为损害。就该方面而言,在象征性损害赔偿中,权益侵害说亦不符合英美法上的“任何侵害必然导致损害”规则。
2.精神损害说
精神损害以程度为标准可以分为轻微精神损害、一般精神损害与严重精神损害。(41)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862页。轻微精神损害是指较低层次的不舒适感,例如守约方因相对人违约而产生的不舒适感,此不舒适感并未达到精神上痛苦的程度。一般精神损害是指较低层次的精神上痛苦,例如受害人因个人信息被泄露而产生的精神上痛苦。严重精神损害是指已对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的精神上痛苦,例如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致残而产生的精神上痛苦。而以形成原因为标准又可将其分为侵权精神损害与违约精神损害,前者又分为人身侵害的精神损害与物之侵害的精神损害。就此而言,精神损害说符合英美法所承认的“任何侵害必然导致损害”规则,因为不论是人身受侵害、财产受侵害抑或违反合同义务皆会导致精神损害,上述情形仅在程度上存在差别。此外,并非所有的精神损害皆具有可赔偿性。除个别国家不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限定外,大部分国家都认为仅在满足严格的条件下才可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42)[英]W.V.霍顿·罗杰斯:《比较法视野下的非金钱损失赔偿》,许翠霞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29页。就我国法而言,根据《民法典》第996条与第1183条的规定,原则上仅于存在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才允许获赔。(43)有学者认为,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2款的规定,在个人信息被侵害时,精神损害无须达到严重精神损害的程度即可获赔。参见程啸、曾俊刚:《个人信息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载《云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107-108页。根据反面解释可知,除上述情形之外的精神损害皆属于不可赔偿的精神损害。如上所述,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应为不适格的损害,据此,轻微精神损害与一般精神损害满足该项要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根据“轻微损害不予赔偿”的理念,轻微精神损害原则上不应当获赔,即使获赔也应属于上述所谓的蔑视性损害赔偿,而非象征性损害赔偿。据此,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应为一般精神损害。
综上所述,若需将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进行性质归类,应将其认定为一般精神损害为宜。此结论与象征性损害赔偿所要实现的目的较为相符。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原告主动诉请象征性损害赔偿,抑或是法院主动判予象征性损害赔偿,其背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抚慰受害人因权利被侵害或义务被违反所造成的沮丧、愤怒、羞辱等精神上的痛苦,而此等精神上痛苦因不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而无法获赔,故而以象征性损害赔偿金对其进行弥补。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象征性损害赔偿之所以不能与补偿性损害赔偿并行不悖,其原因在于其客体本身不属于可赔偿的精神损害,法院是为了使受害人不至于因权利遭受侵害仍承受败诉的不利后果,而将其作为一种“兜底”性质的请求权赋予受害人。此过程实际上属于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44)See Andrew S. Gold, The Right of Redress, Oxford, 2020. p. 126.具体而言,立法者将不可赔偿的精神损害视为可赔偿的损害,进而在满足其他责任成立要件的情况下赋予受害人以损害赔偿请求权,由此创立了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然而,在我国法上,若以立法形式确立象征性损害赔偿,由于其本质上是对一般精神损害的救济,故而其无须以无补偿性损害赔偿为前提。换言之,若以立法形式将一般精神损害认定为可赔偿的损害,进而赋予其具有象征意义的象征性损害赔偿,则其已与英美法上的象征性损害赔偿截然不同,即无须以不存在实际损害为要件。
(二)1元精神损失赔偿的性质
经在北大法宝网上检索和甄选,与1元精神损失赔偿有直接关联的有效案例有75个。经统计,判决结果及理由如表1所示。

表1 1元精神损失赔偿案例
从表1中可知,在当事人请求赔偿财产损害而附带请求1元精神损失赔偿的案件中,法院皆是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1元精神损失赔偿的诉求,原因皆在于此等精神损害不符合“严重性”特征。在我国法上,其因属于不适格的精神损害,故而不予赔偿。此种情形通常发生于违约责任中,法院通常认为守约方此时仅遭受轻微精神损害,故而不予支持。
在仅请求1元精神损失赔偿的案件中,支持的判决可分为两类情形:(1)不符合精神损害“严重性”特征,其支持的理由是:侵害行为必然导致原告产生一定的精神损害,且原告所主张的1元精神损失费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故而予以支持。(45)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2020)川1025号民初899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0民终4127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8)豫1002民初3613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奉贤区(县)人民法院(2017)沪0120民初8011号民事判决书。(2)符合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特征,其支持的理由是:原告的权利遭受侵害且满足精神损害的构成要件,而原告又仅诉求1元精神损失赔偿,由于诉讼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当事人未提出的事项法院不得作出裁判,因此,法院亦无须考量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进而直接对该诉求予以支持。(46)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3民终2111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终3742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5民终1017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终8689号民事判决书。由此观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以“严重性”为要件是上述案件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法上,精神损害赔偿须以精神损害达到“严重性”程度为条件已为大众所普遍认可。《民法典》第996条及第1183条皆以精神损害的“严重性”为要件,比较法亦多采此等见解,(47)See Christian v. Bar, Eric Clive, Hans Schulte-Nölke (eds.), 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DCFR), Munich, Vol. 4, 2009, pp. 3743-3746.理由主要在于“轻微损害不予赔偿”。有学者虽赞成此项见解,但对该理由提出疑义,认为“轻微损害不予赔偿”与“严重损害方可赔偿”仍有所不同,对于二者之间的部分会因两种不同的理由面临不同的命运安排。(48)参见叶金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框架》,载《法学家》2011年第5期,第90页。因为若以“轻微损害不予赔偿”为理由,一般精神损害应属可赔偿的范畴,因为一般精神损害并非因其程度轻微而不予赔偿,而是因其程度难以界定而不适格;而若以“严重损害方可赔偿”为理由则会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
当然,亦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应当在立法上放弃“严重性”这一限制性条件,主要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1)严重性的标准难以确定,若将其成文法化会使得适用条件过于狭隘、僵化;(49)参见马俊骥:《论精神损害的可赔偿性》,载《时代法学》2019年第1期,第97页。(2)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程度只是确定赔偿数额的因素而不应作为承担责任的决定因素,故而应将精神损害赔偿扩张至一般精神损害。(50)参见张新宝:《从司法解释到侵权责任法草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页。对于第一点,有学者提出可通过动态体系标准予以解决,即通过将法益位阶、归责事由等多种因素的协动来判断是否达到“严重性”标准,(51)参见马俊骥:《论精神损害的可赔偿性》,载《时代法学》2019年第1期,第97-98页。此观点可资借鉴。然而,对于第二点,主流观点仍认为,不论就实践还是理论而言,精神损害赔偿都应当坚持以“严重性”为要件,原因主要在于诉讼水闸理论,即若放弃“严重性”要件则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泛滥成灾,法院无法承受此种沉重负担。(52)参见最高法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对此,张新宝教授认为法院根本无须担忧“水闸效应”,因为这一担忧的前提是,受害人因精神损害赔偿而获得数额可观的赔偿金,若数额不大,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上的价值,那么只有真正感到精神上痛苦的受害人才会坚持诉讼,对他们而言赔偿金的数额无足轻重。(53)参见张新宝:《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第58页。
上述反对诉讼水闸理论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将精神损害可赔偿的范围扩大至一般精神损害的做法仍存在些许问题。因为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填补功能,若如张教授所言为了克服诉讼水闸理论而仅赋予象征性金额,填补功能荡然无存,又因何可谓其为精神损害赔偿。若是为了保持填补功能,而以与其程度相符的合理金额进行赔偿,一方面由于一般精神损害的程度因人而异故而法院难以衡量其具体金额,另一方面“水闸效应”又将卷土重来。对此,有观点认为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部分情形不应囿于精神损害的“严重性”要求,象征性损害赔偿即为例证。(54)参见叶金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框架》,载《法学家》2011年第5期,第90页。此应是最为妥适之解决方案,因为其并非消解“严重性”要件,而是以例外思维对原则进行补充。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象征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之间存在区别,精神损害赔偿是通过一定的金额对受害人进行抚慰,因此该金钱赔偿不仅具有抚慰功能,亦具有填补功能,其中填补功能更居主要位置,甚至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功能实际上是填补功能的作用。(55)Vgl. Karl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 Allgemeiner Teil, 11. Aufl., München 1976, S. 380.而象征性损害赔偿仅具有抚慰功能,其金额仅具有象征性意义而不具有填补功能,其仅表明被告行为的违法与原告权利遭受侵犯的事实。简言之,象征性损害赔偿实际上是象征性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此时不应将其称为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其本身不具有损害的填补功能。
由上述可知,1元精神损失赔偿的判决可分为两类情形:一为不符合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特征;一为符合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特征。仅前者与象征性损害赔偿有关,而后者已然满足法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若当事人请求更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亦非不可,但仅是因为民事诉讼法上的处分原则,导致法院仅需就1元精神损失赔偿进行裁决。因此,此1元精神损失赔偿本质上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而就前者,其事实上并不满足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但若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难谓符合实质公平,在案件中不乏当事人提起诉求时或法院裁判时表明该精神损害赔偿仅具有象征意义,故而应对其表示认可。因此,此精神损害赔偿本质上应属于象征性损害赔偿。
四、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功能
由上述所知,象征性损害赔偿实际上是对一般精神损害的救济,其虽不具有损害填补功能,但其抚慰功能与精神损害赔偿并无二致。然而,除了抚慰功能外,其在程序法上亦具有积极作用。对程序法上的功能之探讨对其必要性探究亦有助益,其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降低诉讼成本
在美国,象征性损害赔偿被认为是“悬挂诉讼成本的钩子”(peg on which to hang costs)。(56)Kanahele v. Han, 125 Haw. 446, 263 P.3d 726 (2011).因此,有学者将象征性损害赔偿形象地描述为法院的“救援行动”(rescue operation),法院采取此行动的目的在于保护已确立诉讼事由但未遭受损害的原告,使其不必承担诉讼费用。(57)See Dan B. Dobss, Caprice L. Roberts, Law of Damage: Damages-Equity-Restitution, West Academic, 3rd ed.,2018, p. 226.此功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亦可发现端倪,例如在“王某某与李某名誉权纠纷案”中,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律师费15 000元及诉讼费用。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虽给原告的名誉造成一定影响,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对于精神损失费应予以支持(未说明理由),但律师费并非原告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故而不予支持。(58)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2020)川1025民初899号民事判决书。在司法实践中,若判予原告以象征性损害赔偿金,则表明原告为胜诉方,此时诉讼费理应由被告承担。然而,律师费是否亦可请求被告负担尚有疑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第2句的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人民法院可支持律师费的请求。由此可见,我国的律师费实行的是“原则自行承担,例外请求赔付”模式。然而,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22条的“等明显不当行为”中难以解释出该例外情形是否包含判予象征性损害赔偿的情形。故而,此时应将目光转向英美法上的律师费赔付模式。
在英国法上,律师费适用败诉转付规则,即败诉方应承担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等在内的相关费用,在此之外设置多种例外情形,例如双方均无过错、双方经济地位严重不对等等情形。(59)See Michael F. Mayer, Wayne Stix, The Prevailing Party Should Recover Counsel Fees, Akron Law Review, Vol. 8, Issue3, 1975, pp. 429-431.因此,英国的律师费实行的是“原则请求赔付,例外自行承担”模式,此“英国规则”亦为国际上律师费承担的主流模式。(60)See Werner Pfennigstorf,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with Attorney Fee Shifting,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47, Issue 1, Winter 1984, p. 37.与此相反,在美国法上,胜诉方通常无权向败诉方请求合理的律师费,仅在例外情形下允许请求赔付律师费,例如恶意诉讼、藐视法庭等。(61)See Wesley W. Peltzer, Attorney Fees: The American Ru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aw, Vol.1, No.2, Spring 1975, pp. 365-361.因此,美国的律师费实行的是“原则自行承担,例外请求赔付”模式,此被称为“美国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上的律师费承担规则与美国规则更相类似。然而,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若判予象征性损害赔偿,仅在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原告的律师费才可能由被告承担。(62)King v. Brock, 646 S.E.2d 206, 207(Ca. 2007).据此,在我国法上,若法院判予象征性损害赔偿,则亦应当仅于法律规定(6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54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71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3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2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号)第3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法发〔2007〕1号)第13条。或合同约定情形下才可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
综上可知,在上述案件中,法院驳回律师费诉请的理由并非因为律师费不是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支出,而是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约定而且此案件又不属于法定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的情形之一。当然,若我国未来采取律师费转付制度,此判决结果亦可发生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提案的答复》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对律师费用承担转付模式的前提、双向转付模式为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因此,若我国法上亦采纳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则在其与未来的律师费用转付制度的配合下,更能发挥其降低诉讼成本的功能。
(二)确权及矫正不法
有学者认为,部分象征性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类似于德国法上的确认判决(Feststellungsurteil),只是后者并未赋予受害人象征性损害赔偿请求权。(64)See Cees Van Dam, Damage and Damages, European Tort Law, Oxford, 2nd ed., 2013, p. 349.确认判决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预防性判决”,主要目的是结束权利义务的不稳定状态。上述见解有一定道理,因为象征性损害赔偿是为了确认原告享有权利及被告行为违法的手段。此功能亦体现于我国司法实践中,例如在“江西英赛压缩机有限公司、陈某某侵权责任纠纷案”中,经法院确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对原告经营阻拦或妨碍的情形已消失,侵权行为已经停止,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1元的损失。(65)江西省莲花县人民法院(2022)赣0321民初987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件中,象征性损害赔偿的作用即在于再次确认权利自由的边界,防止被告未来再次对原告的权利造成侵害。在美国,具有确权功能的象征性损害赔偿之典型案件是非法入侵案件(trespass),例如在Davisv.Overall案中,地役权人对供役地权利人提起诉讼,声称供役地权利人妨害其进入墓地的地役权。法院认为,法律推定侵犯财产权可造成损害,若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对特定损失进行证明,则可通过判决赔付象征性损害赔偿金来确认原告享有该权利。(66)Davis v. Overall, 686 S.E.2d 839, 841(2009).
此外,相较于确认判决,象征性损害赔偿还具有矫正违法行为的功能。例如在著名的Uzuegbunamv.Preczewski案中,校园警官禁止学生在学校指定的“言论自由区”中分享各自的信仰和宗教资料,学生以言论自由被侵害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象征性损害赔偿和禁令救济。该案件的焦点问题在于象征性损害赔偿是否可以矫正侵害言论自由的违宪行为。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多数大法官认为,虽然早期英国法院要求原告必须证明金钱损害,但后来他们认为“每一项权利侵害必然导致损害”,因此即使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损害,法院亦可裁定象征性损害赔偿,此时的象征性损害赔偿可以矫正所有权利侵害行为。(67)Uzuegbunam v. Preczewski, 141 S.Ct. 792, 800(2021).当然,对此功能不乏异声,如该案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Roberts)声称,若被告未获得补偿性损害赔偿,仅象征性损害赔偿根本不会改变原告的状态或地位。(68)Uzuegbunam v. Preczewski, 141 S.Ct. 792, 804(2021).实际上,亦有学者就类似的争议提出疑问,即当侵害无法转化为赔偿金,则给付赔偿金如何相当于纠正,以满足矫正正义的要求?结论是仅能通过建构一种不需要“纠正”的矫正正义理论来解决。此时可以借助美国学者雷丁(Radin)的“救济措施理论”,即作为救济的赔偿将对原告权利的尊重和对被告违法行为的谴责作为象征来恢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道德平衡。(69)参见[美]戴维·G.欧文主编:《侵权法的哲学基础》,张金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7-428页。由此可以表明,象征性损害赔偿应当属于雷丁“救济措施理论”中的救济措施,其应具有矫正不法的功能。(70)与之相类似的观点参见Andrew S. Gold, The Right of Redress, Oxford, 2020, p. 126.
(三)恢复名誉
原告起诉请求象征性损害赔偿的目的大多是希望通过审判程序提供可靠的信息以恢复自身名誉。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层出不穷,例如在W.J.A.v.D.A.案中,原告起诉被告诽谤,称被告在其网站上发布原告猥亵儿童的不实言论,侵犯原告的名誉权。法院认为,虽然原告未提交其声誉实际受损的证据,但推定损害赔偿理论可以有效保护原告的权利,使其获得象征性损害赔偿,进而维护其自身名誉。(71)W.J.A. v. D.A., 43 A.3d 1148 (N.J. 2012).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亦有类似的案件,例如在“万婴凯恩藏珑幼儿园诉四川磅铂传媒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中,被告在其经营的网站发表诽谤原告的文章,原告以名誉权侵害为由对其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1元。法院认为,由于原告属于法人,法人的名誉权遭受侵害导致的是财产损失,虽然原告并未提交有关财产损失的相关证明,但其要求被告赔偿1元损失的诉请符合情理,故而支持。(72)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5民初6632号民事判决书。实际上,此案原告的目的显然并非希望制裁被告,其只是希望通过诉讼恢复自身名誉,赋予象征性损害赔偿请求权符合此诉讼目的的实现,与实质公平正义目标亦相符。
综上可知,象征性损害赔偿在程序法上具有上述三项功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项功能中,美国学者及法院原本仅承认象征性损害赔偿的确权功能,但在2021年的Uzuegbunamv.Preczewski案判决后,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象征性损害赔偿的矫正不法功能,后来美国学者对该案件及该功能进行广泛讨论,最终亦对该功能表示肯定。(73)See Michael L. Wells, Uzuegbunam v. Preczewski, Nominal Damages, and the Roberts Stratagem, Gerogie Law Review, Vol. 56, 2022, p. 1186.
五、我国构建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及其建议
(一)我国构建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可知,若精神损害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可以请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若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据此,若受害人仅遭受一般精神损害,则仅可以请求加害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责任。而象征性损害赔偿亦是对一般精神损害的救济。因此,上述侵权责任形式与象征性损害赔偿责任的关系决定了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法上是否具有必要性。
1.赔礼道歉与象征性损害赔偿
赔礼道歉体现了我国传统的“礼治”文化,它的成文法化属于道德责任向法律责任的转变。总体而言,需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说明。首先,就赔礼道歉的功能而言,对于不同当事人其所发挥的作用亦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其可以起到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的作用。在美国,若当事人自愿主动道歉,陪审团亦会降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其次,就执行方式而言,包括自愿执行、替代执行与间接执行。自愿执行指被告自愿口头道歉或书面道歉,此为最佳的执行方式。替代执行通常有两种情形:一是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文书发布于报刊、网络等媒体上,费用由被告承担(《民法典》第1000条第2款)。二是由执行法院草拟道歉声明,将其公布于众,费用由被告承担。(74)参见赵晋山:《行为请求权强制执行研究》,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强制执行指导与参考》(总第7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间接执行是指法院以罚款、拘留的方式强迫被告执行赔礼道歉。(75)参见孙加瑞:《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概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621页。最后,就适用范围而言,只要权益的保护范围涉及精神利益,若侵害该权益,赔礼道歉即有适用的余地。若仅财产权益受到侵害,不应要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76)参见葛云松:《赔礼道歉民事责任的适用》,载《法学》2013年第5期,第93-97页。
总而言之,赔礼道歉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然而,其合理性长期以来亦饱受诟病。于比较法而言,法律直接规定赔礼道歉的国家仅有加拿大,其通过《道歉法案》明确将赔礼道歉作为一项责任承担方式,(77)参见郝维华:《加拿大-中国道歉法的比较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第67页。除此之外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其皆无明文。法律间接规定赔礼道歉的国家及地区有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其将赔礼道歉作为“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的手段之一,但亦引发了赔礼道歉判决是否合宪的宪法诉讼。(78)参见吴小兵:《赔礼道歉的合理性研究》,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6期,第147-148页。对于是否应当肯定赔礼道歉作为一项侵权责任,我国学界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分。肯定说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1)赔礼道歉作为法律责任,通过将判决文书公开的方式进行强制执行并未违背良心自由;(79)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74页。(2)赔礼道歉作为一项无强制力之法律责任,法律只能宣判而不能强制执行;(80)参见张红:《不表意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以赔礼道歉民事责任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22-124页。(3)赔礼道歉应以加害人自愿以及严重过错作为赔礼道歉的限制条件;(81)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60-661页。(4)仅允许以受害人谴责声明的替代方式执行赔礼道歉。(82)参见葛云松:《民法上的赔礼道歉责任及其强制执行》,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25-128页。其中第二种与第三种观点具有相似性,后者属于前者的具体化。否定说认为应取消赔礼道歉的责任形式。(83)参见周友军:《我国侵权责任形式的反思》,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第21页;耀辉、段睿:《“赔礼道歉”的异化与回归》,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11-112页。
笔者以为,一方面,需考虑到“自愿”赔礼道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仍具有其独特价值,其在抚慰受害人以及传扬积极社会理念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另一方面,亦需考虑到“强制”赔礼道歉作为一种良心自由的强制,不应被认可。因此,在保留赔礼道歉作为一项无强制力之侵权责任的前提下,应将象征性损害赔偿与赔礼道歉共同作为一般精神损害的救济手段。
究其具体原因,首先,于替代执行方式而言,赔礼道歉的第一种替代执行方式是将判决内容予以公开,其实际上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手段。在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亦将赔礼道歉作为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然而,恢复名誉与否应着重于对诽谤、侮辱性等言论的纠正以及对受害人社会性评价的提升,而非在于赔礼道歉。因此,将判决内容予以公告与赔礼道歉并无直接关联。第二种替代执行方式并非加害人对受害人进行道歉,而属于法院的“捉刀”道歉行为,有自欺欺人之嫌,此对于受害人而言抚慰作用意义亦甚微。
其次,于间接执行方式而言,赔礼道歉的间接执行方式是对我国宪法上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违反。(84)参见葛云松:《民法上的赔礼道歉责任及其强制执行》,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25-128页。在比较法上亦采同样的见解,在美国,法院认为判决赔礼道歉有违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与良心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conscience)。(85)See Nick Smith, Against Court-ordered Apologies,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6, No. 1, 2013, p. 44.在德国,强制赔礼道歉因违反违宪审查中的比例原则,因此仅自愿情形下才可进行赔礼道歉。(86)Vgl. Gerhard Wagner, Deliktsrecht, 14 Aufl., 2021, S. 160.而葛云松教授所支持的以受害人谴责声明方式替代赔礼道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此种方式已不能称之为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名存实亡尔。对此,有观点认为,可将强制道歉视为一项无强制力的法律责任,此种宣示性条款目的是恢复名誉及保障人格权,且手段适中,因此并不违宪。(87)参见张红:《不表意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以赔礼道歉民事责任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20页。此观点虽然解决了赔礼道歉强制执行的违宪问题,但仍难解决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拒绝履行赔礼道歉的情形。
再次,于适用范围而言,我国司法实践将赔礼道歉适用于所有的人格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这是道德责任完全成文法化的体现。此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的问题有考量因素存在分歧、执行方式不一等。然而,在承认可以将赔礼道歉作为侵权责任的国家及地区中,大多是将其作为恢复名誉的手段,即仅在名誉权被侵犯时才可适用。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认为,将赔礼道歉作为恢复名誉之处分并不违宪,但在适用时仍应秉持谨慎的态度,即在公开判决不足以恢复受害人名誉时,才可使加害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
最后,对于象征性损害赔偿的作用而言,在精神损害未达到严重程度时,象征性损害赔偿可以对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起到良好的抚慰作用。虽然象征性损害赔偿不具有填补功能,但一般精神痛苦的程度因人而异,皆予以填补将导致法律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且由于象征性损害赔偿具有矫正不法的功能,因此,以象征性损害赔偿对精神上痛苦予以抚慰足以满足侵权法的矫正正义(88)参见上文所提及的雷丁的“救济措施理论”。的要求。就此而言,在赔礼道歉无强制执行力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象征性损害赔偿对于一般精神损害的救济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2.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与象征性损害赔偿
停止侵害的主要功能在于预防侵害行为或状态的持续。就此而言,其所附带的确权功能与象征性损害赔偿有些许重合,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明显缺乏矫正违法的功能,例如当侵害行为在庭审阶段已经停止,此时受害人的停止侵害请求被驳回,虽然可以认定被告过去的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原告也只能承受败诉的结果。(89)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2)粤1971民初9573号民事判决书。就此类情形而言,象征性损害赔偿则可以起到良好的矫正不法的作用。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作为侵权责任形式长期饱受非议,因为其只是名誉权遭受侵害后恢复原状的结果,而非手段。司法实践中,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公布于众是作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主要具体方式。一般认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虽具有一定的抚慰功能,但这仅是其反射作用,其主要功能应在于使受损害的人格权恢复至原有状态。(90)参见崔建远:《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兼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74页。而象征性损害赔偿所具有的抚慰功能与精神损害赔偿相当,即直接作用于受害人。从性质上而言,前者属于人格权请求权,而后者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属于不同领域范畴,对于权利侵害救济发挥着不同作用。
总而言之,象征性损害赔偿在我国法上有构建的必要性,对于损害赔偿而言,象征性损害并无执行难的问题,可在赔礼道歉无法强制执行时,替代其发挥作用,并与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侵权责任形式共同作为一般精神损害的救济措施。
(二)象征性损害赔偿在我国法上的构建
1.象征性损害赔偿的立法展望
若需将象征性损害赔偿纳入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仅能将其解释为《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第8项的“赔偿损失”,此亦仅为权宜之策。最佳的方式是通过立法于侵权责任编中予以明确规定,例如可以在第1183条下增加一个条款,即第1183条第3款:“上述情形未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象征性损害赔偿。”因为第1183条的“一般性目的”在于,保护他人人身权益的同时,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必要性限制,从而防止该制度被滥用,(91)参见朱震:《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严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2期,第140页。而象征性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并不足以对滥诉形成足够的内在动机。就此而言,象征性损害赔偿条款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范目的并不相悖,而且其以更为包容性的方式将造成一般精神损害的情形予以囊括。
此外,除了上述提及的填补功能与抚慰功能外,有学者认为,第1183条中的“严重性”要件与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之间的关系亦十分密切。(92)参见朱震:《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严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2期,第150-152页。在严重精神损害赔偿上,预防功能更多体现于高额的损害赔偿费用上,其可对加害人起到一定的震慑效果。在象征性损害赔偿上,预防功能亦有所体现,即以加害人角度而言,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程序法上降低诉讼成本的功能无疑亦可使得侵权成本显著增加,其亦可起到预防侵权行为的作用。就此而言,第1183条凸显出的预防功能亦与象征性损害赔偿条款相契合。由此可见,《民法典》未对一般精神损害设置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总而言之,若立法者在第1183条下增加象征性损害赔偿条款,其可形成的优势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第一,象征性损害赔偿条款使得本身难以界定的一般精神损害得到充分救济,进而使得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该条款本身并不是消解精神损害赔偿的“严重性”要件,而是以漏洞填补的方式对一般精神损害的情形予以涵盖。就功能而言,象征性损害赔偿并非具有填补功能,其本质虽是为了救济一般精神损害,但主要功能在于抚慰精神痛苦,这与以“严重性”为要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并不相同。因此,不能仅通过否定“严重性”要件将二者混为一谈。第二,象征性损害赔偿条款可避免“闸门效应”的产生。如张新宝教授所言,象征性的金额并不会使得原告有动机去起诉,仅法感情遭受严重侵害的当事人才会为了维权而起诉,这并不会使得大量的诉讼涌入法院。第三,该规定可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公益性质的诉讼(93)因诉讼主体及诉求不完全符合公益诉讼的要求,因此应称其为“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只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诉讼。另一方面,一般认为虽具有社会影响但仅涉及私益保护诉求的案件不应划入公益诉讼之列。中,例如在“武汉大学生状告美图秀秀”案中,法院认为,“摇一摇”开屏广告形式侵犯了原告的自主选择权,因此应赔偿原告月数据流量损失1元。(94)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3)闽0203民初4132号民事判决书。实际上“摇一摇”跳转后的广告只是一个商业广告,因此并没有造成额外的损失,1元应当是对原告所产生的一般精神损害的救济。不可忽视的是,此诉讼请求有助于其他消费者的私密空间不因经营者的商业行为而受到不必要的侵扰,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亦如在Muellerv.Swift案,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诉请1美元的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希望帮助遭受性骚扰及性侵犯的人发声。(95)See Daniel Kreps, Taylor Swift Talks ‘Symbolic’ Lawsuit, Groping Trial, Sexual Assault, RollingStone (Dec. 6, 2017), https://perma.cc/RN26-9XND.
2.象征性损害赔偿的数额认定
由于象征性损害赔偿是在表明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判决的,因此,它仅是被作为一项程序救济措施而非经济救济措施。就此而言,赔偿数额通常被认为应当是微不足道的。在美国,大多数案件中的象征性损害赔偿的数额仅为1美元。(96)Cummings v. Connell, 402 F.3d 936(9th Cir. 2005). State, Dept. of Corrections v. Niosi, 583 So.2d 441(Fla. 4th DCA. 2007). Green v. Study, 286 S.W.3d 236(Miss. SD. 2009).有的法院虽然认为象征性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必限制为1美元,但就其本质而言,其数额应尽量低额。(97)Romano v. U-Haul Intern., 233 F.3d 655, 671((1st Cir. 2000).此外,有的法院认为应当设置最高限额,例如500美元。(98)Graphnet, Inc. v. Retarus, Inc., 269 A.3d 413, 422(N.J. 2022).在英国,象征性损害赔偿的金额亦不一致,例如在Liverpool City Councilv.Irwin案中,法院将象征性损害赔偿的金额从10镑降低至5镑。(99)Liverpool City Council v. Irwin [1977] AC 239.而在Radfordv.De Froberville案中,法院认为适当的数额应为40先令(2镑)。在其他普通法系国家亦如此,例如马来西亚联邦法院认为,象征性损害赔偿的金额应限定在10令吉至1 000令吉之间。(100)Pancaran Prima Sdn Bhd v. Iswarabena Sdn Bhd [2020] MLJU 1273.
实际上,是否统一象征性损害赔偿的数额并非十分必要,只要满足极小数额(trivial sum)的特点即可。然而,若出于“同案同判”的裁判理念的考量,统一量化其实更符合其象征性目的。这是因为不同案件中的事实情节虽各不相同,但若判予原告象征性损害赔偿,实际上只是一种原告胜诉的信号,其目的在于抚慰受害人而非出于补偿的考量。因此,若需要建立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不妨在实践操作中将其统一为一定的金额,此虽不必出现于实体法律条文中,但可作为裁判时参考的依据。
六、结语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1元财产损失赔偿并非象征性损害赔偿,其仅是在损害额酌定制度下原告行使处分权的判决结果。1元精神损失赔偿亦并非皆为象征性损害赔偿,其中部分因已满足精神损害赔偿要件,法院亦因处分原则而仅判决赔偿1元精神损失费。仅精神损害未满足“严重性”要件而仍支持1元精神损失赔偿的情形才属于象征性损害赔偿。
在英美法上,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看似无法逾越“无损害则无赔偿”的鸿沟,然而,若具体分析可知,象征性损害赔偿的客体实为一般精神损害,若对该损害予以认可,则与该原则并不违背。就此而言,象征性损害赔偿制度不论在实体法上抑或程序法上皆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拿来主义”的前提下,需要对该制度进行法教义学分析,进而判断我国法律体系中是否有必要引入该制度。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由于强制赔礼道歉属于对良心自由的强制,故而不应予以认可。因此,应通过立法方式将象征性损害赔偿作为一般精神损害的救济方式,在赔礼道歉无法强制执行时,替代其发挥抚慰受害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