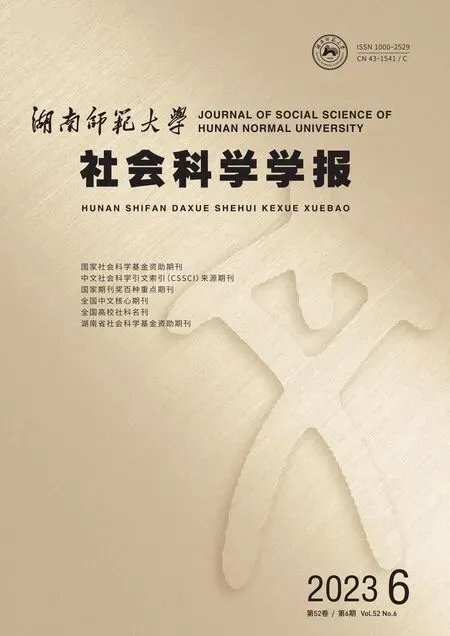“侧附”说与赋体创作生态
许 结
在赋论史上,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其中包含了有关辞赋创作历史、风格与技法等范畴的讨论,并提出了诸多批评词语。例如“体国经野”以彰气象,“铺采摛文”以明词章,“蔚似雕画”以示风格,或沿用成语,或自创新词,均有丰富的赋学蕴涵。在刘勰论赋的自创语中,其“侧附”一词鲜有关注,诸家注本仅有词义的解释,而缺少赋体的批评。然词无妄设,其必有理,本文拟结合赋体的创作生态及赋史的发展变迁,对“侧附”说作些赋义的疏证。
一、赋体“侧附”释义
“侧附”一词由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提出,是针对赋体的“鸿裁”与“小制”的区分而论。如其论“鸿裁”云:“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指的是“兴楚而盛汉”的骋词大篇。而紧接其后,刘氏复论“小制”云:
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1]135
所谓“小制”,即短篇,显然指的是汉晋以来赋家咏物、抒情的小赋。对这段话语,如谓“庶品”“取会”“形容”“纤密”“物宜”等,皆常语,唯有“理贵侧附”的“侧附”一词,为刘氏独创,相关解释多限于词语本身,未能深入探讨。为厘清词义,先列举几家释义如次:
“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这里四句话的意思是说:描摹事物的形貌时,言词务必细密,取象时则贵在根据物性之所宜而作出贴切的比附。①
“拟诸”四句,互文见义,实谓作者考量外物的形状容貌,然后作赋,辞采务必细密确切,摹写才能适当。[2]115
侧附:贴切相和。[3]
“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象,谓形象,动词,与形容同义。理,谓道理、事理也。此言将与情为一之物,明其所宜而描绘之,则其理贵于侧附,谓不宜于直接陈述也。[4]
侧附:指理寄托在物象上。[5]
侧附:从旁附会,有所寄托。[6]
侧附:从旁比附。[7]
侧附:指不直接描写,而从侧面说明。[8]
侧附:不直接说明而从侧面说明,指理寄托附着在物象上。[9]
以上罗列的解说大同小异,就方法言,即“从旁附会,有所寄托”;就功用言,即把“理寄托在物象上”,释义比较清简,亦甚合意。但作为一个词语的出现,后世的沿用往往会脱离刘勰说赋的理念,产生歧义。比如清人吴锡麟《插菊》诗云“横生侧附画家意,粗服乱头处士巾”,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试帖诗课合存序》评吴锡麟诗“予所尤服膺者乃其八韵诗也”[10],皆以“横生侧附”喻旁渲侧击之意。又如《杜樊川诗集注序》谓“不穿凿以侧附”[11],王闿运《致游署督》谓“奉教日浅,未能尽窥蕴蓄,然侧附有道,自谓知心”,又仅用附着或附会义,其中不乏贬斥某些人品的意思。至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释“夭”谓“凡草木既生枝叶,其秒有旁出侧附之形,故曰夭”[12],指的则是树的枝叶横斜而附着于主干的形象。
如果回到“侧附”一词释“赋”的本义,前引诸家的解说并不重要,而在释义时的旁引文献或许更具有启发意义。
例一,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纪评”云:
分别体裁,经纬秩然。虽义可并存,而体不相假。盖齐梁之际,小赋为多,故判其区畛,以明本末。[1]141
正因纪昀将侧附义指向小赋,所以范氏的“注”引录小赋作品就有枚乘《柳赋》、魏文帝《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几赋》、中山王胜《文木赋》[1]142-143,是以作品印证批评,实为参证。
例二,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引录《易·系辞上》: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13]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同引此语并作释义:
见,同现。赜,奥秘。拟,考量。诸,于。形容,形状容貌。象,效法,本篇谓摹写。“圣人”云云,本言圣人发现外物的奥秘,从而考量其形状容貌,适当地效法外物;本篇“拟诸”两句,暗引《系辞》,就作赋说。纤,细。《玉篇》:“理,文也。”辞采也。贵,重也。侧,委曲。附,著合,确切。[2]114-115
这依据刘勰《诠赋》借用《易·系辞》“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语,以说明其“侧附”含有“委曲”和“著合”于“物象”的意义。
例三,詹瑛《文心雕龙义证》在解读《诠赋》“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四句话后,引录王芑孙《读赋卮言·造句》评语:“侧附二字,可谓妙于语言。”这是在我国古代赋论史上罕见提出“侧附”二字,并认为是“妙于语言”的说法。
何以“妙于语言”,还应回看王芑孙原话的完整语境:
篇则统前后而谋之者也,句则随时而谋之者也。随时而谋,又必统前后而谋,商量生熟,刻画分秒,斯固雕虫之业也。营篇既得,将增壮于数联;制局已乖,冀求援于几句。苟痴钝其一字,必岨峿乎全章,然而不贵尖鲜,务归坚緻。……《诠赋》曰:“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侧附”二字,可谓妙于语言,唐人尤得其法。[14]324-325
如果我们结合王氏《读赋卮言》的《立意篇》的“意之不立,辞将安附”[14]314,《小赋篇》的“赋者用居光大,亦不可以小言;聊以小言,犹云短制。在汉则刘安……碎金屑玉,慭遗《选》外。魏则……晋则三傅之余,二该特妙。宋、齐之际,非惟王谢;陈梁以上,岂止江萧”[4]325-326,可知这一说法不仅将“侧附”归于“小赋”,而且历述其作家作品,以证其义理。由此返观他说的“妙于语言”与“唐人尤得其法”,其中内含的赋体创作生态,或可发掘并彰显“侧附”说的赋史价值。
综上所述,“侧附”除了诸如“从旁附会,有所寄托”类的文辞表达,以及“寄托于物象”类的写作方法,尤其要关注有关赋的两个视点,即“赋体”(小制)与“赋理”(理贵),这其间又有着由小制延展的从“谋篇”到“句法”之创作路径,由“理贵”旁渲寄托又引申出对赋体创作“比法”介入的思考。
二、小制与句式
赋体的“侧附”说被刘勰明确规定在“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的批评范畴,也就是说“体类”乃“小制”,“奇巧”属“技法”。由此探讨作为技法奇巧的小赋写作现象,其间有丰富的内涵,如果对照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丽辞篇》中所述,自扬、马以后“崇盛丽辞”,到魏晋群才作文写赋则“析句弥密”[15]588;其《才略篇》又谓张华“鹪鹩寓意”,陆云“敏于短篇”[15]700-701,赋史的批评走向已然关注“丽辞”“析句”“寓意”“短篇”,均与“侧附”说的提出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作为这一技法载体的“短篇”小赋,后世解读刘勰的赋史视域或批评指向,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汉书·艺文志》所载“《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16]。对此,范文澜注引王应麟说“刘向《别录》有《行过江上弋雁赋》《行弋赋》《弋雌得雄赋》”,又引述“《西京杂记》虽云出自吴均,然其时或尚及见汉代杂赋之遗”[1]141。此类杂赋当为小制咏物体,赋作不存,当年刘勰是否见到只能推测,很难以“侧附”说明此类作品。
二是汉初“梁王菟园”文士的咏物小制,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评述刘勰所言“小制”引录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羊胜《屏风赋》等诸作品。有关本事见载《西京杂记》卷四“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17]等。由于《西京杂记》书的归属争议颇多,且诸赋皆不见载《文选》,所以对其时代的真实性或认同,或质疑,均无定论②。而且在《文心雕龙》中涉及赋名,也全无上述篇章,“侧附”说应该同样与之相距甚远。
三是由东汉以来至魏晋齐梁的小赋创作,包括由梁武帝《历代赋》(已佚)延及萧统《文选》所收作品,和当时流行而未收的“小制”赋篇,这应该才是刘勰“侧附”说的言说对象(文本)。如《诠赋》所论“仲宣靡密,发端必遒”,观其《登楼赋》短篇,其写作方法是典型的“景”因“情”变,其登高销愁时观其景则“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以示广远而丰沃;而回想到“遭纷浊”之乱世与“漫逾纪”之困顿,“忧思”难“任”,于是所见景则为“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18]162-163,其以景句言情以明理(忧思)。又如《才略》言及“鹪鹩寓意”,读张华《鹪鹩赋》所言“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所寓之意,诚如赋序所说“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18]202。王粲与张华赋均载《文选》,其状思与寓意,皆内含“侧附”之义。而其《才略篇》称陆云“敏于短篇”,以及《丽辞篇》以为魏晋群才“析句弥密”,包括前引王芑孙《读赋卮言·小赋》所及“晋则三傅之余,二该特妙”,其所及诸多赋作或未载《文选》,亦当属刘勰论述“小制”的创作范围。
以篇象寓意,固然不乏“侧附”之义,但依据刘勰强调的“象其物宜”与“析句弥密”,其“侧附”之法主要呈现于“句象”,即以一物一事喻一理,其旁渲寄托,均重在“句法”。换言之,其重于句式的“侧附”之法,与魏晋中人对诗赋“佳句”的提倡有关。如评诗句,钟嵘《诗品》中“宋法曹参军谢灵运诗”云:
《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19]
如评赋句,《世说新语·文学》记述: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20]
如评诗、赋句,《南史·谢庄传》载:
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答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21]
当时人以诗赋佳句为谈资,既是文学崇尚辞章的风气,也与创作技法的演进相埒,类似陆机《文赋》在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创作体义的同时,又强调“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句法”审美[22]。落实到小赋的句法,刘勰的由“象其物宜”到“理贵侧附”,正是一种以事、物喻理的书写,并起到“片言”以“警策”的效果。
正因为魏晋以后赋家对佳句的重视,刘勰的“侧附”说主要指向“句法”的技艺。我们可以王芑孙列举的晋世“三傅”中的傅玄、傅咸父子咏物小赋为例,在象物之宜后无不以寄托理趣以终篇。例如:
“辟凶邪而济正兮,岂唯荣美之足言。”[23]1718(傅玄《桃赋》)
“同志来游,携手逍遥。”[23]1719(傅玄《柳赋》)
“清击畼于遐迩兮,时感君之丹心。”[23]1721(傅玄《蝉赋》)
“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23]1752(傅咸《纸赋》)
“睹日观之有瑕,则稽训于儒绅。”[23]1752(傅咸《镜赋》)
“此谦卑以自牧,乃无害之可贾。”(傅咸《叩头虫赋》)[23]1755
其或以“桃”喻避凶,或以“柳”喻景境,或以“蝉”明秋洁之心,或以“纸”展书写之志等,无不正言其“象”,而侧喻其“理”。值得一提的是,自楚汉以来,辞赋的句式与作法是创作的基础,那为什么讲刘勰“侧附”说是建立在重视句法的基础上?这里内含辞赋句法论两大走向[24]:一是从“丽辞”到“寓意”。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论汉赋以为“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并称“丽辞之体,凡有四对”,如述言对则司马相如《上林赋》之“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事对则宋玉《神女赋》之“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等[15]588-589,均以对偶藻采为佳句。魏晋赋虽亦承汉丽辞,对偶变本加厉,但刘勰关注的“侧附”,则显然更重在寓意。以王芑孙前称“二该”中的孙该《琵琶赋》为例,其对作为乐器的琵琶之构造、功用的描写后,不重尚辞,而重寓意,所谓“绌邪存正,疏密有程”“缓调平弦,原本反始,温雅冲泰,弘畼通理”[23]1277,虽为旁附,却片言明理。二是从“经义”到“物理”。汉代大赋,虽藻采丽辞以为美言,但凡寓意,赋中警句又多引述或化用经词与经义。如用经词,扬雄《河东赋》“播九河于东濒”,取《尚书·禹贡》“北播于九河”;用经义,张衡《思玄赋》“惟盘逸之无斁”,取《诗·周南·葛覃》“服之无斁”[25]。魏晋以降,赋家更多于物象之本原探寻物理以寄托意旨,其中张华《鹪鹩赋》咏微禽借《庄》典以明“逍遥”义最为典型。我们不妨再看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称述“敏于短篇”的陆云赋作,如《喜霁赋》之“托芝盖之后乘兮,餐琼林之朝华”[26]13;《登台赋》之“委普天之光宅兮,质率土之黎彦”[26]16;《逸民赋》之“鄙终南之辱节兮,韪伯阳之考槃”[26]2;《寒蝉赋》之“咏清风以慷慨,发哀歌以慰怀”[26]23,紧扣题义,借物象以寄托物理,表达出与所咏之物相即相离的情怀。
“侧附”用之于赋家句式,与魏晋以降文士关注情之“本”与物之“理”相关,而这种旁渲寄托的方法在赋语中的体现,到唐宋时期又有了风格的变化。王芑孙《读赋卮言·造句》以为“侧附”妙于语言而“唐人尤得其法”,宜指唐赋句法寓意的缜密与高妙。其实对照唐宋时小赋句法的“侧附”,又出现了向汉赋藻采与经义的回归。浦铣《复小斋赋话》上卷载:“赋贵琢句。唐张仲素《管中窥天赋》云:‘月既满而犹亏,日将中而如昃。’又无名氏一联云:‘桂魄未圆,余晖来而尚溢;阳乌当昼,远色照而全亏。’同是一意,而笔用反正,加以锤炼,便觉出色。”[27]赞述唐赋的警句或秀句。清人汤稼堂认为:
唐人琢句,雅以流丽为宗,间有以精峭取致者。皇甫湜《山鸡舞镜赋》云:“类凤因箫感,哂鹤为禽召。”赵蕃《月中桂树赋》云:“谓扇花薄,如珪玷浮。”杨宏贞《隙尘赋》云:“疑琢玉成环,环中屑坠;若窥壶入洞,洞里云残。”张随《海客探骊珠赋》云:“初辞碛砾,讶潭下星悬;稍出涟漪,谓川旁月上。”刻酷锻炼,皆所谓字去而意留者。[28]
所谓“刻酷锻炼”而字“去”意“留”,实与“侧附”之法相通。只是唐人赋句的“象物”而寓“意”,与晋赋多明物理稍异,转向对经义的借用。对此,李调元《赋话》卷四有一则记述:
唐人体物最工,么麽小题,却能穿穴经史。……李子卿《水萤赋》云:“色动波间,状珠还于合浦;影悬潭下,若星聚于颍川。”字字典则,精妙无双。[29]33-34
继此,李调元又于《赋话》卷五记述宋人赋句,尤多依“经义”而观“器识”。如列举苏轼《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三法求民情赋》《六事廉为本赋》等警句,以为“以策论手段施之帖括。纵横排奡,仍以议论胜人。然才气豪上,而率易处亦多,鲜有通篇完善者”[29]41。又举朱长文《乐在人和不在音赋》警句,以为“寓议论于排偶之中,亦是坡公一派”[29]41。他以古典经义寄托当世情事者,如前引汤稼堂《历朝赋衡裁·余论》引载苏轼《通其变使民不倦赋》末段“制器者皆出于先圣,泥古者盖出于俗儒。……王莽之复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车战,众病其拘”,认为是“隐斥荆公新法”;又引载李纲《折槛旌直臣赋》“所求者名,不务其实,文虽足观,质焉可述?宠昭仪而绝皇嗣,大斁天伦;恩元舅而杀王章,遂倾帝室。虽存折槛,足为后世之规;实废嘉言,讵救当时之失”,认为“切中汉成之病,而忠定之忠肝义胆,亦可见矣”。其赋句寓意的传承与变化,亦可视“侧附”说在后世赋创作中运用的更化与发展。
三、理义与比法
刘勰提出的是“理贵侧附”,究其根本在赋家以物象或事象寓意明理,可视之为“赋理”的范畴。考查赋家述理,祝尧《古赋辩体》颇多言说,如卷三论汉赋以为“长卿长于叙事,渊云长于说理。……盖其长于叙事则于辞也长,而于情或昧;长于说理则于理也长,而于辞或略”[30]141-142;卷八论唐宋赋“考唐、宋间文章,其弊有二:曰俳体,曰文体。……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30]419。这是在整个赋论史上,比较明确提出赋体创作应该“情”“辞”与“理”兼备的批评观。而就所述赋“理”而言,祝尧所言王褒、扬雄“长于说理”,具体呈现于像扬雄《长杨赋》这样多发议论的作品,是以赋篇述理的一种方式,这与刘勰所倡导的以赋句喻理的“侧附”不同。究其原因,也在于汉、晋赋“理”的差异,可以说,从汉代骋辞大篇到魏晋体物小制的赋史大势来看,这一时段(由汉到晋)经历了由赋“礼”(重仪象)到赋“理”(重物象)的嬗变。
有关汉代骋辞大赋的兴盛,班固《两都赋序》指出:“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18]21《汉书·礼乐志》也记述了赋与礼的关联:“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31]考察汉大赋的书写,除了如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写天子游猎礼,扬雄《甘泉赋》《河东赋》写天子郊祀礼,到东汉时期以班固、张衡为代表的赋家笔下京都大篇的制作,其中铺采摛文描绘的也多是天子的礼仪。例如班固的《东都赋》中有关汉天子春日行“元会礼”的书写:
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鍧,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18]33
其写作内容是行“礼”的过程与仪态,其写作方法是以礼仪展礼事而喻礼义。与之不同,魏晋咏物小赋的兴起,更关注的是物态与物理,其赋学观的哲学基础是王弼《周易略例·明彖》所说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32],以及如《魏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记述荀粲对《周易·系辞》的驳议“盖理之微者,非物象(卦象)之所举也”[33]。我们阅读魏晋时期的咏事与物的小赋,如潘尼《钓赋》“抗余志于浮云,乐余身于蓬庐。寻渭滨之远迹,且游钓以自娱。……且夫燔炙之鲜,煎熬之味。百品千变,殊芳异气。随心适好,不可胜纪”[34]545,以“自娱”“适好”寓意,阐发的正是个性化的“逍遥”理义。这类作品,或以物态喻理,或以景候喻理,或以情志喻理,赋“理”为其同一指向。如傅玄《柳赋》云:
美允灵之铄气兮,嘉木德之在春。何兹柳之珍树兮,禀二仪之清纯。受大角之祯祥兮,生濛汜之遐滨。参刚柔而定体兮,应中和以屈伸。……居者观而弭思兮,行者乐而忘归。……同志来游,携手逍遥。[34]692
对照《西京杂记》所载汉人枚乘的《柳赋》“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醪。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于边撩”[35],傅赋更偏重自然之物,以喻人生哲理,其“弭思”与“忘归”,乃以片刻的宁静达致“心斋”“坐忘”的思境[36]。
赋“理”必附于“事”与“物”,对此祝尧《古赋辩体》卷五论“三国六朝赋”,认为“尝观古之诗人,其赋古也,则于古有怀;其赋今也,则于今有感;其赋事也,则于事有触;其赋物也,则于物有况”[30]262,其触“事”以况“物”,与刘勰“侧附”说有相通之处。但与后世“理题”赋不同的是,“侧附”乃以句式为单元的象物明理,所以其方法又与魏晋以后赋学批评的“比兴”入赋有关,当然这也与后世如祝尧以“比”或“兴”明赋篇(体)不同,仍是限于句法的意义。对照《文心雕龙·比兴》,刘勰虽兼言“比兴”,但其中论述最突出的是以赋句喻“比”体之义。因为刘勰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比的“附理”,正是“理贵侧附”的另一种说法。由此观其论“比”: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乣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15]602
其中以汉赋例句说“比”义,与其论魏晋小赋的“侧附”句式是相关联的。可以说“附”有比附义,而“侧”的旁渲则通于暗喻之旨。对此,清人魏谦升《赋品·比附》云:“太师教诗,其三曰比。东筦有言,侧附者理。……象其物宜,图穷见匕。”[37]这种“象其物宜”以比附明理的赋句,在晋人咏物赋作中最为常见。比如夏侯湛的《观飞鸟赋》“动素羽之习习,乱白质于日光”,以简笔勾勒,既明晰如画,又喻示了“见素抱朴”与“和光同尘”的处世哲理。又如孙楚的《雁赋》“得天时而动静,随寒暑而污隆”,以雁行的自然时序,比附人生行藏的适性之理。晋人咏物,附理者多,试以几则咏动物赋为例:
何兹虫之资生,亦灵和之攸授。……俟日月之代谢,知时运之斡迁。[23]1657(卢谌《蟋蟀赋》)
有金刚之俊鸟,生井陉之岩阻。超万仞之崇巅,荫青松以静处。体劲悍之自然,振肃肃之轻羽。[23]1801(孙楚《鹰赋》)


其中“俟日月之代谢,知时运之斡迁”“超万仞之崇巅,荫青松以静处”等赋句,无不以物状人,含侧附之义。
刘勰赋句贵“理”的“侧附”法,因与赋体比法的结合,对后世论赋以“比法”用于“句法”的批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唐人无名氏《赋谱》论赋的比法,即以赋句为喻:
比喻有二:曰明,曰暗。若明比喻,即以被喻之事为干,以为喻之物为支。……若《秋露如珠》,“露”是被喻之物,“珠”是为喻之物,故云“风入金而方劲,露如珠而正团。映蟾辉而回列,疑蚌割而俱攒”。[39]
宋人郑起潜《声律关键》论赋的“琢句”,认为:

孙奕《文说·赋贵巧于使事》记述:
高安解试《由也升堂赋》,满场皆苦其无故实。林振体状题意,独得活法,只用孔门同时之事映带,其第六联云:“攀鳞附翼,仰窥在寝之渊;闻礼学诗,下视过庭之鲤。”主文李先之(朴)抚案称赏曰:“只消此联,已见由也果在堂上矣。”遂置首选。[41]
或言喻物之警策,或言观句之器识,或谈闱场故事,其以句为单元,以比为方法,正是刘勰所倡“侧附”说的传承。到了清代,类似的赋论尤多,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小赋》云:
欧文忠有《鸣蝉赋》,王守溪云:“大凡作此小赋,略靠在人事上说道理,方说得有去处,且觉艳丽动人。不然,一蝉之微,有何可说?纵说亦无味了。”此论能开后来无限法门。又如陆龟蒙《零陵总记》:“张登长于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往往蹙金之状。”数语尤令人叹绝。[42]
浦铣《复小斋赋话》上卷认为:
赋中最多比体,然以人比物,如何着笔?王棨《回雁峰赋》云:“稍类乎王子乘舟,已尽山阴之兴;曾参命驾,因闻胜母之名。”得此三虚字,便觉死处皆活,实处皆虚,并不嫌其拟不于伦。[27]377
刘熙载《赋概》相关言说如“实事求是,因寄所托”“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43]等,均可视为遥承“侧附”的话语体系。万殊《赋体物而浏亮赋》有句云“况植物之葳蕤,为比兴之所由……伊氛物之毕陈,贵曲体而勿误”[44],虽兼及比兴,其言“曲体”,却内含“侧附”的旁渲寄托之义。
综上所述,刘勰论赋“侧附”说既指向“言务纤密,象其物宜”的奇巧“小制”,又有以“理贵侧附”彰显赋“理”意义。从赋体创作生态看,对“侧附”的释解必须关注“赋体”与“赋理”,阐发赋史中“小制”从“谋篇”到“句法”的创作路径,而“理贵”旁渲则引申出赋体创作与批评的“比法”介入。
注释:
① 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8页。按,詹著引录李曰刚《文心雕龙诠》“此数句论杂赋之特色。……侧附,谓逼近切合也。《仪礼·公食大夫礼》:‘侧其故处。’疏:‘侧,近也。’……附,合也”。
② 参见费振刚《梁王菟园诸文士赋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的考辨》、康达维《〈西京杂记〉的赋篇》,载《新亚学术集刊》第十三期《赋学专辑》,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4年。
——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考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