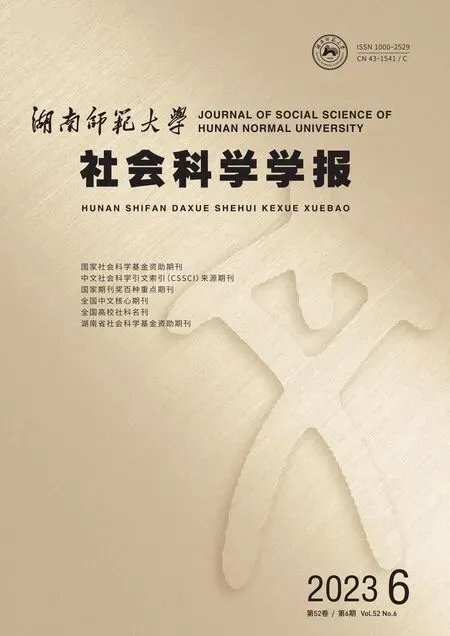乐府赋题法与唐代歌行体的形成
吴大顺
引言
赋题法是齐梁时期文人拟乐府普遍使用的一种创作方法。汉唐时期,在诗乐逐渐分离的历史进程中,文人拟乐府蔚成风气。汉魏时期的文人拟乐府,或按照曲调的旋律特点模仿原辞,保持拟作与原辞的相似性,以符合曲调的旋律要求;或以原辞内容为蓝本,强调拟作在主题、题材和内容上与原辞保持某种内在联系[1]。刘宋文人的拟乐府要么依循原作主题延展,要么从原作某一点生发拓展新主题[2]。齐梁文人以赋“鼓吹曲”“横吹曲”的曲名为标志,开启了文人赋题乐府创作的高潮[3]。无论拟赋曲题与原辞有关之题,还是曲题与原辞无关之题,拟作都主要是从曲题的意义层面展开联想和想象,突出曲题蕴含的内容倾向,与古题的音乐风格、原辞主题内容和体式结构已经没有太大的关联;对原辞已佚或本无原辞之曲题的拟赋更是与曲题的音乐及体式相去甚远。齐梁文人拟乐府的这种转变摆脱了对汉魏乐府古题、古辞或原辞的依循,逐渐构建起拟乐府主题与曲题的对应关系,使文人拟乐府创作获得了更自由的空间,为文人拟乐府创作在题材主题和体制结构方面随时而变提供了便利。赋题法的使用为文人拟乐府创作注入了新活力,唐代文人在古题乐府中对赋题法的普遍使用以及创造性发展,逐渐孕育了唐代的歌行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唐代歌行的体式结构、抒情、叙事特征探讨者较多[4],葛晓音从字法句式和篇法结构等方面探讨了歌行形制体调的规范问题[5],薛天纬在讨论盛唐歌行本质特征时,论及到歌行的命题方式问题,但对歌行命题方式与歌行体生成的关系未予深究[6]。歌行之名起于唐人对具有“歌”“行”“曲”“引”等音乐性标题类诗歌的泛称,从拟题方式角度对歌行体进行审视,将有助于揭示歌行体的生成机制及其与乐府诗的内在关联。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唐代古题乐府赋题法的运用入手,探讨赋题法与歌行拟题方式的关系,揭示乐府赋题法对唐代歌行体形成的意义。
一、拟赋古题:唐代古题乐府的基本方式
唐代文人在古题乐府中使用赋题法较齐梁更为普遍,从而带动了文人乐府诗的新发展。唐代古题乐府的拟题方式,元稹《乐府古题序》有详细论述。在元稹看来,拟赋古题的乐府诗,有“沿袭古题”和“寓意古题”两种情况[7]。元稹所说的“沿袭古题”主要是指以古题为主题的唱和之作,“寓意古题”则是指从古题中引发寄托,刺美见事,以古讽今。
(一)唐代古题乐府的几种类型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唐人古题乐府来看,有拟鼓吹曲、横吹曲、相和三调、吴歌西曲、琴曲和杂曲等类型。
拟鼓吹曲者:《乐府诗集》收录唐人作品四十余首,涉及《朱鹭》《艾如张》《上之回》《战城南》《巫山高》《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稚子斑》《临高台》《钓竿》等十余曲,作者有沈佺期、王勃、卢照邻、李白、韦应物、元稹、张籍、李端、孟郊、李贺等二十余人。
拟横吹曲者:《乐府诗集》收录唐人作品近百首,涉及《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望行人》《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刘生》等二十余曲,作者有卢照邻、王维、陈子昂、沈佺期、王昌龄、张九龄、李白、杜甫、韦应物、白居易、孟郊、张籍等四十余人。
拟相和三调者:《乐府诗集》收录唐人作品二百六十余首,涉及《箜篌引》《公无渡河》《江南曲》《度关山》《对酒》《陌上桑》《采桑》《日出行》《王昭君》《楚妃叹》《王子乔》《长歌行》《短歌行》《铜雀妓》《猛虎行》《君子行》《燕歌行》《从军行》《苦寒行》《豫章行》《相逢行》《秋胡行》《善哉行》《陇西行》《野田黄雀行》《雁门太守行》《蜀道难》《白头吟》《怨歌行》《长门怨》《婕妤怨》等六十余曲,作者有宋之问、王昌龄、高适、李白、杜甫、张籍、白居易、李益、李贺、李商隐等五十余人。
拟吴歌西曲者:《乐府诗集》收录唐人作品七十余首,涉及《子夜歌》《丁都护》《团扇郎》《碧玉歌》《懊侬歌》《读曲歌》《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乌栖曲》《莫愁乐》《估客乐》《襄阳乐》《江南弄》《采莲曲》等三十余曲,作者有王勃、张若虚、王昌龄、王维、李白、李贺、刘禹锡、张祜等三十余人。
拟琴曲者:《乐府诗集》收录唐人作品五十余首,涉及《白雪曲》《湘妃怨》《湘夫人》《拘幽操》《越裳操》《岐山操》《履霜操》《雉朝飞操》《思归引》《猗兰操》《龟山操》《双燕离》《烈女操》《别鹤操》《走马引》《昭君怨》《蔡氏五弄》《胡笳十八拍》《飞龙引》《婉转歌》等三十余曲,作者有沈佺期、李白、韩愈、孟郊、白居易、张籍、刘商、张祜、李贺等二十余人。
拟杂曲者:《乐府诗集》收录唐人作品二百八十余首,涉及曲题百余个。据《乐府诗集》解题,杂曲歌辞有几种情况:一是名存义亡,不见所起,而有古辞可考者,如《伤歌行》《生离别》《长相思》《枣下何纂纂》之类;二是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拟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如《出自蓟北门》《结客少年场》《空城雀》《悲哉行》之类;三是因意命题,学古叙事者,如汉阮瑀《驾出北郭门》,曹植《惟汉》《苦思》等行,《磐石》《驱车》《吁嗟》等篇[8]885。郭茂倩收录的杂曲歌辞或存古辞、或存拟辞、或学古而自作,说明这些杂曲其实早已不可歌了,而曹植、傅玄、陆机、鲍照等文人的杂曲歌辞大多是“因意命题”的赋题之作。唐代文人的拟作,或拟赋魏晋六朝文人的旧题,或从魏晋六朝文人的拟作中衍生新题。
(二)赋题法在唐代古题乐府中的广泛运用
郭茂倩《乐府诗集》在以上六类乐府中,收录了唐代古题乐府七百三十余首,涉及曲调二百余题。无论是鼓吹曲、横吹曲、相和三调、吴歌西曲、琴曲,还是杂曲,唐人的拟作大多是沿袭古题的“唱和”之作。赋题法在唐人古题乐府中已得到广泛运用。
如沈佺期、卢照邻、李端、孟郊、李贺、僧齐己等人的《巫山高》诸作,皆从横吹曲曲题“巫山高”着笔,以“巫山”“云雨”“神女”“楚王”等意象建构诗意,铺叙巫山环境,杂以楚王与巫山神女典故,其主题不离“巫山”之事。横吹曲《折杨柳》,唐代文人拟作均从曲题“折杨柳”立意构思。如卢照邻《折杨柳》:
倡楼启曙扉,园柳正依依。鸟鸣知岁隔,条变识春归。露叶疑啼脸,风花乱舞衣。攀折聊将寄,军中书信稀。[8]330
沈佺期《折杨柳》:
玉窗朝日映,罗帐春风吹。拭泪攀杨柳,长条宛地垂。白花飞历乱,黄鸟思参差。妾自肝肠断,傍人那得知。[8]330-331
这两首作品是对曲题《折杨柳》的直接拟赋,通过对女子攀折杨柳情态的铺叙,表达其相思离别之情。张九龄、孟郊、李端等诗人的作品也是直接赋题,如“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张九龄);“杨柳多短枝,短枝多别离。赠远累攀折,柔条安得垂”(孟郊);“赠君折杨柳,颜色岂能久”(李端)等。这些诗句直接绾合曲题“折杨柳”之意。卢思道、沈佺期、刘方平等人的《梅花落》,也是专咏梅花的赋题,通过咏梅之落以感时迈、聊寓相思。
唐代文人拟相和三调也多赋题之作。如李益《从军有苦乐行》,开篇“劳者且勿歌,我欲送君觞。从军有苦乐,此曲乐未央”四句,点明“从军有苦乐”的题旨,接着铺叙“仆”从军报国的“苦”与“乐”。这是以王粲《从军行》首句“从军有苦乐”为题的赋题之作。又如李白《相逢行》言“相逢其人仍不得相亲”,韦应物《相逢行》言“邂逅两相逢,别来间寒暑”,都是以《相逢行》曲题之“相逢”确立主题的。《相逢行》一名《相逢狭路间行》,又名《长安有狭斜行》。《乐府解题》曰:“古词文意与《鸡鸣曲》同。晋陆机《长安有狭斜行》云:‘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则言世路险狭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矣。”[8]508所谓“古词文意与《鸡鸣曲》同”,是指二曲歌辞中都有“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置酒作倡乐为乐”[8]406的内容,其字句和文意基本一致。古词《相逢行》和陆机《长安有狭斜行》是以歌辞的首句为题的,歌辞的主题和曲题并不相同,而李白、韦应物的《相逢行》则是以曲题为主题的赋题之作。《櫂歌行》,晋乐奏魏明帝“王者布大化”歌辞,“备言平吴之勋”;而陆机“迟迟春欲暮”,梁简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櫂而已”[8]592-594,已属赋题之作。骆宾王的《棹歌行》“写月涂黄罢”和徐坚的《棹歌行》“棹女饰银钩”,以叙写棹女乘舟、采莲、棹歌的场景为主,是沿承陆机、梁简文帝萧纲的赋题之作。
唐代文人拟赋魏晋文人旧题以及从旧题衍生新题的杂曲歌辞创作,其赋题性质更加明显,此不赘述。
二、寓意古题:唐代古题乐府歌行化转向
歌行体是唐代新兴的一种重要诗体,也是唐诗繁荣的标志性诗体之一,其与乐府诗的关系十分密切。以往学者对歌行与乐府的渊源关系多有论述,但歌行究竟是如何从乐府中生成的?其重要的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则相对较少。上文已述唐代文人的古题乐府诗创作很兴盛,而且在创作中普遍使用乐府赋题法。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人的古题乐府不止于简单拟赋古题,往往以古题之义寄寓社会现实,起到“引古以讽”的效果,元稹称之为“寓意古题”。这种“寓意古题”的创作方式对古题乐府的歌行化转向具有重要作用。
(一)歌行本出于乐府
歌行与乐府关系密切已成为历代学者的基本共识,有学者直接指出歌行来源于乐府。如明代“后七子”代表诗人王世贞曰:“七言歌行,靡非乐府,然至唐始畅。”[9]清人冯班《钝吟杂录》曰:“既谓之歌行,则自然出于乐府。”[10]42清人钱良择《唐音审体》曰:“歌行本出于乐府。”[10]781唐代歌行确实是在汉魏六朝乐府诗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诗体。
对唐代歌行的诗体学体认应该是从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开始的。元稹首先在《乐府古题序》中称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为“歌行”。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有“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并自注曰:“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11]此处的“歌行”与“新乐府”是互称的。白居易在其自编的《白氏长庆集》“感伤诗”类有一卷为“歌行曲引杂言”,《长恨歌》《琵琶行》皆在此卷。被元稹称为“歌行”的杜甫的4首作品均为“七言古体”诗,白居易称为“歌行”的一卷作品也是“七言古体”诗。另外,白居易《新乐府》50首和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在体式上也均为“七言古体”。可见,元白是将“歌行”和“新乐府”互称的,而且这些诗歌均是“七言古体”。宋初任昉等人编纂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将“诗”与“歌行”并列,“诗”类有“乐府”二十卷,多收“古题乐府”;“歌行”类二十卷,多收有“歌”“行”等音乐性诗题的“七言古体”诗和“新题”乐府诗。明代胡应麟则认为“七言古诗,概曰歌行”[12]。清代冯班《钝吟杂录·论歌行与叶祖德》曰:“今之歌行,凡有四例:咏古题,一也;自造新题,二也;赋一物,咏一事,三也;用古题而别出新意,四也。”[10]41
自唐以来,历代对歌行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尽一致,但从唐代诗歌创作实际看,唐代歌行是一种与七言古诗、古题乐府、新题乐府有诸多交叉关系的古体诗,其主体应包括七言古题乐府、新题乐府、有“歌”“行”等音乐性诗题的非乐府古题七言古诗以及记事性或酬赠性的七言古诗等四类。在这四类歌行中,七言古题乐府既是乐府诗也是歌行诗,是古题乐府创作歌行化的结果,其歌行化的重要机制就是乐府赋题法在唐代向寓意古题的创作转向。以下将以李白诗歌为例,具体分析古题乐府的歌行化问题。
(二)寓意古题与李白古题乐府的歌行化
李白的古题乐府在寓意古题、别出新意方面最为突出。如他的拟相和三调歌辞《猛虎行》开篇点题,“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接着引入安禄山叛乱、河北河南州郡相继陷没的现实,继而诗歌又以张良、韩信自况,感叹今时朝廷“亦弃青云士”,自己“有策不敢犯龙鳞”,表达诗人空有一腔报国之志,而不为朝廷任用的悲叹。《猛虎行》古辞云:“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陆机《猛虎行》“渴不饮盗泉水”是“言从远役,犹耿介,不以艰险改节也”[8]463,曲题与歌辞主题是不一致的。李白《猛虎行》以《猛虎行》曲题作为立意的基础,以古讽今,关涉唐代的现实问题。
又如,李白《出自蓟北门行》叙写一次反击匈奴的激烈战斗。诗歌通过对惨烈战斗场面和艰苦环境的渲染,赞美将士们“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的英勇气概。《乐府解题》曰:“《出自蓟北门行》,其致与《从军行》同,而兼言燕蓟风物,及突骑勇悍之状。若鲍照云‘羽檄起边亭’,备叙征战苦辛之意。”[8]891曹植《艳歌行》有“出自蓟北门,遥望胡池桑”[13]的诗句,可见《出自蓟北门行》曲题当来自曹植的诗句,徐陵“蓟北聊长望”、庾信“蓟北还北望”是对鲍照《出自蓟北门行》的赋题之作。李白《出自蓟北门行》未拘泥于古题的蓟北征战之义,而是通过古题寄寓了对唐王朝征伐北方诸部之战的高度关注。如瞿蜕园所说:“太白此词则必为开元、天宝之际,命将征伐吐谷浑、奚怒、吐蕃而作也。”[14]403李白《北上行》是拟赋曹操《苦寒行》“北上”篇的作品,该诗写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诗歌开篇“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点明古题“征行之苦”;接着写北上太行的艰难之状,并以“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暗喻安禄山范阳兵乱导致的河北大面积战乱,以“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暗喻安禄山攻占东京洛阳僭位称帝,渲染河北人民遭遇战火的流离之苦;结尾“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四句绾合开头,突出“北上苦”的主题,表达恢复王道太平的强烈愿望。诗歌以《苦寒行》古题的“征行之苦”寄寓安史之乱导致的人民流离之苦,以古题刺时事。元人箫士赟评此诗曰:“隐然有《国风》爱君忧国劳而不怨厌乱思治之意。”[14]407可谓的评。
李白的古题乐府大多具有“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的特点,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古题乐府的主题,还有意识地突破古题乐府的体制结构,如前举李白《猛虎行》《北上行》都是将古题乐府《猛虎行》《苦寒行》的五言体制改用七言;又如六朝萧纲、刘孝威、阴铿三人的古题乐府《蜀道难》都是五言体,李白将之七言化,古辞及晋乐所奏的《白头吟》两个文本都是五言体,李白则改用七言创作。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李白古题乐府120余首,其中七言达到近60首,几乎一半采用了七言歌行体。所以,有学者认为“李白的‘古题乐府’实际上已经‘歌行化’”[15]。
唐代文人在古题乐府创作中的寓意古题之法,不仅拓展了古题乐府的主题和创作空间,也突破了古题乐府的体制约束,使古题乐府的创作逐渐歌行化。元稹《乐府古题序》不仅肯定了寓意古题的古乐府之法,而且将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抛开传统乐府古题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作直接称为“歌行”了。
三、乐府赋题法与唐代歌行的拟题方式
从拟题方式看,唐代歌行大体有拟赋古题、主题+歌词性诗题、自拟非歌词性新题等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中,前两种拟题方式都是乐府赋题法在歌行中的创造性运用,第三种类型则是对乐府赋题法的超越。
(一)拟赋古题

唐代文人的拟乐府多“寓意古题”而别出新意,是对乐府诗赋题法的开拓和创新,在体式上则有明显的歌行化趋向。如李贺《艾如张》:
锦襜褕,绣裆襦。强强饮啄哺尔雏。陇东卧穟满风雨,莫信笼媒陇西去。齐人织网如素空,张在野春平碧中。网丝漠漠无形影,误尔触之伤首红。艾叶绿花谁剪刻,中藏祸机不可测。[8]234
《乐府诗集》解题曰:“古词曰:‘艾而张罗。’又曰:‘雀以高飞奈雀何?’《谷梁传》曰:‘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谓因蒐狩以习武事也。兰,香草也,言艾草以为田之大防是也。若陈苏子卿云:‘张机蓬艾侧。’唐李贺云:‘艾叶绿花谁剪刻。’俱失古题本意。”[8]226诗歌不依《艾如张》古题本意,而是直接赋题的。
又如张籍拟赋《朱鹭》:
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树。羽毛如翦色如染,远飞欲下双翅敛。避人引子入深堑,动处水纹开滟滟。谁知豪家网尔躯,不如饮啄江海隅。[8]233
该诗写一只翩翩而飞的朱鹭,春日在绿树间嬉戏,为了躲避人的箭头而掉进深沟中的情景。末两句“谁知豪家网尔躯,不如饮啄江海隅”,以朱鹭的口吻表达了诗人逃避残酷现实的归隐之情。全诗主体以铺叙朱鹭为主,末两句笔锋转向现实,见出新意。
《朱鹭》《艾如张》是《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古曲调,《艾如张》古辞句式由四言、三言、七言构成的杂言体结构,陈代苏子卿拟作为用五言八句齐言结构,李贺《艾如张》则使用七言歌行结构。《朱鹭》古辞句式由三言、五言构成,梁代王僧孺、裴宪伯、陈后主、张正见、苏子卿拟作均为五言体结构,张籍则使用了歌行体结构。
可见,唐代古题乐府的“寓意古题”之法是对赋题法的有效拓展,通过寓意古题,或以古讽今、美刺时事,或别出新意,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古题乐府的创作空间,还超越了古题乐府的体制约束,成为乐府诗创作歌行化转向的关键。
(二)主题+歌词性诗题
“歌”“行”“曲”“引”等音乐性字眼本身就是乐府诗常用的诗题,表示乐府诗的音乐类别。正如胡震亨说:“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18]其中以“歌”“行”名题者最多。唐代文人在乐府诗创作中,已不满足于齐梁乐府诗的赋题之法,想极力摆脱乐府古题及其体制的约束,尝试在诗题上突出诗歌主题,但又要体现这些诗歌与乐府诗的渊源关系,尽量保留乐府诗题那些歌词性的字眼,于是形成“主题+歌词性诗题”的拟题方式。因“歌”“行”在乐府歌词性诗题中的数量最多,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类音乐歌辞,于是人们将这类作品称为“歌行”。这类拟题方式的作品在唐代歌行中最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歌行体的重要“标识”。
在具体拟题上,有的将主题字置于歌词性诗题前面,如李白《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杜甫《兵车行》《丽人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李颀《听安万善吹筚篥歌》、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望云骓马歌》等。有的则将主题字置于歌词性诗题后面,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李白《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杜甫《玄都坛歌寄元逸人》《狂歌行赠四兄》《短歌行赠王郎司直》《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释皎然《白云歌寄陆中丞使君长源》《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等。
这种拟题方式因自拟诗歌的主题而消弭了乐府诗的古题,仅保留了古题歌词性诗题的字眼。若从其对乐府歌词性诗题保留的角度看,这种拟题方式还没有完全超越乐府诗的赋题法,仍然属于对乐府诗赋题法的创造性拓展。当然,在这种开拓创新中,逐渐孕育了唐代歌行诗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抒写模式和气势流畅、声情跌宕的体制特征。
(三)自拟非歌词性新题
从唐代创作实践来看,这类拟题方式大概包括两类诗歌:一类是新题乐府,新题乐府从杜甫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后来得到李绅、元稹、白居易的大力鼓吹和积极倡导。其作品如杜甫《悲陈陶》《哀江头》、白居易《新乐府》50首、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等都明确宣称是新题乐府,又称为歌行。另一类则是非乐府的新题歌行,如《文苑英华》“歌行”类收录的李白《忆旧游赠谯郡元参军》、李颀《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送陈章甫》、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送张山人归嵩阳》、李贺《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等,这些作品都是自拟的非歌词性新题歌行。白居易《感伤诗·歌行曲引杂言》卷收录的自拟非歌词性新题有《王夫子》《江南遇天宝乐叟》《山石榴寄元九》等作品。从诗歌的拟题方式来看,这类歌行已超越了乐府诗的赋题之法,完全是“因事立题”“即事名篇”的自拟新题,因诗题突出主题而忽略诗歌的体类属性,使之与其他类别的文人诗在诗题上没有分别。这种自拟新题的非乐府歌行,句式以七言为主、章法转换层叠、叙事铺张扬厉、篇制长短自由,其体类属性主要通过诗歌的篇章结构体现。盛唐称之为“长句”,中唐则多称之为“歌行”①。
关于唐人歌行的赋题之法,清人冯班《钝吟杂录·正俗》有一段评析:
文人赋乐府古题,或不与本词相应,吴兢讥之,此不足以为嫌,唐人歌行皆如此。盖诗人寓兴,文无定例,率随所感。吴兢史才,长于考证,昧于文外比兴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记其柱也。必如所云,则乐府之文,所谓床上安床,屋上架屋,古人已具,何烦赘剩耶?又乐府采诗以配声律,出于伶人增损并合,剪截改窜亦多,自不应题目,岂可以为例也?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忠志远谋,方为百代鉴戒,诚杰作绝思也。[10]42
这段话重点强调了两方面意思:一是唐人拟赋古题的歌行多是与古题本辞不一致的寓兴之作;二是杜甫的新题乐府,指论时事、颂美刺恶的现实精神,符合诗歌对比兴寄托的追求。在这里,冯班肯定了唐代歌行的赋题之法,特别是称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为“杰作绝思”。冯班对歌行体的评析是符合唐代歌行体实际的。
结语
总之,齐梁以来的文人乐府赋题之法,对乐府古题和本辞产生了极大的消解作用,这种消解为拟乐府提供了自由的创作空间。从此,乐府拟作既可以沿袭古题之义而赋予时代新的体式结构,也可以寓意古题,挖掘古题的时代意义,从而为乐府拟作在主题内容和体式结构上的创新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因赋题法的广泛使用而形成的乐府诗主题与曲题的对应关系,为自立新题的新乐府创作提供了思路,唐代的歌行诗创作就是循此思路展开的。唐代拟赋古题的那些歌行诗本是在拟古乐府的创作中形成的,诗人在古题乐府的创作中大胆创新,或通过古题寄托时事、以古讽今,或从古题中别出新裁、另立主题,积极拓展古题乐府的创作空间;诗歌体式也开始超越古题乐府的制约,逐渐歌行化。当然,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歌行诗是“主题+歌词性诗题”的一类,这类歌行突出诗歌的主题,是对古题乐府赋题之法的进一步突破,其对“歌”“行”“曲”“引”等歌辞性字眼的保留,表明其与乐府诗的渊源关系,最具歌行诗的“标识”意义,歌行体之名就是在对该类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歌”诗与“行”诗的泛称中形成的。自拟非歌词性新题的一类歌行诗当是诗人对诗歌主题的一种强化,其体类属性只体现在诗歌的篇章结构上。可以说,唐代歌行体创作的兴盛与繁荣与文人乐府诗对赋题法的开创与拓展关系甚为密切。
注释:
① 岑参有《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自称“长句”。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云:“玉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长句。”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仇兆鳌《杜诗详注》曰:“计东曰:长句,谓七言歌行,太白所最擅长者。太白长句,其源出于鲍照,故言何刘沈谢但能五言,于七言则力有未工,必若鲍照七言乐府,如《行路难》之类,方为绝妙耳。公尝以‘俊逸鲍参军’称太白诗,正称其长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