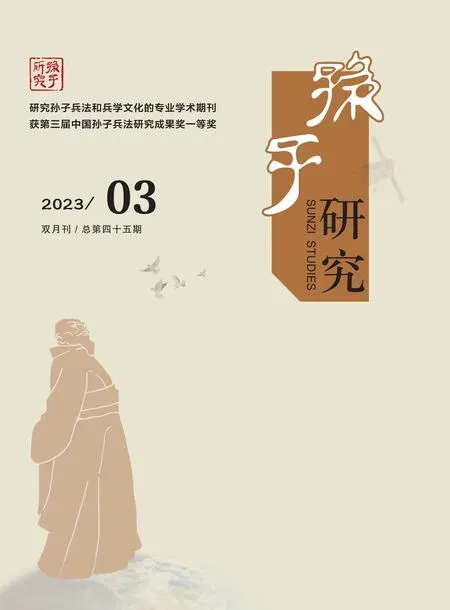有备无患:《盐铁论》的备战军事思想论析
吴功翔 桂珍明 夏保国
《盐铁论》是一部西汉昭帝时期召开的全国性经济会议的会议记录,宣帝时由时任庐江太守丞的桓宽整理而成。书中记录了以桑弘羊为首的“公卿”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生围绕汉武帝时期施行的包括盐、铁、酒榷、均输等国家专卖的经济政策而展开的全面讨论。这场大论辩反映了西汉中期汉王朝的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举措。会后,取消了酒的专卖和部分铁官,对汉武帝时期实行的官营政策做了限制和修改。〔1〕这不仅影响了昭宣时期国家政策的走向,还对西汉建国百余年来针对匈奴的国防策略有一定的调整。
近年来,学界对《盐铁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汉中期的国家财政、经济政策方面,间或有文献学、思想史和社会史方面的成果问世,而对于《盐铁论》中的军事思想研究则较为薄弱,目前少有专门研究论著。〔2〕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长达百余年的战争背景下,《盐铁论》记载了公卿与贤良、文学对于战争的性质、准备过程及战后影响等方面所持彼此对立的观点,尤其在针对匈奴的军事备战方面,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公卿”,面对贤良、文学批评“贵以德而贱用兵”“废道德而任兵革”、大肆鼓吹战争无益和领土无用的消极论调,据理力争,强调了对匈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阐明了“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的备战思想。
一
终西汉之世,统治者非常重视军事战备,尤其在北方匈奴对汉王朝造成强大的军事威胁情况下,积极备战御边的作用十分突出。自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匈奴已然成为汉王朝最强劲的军事对手。匈奴凭借骑兵的高机动性及投降匈奴的汉族将领的指引,频繁侵扰北方边境,刘邦为此忧虑不止。“是时匈奴以汉将数率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高祖患之,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3〕此后直到武帝前期,汉王朝一直奉行“和亲”政策,以求得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防备匈奴侵扰也成了汉王朝军事行动决策中首要考虑的因素。南朝刘宋何承天作《安边论》就曾明确指出:“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 志。”〔4〕此即点出了汉代在对匈奴方面“武夫”和“儒生”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态度,而这种差异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自刘邦建立西汉之初到武帝前期,尽管汉王朝整体上崇尚“黄老”思想,施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朝堂之上对匈奴的战和抉择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主和派以高祖时期的刘敬、惠帝吕后时期的季布和武帝时期的韩安国为代表,他们主张继续奉行和亲政策,将宗室之女嫁予单于,其所生之子理论上必为匈奴政权的继承人,企图在血缘纽带的牵制下减少战争冲突,进而将政治关系转化为亲情关系,从心理情感上解决双方的政治矛盾。这从刘敬给刘邦的对策中不难看出:“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5〕季布主张和亲的理由源于对匈奴的畏惧心理,这是在高祖时期就遗留下来的。“夫以高帝兵三十余万,困于平城,哙时亦在其中。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谩!且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6〕意即雄才大略的高祖刘邦率三十余万身经百战之众尚且为匈奴所困,今国家百废待举,满目疮痍,何以与匈奴战?而“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此即为典型的“匈奴不可战胜”心理在作祟。韩安国则认为发动对匈战争百害而无一利,不如和亲。他认为对匈战争:“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飘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7〕
主战派则以高祖吕后时期的樊哙,文景时期的贾谊、晁错,武帝时期的王恢、张汤等为代表,极力主张汉王朝对匈奴用武。吕后时,匈奴寇边,樊哙自认为“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贾谊是主战派中观点最为激进的,他认为汉王朝与匈奴本是君臣关系,奉行和亲政策是本末倒置的体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8〕进而认为应该武力征服匈奴,并将之变为郡县以防备其他边地民族,“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皆属之置郡”〔9〕。晁错认为,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军事装备,汉王朝都对匈奴具有绝对优势:“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10〕不过,在政策执行方面,晁错则偏向理性,强调要从实际出发,练兵备战。高祖刘邦亲征匈奴惨败而归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汉王朝君臣之中,数十年挥之不去。甚至匈奴侵略边境而武帝问计于朝臣时,韩安国及博士狄山仍以高祖被围白登之故事极力劝阻武帝征伐匈奴。王恢针对蔓延朝堂的恐战心理,认为高祖的失败不过是偶然的,毕竟胜败乃兵家常事,“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他认为目前对匈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诱敌深入,做好充分准备,采用伏击战术,必定能战胜匈奴。“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11〕张汤也反对“和亲”,据《汉书·张汤传》载:
匈奴求和亲,群臣议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天下寒心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12〕
狄山所谓“兵,凶器”也见于《国语·越语》及《尉缭子》之《武议》《兵令上》两篇,与《道德经》“兵者,不祥之器”近似,具有较为典型的黄老思想特征,主张“和亲”者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这种“凶”和“不祥”的现实原因是战争导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而张汤具有法家的特征,他反对在匈奴问题上采取妥协政策,故其支持“兴兵击匈奴”的政策。法家对内主张严刑峻法以集中君权,对外则“尚首功”以扩张疆土,主张实施积极的国土防御之策,因而他对于带有黄老道家特征的儒生及部分臣子老生常谈的国家疲敝、资费耗巨、匈奴不可战胜等观点弃如敝履也在情理之中。
二
西汉前期,汉王朝在对匈奴的战和之间举棋不定,执政者多有“主和”意向。一方面,由于高祖“白登之围”遗留下的恐战心理迟迟得不到消解,匈奴不可战胜的阴霾长久挥之不去;另一方面,匈奴离汉王朝数千里,其社会制度、军事组织等情况对汉朝君臣来说十分不熟悉,无法做到知彼知己,从而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此外,一些具有黄老思想的儒生大肆鼓吹“贵以德而贱用兵”“王者行仁政”、领土无用、民生凋敝等言论,对统治者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直至武帝前期,每当匈奴侵扰边地,即便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对此也十分谨慎,只能组织朝臣廷议,分析利弊得失,极少表现出中后期的杀伐果断。在此种趋于保守的大环境下,汉廷在坚持“和亲”政策的前提下,在边境地区以略为保守的军事备战为主。《史记·匈奴列传》载: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13〕
同书《孝文本纪》亦载:
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14〕又《汉书·李陵传》曰:
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15〕
综上,可见西汉前期汉王朝在“和亲”政策主导下,也做了两手准备。为防备匈奴而展开的一系列的“备胡”军事行动,激发了汉王朝强烈的备战意识,这为武帝中后期反击匈奴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并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除了在边境地区派兵遣将、布置防务外,朝堂内部也积极就备战问题讨论相应的举措,晁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主张积极备战的一位大臣。他先后向朝廷上《言兵事疏》《复言募兵徙塞下》《守边劝农疏》等奏疏,认为汉初边地实行逐年轮换的“卒戍”之策存在很大缺陷,应更换常驻军队以屯垦备之。“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 之。”〔16〕另外,他认为朝廷应该从将帅选择、训练士卒、移民实边、纳粟拜爵及以夷制夷等方面提高对匈奴的战备水平〔17〕,这与刘敬的“强本弱末之术”有相同之处。(刘敬主张迁关东六国贵族以实边地,这不仅便于控制,防范叛乱,而且可加强防备匈奴入侵的军事力量,此即所谓“强本弱末之 术”。〔18〕)不仅如此,晁错还就军制改革、选贤任能、赏罚分明等方面阐明自己的主张: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19〕
西汉王朝备战匈奴的另一大表现,就是十分重视马政建设,这不论是在传世典籍里还是在近现代出土的简牍材料中都有重要体现。《汉旧仪》载:“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20〕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悬泉汉简等简牍皆有相当的篇幅专门记载汉代的马政情况,内容包括马匹日常饲料的供给、记录马匹相关情况的详细信息以及马匹疫病的治疗等。〔21〕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即反映出西汉政府对马匹流动管控十分严格,表明这一时期政府对“马政”的重视程度:
议,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扞)关、郧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其买骑、轻车马、吏乘、置传马者,县各以所买名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内史、郡守各以马所补名为久久马,为致告津关,津关谨以藉(籍)、久案阅,出。诸乘私马入而复以出,若出而当复入者,出,它如律令。御史以闻,请许,及诸乘私马出,马当复入而死亡,自言在县官,县官诊及狱讯审死亡,皆津关,制曰:可。〔22〕
而依据悬泉汉简的记载,马匹在出入关津时要将马匹的数量、颜色、马龄、身高、牝牡等信息详细记录在册,可见汉代对马匹控制之严,目的之一就是保证国家军马的来源。
由于常年与擅长骑射的匈奴骑兵作战,汉廷尤其需要强大的骑兵作为机动部队,因而军马输送就成为战备工作的重点。西汉时期的马政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高效的运转机制,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组织完备,分工明确。养马的机构既有国家常置的马厩,也有边郡畜牧条件优良的牧苑;管理的方式除了国家专设的政府机构,也鼓励民间私人养马以及通过“官贷民牧”的方式为军队提供充足的战马资源。〔23〕中央设太仆统管国家养马业,地方则有专门掌管地方马政的官吏,近世出土的汉代印章多有“马丞印”“骑丞印”“厩丞印”“中厩”等,证明了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完整的马政系统。〔24〕
三
汉廷君臣在对匈奴是战是和的选择上产生了长达数十年的分歧。虽然文帝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府库充盈,武备齐整,但仍不敢贸然主动出击匈奴。景帝时更是没有利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余威北上反击匈奴,而是继续维持“和亲”政策下的双方暂时和平。及至武帝中后期,方才实现了对匈奴从前期的保守向积极防御甚至主动反击的策略转变,并取得了重大战果,有效遏制了匈奴南下的势头,甚至使匈奴出现了“幕南无王庭”的局面。但这仍是在武帝个人意志下推行的饱受争议的对匈奴战略,朝堂之上仍有不少反对战争的声音,且这一现象在武帝去世后愈演愈烈,盐铁会议则是将对匈奴战与和的争论推向了高潮。
武帝时期对外战争占据了其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对周边的匈奴、百越、朝鲜、西南夷和西域等发动大规模战争并多数取得胜利,“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使中国“千万年皆食其利”〔25〕。同时,连年征战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不仅使文景时期留下的雄厚物质财富挥霍一空,而且行政僵化导致吏治腐败,民力疲敝,关东流民就达数百万之巨。〔26〕尽管武帝晚年发布《轮台诏》似有调整路线之意,然而这并未使得本不乐观的国内形势得到改观。〔27〕班固对此评论道: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28〕
针对武帝晚年遗留的社会问题,昭帝即位后,国内秩序在霍光、桑弘羊等重臣的辅佐下基本走向稳定。为进一步化解国内矛盾,“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于是始有盐铁之会。盐铁会议的主题是贤良、文学认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因此,“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29〕。但桑弘羊一针见血地指出:
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30〕
也就是说,盐、铁、酒榷、均输等专营政策的实行是为对匈奴战争服务的,而这些政策正是武帝时期汉廷主动发起对匈奴战争并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保障。桑弘羊正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他目睹了这些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利好,因此坚决反对废除盐、铁、酒榷等专营政策。丞相史也说:“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私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31〕证明桑弘羊完全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并非为了一己之私。
四
然而,贤良、文学打着“贵以德而贱用兵”(《本议》)的旗号大肆宣扬仁义道德,认为对匈奴反击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本议》),战争持续下去只会导致“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胡》),“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本议》)。他们认为当下应“偃兵休士,厚币结合”“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世务》),极力主张削减军队,废毁关梁,倡导文德道义,“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32〕。他们认为“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本议》)。更荒谬的是,他们竭力主张“领土无用”,“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今去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阪菹泽 也”。〔33〕因此,儒士认为只需守护好汉王朝这片土地即可,经营边境之地实乃劳民伤财之举,不但使得百姓困于赋役,还要耗费大量财政用于边境防务。
面对贤良、文学的百般刁难和种种谬论,桑弘羊坚定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坚守中央集权的根本国策,坚持对匈奴的反击战争,大气凛然地批驳了贤良、文学们不愿备战而走“不如和亲”的投降主义路线,掷地有声地反问:“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34〕桑弘羊正确总结了“和亲”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训,指出匈奴“贪侵”成性,“百约百叛”,一贯反复无信,一有机会就发动侵略汉朝北部边境的战争,给边地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面对这样反复无常且狡诈凶恶的敌人,绝不能存有任何幻想,只能用反侵略战争彻底将其打败,而不可能试图以仁义道德感化之。
至此,桑弘羊明确阐发了他的备战思想:“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不征备,则暴害不 息。”〔35〕“事不豫辨,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诗》云:‘诰尔民人,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备。昔宋襄公信楚而不备,以取大辱焉,身执囚而国几亡。”〔36〕也就是说,事先不做准备,临时就不可能应付突然事变,而匈奴长年侵扰边境,因此必须坚持屯边政策,“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37〕。坚持备战就必须依靠强大的财政支持,而盐铁专营则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保障,“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38〕。针对贤良、文学的“领土无用”论,桑弘羊认为边境地区是汉王朝的屏障,没有边境的宁定,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他说:
缘边之民,处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扞也。《诗》云:“莫非王事,而我独劳。”刺不均也。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何求而不默也?〔39〕
在桑弘羊看来,对匈奴战争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的正义之战,但在道义上占据主动只是其一,现实状态下必须积储国力,长期坚持练兵备战,强化备战意识,做到武帝强调的“‘无(勿)废备’者,无(勿)乏武备,常备匈奴也”〔40〕。简而言之,桑弘羊的备战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 人”〔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