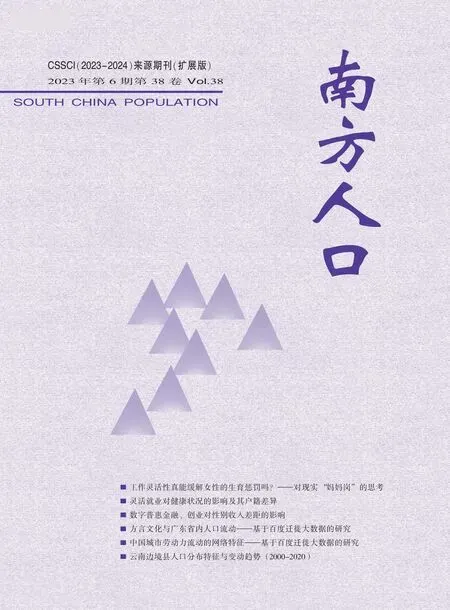灵活就业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户籍差异①
陈彦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1 引言
20 世纪70 年代经济“滞胀”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社会受到了质疑。一些西方国家对资本的管控有所放松;对工人的保护政策弱化;政府的货币政策收紧,公共福利支出紧缩;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以实现自由贸易[1]。在这个背景下,发达国家资本的权力有所扩张,雇主偏好以灵活用工的方式降低用工成本,由于对工人保护措施弱化,解聘工人也变得更加容易,工人稳定就业的难度变大,灵活就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随着20 世纪80 年代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缩紧,拉美与非洲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下以结构性调整的方式应对债务危机,这种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全球化体系面临困境,失业率上升,非正规经济不断发展,灵活就业群体在发展中国家也趋于扩张[2]。
灵活就业意味着非规范的雇佣关系,包括兼职工作、劳务派遣、短期与临时性的工作以及独立承包等[3]。在中国内地,灵活就业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困境也变得更加明显,就业稳定性的差异带来了劳动者的工资差距[4],逐渐成为区分劳动者地位的重要方式。与其他职业分类方式不同,灵活就业是一种就业状态,职业地位高的群体与职业地位低的群体都可能是灵活就业者。
灵活就业者往往面临着工作质量更低,组织支持较少与工作不安全感等诸多困境[5],这些因素使得他们的健康状况比稳定就业者更差。随着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增加,灵活就业人员的健康状况对社会整体健康程度的重要性也在提高。那么,中国灵活就业者是否与稳定就业者有着明显的健康差距,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与西方国家是否相同?
稳定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在健康状况上的差异还受到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以往,灵活就业者往往指的是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群体,但随着单位制消解、民营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兴起,城镇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不断增加。那么,不同户籍制度劳动者,灵活就业对健康的影响是否有差异呢?在中国,户籍制度从两个维度界定了人们的社会身份,一是“农业-非农业”维度,二是“本地-外地”维度,非农户籍劳动者与本地户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户籍甚至已经构成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结构。然而,关于外来农民工与本地户籍居民的健康差异,一直存在争议。健康移民效应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健康状况平均要优于本地人,因为健康状况相对更好的个体更可能选择迁移[6]。健康损耗效应则强调,迁移经历会对个体的健康带来损害[7]。经验研究发现,中国同时存在着健康移民效应与健康损耗效应[8-9],并且健康损耗严重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可能离开城市,这使得外来农民工与本地户籍居民未出现明显健康差异[10]。然而,这些研究并未涉及外来农民工中灵活就业者与稳定就业者的健康差异,那么,在外来农民工群体中,灵活就业者与稳定就业者的健康差距是否更大,优势户籍身份能否会为其他灵活就业者提供庇护效应?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灵活就业者的健康状况
关于灵活就业如何影响健康,西方社会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视角:
其一是工作质量上的差异。稳定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工作强度、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与工作回报是不同的。首先,灵活就业者接触的工作强度大,更高的工作强度会增加他们面对不利健康状况的风险[11]。其次,灵活就业者的工作环境更糟糕,更容易接触物理/ 化学危害,以及出现肌肉骨骼和精神方面的不良症状。针对希腊劳动者的研究发现,希腊的职业事故率并没随国内生产总值的降低而减少,而是随非全日制和轮换期工作合同的显著增加而增加[12]。再次,灵活就业者虽然拥有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但是他们往往需要工作更长时间来维持收入,这种过劳会对健康带来负面影响[13];除此之外,灵活就业还直接带来了收入上的惩罚,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回报[14]。
其二是组织支持上的差异。工作组织与劳动者较低程度的身心契约关系使得劳动者失去了组织能够提供的健康保护。首先,灵活就业会导致工人议价权力的下降,带来工作强度的提高。工会是保障工人议价权力的重要因素,而灵活就业者更可能失去工会对自身的保护作用。临时工人由于其工作的不稳定性无法与工会建立较稳定的联系,因而处于劣势地位。其次,灵活就业者在通过组织获得社会保障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更不可能依靠组织力量缴纳医疗保险。根据马萨诸塞州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女性移民的访谈发现,低技能的临时工作是围绕着满足雇主的工作绩效期望而形成的;由于雇主与工人关系的契约关系较弱,工人的福利保障需求因而也得不到满足,进而导致工作环境差、工人受保护较少、健康状况不佳[15]。雇主在工作福利与社会福利方面的缺席,对工人的身心健康乃至其家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负面溢出效应[16]。
其三是社会心理上的不平衡,灵活就业还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状况来影响健康。韩国与意大利的研究者都证实了灵活就业会导致心理问题:相比于稳定就业者,灵活就业者更可能变得抑郁和脆弱[17],这种心理上的抑郁与脆弱性会最终带来个人健康的损耗[18]。灵活就业影响健康的机制会通过两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来实现的:第一,灵活就业意味着更低的社会认同和自尊。恶劣的工作条件、不断寻找工作所需的投资以及反复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则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当就业不能促进个人自我实现、发展能力和与他人建立关系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就变成了“非工作”[19],这种“非工作”将会降低工人的社会认同。第二,灵活就业带来相对剥夺感。稳定就业者在社会结构中占有更有利的地位,面对更少的风险,具有更好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而灵活就业者往往有着较长的工作时间,付出更多的精力,但是仍然在经济收入中处于不利地位,根据工作付出—回报不平衡模型(the 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高付出—低回报”也同样带来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发展出不利的健康地位[20]。主观社会地位的下移与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是影响身体健康的重要心理机制。
本文认为,在中国,灵活就业者与稳定就业者在工作质量、组织支持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可能也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二者的健康状况出现差异,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1:相对于稳定就业者,灵活就业者的工作质量更差,即工作收入更低,工作时间更长。
假设1.2:相对于稳定就业者,灵活就业者的组织支持更少,即加入工会的可能性更低,参与社会保险的可能性更低。
假设1.3:相对于稳定就业者,灵活就业者的心理失衡更强,即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地位认同更低。
假设1:相对于稳定就业者,灵活就业者的健康状况更差。
2.2 制度分割下的灵活就业与健康不平等
制度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灵活就业者的健康程度与这个国家针对劳动者的工作制度与福利制度密切相关,在一个对灵活就业者给予充分保障的国家,灵活就业者面临的健康风险会大大缩小。
西方学者在关注健康不平等的宏观制度因素时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制度与福利制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工业制度,西方以市场为导向、强调高度分工的福特主义(Fordism)是影响灵活就业劳动者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在福特主义企业,雇主采用多种方式破坏工人群体之间的团结,提高管理效率,而雇员由于工作场所的不确定性而难以结成稳定的工会组织。这使得灵活就业的雇员们面临着较多的职业暴力风险[21]。考虑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去工会化趋势,灵活就业者的健康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其次是福利国家制度,研究者根据六种福利国家类型对选定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类,结果表明,福利制度可能是灵活就业与健康关系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福利国家,灵活就业者的健康状况比稳定就业的同龄人更好或相等。在这些国家,失业工人在寻找新工作、收入补偿、教育和工作培训方面得到了大量的保护和帮助[22]。临时性的工作通过给予工人一种自主性和协商工作条件的自由感来增进工人的健康和福祉。相比之下,在其他的福利制度中,灵活就业意味着与不良的健康结果相关。
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揭示了,灵活就业与健康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各种制度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福利制度的调整与工业制度的变革将会使其关系不断变化。同时,职业对健康的影响机制需要纳入特定制度的框架下加以考察。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福利制度具有户籍分割属性。虽然自2014 年之后,国家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政策措施一定程度缩小了户籍间的不平等,但并不代表户籍差异的消失;尤其是优势户籍的劳动者会继续享受一定程度的庇护。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其一,本地与外地户籍的区分;其二,非农与农业户籍的区分。本研究根据户籍的两种属性将城市就业的劳动者区分为四种类型:外地非农户籍、外地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与本地非农户籍[23]。
同样是灵活就业者,不同户籍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在常规模式下,灵活就业与稳定就业在健康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在户籍分割体制下,优势户籍劳动者可能受到户籍制度的保护。这些积极效应体现为对于诸多影响健康的因素产生了保护效果:
首先,户籍制度使得优势户籍的灵活就业者受到的工作排斥更少。从社会排斥的视角来看,户籍制度会在获取资源方面对非优势户籍的成员产生排斥[24-25]。相比于非农户籍和本地户籍,外地农业户籍的劳动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的收入得到增加。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户籍分割的存在,同样是灵活就业,本地户籍与非农户籍的劳动者更可能从事的是收益更高的灵活就业,而外地农业户籍的劳动者集中于灵活就业的底层。这些底层的就业岗位往往收入较少而劳动时间更长、工作强度更大,比如按日结算工资的体力劳动者与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户。这些外来农民工群体在工作时间方面往往处于被动选择的状态,难以获得劳动法的保障[26]。因而,由于户籍歧视的存在,外地农业户籍内部稳定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工作质量差异可能更加明显,而优势户籍的灵活就业者则可能受到庇护。
其次,户籍制度使得优势户籍的灵活就业者得到更多的组织支持。根据制度主义的观点,组织对员工的福利承诺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一种基本社会制度,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组织支持。
最后,户籍制度使得优势户籍的灵活就业者较少受到刻板印象威胁。根据社会边界理论,户籍身份本身是一种符号屏障,外地农业户籍人口被长期排斥在城市的社会边界之外,特定的身份特征会引发优势对非优势户籍居民的异己感,带来居民间的社会矛盾;外地农业户籍的社会成员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困难,这引发了心理的疏离感与不安全感[27]。在2006 年至2015 年期间,中国劳动力出现了“短工化”的现象,外来农民工自评的社会地位呈现了下降趋势[28]。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形成以下假设2:本地户籍身份或非农户籍身份会对灵活就业者的健康状况产生保护效应,即健康状况上的差异在外地农业户籍的“稳定—灵活”之间表现得更明显。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为确保数据搜集的连续性和变量测量的一致性,本研究使用CGSS2012、2013、2015、2017 四期数据进行分析,并筛选了城市地区工作、年龄为18-60 岁、从事非农职业的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共计13979 个。本研究对主要自变量(灵活就业)与所有中介变量的缺失值进行了多重插补,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3836 个。
3.2 变量
本研究主要的解释变量是灵活就业,并将无雇佣单位、临时工作人员、受雇但非全职工作、受雇于私营单位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归为灵活就业者,其余劳动者归为稳定就业者。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者自评健康状况,上述各期CGSS 询问了受访者的健康状况:“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健康=5)”。考虑到对有序logit 模型的解释较为困难,而采用logit 模型对“一般”的健康分类存在争议,本文将自评健康处理成取值为1-5 的连续型变量,得分越高表示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分别为工作质量、组织支持与心理状态。一是工作质量,用个体年收入与工作时间两个指标来测量,本文将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后放入模型,考虑到不同年份劳动者收入的可比较问题,对个人年收入按照当年物价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CGSS 询问了受访者“一般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多少个小时”,在对特殊值进行处理后作为“工作时间”变量纳入模型。二是组织支持,通过工会参与及医保参与两个指标进行测量,CGSS 询问了被访者工会参与(“请问您是不是工会会员?”)及医保参与(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城市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公费医疗)的状况。三是心理状态,通过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公平感进行测量,将受访者关于自身在社会中等级的看法作为对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其取值均为1-10;将“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完全不公平=1,比较不公平=2,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3,比较公平=4,完全公平=5)”作为社会公平感的测量,得分越高代表相对剥夺的程度越低。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层次的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政治地位、教育年限以及时期变量,其中,时期变量以2012 年作为参照纳入模型。
3.3 模型
本文主要运用的是OLS(普通最小二乘法)。考虑到灵活就业与自评健康状况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替代被解释变量、倾向值匹配以及工具变量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就自评健康状况而言,外地农业户籍劳动者的自评健康状况要好于其他劳动者,尤其是显著好于本地农业户籍的劳动者,但本地与外地的非农户籍劳动者在健康状况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就业的稳定性方面,外地农业户籍中有63%的人从事灵活就业,比本地农业户籍劳动者从事灵活就业的比例(72%)要低,但远高于非农户籍的劳动者。从工作质量方面来看,外地农业户籍劳动者的收入仅高于本地农业户籍,但要落后于非农户籍;外地农业户籍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也仅比本地农业户籍的低。从组织支持方面来看,外地农业户籍参与工会以及参加医疗保险的可能性都是最低的。从心理状态方面来看,外地农业户籍也同样面临着最明显的弱势。描述性的结果初步反映出外地农业户籍与其他相对优势户籍之间在工作质量、组织支持与心理状态方面存在差异。另外,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年龄总体上要比其他类型的劳动者更年轻,在人力资本方面不如非农户籍的劳动者,但要好于本地农业户籍的劳动者;在政治资本方面,外地农业户籍的劳动者中党员的比例最低(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2 稳定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健康差距
表2 模型1 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灵活就业对自评健康在显著性水平为0.05 的情况下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假设1 得到了验证。考虑到存在异方差等违反残差经典假设的问题,本研究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均使用稳健标准误,并计算了模型的VIF 值(均远小于10),确定各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模型2 在模型1 的基础上纳入了与工作质量相关的两个变量,工作时间更长、收入更低会对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模型3在模型1 的基础上纳入组织支持相关的变量,参加医保的影响不显著,但参与工会的影响负向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工会组织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肩负着经济发展的任务[29],在影响劳动者健康方面的作用有限,且可能存在着健康与组织支持的反向因果联系,即健康状况更差的人更可能寻求组织支持,假设1.2 未能通过检验。模型4 在模型2 的基础上加入了心理状态的相关变量,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公平感的系数均在显著性水平0.001 的情况下显著,灵活就业系数的绝对值下降并且变得不再显著。模型5 将所有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由于不同的中介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各中介变量的系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工作质量与心理状态等中介变量依然有显著影响。

表2 灵活就业对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
在删除组织支持变量之后,本文对灵活就业影响健康的中介机制进行KHB 分解(见表3)。在单独纳入变量时,收入的对数、工作时间、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公平感分别解释了灵活就业对自评健康负面影响的35.14%、2.98%、40.29% 与3.41%,由于不同中介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在将所有中介变量纳入模型时,各变量解释的比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四个变量共同解释了灵活就业负面影响的64.20%,其中工作质量(收入的对数与工作时间)解释了灵活就业影响健康的26.74%,心理状态(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公平感)解释了灵活就业影响健康的37.47%。总体而言,假设1.1 与假设1.3 得到了支持。

表3 基于KHB 方法分解灵活就业对健康的中介效应
4.3 户籍制度下的稳定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
表4 显示了不同户籍稳定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在自评健康得分上的差异。首先,无论是农业户籍还是非农户籍,外地户籍还是本地户籍,从事稳定工作的劳动者自评健康得分都要高于灵活就业者。其次,外地农业户籍的稳定就业者,其自评健康得分比灵活就业者高出0.17 分,本地农业户籍稳定就业者的自评健康得分比灵活就业者高出0.12 分,但本地非农户籍与外地非农户籍中稳定就业者仅分别高出0.08 分和0.10 分,这说明外地农业户籍的劳动者,稳定就业与灵活就业的区别更大。最后,对于稳定就业者而言,外地农业户籍劳动者的自评健康得分(4.19 分)高于其他三种户籍类型的劳动者,而对于灵活就业者,外地农业户籍与其他三种户籍类型的自评健康差别要小很多,这表明非农户籍身份可能会对灵活就业者提供制度保障。

表4 不同户籍的稳定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自评健康差异
表5 展现了不同户籍灵活就业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在外地农业户籍的样本中,灵活就业会显著降低自评健康得分。相比于灵活就业者,外地农业户籍的稳定就业者自评健康得分要高出0.104 分,这一影响程度要高于其他样本中灵活就业的影响程度。在其他三种户籍类型的回归模型中,稳定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自评健康得分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也就意味着,相比于外地农业户籍身份,非农户籍身份或者本地户籍身份能够给灵活就业者的健康状况带来一定的保护效果,灵活就业只会给外地农业户籍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本研究的假设2 也得到了验证。

表5 不同户籍灵活就业对健康的影响
4.4 稳健性检验
首先,灵活就业这一变量面临着样本选择的问题,灵活就业往往是较低人力资本劳动者选择的结果,这需要用更好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内生性偏误。本研究以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民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等作为协变量进行倾向值匹配,以控制样本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相比于OLS,PSM 能够较好地克服灵活就业这一变量的选择性偏误,从而部分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为了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了最邻近匹配(1:1)、半径匹配(控制距离0.01)、核匹配与马氏距离匹配四种匹配方法,四种方法均采用stata 软件默认的规则进行分析。
从协变量平衡性检验来看(见表6),除部分最近邻匹配的结果之外,其余模型LR 值的p 值都不再显著,并且偏差均值都小于或者等于5.2,符合“Mean bias<10”的标准设定,这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匹配效果较好。就平均处理效应(ATT)而言,全样本的系数在-0.04 左右,且系数都显著,这表明了灵活就业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灵活就业者的自评健康得分比稳定就业者平均约低0.04 分。从分样本的倾向值匹配结果来看,外地农业户籍样本的ATT 值在-0.10 左右,且都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该户籍类型的灵活就业者健康评分要比稳定就业者约低0.10 分左右;其他户籍类型样本中的ATT 值大多为负,但都比外地农业户籍样本的ATT 值更低,且除外地非农户籍的马氏匹配结果外,在0.1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显著,这表明外地农业户籍的劳动者受到了灵活就业的影响,而其他户籍灵活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倾向值匹配的结果表明,在克服样本选择问题之后,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仍然成立。灵活就业会对自评健康产生影响,但灵活就业与稳定就业者的健康差异在外地农业户籍中表现得更明显,而本地户籍或非农户籍的灵活就业者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

表6 灵活就业影响健康的倾向值匹配
其次,采用主观自评健康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误,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将因变量替换为日常健康状况(“在过去的四周中,由于健康问题影响到您的工作或其他日常活动的频繁程度”)这一相对客观的测量,在进行反向编码后,得分越高代表健康对个人的影响更明显。结果发现(见表7),灵活就业者的日常健康状况更差,而且,对于外地农业户籍来说,灵活就业与稳定就业的差距最为明显,这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7 不同户籍灵活就业对日常健康状况的影响
最后,灵活就业与健康之间还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可能。一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可能会由于工作投入高、工作回报较低、心理状态弱势导致健康状况较差,另一方面,健康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劳动者之所以选择灵活就业可能是因为其对健康要求较低。此外,在估计灵活就业对于健康的影响时也可能会遗漏变量。解决互为因果与遗漏变量问题的较好方式是借助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然而,在微观调查数据中,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较为困难。考虑到配偶的溢出效应[30]与区域聚集特征变量[31-32]是工具变量的来源之一,本文采用“受访者配偶的就业状况”与“同一乡/ 镇/街道灵活就业比例”作为灵活就业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在配偶溢出效应与区域特征的作用下,重要他人与附近群体会影响自身的就业选择,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配偶与特定区域的就业状况相对外生,与自身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是那么紧密。
本研究采用2sls 进行工具变量估计(见表8),对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发现,第一阶段F值为516.127,远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过度识别检验的p 值为0.786,也不显著,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而且,灵活就业者仍然具有显著的健康劣势,本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8 灵活就业影响健康的工具变量检验
5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在中国的情境下检验了灵活就业对于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并对不同户籍的劳动者进行区分,分析制度在灵活就业与健康关系中发挥的作用。首先,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灵活就业者与稳定就业者在健康方面已经有了较明显的差异,灵活就业者自评健康得分要显著低于稳定就业者,伴随着中国灵活就业者数量的增加,灵活就业造成的新的健康不平等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在鼓励灵活就业的同时,需要提供配套设施以保证劳动者的健康权益。其次,就业的稳定性程度也是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质量的表现形式。灵活就业者的健康劣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与稳定就业者在个人收入、工作时间、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公平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的。这些差异带来了两个群体的健康不平等,其中灵活就业带来的收入惩罚与主观社会地位的下移是最重要的因素,过劳与相对剥夺感次之,“工作付出—回报不平衡”理论在中国的背景下得到了验证。最后,福利制度是影响灵活就业者获得健康的宏观力量,制度主义观点在中国情境下得到了验证。非农户籍与本地户籍会对灵活就业者的健康状况产生一定的保护效果,而外地的农民工群体则成为了受灵活就业影响最大的群体。21 世纪以来,中国在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今,不同户籍类型之间在政府文件上的差距已相对较小,但是城市居民与外地农民工群体在享受社会保障待遇方面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这既体现在居民之间的排斥,也体现在制度实施中的隐形设置。虽然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是所有社会长期存在的,但是制度能够缓解其他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相对剥夺感与心理健康问题,减少区隔仍然能有助于控制居民间的健康不平等。
本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灵活就业与自评健康关系的稳健性难以得到更有效的检验,虽然依靠工具变量等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但受限于微观调查数据,灵活就业可能还有更加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以后进一步探索。其次,工作强度与工作环境也是工作质量的重要表现,也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受限于数据,本研究难以对这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最后,灵活就业还可能通过其他机制对健康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