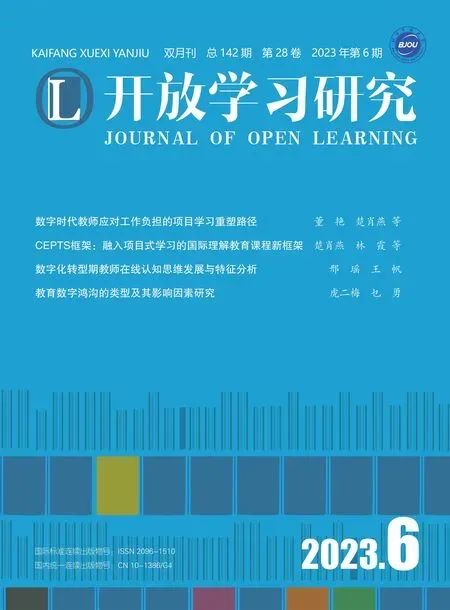数字时代教师应对工作负担的项目学习重塑路径
董 艳 楚肖燕* 翟雪松 黄世举
(1.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2.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3.曼彻斯特大学 数字技术、传播与教育系,英国 曼彻斯特 M13 9PL;4.莆田第一中学,福建 莆田 351100)
一、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时代,各个领域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与变革。教师是教育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落地的关键力量。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教师的超负荷工作严重阻碍了各国教育教学系统的良性运转和优化提升。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曾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协调好学校管理与教育教学的关系,通过提高水平、发展专业,从根本上减轻教师负担。
同时,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双减”政策的指引下,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被进一步加强,而学校承担的责任越多,越容易引发教师工作负担的连锁风险(于川,杨丽乐,2022)。2022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指向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新型教学模式,要求转变教学方式,对基础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创新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文森,2022)。“双减”与“新课标”的修订都旨在实现人才培养的长远目标,而要培养创新的学生则需要创新的教师,要想做好教育教学的提质增效与高质量发展,则需要减少教师现有工作负担,使其更集中精力关注创新教学是重要议题。基础教育教师减负与“双减”等政策方向保持高度一致,“双减”不等同于学习任务的简单减少,教师减负也不仅仅是工作量的削减,而是亟须探索出适合中小学教师的高效工作机制。
然而,目前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开展仍普遍存在较大压力,当前基础教育教师减负的相关措施还有可以完善的空间。一方面,现有教师减负方案多聚焦外部组织管理和政策支持。此类方案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面临的工作负荷,但忽视了中小学教师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在此过程中教师本身的活力没有得到激发。另一方面,面对“双减”政策和“新课标”提出的要求,在满足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当前的减负方案难以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有效工作机制,导致教师减负工作的开展缺少有力抓手。
根据2022年4月发布的《剑桥学习科学手册》第三版,面向数字时代的人才培养需求,项目式学习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形式或教学模式,而是已经成为学习科学领域的基础(Sawyer,2022)。面向指向核心素养的素质教育,项目式学习是突破基础教育改革瓶颈的重要手段,是一种更加综合化的教育实践形态,能够为促进学校育人方式和教师工作方式的转型带来启示(杨明全,2021)。
因此,本研究聚焦数字时代基础教育教师负担的症结,在对现有负担来源和减负方案进行诊断的基础上,分析项目式学习支持下教师减负的作用机理,从教师自身的视角出发,提出融入项目式学习的教师减负工作路径,以期能够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工作效能,促进核心素养导向的教育教学工作开展,助力数字时代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时代教师负担的症结分析
(一)数字时代教师负担
当前正处于技术飞速发展与教育改革不断推进的数字时代,中小学教师面临的负担包括不同类型和不同来源。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社会活动系统,并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互联系(尹超,和学新,2017)。因此,需要从系统的、整体的视角,对数字时代的教师负担进行分析。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了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将个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划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围系统和宏观系统,这一理论从整体的视角对个人成长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解释(Bronfenbrenner,2005)。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运用于对教育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当中(Nobre, Valentini, & Rusidill, 2020; Mulisa, 2019)。
数字时代的教师工作负担也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从微观系统来看,角色和人际关系是教师工作负担研究的基本要素。作为教师,工作角色是否清晰,身心体验是否良好,都将在微观系统层面影响教师工作负担。日益增加的职业倦怠感和群体性疲惫感使得教师难以应对数字时代的教育变革要求,给教师带来了较重的身心压力(张家军,闫君子,2022),工作负担管理能力不足也是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异化的原因之一(李跃雪,赵慧君,2020)。在人际关系方面,布朗芬布伦纳引入了“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概念。因此,教师工作负担的产生也有可能是因为缺少具备反馈素养和学习积极性的学生,或缺少支持性的高效教师协作,难以形成师生以及师师之间的学习共同体(董艳,2020;杜静,王晓芳,2016)。从中观系统来看,教师工作负担还受到微观系统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社会系统之间的广泛联系使得教师往往需要承担多重身份,家校责任的协调冲突带来了教师工作角色与生活角色之间的失衡,并进一步导致了工作负担的增加。从外围系统来看,虽然已经有相关政策关注教师减负问题,但由于自上而下变革的滞后性,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还存在管理制度不佳、组织氛围不良、教师培训名目繁多等问题,进而带来了教师工作量和工作负担的增加(张家军,张迪,2022)。从宏观系统来看,社会长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会成为中小学教师压力的来源。尽管存在尊师重教的传统观念,但现代社会对于教师角色显现出“低认可、高期望”的认知偏差。一方面,研究表明过去十五年对教师职业的社会尊重呈现下降趋势(徐晓虹,2017),另一方面,社会对于教师的认知又过于理想化,大众对于教师角色价值的“神化”无形中抬高了社会对于教师的道德要求,同时降低了宽容度,使得教师面临巨大的“期望压力”(Expectation Stress)(Collie & Mansfield, 2022)。
在教育这一复杂系统中,教师工作负担相关的微观、中观、外围和宏观系统之间也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造成工作负担不断叠加。外围和宏观系统对于教师的高要求,中观系统带来的教师工作量增加,都会导致微观系统中教师个人承受的身心压力增大,产生倦怠感和疲惫感。同样,当教师自身积极性不高、经验不足或工作方法不得当时,也会导致教学任务无法保质保量的完成,甚至造成工作的堆积,形成难以处理的负担。
技术的飞速发展是数字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并且由数字技术引领的变革正在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技术在赋能教育的同时,数字化变革是否会带来技术压力的问题也导致了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忧虑。在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中,技术对于基础教育教师工作的重塑是一个非线性、长期性的过程,难以一言蔽之,而需有进一步的认识。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教育变革是必然趋势。祝智庭和胡姣(2022)指出,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技术革新的动力、国家政策的发展以及教育系统的内生发展四个驱动因素形成合力,不断促进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且教师能力的增强是转型的重要内核。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生,德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先后出台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并运用数字手段革新教育教学范式,实现师生数字素养的提升(李文静,吴全全,2021;杜岩岩,唐晓彤,2022)。数字技术与教育的不断深入融合在给教学赋能的同时,也给教师带来了一定的“技术压力”(Techno-Stress)(Joshith, 2021)。
然而,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技术与压力之间的映射关系。长期来看,数字技术对于教师负担的影响其实是一个“先增后减”直至“动态下降”的过程(见图1)。在新技术被引入教育领域的初始阶段,教师确实需要花费额外的努力和精力去学习和适应教育技术的使用。但随着教师经验的逐渐增加、教育技术的迭代更新以及教学设计的不断完善,教师将积累更多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策略。充分的教学实践和恰当的工作机制将使得教师更加适应数字化的教学形式,也能够真正实现数字技术对于教师的赋能作用,实现教师工作负担的逐步减少和数字素养的逐渐提升。此后,即使教师再次面临新的数字挑战,在具有较高的数字素养的基础上,教师所面临的技术压力也只是稍有增加,其整体趋势则是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教师的负担在不断下降。此外,在整个社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教师和学生群体中的“数字原住民”的比重将会天然地增加。新的数字技术出现时,教师所承受的技术压力也会越来越小。

图1 技术支持下教师负担随时间变化关系图
教师工作压力的产生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教育研究者应当以一种发展性、战略性的眼光看待数字技术突出的效率优势和潜在的压力风险。在厘清负担来源的基础上,探寻合适的教师工作机制和教师减负方案,实现数字技术赋能的长期效益。
(二)现有教师减负方案
当前已经有众多研究针对教师减负问题展开讨论,从政策实施、社会支持、学校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首先,在政策层面需要精准施策,制定明确教师工作职责和适当工作量标准的相关法规制度,并建立起配套的评估与监督制度,保障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减少教师的工作负担(张倩,2022)。其次,调整社会对于教师角色的认知,既要倡导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也要避免对教师价值的过度神化和道德意义的被迫承载,确立教师的主体性,并给予教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减少教师的内在心理压力(迟明阳,李祥,2020)。此外,构建良好的学校管理机制和组织氛围也是减少教师负担的有效途径。学校不仅要合理地进行工作任务的组织和分配,而且要努力促成较好的师校关系、师师关系以及师生关系,有效促进工作任务的高效完成和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
这些方案都是对于教师负担这一系统问题的适切回应,但仍有可以提升的空间。一是当前的研究往往更加聚焦为教师提供外部支持,多为自上而下的变革措施,忽视了教师作为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内生力量,缺少对于教师自身能动性的激活。二是虽然部分减负方案也已经开始关注教师在其中的作用,但仍然缺少切实可行的创新工作机制。譬如已有研究指出,教师在面对工作负担时,需要从心理状态和专业素养等方面进行调适,以积极的心态看待各类教学事物,并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专业经验和数字胜任力以应对教学工作中的负担和挑战(赵健,2021)。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教师开展工作仍然缺少有效的抓手。因此,教育研究者还需进一步创新数字时代教师工作机制,结合数字时代的特征,重塑包括教师学习方式变革、工作效率优化、教学效果提升、工作负担减轻的有机统一的未来教师“减负增效”工作路径。
三、融入项目式学习的教师减负作用机理
教师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师减负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项目式学习不仅本身是一种科学的教育实践形态,更有助于以项目式的思想激发教师的主动性、优化教师工作流程、提高教师工作效能。
(一)教师自身的主观能动:理论与现实
1.理论基础
一方面,从管理学中主流的组织行为学理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来看,教育正面临数字化转型,工作要求和资源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仅仅依赖针对外部压力的措施实现减负较为困难。教师工作负担的产生是当前实际教育资源难以满足教育发展变革要求的必然结果。根据JD-R模型,“工作资源”的概念指向工作中的各种正向因素,包括个人的成长、发展和自我效能感等心理资本(Lesener, Gusy, &Wolter, 2019)。另一方面,在教师减负的研究中关注教师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和能动性的激发,是一种以教师为主体,超越工具理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下,美国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有天生的自我发展、应对环境挑战和将新的经验整合成自我意识的倾向(李敏,2014)。
因此,教师在减负的语境下并非被动的、无意识的教学实践工具或压力承载对象,而是能够自主调用工具和资源,实现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契合以及工作任务的达成,并对更广泛的外在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赵钱森,石艳,2021)。特别是在数字时代,教师在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学过程中的行动意识、反馈理解和工作机制将成为工作减负的重要突破口(董艳,李心怡,郑娅峰,翟雪松,2021),也为融入项目式学习激活教师主体性,自下而上实现“减负增效”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现实意义
第一,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激发出自身潜能,让教师以更高的专业水平应对当前挑战。无论是数字时代的技术压力还是教育变革带来的教学压力,造成教师负担的根源仍在于教师变革意向和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项目式学习的思维帮助教师转换认知,将自己视为主导项目的角色,从而更加积极地面对变革、改变惯习。具有变革积极性的教师具备更强的学习和发展的动机,能够主动、持续、深入地了解新技术、学习新知识,并将寻求策略改进工作方法、优化工作管理,寻求方法对抗职业倦怠和工作压力。教师内生动机的激发不仅能够取得更好的教师学习效果和教师专业发展,也能够实现通过教师自身这一微观系统的变革促进中观、外围、宏观系统的良性运作。以教师自身为主,实现教育发展变革的项目化推进和运行,带动系统的正向循环,内外协同发力逐步减少工作压力。
第二,主观能动性的提高也会随之带来教师心理资本的增加,使得教师自身具备更强的韧性面对未知的风险。对教师来说,教育的发展变革落地于真实的教学问题,教师将长期面对未知的风险和挑战,需提高自身韧性,从真实问题出发,运用项目化思维,成为适应性专家。教师的韧性是教育数字系统的终极韧性,表现为长期的耐受性和抗压性,能始终借助不同条件和数字化工具进行学习与提升,使自己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环境,以致给外部环境带来积极影响(祝智庭,彭红超,2020)。此类韧性心理资本包括情绪管理、冲动控制、理性乐观、灵活思辨、自我效能、同理共情以及积极拓展七个方面,能够帮助教师在自身技能激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内心抗压能力的长期保持和提升(Reivich, 2013)。
第三,教师只有提高主观能动性才能在根本上实现“减负增效”,最终提升教学质量并促进教育发展。随着教育发展变革和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双减”政策下学生的课时量减少,教师普遍面临更大的工作挑战。在实际教学一线,面对更高的教学要求和更少的教学时间,自上而下的教师减负方案很难落实,且一些措施也难以为教师提供具体细致的做法指导。教师长期躬耕教学一线,对于实际的教学工作更加熟悉,辅以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工作支架,教师的内生动力被激活后,才能更加主动地应对相应的工作压力,以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手段重塑提高效率、减轻负担的工作机制。
(二)有效的教育实践形态: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体现了项目管理的有效性与行为主体的主动性,教师在有效运用项目式学习指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时,增加自身的“学习者”角色,灵活运用项目化思维,不仅能够帮助自己激活主观能动性,也能在实践工作中找到有力抓手。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是一种建构主义理念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与教学模式,以真实问题为驱动,通过跨学科的项目设计,引导学习者在探究问题与协作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必备的知识、技能与素养(董艳,和静宇,王晶,2019)。随着教育教学的不断改革发展,项目式学习也在不断迭代完善,逐步突破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的有限认知,成为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教育实践形态,在教学系统中赋能学生和教师,提升教与学的效率。项目式学习不仅是一种锻炼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活动,更是一种有目标、有计划、有评价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其扎根于真实情境,以系统思维和产品导向为特征,具备统筹工作、提高效率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滕珺,杜晓燕,刘华蓉,2018)。
在智能时代,教师学习面临完成教学目标、学习前沿理论、提升教学实践等多重难题,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问题驱动、自主探究式的教育实践形态,能有效激发教师在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与内在活力。此外,项目式学习结合技术手段,能够为教师自主学习探究、协作学习,包括教学事务的管理提供实用支架。在尊重教师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形成融入智能技术的综合解决方案,提高教师的心理资本、专业素养和数字胜任力,帮助教师以数字韧性面对工作挑战(张志祯,徐雪迎,李英杰,吕雅楠,2022)。
在教学活动中,已有许多循证研究的结果证明了项目式学习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于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学习者均有积极影响(张文兰,胡姣,2019)。项目式学习以其特有的项目及管理体系的特征,融合了产品引领、情境真实、整体系统、团队协同、渐进探究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被充分地激发,项目背景的真实性也能够锻炼学习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达成通过完成作品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卢小花,2020)。同时,项目式学习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在线学习、研学旅习等场景,并不断衍生出融合大概念的项目式学习、促进跨学科学习的产生式学习(DoPBL)等样态(孙阳菊,2021;董艳,孙巍,2019)。
项目式学习在教师发展和学生学习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证明了在教学实践中应用项目式学习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而且项目式学习这一教育实践形态自身及其背后的项目思想具备提升教师工作效能的潜力,将为数字时代教师减负提供启发性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流程。
四、融入项目式学习的教师减负工作路径
融入项目式学习的思维实现教师工作减负,需要教师从观念开始转变,主动学习并运用项目策略,在教学实践中优化工作流程和项目管理,且在此过程中通过协作反馈不断反思迭代,形成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一)观念转变:激发内在原动力
首先,更新教师的育人观念,认识到素养导向的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转变因循守旧的固有认知。当教师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更加了解教改政策和工作任务背后的战略价值和重要意义之后,教师就不会将其理解为无意义的额外工作负担,也会避免教师抵触心理的产生。此时,教师面对变革中的工作挑战会更加具有使命感,并以专业性和认同感激发自身的潜能。在此基础上,教师将会具备更强的变革意愿,积极寻求多种技术和策略改善教学效果,提升工作效能,包括主动学习项目式的思想改进工作路径。此外,明确素养导向的教学与育人要求也是教师合理运用项目式学习赋能项目设计和工作安排的必要前提。
其次,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和在教育系统的重要作用。在项目式学习中,教师成为了整个项目的主导者,教师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强化。即使教师难以决定外部的工作要求和安排,但项目式学习的工作管理模式也能够增加教师的认知理解和工作经验。且这一主导者的角色能够增强教师对自身的“掌控感”,消除引发倦怠的“无力感”,进而激发出教师的内在原动力,从认知提升、工作提效和心理减负等多方面抵消工作负担。
最后,深化“部分”与“整体”的认识论,运用项目式的思维进行工作整合,采用更加系统和全局的眼光审视工作,并积极参与教育问题的决策和教学工作的管理。在项目式学习中,教师不再仅仅按照指示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而要会从整个项目的视角去思考工作安排和分配是否合理;不只是局限于一小部分的工作,而要根据项目的总体目标更好地统筹工作安排。这样才能保证教师在工作中抓住主要矛盾,锚定素养导向的育人目标,综合提升项目的系统效能,为教师工作赋能。
(二)方法学习:运用项目式策略
不同于将项目式学习应用于各个学科、各个学段的教学过程,要将项目式策略真正融入教师的工作路径以实现工作减负,需要把握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工程思维(Engineering Thinking)的合理运用以及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
设计思维包括框架确立、模式开发与在行动中反思三个关键环节,能够帮助教师提升问题解决、智慧生成和知识创造的能力,辅助课程设计和项目管理,实现融入项目式学习的减负工作路径(尹睿,张文朵,何靖瑜,2018;Wu, Hu, & Wang, 2019)。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出的EDIPT设计思维五步骤模式,教师首先运用“同理心”(Empathize)加强对项目的理解,认识到数智时代教育变革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项目目标;在“定义”(Define)阶段聚焦关键问题,将项目关联真实教学情境,确立项目框架;在“构思”(Ideate)阶段加强项目成员、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在“原型”(Prototype)阶段进行教学事务工作的模型开发;最后,在“测试”(Test)中开展行动反思,检验教学质量、工作完成情况以及长久的专业发展路径建设,不断优化整个项目流程,形成科学的、可复用的标准化项目管理工作范式,提高教师的工作效能(王妍莉,张红妍,毛晓龙,2022)。
工程思维更强调复杂性、集成性以及理性与实践的非线性结合,能够帮助教师从工程视角理解教学法和教育技术的变革,变教师专业发展的学习压力为工具动力,培养教师运用多样化工具的思维主动性,进一步保证教师工作项目的有效开展(赵晓闻,刘宁,2013)。教师在塑造融入项目式学习的减负工作路径时,可以遵循工程思维的集成性特点,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将纷繁复杂的教学任务、教学管理、家校沟通等工作要求进行整合,从整体的视角统筹工作安排,在教学中注重学生能力提升而非知识传递,在管理中塑造学生行为品格而非被动约束,在交流中激活父母角色而非疲于应付,打造积极运作、良性反馈的“家—校—生”协同发展的工程体系,缓解教师单点支撑的工作负担,也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数字赋能也是建设项目式学习减负工作路径的策略之一。一方面,技术支架是项目式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实现远程协作、产品制作、公开展示等项目式学习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大数据等技术能够为项目式学习的模式提供更多的科学证据,辅助基于证据的教学、学习和评价,不断优化项目式学习范式(马宁,郭佳惠,温紫荆,李维扬,2022)。对于教师来说,数字技术有助于将其从低效率、低水平、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教师能够聚焦更加必要、专业、复杂的教育问题和工作任务,特别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创造性教学和社会育人工作(杨韵莹,罗泽兰,董艳,2022)。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技术与教师教学工作的融合需要保证一定的合理性,应用成熟、可靠、经过证明的用户友好型技术,避免给教师带来新的技术压力。
(三)教学实践:重塑工作新流程
在观念转变、方法学习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将项目式学习的理念运用至切实的教学实践当中,开展项目式教学并且将项目式学习的思想运用至工作管理的多个方面,在此过程中创新重塑工作流程。
教学工作是教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职能,在教学中使用项目式学习的范式不仅是发展高质量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减轻教学负担的合理方式。数字时代,教师的角色更加趋向综合性,而非单一的知识传授者。因此,教学模式需要从“只有教师教”转为“启发学生学”,让学生在项目式学习中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探索和学习,发展包括知识学习在内的综合技能。项目式学习的运用不仅会让教学效果更好,让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进一步发展,也会使教师的工作更聚焦,让教师有更多的精力进行高层次教学,如进行项目的系统设计、改进师生反馈和提升教学评价等。
同时,这一工作的重塑也是项目式学习思想泛化运用的过程。在融入项目式学习的工作路径中,教师不再是“无意识地完成”而是“自发性地调控”。与项目式学习类似,教师以切实存在的教育问题与期望达到的教育目标为驱动,积极主动地开展探究工作以及与同事的协作,在获得学生、同事、领导等重要他人的反馈之后,及时对自身的工作安排进行调整,以提高整体的工作效能。同样,这一思维模式的运用也可以进一步推广至教师工作、家庭、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以高效率的方式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管理,调节工作要求与家庭责任、内心压力与社会期望等之间的冲突。以教师自身这一微观系统对中观及外围系统施以影响,减小工作、生活中的身心负担。
(四)反思迭代:形成专业共同体
对于教师自身作用的强调不同于只依靠教师个人来解决问题,更是要调动教师群体的积极性,打造教师协作发展的专业共同体,形成自下而上应对教师负担的有生力量。在群体协同中,教师也能获得对于自身当前工作情况的有效反馈和积极支持,不断对工作中的项目进行打磨与提升,以实现“专业共同体”的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教师专业共同体是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项目式思想为教师减负的有效手段。通过协作,教师能够进行知识共享、工作改进、信息传播和情感支持等多种活动(Nguyen & Ng,2020)。在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中,教师的协作往往还拥有能够包容冲突的组织氛围和涵盖个体愿景的共同目标,保证了共同体中教师协作的有效开展(杜静,常海洋,2020)。在项目实施前,多名教师协作完成项目的设计、研讨与改进,结合群体智慧找寻工作突破口;在实践中,不同教师可能会获得不同的反馈或发现不同的问题。在专业共同体中,这些问题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讨论和研究,进而对项目方案进行完善。多轮迭代后形成的方案再经由共同体成员广泛传播应用,辐射到更多的教学和工作场景中,通过较低的工作量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教师减负。
专业共同体内教师的相互支持也使得整个系统的韧性得到增强,多次的反思迭代也使得整个机制更加具有生命力。以项目式学习的方式促进教师工作负担的减少不在于为每位教师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要运用项目式的思想,不断提升教师的工作效能。专业共同体支持下的项目方案迭代完善增强了这一机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是教师主观能动性的综合运用和内在潜力的充分激活,也增加了项目思想赋能教师减负的灵活性、发展性和可持续性。
五、总结
教师在开展教学实践和推动教育变革的进程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具备改进教育这一复杂系统的巨大潜能。在应对数字时代教师负担的问题上,本研究以教师为突破口,融合项目式学习的思想提出了实现教师减负的工作路径。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减负方案不仅符合促进素养导向的教与学改革的要求,鼓励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式学习,而且充分激发了教师自身的内在潜能,将负担来源转变成减负动力。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创新重塑教师工作机制,让教师以项目式思想为抓手,进行主动学习和主动转型,以数字化素养和数字化韧性面对持续的变革挑战,在工作压力下激发出更大的工作潜能。
虽然本研究强调教师的主体作用,自下而上地运用项目式学习的策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并非是对自上而下的减负方案的否定,而是希望从更加系统和全面的角度对先前策略提供补充。自我决定理论也曾指出,个体的内在发展趋势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类有机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辩证关系。想要依靠教师自身的力量对抗教师面临的负担也离不开一个支持教师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特别的,这种支持不仅仅是资源设备层面的支持,更应该尊重教师的主体性,且要引导社会大众形成对于教师职业的正确认识。教师自身与外部环境协同发力,才能促成教师工作机制和工作环境的不断优化,最终在满足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实现教师工作负担的有效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