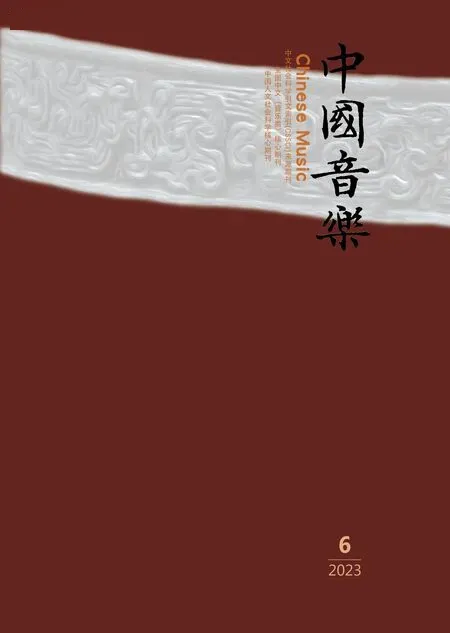音乐诠释学的历史溯源与当代走向
○ 李鹏程 李云非
一、音乐诠释学哲学溯源与初期探索
作为当前国内外音乐理论界较为关注的一门学科,音乐诠释学(musical hermeneutics)在音乐理论学科建设与音乐批评实践中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参与。不过相较于音乐叙事学(musical narratology)、音乐修辞学(musical rhetoric)、音乐符号学(musical semiotics)这类有着明确论域的音乐学分支,对音乐诠释学内涵的理解似乎总是处在一种不平衡状态之下,即模棱两可的理论概念与顺其自然的实践应用。这种内涵把握上的困难并非因为“诠释”一词有多么艰深晦涩的词义,恰恰相反,正是诠释行为与人类活动间过于紧密的联系,才导致我们总是难以将其从日常经验生活的范畴中抽离出来,并在语言异化下于理论层面加以讨论。《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中的“诠释学”(hermeneutics)词条于开篇便谈及了有关“诠释”一词的多义现象:“它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实际的实践,有时又被认为是一种理论,隐藏在解释的实践背后……在传统意义上,它构成了从源头到接受者的信息。而在其他情况下,它可以表示作品在同时代社会中的角色;或将作曲家的思想世界向听众(或乐谱阅读者)敞开;或是在聆听中展开动态体验;或是向听众展示自己的经验领域。”①Ian.Bent.Hermeneutics.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2001,Vol.11,pp.418-426.
音乐诠释学显然继承了“诠释”一词如此泛化的特征,这一广阔的意义空间给予其极大灵活性,使音乐诠释学在各种语境、思潮、观念的催化下派生出截然不同的学术立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音乐诠释学与音乐哲学密切相关,有时也与音乐心理学联系紧密;而在近代,它已然接近音乐社会学。对其某些机制的考察使它与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相接触,而最近一股音乐诠释学则与接受理论融合。有时,它与音乐分析相互关联;而纵观其历史,它也与音乐批评并行发展,时而交融、时而分开。”②Bent 2001,pp.418-426.面对如此纷繁交织的状况,明晰其理论原点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音乐诠释学论域及其所承载的学术使命,对其诞生语境的考察必不可少。
长久以来,音乐界对音乐意义问题的思辨与探讨无疑是推动音乐观念不断更迭的核心动力之一。劳伦斯·克拉默(Lawrence Kramer)指出,自19世纪中叶起,“有关音乐意义的问题随着欧洲音乐的发展而出现,这一发展脉络将音乐视为一种用于聆听的、‘自律’的艺术或娱乐形式,而不是混杂了社会因素、戏剧或习俗的形式。以这种方式创作的音乐最终构成了一项发现,它永久地改变了欧洲传统内外音乐的特征与概念”③Lawrence.Kramer.Musical Meaning: Toward a Critical Histor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1.。得益于德奥器乐音乐的璀璨成就,自律论迅速在欧洲音乐版图上攻城略地。正如金斯利·普莱斯(Kingsley Price)所言:“这一传统的伟大性令批评家深受触动,纷纷将之看作一切音乐的终极典范。他们似乎也据此主张,一部音乐作品的音高之间必须建立有机联系。因此,分析作品、理解作品、帮助他人把握作品,就意味着将作品视为音高组成的构造。”④〔美〕查尔斯·罗森等著、〔美〕金斯利·普莱斯编:《音乐批评的五种哲学视角》,刘丹霓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页。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德奥音乐传统需要一套能够突出其自身优异性的评价体系;同样,这套体系也需要一个至臻完美的音乐类型为其范例、为其背书。于是这个囊括了从创作、演绎到接受等各个环节的音乐共同体彼此捆绑在一起相互成就,成为西方音乐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要内容。
然而,如果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加以考察,音乐诠释学所代表的学术立场长期与形式自律论美学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其学科性质也在这种对峙下得以清晰显现:这门肯定音乐具有除乐音之外内容与意义的学科,旨在以各种身份、姿态、视角、方法介入对音乐意义的解读,积极地将种种隐藏于音乐形式语言之下的意义转换至人类可理解的经验世界,最终在与历史并进的无数次主观解读中,呈现并延伸作品意义与价值。
音乐诠释学的发展历程几乎总是围绕着对历史与当下、作者与读者、形式与内容这三对概念以及由其衍生出三个问题的思考:面对音乐作品,是重返其历史语境之中还是始终立足于当下?是以作者创作意图为诠释依据还是专注于对作品的自我感受?是聚焦于形式语言还是探讨其内容隐喻?对上述问题所持有的不同倾向已成为把握音乐诠释学不同流派特征的重要线索,而这些倾向早在诠释学发展的语境中已有显现。
关于诠释学(hermeneutics)的词源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可追溯至赫尔墨斯(Hermes),这位古希腊信使之神的职责之一便是将来自神界的消息传达给人类⑤〔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页。。因此,理解与解释(interpration)在有关诠释的思想及实践传统出现伊始便是其内在核心。围绕着神谕、圣经、法典等特定文本而展开的诠释活动在整个诠释学发展史上占据了大多数时间,但直到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首次提出普遍诠释学(general hermeneutics)的概念,诠释学才上升为真正的人文科学方法论。这场在诠释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向,主要体现为解放了诠释学的对象与方法。
早期诠释学将对象锁定在特殊文本之上,是因为只有那些大众不易接触且难以理解的文本产生了相应的诠释需求;但施莱尔马赫扩大了误解的范围,他认为误解普遍且广泛存在于对各种事物的理解之上。因此,为了尽可能消除误解,诠释学作为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在施莱尔马赫的努力下,走出了诠释对象上的局限,成为一门向一切文本对象敞开的方法论。而诠释学在面对文本的具体方法上的改变则首先来自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他将此前的语文学定义为“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而将他所提倡的语文学定义为“渐进语文学”(progressive philologie)。⑥牛文君、王骏:《诠释学的现代源起:在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之间》,《哲学动态》,2022年,第9期,第109页。这种渐进语文学较之以往的“先进性”反映在诠释学之上,便是对原来那种按固有、教条、循规蹈矩路径进行诠释的批判与反思。
诠释学真正意义上的蜕变以完成向本体论的转变为标志,这次转变的直接来源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主义哲学中对理解与解释的见解。在他看来,人有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具有“理解”这一特性,人通过理解与存在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理解不再仅是方法论或认识论,而是一种关乎存在本身的本体论问题,以理解为核心的诠释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本体论哲学。
纵览诠释学漫长发展史便不难发现,有关其诠释对象、诠释视角、诠释方法等内部要素的演进总体上呈现出由特殊到普遍、由客观到主观、由封闭到开放的姿态。这些改变源源不断地辐射至其他人文科学领域,音乐诠释学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在其影响之下。
有关音乐诠释学学科的最早表述在德国音乐学家克雷兹施马尔(A.H.Kretzschmar)于1902年发表的《关于促进音乐释义学的建议》一文中有所体现。⑦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但对于一门以解析音乐意义为目的的学科而言,其悠久的实践传统导致我们对音乐诠释学的考察要追溯到20世纪之前。由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音乐在西方音乐坐标系中的核心位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其展开的大量音乐评论/批评,对音乐诠释学早期阶段的考察作为题中应有之义本就应纳入研究之中。
19世纪,普遍诠释学的方法论自然而然地渗透进音乐领域。不过由于体系化、学科化的理论尚未生成,“音乐诠释学”并未在该阶段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语言,这种结合诠释理论的音乐分析只能充分汲取其他成熟学科的诠释经验,借鉴文学、诗歌等其他姊妹艺术的学科语言对音乐作品进行解读,所以这类“文学性诠释”⑧本文有关“文学性诠释”“审美性诠释”“文化性诠释”的表达皆来自陈新坤《音乐诠释学的三种意义取向》一文,此种表述很好体现出了音乐诠释学于不同阶段的典型特征。成为该阶段音乐诠释的主要模式。在这类诠释的创作者中,有文学家霍夫曼(E.T.A.Hoffmann),有作曲家舒曼、瓦格纳、柏辽兹,也有音乐学家克雷兹施马尔、唐纳德·托维(Donald Tovey)等等。
在施莱尔马赫同时期的音乐评论撰写者中,有证据表明仅有霍夫曼一人在其生前与其相识并明显受其方法论影响,而除霍夫曼外“没有任何作家打着诠释学的旗号写作音乐评论”⑨Bent 2001,pp.418-426.。身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的霍夫曼对贝多芬风格,尤其是贝氏音乐形式语言的敏感程度甚至超越了许多圈内人士,伊恩·本特曾表示,“在某些方面,人们可以说霍夫曼对贝多芬结构的反应是真正的理论家”⑩Ian.Bent.Music Analysis in the Nineteen Centu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43.。在1810年针对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所发表的经典分析中,霍夫曼写道,“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成分只会导致一些脱节和难以理解的东西,但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整体的模式,以及动机与单个和弦的不断重复,使精神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状态”⑪Bent 2009,p.153.。此处对该乐章短小动机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其内容隐喻上的精准描述展现出形式语言与内容指涉的融合,类似的分析在一个多世纪后才由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复兴。
在霍夫曼之后的文学性诠释中,音乐的形式要素以更简化的方式服务于对内容的文学性解析。以克雷兹施马尔于1898年为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撰写的文字为例,“在这之后,主要主题再次回归,但这次与对位声部交织在一起的主题清除了它令人不寒而栗的葬礼音调。音乐带着一种变形的气氛,最后在一首凯旋的歌曲中爆发出来。在布鲁克纳辉煌的管弦乐队配器中,战胜悲伤的胜利在坟墓和送葬队伍中响起,指明了通往天堂和永生的道路”⑫Bent 2009,p.114.。这段文字既展示了克雷兹施马尔将音乐形式语言转换为外部指涉的主要方式,也反映了此类诠释旨在于音乐语言和文字语言间建立一种广泛、准确对应关系的学术愿望,而更为典型的文学性诠释在托维于20世纪初撰写的一系列具有导赏性质的交响音乐分析中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这种文学性诠释在西方音乐圈中的活跃至少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此外,以瓦格纳为代表的部分诠释者在普通文字描述的基础上还倾向于大量使用诗歌或具有诗意的隐喻深化音乐形式后的意义内涵,代表性案例便是他在歌德的《浮士德》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之间建立的一种以共有精神内涵为基础的关联。⑬Bent 2009,pp.58-68.
总的来看,音乐诠释学早期阶段的所谓文学性诠释是一种通过揣测、理解作曲家心理意图,解析音乐形式的内容指涉并以文学、诗歌等隐喻性文字加以描述的音乐诠释路径,它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西方音乐在古典与浪漫时期的一种文化景观。当然,这种写作路数在出现之初就遭受了质疑,音乐学家汉斯·凯勒(Hans Keller)就认为“大多数所谓的‘批评’和‘分析’都是描述性和隐喻性的混合体”,而这类著作也仅仅是“重复的描述”,这些诠释“没有注意到描述与分析之间的区别,也没有注意到批判性的、基于印象的评论和严格的解释联系之间的区别”⑭Bent 2009,preface.。因此,这类“音乐内容解析”在实证主义的崛起中便逐渐式微。
二、德国音乐诠释学的当代探索
自音乐诠释学作为一门学科于1902年被首次提出以来,在克雷兹施马尔、谢林等德国音乐学家不遗余力地实践下,一条贯穿巴洛克音乐情感美学、E.T.A.霍夫曼乐评模式以及该“新型”音乐诠释方式的音乐解读路径已然形成,并与同时期胡戈·里曼(Hugo Riemann)所倡导的基于结构层面的形式分析形成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内容美学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音乐诠释学几乎在形成伊始便被限定于一个狭窄的定义域中,直到诠释学在哲学层面迎来巨大变革后,音乐诠释学的局限性才随之松动。其再次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此次兴起并非偶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标志着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直接促成了以哲学诠释学概念为核心的诠释思想在学术界的回暖,而德国音乐学界作为此次冲击的中心地带自然地将有关音乐诠释学的话题再次搬上学术舞台。这一阶段,音乐诠释学往往以大学或研究所为学术中心,围绕着一位或几位带头学者,以共同署名的方式发表学术文章阐述观点。在这种学术机制作用下,达尔豪斯于1973年法兰克福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基本体现了该阶段音乐诠释学的主要特点。这次会议的论文在其编撰下汇集成册并以《音乐诠释学论文集》(Beiträge zur musikalischen Hermeneutik)为名在1975年出版,从论文集中我们可以得知该阶段的音乐诠释学视野已不再局限于自律论与他律论、形式与内容这种二元对立,而是强调一种“对分析路径的预设以及其意涵的相互理解,一种对于分析的自我反省”⑮Carl.Dahlhaus.Beiträge zur musikalischen Hermeneutik.Regensburg: G.Bosse,1975,p.9.。此外,以汉堡为中心的康斯坦丁·弗罗洛斯(Constantin Floros)研究团队、以弗莱堡为中心的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希特(Hans Heinrich Eggebrecht)研究团队、以萨尔茨堡音乐诠释学研究所为中心的齐格弗里德·毛瑟(Siegfried Mauser)研究团队等都为该阶段音乐诠释学在德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下文将以最具代表性的弗罗洛斯、达尔豪斯、埃格布雷希特、毛瑟四人为对象,介绍他们及其团队在音乐诠释学上持有的主要立场。
在整个1973年法兰克福研讨会议程中,一种受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思想启发,试图弥合此前形式与内容分析两种路向间越发巨大裂痕的音乐诠释尝试作为会议的核心议题被反复关注,其更具体表现为对马勒及柏辽兹等作曲家充满“幻想意味”作品的再解读。而弗罗洛斯在德语音乐学界被广泛知晓的原因之一在于其针对马勒展开的大量研究及其三卷本著作—《古斯塔夫·马勒》⑯Constantin.Floros.Gustav Mahler I: Die geistige Welt Gustav Mahlers in systematischer Darstellung.Wiesbaden:Breitkopf &Hartel,1977,2016;Gustav Mahler II: Mahler und die Symphonik des 19.Jahrhunderts in neuer Deutung.Wiesbaden: Breitkopf&Hartel,1977,1987;Gustav Mahler III:Die Symphonien.Wiesbaden: Breitkopf &Hartel,1985.。尽管未有充分证据表明该系列研究是弗罗洛斯为响应本次音乐诠释学研讨会的号召而展开,但著作所展示出的研究路径却无不显示出弗罗洛斯与德国音乐诠释学传统间的紧密关联,甚至可以说弗罗洛斯所进行的音乐诠释实践是克雷兹施马尔、谢林等人音乐诠释思想的延续,“由克雷兹施马尔和谢林所发展出来的偏重内容解析(inhaltsdeutung)的音乐诠释学方向,后来在不同的面向上被继承着。比如,连接着维也纳传统的申克注重于修辞学的面向,在汉堡的弗罗洛斯则是试图透过传记、手稿与声响拓扑学的研究,将音乐以外的‘沉默的标题’展现出来”⑰王尚文:《音乐诠释学:一个历史与系统的探究》,《哲学与文化》,2020年,第7期,第90页。。因此,若是按照达尔豪斯对音乐诠释学所寄予的改革期望来看,弗罗洛斯的诠释实践仍然是对立思想下的调和产物,其著作中针对马勒交响曲所采取的大致分析步骤体现了形式、风格分析与内容、符号(象征)解析在弗罗洛斯诠释模式中的不平等性与优先顺序。尽管如此,弗罗洛斯依然可被视为德国当代音乐诠释学复兴的关键人物,宋佳在其论文中曾说道:“他从受到社会文化深刻浸染的音乐传统出发,透过大量历史音响的互补互证,从而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勒等作曲家的音乐语义内容。由此避免了如同自律论者一般让音乐的自身形式‘包罗万象’,但也不像情感论者那样让音乐之外的内容过多地影响音乐自身,实属难能可贵”⑱宋佳:《历史思潮中的马勒印象—评康斯坦丁·弗洛罗斯〈古斯塔夫·马勒与19世纪的交响曲〉》,《音乐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5页。。弗罗洛斯至少在平衡音乐诠释过程中形式分析与内容解析各自所占的权重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传统,向德国音乐诠释学的当代复兴迈出了一大步。
达尔豪斯敏锐地察觉到,许多美学争鸣实际上是不同时代美学价值取向之间摩擦碰撞的产物,他用西方音乐史中有关音乐本质变迁的一些阶段性“范式”说明了这种现象:“16世纪和17世纪的艺术理论基于作曲技巧与社会功能的关系;17世纪和18世纪基于‘感情类型’即音乐中所再现的‘客体对象’;18世纪和19世纪基于个别作曲家的个性;19世纪和20世纪基于自足作品的结构;而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则出现了将作品看作是文献证据的愈来愈甚的倾向”⑲〔德〕卡尔·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杨燕迪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8页。。这种凝聚着历史意识的审美观察使当代音乐诠释学的特征得以明确。在面对形式与内容问题时,达尔豪斯从某种程度上复兴了霍夫曼的音乐诠释学模式。文学性诠释得以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抗如日中天的形式自律论美学,它通过文学化的修辞增强音乐与外部内容的联结,以此来削弱音乐形式的作用。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加深了形式与内容间的二分与对立,达尔豪斯反对这种音乐整体的一分为二,他认为音乐形式与内容本质上不是二分的,只是音乐表达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内容实际上是由形式生成并表现出来的。这就意味着,达尔豪斯的音乐诠释深耕于音乐形式之中而又不拘泥于音乐形式,他通过对音乐结构形式的一种美学观照,结合此前所论及的历史视野,最终达到一种比纯粹形式分析更高级的音乐诠释境界。
与达尔豪斯相比,埃格布雷希特在音乐诠释的历史取向问题上所持有的“从当下出发”视角就显得十分明确,在其著作《西方音乐》的开篇便写道:“对一个人来说,最有历史现实意义的是(或者理应是)他自己的现在。他始终将从现在开始来思考和理解历史,尽管他并非出于自愿而致力于完全撇开‘过去是什么样’的问题”⑳〔德〕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希特:《西方音乐》,刘经树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页。。就像达尔豪斯强调音乐诠释中的历史感知一样,埃格布雷希特格外注重诠释者的“主体性”,其音乐诠释学思想与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紧密相连,在这一“游戏主题为游戏本身”的定义影响下,艺术作品并非“与自为存在的主体相对峙的对象,而是在它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了它的真正存在”㉑刘经树:《前理解、游戏、音乐的理解—埃格布雷希特的音乐分析解释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11页。,由此一来,音乐诠释者的主体地位被埃格布雷希特带入更高的层次。就诠释者的理性层面而言,其掌握的知识总是有上限的,因此诠释的视界便受到了天然的限制;就诠释者的感性层面而言,即使被诠释对象完全处于诠释者的智识结构之中,对诠释角度、方向、材料等因素的抉择也仍然受制于诠释者的主观或感性,所以也就无法确保诠释过程中的偏差与谬误。结合以上两点能够推导出:诠释历史作品也好,事件也罢,永远无法做到绝对客观中立,甚至常常谬以千里。但历史却仍以这样的方式连续传递了下来,这足以证明,历史本身的存在正是依靠着“主观”的诠释,而诠释存在的价值又依附于历史,因此二者构成了一个从事件到诠释的循环。类似的表述我们在《真理与方法》中也时常见到,“我们对诗人的理解必然比诗人对自己的理解更好,因为当诗人塑造他的本文创造物时,他就根本不理解‘自己’”,“我们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㉒同注⑤,第249页。。
在诠释音乐作品的历史视角问题上,以毛瑟为中心的萨尔茨堡音乐诠释学研究所基于理解行为的动态现象建立了一个全面的音乐诠释学模型(表1),该模型所涉及的要素几乎囊括了有关音乐的全部视角,因此这一视角“让音乐诠释学成为一个具有逻辑性的音乐研究的纲要”㉓同注⑰,第91页。。具体来说,毛瑟将音乐活动分成了四个层面:事实性层面(ebene des faktischen)、意向性层面(ebene der intentionaliät)、实现性层面(ebene der aktualisierung)与历史性层面(ebene der geschichtlichkeit),而后在事实性层面之上又将音乐从产生到接受的过程分为四个层面即作者(autor)、文本(text)、演奏者—音响事件(aufführender-klangereignis)与听众(hörer)。由此两向八层生成了一张包括各种诠释倾向的网络,在这一“4×4”的网络中,有关音乐的全部事件被尽可能地揭示并得以解析。毛瑟的这一音乐诠释模型显然打破了此前仅以作品为导向的理解方式,其所包含的整个音乐活动领域打通了作者与读者、历史与当下,并使整个理解与诠释活动摆脱了静止状态的局限,作为一种动态现象而成为历史本身。由毛瑟所归纳的这种模块化音乐诠释流程,是“对音乐现象作为文本和声音事件,作为固定的、编码的符号和流动的声学事件的构成性双重特征的洞察力”㉔Siegfried.Mauser.Hermeneutik.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1996,Vol.4.pp.261-270.,它所列出的每一环节都参与了音乐作为现象而被理解与诠释的过程之中,这一音乐诠释模式也代表了当前德国音乐诠释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表1 毛瑟的音乐诠释学模型㉕本表来自王尚文的《音乐诠释学:一个历史与系统的探究》一文,表中内容来自Siegfried Mauser,Entwurf einer Grundlegung musikalischer Hermeneutik一书。
三、美国音乐诠释学的当代发展
宋瑾曾将西方音乐阐释(诠释学)理论大致分为中心主义与多元主义两类,强调“各种音乐意义的阐释理论或观点都有各自的历史语境,亦有各自的逻辑结构”㉖宋瑾:《西方音乐阐释理论的历史梳理》,《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12页。。他认为这些不同的诠释学流派在时间先后上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分布特征,但巧合的是这一历史分布与不同诠释学流派在地理分布上的特征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中心主义的诠释学流派在历史上处于整个诠释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且基本集中在德国学术圈;而多元主义的诠释学流派在历史上则晚于中心主义出现,且基本以美国学术圈为中心。这一地理分布特征在音乐诠释学的发展状况上同样适用。
作为当代音乐诠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音乐学者对当代音乐诠释学的贡献同样不可忽略。不同于德国当代音乐诠释学与音乐诠释学传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美国的当代音乐诠释学似乎直接建立在对实证主义研究的批判之上,这一反思潮流源于约瑟夫·科尔曼(Joseph Kerman)在1965年发表的《美国音乐学侧影》(A Profile for American Musicology)一文。他在1980年出版的《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一书中表示,执着于史料搜集的许多音乐学家“回避‘音乐本体’;所以他们遇到分析实际音乐作品时,又常常显得草率而又肤浅得令人失望”㉗〔美〕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朱丹丹、汤亚汀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第58页。。随即他又认为“这反而使得分析—尽管自身有明显的局限—能够吸引那些试图发展当代严肃音乐批评的人”㉘〔美〕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朱丹丹、汤亚汀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第58页。。在这种对比下,实证主义实际上被科尔曼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以史料考究为代表的“旧实证主义”和以申克主义分析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如果音乐学家特有的失误在于肤浅,那么分析家的问题就是学术眼光的短浅。”㉙〔美〕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朱丹丹、汤亚汀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第58页。科尔曼倡导一种将实证主义与人文诠释相融合的新境界。这种期望理应视作美国当代音乐诠释学的直接源头,所以本特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诠释学”词条有关美国音乐诠释学发展的部分写道“科尔曼的辩论本身并不完全是一种新的音乐诠释学的宣言,但他的辩论有助于开辟几种关于音乐的新论述,至少与诠释学有关”㉚Bent 2001,pp.418-426.。
列奥·特莱特勒(Leo Treitler)与爱德华·科恩(E.T.Cone)等美国音乐学家都做出了回应。特莱特勒将音乐意义锚定在文本之外社会文化流动中的观点,与哲学诠释学所主张的敞开的意义空间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他怀疑申克主义分析能否揭示作品的内容:“申克尔声称要给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内容解释,这就好像某人宣称要通过分析《哈姆雷特》的语法和句法而置意义于不顾来给出此剧的内容解释”㉛〔美〕列奥·特莱特勒:《反思音乐与音乐史—特莱特勒学术论文选》,杨燕迪编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页。。克拉默则向特莱特勒证明了融合的可能性,他的论文《海顿的混沌和申克的秩序:或者,诠释学和音乐分析,能否混合?》㉜Lawrence.Kramer.Haydn's Chaos,Schenker's Order;Or,Hermeneutics and Musical Analysis Can They Mix.19th-Century Music,1992,Vol.16,p.4.直接将申克的分析图表搬了过来,对应阐释了海顿的清唱剧《创世纪》序曲的内在构思。
科恩旗帜鲜明地声称“纯粹的音乐语境也可以由表现因素(形式因素)来确定……然而,音乐中总会有语境,于是便也总会有内容”㉝〔美〕爱德华·T.科恩:《作曲家的人格声音》,何弦译、杨燕迪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他基于对《降A大调音乐瞬间》(D.780 No.6)的分析,论证了未按规则解决的特征音是舒伯特罹患梅毒病痛在作品中留下的痕迹,成为在英文音乐学界被反复引述的诠释学分析。㉞Edward.Cone.Schubert's Promissory Note: An Exercise in Musical Hermeneutics.19th-Century Music,1982,Vol.5,p.4.
科恩的诠释学分析范例给当今的音乐理论家们很多启发,约瑟夫·施特劳斯(Joseph N.Straus)近年来借助残障(disability)研究的方法㉟施特劳斯投身于音乐残障研究起因于儿子被诊断出自闭症,成为残障人士父亲的他开始以独特的视角重新思考音乐作品,这一系列相关论著集中体现了一位音乐理论家的“视域融合”。,从实证主义研究迈入了诠释领域。他在《非凡的作品:音乐中的残障》㊱Joseph.Straus.Extraordinary Measures: Disability in Music.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一书中将音乐作品比喻为人的身体(body),而残障在音乐作品中体现为三大特征:调性问题(tonal problem)、失衡(imbalance)以及异常形式(abnormal form)。延续这种研究模式,施特劳斯又写出了《残缺之美:音乐的现代主义和残障》㊲Joseph.Straus.Broken Beauty: Musical Modernism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sabil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这本书在2020年获颁美国音乐理论学会(SMT)的最高奖“华莱士·贝瑞大奖”(Wallace Berry Award),可见当今的北美音乐理论界对诠释研究是持鼓励态度的。笔者曾问施特劳斯是否有意识地在音乐残障研究中运用了诠释学方式,他回答:“是的,在我关于音乐和残障的研究中,我很感兴趣解释和探索音乐的涵义—即音乐可以被如何理解。”㊳见约瑟夫·施特劳斯2023年3月24日回复笔者的邮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尔曼引领的“新音乐学”已然打破了北美音乐理论界固有的实证主义壁垒,如宋瑾所言:“释义学转变在音乐学领域主要体现在‘新音乐学’理论及其释义的学术实践”㊴同注㉖,第20页。。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诠释学对诸多音乐学者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并非这类成果都属于音乐诠释学的范畴,对这一学科的界定还是要参照研究者及其成果是否以诠释学为出发点。
针对音乐诠释中的历史观照问题,如果说达尔豪斯是出于其音乐史学家的职业素养,埃格布雷希特是来自他对诠释过程中主体性地位重视,那么美国音乐学家克拉默的历史取向便是受到了新历史主义影响下的产物。新历史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因此也自然带有后现代主义鲜明的去中心化与多元化特征;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对于史料的真实性与严谨性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而这最终也只能导向唯一的答案或结论,其目的便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但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真相这一词语存在本身便是悖论:“人们面对的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文本,而非历史本身”㊵屠艳:《劳伦斯·克拉默音乐诠释思想探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0年,第2期,第65页。。
因此,对于音乐作品的意义,克拉默在肯定其存在的基础上也突破了对意义的普遍理解。在他看来,音乐作品中的意义并非一种类似于真理的、具有中心性的答案,而是作为社会活动的一种文化实践而存在。为了理解这种层次的意义,我们必须借由“诠释学之窗”(hermeneutic windows)这一突破口找出隐藏在音乐形式之下的深层意义,因为“音乐拒绝完全展示自己”㊶Bent 2001,pp.418-426.。在克拉默看来,这些窗口往往会出现在音乐连续进行的异常之处并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类型:文本的内含、引证的内容以及结构隐喻,其中,结构隐喻往往是“寻找‘诠释学之窗’的最具有暗示性、最重要而有效的方法,能够获得各种实际的理解和认识的结构上的程序,作为特有的表现行为在某种文化、历史的体系中发挥作用”㊷同注㊵,第67页。。克拉默针对贝多芬的《“幽灵”三重奏》(Op.70,No.1)中的广板段落所作的诠释分析便是证明其结构隐喻路径的绝佳案例。他将作品中的不寻常调性布局作为诠释学之窗,从“呈示部d小调与C大调的两副面孔”㊸Lawrence.Kramer.Interpreting Music,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p.162.出发,将其与“1808年前后欧洲空气中弥漫的世俗观念:当时的科学与艺术都从美学的崇高与美丽中吸收了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形成关联,并进一步将其视为“康德的启蒙原则与其自身对立起来,以怀疑的态度反思启蒙主义的怀疑论”㊹Kramer 2010,p.166.,最终得出“贝多芬的这首广板是一首饱含不满的轰鸣,他表明康德式的形而上学不可取”㊺Kramer 2010,p.167.的结论。
正是以上这种基于新历史主义诠释路径所采取的开放性态度,克拉默对于以达尔豪斯与埃格布雷希特为代表的审美性诠释视角,并未采取完全否定的姿态;他绝不否认过去人们所感兴趣的音乐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不否认音乐作品风格的内在机制,但他已与早期的策略决裂而不再把音乐作为一种工具或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或历史状况的反映,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驱使人们形成并介入这些状况的能动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克拉默的这种诠释姿态可以视为达尔豪斯与埃格布雷希特的更高级版本:他们同样都是从音乐形式的具体结构出发,只是相较于达尔豪斯等对于结构要素的纯粹审美诠释,克拉默选择了更为宏大的社会人文视角,他主张将作品中发现的“结构隐喻”在符合其文化语境与社会架构的框架内自由运用,从而尽可能地使诠释者发掘作品意义的同时通过诠释行为实现作品的价值。而他对音乐作品与历史现实间“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追求也使他在充分发挥当下诠释者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之上,将诠释视野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所有人文学科,将音乐与上述文化现象一并视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整体,这种对于音乐意义的开放性、多元性与非中心性诠释无疑是当今音乐学领域的主流旨趣。
余论:音乐诠释学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对于音乐诠释学而言,“古老且新潮”一词大概能够较为准确地概括其历史轮廓:一方面,音乐诠释自古有之,甚至可以说,音乐的历史有多长,对音乐进行诠释的实践史就有多长;另一方面,音乐诠释学也是一门呈迅猛上升势头的朝阳学科,它从早期对抗形式自律论美学的局限中逐步演变为符合现代及后现代社会思想特征的音乐美学流派不过百余年。在这一历程中,有关历史视角的取舍与对待音乐本体的姿态无疑成为指示发展阶段的重要线索。达尔豪斯在吸收历史诠释学的基础上将历史差异纳入音乐诠释之中,使此前扁平的音乐诠释因历史维度的加入而更加立体;此外,他重返音乐的形式海洋中,将深度理性的结构分析与诗意感性的审美体验结合,开审美型诠释之先河。埃格布雷希特继而肯定了音乐诠释中历史因素的重要影响,并在达尔豪斯的基础之上选择以当代视角打破传统作品诠释的历史局限。而克拉默更是将后现代语境中反对权威、提倡多元的主体性与音乐诠释的当代视角相融合,揭示出音乐作品更加多元与开放的意义;而其对待音乐本体的理论姿态也脱胎自审美型诠释,只是将其以个人为中心的审美体验替换成有着更广阔空间的社会人文论域。因此不难发现,上述三人有关音乐诠释学的历史关系与本体问题研究呈现出较明显的继承与进化姿态,这种姿态直接导向当下的音乐诠释并延伸至未来。
在中国,不少学者将诠释学的方法用于作品分析中,他们大多兼有作曲理论学习背景和西方音乐史研究实践。较早的代表是钱仁康先生,他于1964年写出《肖邦叙事曲解读》㊻钱仁康:《肖邦叙事曲解读》“序言”,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初稿,如今看来,正是诠释学分析在中国的早期范例。20世纪90年代,西方音乐诠释学对中国音乐分析学科开始产生直接影响,这体现在于润洋先生的一系列理论构建和分析实践中。他在1990年至1991年发表了论文《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末尾特意强调了“视域融合”:“不是放弃自己的视界去单纯追求历史的视界,而是拓宽自己的视界,使之与历史的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超越自身,形成一种新的视界,对艺术作品进行一种新的理解”㊼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下)》,《音乐研究》,1993年,第2期,第100页。。姚亚平解读音乐学分析多年,他认为音乐学分析就是要将于润洋所说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打通:“在真正的音乐学分析者那里,形式本身已经是具有文化或社会内涵的形式了”㊽姚亚平:《于润洋“音乐学分析”再探究》,《音乐研究》,2023年,第1期,第47页。。得益于钱仁康和于润洋两位前辈奠定的学术传统,使得诠释学对音乐分析产生了深远影响,不断催生出新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模式,这较为明显地体现在了他们的两位得意门生—杨燕迪和韩锺恩近年来的诠释学分析中。例如,杨燕迪曾在《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肖邦〈第一即兴曲〉作品29的个案研究》㊾杨燕迪:《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肖邦〈第一即兴曲〉作品29的个案研究》,《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一文中对诠释学分析的学理意义和操作方式进行探讨,与其导师钱仁康对肖邦的研究路数一脉相承。韩锺恩曾在《音响诗学—瓦格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乐谱笔记并相关问题讨论》㊿韩锺恩:《音响诗学—瓦格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乐谱笔记并相关问题讨论》,《音乐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和《之于特里斯坦和弦集释的别解》51韩锺恩:《之于特里斯坦和弦集释的别解》,《音乐研究》,2023年,第1期。中,试图“从音响结构形态的分析、听感官事实的隐喻与暗示、音响诗学的直言与明示,对其进行别样的诠释”52同注51,第5页。。笔者曾询问韩锺恩教授这一系列研究是否受到了音乐诠释学的深刻影响,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不得不承认,国内的音乐诠释学在学科层面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而围绕中国音乐作品的相关诠释还远远不够。中国音乐自古至今以他律论美学为主导,当代作曲家们也习惯为作品注入明确的标题指向与强烈的情感色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动强调主观体验和文化解读,逐渐摆脱了一度纯音乐结构分析的方式,这无疑更有利于世人理解和传播中国音乐作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仅能借鉴西方音乐表演理论和诠释学成果,还能接续中国自古以来围绕音乐表演展开的理论言说,那么对中国音乐作品的多维诠释就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总之,当代中外学者普遍认同音乐诠释学与音乐分析应当深度融合,主观感性体验与客观理性分析理应形成统一,但究竟如何形成体系化和普适性的学科方法,依然在面向音乐作品的言说实践中不断摸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