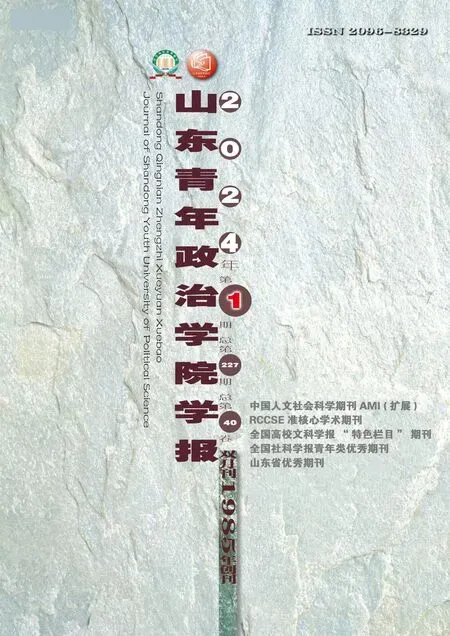重塑交往: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机制与防治路径
——基于37名欺凌卷入者的访谈
曹 文, 张香兰
(1.重庆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1331;2.鲁东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烟台 264011)
校园欺凌是一种特殊的攻击行为,这种特殊性首先体现在未受到侵犯/激惹的情况下,由欺凌者主动发起对被害对象的欺凌。(1)Olwers Dan,“School bullying: development and some important challenges,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no.1(2013):751-780.欺凌者在欺凌过程中常会获得同伴支持,而校园欺凌的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多为较熟悉的对象,欺凌的发生可能源于欺凌者期望在同伴中取得较高地位。(2)Pellegrini A. D, Bartini M, Brooks F, “School bullies, victims, and aggressive victims: factors relating to group affiliation and victimization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no.2(1999):216-224.(3)Espelage D. L, Holt M. K,“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peer influences and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no.3(2001):123-142.这也说明,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主体交往。交往是学生能动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学生交往的基本范式与过程常作为评判青少年社会认知水平的内在依据,影响着学生欺凌行为的选择。考虑到交往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以中小学校园中的欺凌者、被欺凌者的深入访谈资料为主要研究数据,以交往行为理论作为研究切入点,力图解析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机制并尝试建构防治路径。
一、研究设计
交往行为指有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以言语的有效性要求为媒介基础,以达到相互理解为目的,在意见一致基础上遵循(语言和社会的)规范而进行的,被合法调节的、使社会达到统一并实现个人同一性与社会化相统一的合作化的、合理的内在活动。(4)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第318页。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本质上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作是人类提升认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5)刘伟:《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认知演化图景》,《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交往行为理论以合理性思想为指导,更注重不同主体在语言符号、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等方面的联系,凸显主体间精神的沟通、视界的融合、道德的同情等。哈贝马斯将以语言符号互动的沟通模式作为社会大众“普遍行为”的基础,梳理了“揭示理解”的普遍条件,强调语言方面的“互动”交往或“沟通”理解的重要性,阐释语言在交往中的平等性、同一性与互通作用,以及主体间语言交往模式的普遍性、规范性与非历史性,并指出交往合理性存在于主体的日常交往实践及语言沟通中,言语有效性是主体交流沟通的前提要素,主体间的“言说”或“交谈”是交往的最基本形式,也是产生“相互作用”的基础要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意义沟通”。只有交往行为才是真正的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交往行为比其他行为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6)傅永军:《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述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交往行为的实现需要满足主体间的理解,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7)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 2页。作为交往共同体的成员,采取行动应当自觉以主体间所认可的规范要求为取向。(8)德特勒夫·霍斯特:《哈贝马斯》,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76页。
在交往过程中,建立、维护学生间的合理交往,才能在源头上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9)罗超:《社会交往视野下校园欺凌的学校治理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4期。是故,对校园欺凌问题的本质认知与防治路径探析理应关注个体间的交往作用机制。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设计访谈问卷,通过对中小学校欺凌者、被欺凌者的半结构式面对面访谈获得研究资料,运用NVivo11.0软件的编码功能分析访谈资料,检验学生交往行为与校园欺凌的关系。在访谈开始前,先通过学校向学生家长、教师、学生本人说明访谈意图,经学生家长同意后进行录音,不能录音的做好资料记录准备。访谈问题主要集中于让受访者阐述“卷入的欺凌事件”“欺凌发生原因”“社会交往情况”“学生自我感知欺凌”“欺凌者对纪律规范的接受程度”“欺凌发生时的旁观者情况”等方面。研究样本来自12所中小学校,被访对象人数以研究内容是否饱和作为研究终止的标准,每人访问时长为40~60分钟,共确定37名访谈对象,包括欺凌者21名、被欺凌者16名,被访学生基本信息详见表1。

表1 被访学生的基本信息情况表
二、交往异化与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机制
哈贝马斯主张发挥理性力量的作用,行为主体通过沟通、对话以及理解建立真正联系,进而构成主体间性,克服传统“主体-客体”模式所造成的现代危机。其对“曲解交往”或“伪交往”的研究也揭示了现代社会交往中的非合理成分。哈贝马斯将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并指出其中的“非交往行为”要素。结合对37名欺凌者、被欺凌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校园欺凌行为中存在哈贝马斯提出的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中的“伪交往”因素,忽略交往行为的内涵要素,表现在以自我为中心、虚假接受规范、伪装经验表达、偏离生活世界等方面。
(一)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意念的权威话语独白
哈贝马斯指出,目的行为是行为主体通过对有效手段的选择,以适当方式运用这些手段使目的得以实现,或者促使所期望状况出现的行为。目的行为以行为抉择为中心,实质上是非社会的,但社会行动必须考虑到他人。目的行为缺乏主体间向度,常以经验知识为基础,而不管这些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及公正性,话语方式以“命令”而非理性协商的形式出现,常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载体。
在校园欺凌行为中,目的行为的“认知-意志”指向于欺凌者对于欺凌的实际态度,意图是把原有的欺凌设想在生活中实践。通过对欺凌者行为方面以及欺凌对他人的感受方面的访谈资料分析,发现欺凌者希望他人能够理解自己的意图,但在现实中可能并未达到其原本预期。校园欺凌行为中的语言媒介,是指欺凌者对被欺凌者发号施令,或故意威胁、侮辱、嘲笑、讥讽被欺凌者,甚至逼迫被欺凌者说出某些话语、做出某些动作等,并未考虑到他者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自我意念的话语式狂欢。例如,在本次访谈中,有欺凌者(07FL)表示,“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家人都不敢动我的东西,要是在学校里别人动我的东西,我就很生气,有一次别人把我的试卷折了一个角,我就和她吵了起来,还动手打她了。”也有欺凌者指出,“当别人不按我的方式做事时我会感到很生气。”(08MW)“有些同学就是欠打,他们挨打就是罪有应得。”(11MX)可以看出,欺凌者常通过言语命令方式促使被欺凌者“服从自己”。这种行为并不是以一种双向沟通的方式进行,更多地是欺凌者自身的权威式话语独白。也有欺凌者表示,“欺凌同学也不会想很多、不管他,就是揍他。”(15MC)“欺凌的时候不会考虑那个同学感受,不会管他怎样。”(21ML)“就是有时候觉得好玩。”(06MQ)“不管三七二十一不会考虑那个同学,就是生气、愤怒,骂他王八蛋之类的。”(20MW)不难发现,欺凌者多以自我为中心,试图控制他人,保护自己,很少顾及他人的感受,与目的行为描述的情况基本吻合。
(二)虚假接受规范:对欺凌行为的掩饰与美化
规范调节行为指向社会世界。哈贝马斯关注“行为者的动机和行为是否能与现有规范一致”,“已有的规范的价值体现是否能够把相关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表达出来,并获得所有接受者的认可”。(10)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89页。规范行为是指社会个体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之间遵循共同价值规范取向的行为,以遵循规范为中心,期望实现一种一般化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与社会世界相对应,隶属于社会世界的行为者在关系中的角色为规范接受者,而这种人际关系的确立是基于遵循与接受规范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认为,规范行为的判断需要分清行为语境下的实际内容与规范内容。
在校园欺凌行为中,欺凌者对于规范的接受只是一种观念意识层面的假意规避。一是表现在欺凌者对纪律规范等的认识程度较低。本次访谈发现,有一半以上的欺凌者表示不是很清楚校规、班规、法规,并表现出对这些规范的漠视,甚至持有“无知者无罪”的态度,多认可“若不知道有相关的纪律规范而有不良行为不应该受到指责”的观点。二是否认/弱化欺凌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例如,有欺凌者称,“也没对他造成伤害,大约5~6分钟就会和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以后还会一起玩。”(10FL)“觉得有时候做的不对了,比如拿了别人东西然后又放回去了,不太会对他们造成影响。”(12ML)“不会对他造成伤害,顶多抓伤胳膊,衣服弄坏了。”(19MH)“没有想过他们的感受,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09MD)三是对自我违规行为的美化。例如,有欺凌者表示,“我们班有同学因为比较肥胖,是大家嘲笑的对象。但是往往就前面2~3天这样对他,之后就好了,也会和他一起玩。”(21ML)“有时候他们找事,骂我,男的女的都有。女的就是脸皮厚,会骂人,说话不好听,有时候就会打他们。”(17MW)“有时候拿了别人东西然后跑出去,后来发现这样做不好,最后又还给他了。”(02MY)
可以看出,在一些欺凌行为中,欺凌者并不承认自己的“越轨者”身份,而多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嬉笑玩闹的一种方式,或者只是将之视为正当人际关系建立的途径之一。由是观之,若把欺凌行为置于“规范行为”视域下,欺凌者可能也在尝试向规范接受者的角色转变,表现为在欺凌者的观念中,并不认为自身行为是在有目的地对被欺凌者施加压力,否认对规范条例的破坏以及对被欺凌者造成的伤害,有意对自我欺凌行为进行美化,将欺凌行为的发生归咎于被欺凌者或迫于其他方面的压力等方面。
(三)伪装经验表达:与他者非合理性情境互动
戏剧行为是指行为主体有意识地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期望在公众中能够形成自己观点和印象的行为,并将自我表现作为中心概念,类似于培根的“剧场假象”。但是行为者面对在场的公众,若只关注自我的主观世界,可能出现行为者表达的经验只是一种伪装形态,并非其真正的意见或意图,脱离了反映的真实情况。(11)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第93页。戏剧行为对语言采取形式主义态度。诚然,欺凌者在欺凌过程中作为行为主体必然也有愿望和情感的流露,但愿望和情感存在着功利主义角度和直觉角度的偏差。这也就意味着,行为人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本身意图可能是相悖的,或者并不能完全表露出原本的真实状态。
在戏剧行为模式下,欺凌者为获得自己的预期效果,特别是在众人围观的情形下可能更会变本加厉地对被欺凌者加以伤害,以期获得所谓的“更好的心理体验”。欺凌者的愿望在此境况下可视为通过欺凌想要达到的一种结果。在本次访谈中,有欺凌者表示,“有其他人在场的话,可能会有表演欲望。”(04MZ)“有时候会有其他旁观者在旁边说,也会受点影响。”(15MC)“当时也有一些人说,有些朋友会告诉我就应该打他。”(21ML)“有煽风点火的就想再揍那个人。”(19MH)“有时候会因为旁观者在场觉得更不能认输。”(05MS)可以看出,在欺凌过程中,有些欺凌者会依据旁观者反应来调整自己的欺凌策略,旁观者中的围观起哄者,更易激发欺凌者的“表演”欲望,欺凌者可能会因外部世界的某种限制而产生了欺凌行为。在这种看似为戏剧行为的模式中,欺凌者面对作为旁观者的“观众”,在此情境下而被迫做出欺凌举动。
(四)偏离生活世界:忽略交往行为的内涵要素
交往行为能够实现合理化,关键在于双方对社会规范效准(伦理学的普遍原则)的承认遵守以及恰当对话与理解。(12)傅永军:《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述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交往行为的主体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的关系是合理性的。“理解”“互动”“社会化”是交往行动的前提,每个主体都参与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中进行交往,从而使生活世界构成交往行为的背景。(13)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326页。校园欺凌行为显然与交往行为的内涵要素背道而驰。置于交往行为范式下,可知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的交往失实,存在力量失衡、交流失真、理解沟通错位等问题。
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力量失衡。交往行为是以双方平等地位为基础,以共同的价值规范遵守为前提,并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交往行为强调主体之间的平等状态,以完成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进而实现理解和融合。但若双方力量处于失衡状态,那么主体与客观世界关系即是非合理性的。显然,校园欺凌行为中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常有严重的力量失衡,有违交往行为中的合理性要素,脱离了真实性。例如,本次访谈中有欺凌者称,“我那些朋友都比较重哥们义气的,大家经常一起做事(指的是欺凌他人)。”(13MT)“我们这个团体一共有九个,我在男生里面排第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排名,小的要听大的,大家去干什么也都一起。”(15MC)“看到那些身体肥胖的会想去欺负他。”(21ML)“我不能听见他说话,感觉他说话好烦,太娘了。”(09MD)也有被欺凌者表示,“朋友一般不会帮,很少帮,其他旁观者也不会帮。”(34MS)“有5~6个人经常说我。”(33FL)“他挺高的,也有点壮,上上周他主动挑衅我,我被他扇耳光了,同学有看见的也不敢对他怎么样,在班里(同学)都很讨厌害怕他。”(28ML)“欺凌我可能看我不顺眼,他们骂我畜生,还说其他难听的话。”(37MJ)从中不难看出,欺凌者多有小团体,而被欺凌者常孤立无援受到同学排斥,双方有明显的人员数量差异及身体特征差异,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处于力量不均衡状态,这也冲击着“交往行为”中的平等内核。
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交流失真。交往行为强调社会规范的遵守,而这种社会规范是实现理性化行为的有效根基。交往行为的媒介主体符号或语言是用以建立和改善人际关系的有效途径。但在校园欺凌行为中,卷入欺凌事件的主体之间的交往内容并非是本真的“生活世界”,文化、社会和人格并未得以诠释,主体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也是非合理的。有欺凌者表示,“欺凌别人不清楚什么原因,就是觉得不顺眼,以前几乎天天都揍人,现在好点了,一周一次吧,也不为什么,就是觉得该揍他。”(06MQ)“冲动的时候我说过别人,声音很大。”(16MX)“平常跟其他同学交流不多。”(11MX)有被欺凌者称,“坐在后面的那俩同学总是说我。”(32FJ)“嘲笑我,给我起外号,我有时候就和他们吵架。”(25MG)“有的同学老是弄我,我就一直给他说你别动我了、别动我了……就一直这样说,有时候他也就不动我了。”(35ML)“我不太喜欢与人交流,朋友很少,经常觉得压抑、孤独。”(36FY)不难发现,欺凌者、被欺凌者同他人真正交往的情况较少,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言语交往,而这种交往也可能会被一些手势、动作等符号所取代,多是一种非言语交流,双方交流出现失真的态势。
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理解错位。交往行为强调以理解为导向,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为参照标准。若行为偏离理解向度,主体与主观世界的关系随即也呈现出非合理性态势。在校园欺凌行为中,被欺凌者的身份实则是片面、被动、非自由人的身份,而不是表现为作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与其他个体进行平等的交往。被欺凌者因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地迎合欺凌者,而欺凌者也并不期望获得被欺凌者的理解,仅以达成自我目的为愿景。这一向度与目的行为中强调的“自我中心”要素相呼应。
三、重塑交往:校园欺凌的防治路径
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欺凌行为实则只是交往行为的临界状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交往行为。行为主体之间亦未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但可以沟通的语境才是通向合理化行动的必要条件。合理化行为是指人们运用语言与非语言的符号作为理解彼此的信息和各自行动计划的手段,以便能够协调自身行为进而达成一致。因此,使校园欺凌行为中的行为主体意识到交往的重要作用,克服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方式中的“非交往行为”要素,把握交往行为的内涵要素,成为防治校园欺凌的关键。
(一)扩充理解向度,发挥有效沟通的积极作用
哈贝马斯坚持“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要素和导向的行为”(14)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3页。,行动者拥有寓意丰富且可共享的有关文化传统、价值观、信仰、语言结构以及在互动中如何应用它们的常识。行动者在相互理解、沟通方面除了依赖现有的文化资料作为沟通的媒介外,在沟通过程中会同时传送和更新文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沟通性是合理化行动的一个缩影。交往者之间的相互理解需要通过交往者之间的共识实现。增加学生理解向度则可以促使其行为赋有更多的理性化成分,从而避免校园欺凌的发生。基于此,需要加强学生对文化要义中所属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的认同,如引导学生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信仰、审美、思维方式等,不随意嘲笑讥讽他人,深化对所属的社会文化、学校文化、班级文化的理解,秉持包容接纳的原则。哈贝马斯认为语言不仅具有客观性特质,同时也具有沟通维度,交往行为与各种各样的策略行为不同,是为了达成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理想的沟通方式则是达成共识。(15)Kogan G, “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s of school bullying from the framework of Jurgen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PhD diss.,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11 ).是故,还应注重学生交往过程中言语等符号互动的理解,增强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提升学生的自我修养,教给学生稳定情绪、减少敏感多疑的方法,让学生学会控制自我欲望与言行,培养学生的关怀意识。
(二)加强规则教育,凝聚他律与自律教育合力
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中人们能够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样行动,以及什么是合乎规范的,什么是越轨的;同时也懂得沟通行为能达至社会化的过程,促使个人自我角色的建构与确立。欺凌者在欺凌过程中常有意将规范模糊化,达到淡化或免除自己责任的目的。“无规则就是无理性。”(16)伊曼努尔·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135页。学生在这种“无规则”意识下的行为显然有违交往行为中的理性契约精神。“一切有意义的行为(因而所有特指的人类行为),就其有意义这一事实而言,都是由规则支配的。”(17)彼得·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张庆熊、张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52页。遵守行为规则、养成规则思维、自觉接受规则对于干预校园欺凌行为至关重要。在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中,一是要明确规则教育内容,注重规则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中小学生进行的规则教育不仅包括班级规范、学校纪律等方面,还应向学生普及法律规则,强化组织性与纪律性,阐明各项规章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重要程度,通过案例讲授、影片鉴赏、实地研学、组织宣讲等形式,帮助学生了解规则的丰富内涵。二是凝聚他律教育和自律教育的合力,让学生理解他律规则意在调控个体外在行为符合规则,自律规则多强调个体对规则的自觉接纳,并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他律规则、自律规则的教育比重。针对学生个体存在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让学生真正理解、接纳规则,使个体行为更多地被自我要求或内在规则支配,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转变互动模式,唤醒旁观者积极角色意识
哈贝马斯认为,人们认识到并知道如何去组织社会关系以及选择何种种类与范式的协调性互动是恰当和合适的,懂得沟通行为不仅能调节不同意见或社会行为,并且能够促使社会整合,产生人类的归宿感。本次访谈发现,校园欺凌的发生多因学生之间的琐事引起,欺凌者常有较高的冲动性,自我控制能力较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利于减缓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有研究者指出,互动利于帮助学生控制攻击冲动。(18)李德显:《学生互动分析》,《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2期。同伴之间的积极互动利于促进学生的良好发展,提升其社会交往能力。欺凌者、被欺凌者与旁观者的互动博弈影响着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中可能会以协助者、附和者、保护者及局外人的身份出现,而成为欺凌者的“兴奋剂”、被欺凌者的“保护伞”。是故,应关注互动仪式的积极作用,加强学生群体之间的有效互动。互动仪式链是参与者建立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的日常情境性活动。(19)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79页。在校园欺凌中,欺凌者、被欺凌者与旁观者在物理空间上共同在场,增加了彼此对共同关注焦点的情感体验与情绪反馈的可能。因此,学校应多积极营造和谐、同情、关怀的校园文化氛围,缓解冲突性紧张,开展生命教育、情感支持教育等方面的教育活动,关注学生之间的真诚、真爱、真情交往,增强学生相互关心、相互容纳的意识,提升移情能力,加深学生对同伴支持的理解,发挥同辈群体在校园欺凌干预中的重要作用。
(四)明确交往导向,把握生活世界的价值意蕴
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动的主体必须在生活世界范围内进行。“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中的奠基要素,与“交往行动”相辅相成。应把生活世界的概念首先作为理解过程的关系引入。(20)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第69页。交往行为通过生活世界协调地处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而“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者‘始终’(immerschon)置身其中的境域”(21)艾四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文化、社会和人格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三个维度,对应知识储存、合法秩序、能力权限。丰富的知识储备利于学生在交往中更好地理解他者、消减紧张冲突,良好的秩序遵守易于维系社会关系、加强集体团结,个体同一性利于规约个体行为、提升自我认知。预防校园欺凌,应注重让学生厘清交往的真正内涵,明确交往导向并在生活世界范围内进行主体间活动。一是注重增加学生知识储备,依据学生知识体系层面,有序拓展知识体系的宽度和深度,开阔思维视野,引导学生积极汲取新知识、接受新理念,培养学生善于学习、注意观察、勤于思考的习惯。二是提升学生对社会权力的认知,指导学生运用社会权力信息合理指导自我社会行为,通过品读优秀读物、塑造同伴典型、榜样示范、角色扮演、主题实践等方式促进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三是增强个体同一性认识,促进学生全面自由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帮助学生进行积极心理建设,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