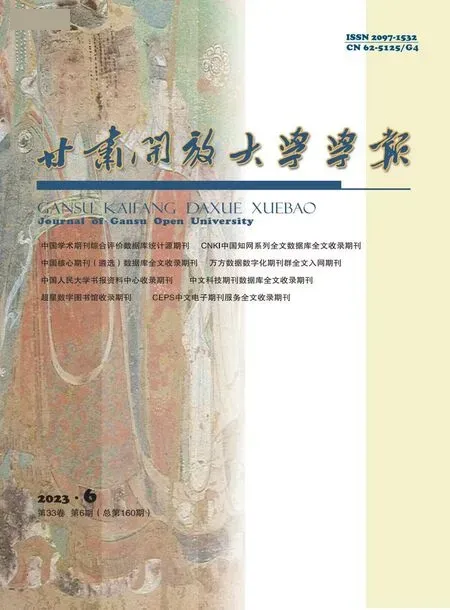我国传统典籍中的孝文化表达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张番红,芦彦琴
(甘肃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1],为加强思想教育、道德教化,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旨在着力引导青年一代自觉担当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促进家庭和睦,也是新时代增进亲人相亲相爱,彰显讲仁爱崇正义、树新风化新人的伦理规范与道德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孝是我国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的逻辑起始,孝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对于中华民族繁衍不息、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向性。
一、我国传统孝文化研究述评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和灵魂。正所谓,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强。自古以来,中华传统孝文化始终受到人民尊崇,可以说,“孝”字贯穿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观念的“孝”最早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从语源学意义上的释义为,善事父母者谓“孝”。作为会意字的“孝”,上为“老”、下为“子”,形似孩子搀扶龙钟的老人状态,其初始含义指向作为晚辈的子女尽心竭力扶持陪伴和奉养父母亲人,据而引申为长辈尊亲去世后晚辈要遵守的守孝礼俗[2]。以孝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征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和魂,彰显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深厚的精神追求。学者们围绕孝文化的起源与演变、孝文化的价值层面和性质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理论阐释,取得了一定的数量研究成果。
1.考察孝文化的起源与演变层面
学者曾振宇认为[3],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行仁、行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起点,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地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孝是天之道的自我展现与自我运动,孝文化孕育生成于父系制家庭的崛起,孝是我国传统家庭道德和政治规范的浓缩表达,也是我国古代一切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孝的基本内涵聚焦于孝养、敬亲以及慎终追远,以孝为代表的伦理文化映射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
2.审视孝文化的价值层面
学者王正平认为[4],我国传统孝文化在道德价值的终极目标聚焦天人合一,在道德价值的应用目标指向道德思想与政治思想的融合,在道德价值的导向目标捍卫血缘宗法的集体性,在道德价值的分寸目标把握上映射中庸居间性质,在道德价值的取向目标上具有重义轻利倾向。学者尹艳阳认为[5],孝作为天经地义的人类内心的纯真本性,早已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精神内核,重视中华传统孝文化,就要弘扬优秀孝文化,发挥中华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推动人们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塑造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归宿。
3.审视孝文化的性质层面
学者陈正宏认为[6],孝是仁的根源,又是仁的实践,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围绕着孝而梯次展开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逻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强大,总是以文化兴盛为软实力支撑,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亟需夯实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
综上,从学者们多角度对孝文化的研究成果看,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讲孝尊孝守孝始终是凝聚和团结华夏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纽带。孝的社会维度指向道德之本,孝的个体维度聚焦于立身之本。民族兴盛、社会文明、良好的家庭氛围,乃至于立身行道,都有赖于培育和践行孝文化。在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之际,积极倡导“孝”文化,着力践行“孝”文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孝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内涵阐释、价值确立以及创新路径探索等方面。从整体来看,孝文化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不过也存在着研究系统性成果少,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孝文化,理论界要兼顾孝文化研究的微观和宏观层面,加强对孝文化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丰富基础理论成果,并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及综合多种方法研究,以此推进孝文化研究的发展。
二、我国传统典籍中的孝文化回顾与梳理
孝文化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发展阶段之后的产物。以《孝经》为代表的我国传统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孝文化资源,回顾和梳理孝文化演进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1.孝文化的孕育生成
任何道德观念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孝文化的孕育生成也遵循这个铁律。当然,孝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着时间长河的推移而发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孝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应运而生,自从人猿辑别,文明肇始,孝文化就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演进。
第一,孝文化的成型。早在远古时代,人们由于敬畏生命而创造了祖先崇拜。在母权社会,妇女的祖先是祭祀的主角,到了父权制社会,男性的祖先逐渐被人们尊崇。父系氏族共同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夫一妻对偶制婚姻,随之家族为核心的宗族正式诞生,这样就历史性地建构了孝文化的源起。成书于元朝的儒家孝文化典籍《二十四孝》记载,舜之父为瞎子,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兄弟象,生性桀骜,他们都想杀了舜,但是舜恭敬,对他的父母和兄弟都很好。他的孝心使尧帝深受感动。尧帝以孝廉为先,知舜仁孝,便将女儿许配给了他。舜继位后,以德治国,乐善好施,百姓安居乐业。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的记载,意即在劳动生产活动中,渴求和平而进行的尊祖敬宗的礼仪便是“孝”的原初蕴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孝亲、祭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越来越多元化,也促使孝文化逐渐成型。
第二,孝文化上升到道德高度。在西周时期,周人审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首的“礼”以“亲亲”和“尊尊”为中心。“亲亲”聚焦于血缘关系、重视伦理秩序和亲属认同。“尊尊”是指向政治关系的层级制度。所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从亲亲、尊祖到敬宗、收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团结统一,彰显了孝亲强大的政治意味。自西周以来,我国历朝历代的社会精英普遍崇尚孝文化,在父权制场域将父权与专制精致地相融合以强化统治,使孝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上升成为人人都要遵守,全社会都在倡导和践行的道德律令。
第三,孝文化成为道德之首。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为了争权夺利,诸侯之间乃至骨肉至亲自相残杀的形象司空见惯。生逢乱世,也促使人们对孝文化重要性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孔子是孝文化的忠实践行者和重要推动者,《孝经》相传为孔子所作。儒家孝文化的框架以“仁”为中心,映射了当时天下大乱、人心无仁慈的现实困境。孔子强调,孝作为人的天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作为人性普遍共性的“孝”是人性中的一种本性。从“孝”的角度来培育人的“仁”,可以让“仁”更容易被人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于是孝文化成为了所有美德之首,并把孝作为道德基础加以推广。
第四,孝文化成为治国理政之策。在古代,孝是天地自然的规律,是人的基本行为规范,是治国之道。把“孝”外化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思想始于汉代。魏晋唐宋,一直到明清时期都尊“孝治”为上策。汉代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孝经》《论语》的“以孝治天下”理念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可,逐渐作为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大学》有言:“以德治天下,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镜像的生动解说。
2.孝文化的丰富内涵
第一,孝文化的原初之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孝”起初是作为家庭伦理观念,孝文化的核心内容指向“养亲”。《孝经》的“孝,始于事亲”[7],《孟子》的“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8],充分表明我国传统文化中孝的第一要义是奉养父母。《弟子规》的“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9],是说人要顺应自然规律,获得丰富的物质资源,保护好自己,以便更好地侍奉父母,此为“孝”的本真内涵。在我国传统的孝文化中,不论任何阶层、任何年龄段的个体,养亲的前提是爱惜好自身。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了良好的身体条件,才能更好地奉养双亲。而“敬亲”是“养亲”的衍生。《论语》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0]。孔丘认为,如果仅仅供养物质生活,却忽略了发自真心地爱护父母,与牛马有何分别?《礼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说儿女养亲,必须遵从父母的意愿,使他们耳目快乐地休息和生活,让父母从内心觉得安稳愉悦。也就是说真正的“孝”不仅要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让父母衣食无忧,还要做到从精神上真正尊敬父母,让父母身心愉悦。“荣亲”是“养亲”与“敬亲”的深化。《孝经》认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1]意指阐明人生在世,要修养身性,遵守道义,奉行道德,扬名于后世,以使父母显赫荣光。荣亲是大孝,是孝的圆满境界,古代的科举考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孝文化中“荣亲”的具象体现和现实表达。
第二,孝文化的衍生之义。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孝文化在家族内部倡导的是孝敬父母长辈,扩展到国家层面形成家国同构思想,并逐渐上升为治理国家的准则。社会道德作为家族习惯的延伸,是通过孝悌的方式来传播。这表明了“孝”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扩展和提升,由最平凡的“亲情”到“人道”“德”,进而“治世”“平天下”。从家庭到整个社会,孝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移孝于国”的理念可以溯源到春秋战国时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观点,即在家里孝敬父母,在外面就能忠诚于国家。孝亲、尊师、敬君、敬长、爱国共同建构了“孝”的衍生之义。为儒家以后的孝文化筑牢了理念根基,也奠定了“移孝于国”的思想基础。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孝”理念并进一步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的观点,表明孟子希望能将家庭的“孝悌”美德推广到全社会。汉魏隋唐时期的社会治理者借鉴孔孟“孝慈为忠”的理念衍生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思想,将“孝文化”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将家庭伦理上升到政治层面。而“举孝廉”的干部遴选制度更是促进了孝文化与国家联系的加深,于是“孝”不仅聚焦于家族的“孝”,更指向对国家的“孝”,从“孝”迁移到“忠”即为“国孝”。
三、传统孝文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孝”内在要求个体从小对父母恭敬友善,而不仅仅是某一时段孝心的迸发和浮于台面的表演。其实,作为个体要想真懂行孝,就需要不断躬身实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细心体味“孝”的真谛,遵循青年的认知及教与学的内在规律,脚踏实地将中华优秀传统孝文化综合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立德树人教育。
1.传承孝文化重在日常生活教育。古人云,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儿方知父母恩。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考试成绩是衡量学生学业水平的核心指标,重智育、轻德育现象抬头,我们要着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中的孝文化教育,通过设立孝文化节日等的方式,以日常生活为基础落实落细落小孝文化教育。
2.传播孝文化重在生活体验。古人云,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在中学教育阶段应侧重夯实以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孝文化根基,思政课教师要在日常教育中融入和渗透“孝文化”,润物细无声地对中学生进行孝文化熏陶。此外,还可以在第二课堂中,积极组织一些诸如创设教育情境类的孝文化课外活动,积极进行孝文化的社会实践教育和传播活动。
3.实践孝文化重在理性认同。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高等教育是个体脱离父母双亲监护的开始,也是和父母越走越远的第一步。当代作家龙应台在其代表作《目送》中指出[12],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意味着你与父母的缘分就是今生不断地目送父母的背影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父母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赶……的确如此,人生就是一场邂逅的相遇,然后黯然别离,而父母则是这趟旅行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当我们目送父母的背影渐行渐远时,只要我们问心无愧,真正做到孝父母、敬父母、爱父母,再回首,也是坦然。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任何一种道德准则抑或行为规范,只有当世人真正发自内心地认可它,并以具体行动实践感知,才算是真正成为了人的一部分。因此,在高校的思想政治课中融入孝文化教育时,要着力通过自身的孝行去感化他人,从而在知、情、行的有机融合中提升自己的幸福感与责任感,这对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内涵以及实践的针对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作为高校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坚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道德至上正确方向[13],着力加强新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突破学段孤立,着力推进大中小学孝文化一体化教育的衔接和提升,真正做到管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统一于强化孝文化认知认同、深化孝文化情感认同、固化孝文化价值认同,在对孝文化的认知体悟中增强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
4.推动个体对父母双亲的孝升华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对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情感引导、思想引导、政治引导,积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孝文化教育,推动人的道德社会化,进一步把“孝”与“仁”相结合的“家”精神升华为“一家亲”。思想政治教育要着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爱家与爱国有机融为一体,努力将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到国家梦、民族梦。也就是说,传承孝文化的终极目标旨在让青年一代从理解“小孝”到“大孝”,把对父母、宗族的孝升华成为国为民的孝道,引领青年学生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灿烂文化,关心祖国发展进步,为祖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培育青年民族精神、激发爱国情怀。
5.凝练孝文化精义,着力加强青年一代的生命安全教育[14]。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文化孕育生成于我国特定历史情境中,就必然注定了不可避免地蕴含传统元素。在推动孝文化教育的内容设计和具体实施中,教育者要秉持“扬弃”原则,既要保持和发扬优秀的孝文化精髓,也要摒弃不符合社会认知的封建糟粕。在“孝养”的基本前提下,更应该实现“孝敬”,也就是对父母的充分尊重、关怀和关爱。正如《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得父母,不敢毁,孝之始也”,要教育引导青年热爱自己的生命、保全身体,是行孝的先决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把孝文化提升到全民参与和实践的多维层面,着力教育引导青少年积极传承和弘扬孝文化,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时代新人的关键环节,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途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