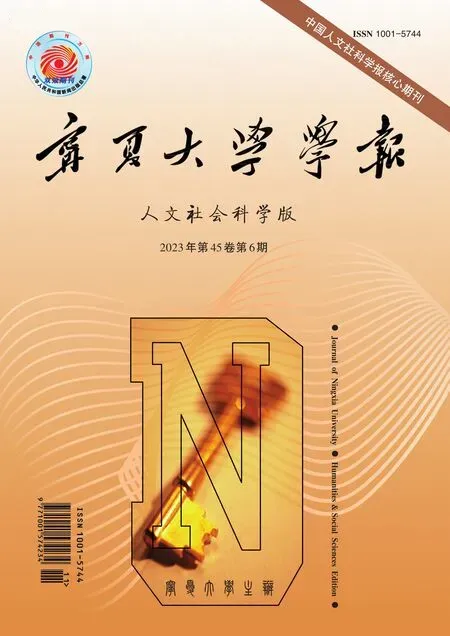本性与秩序
——论莎士比亚悲剧主角的“心灵之战”
朱 琰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莎士比亚戏剧以描绘人内心世界的冲突见长,尤其在《哈姆莱特》等四部后期悲剧中深刻呈现。一百多年前的莎学专家布雷德利(A.C.Bradley)认为,相较于剧中不同人物或集团间构成的“外部冲突”,角色个人心灵的“内部冲突”更令人难以忘怀,同时也尽然彰显莎氏悲剧的非凡之处[1]。长期以来,评论者们从人物性格、外部影响、来源以及现代性的角度解读悲剧主角的心灵冲突,如布雷德利指出,主角的内心冲突是人物性格的表现[2];黑格尔将心灵冲突视为不同理念在人物内心呈现的敌对状态[3];坎利夫(J.W.Cunliffe)将塞内加(Seneca)笔下的自省性人物视作主角内心冲突的影响来源[4];马尔科姆·希伯伦(Malcolm Hebron)则强调内心冲突是现代个人意识上升的体现[5]。上述研究解读深入,但少有学者从人性认知的角度对人物内心冲突的现象作出解释。
在剧中,四位主人公常在关键行动之前陷入复杂的心灵冲突中,或者是人物漫长的内心战争贯穿全剧。 本文结合中世纪道德剧“心灵之战”的书写传统,对人物内心冲突反映的人性“善恶二重”的本质以及人无法避免堕入邪恶的悲剧性处境进行解读。“由于本性存在善恶两种倾向,人可能上升与天使相似,也可下降至野兽的处境,因此,人的命运并非取决于上帝,而在于自身”。剧中,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探讨也不仅局限于个人层面,还在个人—国家—宇宙的整体秩序中进行认知——当个人本性的秩序失衡时,国家及宇宙的秩序也会随之发生混乱。此外,戏剧家在剧作结尾中都以“认知自我”的方式恢复心灵秩序,结束由“心灵之战”引发的外部混乱,从而实现作者本人维护个人、国家及宇宙和谐秩序的人文主义理想。
一 “心灵之战”与“善恶二重”的人性
哈姆莱特、麦克白等悲剧人物常常在关键行动实施前陷入左右摇摆的内心冲突中,他们通过自我对话或与其他角色倾诉的方式表达内心正在经历的灵魂战争。如哈姆莱特在戏剧终幕说道:“在我的心里有一种战争,使我不能睡眠;我觉得我的处境比套在脚镣里的叛变的水手还要难堪。”[6]他在复仇过程中饱受内心冲突的折磨,“好像绑在拷刑板上向不同的方向分裂开来”[7]。
心灵冲突的“难堪”处境在其他三位主角身上也经常出现。麦克白的弑君行动在开场第二幕就已完成,但莎士比亚除笔力集中地描绘他在杀人前的内心冲突外,还对其犯下罪行后的内心之战进行细致呈现。麦克白第一场内心之战发生在第一幕七场,他反复思索着“杀,还是不杀国王”这个问题;第二场内心之战则作为暗线漫长地贯穿在犯罪后的麦克白心中。奥瑟罗内心激烈的冲突主要集中于戏剧的最后两幕,他听信伊阿古的谎言而怀疑苔丝狄蒙娜不忠,一方面想着“嗯,让她今夜腐烂、死亡、堕入地狱吧”[8],转念间又于心不忍。等奥瑟罗真正下定决心杀死妻子时,再次陷入内心的挣扎中:他既不愿意将苔丝狄蒙娜杀死,又转头为自己杀人的行为找到正当理由——“可是她不能不死,否则她将要陷害更多的男子”[9]。心灵之战在《李尔王》中贯穿戏剧始终——从开场李尔王的错误选择,到最后带着悔恨与痛苦之心寻找科迪利娅。另外,莎士比亚还在剧中刻意设置李尔王在荒野中被暴风雨侵袭的场景,这场自然界的暴风雨是李尔王激烈内心冲突的隐喻[10]。由此可见,无论处于何种情境中的主人公,由内心冲突引发的心灵震颤都是他们无法避免的困境。蒂利亚德(E.M.W.Tillyard)曾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他指出,“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的新教徒将保罗列出的精神战争加工成他们自己最鲜活的神话,……他们乐意揭露人的所有相互矛盾之处,尤其是极尽可能地描绘人在兽与天使之间的摇摆,给了旧有的(理性和激情)古老交锋以新的力度”[11]。简而言之,莎士比亚描绘灵魂左右摇摆的状态是对传统的精神之战主题的继续发展,人物内心冲突的困境实质上展示了人性“善恶二重”的本质。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他深入探索人的内心世界,通过灵魂深处的冲突,将人性“善恶二重”的本质面貌在哈姆莱特、麦克白等人身上进行呈现。当麦克白意图弑君时,自身罪恶的野心催促其迅速展开谋杀行动,尽快享受临登王位的快乐;但同时,理性本性又百般劝阻,防止他堕入欲望的世界。表面上看,麦克白与三个女巫的两次会面表明,他似乎是听信了超自然的诱言才导致堕落,但实质上,麦克白是受自身邪恶本性的指引才走向了毁灭[12]。同样的,奥瑟罗经历的“心灵之战”也深刻地体现出戏剧家对人本身“善与恶”或“高贵和兽性”对立本性的探讨[13]。“理智与情欲”作为奥瑟罗内心战斗的双方不断产生冲突,最终在他扼杀善良的苔丝狄蒙娜后得以平息。奥瑟罗本人也明白,致使自己犯下罪行的并不是伊阿古,而是自我灵魂中的恶:“只是为了一个原因,只是为了一个原因,我的灵魂!……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14]李尔王一开始之所以会听信里甘和戈纳瑞,甚至愤怒地驱逐科迪利娅,都因长女们的“美丽的语言”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因此,他才错误地选择了恶的虚假阵营,而忽略了善的真理[15]。哈姆莱特虽然是苦思善恶问题的思考者,但邪恶的本性又使这位“高贵的王子”心中“充满了报复与仇恨的念头”[16]。
实际上,莎士比亚通过人物内心冲突呈现人性的方式可以在中世纪晚期的道德剧(The Morality Play)中找到源头。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人拥有善恶两种本性,这两股力量在人的灵魂中相互斗争,共同驱使着灵魂,引导人作出相反的行动。中世纪的基督教道德家们常借用善恶在人类灵魂中斗争的“心灵之战”(Psychomachia)主题宣传宗教道德观[17],晚期的英语道德剧便是典型。并且道德剧在沿用传统的“心灵之战”主题时进行了两方面的创新,一是增加“人类”角色,二是以演讲或说教的方式替代打斗场面[18]。诸如创作于15 世纪初的道德剧《坚韧的堡垒》(The Castle of Perseverance)便是将人的一生描绘成灵魂反复经历心灵战争的精彩之作。在剧中,主人公“人类”(Mankind)本性中的善与恶被拟人化成“善天使”(Good Angle)与“恶天使”(Bad Angle)两个角色,人依据自由意志进行选择的过程则被戏剧化地展现为两大天使对“人类”及其灵魂进行争夺的战争。“人类”在双方战斗的过程中陷入“难堪”的处境——“到底将跟随谁呢,你(善天使)?还是你(恶天使)?……我心不定如波涛起伏”[19]。莎士比亚借鉴道德剧的戏剧技巧,围绕主人公灵魂深处的激烈冲突构思剧本[20],将善恶天使对“人类”灵魂的争夺之战变成哈姆莱特等人自我的“心灵之战”,借此呈现善与恶共同存在于人类本性中的事实。
在向人的内在世界不断探究的文艺复兴时期,曾主导着希腊悲剧发展的外在命运观不足以让已抵达人类内心并找寻自我力量的人们信服。莎士比亚在剖析人内心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人类灵魂中的冲突与混乱,借此认知了人性“善恶二重”的本质,为全面认识人本身、尊重人的价值提供了前提。
二 “心灵之战”的结局——“无可避免的恶”
阿尼克斯特曾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是从肯定人性本善开始的。到了莎士比亚时代,人文主义者对性善说产生了怀疑”,莎士比亚与同时代的作家“在人的身上发现了撒旦的因素”[21]。莎士比亚已然通过主人公共同经历的“心灵之战”,展现其对人本性的认知——人性中善恶并存,两者相互斗争、势均力敌,但这只是他对人性本质的初步探索。在四部悲剧中,无论是最终走向毁灭的哈姆莱特与麦克白,还是在临终之际获得灵魂救赎的奥瑟罗与李尔王,戏剧家都让他们在历经“心灵之战”后作出了恶的选择。人无可避免地陷入罪恶的悲剧性处境被莎士比亚在这些人物身上尽然展示,其意在于进一步揭露人性的真实本质,直指其中令人忧虑的一面,对以赞美人性为主流的人文主义进行反思。
莎士比亚通过奥瑟罗呈现了恶如何逐渐膨胀并最终蚕食人的意志的全过程。一开始,奥瑟罗以完美形象出场,他是“高贵的摩尔人”,凭借卓越的战功为自己赢得荣誉与名声,与此同时,他对待爱人也温柔坚定。但在伊阿古恶意的暗示和自己的疯狂想象中,忌妒的本性逐渐占据他的内心,心中巨大的怀疑转化成怨恨。奥瑟罗在面临灵魂的十字路口时选择了邪恶的本性,致使其强大的情欲控制了理性。最终,他对苔丝狄蒙娜的解释置若罔闻,在疯狂中扼喉杀妻。埃德蒙·克里斯(Edmund Creeth)曾指出,奥瑟罗的肤色实际上是对其人性中的兽性(恶)部分的象征,与苔丝狄蒙娜象征美德(善)的白皙肤色形成对比,因此,堕落至邪恶的处境是他必然的宿命[22]。由此可见,本性中的恶一旦被选择就会不断膨胀,最终使得人的灵魂逐渐迷失,直至堕落。
在《麦克白》中,莎士比亚不仅以加速的方式呈现了善的人性如何堕落的过程,还对人陷入罪恶后恶的无限发展进行揭露。如果说麦克白经历的第一场“心灵之战”是因其本性中固有的善恶冲突导致其陷入痛苦的处境,那么第二场漫长的灵魂冲突则是麦克白明知故犯成为罪人(Sinner)后灵魂必然经受的折磨。在完成弑君、登上王座等一系列行动后,麦克白意图通过犯下更多的罪行使自己“内心坚硬”,从而杜绝忏悔。但充斥于内心的恶并不能将人性中固有的善全部取而代之,因此,麦克白再次面临的内心战争可以看作善的本性对恶的不断“谴责”[23]。麦克白在一次选择恶之后决定向罪恶全然奔赴,他坚信“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24]。麦克白对恶的选择以及巩固证明了人性的罪恶不存在极点,恶一旦开始,就会把人不断地推向恶之深渊。
李尔王是表现人类虚荣心的君主典范。他人性中的恶在戏剧开场时就得以呈现,他制定了亲情之爱可以换取财富与权力的规则,由此展开一场“测试”。李尔王高傲地说:“我要看看谁的天性之爱最值得奖赏,我就给她最大的恩惠。”[25]此时,狂妄任性的李尔王既不清楚自己是谁,也体会不到事物的本质。两位女儿极尽奉承的回答令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在灵魂的十字路口已经表现出跟从邪恶本性的倾向。随后,当科迪利娅遵循理性并未给出顺他心意的回应时,李尔王的愤怒便倾泻而出。他在瞬间听从恶本性的指引,怒斥科迪利娅,并将她驱逐出去。愤怒的情欲将李尔王头脑中的正义、判断与智慧一扫而空,导致他作出愚蠢、邪恶的行为[26]。事实上,李尔王分割国土的方式也并不符合自然法则,刚愎自用的君主凭借自己骄傲的意志恣意妄为,最终给个人、家庭甚至国家都带来巨大的灾难。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揭露了诸多现实的罪恶,他借哈姆莱特之口评价现实世界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27]。但实际上,作为“人伦的典范”的哈姆莱特,一方面在思考着人为什么会变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受自我邪恶人性的支配。其对奥菲利亚毫无道理的嘲弄和羞辱正是其人性中恶的表现[28]。他向无辜的非报仇对象肆意发泄愤怒与怨恨也是其残忍心理的外现,是绝对强者对绝对弱者肆无忌惮的蹂躏[29]。剧中的哈姆莱特曾这样评价自我,“我很骄傲、使气、不安分,还有那么多的罪恶,连我的思想里也容纳不下……”[30]尽管这段话常被视作疯话,以便为他的美好形象开脱,但这番自我描述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道出了哈姆莱特本性中存在恶的事实。复仇王子在维护和实现自我追求的伦理理想中,也作出了一些残酷的行动。诸如他在疯狂中错杀波洛涅斯却不以为意,内心充满报复与仇恨的念头使得哈姆莱特逐渐失去理性,令他在复仇的过程中作出诸多像野兽一般的行动。学者莉莉·坎贝尔(Lily B.Campbell)指出,哈姆莱特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中,一味地悲伤,最终导致了世界的灾难[31]。无可避免的人性之恶在哈姆莱特身上全然暴露,即便他拥有美好的德行、行正义之事却也无法脱离陷入罪恶的处境。
四位悲剧主角共同表现了人性恶必然存在的事实,并且不同形式的恶支配着人的命运,最终使人陷入悲剧性的处境。正如布雷德利所指出的,恶是莎士比亚悲剧故事的根源。尽管他曾将人物“心灵之战”的产生归因于性格,但是他也进一步确认悲剧主角性格中的缺陷就是邪恶,它使人物遭受苦难和自行糟蹋[32]。《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神父劳伦斯对悲剧主角的命运一语成谶:“草木和人心并没有不同,各自有善意和恶念争雄;恶的势力倘然占了上风,死便会蛀蚀进它的心中。”[33]事实上,在莎士比亚创作悲剧的时期,他对人本身以及处境的理解始终笼罩着巨大的乌云。他一改前期对人可爱之处的书写,转而在哈姆莱特等悲剧人物身上展现出一幅幅人性之恶的图景,真实地呈现了人性善恶的本来面目。并且,尽管善恶两者等量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但人在经历“心灵之战”后受自由意志中欲念的影响,也会无可避免地堕入罪恶中。
三 “心灵之战”与整体秩序
莎士比亚通过悲剧主角的“心灵之战”展现其对本性的两方面认知:善恶两者共存于人性中;人在凭借自由意志进行选择时,罪恶便无法避免。另外,通过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莎士比亚对于人性的理解不仅局限于对个人本身善恶的探讨,还在个人—国家—宇宙三者联系的整体视域中展开。当哈姆莱特、麦克白等人因“心灵之战”引发个人的本性失序时,国家及宇宙的秩序也会出现相应的混乱状况。莎士比亚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已借俄底修斯之口表达他对三个领域内秩序问题的看法:诸天星辰只有恪守秩序各安其位,才能使太阳高拱中天、炯察寰宇;国家需要遵守秩序,社会才能井然有序;个人若将秩序扼毙就会被欲望吞噬,无法明辨是非,无以安身立命。总之,如若“把纪律的琴弦拆去”,各个领域便会发出“刺耳的噪音”[34],陷入混乱之中。在文艺复兴时期,个人、国家及宇宙常被视作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整体,因此,无论哪一方出现破坏秩序法则、逾越本分的现象,都会导致其余领域发生相应与相似的连锁灾祸。蒂利亚德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认为万事万物都被包含在“存在之链”(Chain being)中,并且人在其中处于特殊的位置:天使之下,野兽之上[35],所以,人不仅拥有与天使相似的高级理性本性,也有着与野兽相似的低级兽性。哈姆莱特、麦克白等人因内心的善恶之战导致自身两种本性不安其位,出现混乱现象,在四部戏剧中,因个人本性的失序而引起国家、宇宙发生混乱的现象被戏剧家细致地呈现出来。
在《李尔王》中,个人与国家、宇宙秩序的联系最为直观。与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反复探讨的主题(君主的心灵秩序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样,李尔王作为最高统治者,其个人本性的失序势必会影响社会安定,导致国家陷入战争的动乱中。全戏展现了两种类型的战争,一类是支持李尔王的人与现任统治者之间的内战;另一类是英法之间的国家战争[36]。而两类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都可追溯至李尔王的愤怒之情。在戏剧开场,即将逊位的李尔王在愤怒中分封国土、驱逐幼女。这一“任性”的非理性行为为之后国家战争的爆发埋下隐患。两位女儿因忌惮老王的权威,于是通过削减扈从的方式进行夺权,以消除威胁。而因不满里甘与戈纳瑞对李尔王的残酷对待与疯狂夺权的行为,肯特等人与两位当权者形成对立之势,杀戮、背叛随之发生,致使国家陷入动荡。此外,通过奥本尼在出征前所说的话可知,掌握新权的统治者在国内实行“苛政”,不平之声早已此起彼伏,国家已然呈现出分裂的态势。因此,可以说李尔王作为国家之首,因未能管理好自我的本性秩序,导致其作出错误的行动,从而直接影响国家秩序的安定。至于法国对英国“掀动干戈”也并非出自法国“非分的野心”,而是在科迪利娅领导下的拯救行动——她希望通过战争拯救在英国受苦的父亲,并恢复老李尔王应有的权利,但李尔王如今的落魄处境也由自我先前的行为所造成。值得注意的是,李尔王由本性乱序引发的国家动乱之象也在宇宙天象中映射,葛罗斯特在第一幕中就已说明,他指出,最近日蚀、月蚀异象频发,“大自然被接踵而来的现象所祸害”[37]。他所说的“祸害大自然的现象”正是指“城市发生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发生叛逆”等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由此,李尔王自我人性秩序的问题不仅关乎个人道德,还与国家、社会的稳定以及宇宙的自然天象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联。
如果说李尔王是俄底修斯蜂房之喻中的“蜂王”,其能否维护好个人心灵秩序对国家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麦克白则是其中的“工蜂”,其若因本性失序不分等级、“各自为政”,势必也会破坏社会良序,造成国家动乱。剧中,麦克德夫在见到国王邓肯的尸体后,一语道破麦克白弑君行为的本质:“混乱已经完成了他的杰作”[38],这句话可理解为麦克白因自我本性混乱从而被欲望引导,驱使他作出了破坏伦理纲常的事,也极大危害了国家的稳定秩序。事实上,麦克白的弑君行动必然会导致苏格兰陷入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中。一方面,因邓肯早已将长子马尔康立为王储,尽管他在国王被谋杀后远逃英格兰,但马尔康作为真正合法的君主必定会与新王麦克白形成对立之势。而后,他在麦克德夫等人的协助下借英格兰的军队讨伐麦克白,战争在所难免,国家也因王位争夺陷入动乱。另一方面,麦克白在登上王位后为巩固王权展开了疯狂的杀戮行动:谋杀班柯父子以绝后患、肆意屠杀无辜之人、残杀麦克德夫全家,这些暴行早已引起众人的不满。更何况麦克白作为新君也无治国之能,他在苏格兰推行暴政统治,导致贵族们惶恐不安、百姓苦不堪言。民众对麦克白的反感情绪已达顶峰,抗争分裂的态势一触即发。同样的,由麦克白的失序之心引发的混乱在宇宙自然领域也产生连锁反应。在邓肯王被杀的夜晚,自然界异象频发:狂风大作,大地发热颤抖,可怕的怪鸟整夜鸣叫。第二天,时钟上已显示白昼的时辰,但黑夜却依旧将大地笼罩。甚至麦克白本人也明确表明自己所行之事的本质是破坏国家及宇宙秩序的行为:“让一切秩序完全解体,让天地一起遭受灾难吧。”[39]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马尔康将自己起兵讨伐麦克白的行为称为“匡正”,此场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父报仇、夺回王位,更是恢复因麦克白的失序之心而陷入混乱的国家及宇宙的秩序。
在《哈姆莱特》中,王子的“弑君”之举不是像麦克白一样出于个人的野心和欲望,而是一场经过理性思考的正义复仇。哈姆莱特将此视作重新恢复“混乱颠倒时代”秩序的行动。但在漫长的复仇过程中,复仇王子的理性并非总处于主导之位,悲伤和暴怒的“感觉”将其操控,导致他犯下诸多伤害自我与他人的罪行。但个体的本性之乱不仅使哈姆莱特本人陷入痛苦的处境,更引起丹麦国的政局动荡,甚至导致国家主权移交异国的结局。事实上,无论是克劳狄斯的继承王位,还是他的婚姻,都得到了丹麦群臣的允许与支持,尽管众人是处于被蒙蔽的状态下才认可新王的合法性,但克劳狄斯在掌权后的确已建立起新的国家秩序,他甚至还阻止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发生,维护了国家和平与安定。而在哈姆莱特复仇计划的推进中,国内由此形成了两派势力:支持新王的波洛涅斯等朝臣以及与王子同一阵营的霍拉旭等人,这一对立之势为宫廷陷入动乱埋下隐患。此后,哈姆莱特在疯狂的状态中错杀老臣波洛涅斯,致使雷欧提斯发生叛变,企图“弑君”并另立为王,由此使得整个国家陷入真正的混乱中。此外,哈姆莱特在经历漫长的延宕后终将复仇之剑刺向克劳狄斯时,其身边大部分人都因卷入复仇事件而为此丧命,厄耳锡诺城堡血染宫墙,丹麦国的王冠最终落在了挪威人的手中[40]。由此可见,哈姆莱特的复仇原是“重整乾坤”的义举,但在此过程中因其未能规范好自我本性的秩序而给国家招致诸多灾祸。国家之乱的现象也在宇宙自然界中呈现,丹麦国内预报重大变故的征兆屡屡发生——“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噬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41]。
相较于上述三位主角而言,因奥瑟罗个人本性的混乱引发对其余领域秩序的影响并未直观呈现,但莎士比亚在剧中留下诸多线索,用以引导读者将个人本性与国家、宇宙整体秩序建立联系。比如奥瑟罗在处理凯西奥与蒙太诺的争端时表明此时的塞浦路斯并不安定,虽然土耳其带来的战争隐患已经消弭,但在这个新遭战乱的城市,“秩序还没有恢复,人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42]。所以,一旦民众得知在治安守卫处发生了争吵与斗殴,必然会“扰乱岛上的人心”。奥瑟罗作为小岛的总督,他对保卫城市和平、稳定民心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疯狂的忌妒之情占据奥瑟罗的大脑并破坏他内心的稳定秩序时,奥瑟罗无心顾忌城市安定,一心只想杀死苔丝狄蒙娜,也同意谋杀凯西奥。那么,可以想象,奥瑟罗的疯狂杀戮行为势必会造成比此前斗殴事件更恶劣的影响,从而引起塞浦路斯民众的巨大恐慌,影响社会秩序的和谐。另外,苔丝狄蒙娜对于奥瑟罗而言,不仅是他内心秩序的象征,也是其与威尼斯的重要联结。奥瑟罗在剧中多次表明,妻子如天使般维护着他内心秩序的稳定,假如当他不爱苔丝狄蒙娜时,内心世界便会归于混沌。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奥瑟罗作为外邦人,他只是威尼斯的一名“雇佣兵”,与苔丝狄蒙娜的结合可以使他真正“嫁接到这个威尼斯共同体”[43]。而奥瑟罗因本性之乱杀害苔丝狄蒙娜,一方面证实其已彻底倾覆本性秩序;另一方面,这场具有“僭越”意义的谋杀也必定会引起威尼斯朝野的震惊与愤怒,奥瑟罗也因此被撤下兵权,这意味着威尼斯失去了最得力的维护国家安定的战士。事实上,奥瑟罗在谈话中常提起天体的意象,他要求自己的内心必须沿着恒常的轨道进行,不受欲望的影响。当他犯下杀妻恶行时,奥瑟罗为自我的失序之心感到痛苦,同时也认为他的堕落行径引起了天象的异常变化——“不幸的时辰!我想现在日月应该晦暗不明,受惊的地球看见这种非常的灾变,也要吓得目瞪口呆”[44]。至此,奥瑟罗个人本性的失序也引发其余领域陷入混乱之象中。
四 结语
总而言之,莎士比亚通过四位主人公的“心灵之战”呈现其对人性“善恶二重”本质的认知,回应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潮流。戏剧对人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处境进行揭露,借此反思17 世纪的“人性解放”主张,以期在人文主义危机和个人主义陷阱中找到人合理的存在方式。并且,戏剧家将个人的人性与国家、宇宙的秩序相联系,强调了人对自我人性的关怀不仅关乎个体,更负担着与生存的外在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责任。戏剧家通过主角的“心灵之战”在个体与整体两方面对人性进行关照与规范,是其实现个人、国家及宇宙三者秩序和谐的人文主义理想的有效实践。
——他者形象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