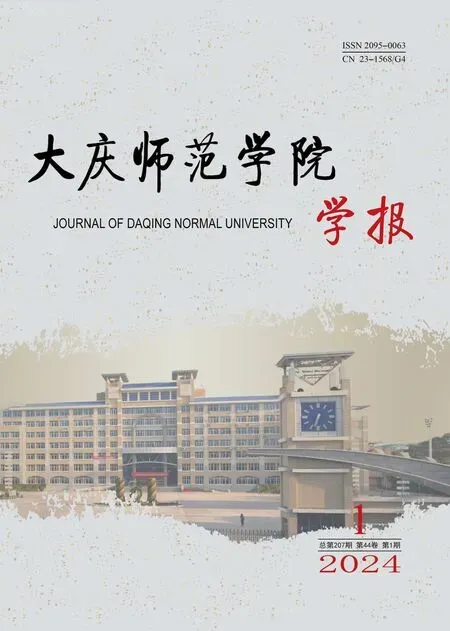唐宋词中的禽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赵 丽,刘 玲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禽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意象,上古先民认为鸟是沟通天地的图腾,是自由的象征。闻一多先生指出鸟类的不同属性代表了人类的各种属性,“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理,最初本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为喻,但为一种修词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淡,而修词意味愈浓,乃以各种鸟类不同的属性分别代表人类的各种属性……后人于此类及汉魏乐府‘鸟生八九子’、‘飞来双白鹄’、‘翩翩堂前燕’、‘孔雀东南飞’等,胥以比兴目之,殊未窥其本源(1)闻一多:《古典新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1页。”。这些极具艺术魅力的精灵们,展开灵动的翅膀,跨越漫长的历史长河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上空自由飞翔,不受羁绊。

词人们关注自然、体物察情,对自然意象的禽鸟极尽描摹,展现其灵动的身姿、绚丽的色彩,描写其欢愉或悲伤的啼鸣。通过对鸟之形、鸟之声、鸟之色倾尽笔墨的描绘赋予其内涵丰富的情感意蕴,仙鹤高蹈世外,白鹭闲野不俗,杜鹃是凄楚哀怨的化身,鸳鸯是爱情的象征,禽鸟意象成为词人传情达意、比兴寄托的重要媒介。
一、禽鸟意象是物候的象征
禽鸟意象展现了自然的美景、节序的变化与生命的律动所带来的美感愉悦和对人生的思考,表现了词人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
(一)禽鸟意象展现了自然的美景和节序的变化
1.禽鸟是物候的象征
物候是“自然界中生物或非生物受气候和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出现季节性变化的现象。例如,植物的萌芽、长叶、开花、结实、叶黄和叶落;动物的蛰眠、复苏、始鸣、繁育、迁徙等”(5)《辞海》(4),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433页。。古代的先民们观察到了四季景物的变化,鸟儿飞来又飞去等自然现象与气候的关系。四时之景不同,四时之鸟亦不同,禽鸟成为了物候的象征。
燕子、莺、黄鹂是春天常见的禽鸟,词人往往把它们当作春天的象征,如:
小园东,花共柳。红紫又一齐开了。引将蜂蝶燕和莺,成阵价、忙忙走。(柳永《红窗迥》)
晴鸽试铃风力软,雏莺弄舌春寒薄。(张先《满江红·初春》)
春风不负东君信,遍拆群芳。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晏殊《采桑子》)
晏殊在《破阵子·春景》中描写春天的景色时也写到了燕子和黄鹂: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词中新社指春社,立春之后燕子飞来衔泥筑巢,梨花落后是清明时节,黄鹂鸟在茂密的树叶间娇啼,在明媚亮丽的春光中,年轻的采桑女们巧笑相逢,“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用自然的美景映衬生活的美好。
燕子是候鸟,古人认为燕子于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飞回北方,秋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飞到南方。因此它同时也是初秋的典型意象。晏殊在《蝶恋花》(梨叶疏红蝉韵歇)中描写秋夜时写道:“枕簟乍凉铜漏咽,谁教社燕轻离别。”在《清平乐》(金风细细)中他写道:“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
雁、鸦则是秋冬季节常见的禽鸟。欧阳修曾经写过十二月《渔家傲》鼓子词,其中有三首写到雁:
九月霜秋秋已尽……新雁一声风又劲。云欲凝,雁来应有吾乡信。
十月小春梅蕊绽……风急雁行吹字断。
十二月严凝天地闭……马前一雁寒空坠。
黄庭坚元符二年(1099)重阳节创作了《鹧鸪天·重九日集句》:“塞雁初来秋影寒,霜林风过叶声干。”秦观于元丰二年(1079)岁末离开会稽时创作的《满庭芳》中有“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在另一首《菩萨蛮》中写秋夜辗转难眠,又提到了鸦:“毕竟不成眠,鸦啼金井寒。”
2.禽鸟意象展现的节序变化触动了词人的心绪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美好的春光和人世间的美好感情共同生发。奈何岁月易逝,韶华难在,伤春惜春之情油然而生。词人或直接或间接借禽鸟意象抒发伤春悲秋,相思念远,离愁别恨,感时伤事,人生感悟等:
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王安石《菩萨蛮》)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王安石《清平乐》)

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晏殊《木兰花》)
春光易逝,韶华难留,人生也是如此。美好的春光,美好的年华,美好的感情就像春梦一样易醒易逝,像天边的秋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如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王安石《千秋岁引·秋景》)
王安石退居金陵时,身为客居他乡的游子,耳闻寥廓秋声,眼见“东归燕”与“南来雁”穿梭不停,心中无限怅惘,不禁发出“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的叹息。
(二)禽鸟意象表现了词人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
禽鸟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人类的朋友。对禽鸟的描写表现了词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闲适恬淡生活的向往。张志和在《渔父》中写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白鹭在西塞山前自由飞翔,明艳绚烂的桃花在流水的映衬之下愈发显得娇艳欲滴,肥肥的鳜鱼在潺潺的流水中游动。青山、白鹭、桃花、流水,色彩鲜明,如诗如画。江南风物之美让词人流连忘返,直呼:“斜风细雨不须归。”“禽中唯鹤标致高逸,其次鹭亦闲野不俗。”(6)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16页。白鹭意象形象地表达了词人高蹈世外、寄情隐居生活的乐趣。宗白华在《美学漫步》中曾经说过:“鸟启示着自然的无限生机。中国人……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表现了无限,所以他的态度是悠悠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7)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9页。张志和笔下的白鹭意象恰切地反映了词人“悠悠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态度。清代黄苏评价这首词:“数句只写渔家之自乐其乐,无风波之患,对面已有不能自由者,已隐跃言外,蕴含不露,笔墨入化,超然尘埃之外。”(8)王兆鹏主编:《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蒲寿宬的《渔父》和张志和的这首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江渚春风澹荡时。斜阳芳草鹧鸪飞。莼菜滑,白鱼肥。浮家泛宅不曾归”,同样表达了词人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只是“斜阳芳草鹧鸪飞”远不如“西塞山前白鹭飞”的空灵明秀,超然世外。
二、禽鸟意象是爱情的象征
自从《诗经·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启了用禽鸟意象表达男女之情的滥觞,禽鸟意象就成为男女之间寄托浓情蜜意和相思愁怨的载体。
(一)成双成对的禽鸟意象是夫妻恩爱的象征
鸳鸯自古以来就是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寄予了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理想。李时珍云:
鸳鸯终日并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也。或曰:雄鸣曰鸳,雌鸣曰鸯。崔豹古今注云:鸳鸯雄雌不相离,人获其一,则一相思而死,故谓之匹鸟。(9)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年,第2053页。
司马相如在《琴歌》中借鸳鸯交颈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倾慕和大胆表白:“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我们如何才能结为夫妻,像交颈的鸳鸯一样恩爱亲昵。张孝祥在《浣溪沙》中用“豆蔻枝头双蛱蝶,芙蓉花下两鸳鸯”比喻沉浸在柔情蜜意中的情人。
唐宋词中除了用鸳鸯表达夫妻恩爱,情深弥笃外,还有燕子和鹧鸪。
鸳鸯、玄鸟爱其类。鸳鸯,匹鸟也。玄鸟,燕也。二鸟朝倚暮偶,爱其类也。(10)师旷:《禽经》,张华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燕子朝暮相随,鹧鸪雌雄对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如鸳鸯、鹧鸪、梁燕、鸾凤一样比翼齐飞,相濡以沫是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愿望和憧憬。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冯延巳《薄命女》)
酒阑歌罢两沉沉。一笑动君心。永愿作鸳鸯伴,恋情深。(毛文锡《恋情深》)
所以成双成对的鸳鸯、鹧鸪、梁燕、鸾凤等意象成为夫妻恩爱、忠贞不渝的象征。
(二)成双成对的禽鸟意象反衬主人公的孤独凄凉
词人有时反其意而用之,用鸟的成双成对反衬主人公的孤独凄凉,寄托闺中怨妇的愁思。温庭筠的《菩萨蛮》把这种写法运用得特别娴熟。如“凤凰相对盘金缕”(《菩萨蛮》),“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菩萨蛮》),“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尤其是“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一句,主人公睹物伤神,对影自怜,孤独寂寞的形象呼之欲出。牛峤两首《梦江南》,一首咏燕,一首咏鸳鸯:
衔泥燕,飞到画堂前。占得杏梁安稳处,体轻唯有主人怜。堪羡好因缘。
画梁上衔泥的燕子在建造幸福的窝巢,让主人公羡慕不已。
红绣被,两两间鸳鸯。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全胜薄情郎。
红色绣被上一对对笃定情深的鸳鸯让主人公想起了薄情负心的情郎。
“以乐景写哀情,一倍增其哀乐。”毛熙震《小重山》“梁燕双飞画阁前,寂寥多少恨、懒孤眠。晓来闲处想君怜,红罗帐、金鸭冷沉烟”,用梁燕双飞反衬女主人公的寂寥孤独。周紫芝《生查子》“帘幕卷东风,燕子双双语。薄幸不归来,冷落春情绪”,用燕子双双语反衬女主人公的冷落孤寂。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用燕子双飞反衬闺中思妇的忧伤惆怅。“各种现实的事物,都必须被想象力转化为一种完全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作诗的原则。”(11)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99页。用禽鸟的成双成对反衬女主人公的孤独寂寞成为一种表达闺中相思幽怨情感的固定模式,并成为一种递相沿袭的表情达意的艺术符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孤鸟意象。成双成对的禽鸟意象是夫妻恩爱的象征,劳燕分飞、鸳鸯失伴则是孤单寂寞、相思离别的象征。吴文英在悼亡词《绛都春》中称亡妾为“南楼坠燕”。贺铸中年丧妻,写下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青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用鸳鸯的失伴比喻自己的丧偶。头白二字是双关语,既是写鸳鸯头白,也是写自己满头白发。
三、孤鸟意象是词人的自我写照
词人经常用孤鸿孤雁自比,“人是岭头云,聚散天谁管。君似孤云何处归,我似离群雁。”(周紫芝《卜算子·席上送王彦猷》)“鸿雁属,大曰鸿,小曰雁,飞有行列也。”(12)师旷:《禽经》,张华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孤鸿孤雁是失群的鸟,没有伙伴,找不到栖息之处。宋词中的孤鸿孤雁意象,北宋以苏轼的《卜算子》为代表,南宋以张炎的《咏孤雁》为代表。
1.“乌台诗案”后的苏轼自比为孤鸿
元丰三年(1080),从“乌台诗案”中侥幸脱身远贬黄州的苏轼触景生情,写下了《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正是被君主疏离,被群僚陷害,“忧谗畏讥”的苏轼的真实写照。“独”“惊”“恨”“寒”“寂寞”“冷”,这哪里是在写孤鸿,分明是刚刚从牢狱之灾中脱身的词人的自我写照。孤鸿的身影触动了苏轼的心弦,引发了词人的悲叹。嘉祐六年(1061),26岁的苏轼写下《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年轻的苏轼将奔波不定的人生比作杳渺的旅途,把自己和弟弟比作“飞鸿”。2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当年的“飞鸿”如今离群索居,沦落成了“孤鸿”,词人咏物伤怀,无限落寞。
2.孤雁寄托了张炎的身世之感
南宋张炎的《解连环》专咏孤雁,寄予身世之感。张炎是贵族后裔,六世祖张俊是南宋初年著名将领,曾任枢密使,受封清河郡王,家世显赫。祖父张濡任浙西安抚司参议官时镇守独松关,因手下错斩元使,南宋灭亡后遭到元军报复,处以磔刑,家产籍没。29岁的张炎家道中落,贫难自给,晚年靠卖卜维持生计。他的词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和个人身世的飘零融合在一起。《解连环·孤雁》的上片写道: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孤雁“离群”“惊散”后,惆怅万端,顾影徘徊,寻找栖息之地的凄凉境遇和词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凄惨遭际是那样相似,在孤雁的身上,作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咏孤雁实际上也是在咏自己。
3.南渡中的朱敦儒自比为失群的旅雁
类似的还有南宋词人朱敦儒。建炎元年(1127)秋天,词人为躲避金兵南侵之乱,离开故乡洛阳南下逃难途中,仰望长空,失群的旅雁和孤云恰似仓皇避难的自己,词云: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碧山对晚汀州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朱敦儒《采桑子·彭浪矶》)
词人用旅雁意象寄托自己辞乡去国的伤时感乱之情。在《卜算子》中,他更是以南飞失群的孤雁比喻靖康之变中颠沛流离、孤苦无依的百姓们:
旅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鸥鹭苦难亲,矰缴忧相逼。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朱敦儒《卜算子》)
词人写孤雁也是写自己南渡过程中流离失所,饥渴辛苦的凄惨遭遇。
四、禽鸟意象是传情达意的信使和媒介
(一)禽鸟意象是男女之间传递相思之情的信使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
《汉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侠侍王母旁。(13)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77—1578页。
唐宋词中的青鸟成为男女之间传情达意的信使,如:
青鸟传心事,寄牛郎。(牛峤《女冠子》)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浣溪沙》)
因遣林间青鸟,为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许,窃香解佩,绸缪相顾不胜情。(曾布《水调歌头·排遍第二》)
几时待得,信传青鸟,桥通乌鹊。(秦观《水龙吟》)
似近日,曾教青鸟传佳耗。(晁补之《安公子·和次膺叔》)
红叶波深,彩楼天远,浪凭青鸟信音乖。(张孝祥《多丽》)
鸿雁也是情人间传递相思之情的信使,如:
雁书不到,蝶梦无凭,漫倚高楼。(晏几道《诉衷情》)
雁来书不到,人静重门悄。(李之仪《菩萨蛮》)
雁信绝,清宵梦又稀。(周邦彦《四园竹》)
漫写羊裙,等新雁来时系著。(姜夔《凄凉犯》)
(二)禽鸟意象是亲朋故旧之间沟通联系的媒介
雁足传书的典故源于苏武,《汉书》卷五四《苏建传》附《苏武传》:
昭帝即位。数年,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
自苏武雁足传书之后,鸿雁就成为了古代的邮差,它传递的不仅仅是情人的消息,还有朋友之间的惦念,如:
雁不到,书成谁语。(张元干《贺新郎》)
重倚阑干相忆处,寻过雁,作书邮。(洪适《江城子·赠举之》)
应难奈,故人天际,望彻淮山,相思无雁足。(史达祖《八归》)
也有亲人之间的牵挂,如:
假饶真个,雁书频寄,何似归来早。(程垓《孤雁儿》)
雁足无书孤夜色,音尘千里隔。(赵师侠《谒金门·常山道中》)
最凄惨的莫过于秦观,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秦观受苏轼牵连被贬郴州,郴州偏远荒僻,根本无雁可传书: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秦观《阮郎归》)
宋钦宗赵桓笔下的塞雁则是对故国家园的眷恋,塞雁意象在这里被赋予了家国情怀:
塞雁嗈嗈南去,高飞难寄音书。只应宗社已丘墟。愿有真人为主。(赵桓《西江月》)
南宋中兴名臣胡松年绍兴间出使金国作《石州词》,写尽了出使金国行役之苦和淹留之久:
愁绝。雁行点点云垂,木叶霏霏霜滑。正是荒城落日,空山残月。一尊谁念我,苦憔悴天涯、陡觉生华发。
五、禽鸟意象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
(一)寄托了古今兴亡之感
禽鸟意象是朝代兴亡,人事代谢的见证。
江南燕,轻飏绣帘风。二月池塘新社过,六朝宫殿旧巢空。颉颃恣西东。
王谢宅,曾入绮堂中。烟径掠花飞远远,晓窗惊梦语匆匆。偏占杏园红。
北宋词人王琪《望江南》表面上是咏燕,实际上是咏史怀古。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称欧阳修极爱此词。这首词化用了刘禹锡的怀古名篇《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句意。池塘上翩跹飞舞的燕子似乎是从六朝宫殿之上的旧巢飞来的,昔日的王谢堂前燕,如今在普通百姓家的绣帘之间随意穿行。六朝宫殿和王谢堂前的繁华鼎盛早已成为历史。朝代兴亡、人事代谢、沧海桑田,变化的是岁月和人事,不变的是燕子,依旧掠过烟霭纷纷的小径向远方飞去。词人将古今兴亡之感慨寄寓在对“江南燕”的细致描摹之中,含蓄蕴藉,余味深长。
无独有偶,周邦彦《西河·金陵》同样借“燕子不知何世”来表达古今兴亡之感:
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如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词中斜阳中的燕子呢喃对语,不是倾诉相互的情思、离别的伤悲和对故乡的眷恋,而是在“说兴亡”。
(二)蕴含了丰富的感情色彩
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同是一棵古松,千万人所见到的形象就有千万不同,所以每个形象都是每个人凭着人情创造出来的,每个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就是每个人所创造的艺术品,它有艺术品通常所具的个性,它能表现各个人的性分和情趣。”(14)宗懔:《荆楚岁时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9页。同样的禽鸟,在不同词人眼里感情色彩迥异。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赵佶《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在被金兵虏获沦为阶下囚的宋徽宗赵佶眼里,燕子是不谙人情的。在吴文英的梦中,燕子在为离别的情人黯然神伤。
门隔花深梦旧游,夕阳无语燕归愁。(吴文英《浣溪沙》)
同样是燕子,在没有经历过宦海风波的宋祁眼里,是活泼的、欢愉的、美好的。
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宋祁《锦缠道》)
燕语莺啼是美好春光的典型景象。
风帘燕舞莺啼柳。(牛峤《菩萨蛮》)
微雨小庭春寂寞,燕飞莺语隔帘栊。(张泌《浣溪沙》)
君前对舞春风,百叶桃花树红。红树,红树,燕语莺啼日暮。(王建《宫中调笑》)
巧莺喧翠管,娇燕语雕梁留客。(刘几《花发状元红慢》)
可是在婚姻不幸的朱淑真眼里,莺和燕却让女主人公愁肠百转。
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朱淑真《谒金门》)
在饱经离乱的朱敦儒眼里,燕语莺啼触动了词人的别离情绪,让词人心中充满悲戚。
别离情绪,奈一番好景,一番悲戚。燕语莺啼人乍远,还是他乡寒食。(朱敦儒《念奴娇》)
“这主要是由创作主体之性分、情感、思想、观念乃至经历、遭遇方面的特殊性所致。”(15)王兆鹏主编:《唐宋词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44页。北宋灭亡,中原沦陷,宋室南渡,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国破家亡的深悲剧痛使禽鸟意象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和象征意义变得更加深刻而深远,由北宋初年的相思离别、伤春悲秋、乡愁旅思等个体情绪的抒发与宣泄上升为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个人的身世之感融入了民族国家的兴衰与时代精神的变迁。
(三)适于抒发凄凉感伤的情怀
1.恋人间离别的哀歌
离别之时,鸟儿的啼鸣触动了词人的心弦,似乎在为难舍难分的恋人吟唱离别的哀歌。如: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李白《菩萨蛮》)。
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刘禹锡《浪淘沙》)
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叶梦得《贺新郎》)
何处今宵孤馆里,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曹组《青玉案》)
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愁敛双蛾。落花深处,啼鸟似逐离歌,粉檀珠泪和。(李珣《河传》)
2.贬谪移徙的悲吟
远去的飞鸟寄予了词人的贬谪之情。
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刘长卿《谪仙怨》)
刘长卿由随州刺史左迁睦州司马,于祖筵之上写下《谪仙怨》,抒发自己被贬的惆怅。
鹜落霜洲,雁横烟渚,分明画出秋色……想绣阁深沉,争知憔悴损,天涯行客。(柳永《倾杯》)
柳永擅长通过秋天景色的描绘抒发羁旅行役的悲吟,鹜鸟落在霜洲,雁阵排列在江渚之上,清冷的秋景烘托出天涯行客的离愁。
3.亲人间离别的悲伤

《本草纲目》记载:

杜鹃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春暮即鸣,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18)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年,第2117—2118页。
古人认为杜鹃是思归的怨鸟,又名催归,昼夜悲鸣,至血出乃止。最先听到杜鹃叫声的人就会离别,“杜鹃啼血”的传说让它成为典型的怨鸟恨鸟形象,变为凄楚哀怨的化身,特别适合抒写离恨。这首词写于绍熙五年(1194)至嘉泰二年(1202),辛弃疾谪居瓢泉期间。词中提到的茂嘉是辛弃疾的族弟,被贬到广西桂林。张惠言《词选》中说:“茂嘉盖以罪谪徙,故有是言。”(19)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这首词开篇便用三种禽鸟的悲鸣来营造离别的气氛,烘托词人离别的悲伤以及自己与族弟一腔报国热血却惨遭贬谪的悲愤,然后用《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的句意写人间离别,最后用“啼鸟”作结渲染离别的悲伤。
4.悲苦哀怨的典型意象——鹧鸪、杜鹃
鹧鸪、杜鹃都出现于暮春时节,且啼声悲切,常常用来抒写词人心中的悲苦哀怨之情。这种悲苦哀怨之情,情感来源非常丰富:
(1)源于亲人间的离别之苦,如辛弃疾《最高楼·送丁怀忠》:“苍梧云外湘妃泪,鼻亭山下鹧鸪吟。早归来,流水外,有知音。”
(2)源于游子思乡的孤独寂寞,如李珣《南乡子》:“烟漠漠,雨凄凄,岸花零落鹧鸪啼。远客扁舟临野渡,思乡处,潮退水平春色暮。”
(3)源于宦途羁旅的凄凉感伤,如赵鼎《贺圣朝·道中闻子规》:“征鞍南去天涯路,青山无数。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
(4)源于忧国伤时的忠义情怀,如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皂口壁》:“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5)源于科举失意之后的落寞苦痛,如秦观的《画堂春》: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元丰五年(1082)秦观二次赴京应试,又没有考中。这首《画堂春》就是他二次落第后所写,表面上抒发的是惜春怨春之恨,实际上表达的是科举失意之后的落寞与痛苦。落红满径,小雨霏霏,杜鹃的声声啼鸣在耳畔响起,似乎在提醒词人此时已是暮春时节,春已归去,无法挽留,又似乎在劝慰词人“不如归去”,远离这伤心之地。
(6)源于贬谪移徙的凄苦凄凉,如绍圣四年(1097)暮春秦观被贬徙郴州时写下的《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向潇湘去。
词人心中的痛苦愈发沉重,已经到了“砌成此恨无重数”的地步。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两句是典型的“有我之境”,贬谪之地本已凄寒冷寞,再加上黄昏时节杜鹃的声声哀鸣更让孤独落寞的词人倍增凄凉感伤,词人凄苦之心境在凄厉的氛围中愈发悲凉。王国维评价这两句:“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20)朱光潜:《朱光潜谈美·陶冶》,李松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0页。唐圭璋先生说这首词:“写羁旅,哀怨欲绝。起写旅途景色,已有归路茫茫之感。‘可堪’两句,景中见情,精深高妙。所处者‘孤馆’,所感者‘春寒’,所闻者‘鹃声’,所见者‘斜阳’,有一于此,已令人生愁,况并集一时乎!不言愁而愁自难堪矣。”(21)路成文:《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之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杜鹃啼血之声更增加了词人的孤寂悲伤,周紫芝甚至在他的绝笔中以杜鹃作结,“杜鹃只解怨残春,也不管、人烦恼。”(周紫芝《忆王孙·绝笔》)
可见,禽鸟意象适于抒发伤春悲春,羁旅思乡,故国之思,贬谪移徙等凄凉感伤的情怀。
结语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页。禽鸟意象在唐宋词中的广泛出现,显示了唐宋时期的词人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对自己所处的外部世界的关注。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每一个幼年民族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倾向,愿意用可见的、可感觉的形象,从象征起,到诗意形象为止,来表现他们的认识范围。”(23)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十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第59页。禽鸟作为大自然客观存在的物种,经历了漫长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已经由自然物象成为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意象,成为表现丰富文化意蕴的艺术符号,被词人们反复吟咏并固化成特定的表情达意的模式,体现了深婉旖旎的审美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