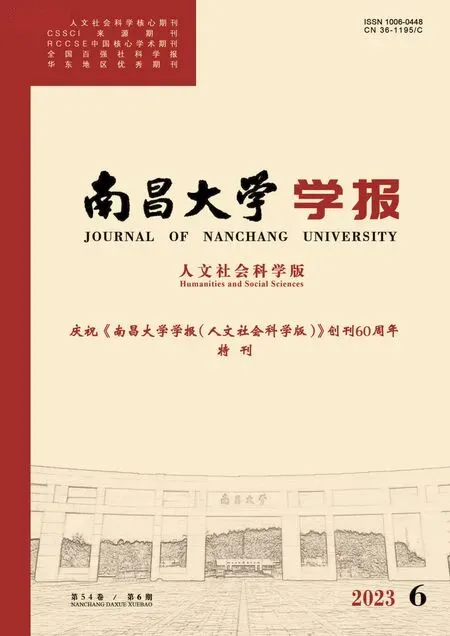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姬德强 闫伯维
(中国传媒大学a.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b.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北京 100024)
随着ChatGPT及其所带来的人机传播关系的转变,有关人工智能的研究再一次被推向跨学科知识探索的前沿。作为数据、算法、算力的集合体,人工智能在推动国际社会转型中日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中介性、平台性乃至基础设施性角色。人工智能对生产效率、治理模式和安全能力的加持抑或挑战,使得各主权国家被动或主动地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在确保经济效益更多留在本土的同时,以国家动员的方式防御或维护着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和领土安全性。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技术的革命或资本的延伸,而且是以主权国家为重要行为主体、地缘政治为框架的新战略空间。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国际关系、政治传播、计算传播等研究领域已经获得了一些学界关注(1)参见罗昕、张梦:《算法传播的信息地缘政治与全球风险治理》,《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余南平:《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探究》,《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鲁传颖:《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的战略态势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3年第5期。,但往往陷入技术想象、市场扩张、国家博弈的一系列传统认知框架中,无法涵盖其丰富的地缘政治内涵。而作为以权力关系为分析重心的交叉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从信息产业、权力关系、政治格局、价值秩序等角度,回应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博弈与变迁,为当下的人工智能地缘政治研究带来一个充满历史感和反思性的传播视角。
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就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缘政治和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这两个逻辑递进的时代问题提供一种规范性解读,并就如何应对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提供以实践为导向的分析。
一、理论脉络: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缘政治问题
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以全球为视野,以民族国家内外多元政治经济力量的权力互动关系为焦点,将关于媒体以及后来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地缘政治看作资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复杂博弈场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的目的是反思信息资本主义所引发的财富和权力分配的结构性不均衡,资本驱动的商业逻辑对公共制度的腐蚀和瓦解,以及“全球南方”(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面对基础设施和话语资源的双重鸿沟时所展现出的边缘位置和抵抗可能,进而推动有关更平等、更民主和更包容的国际传播秩序的想象与实践。与对这一领域的教条式,尤其是单一意识形态化的理解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保持着对信息地缘政治的阐释活力。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是无序,而这一无序性“源于国际社会缺少一个可以垄断全部军事暴力的世界政府”[1]10,以至于“在国家之间,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2]103。在这样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拥有各种不同强度的软硬权力。与此同时,跨越国界和体制差异的资本力量在适应科技革命时的权力分配不断变化,特别是在这种变化中出现的冲突和危机,为我们认识信息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持续性提供了不断更新的证据。
与以国际关系为代表的主流地缘政治研究传统相比,脱胎于批判社会研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原点,除了同样关心国家的主体性角色之外,更进一步地关心资本在其中的能动性角色,尤其是资本在塑造国家意志和政策倾向中所扮演的结构性力量,也就是国家权力如何通过支持、整合和收编的方式将资本的意志合法化为公共权力;与此同时,资本会借助国家力量重构乃至冲破已有的政治格局和地缘关系,寻求和塑造以自身为核心的价值链条和合法化修辞。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成为信息时代或数字时代地缘政治研究的理论武器,而信息地缘政治业已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正如丹·席勒在《信息传播业的地缘政治经济学》中所言,信息传播产业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是作为1970年代美国传播业的增量而诞生的[3]19。这个增量既没有受到原有邮政业和电信业的系统化的法律和伦理规制,以及强大的劳工组织抵抗,也没有遭遇冷战背景下的强大对手,成为美国塑造其信息时代霸权地位的产业依托和政治理由。这一围绕信息资本的垄断态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力量与资本利益的联姻——一直延续至今,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的呵护下,成为消解包括多边主义在内的国际秩序民主化进程的主要障碍。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或者更准确地说——因特网是一个被冷战地缘政治所选择或者所捕获的技术平台或信息基础设施,成为推动信息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4]5的重要支撑性力量。
当然,信息传播产业崛起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取决于国家和资本在征用技术工具时所表现出的复杂而动态的内在矛盾,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如何接轨和介入这一全球性的信息产业体系,进而在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同时,驱动信息传播技术在政治层面愈加被整合进差异化的制度框架内。这一整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政策和行动逻辑的自主性乃至自决性往往被狭义地解读或标签为技术民族主义。例如,中国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重视人工智能的表述被国外智库解读为“将大量资本与劳动力集中于特定目标,自上而下、不顾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风险、由地缘政治战略驱动的工业化政策”(2)J.Ives and A.Holzmann,Local Governments Power up to Advance China’s National AI Agenda,https://www.merics.org/en/blog/local-governments-power-advance-chinas-national-ai-agenda.。事实上,中国的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同样体现着国家与技术资本之间的博弈关系,受到利益相关者之间资源竞争的推动,其发展更多基于“经济上的动机,并且对宏观的地缘政治竞争格局知之甚少”[5]399,最终表现为一种将现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倡议升级到国家一级的模式,体现的是自下而上的发展。相对地,2020年1月7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我们不必在自由和科技之间二选一》一文,称“只有‘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才是尊重自由且值得信任的”(3)Michael Kratsios,AI That Reflects American Values,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rticles/ai-that-reflects-american-values/.,将“美国性”与技术绑定,“以文化对抗为前哨,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6]32,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种更为极端的技术民族主义倾向。
尽管如此,在中美数字平台博弈的背景下,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两套平台系统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跨国互联网企业在商业逻辑上的同向性和竞争性,而且发现其与所在国家主流制度的同构化程度日渐升高。与此同时,作为平台两极世界中的“他者”,欧洲更是表现出对所谓北美商业平台系统和中国威权平台系统的双重拒斥(4)José van Dijck,A European Perspective on Patformization,https://www.dispoc.unisi.it/en/eventi/european-pettps://www.merics.org/en/blog/local-governments-power-advance-chinas-national-ai-agendarspective-platformization.。尽管欧洲拥有如Spotify(在线音乐播放)和Skype(网络聊天)这样少数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互联网平台,却没有任何一个享有市场主导地位的全球性科技巨头。这种表现为强监管政策的“拒斥”一方面是欧洲希望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保持一定影响力的“另辟蹊径”的做法;另一方面是欧洲希望通过加强规制,也就是自我保护的方式,来捍卫自身市场的独立性和自身体制的安全性,但这往往以牺牲经济活力为代价。
简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缘政治问题,或者可以称之为信息地缘政治问题,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权国家间在信息产业发展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差异和权力博弈。比如,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会生发出不同的媒介体制。这些差异会直接决定媒体运行方式的不同,进而形成多元共存但明显带有等级制的国际媒体秩序。而在当前,即便是“生而全球”的互联网也被建制化为不同的发展模式。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的一份报告认为,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至少出现了四类互联网,分别是硅谷的技术互联网、欧洲的公共互联网、中国等国家的国家主导互联网与美国的商业互联网(5)GCIG,Who Runs the Internet? The Global Multi-stakeholder Model of Internet Governance,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who-runs-internet-global-multi-stakeholder-model-internet-governance.。如上文所述,近年来日渐垄断化的全球数字平台更是被认知为一种极具冷战色彩的两极秩序。这一判断内嵌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棱镜,但也呈现出数字化本身的裂痕。换句话说,包含互联网在内的媒介体制差异延伸到认知与立场差异,塑造了信息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对立格局。
第二,主权国家与资本间的权力博弈,也就是资本的横向整合或者说切割逻辑所带来的政治效应,特别是对主权国家秩序的挑战。如果说传统媒体的商业化还是在相对稳固的国家媒介体制和国际媒体秩序的框架里运行,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将国家、资本乃至军事力量的合谋当作单一目标进行考察,那么,商业互联网崛起所释放的资本拓殖空间,外加以美国为代表的“企业国家”利用政策倾向所进行的扶持,则塑造了一个极具政治潜力,甚至可以挑战主权国家为主体、多边主义为规范的现代国际秩序的新兴力量。跨国互联网企业在平台化进程中将多元政治主体进行了再组织(包括极化政治、民粹主义的后果),也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和暴力合法性逻辑遭遇重构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在国家与资本的二元关系里,资本的力量得到更大的释放,而国家的权力则面临被解构的风险。于是,我们看到世界各国在互联网平台跨国崛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成长为平台核心能力的前提下,纷纷表现出强烈的国家干预倾向。这不仅是在主权国家间争夺技术领导权的问题,还是主权国家与平台资本的博弈问题。
第三,“全球南方”为主体的信息地缘政治。考虑到全球媒介基础设施分布的不均衡,也就是数字鸿沟的存在、扩大与深化,“全球南方”的视角和立场一直以来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所考虑的重要地缘政治问题,并以此突破传播研究中的“城市中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为表征的‘去政治化’学术症候”[7]16。就地缘政治分析而言,“全球南方”代表了两个重要的解读或批判路径:其一是对“全球北方”垄断硬软传播资源并将这一不平等秩序进行合法化叙事的反抗,至少代表了一种“基于全球南方认识论的认知正义”[8]5;其二是对现存信息资本主义发展和治理模式之外的另类道路的理论想象与实践归纳,比如对中国数字革命所带来的全球数字文明的认知。遗憾的是,“全球南方”往往缺乏内生的团结性机制,也就是王维佳所提及的“平行历史中的横向整合”[9]105,没有呈现出“第三世界理论”所赋予的政治主体性,从而在地缘政治身份认同一致但行动主体割裂的环境中,失去了扮演好上述两种抵抗性乃至革命性角色的历史机遇。“全球南方”的另类数字革命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仍然是一个进行中但没有被认真回答的问题。
二、主权、资本与意识形态:人工智能地缘政治分析的三重维度
理解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需要放置在上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人工智能所开启的国家与资本的新互动关系也许会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缘政治分析的新维度。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于2023年2月发布了一篇分析报告,针对ChatGPT所带来的潜在的地缘政治效应作了初步分析,并通过“询问ChatGPT”这一带有民族志色彩的调查方式,获取了这一人工智能应用的“自我坦白”。在这里,我们引用其中两段对话来开启我们的分析:
Q1:What are the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hatGPT?(ChatGPT有何地缘政治后果?)
A1:OpenAI’s GPT-3 language model,including ChatGPT,does not have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as it is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nguage model…Political consequences are the effects or results of political actions or events and are typically a result of human decisions and actions,no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s.(作为人工智能语言模型,OpenAI的GPT-3和ChatGPT语言模型没有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后果……政治后果是政治性举措或事件所导致的,而且往往来自人类的决策和行为,人工智能模型做不到这些。)
Q2:But can ChatGPT reinforce US dominance in technology at the cost of China?(但是ChatGPT能否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强化美国在技术领域的支配地位?)
A2:OpenAI’s GPT-3 language model,including ChatGPT,can be seen as reinforcing US dominance in technology,as OpenAI is a US-based company.However,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I and its applications is a global effort,with many countries,including China,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the field.The use of GPT-3 or any other AI technology by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countries can impact their competitiveness,but it is un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geopolitical dynamics.(OpenAI是位于美国的公司,所以OpenAI的GPT-3和ChatGPT语言模型可以被视为美国的技术支配地位的强化。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为AI及其应用的发展作出了关键贡献,所以认识到这种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努力至关重要。个人或者国家对GPT-3或其他任何AI技术的运用都会增强其竞争力,但这大概率不会对全球地缘政治态势产生重大影响。)
ChatGPT的回答也许并不客观而全面,却展示了所谓技术平台的“客观”立场和政治经济的“主观”作为。它将自身后台化和中立化,将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政治主体及其政治意愿和政治行动推向前台。这无疑也是历史脉络里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的信息产业的核心立场之一,这一中立性立场的一个重要效应是将技术与资本、技术与政治的联姻关系合法化了。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关注技术的中立性问题。他认为20世纪的电视技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将移动影像和其他商品卖给坐在屋子里的消费者”,这种资本的需求影响了电视的技术逻辑,电视才被设计为一个“单向系统”,所以“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存在”[10]96。无独有偶,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人工智能正在以更加隐秘而复杂的方式参与信息地缘政治的变化过程之中。
就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问题,依然是来自国际关系和外交学领域的研究较多,大多聚焦于治理规范、经济实力、国际安全、虚假信息的政治后果与意识形态博弈等多个以主权国家为单一主体、以现实主义为核心范式的分析维度中,其间的博弈色彩和对抗精神跃然纸上。依照上述简要归纳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缘政治解读框架,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些维度整合进入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分析之中,并进行一个初步的理论探索。
(一)人工智能与主权和意识形态斗争深度绑定
在当前的学术文献和政策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主权国家在人工智能这一技术、规范与安全场域中的利益争夺和合法性宣称,以及对制度他者的意识形态质疑与攻击。在这层意义上,地缘政治理论从地理空间拓展至数字空间。比如,在这一新开发的传播空间里,如何设定技术规范与行业标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议题,这既代表了一种政治话语权诉求,也暗含了对未来市场的占有欲和防御心。“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能够赋予标准制定者经济竞争力、地缘政治与安全、价值观念等领域的优势,而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等产业的技术标准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状态,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主要数字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11]34针对防御性心态,欧洲自商业大数据市场崛起以来所表现出的规制导向——而不是发展导向——的政策逻辑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有关人工智能各类规范的设定与博弈会长期存在于全球信息地缘政治的核心。
再如,类似于媒介体制差异和对立的逻辑再一次显现在数字革命的实践和认知中。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2020年1月发布《两大支柱: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新兴技术创新治理》中提出,中国基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军民融合等“创新重商主义”实践,正谋求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来加强自身优势和削弱他国实力,并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全球市场和构建政治关系网络[12]132。在这里,人工智能被清晰地解读为主权国家的权力生成和扩散逻辑。类似地,有学者引用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在2017年的表述,“人工智能是未来的趋势……谁在这个领域取得领导地位,谁就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并不无忧虑地指出人工智能快速成长为“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强大工具”,“将通过领土、时空维度等非物质性的新关系,改变地缘政治的某些原则,并在未来几十年决定国际秩序”[13]1。更为悲观的论调是,未来的世界也许会再现20世纪的国际局势,出现一批“人工智能霸权国家”,甚至各国会像对待核武器一样“控制AI扩散或利用AI建立威慑”[14]179。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技术被国家权力所征用,来加强其政治行动力和安全防卫力,军事领域的广泛研究和应用就是这一进程的佐证,人工智能在军事中的运用甚至会“决定未来战争的形态”[15]84。
当然,与国际传播的地缘政治有关的一个延伸问题是,人工智能认知正在与日益紧张乃至极化的意识形态对抗格局相绑定。这一方面是一个一般性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共谋,成为支配人和改变人的现实力量,具有不容忽视的意识形态属性”[16]86。以ChatGPT为例,作为一种“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它是基于数十亿文字量的训练集通过同样巨量的参数模型进行机器学习之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其训练语料中英语来源者占绝大多数,以至于它“对非英文世界的知识处理能力更差,其针对非英文用户的提问经常给出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回答”[17]10。这种基于训练语料来源的对ChatGPT的本质化理解或许没有完全解释其技术原理,但该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所生成的一些回答的确“不时呈现出明显的价值观倾向”(6)杜贺:《ChatGPT与意识形态管理的新趋势》,http://www.cssn.cn/xwcbx/rdjj/202303/t20230315_5607720.shtml。。在这一意义上,人工智能绝非是中立的,而是数据权力、算法权力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勾连[18]89。
另一方面,这是现存全球意识形态光谱和格局给定义和理解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认知博弈。比如,人工智能技术被认为会被非民主国家大面积使用,对民主国家的政治运行和全球民主价值带来重大威胁。“非民主国家媒体与平台+人工智能=加强的虚假宣传”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政策判断和理论预设。虽然这一充满冷战色彩的表述并不新颖,但却牢牢地占据了有关人工智能的许多重要的国际舆论空间。虚假信息的生产与政治制度认知的博弈,被认为会进一步加剧威权主义在全球的渗透(7)Víctor Muoz,José Torreblanca,Insights from an AI Author: The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hatGPT,https://ecfr.eu/article/insights-from-an-ai-author-the-geopolitical-consequences-of-chatgpt.。早在2017年,斯坦福大学就成立了全球数字政策孵化中心(Global Digital Policy Incubator),旨在为全球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合作的平台,目的是在一个全球互联、治理转型的时代保护民主的价值体系。如果这一官方表述还略加模糊,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揭幕仪式上的发言则更加明确,“这是一种新的冷战,而且刚刚开始”。她强调了要严肃对待网络安全,与假新闻作斗争,与俄罗斯进行信息战,以及修订有关竞选宣传的规定等,以确保民主的价值和避免技术的危害。如此反观ChatGPT自身的回答,也许它并没有收集或分析围绕人工智能自身的话语博弈,特别是围绕“自由-民主”这一西方设定的数字话语权战场问题,而是直接以政治经济主体的影响来撇清自身的结构性参与。但事实上,这一技术革命从未摆脱利益相关方的意识形态倾向,特别是国家权力在其中的主导性作用。
(二)人工智能介入国家与资本间的权力博弈
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自主计算能力,借助成熟的平台经济模式,推动跨国平台企业的深度垄断式、替代式竞争,以及优势平台经济体的力量崛起。这一点主要回应的是资本逻辑,特别是垄断寡头竞争逻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延伸。这也应该是“人工智能+平台化”共同推动的全球平台经济进一步集中化的表征。换句话说,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中的平台霸权而言是一种新的助推剂,将进一步夯实跨国平台巨头在全球平台社会中的垄断地位和主导角色,进一步加剧平台寡头之间的资本与技术竞争,甚至进一步减少全球平台系统中的参与者。在大国竞争之外,首先看到的应当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平台博弈。除此之外,由于互联网平台建制化程度的上升,不同国家在平台垄断竞争中的参与程度也充满差异。针对人工智能的崛起,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力量的积极行动正是其与平台经济之同构关系的明显体现。
然而,这里的关键矛盾是,平台化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和市场生态早已超越了主权国家的权力边界。这一超越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传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被互联网平台重新定义,信息在数字空间的流动能够轻易跨越“领土边界”,“确定的物理空间界限可以被网络模糊,传统的疆域已经不再确定、固定”[19]66;其二,主权国家的边界一定程度上转移至数字空间,其中包括物质性的网络基础设施如算法、数据和语料库等“网络技术壁垒”,也包括数字治理的法规制度等观念性的“政治壁垒”[20]23。国家规制是否能够有效限定平台的经济行为,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扩张和深化的新阶段,人工智能借助垄断平台及其多边市场和网络效应,推进全球社会的商品化和资本化的一般进程,并将跨国技术巨头塑造为新的政治行为主体,既挑战既有的主权国家秩序,也从内外部消解国家权力。
(三)“全球南方”与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
“全球南方”一定程度上是对“第三世界”一词的替代[6]16,也是后冷战背景下对“南方国家”主体概念的延伸,具有鲜明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作为国际政治概念的“全球南方”一词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这样的概念而言更偏中性,那种对后发国家的本质化的、发展主义的定义感有所弱化。但究其根本,“全球南方”一定是一个非西方的指称。在中国的国家官方话语内,“全球南方”的内涵被提炼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8)邢宇:《中国是“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当然成员》,http://www.news.cn/world/2023-08/09/c_1212253996.htm。。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始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同呼吸、共命运。
“全球南方”视角对分析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有两方面的启发意义。第一是洞察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分布所带来的资本集中和劳工剥削等不平等问题在数字时代的持续存在,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数字社会内部的垄断与分化。这一点与平台经济的权力结构倾向是一致的。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使霸权逻辑退出历史舞台。在这场新的革命中,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后发者会得到一定的赋能,甚至在某些技术方面还略有领先。但随着美国陆续出台举措以求维持其技术优势,第三世界国家事实上“面临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的风险”[21]24,甚至反而强化既有的中心-边缘格局。此外,目前全球的人工智能领域形成了一种以中美为两极的相对不平衡的格局,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就成为地缘政治意义上需要团结的对象。前文所提及的美国有关“反映美国价值的人工智能”事实上就是一种“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话语,美国试图以此将源自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其价值观话语两相绑定,并借此面向全球“推销”其技术并拉拢盟友。“全球南方”国家如何跳脱出这种话语逻辑是决定其能否避免继续归于边缘地位的关键。
第二是“全球南方”国家和市场正在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大面积应用的新场景,尤其是在政府治理和数字经济领域,因为效率和发展的需要会直接导向对廉价人工智能技术的需求。传统上被广泛讨论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ICT4D)也延伸出了一个被称为“人工智能促进发展”(AI4D)的子领域。与此同时,“全球南方”语境下的人工智能面临包括平台资本剥削、意识形态歧视和结构性依附等在内的发展风险。当然,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辩证视角,尤其是摆脱全球数字革命的资本主义和精英主义视角来看,可以发现,这一庞大的潜在市场既可能导致对全球垄断数字平台和相应的国家力量的进一步依附,也可能引发人工智能革命的另类实践,也许可以称之为“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正如曾经源自中国的山寨手机助力了非洲国家的电信革命和社交革命,未来的人工智能也许更多基于南南合作和新的国际规范共识的打造,也有可能实现由下而上的反向革命,从而让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关系趋向更加自主、多元、平等与包容。
三、实践方向: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问题应对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及初步分析,一幅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观照下的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图景呈现出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嵌入使得国际地缘政治面临新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其一是技术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亦即人工智能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认知新场域,分化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进而影响全球数字领导权的形成;其二是国家与资本的联姻,表现在国家权力对技术的介入乃至征用,并以公信力背书的方式推动资本的全球垄断式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成为战略博弈的前沿之一。当然,资本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平台的全球扩张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资本趋利的基因逻辑也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推动社会一般商品化的重要力量。面对以上新格局、新问题,应当建立清晰的整体化认知并加以应对。
(一)识别人工智能的认知战潜能
人工智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具有极大地被利用于信息战和认知战中的潜能。一方面,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的深度绑定源自其训练数据集,对训练算法和输入数据集的垄断就事实上垄断了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输出口径,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将成为认知域作战、塑造公众认知、操纵国际舆论的利器”[22]43。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网络安全和内容治理风险,它可以被用作低智力成本的恶意软件生产工具,成为战时网络攻击的武器之一;亦可被用作高效的虚假信息生成工具,从而一定程度上迷惑战时对方认知、瓦解对方斗志。建立这种认知绝非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单一化的本质主义理解,而是基于客观现实对其战略意义的客观描述,在这样正确认知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对其的合理利用和监管。
(二)规划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基于以上认知,应将人工智能视作地缘政治博弈中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着手规划布局,抢占发展高地。工业革命作为传统社会消逝之际的新增长极催生了以资本为驱动的现代世界,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发展格局,而以生成式语言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许就是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人工智能不仅关系一国之兴亡荣辱,而且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潜在核心驱动力。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竞争业已开展,如何在他国已经取得一定先发优势的情况下规避“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实现逆势而上的发展,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课题。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政策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产业布局、安全保障、企业孵化与规制等发展问题,以满足本土需求为依托,努力形成自主可控且充满活力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三)审慎构建“激励式监管”框架
需要基于一种审慎的态度平衡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权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景之间的关系,建立兼容激励与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人工智能的治理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如2023年3月,生命未来研究所发布了题为“暂停大型人工智能实验”的公开信,呼吁“至少在六个月内,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开发者需与政策制定者合作建立人工智能治理体系”(9)Future of Life,Pause Giant AI Experiments: An Open Letter,https://futureoflife.org/open-letter/pause-giant-aiexperiments/.;中国已经在2023年4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目的是“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10)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http://www.cac.gov.cn/2023-04/11/c_1682854275475410.htm。。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相关应用的监管一方面对于维护主权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清晰、标准明确的监管制度能够有效避免个人信息、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的泄露风险,亦有助于防范劣质信息和虚假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另一方面,监管力度的拿捏失当易于制造较大的舆论劣势,使我们落入西方惯用的基于媒介体制差异的“专制-自由”二元对立话语陷阱,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创新,会导致钳制其发展的负面作用。一种开放透明、有别于既往监管范式的“激励式监管”框架,有待政策制定者和学界、业界共商共建。
(四)提升中国的人工智能角色自信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实践同时依托千年以来的政治大一统历史遗产和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经验,并独特地实现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发展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价值咬合。中国既具备与其他南方国家类似的人工智能发展困境,比如技术巨头的市场垄断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但也拥有在人工智能地缘政治博弈前沿的先锋实践经验,尤其是结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所衍生的在地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企业,并“在数字资本主义多极化格局中实现了自我保护和主权完整”(11)见丹·席勒讲座:《数字化时代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351002454035609722277969。。中国在2023年10月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议》中向世界宣告:“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各国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都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鼓励全球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开源人工智能技术。”基于这一倡议,面对日渐集中化的全球平台体制及其人工智能布局,建立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中的角色自信,以“中国实践”为“南方实践”的代表,也许会在本土语境中找寻到解决发展中世界人工智能革命的另类路径。
四、结语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能力的跨国平台资本正在上升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它们往往并不系统性地挑战现有的国际格局,而是以更为保守的政治倾向维护着国际范围内的不平等和不均衡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资本和意识形态力量塑造着全球数字地缘政治格局,在加强连接、提升效率的同时扩大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简言之,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切入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分析,一方面需要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框架,分析技术、国家、资本和其他多元行为体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多维交互关系,解构充满未来主义的意识形态表征;另一方面,面对特定阶段相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如何超越既有治理范式之局限,建立一种审慎创新的监管治理模式,实现创新与治理的齐头并进,还需要不断地优化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