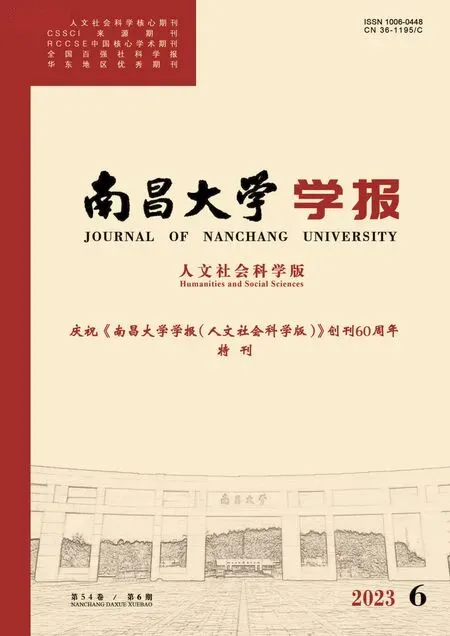文学的审美与道德关系论析
常 娟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003年,英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完成《理论之后》一书并获得出版。面对喧闹的文化理论,他略带嘲讽地批评:“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却属于传媒世界、购物中心、香闺密室和秦楼楚馆。”[1]5在《理论之后》这本书的开篇他断言“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1]3,并认为新的理论必须重新重视道德、价值和真理等命题,因为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和主题。有学者评价伊格尔顿“思考模式在本质上是伦理型的。他认为与认识论或世界观相比,伦理学更重要”[2]223。作为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将理论道路的重建之途回归到了伦理学的思考上。
实际上,不仅伊格尔顿,还有沃尔夫冈·韦尔施、玛莎·努斯鲍姆、韦恩·布斯、米歇尔·福柯等理论家也纷纷重新关注文学的伦理价值,由此形成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伦理转向。国内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以聂珍钊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推进了文学伦理研究的深化,出现了文学伦理批评、叙事伦理等热门研究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过于注重道德之于文学批评的实践运用而忽略了两者逻辑关联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3]243因此,回到问题的起点,对文学活动中的审美属性和道德功能的关系进行探究显得尤为必要。
一、审美与道德关系的历史溯源
在中西方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审美和道德关系的探究是一个基本理论命题。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溯源来看,自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已将文学与道德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孔子在《论语·为政篇第二》中评价《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为《诗经》从总的来说“思想纯正”[4]11。朱熹将“思无邪”直接解释为:“读三百篇诗,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故使人‘思无邪’也。”[5]539文学被儒学大家赋予了道德教化的重任:文学可以塑造个体的品德修养,由小及大,还可以建构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秩序。孔子在《论语·泰伯篇第八》中提出培养士子的路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81文学被置于教育的启蒙阶段,为塑造彬彬君子的品行修养树立了具体感性的榜样。魏晋时期,何晏在《论语集解》中认为:“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6]18到汉代,《诗大序》将《关雎》的诗意解读为“后妃之德也”,蕴含了规范家庭伦理和教化天下万民的深层用意。文中“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6]63的表述进一步开掘了诗的感染和教化作用。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文学不但建立起个体的道德意识和价值判断,而且从个体培养扩展到群体塑造,进而形成家国同构的宏观社会伦理秩序。这一观点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思想重视伦理、重视政教的内涵和特点。
儒学发展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周敦颐在《周敦颐集·文辞第二十八章》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7]46文被视为轮辕的装饰,道被比喻为车。周敦颐认为应当文道合一,既要有内在的道德充实,也要有外在的审美形式,只有二者合一才能传承久远。这一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核心的文论观点早已有之,先秦“诗言志”已蕴含了文以载道思想的萌芽。至唐代,柳宗元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8]873。从这一观点出发,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寄予厚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渴盼小说承担起挽救国家的重负。这一观念背后正是以文以载道思想作为支撑的。
综观中国传统的文学发展,儒家思想作为文化的主流占据文学思想的重要位置,使得中国的文学观念一直和道德教化密切地交织在一起,重视文学的道德功能和伦理引导作用,成为文学显著的价值功能。
这一状况在西方也有相似的表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已经从道德功能的角度来考量文学价值。他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指责诗人“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毁理性的部分”[9]84,诗歌助长了读者的“感伤癖”和“哀怜癖”[9]86。后世学者甚至据此得出柏拉图否定文学的结论。其实,柏拉图是根据理想国建设的需要驱逐一些诗人,但他欢迎有益于理想国建设的诗人及其作品,因为他们可以为保卫者设计好的教育模式,比如那些歌颂神明和赞扬好人的颂歌就被柏拉图允许进入理想国的城邦。可见,柏拉图是以是否有利于伦理秩序建构的标准来审视诗人和诗作的,他的文学观以道德功利主义为思想内核。
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也十分重视文艺的道德教育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种艺术和科学的研究都是在谋求某种善的目标。他在《修词学》中直接将美善同一化:“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10]84他在《诗学》中论述悲剧的审美效用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1]16。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效应(也即陶冶)与柏拉图考察文学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视野不同,亚里士多德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分析文学的道德价值。怜悯是由自身指向他人,恐惧是从他人投射到自身。借助情感的双向流动,戏剧演员与观众、局中人与局外人、叙事者与接受者等等的情感应和达到交融共鸣,从而在戏剧表演中完成集体的道德教育仪式。
对于文学道德价值的重视从古希腊开端,在后世的文论思想中不断获得回响。古罗马时期,贺拉斯指出诗歌具有娱乐和教益的双重功用,应当“寓教于乐,既劝喻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2]155。到中世纪,宗教力量强盛,许多欧洲诗人如约翰·高厄等,无不用诗歌进行道德的说教和宗教教义阐释,表达对道德丧失的愤怒[13]32。18世纪,康德对艺术和伦理的思考最终落脚于“美是道德的象征”的断语中。康德认为艺术“直接或间接地结合着道德诸观念”[14]173。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西方传统中都存在较为相似的文学道德主义观念。但是进入近代,西方的文学自律观逐渐抬头,黑格尔就已经开始质疑,“如果艺术的目的被狭窄化为教益”,“快感、娱乐、消遣就被看成本身无关重要的东西了”,艺术“就要附庸于教益”[15]63。这种对文学道德价值的质疑声音到了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兴起时越来越强大。
唯美主义大约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较大的创作规模和理论声势。法国作家戈蒂埃发出了唯美主义的宣言:“真正称得上美的东西只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体现了某种需要。”[16]44王尔德将这一艺术理论发扬光大:“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16]179在王尔德看来,文学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艺术的目的就是审美,并不为其他的目的——包括道德——而存在。他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批判他的论战对手:“他们总是用两种愚蠢的措辞——一种是这件艺术品完全不知所云;另一种则是这件艺术品极不道德。”[17]305
艺术家摒弃文学艺术的道德功能,淡化了艺术中的社会性和内容因素。他们将眼光聚焦到艺术形式上,这使得形式主义的文论观点逐渐走到理论的前台。如果说唯美主义是文学创作旗手吹响的号角,那么形式主义则是文学理论为艺术家铺垫的道路。形式主义者从语言研究入手,将各种非审美的因素都从文学的创作与阅读中剔除出去。他们认为真正的审美与政治、道德等各种社会性功能都没有关系。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艺术是永远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18]11形式主义文论从俄国开始,流布于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它反对文学的工具性,主张文学是一个独立的自足体,从而确立了审美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本体地位。
纵观中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对于文学的审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我们清晰地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文学的道德功利主义价值观和文学自律性的审美自由主义。正如西方有学者指出:“自柏拉图以来,艺术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艺术家、批评家和美学家中讨论最多的论题之一。事实上,我们能够区分出两种极端的见解:绝对的道德主义和唯美主义。”[19]212
二、审美与道德关系的逻辑考察
从词源学上来看,审美与道德两个概念在出现早期就存在紧密关联。东汉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美的注释是:“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20]78羊是人们的主要膳食。许慎借用口腹之欲的膳食满足来解说“美”,是从伦理学最基本的“善”的内涵来理解“美”,所以他直接得出结论:美与善同意。在西方,“美”的英文表达beauty是从拉丁文bellusy中演化出来的,这一拉丁语及其相近词汇bene、bouns等表达的都是幸福、善良、愉快等意思。由此可见,在人们的思维认知中,审美与道德本就是富有亲缘性关系的,二者具有相似性和统一性。
审美与道德作为人类重要的两种精神实践形式,两者的相似性首先表现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道德之善引导我们追求应然的生活,对现实的生活现象作出价值判断。如康德所说:“道德学说,真正说来,并不是关于如何使我们自己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我们何以配得上幸福的学说。”[21]165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活“是如何”的基础上进行“应当如何”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当我们或者向往或者鄙弃一个对象时,我们就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向着理想境界靠近。如果说道德之善是在日常的实践行动上引导我们达到理想的目标和境界,那么审美则是让我们静观实现理想的过程。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是同向而行的。如贺拉斯所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12]155审美在艺术的虚拟世界中呈现各种生活场景,塑造人物的命运和性格,让读者在美感愉悦中沉思,提升自身的伦理认识和道德水准,并最终作用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活动。
审美与道德追求的最终目标也具有相似性,二者经由不同的路径,最终都是通向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终极之地。道德通过限定个体自由的边界形成社会的伦理规约和法律条文,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也造就每个个体的最大自由空间。一方面,制度总是以其自身的方式强化人们的道德行为,使人们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形成道德心态和道德习惯[22]54;另一方面,个体在长期自我修炼中不断完善自身,塑造出完美人格,这种精神性人格的最高特质就是自由[23]134。审美是在理解力和想象力的和谐“游戏”中获得愉悦感,其中蕴含自由的创造。席勒说,“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想和意志的主动状态这一转变过程,只有通过审美自由这个中间状态才能实现”[24]181。席勒认识到审美将道德意识汇聚到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中,最终实现了主体对道德的体认,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审美与道德也融合为一。
审美和道德在实践效能上还具有交融性,从上文的阐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二者的紧密联系性。审美活动不仅使人们的审美能力获得提高,而且使人们的伦理认知和道德意识受到陶冶和熏染。卢梭说:“只要有热心和才能,就能养成一种审美的能力;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25]557
我们应当看到,在审美与道德具有亲缘性的同时,二者是彼此相互独立和疏离的,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思维特征和现实指向。
道德是依赖概念和信奉逻辑优先的;美的判断既不受概念和逻辑规则的制约,也不是通过推理得出的结果,它是建立在主体愉悦的个体体验基础上的。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事物或事件,伦理视角会给予明确的结论:它的性质是善还是恶,抑或从动机、成因、结果、影响等角度进行善的因素、恶的成分等等的分析。与伦理活动大不相同的是,审美活动对对象的观照是直觉性和整体性的。冷静的推理和逻辑分析不会助长审美效果,反而会破坏情感体验的愉悦度。审美一般是由对象引起主体的感官兴奋,由最初的快感进一步引发心理的情感反应,形成审美体验的心理愉悦。整个过程具有混沌整一性和不可言传感。
审美和道德除了思维特征上的差异性之外,它们对现实把握的方式也是有所区别的。道德伦理活动始终扎根于现实,直接探究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文学活动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虚构和想象活动。道德伦理活动的实践性在于伦理判断的主体是以现实中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为关注对象,判断的根据和标准是客观存在的事件真实,因此,首先需要的是尽可能呈现事件的真实面貌,然后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纳,最终作出伦理判断。伦理活动的整个过程应当避免主观臆断和先在偏见。审美活动并非如此,审美恰恰要求与现实维持一定的距离感;如果过于贴合现实,文学的艺术价值可能反而会受到损伤。审美不要求符合事物的客观存在,它希望诗人富有个性化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方式。这是具有主观性的真实,也是符合审美特征的真实。正是因为认可诗人的主观性在艺术创造中的合法地位,文学不仅不摒弃反而弘扬想象等在创作中的重要价值。黑格尔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15]357
此外,审美和道德在实践活动中关注现实的侧重点也是有差异的。文学活动中的作家和读者都是以个体生命体验的姿态进入文学的创作和欣赏中的,在文学活动中关注和体会各种各样生命存在情态的独特性,并在审美的过程中获得心理上的感染和满足,积淀出艺术的情感形式。在道德领域,伦理学家面对现实存在的复杂感性生活内容,从中抽象出相关要素,运用既成的群体伦理规约来进行价值判断。简而言之,审美表现出个体性、体验感和情感满足等要素特征,道德呈现为公共性、规约感和理性判断的特点。
审美是人的精神实践活动的情感体验,它追求的私人化、主观性与道德寻求的群体共识与社会规约等背道而驰。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前者是个体行为,后者是公共实践。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写作“尽管其材料可能是极其私人的,但却是真正‘道德的’行为,因为它暗示着某种反应的公共性”[26]41。在文学活动中,审美和道德的关系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状态:不但文学的审美性臻于完美,而且它具备高妙的德育效用。它们经常处于此起彼伏的不平衡状态,甚至二者可能走到极端的背离状态。二战时期,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的电影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影片具有宏大的秩序和充满力量的史诗性美感,但它却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作了渲染和鼓动,审美的价值反而助长了道德的败坏。在这样的情形下,审美和道德堕落为消极的结合。
三、文学的道德在场与超越
综合以上文学活动中的审美与道德关系的历史梳理和逻辑考察,我们认为就文学活动来说,审美可以视为文学的内在价值,道德可以视为文学的外在价值。审美价值是其自身具有的属性及其由此而生发的价值,是文学自身固有的;道德价值相对独立于文学之外,道德功能是在二者发生联系之后文学显现出的社会效用[27]33。一般而言,审美属性是文学呈现出的语言特点、风格、情感和形式感等因素,道德价值是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及其行动的正义美德抑或邪恶恶行而生成的道德内容和道德品格。
审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关系,呈现在文学活动的具体实践中,就表现出了文学的道德在场和超越的双重性:既具有私人化的写作和阅读状态,又生产出公共性的精神产品。就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活动而言,不论是作家的伏案写作还是读者的一卷在手,从外在形式上来看都是个体独立式的,这种个体独立式的精神体验暗示了人们摆脱公共性规范约束向自然本真状态回归的潜在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是天然地与道德规约的集体性特征相对立的。文学作品又是具有集体性的,人们可以交流、分享彼此的阅读经验,并产生共鸣或是争辩,这些行为又标识出文学的公共性。文学的私人化和公共性成为文学性质的二律背反特征。前者提供文学道德超越的可能性空间,后者喻示文学总体上是无法脱离道德在场的。
文学的道德在场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是对审美主体尤其是创作主体提出的要求。从文学创作的历史来看,早期的文学较为简单地追求道德功能的实现,道德要求压倒审美要求,创作者的道德在场是显性的;随着文学逐渐发展成熟,道德在场的状态逐步呈现出隐蔽化和丰富性的特点。
以小说为例。文本中能够直接显示作家道德在场和伦理立场的内容主要是叙述人语言,叙述人语言可以通过直接的评论、间接的语言风格和情境氛围的营造等方式来实现道德在场。中国古典小说多直接对人物行为进行褒贬指摘。如《醒世恒言》中的《三孝廉让产立高名》,故事开头便说道:“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楼中诸李,随你不和顺的弟兄,听说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28]13-14道德劝勉的意图显豁直白。小说发展到了成熟时期后,道德在场含蓄得多。如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小说结尾写到爱玛走投无路后服下了砒霜,躺在床上,身体备受毒药的折磨。忽然河边小路上一个盲者用沙哑的嗓音唱道:“暖洋洋天气放晴,大姑娘动了春心。”[29]297爱玛触了电一样坐了起来。“瞎子!”爱玛喊道,然后倒在床上,断了气[29]297。福楼拜用冷静的笔调隐匿了叙事的价值判断立场,但仔细品味,我们通过“瞎子”一语的双关,清晰地看到了爱玛临死前的醒悟和自嘲。现代小说叙事者则更进一步,将叙述声音客观化,采用非道德的价值中立观。如海明威的《杀人者》,讲述了一家小饭馆里两个杀手在等着一个名叫安德烈森的人,但安德烈森并没有出现,他们盘问了伙计和厨师之后离开;一个伙计去给安德烈森通风报信,但他却并不在意和吃惊。作品全文基本上只有人物语言,叙述人语言被大幅度弱化,暴力和凶杀的主题在作者笔下几乎没有任何情绪渲染和情感投入,他吝啬给予读者任何道德在场的信息。正如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说,现代作家应是客观的,他必须保持“中立性,公正,还有冷静”[30]74。
实际上,现代文学家宣称的反传统的道德价值中立或非道德立场,并不是摒弃道德价值判断,只是将道德判断隐蔽化了。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将道德判断的主动权移交到读者手中。文学的道德功能并未缺失,只要文学还无法割断与现实生活的纽带关系,它就不可能超然物外。退一步来看,即便是作家力求的非道德立场,实际上也是众多的道德立场之一。因此,文学的道德在场是必然的,只不过这种道德在场的表现或隐或显罢了。阿多诺说,文学应当精心制作,“正是通过这一点,而不是道德信条宣谕或取得某种道德效果,艺术才参与或分有德行,并将自身与更富人性的社会理想联系起来”[31]341。阿多诺期待作家将德行与艺术融合起来,从而使艺术成为精品和经典之作。
文学的道德在场的另一维度表现为文学的道德超越,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中,审美表现出对道德规约的超越并非罕见状况。哈代笔下的苔丝杀了欺辱和纠缠她的富家子弟亚历克。杀人是道德和法律不能允许的恶行,但是小说的副标题却给予女主人公赞美和怜悯——“一个纯洁的女人”。显然,文学的叙事伦理突破了现实社会的伦理边界,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讲述呈现出关怀个体生存境遇的道德观。
就道德自身来看,某时某地的道德规约往往具有有限性,在当时当地看是善的,但易时易地考察可能是恶的。这就是善恶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文学在面对道德的有限性时会形成对道德的超越,况且有时现实生活中的善恶是复杂的,往往并不能作简单的二元式的判断。这时,文学的伦理态度也会呈现一定的复杂性,与道德规约保持一定的距离,形成文学对道德的超越关系。文学作品中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往往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好人或是坏人,而是善恶兼有、好坏皆备于一身的人物。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少女时有着纯真和憧憬,嫁为人妇后心怀过隐秘的爱情。但这些美好的情愫终于都被断送,于是“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32]260。显然,对这一人物形象的评判已经不是简单地用道德的善或恶就能完成的。
不仅如此,文学还要把人物置于道德的困境中,令人物在道德的冲突中徘徊、挣扎,以此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正是文学艺术富有魅力之所在。在这种境况下,道德的规范律令在个体充满激情的生命体验面前已显得单调,文学艺术在对生命丰富性的体验中超越了道德的规约,呈现出生命存在的本色。小说发展到成熟时,文学的这一特征表现得越发明显,写作成为个体化隐秘情感的表达和宣泄,文学把受到道德规范压抑的欲望置于冲突和困境中表达,使得我们直面现实和人性,文学中的道德主题也更加个体化、生动化。它摆脱道德规范化的森冷面孔,使得人生和人性被还原成为具体鲜明的生活情境的悲欢离合,并让读者在感受人物的冲突、挣扎、抗争的诗意化情境中动情乃至体悟。例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鲁迅笔下的涓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等等一系列人物,都让我们在超越简单的道德指摘之后,获得对人性、人生和世界的更多样和更深刻的领悟。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生存方式,它的最终目的不是在论辩中达成统一的是非对错的道德判断,而是尽其所能地展示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人们在文学的无尽想象中返回现实来思考生存价值。因此,文学超越了具体的道德要求,以更高的终极关怀的立场来审视生活与现实。这就必然导致文学对现实的审视和反思,形成对现有社会道德观念的质疑和反抗。在更高层次上,文学的自我内在性质决定了它不仅需要把握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意识和道德观,而且需要在超越某一特定时代、地域的范围从人的存在的层面进行宏大视野的观照和洞察,从审美的立场上表达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层道德关注和人文的终极关怀。当文学的道德在场和超越获得统一时,审美与道德的关系会达成和谐和互补。
四、文学的诗性正义
思考审美与道德的关系可能还要面对这样的文学观点:文学对不道德的、恶的内容的呈现,借助情感、形象的感染作用,可能会在现实世界中引发人们的仿效,导致对现实生活的冲击和破坏。柏拉图呼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就是从维护人类道德、政治生活秩序的立场出发。他对文学创作中关于恶的写作和由此导致的可能性恶果充满警惕。鲍桑葵说,艺术中的想象世界像现实世界一样拥有通过榜样形成习惯的力量[33]28。似乎文学艺术展现了不道德的内容,就可能教唆现实世界中不道德的行为和观念的发生。这大约就是文学史上出现如下一些情况的由来:认定某些作品诲淫、诲盗,将某些作品列为禁书,试图隔断它们与读者之间的联系,甚至将写作者推上法庭受审,质疑作家的道德水准和写作动机。这些举动基本上都是基于对文学道德效果的警惕而发生的。
我们应当正视这样的问题:文学对现实的介入能力到底有多大?文学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魅力”,能够左右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道德风气,甚或成为罪恶的教唆犯?反过来说,是不是只要文学纯洁化了,社会环境就秩序井然了?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获得一定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希望借助文艺的纯洁性来完成社会道德的引领和教诲。由此,在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伦理定位边界往往清晰,某一类人物基本上呈现出统一的性格和面貌,易于分辨。如现代文学中的“地主”形象,刻画出的多是为富不仁、贪婪狡诈、无恶不作的恶霸形象,《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王贵与李香香》中的崔二爷等等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地主形象的性格平面化和道德批判性成为相对固定的文学想象模式。这种道德判断的基本模式在面对社会底层人物时,突出其苦难和受欺压的困境,往往不及其余。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方式固定化之后容易导致道德思维的逻辑固定化。我们同样可以假设,如果我们认定和同意文学对现实道德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在这样的文学无菌环境中可以生长出道德完善的人群,但现实的后果却并非如此,道德净化的热情并没有带来文学对人性的净化。“因为在至善论的背后,隐藏着至恶的反逻辑。”[34]127文学承载着整个社会道德建构的重任。
中国当代文坛先后出现了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等各个流派,余华、莫言、刘恒、刘震云、陈忠实和李锐等等作家在写作中表现出明显的叙事者的隐匿意图,审美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阐释的关键概念”[35]23。如果说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表现出的“道德批判色彩和政治化意味还非常浓厚”,那么在后先锋时代,“作家的道德立场宣示,普遍呈现出一种道德审判表象上的缺席和内敛的作品叙事风格”[36]99。这与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37]7的观点不谋而合。米兰·昆德拉说:“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37]7只不过这一道德审判的悬置做法,在中国语境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反抗性叙事姿态。当代作家用“密实流年”的文本景观,“凸显了生活的真实感,还原并尊重生活的复杂性和日常性,深入发微了生活的微观肌理”[38]151。从中国当代文坛的创作脉络中,我们可以窥见既有审美与道德的过度贴近状态,也有审美力求与道德保持距离的情形,审美与道德呈现了文学创作的真实丰富性,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中国当代文学在审美与道德的关系上来回摆荡,力图探索出审美与道德关系把握的恰当尺度。由此可见,在文学身上压载不可承受的道德之重可能会扭曲文学的本性,完全用道德尺度来诊断某时某地的文学状况显然是偏狭的。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的引领和建设是由多种力量、多种因素合力来完成的,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文学显然并不合适。就文学自身来说,道德效应并不构成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的思想力量也不是道德伦理这一种概念所能覆盖的。伦理因素只是文学叙事中的资源之一,它对文学的叙事资源而言并不具有优越性。正如克罗齐所说,审美意象本身在道德上是没有褒贬的,“如果我们说但丁的弗朗切斯卡是不道德的,莎士比亚的考迪利亚是道德的,那就无异于判定一个正方形是道德的,而一个三角形是不道德的”[39]176。实际上,文学提供的是深刻有趣而又内蕴道德的作品,它给予读者开放的审美语境,不断地让读者面对道德问题和矛盾,激发读者的道德探究和思考。如纳博科夫将自己的小说和故事设计成开放式的道德场景,建构虚构作品来引导读者意识到自己的道德立场[40]1-7。如此看来,那些要求文学移风易俗以促进社会道德发展,或是认为文学诲淫诲盗应当为社会的道德堕落负责的观点,往往只是站在一时一地的有限视角对文学道德效应的要求,未免局限。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提出,希望文学作品培养受众公正想象和理性情感的能力,“小说阅读往往不能给予我们有关社会正义的全部叙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桥梁——既通向正义图景也践行这一图景”[41]12。文学的超越性决定文学使命的宏大性,因为艺术家“必须把艺术本身——现在和将来都不是道德的——看作是一项要执行的使命,一个教士的职责”[39]177。这正是文学的诗性正义的使命。
五、结语
文学中的审美与道德关系问题是文学理论的永恒话题,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审美和道德差异性的同时,更应该观照的是二者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从历史和逻辑的十字坐标参照系中,我们既看到了文学自律性的审美价值,也关注到了文学他律性的道德功能。二者关系的适当分寸感表现在文学在其特殊的审美领域彰显其诗性正义。虽然有时道德的在场被作家刻意隐蔽起来,虽然有时作品呈现的道德观点与某时某地通行的道德规约相抵触,但是优秀的作家及其创作是在具体且富有独特性的人物和情节中,呈现出丰富的审美情感体验,表达出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这是文学的审美价值理性对道德的认知逻辑理性的有效补足,也是文学诗性正义的人文终极关怀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