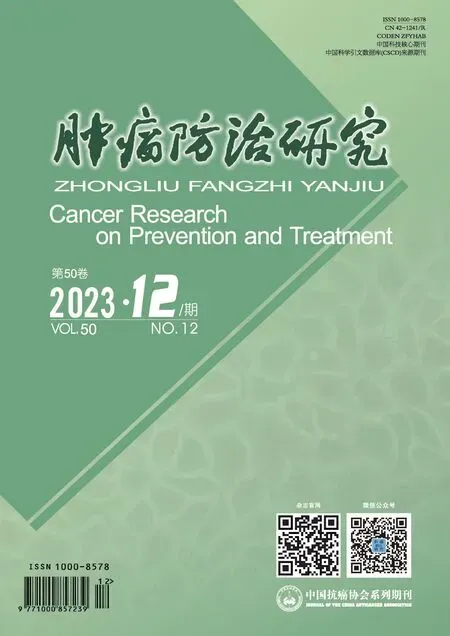泪腺腺样囊性癌临床诊疗中需关注的问题
马建民,任婷婷
0 引言
腺样囊性癌(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ACC)是一种相对少见的恶性肿瘤,在头颈颌面部主要起源于唾液腺,其次为泪腺[1]。泪腺腺样囊性癌(lacrimal gland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LGACC)是泪腺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上皮肿瘤,约占眼眶肿瘤的1.6%[2],具有复发率高、嗜神经生长和易远处转移等特点,其总体预后较差[2-5]。由于LGACC发病机制不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且尚无标准化的诊疗方案,目前关于LGACC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根据笔者所在团队的临床实践经验,对LGACC诊疗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加以述评,希望能够加强眼科医师对该病的认识,从而提高诊疗质量、改善患者预后。
1 关注流行病学和临床表现的特点
研究显示,泪腺肿瘤占所有眼眶占位性病变的6%~12%,上皮性肿瘤约占泪腺肿瘤的20%~45%,LGACC占所有泪腺上皮性肿瘤的25%~40%,是泪腺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上皮肿瘤[6-8]。LGACC的发病年龄具有双峰分布的特点,第一个峰值为平均年龄40岁的中年患者,第二个峰值为10~20岁的青少年患者[7]。提示LGACC不是成年人特有的疾病。笔者曾遇到过1例12岁的LGACC患者,因眼睑肿胀在当地误诊为泪腺炎症给予抗炎治疗,效果欠佳,我院最终活检证实为LGACC。关于LGACC的性别差异目前尚无定论,部分研究显示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有的研究则认为女性患者更多或者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9]。笔者对来自SEER数据库1999—2016年间诊断的118例LGACC进行统计分析,发现LGACC最常见的诊断年龄为40~69岁,中位年龄50~59岁,且男性居多,占所有病例的63.6%,左右眼发病率之比为1.03:1[10]。
LGACC通常为单眼发病,临床上早期主要表现为泪腺区肿块,由于局部占位效应可能导致眼球突出、眼球向下方和内下方移位、向外上方运动受限等症状[7]。其他临床表现还包括眶周自发疼痛或触痛、麻木、视力下降、上睑下垂、眼睑肿胀等[11]。疼痛是LGACC的相对特异性症状,通常提示LGACC呈侵袭性生长,由肿瘤细胞浸润破坏周围组织、骨壁或神经引起。值得注意的是,疼痛仅发生于部分LGACC患者,有些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则始终无疼痛表现。LGACC临床上常表现为眶缘外上方粘连性肿块,边界不清,触之不活动,这是与泪腺良性病变鉴别诊断的要点[12]。此外,由于发展迅速,LGACC患者的临床病史通常小于6个月[13]。且容易发生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其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为肺,其次是骨骼,其他常见部位包括肝脏和大脑[1,9],提示在随诊LGACC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眼眶外其他部位转移的可能性。
2 选择合适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CT检查对软组织分辨率较低,对肿物内部结构显示不如MRI,但可以清晰地显示骨质的改变。LGACC典型的CT表现为病变侧泪腺区形状不规则的高密度肿块,少数伴有点状或结节状钙化,增强后呈中高度强化;部分病灶强化不均匀,可见未强化的囊变坏死区[14-15]。病变常沿眶外侧壁呈匍匐状向眶尖部生长,早期即可越过眶中线,包绕并浸润邻近的眼外肌,病变累及邻近眶壁时多伴有虫蚀样骨质破坏、骨壁受压吸收、变薄或缺损等;进展期病变还可经眶上裂或眶顶向颅内、颞下窝、翼腭窝、鼻腔、鼻窦等结构蔓延,多为直接蔓延,也可沿神经出现跳跃转移,即在远处出现不与泪腺区病变相连的转移灶[15-17]。骨壁受累程度除与患者病程相关外,通常还与肿瘤的恶性程度相关,恶性程度越高,生长速度越快,邻近骨壁受累越严重,因此,CT可作为术前初步判断肿瘤恶性程度的影像学方法。
MRI检查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在显示肿瘤与周围组织关系或肿瘤颅内蔓延方面优于CT。LGACC的MRI表现缺乏特异性,与正常眼外肌相比,在T1WI上表现为低或等信号,在T2WI上呈等或高信号,多数信号不均匀,且增强后呈中到高度强化[15,18]。MRI能清晰地显示病变与眼外肌、视神经的关系,以及肿瘤向颅内蔓延的范围,对颅内、颞下窝、鼻窦等结构的显示较CT更可靠,是指导手术治疗、评估预后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建议将MRI和CT联合使用,从而及时正确地作出临床诊断,并为后续制定治疗方案、评估患者预后提供重要的影像学信息。
对恶性程度较高、影像表现侵袭性较强或者肿瘤复发的LGACC患者,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加做PET/CT评估患者的全身情况。PET/CT对于显示肿瘤性质、是否有远处转移以及病灶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3 重视病理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特点
3.1 病理组织学分型和分级
ACC肿瘤细胞呈基底细胞样外观,胞核深染,染色质浓,胞质稀少或透明[9]。典型的ACC病理组织学改变以腺上皮和肌上皮双向分化为特征,根据肿瘤细胞类型和排列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筛状型、管状型和实体型[9,19]。
根据Szanto等[20]提出的分级标准,可将ACC分为3级:Ⅰ级以管状型或筛状-管状混合型为主,无实性肿瘤区;Ⅱ级以筛状型为主,或含有实性肿瘤区比例<30%;Ⅲ级为实性肿瘤区比例>30%。
3.2 病理组织学与预后的关系
研究表明,实体型ACC预后最差,容易发生复发和远处转移,筛状型和管状型则预后较好[9,19]。Szanto等[20]提出实性肿瘤区比例越高,肿瘤越容易发生复发,预后越差。笔者曾对经病理组织学检测确诊的30例LGACC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和研究,显示病理组织学分型为筛状型9例(30.0%)、实体型10例(33.3%)、混合型11例(36.7%);病理组织学分级为Ⅰ级12例(40.0%)、Ⅱ级4例(13.3%)、Ⅲ级14例(46.7%)。研究发现LGACC病理组织学分型与骨质破坏发生率和复发率显著相关,其中实体型ACC较易复发;但病理学分型与神经侵犯和远处转移发生率无关。病理组织学分级与骨质破坏、神经侵犯、远处转移和复发率无显著相关性[21]。因此,明确ACC患者的病理组织学类型对判断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
3.3 ACC高级别转化的病理组织学特点
近年来,有文献报道ACC可以发生去分化或高级别转化(ACC with high grade transformation,ACC-HGT),表现为经典的ACC组织学背景下出现多形性的、有丝分裂活跃的低分化或未分化癌组织[19,22]。ACC-HGT中肿瘤细胞的细胞核明显增大、核仁明显、核膜不规则、核分裂相增多,可见局灶性粉刺坏死和促结缔组织增生基质,癌巢周围缺乏基底和肌上皮细胞[23-24]。ACC-HGT的局部侵袭性较经典ACC更强,颈部淋巴结转移率和远处转移率更高,预后更差[23-25]。笔者曾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病理科确诊的8例LGACC-HGT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4例(4只眼),女性4例(4只眼),中位年龄44.5岁,结果显示HGT区域占肿瘤显微镜下总面积的60%~90%,肿瘤细胞排列成实性片状,呈未分化癌或低分化癌形态,细胞异型性明显,细胞核显著增大,呈空泡状,染色质增粗,核仁及核分裂相易见。病理组织学显示神经浸润者8例(100%)、脉管侵犯者5例(62.5%);间质促纤维结缔组织增生者7例(87.5%)、坏死者6例(75%);4例伴有钙化[19]。基本与文献报道一致,LGACC-HGT病理组织学特征显著,生物学行为较差。
3.4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特点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ACC中的腺上皮细胞表达CK7和CD117强阳性;肌上皮细胞阳性表达p63、CK5/6、SMA、S-100和钙调蛋白[26-27]。p53和增殖指数Ki-67在经典的ACC肿瘤细胞中呈低表达[22]。而在ACC-HGT中,肌上皮分化丧失,表现为SMA、S-100、钙调蛋白和p63染色减弱或完全阴性[28],而CK7和CD117呈弥漫强阳性表达,显示出肌上皮免疫表型。由于高级别区域增殖率远高于低级别区域,Ki-67阳性率较ACC明显升高,高级别区域p53染色比例较ACC升高,HER-2和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 AR)在ACC中呈阴性表达[22]。c-KIT和SOX10是ACC的敏感标志物[29]。Ki-67的表达增加(≥30%)与较差的预后有关,是确定肿瘤分级和预后的有用辅助手段[30]。p53表达增加也可能是预后不良的独立指标[9,31]。此外,大多数ACC对MYB、Notch1受体、EpCAM、VEGF、HIF-1α、PSMA呈阳性表达[4,32-33]。GFRα-1和RET阳性与LGACC的周围神经浸润和复发相关[34]。RPS3高表达与ACC转移和不良预后相关[35]。RUNX1、SIX1、ME2也可在ACC组织中高表达[36-37]。
4 制定个性化合理的治疗方案
L G A C C 主要根据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分期手册第8版进行TNM分期[38]。临床工作中应重视患者的病史,详细记录肿瘤的大小,结合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TNM分期,这对后续选择治疗方案及判断患者预后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LGACC治疗方案的选择仍存争议,临床上主要采用手术切除联合术后局部放疗,主要治疗目的是实现肿瘤的局部控制和预防远处转移。此外,新辅助动脉内化疗及针对相关分子靶点的靶向治疗也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
4.1 手术治疗
4.1.1 眶内容剜除术和保留眼球的肿瘤切除术 手术是实现LGACC局部控制的主要手段,切除范围主要取决于局部受累情况。由于LGACC的总体预后较差,目前的经典术式为眶内容物剜除术,然而,研究显示根治性手术并不能提高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反而因为毁容和功能障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24,39]。近年来,保留眼球的局部肿瘤切除术治疗LGACC的应用逐渐增多,Esmaeli等[40]对7例LGACC行局部切除术联合同步放化疗,中位随访时间33个月,未见复发、转移和死亡。Han等[41]对10例LGACC行局部切除联合术后放疗,中位随访时间89.5个月,局部控制率为90%,总生存率为90%(1例死于与LGACC无关的食道癌),未见远处转移。笔者团队对35例LGACC行手术切除联合术后放疗,结果显示患者的5年和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5.8%和79.9%,放疗后5年无病生存率为52.7%[11]。尽管局部肿瘤切除术的总体效果良好,患者复发率较低,但并不能替代传统的眶内容剜除术,对于T1~T2期的肿瘤,可以选择局部切除,对于T3~T4期的肿瘤,保眼手术的复发率高于眶内容剜除术[2,24]。随着放疗技术以及化疗和靶向药物的发展,局部肿瘤切除的复发率逐渐降低,且由于LGACC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较为年轻,多数患者难以接受眶内容剜除术带来的术后不良外观。因此,对于T3和部分T4期的患者,如果能相对完整地切除肿瘤,避免视神经和眼外肌功能丧失,并且在患者能够接受术后高复发风险的情况下,也可采用局部肿瘤切除术。
4.1.2 术中是否常规切除眼眶骨壁 LGACC的局部侵袭性较强,易侵犯骨壁,根据影像学检查、术中所见和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对30例LGACC患者的骨质破坏情况进行统计,有18例(60%)存在不同程度的骨质破坏,因此,术中应仔细检查邻近眶骨并切除可疑病变部位[21]。对于切除病变骨的范围,部分学者认为应行骨切除术切除泪腺窝骨瓣,从而控制局部复发率,提高患者生存率[41]。而笔者认为,眼眶骨壁是阻止肿瘤向眶外以及颅内蔓延的天然屏障,过多的不恰当的骨切除术可能会造成复发后的眶周侵犯和(或)颅内侵犯。Rose等[39]报道了53例LGACC,其中9例行眶内容剜除术并切除局部眶骨,44例行局部肿瘤切除术联合放疗(未切除眶骨),结果显示两种治疗方式的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复发率和转移率均无显著差异。因此,笔者建议不对LGACC患者常规行骨切除术,对于伴有骨质破坏的晚期肿瘤,可先行放疗或化疗将肿瘤缩小后再行手术,术中应切除可见的肿瘤组织及周围一部分正常组织,检查邻近骨壁,对可疑病变骨质进行咬切和烧灼,手术后再行局部放疗。
4.1.3 手术时重视多学科联合治疗 对于颅眶沟通性或伴有远处转移的LGACC患者,应重视多学科联合治疗,联合神经外科、肿瘤内科、放射科、病理科、放疗科等科室对患者进行综合治疗,提高患者的诊疗质量。笔者报道了1例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肿瘤科的颅眶沟通复发性LGACC,患者曾因左眼LGACC行手术切除联合放疗,2年后又出现头痛和视力下降,眼眶MRI和CT显示左侧泪腺区恶性肿瘤,外直肌弥漫性增粗并邻近肌锥外异常强化信号,左侧眼眶外壁和蝶骨大翼骨质缺损,病变累及左侧海绵窦、圆孔、卵圆孔及翼腭窝,考虑肿瘤复发。患者于眼科与神经外科联合下行左眼眶颅沟通性肿物切除术,考虑到患者第一次手术后以70 Gy的放射剂量放疗35次,若再行放疗可能会伴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本次术后未行放疗而建议化疗,患者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为实性-管状混合型LGACC[42]。
4.2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是LGACC的重要治疗方式,包括内放射治疗和外放射治疗两种方式。内放射治疗以125I粒子植入为主,笔者对26例行手术切除联合125I植入术和9例行手术切除联合γ射线治疗的LGACC患者进行随访,结果显示其复发率分别为30.8%和33.3%,表明两种治疗方式均具有良好的局部控制率,治疗效果无显著差异,Kaplan-Meier曲线显示T1~T2期患者的预后优于T3~T4期患者[11]。近年来,碳离子放射治疗ACC的效果已在Ⅱ期临床试验中进行了评估[43]。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和血红蛋白值可能是接受碳离子放射治疗的患者治疗前风险分层的潜在指标[44]。混合中子-质子方法治疗晚期ACC的总生存率为93.1%,无进展生存率为79.3%[45]。动态轨迹放疗相比弧形调强放疗在不牺牲靶区剂量的前提下能更好地保护周围重要结构[46]。此外,68Ga-PSMA-PET/CT是检测ACC的一种成像方式,基于177Lu-EB-PSMA-617的PSMA放射性配体治疗在治疗复发性或转移性ACC方面具有潜力[47]。在应用放射治疗时,应关注其眼部毒性,包括干眼症、严重角结膜损伤、白内障、放射性视网膜病变、放射性视神经病变以及放射性脑坏死等。应注意预防和及时处理,在放疗过程中应注意放射剂量的把控,还可在放疗中和放疗后预防性给予患者改善微循环和营养神经的药物,以减少放疗相关并发症。
4.3 化疗
经动脉减瘤化疗(intra-arterial cytoreductive chemotherapy, IACC)作为一种新辅助化疗方式已被应用于晚期或进展性LGACC患者。据文献报道,术前IACC联合眶内容剜除术辅助术后放化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总生存率,减少病变复发[48]。此外,全反式维A酸联合低剂量阿帕替尼可能是复发性或转移性ACC的潜在治疗选择;伏立诺他或奥拉帕尼与标准化疗药物顺铂和阿霉素的联合治疗比单一疗法效果更显著[49-50]。值得注意的是,应用IACC联合静脉化疗时应考虑到药物的副作用,如顺铂的耳毒性和肾毒性、阿霉素的心脏毒性,需对患者进行密切的监护及随访。因此,笔者建议对于肿瘤较大、伴有严重骨质破坏、周围组织受累严重、有远处转移的T3~T4期患者,可以采用这种治疗方式。
4.4 靶向治疗
近年来,LGACC发病机制相关的潜在分子靶点不断被发现,相关靶向药物的研究为治疗晚期和转移性LGACC提供了可能性。MYB-NFIB融合对ACC具有高度特异性,被认为是基因组的标志,但针对MYB-NFIB融合的药理学研究仍然有限。Notch抑制剂AL101的疾病控制率为68%,其中15%的患者表现出部分缓解。表观遗传修饰在ACC的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SMARCA2、CREBBP和KDM6A等染色质重塑突变[51-52]。VEGFR抑制剂阿西替尼和PD-L1抑制剂阿维鲁布的疗效已在Ⅱ期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53]。其他治疗靶点包括B7-H4、PRMT5、RAR/RXR等[54-56]。笔者建立了LGACC患者来源的小鼠异种移植模型,并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贝伐单抗进行治疗,研究结果显示[57]治疗后肿瘤体积明显减小,VEGF、CD34和Ki67表达降低,p53水平上调,HIF1α水平下调,说明抗血管生成药物可能是LGACC的一种潜在治疗方式。
5 总结
综上所述,LGACC作为一种相对少见的恶性肿瘤,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困难,临床上应详细询问患者病史并结合相关影像学检查结果做出初步诊断,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是确诊LGACC的金标准。治疗应根据肿瘤的TNM分期、病理组织学分型、周围组织的受累程度等,为患者制定合理的个性化治疗方案,目前最常用的治疗方式为AJCC分期指导下的手术切除联合局部放射治疗,对于颅眶沟通性或伴有远处转移的患者,应采用多学科联合治疗。病理组织学类型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指标可作为判断患者预后的标志。此外,关于LGACC发病机制、相关分子治疗靶点以及更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开展仍是今后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