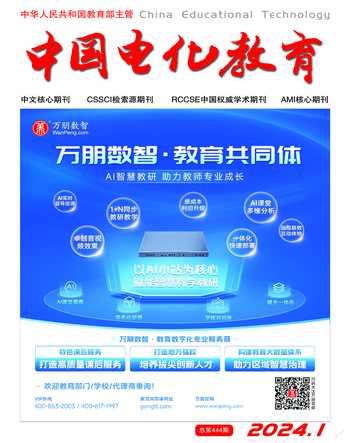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认知误区、潜在挑战与求解策略
傅敏 冉利敏
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数字技术驱动教育生态变革,从而发挥育人效果的过程。澄清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的“技术”误区,教育与数字技术关系的“和谐”误区,人与数字技术关系的“价值”误区,可以發现教育数字化转型本质上遵循了“取决于人,用之于人”的数据伦理。学校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校园围墙消弭,学校边界持续重建;课程模式颠覆,教学实践面临重组;教师角色转换,专业能力有待重构;学生能力弱化,学习生态亟需重塑等困境。学校需要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多元数字平台,加强教师系统培训,健全管理保障机制四种方式来全力打造智能校园,全面革新教学空间,全程提升教师素养,全速创建学习生态。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认知误区;求解策略;教育生态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与培育研究”(项目编号:17BMZ075)、西北师范大学2021年度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五育融合课程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1KYZZ01018)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冉利敏为本文通讯作者。
教育数字化是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当前,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正稳步推进,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教育数字化转型常常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宏大叙事”,难以深入落实到学校层面开展有效实践行动,学校在新旧模式的转换中无法准确找到平衡点,忽略了课程、教学、教师、学生等方面所潜藏的挑战。本研究从实践视角剖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认知误区、潜在挑战与求解策略,批判性地回答学校教育数字化“转什么”“如何转”的问题。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认知误区
澄清认知误区是破解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难题的前提。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在数字化环境中最大化建立人、技术、教育实践之间的整体平衡与和谐关系,推动教育模式与业态创新[1]。因此,误区澄清需要从解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厘清教育与数字技术之间、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的“技术”误区
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之前,首先应该厘清“什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问题。当前一些观点认为教育数字化是在教育场域中介入并应用数字技术,提升教育的数字化水平便实现了转型。这种观点将教育数字化转型窄化为支持数字设备的智能升级、技术软件的应用以及数字平台的建设,呈现出单一的技术驱动,模糊了构建智慧教育的转型目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于教育,而非技术。从宏观层面上讲,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教育要素深度融合,推动教育变革创新的过程[2];从微观层面上讲,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向基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信息技术数字化教学方式转变,以实现高效、便捷、可重复性高的教育服务[3]。询证而论,数字技术并非现代教育的工具与“边缘参与者”,而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点和基本驱动力,不仅能为教育教学赋能信息构建技术和自动决策技术等,还发挥着创新驱动教育变革的功能。
在学校实践视角下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应用到学校教育中,通过发挥数字技术的储存、推理、预测、评估和决策等功能,整体优化学校的课程模式、教学路径、管理体系等多维度的过程,旨在以“人机融合”推进高质高效的教育教学实践,构建支撑教师与学生更高层次生命成长的学校教育新生态。由此可见,教育数字化转型绝不是传统教育与数字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全方位参与来实现学校教育的深刻变革,是一项涉及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管理等全方面转变的系统工程。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需要经历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转型三个阶段,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教育循序渐进地开展全面、系统重塑的过程。在推动教育数字化的过程中,数字技术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全面渗透到教育的观念更迭、模式构建和教学实践中,通过顺应教育的发展规律,持续性地推动教育整体变革,真正发挥数字技术赋能创新教育的功效。
(二)数字技术与人关系的“价值”误区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渗透,教育工作者极易陷入“唯技术论”的陷阱,认为教育领域中的数字化本身是“有价值”的,数字化教育的结果总是趋于向善的。在“价值”误区中,教育的真正主体——人类面临着被边缘化甚至消除的危险,由此延伸出了“智能虚拟空间可以取代实体学校”“算法机器可以取代教师”“智能算法程序可以取代人脑”等错误观念。在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下,教育工作者逐渐忘却了本应承担的育人职责,盲目地将实现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作为现阶段教育目标,将技术理性提至高位,却忽视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要义是育人这一事实。在学校新型课堂建设中,也存在着“只见技术智能,不见人之发展”的发展倒置现象[4]。通过对数字技术进行祛魅,可以发现数字技术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也不能促进纯粹的价值创造过程,它只有在发挥育人效果、提升人类素养的时候才被赋予价值,其产生的终极价值体现在育人效果之上。
如果我们想要保持社会的人类特征,有一些工作就不能被完全自动化,包括教育[5]。在教育自动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人的介入与干预,因此数字技术驱动的教育自动化系统具有“主观性包容”,包含并非同化人的自主性、社会性和自我意识等。数字技术作为“人类大脑的延伸”,在学校教育中扮演教学活动、行政管理、教育决策的辅助者,旨在最终实现技术与生命的耦合。归根结底,教育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实现变革,最终以人的发展为归宿。
(三)教育与数字技术关系的“和谐”误区
与其他领域相比,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融合之路较为坎坷。论及教育与数字的关系,教育工作者常常将数字技术泛化为工具,认为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整合是没有冲突,在教育中应用数字技术就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全面育人效果,不自觉地走入“和谐性”的认知误区。虽然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和便捷性都不言而喻,但它并不是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在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整合中需要思考教育工作者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与适应度,数字技术在不同教学情景中的适切性,以及对学生学习的适用性等因素,盲目地使用数字技术可能会适得其反。教育与数字技术必然是存在冲突的,必然要在漫长的磨合期中经历“阵痛”才能最终走向和谐。
从教育与数字技术的整合过程来看,两者以人作为中介架构出双向融合的路径,数字化赋能教育的逻辑本质上遵循了“取决于人,用之于人”的数据伦理。数字技术通过运行算法程序开展数据收集、数据聚合与数据分析,自动化生成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以人工智能催生教育新生态。从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的过程来看,智能学习系统的“数据聚合”逻辑存在着“数据分析的方向性”这一问题[6]。数字算法机器通过特定的、编码的操作规则来运行,将操作者导向相对固定的、由其编码语言影响的特定方向,同时受数据收集数量与质量的影响,始终带着数据分析的方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价值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需要按照目标要求来开发、设置数字算法程序,在数字技术作用于教育的过程中,人还需要选择合适的数据组合,不断试错与调整数字化的程度、偏重与方向,使其产生预设的育人意义与效果。在这种意义下,教育数字化兼具人文关怀与技术创新双重属性,人工智能等产品通过运行算法来模拟人类智慧创新教育环境,开展教育互动,发挥育人作用。
二、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潜在挑战
数字技术赋能、增效、重塑教育的同时,也对原来的学校教育模式产生了一系列的破坏性。当前学校教育面临着校园边界消弭、课程模式颠覆、教师角色转换、学生能力抽离的困境,隐藏着重建学校空间、重组教学实践、重构专业能力和重塑学习生态的挑战。
(一)校园边界消弭,学校空间持续重建
工厂学校模式过度重视正式课程与正规学习的中心地位,无意中传播了“学习在离开学校的瞬间就戛然而止”的观念,成为了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的阻力。数字时代学校的物理围墙轰然倒塌,成为了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从农业时期的生活校园,到工业时代的围墙校园,再到信息时代、数智时代的全球校园,学校教育经历了“无围墙—有围墙—无围墙”的转变过程。但首尾的“无围墙”教育并不相同,前者是无边界无序的生活教育状态,后者是经过严格规范的知识分类与功能界定后所形成的以学校为中心向外无限扩展的学校教育状态。从“无围墙”向“无围墙”的转变使教育活动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回归教育原点。
一直以来,学校在教育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彻底失去了对知识教育的垄断。在这种窘境之下,部分学校教育工作者陷入了“实体学校正在走向消亡”的担忧之中。这种擔忧并非毫无依据,自信息化浪潮携带着互联网涌入校园之日起,学校的围墙已然开始瓦解。尤其到了数字化时代,传统学校教育中的时空界限被彻底打破,学校的部分教育功能被分化,公信力被削弱。例如,图书馆的知识储备功能被电子书籍部分替代,教室的集体教学功能被线上会议室所分散。受虚拟的网络文化影响,实体学校育人空间对学生学习活动的可控性变弱,对公认标准化的学业水平和教学质量提出了挑战。然而,校园围墙的倒塌并非意味着建立虚拟学校的可行性,实体学校为学生提供了面对面社交和情感交流的机会,这是在虚拟数字校园空间中无法实现的,由此可见,实体学校仍然是,也将永远是学生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场所[7]。
为了应对所谓的面对面教育特权化的挑战,有学者提出“有界空间、网络空间和流动空间”[8]的概念。有界空间强调了学校环境中的物理限制,信息技术主导的在线教育使得网络空间被学校接受并合理运用,数字技术则主导流动空间——一个边界和网络节点不断变化的地方,超越了有界空间和网络空间的二分法。流动空间以教育相关的可读数字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依赖于将教育空间配置为全传感、可编程的环境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数字技术巧妙地将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紧密连接在一起,两者互补与合作,跨越学校教育的距离概念和时间范围。从本质上分析,校园的数字化转型是对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传承与超越。校园从有着物理围墙的校园转向互联网辅助的网络校园,到如今,正在向实体与虚拟并存且界限模糊的数字校园逐步迈进,这时的学校成为了一个开放型办公室。学校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拥有一个从物质延伸到数字的全球校园意味着什么,如何在流动空间中持续重构学校校园的边界,重塑数字时代的学校教育生态成为当代学校的重要挑战之一。
(二)课程模式颠覆,教学实践面临重组
数字化学校教育彻底颠覆了“一支粉笔、一个讲台、一把戒尺”“师教生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将课程教学变成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模式。在互联网介入学校课程教学之前,课程教学主要围绕教室这一物理空间开展,在课堂中以师生的面对面授课形式来开展教学。这种“教室”课程是大规模的学科教师班级授课形式,采取同一种教学方法将所有的学生都看作“一个人”去教授。数字化课程则打破了这种格式化的、固定化的课程模式,个性化定制的课程和全景式情景感知的教学让学生可以以不同的节奏去掌握学习内容,实现对学生个体的具体关照,有效避免了“后进生消化不了、优生吃不饱”的窘境。数字化转型后的学校课程从原来的“千人一课”逐渐转变成“千人千课”,从面向所有人的课程转变成了面向每个人的课程。
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新型教学预示着学校课程教学的变革与重生。当今的学校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是通过代码编写的软件程序进行的,并依赖于算法来实现其功能[9]。考试成绩、上课出勤记录、身心检查报告,甚至在线课程的点击情况都被转化成数据插入到算法程序中,根据每个学生独特的数据配置文件制作出个性化学习课程。数字化为课程教学提供了一个省时省力的“机器人教师”,它不仅可以自动评估作业、题目答案等,提供即时反馈和个性化学术建议,还可以科学分析学习数据,挖掘隐藏的课程学习模式和趋势,通过预测功能不断完善个性化课程与教学服务。此外,人工智能系统依托多模态传感器搜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状态,帮助教师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沟通策略的最佳呈现。在此情境之下,预先设定课程的观念正在被颠覆,课程的概念愈发倾向于“跑的过程”,而非预先规定好的“跑道”。这里需要注意,个性化课程教学模式并不是对预设学习成果的颠覆,而是对生成性、个别化培养目标的强调,也是对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落地。
在数字算法机器的影响下,课程教学开启了从同质化的“教室”模式向个性化的数字模式艰难转型的道路。从原来的课堂集中授课到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场景化微课学习,学生在个性化学习中所获取的碎片化课程难以系统构建,与此相对应的个性化课程评价难以开展。教学活动所发生的环境变成了虚实结合,在这样的教学空间中如何处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如何保证学生主体的在场,都成为了当代数字教育背景下创新课程教学模式的关键问题。教育的数字化形式不是由提高生产力或取代教师的欲望所驱动的,而是由创造知识和存在方式的教学探索驱动的[10]。如何平衡学校课程传统的集中式、标准化“教室”课程教学模式与数字场景化、个性化数字课程教学模式,重组课程教学实践成为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一大挑战。
(三)教师角色转变,专业能力有待重构
人工智能与教师智慧相互交融,共生共长。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技术的高级形态,重新定义了教师的时代角色,赋能教师专注于情感性育人任务,坚守立德树人的教学初心。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教师完成一些机械重复的劳动,主要表现为在线课堂管理,包括课程注册和学生出勤;智能学习资源组织,包括学生签到和任务分配;选择题、读写等多项简单测试的自动评分。这些帮助教师卸下教师的行政负担,让他们专注于与学生的面对面教学工作,完善学生的行为数据库中关于情感等难以量化的部分以及难以观测到的指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通过对人类信息建構能力的功能外化,能够辅助教师完成学生的学习数据搜集、处理与分析的工作,并通过建构学情“画像”与定制个性化方案为教师提供合理的教育决策参考。人工智能承担了知识信息库的职能,慕课等在线平台的海量学习资源与远程教育模式使教师不必再花费大量精力成为“百科全书”,而是与学生共同探索与建构课程的意义。此外,人工智能教育类产品与专业平台可以发挥知识传授与答疑解惑的教学功能,承担了教师传统的“授业”“解惑”角色。反观教师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预测与评估功能对课程开展反思与改进,更加关注自身的教育经验与教学智慧的积累,回归教学初心。整体来看,人工智能让教学过程更加高效、富有魅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教师的职业倦怠感,从根本上达到减负的效果,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然而,随着第四次教育革命的到来,很多预言表示教师职业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消失。算法文化的一味发展似乎创造着实现自动化教育的可能性,也就是创造出“没血没肉的教育者”。数字技术驱动的人工智能不仅“博学”,而且擅长教学,让教师面临着失去学科地位和教学地位的双重困境。尤其随着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教师不再作为官方政策与课程标准在教学中的唯一落地实践者,以及法定知识的权威拥有者。学生超前学习与拓展学习的渠道增加,学生很有可能掌握教师未涉及的知识领域,取代教师获得知识发言权。在旧的教育体制中,公众对教师形成的刻板印象是权威知识的拥有者,一旦当教师开始频繁表达自己“不知道”时,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坏教师的威信,失去了对学生的“控制权”。
面对人工智能在教学过程中的广泛整合,教师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部分教师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对自动化系统呈现完全的主观性包容。他们一方面感谢人工智能辅助自己圆满完成了重复无聊的工作,另一方面依靠人工智能的“机器理性”开展评分、考勤等互动工作,凭恃机器的科学性判断与决策来规避个人情感的负面影响。还有部分教师则对人工智能持有消极、抵触的态度,具体表现为信心不足,认为人工智能不仅挤压了他们的专业空间,取代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且改变了他们熟悉的工作领域,对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此产生了更严重的职业倦怠。事实上,数智时代的教育不可能剔除人类教师这一角色,由于教育的人类交往属性,再智能的教育软件也不能取代人类教师的角色。但是,人工智能在较大程度上会改变教师的工作形式,促使教师行业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虚拟教育空间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教师不再需要亲临现场开展教学,相反,数字技术让教师的教学角色变得更加重要,在与学生的面对面课堂互动中承担了更核心的情感教学任务。在教育环境中纳入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要求准确把握教师的时代角色,如何实现教师在数字环境中的专业发展成为了难题。
(四)学生能力弱化,学习生态亟需重塑
工业4.0颠覆性地改变了教学的方式和场域,也将学习模式带入更加个性化、超高智能化、便携化、全球化和虚拟化阶段[11]。首先,人工智能将个体的信息搜索与建构能力有效整合在一起,将相应能力整体化、均等化,实现了普泛化的驯化[12]。从古至今,关于空间的挑战似乎意味着只有少数经济富足、意识强烈的人才能享受跨越距离“旅行”的权利。数字技术则轻松打破了这种阶级差异,为每位学生提供了超越时间的平等学习的机会。其次,大数据对于支持个性化学习和适应性教学具有独特优势[13]。数字技术驱动的自适应学习系统逐渐成型,终将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节奏与兴趣进行深度学习。数字算法与自动化程序运作让信息获取变得简单,语音识别、视觉模拟、专家系统、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让信息处理也变得快速又准确,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由面部情绪识别、自动难度适应和隐身评估等多项技术组成的人工智能集成管理系统,从学习表现、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认知负荷等多个方面搜集学生的学习特征,通过构建学习数据框架以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评估学生的学习水平,预测学生的学习趋向,从而分配自适应学习任务。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不断渗透与学习空间的不断拓展,对学生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挑战。数字素养不足的学生在数字适应能力与自我管理能力方面都表现较差,过度依赖于人工智能的大容量储存与自动化运行程序。他们开始习惯于不依靠脑袋储存、思考很多内容,而是以算法程序的自动化替代自身的知识建构过程,以AI的自动输出作为学习的结果,产生以花最少的精力达到最终学习效果的功利思想。在数字化浪潮中,学生成为了游刃有余的弄潮儿,浸泡在知识的海洋中,却丧失了扬帆起航甚至遨游的意识和能力。可见,人工智能对学生信息建构等能力的功能外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对非逻辑的直觉建构等能力的抽离。人工智能对知识与决策的直接呈现,在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导致机器理性占据上风,很大程度上使学生在思维上产生惰性,弱化学生的一部分思维能力。
另一方面,数字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去社会化、去情景化的方式构建自适应学习系统。人工智能技术使用包含人类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的结构来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通过问答的方式与学生实现人机互动。在人机对话中,个体学习者与学习内容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互动,学生以脱离社会性的自我个体身份出现,可以独立于课堂、家庭或社区中所隐含的社会性空间之外。在虚拟的数字学习空间中,教育的社会化功能被严重削弱,将学生强行植入设定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之中,弱化了学生自主进行社会交互的意识和能力,影响学生社会情感的生发。学生与没有灵魂的人工智能机器长期交互,会导致社交能力丧失、价值观淡化。此外,人工智能本身没有道德意识与社会情感,即使在数字技术中的算法文化中植入所谓正确的价值观,这方面内容也难以外显为数据以供算法分析与判断,无法保障人工智能可以圆满地完成任务。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支持驱动的数字环境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习思维和学习方式来改变学习体验和结果,学校则需要通过促进学习者与学习环境的共同进化来搭建“学习生态圈”[14],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有效建设智能学习生态,合理利用人工智能软件、平台等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成为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求解策略
为了摆脱数字技术对教育的单一控制,规避人在数字教育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学校应该把握教育变革机遇,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多元数字平台、优化教师系统培训和健全管理保障机制四种方式,全员、全力、全面、全程、全速推动学校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催生学校智慧教育新生態。
(一)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全力打造智能校园
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学习共同体,建设智能化现代化学校环境,打造学生中心的智能校园是实现学校教育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15]。为了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学校首先需要消除教育中的数字霸权,缩小数字鸿沟,确保为每位学生提供平等的技术资源、信息获取渠道和教育机会,通过完善内涉的数字基础设施来创建校园智慧教育生态。学校中宽带网络全面覆盖、智能设备增加、多功能场馆建设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推进智能校园建设的必要内容,也是增加智慧教育中主动性和参与性教学内容的基本要素。教育依赖数字技术开展算法运行的过程,依赖大量关于学生及课程教学活动的“机器可读数字数据”。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有助于开展学生数据的大规模搜集、结构化整合与智能化分析工作,能为开发新教学系统、完善已有智能辅助系统提供数据支持与参考,优化数字教育的育人效果。
首先,学校要主动寻求当地政府与社会公益机构的帮助,持续建设与加强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备。在硬件方面,智能眼镜、可穿戴设备、移动平板、VR眼镜等硬件设备可以进一步简化学习平台中数据的收集、整合、支持和分析。在软件方面,学校尽可能地筛选和完善智能辅导系统和自适应学习系统;其次,学校也要适应当地教育技术的普及程度、使用习惯和社会文化等差异,因地制宜地推进数字设施建设;最后,教学管理与决策的科学化来源于对教学发展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判断[16]。学校需要增强教学空间的“可测量性”,尽可能地将空间中的各要素数据化,方便人工智能的技术诊断与反馈。
(二)构建多元数字平台,全面革新教学空间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日常的教育判断和决策工作已经开始部分移交给自动化软件、系统和平台,从识别学生何时缺乏动力、评价学生的表现到规划未来的课程内容,甚至到“幕后”的学校制度自动化、学校资源分配。在数字空间下,教师的聘用、安置、专业发展与晋升过程也正在数字化。由此可见,从宏观的政策、管理、领导到课堂教学、成绩评估等方面都在逐步数字化,学校传统的管理模式正在颠覆。
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学校需要逐步建立起四个平台。一是利用社会教育信息化共建共享体系,建立共储共享的学校数字资源平台,方便学校管理者、教师与学生随时随地的查询与利用;二是建立学校主导的家校社合作的云端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学校持续发展、教师专业成长与学生终身发展进行长期智能监测,定期反思与调整;三是建立校园智能化教学平台,推进虚实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通过设计智能教学框架、创新数字教学工具、开发学习预测模型、加强在线学习平台、构建虚拟实验室等数字技术手段,丰富课程资源,拓展学习场域,监控学生的进度,分配自适应学习任务,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参与度;四是建立超越学校围墙的教研合作平台,激发教师的创新体验,让教师的教学智慧在数字实践不断生发。数字空间下的教研共同体是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学校突破校园围墙的束缚,为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教师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与机会;另一方面,当前的教育智能系统的研发仍处于初级阶段,旧系统的完善与升级、新智能系统的开发与设计都需要教研共同体的实践反思、经验总结与跨学科技术合作。
(三)优化教师系统培训,全程提升数字素养
教师是推动教育学校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在开发课程资源、开展教学活动方面都扮演着战略决策者的角色。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是应对教师时代角色转变,专业要求持续提升的基本策略,反映在教学活动中,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学生数字素养的生成,应对数字化所带来的能力抽离、脱离社会性等挑战。教师的数字化转型要从教师培训的数字化转型开始,学校组织并开展系统的教师培训是改变教学文化,实现数字迁移的决定性变量,能够帮助教师理解数字化转型的意义和行动方案,弥合教师在数字兴趣与数字能力方面的差距,提高教师的整体数字素养。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关键是将其视为协作与持续的实践,在数字化背景下,学校需要首先明确人工智能为培训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借助数字技术为教师量身定做长期培训方案,提供密切的后续支持等。
在应对数字技术对教育系统的冲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是帮助教师进入智能技术世界的框架,变革教师的教学思维与方法,尤其是具有长期传统教学经验的资深教师。以数字化技术“武装”教师,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是培训的重中之重。这种数字素养除了上述对“数字”的认知之外,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合理运用数字技术的意识和能力。教师的数字差距状态、对技术设备的熟悉程度都会影响着数字技术对学校教育的赋能效果。所以培训要提供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设备与平台的类型和运行原则,包括学习预测系统、概念映射工具、计算机辅助测试系统,在线监考系统等,让教师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自觉地、主动地将技术运用于教学变革实践中的意识,便于教师更准确地选择并运用各类智能系统和工具。与此同时,将资深教师的教学经验与智慧融入到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之中,使学习系统充当智能导师,实现人工智能与教师智慧的共生共长。培训的另一个要点是帮助教师掌握反思数字化环境中教与学的关系,运用ASSISTments、Auto Tutor等优秀的智能导学系统和微软人工智能Tay聊天机器人等工具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工具等的能力。
(四)健全管理保障机制,全速创建学习生态
“线上线下多维深度混合”的在线教育不仅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还承担了学习过程的拆解和重构,学习新生态本身早已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与学习环境等方面发生深刻改变[17]。为了引导学生应对能力抽离、去社会化等数字化困境,学校需要全方位地健全管理保障机制,加速重塑泛在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新生态。首先,教师对数字技术的感知主导着课堂教学实践,直接影响学习生态中学习方式与学习内容的重组。教师对数字教育的态度以及对通过数字技术部署来提高教学效果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他们在课程作业中实施数字变革的意愿和效果。因此,教师需要树立正确的数字化态度,认识到数字教育以学生发展作为学校教育变革的根本驱动力,数字技术本身不能提供成功的知识建构,而是为人提供高效建构的思维工具。例如,基于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情景感知、智能体验等可以有效增强个体技术和智能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学习者可以通过更丰富的个人环境以更开放、更紧密和更丰富的方式参与学习。对于教师来讲,数字化转型不只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更是一场参与的革命。教师需要适应课程教学的数字化趋势,减少挫败感与疲惫感,随时做好角色变化的准备,以“平等中的首席”身份引导学生在数字时代更好地开展学习活动。
其次,学校在建设智能校园中需要通过优化管理保障系统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管理者需要以批判的视角看待数字化,树立正确的数字思维,既需要积极适应数字技术变化,主动作为,又要规避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潜在误区和伦理风险。学生长时间使用网络设备会损害眼睛、耳朵等器官,过度的线上交流会大幅度降低线下的互动与交流,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不仅如此,技术驱动的学习环境会导致学生在搜索繁杂的信息中偏离原来的学习主题,浏览不合适的网站。不止如此,学校对学生的全方位监测,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暴露在开放空间中,剥夺学生的隐私。智能校园的建设必须约束学生和自我约束,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同时尊重学生的隐私。因此,学校需要开发智能系统,提供“学生模式”的学习资料库与绿色安全网络通道,合理规划线上线下教学活动时间。此外,学校还要尊重学生的隐私,确保教育数据的安全性,合理收集、存储和使用数据,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 余胜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路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3):62-67.
[2] 袁振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转什么,怎么转[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3):1-11.
[3] 焦建利.ChatGPT助推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时代学什么与怎么教[J].中国远程教育,2023,43(4):16-23.
[4] 王星.未来课堂如何发挥智能技术的教育价值: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J].中国电化教育,2023,(10):43-49+72.
[5] Fuchs,C.,Sandoval,M..Chapter 2: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M].New York:Routledge,2015.52.
[6] 孙烨超,马和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及其治理路径分析[J].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22,(1):60-76.
[7] [英]安东尼·塞尔登,[英]奥拉迪梅吉·阿比多耶.呂晓志译.第四次教育革命: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教育[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169.
[8] Bayne,S.,Jandri ,P.From anthropocentric humanism to critical posthumanism in digital education [J].Knowledge Cultures,2017,5(2):197-216.
[9] Williamson,B.Big data in education:the digital future of learning,policy and practice [M].New York:Sage,2017.
[10] Bayne,S.Teacherbot:interventions in automated teaching [J].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2015,20(4):455–467.
[11] 祝智庭,戴玲.综合智慧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J].开放教育研究,2023,29 (2):4-11.
[12] 周丰.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外化抑或能力抽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4-18(07).
[13] 何克抗.21世纪以来的新兴信息技术对教育深化改革的重大影响[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3):5-12.
[14] 宋慧玲,帅传敏等.生态学习观视角下虚拟学习社区用户满意度模型构建与验证[J].中国电化教育,2019,(12):68-77.
[15] 朱益明,王瑞德.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规划到实践[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238.
[16] 李铭,韩锡斌等.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的愿景、挑战与对策[J].中国电化教育,2022,(7):23-30.
[17] 翟小宁,吴绮迪.变革与创新:重塑学习新生态[J].中国教育学刊,2021,(12): 41-45.
作者简介:
傅敏:教授,博士,教育部西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教育研究方法论。
冉利敏: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原理。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Cognitive Misconceptions,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Solutions
Fu Min, Ran Limi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driving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 ecosystem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educating people. By clarify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in the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harmon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valu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we can find that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ssentially follows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and “valu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ssentially follows the data ethic of “depending on people and using it for people”.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chools are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the elimination of campus walls and the urgent need to rebuild school boundaries; the subversion of curriculum mod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eaching practi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rol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withdrawal of students competence and the continuous reshaping of the learning ecosystem. Schools need to improve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uild a diversified digital platform,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training of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in order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campus, comprehensively innovate the teaching spac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reshape the learning ecology at full speed.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cognitive misunderstanding; solution strategy; education ecology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8日
責任编辑:李雅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