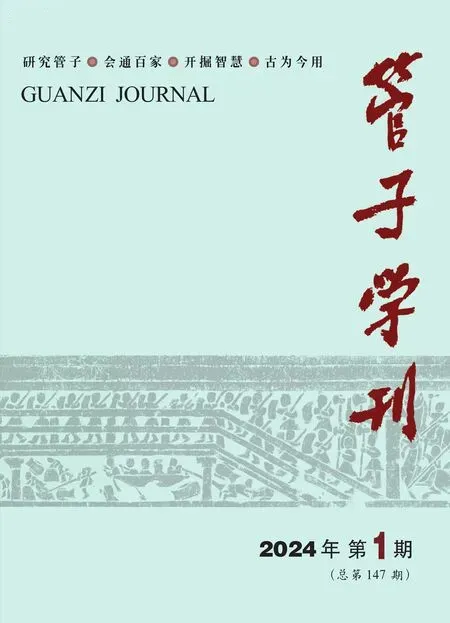“管仲之器小哉”辨正
孙永波
(山东大学 文学院语言科学实验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器量”“局量”说辨正
《论语·八佾》第22章有如下一句: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7页。
关于“器”的解读,历代学者做了不少工作。其主流观点是训“器”为“器量”“局量”,以何晏和朱熹为代表;还有学者训“器”为“器物”“器才(材)”“器用”。此外,不少学者并未具体训释“器”字含义,而是就此句整体义理进行诠释。下面,我们具体讨论一下此句的各种训诂观点,兼论相关问题。
先来看一下将“器”训为“器量”“局量”。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曹魏的何晏和宋代的朱熹。何晏在对“器小”的注释中说:“言其器量小也。”(2)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8页。朱熹《论语集注》说:“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7页。何晏的注释本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论语》古注通行本,也是“十三经注疏”中的古注底本;朱熹在经学史上地位很高,其《论语集注》一书对后世的影响不亚于何晏的古注。两位先贤是《论语》注释史上重要的代表性学者,其观点影响巨大,其作品至今仍是学习和研究《论语》绕不开的经典。何晏和朱熹将此处“器小”理解为“器量小”“局量褊浅”,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直到今天,安徽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简第二辑公布,在收录的《仲尼曰》一篇文献中,整理者引用《论语》此句解读简文时,其理解还是沿用何晏、朱熹的观点,将孔子评价管仲的话“老讫”破读为“小器”,认为含义等同于此处的“器小”,并训为“器量狭小”(4)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49-50页。。当然,安大简整理者的这种破读是有问题的,不足为信。我们曾撰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在《管子》一书中找到坚实的证据,反驳安大简整理者的破读,在此不再赘言(5)孙永波:《〈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集释》,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3年,第42页。。不过,由之可见,“器”训“器量”“局量”之说影响深远。
但这并不是说何晏、朱熹的此种观点正确。相反,我们认为此处训“器”为“器量”“局量”,实际上是没有文献依据的,不足为训。
无论在现存的传世先秦古籍中,还是在已经公布的先秦出土文献中,均暂未发现“器”字有明确的辞例训为“器量”或“局量”者。就《论语》一书而言,除此处外,尚有四章内容提到“器”字,分别为《为政》篇之“君子不器”,《公冶长》篇之“女,器也”,《子路》篇之“及其使人也,器之”,《卫灵公》篇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7、76、149、164页。。就文意及前儒的释读而言,此四处无一处作“器量”或“局量”讲者。不仅如此,直到《孟子》一书出现,其所见之“器”字凡7处,尚无一处作“器量”义讲者。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不再一一列出。总之,先秦时期,至少在孔子时代,“器”字是没有“器量”或“局量”这种词义用法的。
值得注意的是,“器量”一词却出现得很早,只不过这个较早出现的“器量”,其词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器量”“局量”等词的含义并不相同,当然也不可能和何晏、朱熹等人所说的词语含义相同。《周礼·天官·酒正》有“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一句,郑玄《周礼注》说:“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数量之多少未闻。”(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69页。很明显,这里的“器量”词义并非是表示人的心胸狭窄等抽象义的“器量小也”之“器量”,而是指器物的容量。具体来说,指的应该是酒器的容量。
当然,“器量”指酒器的具体容量,很容易让我们类比到人的心胸的容量,即人的“器量”“局量”。只不过,这种类比出现得很晚,至少在《周礼》成书的时代和孔子生活的时代,暂时还未发现明确的“器量”一词的抽象词义。即便是作为指具体的酒器之容量的“器量”一词,大概在先秦文献中,也只在《周礼》一书中仅存一例,其他现存先秦古籍暂未发现用例,遑论其作为抽象义的指人的心胸之“局量”?
“器量”一词在文献中明确用来表示抽象义的人的“器量”“局量”,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最早应该出现在东汉时期。《文选》著录东汉中晚期大文学家蔡邕所作《郭有道碑文(并序)》,即有“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广大”(8)萧统编:《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01页。一句。蔡邕是东汉的著名文人,其所使用的表示人的心胸等抽象义的“器量”一词,我们无法得知他的这种用法是继承自前人,还是其作为文学大师的伟大化用。毕竟从表示具体的酒器的容量,联想到指代人的心胸容量,对于一个文学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大概与蔡邕同时期或稍晚一些的刘焉所作《荐任安表》,亦有“揆其器量,国之元宝”(9)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14页。一句。除此之外,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我们不再一一列举。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器量”一词的抽象义,至少在东汉末年,就已经以某种固定的形式存在了。从与蔡邕同时期或稍晚一点的刘焉等人不止一次使用“器量”一词的抽象义来看,这种用法是蔡邕作为文学家首创的可能性不大。这样的用法或许当有更早的来源,只是限于目前所见的资料,我们只能追溯到蔡邕这里。
通过对现存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的掌握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器量”一词用以表示抽象义的人的“器量”“局量”,在东汉末年开始逐渐出现并增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翻检一下这一时期的史书和文人文集等现存文献资料。就会发现,这种形容人的心胸等的抽象义的“器量”用法大量出现,并成为当时朝廷及门阀士族评价士人品性高低的一种重要方式。何晏主要生活在曹魏时期,此时正是“器量”一词作为抽象义表示人的心胸的快速增长期,用今天的话来说,“器量”一词的这种抽象义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流行的“时髦语”“年度流行词”。何晏注释《论语》“器小”之“器”为“器量”,并将“器量”理解为人的心胸的容量这种抽象义,大概是受当时“流行语”的影响所致,而没有考虑到古今词义的变化,从而犯了“以今律古”的训诂错误。须知,在孔子及其前后数百年的时间内,就现存的这一时期的文献而言,“器”字从未有明确的用例可训为抽象的“器量”“局量”等义。
至于朱熹之训诂,应该是受到何晏《论语注》的影响。朱熹注解经书长于义理而疏于训诂,对“四书”的解读常见词义训诂不精确者。当然,在朱熹的时代,“器量”一词表示人的心胸的容量这种抽象义,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了。不仅如此,即使“器”字单出,也往往有用以指代“器量”者,这样的例子在现存的宋代文献中俯拾皆是,无须举例。有前儒何晏注解在前,又有当时“器”字词义的事实在后,种种原因导致朱熹对此字的误解。
以上我们具体讨论了“器”或“器量”在文献中的词义及其发展过程,从词语词义使用的时代方面,对何晏和朱熹误解此字做了具体分析。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文献中与“器量”相关的语词。
在文献中,经常会出现“气量”一词。“器量”与“气量”在古籍中并见,其词义也很接近,在某些情况下,均是指人的心胸气度。我们认为,二者或当具有通假关系。首先,从音理上来说,“器”字上古音属溪母质部,“气”字上古音属溪母物部,二字上古声母读音相同,韵部物、质旁转,读音接近,存在通假的声音条件。其次,从具体的古籍用例来看,现存文献中也存在二字通假的例证,比如《庄子·人间世》“器息”通作“气息”。虽然两个词语可以相互通假,古籍中当以“器量”为正体,“气量”当是“器量”的音近假借,只是后来二者经常混用,才逐渐变得区别不那么明显。
我们这样认为,是有文献上的依据的。一是如上所述,在现存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是“器量”一词,而非“气量”。“器量”一词词义由《周礼》中表示酒器的容量,进而演变为后世表示人的心胸容量,由具体到抽象,符合词语的引申演变规律。而“气量”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二是在现存传世古籍中,特别是六朝文献,“器量”一词呈井喷式出现,牢牢占据主导地位;而“气量”一词却很少出现,只是零星地出现在个别文献之中,如《华阳国志》“气量倜傥”(10)常璩:《华阳国志新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9页。、《全三国文·请叙郑小同表》“美其气量”(11)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169页。等。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器量”或“气量”表示人的心胸容量,当是由《周礼·天官·酒正》“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之“器量”词义引申转化而来,以具体的装酒的容器容量比喻抽象的人的心胸的容量,从而完成古汉语的词义引申,即由个别的具象义引申为普遍的抽象义。因此,东汉中晚期出现的表示人的心胸、气度等的“器量”词义,其来源与此处讨论的“管仲之器”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进一步认为,“器”和“器量”应该属于不同的词义系统,即使在东汉中晚期,“器”的词义对应的词义系统与“器量”一词对应的词义系统,也不会有过多的纠缠。也即,东汉中晚期以前,即使是用来表示人的心胸、气度等的词,一般用的也是“器量”,而不是“器”。“器”字大概到了很晚才有指代“器量”或“气量”的用法。
综上所述,何晏及朱熹注释《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之“器小”为“器量小”“局量褊浅”,从现存文献上来说,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孔子时期用词的词义习惯,因此我们不赞同这种注释。
二、其余诸说辨正
以上我们主要讨论了何晏和朱熹注解的问题所在及其产生的原因等相关问题,从而认为二位先贤大儒对“器”字的注解不可信。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其他几位《论语》研究者的代表性观点。
“管仲之器小哉”之“器”,训“器物”“器才(材)”“器用”,应该出现得比较早。西汉末年扬雄《法言》中说:“或曰:齐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请问大器。曰:大器其犹规矩准绳乎?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12)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第128页。扬雄以“小器”与“大器”对比,且以“齐得夷吾而霸”为讨论背景,其对“器”字虽没有明确的训诂,但我们一般不会将其理解为“器量”或“局量”,而往往理解为“器物”“器用”,以“大器物”比喻为有大用之人,以“小器物”比喻为用处不大之人。
历代各家注释此句,多有类似扬雄者,他们并未直接说明“器小”的具体训诂,仅仅是就整体句意进行阐述,且基本上是将“器”理解为“器物”“器用”“器才(材)”。我们再举两例进行说明。一是宋代张栻说:“管氏急于功利而不知道义之趋,大抵其器小也。”(13)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第129页。这里说的应该是管仲的器材不大,只知道急功近利而不知道取义。二是日本学者猪饲彦博认为:“大器谓其才能可大用也。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王制》曰:‘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皆谓才能为器。先儒以器小为器量小,恐非古义。”(14)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第129页。猪饲彦博明确提出“先儒以器小为器量小,恐非古义”,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训诂意见。
明确提出“器”字训为“器物”“器用”“器才(材)”等义的,为当代学者安德义先生和韩喜凯先生。安德义先生认为:“器,指器物。古时对人材有‘大器’、‘小器’之分,成大材者为‘大器’,只能作小材者为‘小器’。”(15)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第130页。韩喜凯先生认为:“这里的‘器’,便是器才、器用的意思。”(16)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第130页。安德义和韩喜凯二位先生的观点没有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其影响力远远不能和何晏、朱熹等人相比。从“器”字词义的文献用例来看,安德义和韩喜凯二人对此字的训诂要优于何晏、朱熹二人。“器”字训“器物”“器才(材)”“器用”,在先秦秦汉古籍中是常训。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种训诂存在的不足。
首先,如果将“器”理解为“器物”“器才(材)”“器用”,则“管仲之器小哉”意思是说“管仲是个器才(材)很小的人”。这样理解是有问题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孔子多次称赞管仲“如其仁”,认为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果没有管仲就没有整个华夏民族,即“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4页。。由此可见,孔子对管仲挽救华夏、存亡继绝的伟大功绩是十分肯定的。这足以说明,在孔子心中,管仲是成“大器”的,即管仲是有大用之人。如果“器”能够训为抽象义的“器量”的话,则孔子评价管仲器量小、心胸狭窄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器量大或者小是对个人心胸的评价,属于对人品的评价范畴。一个人的人品不好或者心胸狭隘,并不妨碍其成就伟大的历史功业。
实际上,在孔子看来,管仲确实是一个私德不佳的人。孔子曾这样评价管仲的私德:“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7页。管仲位高权重却不知节俭,不知礼节,这是管仲私德方面的问题所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器”在孔子时代是没有表示人的心胸的容量等抽象义的。因而,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大概没有器量小、心胸狭窄的意思。
与之相对应的是,评价管仲为“器才(材)小”“器用小”也讲不通,因为这是对其生平功绩的评价,就史料记载来看,管仲存亡继绝的功绩绝不可能是“器小”者所能为。同时,在已知的可以确定为孔子言论的文献中,大概没有出现孔子对管仲历史功绩做出过负面评价的记载。孔子对管仲的负面评价,或者说是孔子对管仲的不满,也仅仅局限于对管仲的私德和某些言论方面,例如上文列举的不知节俭、不知礼节,再比如下文将要谈到的管仲关于“成器”的言论。
二是从历史事实来看,管仲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内修政治,外交各国,使得齐国于齐桓公时期在各诸侯国中的威望达到新的高峰。不仅如此,管仲辅佐齐桓公期间,整个华夏各国依赖齐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号召力共同抵抗蛮夷异族,使得华夏种族不亡,华夏文化得以延续。甚至,管仲治国理政的经验被后世从政者及学者不断学习和总结,最终形成《管子》一书。因此,无论是从孔子对管仲所做历史功绩的积极评价来看,还是从现存关于管仲事迹的史实记载来看,管仲都不能说是一个“器才(材)很小”的人。将“器”字训为“器材”,从而解读为孔子认为管仲的器材很小,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因此这种训诂也不可信。
其次,《管子·小匡》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施伯谓鲁侯曰:‘勿予。……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19)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0页。施伯是与管仲同时期的人,当时管仲被鲁国拘押,鲁君想要放管仲回齐国,施伯劝诫鲁公不要放管仲回去,管仲“大器”正是施伯劝诫的理由之一。由此可见,管仲在同时代的人那里,已经被视为“大器”了,没有理由过了百年左右,孔子反而评价其为“小器”。
清代惠栋也注意到《管子·小匡》中的这则材料,认为:“盖当时有以管仲为大器者,故夫子辨之。”(20)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第129页。惠栋的这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从当时的语境来看,此章对话是孔子挑起的,他没有理由一开始就无缘无故地反驳古人之言,更没有理由反对别人对自己推崇的历史人物进行积极评价。当然,最主要的证据还是我们的上述讨论,即从现存的孔子评价管仲的言论以及历史事实来看,孔子评价管仲“器用小”或“器才(材)小”是没有道理的。《管子·小匡》中鲁国施伯评价管仲为“大器”,毫无疑问是指管仲其人有很大的器用,堪当大用之义。
最后,从孔子讲话的情景来看,“管仲之器小哉”如果理解为“管仲的器才(材)很小”,则与后面讨论管仲“俭乎”“知礼乎”逻辑上衔接不起来。此章开头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之器小哉。”接下来是“或曰”者问孔子“管仲俭乎”,孔子回答管仲不俭。“或曰”者又问孔子“管仲知礼乎”,孔子以反问语气回答管仲不知礼。可知,孔子开头对管仲的评价语,当是有感而发的感叹句。而其后“或曰”者的回答,并未围绕管仲的“器才(材)”“器用”等方面展开,而是问其是否俭,是否知礼,这就显得很突兀。由此我们大胆推测,孔子和“或曰”者的对话应当存在一个具体的对话环境(或者是对话的背景),而这个具体的对话环境或背景,并没有被此章内容的记录者记下来,导致人们对这句话的解读认识不清了。那么,如何想办法来还原孔子和“或曰”者的对话背景,就成为解读孔子此句话的关键所在。所幸今天大概找到了此章孔子和“或曰”者的对话背景,以这个背景为前提,我们能够较好地解读此句之“器”字。关于这个对话背景,我们下一小节将详细讨论。
由上,将“管仲之器小哉”之“器”训为“器物”“器才(材)”“器用”,无论是从孔子对管仲的态度上,还是从史料关于管仲事迹的记载上,抑或是从本章上下文的逻辑性方面考虑,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此外,一些注释者还提出了如下观点。日本学者物双松认为:“孔子与其仁而小其器,盖惜之也,亦自道也。”方骥龄先生认为:“疑本章‘哉’字为‘材’‘才’二字之通假。‘管仲之器小哉’殆为‘管仲之器肖材’传写之异。”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批评管仲不懂‘礼’,却称许管仲‘仁’。肯定大于否定,不仅可见‘仁’高于‘礼’,而且造福于民的功业大德高于某些行为细节和个人小德。这与宋明理学以来品评人物偏重个人私德的标准尺度很不一样。”杨润根认为:“器,《说文》:‘器,皿也,像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大学》:‘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可理解为:犬所关心的一切的一切,它们只是与口相关的盛装食物的器皿。可见犬所关心的一切是非常有限的……孔子说管仲小器,也就是说管仲所关心的只是那些非常有限的事物。”(21)此段各家观点,详见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第129-130页。
以上诸家所论,物双松和李泽厚先生没有采用训诂学的方法,故不在我们的论述范围之内。方骥龄先生的观点较为新颖,但无切实可靠之证据,不足为信。杨润根先生对“器”字的解读有问题,观点暂且存疑。
综上所述,无论是先贤大儒何晏、朱熹,还是之后各家学者,由于《论语·八佾》此章孔子和“或曰”者对话背景的缺失,各家的讨论均建立在对话背景缺失而不知对话所云的基础上进行解读,其结论自然经不起推敲。《论语》中这种对话背景缺失的章节很多,想要正确理解文意,找到缺失的对话背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三、“器”字正解
以上我们详细讨论了历代注释者对“器”字的不同解读意见,并指出各种解读意见的症结所在。同时,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推测,即《论语·八佾》此章当存在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话背景,由于《论语》文本对话背景的缺失,各家对此章的注释均很难完美解决各种问题。下面,我们结合出土文献,尽可能复原孔子和“或曰”者此章的对话背景,并对此句之“器”字及句意进行重新解读和思考,同时兼论相关问题。
2016年4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由上海中西书局正式发行,其中《管仲》一篇,记载了管仲和齐桓公之间的对话,内容与传世本《管子》不相对应,但其所蕴含的思想和简文语词,多与之相通。可见,此篇简文当是战国时期单篇流传的关于管仲言论的文章,或为现存通行本《管子》一书未收或散失之佚文。《管仲》篇简24-25中记载了管仲回答齐桓公的这样一句话,即“既年(佞)或(又)忎(仁),此胃(谓)成器”(22)引文句读及隶定从《管仲》篇整理者意见,详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13页。以下引用此句,均直接释读为“既佞又仁,此谓成器”。。此句简文对理解《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句,尤为重要。
我们认为,清华简《管仲》篇“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一句,是《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章的对话背景。下面,我们将结合这一对话背景,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清华简《管仲》篇“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一句,是管仲说的话。管仲认为,一个巧佞之人有了仁爱之心,才能够叫做“成器”,或者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叫做成“器”了。“成器”一词,在《管子》一书中凡两见,即《七法》篇之“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臧”,《形势解》篇之“奚仲之为车器也……成器坚固”(23)黎翔凤:《管子校注》,第117、1174页。。毫无疑问,二者指的是具体器物的成型,而不是比喻人的成才,这和简文词义所指有差别。不过,以器物成型类比人之成才,是很自然的事情,简文就存在这样抽象义的事实,本身能够证明这一点。
此外,《管子》一书中“巧佞”常常搭配使用,如《立政》篇之“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水地》篇之“巧佞而好利”(24)黎翔凤:《管子校注》,第80、831页。等。而管仲描述“成器”时,曾用“巧”字,即《形势解》篇之“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25)黎翔凤:《管子校注》,第1174页。。“佞”字的语词色彩,在先秦时代,尤其是在更早一些时候,大概只是个中性词,并非如后代那样只用作贬义词(26)“佞”字解读,参阅秦力:《释“佞”》,《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年第2期,第19-20页。。因而“佞”字往往和“巧”字搭配使用,表示一个人能说会道。一个人能说会道本来不是缺点,只不过能说会道的人往往为了某些目的而将这种能力变为阿谀奉承,于是“巧佞”就逐渐由一个中性词演化为贬义词。到了后世,“佞”字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而“巧”字则更多还保持褒义的成份。
从《管子·立政》之“谄谀饰过之说,则巧佞者用”来看,大概在《立政》篇撰写的时代,“巧佞”就成为贬义词了。简文《管仲》篇“既佞又仁”之“佞”,也不是什么好词,这从此句简文的上下文文意可以推知(27)详见本文第四小节简文引文及文意分析。。总而言之,《管子》一书以“心灵手巧”含义之“巧”字作为制作车器之“成器”的条件之一,抽象为以“能说会道”之“佞”字作为一个人“成器”的条件之一,是可以讲得通的。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心灵手巧”之“巧”,还是“能说会道”之“佞”,本质上说的都是一个人某些方面的“快”。
至于简文之“仁”是否为“成器”的条件之一,《管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玩味,即《枢言》篇之“既智且仁,是谓成人”(28)黎翔凤:《管子校注》,第246页。。在这里,《管子》定义了“成人”的概念,用的是“智”和“仁”,其下定义的语句格式与简文“既佞又仁,此谓成器”可谓一致。而且,《枢言》中的“成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长大成人之类的表面意思,而与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的哲学色彩浓厚的“成人”内涵具有很高的重合性,由此可见《管子》思想对孔子儒家学说的影响。这种内涵的“成人”,换种表述方式实际上就是“成器”。“仁”既然在《管子》书中是“成人”的条件之一,实际上也就是简文“成器”的条件之一。
由此而论,“巧”和“仁”在《管子》中是成“器”的条件,只不过二者论述的不在同一问题层面上,“巧”是器物层面上的,“仁”是道德层面上的。如果“巧”的这种具体的器物层面上的“成器”条件,进一步引申到抽象义层面上来,则“巧佞”就成为一个人“成器”的条件之一。这样,我们就在传世本《管子》中找到了一个人“成器”的两个条件,即“巧佞”和“仁”。于是,简文“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一句,就能在传世本《管子》中找到思想来源。这同时也说明,简文《管仲》篇和传世本《管子》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诸多瓜葛。传世本《管子》一书,至少其中的某些篇章,无疑是有很早的语料来源的,甚至认为某些篇章或某些语料是直接源自管仲本人,也未尝不可能,而不像后来某些学者认为的传世本《管子》一书成书很晚。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我们上述引用《管子·枢言》之“既智且仁,是谓成人”一句,与简文《管仲》篇之“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一句,句式严格对应,语词基本属于同义替换,唯一的区别在于“智”字和“佞”字的不同。“巧”和“佞”从词源学上来说,二者都表示人的某些方面的“快”。实际上,“智”字也蕴含这种“快”的词源义,即脑子反应快。如果抛开“巧”“佞”“智”语词的褒贬色彩,从词源学角度考虑,则三者均是从某一方面形容人的某一特征的“快”。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看简文《管仲》篇此句的上下文文意,亦可知简文此句和《管子》书中此句,说的是一回事。当然,《管子》书和《管仲》简由于有上下文文意的限制,“智”和“佞”当根据上下文文意随文释读,二者的不同当主要受限于前后文的行文逻辑。
从《管子》一书中找出如此众多与《管仲》篇此句相对照的语词,可以看出,简文中管仲对“成器”的定义“既佞又仁”,是很符合管仲思想言论和用词习惯的,而不是突兀的。
事实上,将“佞(巧)”和“仁”搭配起来进行使用,在管仲及其之前的时代,是比较流行的一种用法。《尚书·金縢》中有周公旦如下一句,即“予仁若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6页。。根据《金縢》上下文意,此处的“仁”“巧”是褒义词,而所谓的“巧”字,实际上词义就等同于“佞”字。只不过到了后来,“佞”和“仁”搭配使用的时候,其语词的感情色彩发生了变化,如在《论语》中孔子就曾将二者搭配使用,即《公冶长》篇之“不知其仁,焉用佞”(3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6页。。这至少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佞”和“仁”搭配使用在先秦时期是常见的,从《尚书》时代到孔子时代都曾出现。这样,简文中管仲将二者搭配使用也就不足为怪了。
要之,在清华简《管仲》篇中,管仲认为一个人成“器”的标准是既要“佞”又要“仁”。孔子作为后世饱学之士,阅读到或者听其他学者讨论到管仲的此句言论,是很有可能的。而且,从情理上来说,管仲作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得力助手,其伟大的政治功绩是后世欲从政者所追求的目标。孔子作为想要在政治上有一番成就的儒者,对于前贤管仲的言论应该是很熟悉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孔子应该阅读到了与清华简此句相类似的更早时期的相关文献,从而认为管仲对“器”或“成器”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孔子不赞同管仲对“器”的定义,因为孔子不认为“佞”是成器的条件之一,因而孔子评价管仲对于“器”的定义时说“小”(31)孔子为什么会认为管仲所说的“成器”或“器”是“小”的呢?这个问题我们在第四小节有专门讨论,此处不再展开。。如此,则《论语》此句当作“管仲之‘器’小哉”。“器”在此指的是管仲对于“器”或“成器”的定义,句意当为“管仲所说的‘成器’太狭隘了吧”。《论语》“管仲之‘器’小哉”之“器”,或当为清华简《管仲》“此谓‘成器’”之“成器”的省略。
实际上,我们上述推测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关于《管仲》篇“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一句,或为《论语》某些篇章的对话背景这一推测,已经有学者提出来了,我们的讨论也正是受此启发而展开的。清华简第六辑出版后,侯乃峰先生就在《孔子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观点即以清华简此句为定点,认为《论语·公冶长》“雍也仁而不佞”一章当是以清华简此句为背景,孔子和“或曰”者的对话是建立在他们都对清华简此句管仲言论有所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32)侯乃峰:《〈论语·公冶长〉篇“雍也仁而不佞”章发微》,《孔子研究》2016年第6期,第57-60页。。侯乃峰先生文章中的观点认为,“或曰”者评价“雍也仁而不佞”是说冉雍不成器,孔子听到别人评价自己的弟子不成器,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于是以重复反问的语气质问“或曰”者,说“焉用佞”。侯乃峰先生的意见与我们的观点相结合,可以对清华简此句为《论语》两处孔子与“或曰”者之间的对话背景形成一条较为理想的证据链。由此也可以证明侯乃峰先生文章中所说:“孔子与管仲、《论语》与《管子》中可以反映管仲思想的文献资料之关系,其间联系应该不少。”(33)侯乃峰:《〈论语·公冶长〉篇“雍也仁而不佞”章发微》,《孔子研究》2016年第6期,第60页。管仲是春秋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实干家,孔子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对管仲的政治功绩是肯定的,对于其流传的言论自然是熟知的。随着战国楚简的不断发现和公布,有关孔子或管仲事迹的资料也越来越多,这都将为研究管仲思想对孔子的影响以及管、孔关系提供不少新的材料。
《论语·八佾》篇“管仲之器小哉”一章,内容也是孔子与“或曰”者的对话,这与《论语·公冶长》“雍也仁而不佞”一章类似。“管仲之器小哉”一章的背景也是孔子和“或曰者”都曾知晓清华简管仲此语的相关文献记载,这句话在他们那里大概是常识性的看法。与“或曰”者在一起的时候,孔子有感而发,说“管仲所说的‘成器’也太狭隘了吧”。这句话是孔子对管仲定义“成器”持不同意见的感慨。“或曰”者听到孔子对前辈先贤的言论有所否定,心中可能会有疑问,但并没有对孔子的感慨进行正面回复,而是就孔子的话题展开追问,问“管仲节俭吗”“管仲知礼吗”。由此看来,此章内容当是记录孔子和“或曰”者关于管仲生活行为的问答,引起这个问答的是孔子对“或曰”者发出的感慨,而这个感慨的背景是二人所熟知的。
由此我们认为,侯乃峰先生的这篇文章结论可信,清华简管仲此句当是《论语·公冶长》“雍也仁而不佞”一章的对话背景。受此启发,我们进一步认为,清华简此句简文还应该是《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章的对话背景。
四、孔子论管仲“器小”之原因及其他
以上我们讨论了《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章之“器”的释读问题,并根据新材料清华简《管仲》篇的相关内容重新理解了此处“器”字的解读。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清华简《管仲》篇的相关记载,从管仲所言“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一句的对话背景着手,讨论一下孔子反对管仲对“成器”定义的原因。
根据清华简原整理者的释读意见,摘抄《管仲》篇“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一段相关的前后简文,内容如下:
桓公又问于管仲曰:“……其即君孰彰也?”
管仲答:“……及幽王之身,好使佞人而不信慎良。夫佞有利气,笃利而弗行。……”
桓公又问于管仲曰:“仲父,今夫佞者之利气亦可得而闻乎?”
管仲答:“既佞又仁,此谓成器。胥舍之邦,此以有国,天下有其机。夫佞者之事君,必前敬与巧,而后僭与,以大有求。受命虽约,出外必张,蠢动勤畏,假宠以放。既敝于货,崇乱毁常。既得其利,昏以行。然则或弛或张,或缓或急,田地圹虚,众利不及,是谓幽德。”(3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第112-113页。
通过上述一段简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是“佞者”是笃利而行的,可以为了利益不顾德行。简文说“夫佞有利气,笃利而弗行”,整理者解读“行”为“奉”,则此句理解为“笃利而弗奉”。我们认为,清华简整理者的这种解读是有问题的。下文有“既得其利,昏以行”一句,此处若作“弗行”,则与下文“以行”一句,显然前后矛盾。基于此,我们认为,此处“弗行”之“弗”当破读为“拂”,训为“违戾”。“笃利而拂行”,意即追求利益而违戾德行,也就是下文所说的“既得其利,昏禄以行”。这一段简文,详细描述了“佞者”追求利益而不顾德行的各种形态,包括事君时前后不一的态度,出使时“假宠以放”的态度,以及为了财货毁坏常法等方面。
二是“佞者”虽笃利而行,但也不是绝对毫无底线。“然则”一词表转折,以下简文介绍了“佞者”的可取之处,即“或弛或张,或缓或急,田地圹虚,众利不及,是谓幽德”。意思是说,佞者张弛有道,缓急有度,田地圹虚中的众多利益,佞者是不会去获取的,这就是佞者的“幽德”。这应该也是管仲前面大力否定“佞者”,却以“佞”作为“成器”条件之一的一大原因。
三是“佞者”如果在“佞”的基础上有了“仁”,就可以称为“成器”了。这种“既佞又仁”的所谓“成器”,可以使“胥舍之邦”保有国家。在管仲看来,“佞者”笃利而行,但是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如果佞者同时也是仁者,那么他就是一位能够保有国家的“成器”之人了。管仲在此并未完全否定“佞”的作用,同时强调了“仁”在“佞者”那里的重要意义。“既佞又仁”,即已经是佞者了,如果又有仁爱之心,那么他的“佞者”之“利气”就会化为对国家和百姓的仁爱之心,其追求利益的本性也会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变得高尚起来。
由以上简文引文及我们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仲作为春秋早期一位具有伟大政治功绩的政治家和实干家,追求“利益”是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结合传世文献《管子》一书所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5)黎翔凤:《管子校注》,第2页。等,可以看出管仲是不讳言“利”的,而且是想方设法地积极求利。
管仲这种积极求利的思想,与孔子思想有所不同。相比管仲这种实干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孔子更多地是追求符合道义的“利”,如《宪问》篇之“见利思义”(3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2页。。《论语》一书中,孔子多次讨论到“利”,如《里仁》篇之“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2、73页。等,多是对“利”的否定。孔子认为,“利”应该建立在符合道义的基础上;不符合道义的“利”,即使再多,也不能去取,如《述而》篇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7页。。同时,《论语》一书中孔子多次谈到对“佞”的意见,也多持否定态度,如《先进》篇之“是故恶夫佞者”,《卫灵公》篇之“放郑声,远佞人”,《季氏》篇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3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0、165、172-173页。等。
由此可知,孔子对管仲“既佞又仁,此谓成器”这样的定义不满,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无论是“佞”还是“利”,都是被孔子定义在否定层面上的概念。而且,管仲以“佞”和“仁”并列而言,这恐怕也不是孔子所能赞同的。如前所引,《公冶长》“不知其仁,焉用佞?”一句,明确表达了孔子对“佞”“仁”并提的不满。
根据简文幽王“好使佞人”“佞有利气,笃利而拂行”等记载,可以看出“佞”字似乎并不是什么好词;但根据后文“然则”这个转折词,可知管仲对于本该是批评对象的“佞者”,也存在褒扬的一面。即在管仲那里,被定义为“佞”的这种人,虽然有其固有的缺点,但某些时候又能够展现出其特有的优点。因此,拥有“佞”这种特点的人,加以“仁爱之心”,即加以“仁”就会“成器”,成为一个有大用的“器才”。根据简文中管仲的描述,“佞”这种人的缺点主要是阿谀奉承,即以“佞”的“口才”进行“拍马屁”。这是孔子深恶痛绝的。孔子最为讨厌说话喋喋不休却不付诸行动的人,这在新出的安大简第二册《仲尼曰》中有所体现,此篇记载了二十余条孔子语录,其中大部分与孔子谈论“言语”有关。我们简单摘取几条列举如下(释文根据整理者意见):
仲尼曰:“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
仲尼曰:“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
仲尼曰:“伊言咠,而禹言丝,以治天下,未闻多言而仁者。”
仲尼曰:“务言而惰行,虽言不听;务行伐功,虽劳不闻。”(40)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3-44页。
由此可见,孔子对“多言”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管仲所说的“阿谀奉承”之“佞”,当然不会认可,即使这种“佞”有其固有的优点。
由于从思想层面看,孔子对管仲“既佞又仁,此谓成器”这种定义持否定态度,因而,把《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之“器”理解为管仲“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之“成器”,是站得住脚的。
此外,结合上述侯乃峰先生文章所讨论的内容,我们还可以探究一些关于孔子反对管仲“成器”之定义的原因。如上所述,侯乃峰先生的文章指出,孔子听到别人评价自己的弟子“仁而不佞”,认为别人在说自己的弟子不成器,于是回驳对方。这就说明,孔子对管仲“既佞又仁,此谓成器”这个观点是持反对态度的。在这一意义上,孔子评价“管仲之‘器’小哉”的对话背景和感情基础就有了。
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明确指出,“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4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6页。可见在孔子眼中,“佞”并不是什么好事。同时也可以推知,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能不能做到“仁”虽然没有把握,但即使做不到“仁”,也不要做“佞”。孔子评价管仲之“器”小的原因,一方面是理论上不认同管仲将“佞”作为“成器”的标准,另一方面是现实中不允许别人拿管仲的这句言论否定自己的爱徒。
从管仲谈论“既佞又仁,此谓成器”,到孔子对其观点的评价“管仲之‘器’小哉”,再到《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和“或曰”者对话中并未出现“器”或“成器”这样的字眼,而孔子通过“或曰”者的语言自然联想到其用管仲的言论暗指自己的学生冉雍不成器,可以看出,早在春秋时期,评价一个人是否“器”或“成器”,已经很流行了。这一时期或晚至战国秦汉时期,古籍中还有不少“器”字的含义与评价人有关,《论语》中就存在不少,例如《为政》“君子不器”,《公冶长》“女,器也”等。除了《论语》外,其他先秦秦汉古籍也有不少,如《庄子·胠箧》“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42)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85页。,《大戴礼记·四代》“君何为不观器视才”(43)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第385页。等。这些都是以“器”的具体物质形态来比喻人之才能,才能大者是为“大器”,才能不足者是为“小器”。不过,它们与管仲谈论“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中“器”的用法稍有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清华简第六辑《管仲》篇简24-25之“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一句,当是《论语·八佾》篇“管仲之器小哉”一章的对话背景和前提。孔子和“或曰”者在此对话产生之前,应当均对记载管仲此语的相关文献十分熟悉。管仲对“成器”之定义,在孔子和“或曰”者那里,应该是常识性的知识。基于此,“管仲之器小哉”当读为“管仲之‘器’小哉”,理解为“管仲所说的‘成器’太狭隘了吧”。管仲和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身份的差别,使得他们的思想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对“佞”者的态度不同,是孔子反对管仲关于“成器”定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