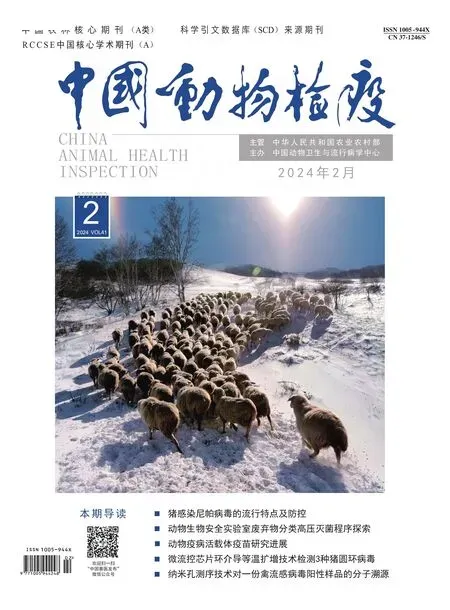越南非洲猪瘟疫苗AVAC ASF LIVE(ASFV-G-ΔMGF)研究工作分析与思考
戈胜强,沙 洲,左媛媛,初薛霏,徐天刚,张永强,李金明,王志亮
(1.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266032;2. 青岛市现代生物工程及动物疫病研究重点实验室,山东青岛 266032;3. 农业农村部动物生物安全风险预警及防控重点实验室(南方),山东青岛 266032;4.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泰安 271018)
2023 年7 月,越南正式将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 弱毒疫苗NAVET-ASFVAC(ASFV-G-ΔI177L) 和AVAC ASF LIVE(ASFVG-ΔMGF)推向其全国市场,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在一个国家全面实施ASF 疫苗防控措施。上述两种疫苗均为引进的美国基因II 型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弱毒疫苗株,其中ASFV-G-ΔI177L为2020年研制的疫苗候选株,ASFV-G-ΔMGF 为2015 年研制的疫苗候选株。据越南媒体报道,NAVET-ASFVAC(ASFV-G-ΔI177L)在临床试验期间出现过接种猪发病死亡事件,但AVAC ASF LIVE(ASFV-G-ΔMGF)未有任何负面信息报道。相比ASFV-G-ΔI177L,ASFV-G-ΔMGF的系统研究资料相对较少,但是国内弱毒疫苗候选株HLJ/18-7GD[1]和CN2018 ΔMGF/ΔCD2v(数据未发表)中多基因家族(MGF)的敲除区域与其缺失位置相似,也可以为其提供一定研究补充资料。为此本文就越南ASFV-G-ΔMGF 疫苗种毒的核心研究数据及国内相关数据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相关研究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ASFV-G-ΔMGF 基因缺失株首次评价数据
2015 年,O'Donnell 等[2]根据以往自然缺失株(OURT 88/3 和E75)、细胞传代适应株(BA71V和ASFV-G-P110) 和基因缺失株(Pr4Δ35 和MALΔSVD)的研究总结,判断多基因(MGF)家族中的MGF360 和MGF505 蛋白编码基因可能与病毒的毒力和复制相关,因此将基因II 型强毒株ASFV-G 基因组的27 928~35 487 bp 位置进行了人工敲除(长度7 558 bp,涉及MGF505-1R、MGF360-12L、MGF360-13L、MGF-14L、MGF505-2R 和MGF505-3R 等6 个蛋白编码基因),结果发现ASFV-G-ΔMGF 毒力减弱且能诱导产生攻毒保护能力。这是第一次明确证明MGF蛋白为ASFV 的毒力决定因子,这也是第一个可对ASFV-G 产生攻毒保护的试验性疫苗。
ASFV-G-ΔMGF 在细胞上的繁殖能力与其母本强毒株相似,不同剂量接种(102、104HAD50,肌肉注射,每组10 只)后,28 d 观察期内无任何临床异常表现。ASFV-G-ΔMGF 接种后会在血液中检测到病毒,且病毒滴度与接种剂量呈一定正相关,但不同接种猪存在一定差异。102H A D50接种组的病毒血症检测结果显示:3 头接近临界值(101.8HAD50/mL),6 头为中等滴度(1 02~4H A D50/m L),1 头滴度较高(105HAD50/mL),但在攻毒前所有血样中均已检测不到病毒。104HAD50接种组的病毒血症滴度普遍高于1 02HAD50接种组,其中4 头高于1 04HAD50/mL,6 头最大滴度区间为103~104HAD50/mL。攻毒前,6 头已转为阴性,但仍有4 头滴度为102~103HAD50/mL。
免疫猪攻毒(ASFV-G,103HAD50,肌肉注射)后,21 d 观察期内,所有猪只均存活。但体温监测结果显示,102HAD50接种组有3 头,104HAD50接种组有4 头体温一过性升高。攻毒后第4 天或第7 天的病毒血症监测显示,102HAD50接种组中,3头检测为阴性,6 头滴度区间为102~103HAD50/mL,1 头为104.55HAD50/mL。利用建立的疫苗株和攻毒株鉴别PCR 方法检测,结果3 头同时检出疫苗株和攻毒株,5 头检测出疫苗株。104HAD50接种组中,3头检测为阴性,4 头滴度区间为102~104HAD50/mL,3 头滴度区间为104~107HAD50/mL(最高为106.12HAD50/mL)。鉴别PCR 检测结果显示,4 头同时检出疫苗株和攻毒株,剩余6 头均检测出疫苗株。以上数据说明,虽然ASFV-G-ΔMGF 免疫后可以保护猪只抵御强毒株攻击,但在30%~40%的猪体中仍能检测到强毒株感染,此外在出现一过性体温升高的接种猪中大多数(6/7)能检测到强毒株核酸。以上试验数据说明,使用ASFV-G-ΔMGF作为减毒活疫苗仍存在一定安全风险,需要进一步评估其接种动物导致慢性病发展的长期影响。2020 年Chen 等[1]对构建的多种ASFV 基因缺失株HLJ/18-6GD(删除编码MGF505-1R、MGF505-2R、MGF505-3R、MGF360-12L、MGF360-13L 和MGF360-14L 蛋白的基因)进行了安全性评价。虽然HLJ/18-6GD 与ASFV-G-ΔMGF 两个毒株使用的母本种毒不同,后者构建使用的种毒是格鲁吉亚分离株(ASFV-G),前者构建使用的种毒是黑龙江2018 年分离株(HLJ/18),但这两个种毒均为基因II 型强毒株,序列高度相似。因此,HLJ/18-6GD 的相关研究数据可以为ASFV-G-ΔMGF 提供一定参考(表1)。HLJ/18-6GD 接种猪后(103和105TCID50,肌肉注射),21 d 观察期内无体温及临床异常表现,表明其具备良好安全性。攻毒后HLJ/18-6GD 接种猪观察期内均存活,但其心、肺、脾、扁桃体、胸腺和5 个淋巴结(肠淋巴结、腹股沟淋巴结、颌下淋巴结、支气管淋巴结和胃肝淋巴结)可检测出不同拷贝数病毒,表明该缺失株具备一定功效。

表1 ASFV-G-ΔMGF 和HLJ/18-6GD 疫苗株首次评价相关数据资料

表2 ASFV-G-ΔMG 和HLJ/18-6GD 疫苗株毒力返强试验相关数据资料
2 二次接种及传代细胞培养株验证
为进一步评价ASFV-G-ΔMGF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受硕腾公司(Zoetis)委托和资助,德国弗里德里希·勒夫勒研究院(Friedrich-Loeffler-Institut,FLI)开展了对该毒株的相关评价[3-4]。此次试验共设置了2 组研究,分别使用了2 种细胞扩繁种毒,A 组使用的是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B组使用的是一种商品化传代细胞系(背景不详,由硕腾公司提供)。A 组和B 组均进行了2 次肌肉注射接种(间隔3 周),每组5 头猪,A 组接种剂量为104HAD50,B 组为103HAD50。两组猪接种后均表现正常,只有1 头猪(B 组)在第12 天时体温升至40.5 ℃但很快恢复。病毒血症监测结果显示:A 组接种后有2 头猪出现病毒血症,基因拷贝数分别为2.8×100copies/5 μL(第7 天)和2.0×102copies/5 μL(第21 天);B 组接种后有2 头猪出现低拷贝病毒血症,基因拷贝数分别为3.5×100copies/5 μL(第7 天)和1.0×100copies/5 μL(第14 天)。
2 次免疫后(第42 天),两组均使用基因II型Armenia 2008 强毒株进行口鼻腔攻毒(鼻腔接种0.5 mL,口腔接种1.0 mL)。后经重新滴度评估,A 组接种滴度约为104HAD50,B 组约为105HAD50。两组攻毒后,在28 d 观察期内均没有任何体温和临床异常表现。排毒/带毒检测结果显示,A 组拭子全部为阴性,但有2 头猪出现病毒血症,基因拷贝数分别为2.0×10-1copies/5 μL(攻毒后第4 天)和3.7×10-1/3.2×10-2copies/5 μL(攻毒后第10/14 天),最终只有1 头猪的剖解组织样本检测为阳性,分别为肺脏(1.1×100copies/5 μL)和腘淋巴结(8.7×101copies/5 μL)。相反,B 组所有拭子、血样和组织样本全部为阴性。病理观察结果显示:A 组中除有1 头猪存在轻度肺实变,肾脏与胃肝淋巴结变暗变红外,其余猪只没有任何病理形态学异常;B 组中除有3 头猪的气管、支气管、肾脏和胃肝淋巴结变暗变红外,其余脏器和猪只没有任何表观异常。以上数据说明:2 次免疫后攻毒,90%的猪(9/10)在试验结束时已无法从组织和血液中检测到疫苗株和攻毒株;使用商品化传代细胞系繁殖的种毒(B 组)与使用外周血单核细胞繁殖的种毒(A 组)在动物试验评价中差异不显著。比较之前单次接种的动物试验数据[2],2 次免疫接种可以进一步减少病毒血症,效果更好。
3 野猪口服接种评价
为评价ASFV-G-ΔMGF 作为野猪口服疫苗的可能性,硕腾公司联合德国FLI 进行了野猪口服接种的免疫攻毒评价。研究[3]发现:8 头6 月龄野猪口腔接种ASFV-G-ΔMGF(105HAD50)后,28 d 观察期内无任何临床异常表现;病毒血症监测结果显示,在第21 天有3 头猪检测为阳性,基因拷贝数分别为9.7×101、3.3×101和1.2×100copies/5 μL。
疫苗接种后第28 天,使用基因II 型Germany 2020 强毒株进行口鼻接种攻毒(鼻腔接种0.5 mL,口腔接种1.0 mL,104HAD50),结果有2 头猪自第5 天时出现食欲减退和活动减少,并最终分别在第8 天和第9 天死亡。另有3 头猪虽然在第5 天和第9 天出现了轻微的食欲和活动减少,但最终都恢复正常。排毒/带毒检测结果显示,攻毒后第21天有3 头猪的血液样品检测为阳性,2 头死亡猪的所有脏器检测均为强阳性(高达105gc),3 头猪的个别组织/淋巴结检测为弱阳性(小于10 gc),3 头猪的组织样品检测为阴性。病理观察结果显示,2 头死亡猪病变较重,出现浆液性腹膜炎和胸腔积液,脾脏肿大,肾脏、各种淋巴结和胃肠道轻度至重度出血等。剩下的6 头猪表现非常轻微的病变,包括肝、胃和肾淋巴结变红,其中3 头猪的脾脏表现轻度至中度肿大、易碎等。该试验发现,口服免疫接种后并非所有猪都能产生抗体(第21 天转阳率为50%),较明显的趋势是但凡产生抗体的猪都能产生攻毒保护能力。有趣的是,有2 头抗体阴性猪也最终抵御了强毒株攻击,其原因可能是,猪只之间的个体差异,Germany 2020 或有一定毒力减弱,或免疫接种诱导产生了一定保护等。
综上所述,1 次单剂量口服接种至少可以使50%的野猪产生攻毒保护能力,但不可否认,可能由于病毒摄入的差异,口鼻接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动物的行为、唾液中的蛋白酶水平以及黏膜的易感性等都可能存在差异,进而导致整个试验系统/数据出现偏差。
4 毒力返强评价
根据兽医产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合作准则中关于毒力返强的试验要求(欧盟文件EMA/CVMP/VICH/1052/2004)[6],德国FLI 开展了该毒株的毒力返强相关评价[5]。该试验将疫苗种毒在猪体内连续传5 代(每组10 头猪,肌肉注射)。第1 代接种剂量为1.75×106HAD50/mL,接种后第7 天(据之前试验数据,此时的病毒含量最高[3])测定血液和组织中的病毒含量,将最高滴度的组织悬浮液接种第2 代,后面以此类推。经计算,第1 代至第4代制备的组织悬浮液(等同于第2 代至第5 代的病毒接种液)的滴度分别为104.25、102.25、104.00和105.75HAD50/mL。临床观察数据显示:第1 代接种猪无发热及临床异常;第2 代接种猪有3 头猪出现了一过性体温升高,体温最高为40.4 ℃;从第3代开始,有接种猪出现最高42.1 ℃的高烧(接种后第5 天和第6 天);第5 代时,10 头接种猪中有9 头出现过41 ℃的体温(部分持续超过1 d),伴随着体温升高,部分猪只还出现了轻度至中度的食欲和精神不振等。虽然有体温升高,但最终所有猪只均恢复正常。在第5 代的21 d 观察期结束时,所有猪只在临床上是健康的,但其中1 头猪(21 号)在接种后立即出现了右前腿感觉和运动功能完全丧失。经地塞米松治疗无效后,出于伦理考虑,该猪只在第7 天时被实施安乐死。病理检测结果显示,第1 代到第5 代的猪均能检测到极少的病变,即淋巴结轻微肿大和肺实变等,但将病变与传代次数进行分析时,未发现相关性及差异。以上数据说明,随着传代次数增加,病毒似乎有毒力变强迹象,但并不十分明显。
每一代接种猪第7 天剖杀的组织样品(脾脏、扁桃体、肺脏、淋巴结和血液等)病毒载量检测结果显示:第1 代接种猪的组织病毒拷贝数均小于7.2×101copies/5 μL,其中还有2 头猪未检测到病毒核酸;第2 代接种猪的组织病毒拷贝数均小于7.2×101copies/5 μL,其中还有5 头猪未检测到病毒核酸;从第3 代开始,每头猪的组织样品中至少有1 份检测为阳性,最高拷贝数可达1.8×103copies/5 μL;到第4 代时,所有样品均检测为阳性,最大拷贝数为2.6×103copies/5 μL;最后在第5 代时,所有样品均检测为阳性,血液滴度与第4 代相似,但组织中的拷贝数略低于第4 代(第21 天剖解),其中在第7 天被实施安乐死的21 号猪拷贝数最大,达2.6×103copies/5 μL。以上数据说明,随着传代次数增加,病毒感染程度有变强迹象,但这也可能是由接种剂量增大导致的。
对各代次代表样品进行病毒全基因测序,结果在第4 代的2 个样品中发现了1 个基因组5'末端出现大范围基因缺失的变异株(命名为ΔMGFnV)。ΔMGFnV 除缺失11 197 bp(涉及18 个基因)外,还在基因组3' 端出现了1 个18 592 bp 的重复序列。该重复序列以反向互补方向与5'端结合,导致29 个基因重复。随后进一步对所有样品进行复检,结果发现该变异株在第1 代接种猪(1081 号)中就已出现,该变异株与原始种毒混合存在;第2 代接种猪中,有2 头猪感染ΔMGFnV,其中1 头是混合感染;第3 代和第4 代所有接种猪均感染ΔMGFnV,且每代次均有9 头猪是混合感染;至第5 代时,4 头猪单一感染ΔMGFnV,6 头猪同时感染ΔMGFnV 和原始种毒。以上数据说明,ΔMGFnV 在出现变异后的混合连续传代过程中,感染比例逐步增加,呈现出更强的复制能力。虽然第5 代接种猪中,单独感染ΔMGFnV 的猪和混合感染的猪没有临床差异,但第5 代接种猪体温普遍上升等情况的出现可能与ΔMGFnV 有关。Chen 等[1]的毒力返强试验显示:对6 头猪接种HLJ/18-6GD(107TCID50,肌肉注射)第1 代后,体温正常,但有4 头猪血液带毒(滴度最高为6.1 log10),1 头猪脾脏带毒;第2~6 代均使用上一接种代次的带毒血液进行接种(第2~5 代接种3 头猪,第6 代接种5 头猪),结果自第2 代开始,血液和组织的带毒比例和滴度逐渐升高,第5 和第6 代时,绝大多数评价组织(心脏、肝脏、脾脏肾脏、扁桃体和胸腺等)和淋巴结(肠、腹股沟、颌下、支气管和胃肝淋巴结)均已带毒,病毒血症滴度最高达9.4 log10,且最终每组均有1 头猪死亡。以上数据说明,HLJ/18-6GD 有毒力返强风险。
5 小结
AVAC ASF LIVE(ASFV-G-ΔMGF)使用的细胞系为DMAC(Diep's Macrophage cell)。该细胞系是一种永生化的传代细胞系(具体背景不详)。AVAC ASF LIVE 在越南的成功上市,首次将ASFV 传代细胞系适应株应用于临床研究,这对于ASF 疫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相比原代细胞培养的疫苗候选株(如ASFV-G-ΔI177L、HLJ/18-7GD、CN2018 ΔMGF/ΔCD2v 和CN2018-LVR等),传代细胞培养的疫苗候选株批次之间差异可能更小,细胞质控可能更便捷,这使得AVAC ASF LIVE(ASFV-G-ΔMGF)具有更可靠的生产优势。但结合现有的种毒试验数据(原代细胞培养、传代细胞培养、相似种毒且缺失基因相似)分析,ASFV-G-ΔMGF 似乎优势并不明显,特别是ASFVG-ΔMGF 接种后未能清除强毒株感染,且毒力返强数据并不理想。国内研究证明,与ASFV-G-ΔMGF类似的HLJ/18-7GD(分别删除编码MGF505-1R、MGF505-2R、MGF505-3R、MGF360-12L、MGF360-13L、MGF360-14L 和CD2v 蛋白的基因)对妊娠母猪具备良好的安全性[1]。但与ASFV-GΔI177L相似,ASFV-G-ΔMGF仍缺乏很多研究数据,如是否能发生垂直传播、基因重组,以及基因I 型的交叉保护能力等。这使得大规模应用后不确定性事件仍有可能发生,因此仍需进行严密监测评估,不断优化毒株工艺(如2 次免疫等),以最大化发挥弱毒疫苗的功效。